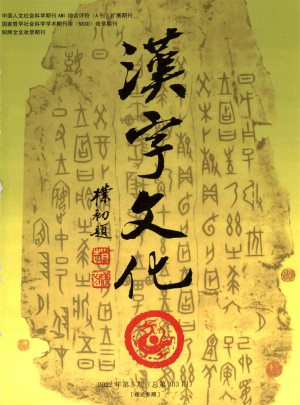引論:我們為您整理了13篇漢字文化論文范文,供您借鑒以豐富您的創作。它們是您寫作時的寶貴資源,期望它們能夠激發您的創作靈感,讓您的文章更具深度。

篇1
2.1、字形組字的表現手法特點是以漢字本身為主要設計元素來進行創意的改變和表達
縱觀現代標志字體設計可看出,以書法體的古樸暢快、宋體的娟秀、黑體的嚴謹肅穆,以及現代化的印刷字體等為元素來進行裝飾而成的設計法則居多。如“生命人壽”的標志,它以印章外形,篆文內容來構形表意,乍見可看出生命兩個字,但仔細看則會發現生命兩個字其實合成了一個“壽”字,代指人壽保險,把生命和人壽兩個含義巧合結合,印章的嚴謹既體現出濃厚的中國韻味又道出了人壽保險的可靠性。
2.2、圖文結合性表現形式。
是以漢字與圖形相結合來表達標志的內涵的形式。漢字作為典型的圖文一體的表象符號,它除了自身的直觀特性之外還有悠遠的內在意蘊。如為國人最為驕傲和喝彩至今的2008年北京奧運會會徽:“中國印•舞動的北京”。這個標志設計準確地把中國特點、北京特點與奧林匹克運動元素的三大主要內容巧妙融合又精煉統一,沒有冗雜的多余附帶,就以帶中國濃郁文化味道的古樸印章為背景框圍,將印章傳統氣質和書法神韻的藝術特點與運動表意特征對接,又經過藝術手法夸張的變形將之幻化成一個形似現代“京”字的、向前奔跑的、舞動著并迎接勝利的運動人形,可謂中國文化意蘊的濃郁與現代設計的靈動生機兼備。二是以印章紅直接作為主體圖案基準顏色,直觀簡練傳達和烘托出中國文化吉祥,喜慶,并帶有代表奧運會以“熱情會友”的氣氛。
篇2
漢字產生之前“上古結繩而治”,自然是沒有規范的。后世從圖畫和契刻受到啟示,文字“是勞動人民在勞動生活中,從無到有,從小到多,從多頭嘗試到約定俗成,所逐步孕育、選練、發展出來的”。“約定俗成”便形成了初步的體系,也就是早期不成文的規范。
漢字規范是客觀存在的,不同時代有不同的規范。舊中國長期以繁體字為正體,那么,以繁體字為代表的正體字也就成了當時的規范字。雖然當時以繁體字作為規范,但是,人民群眾長期以來在社會實踐中創造的手頭字、俗字已經開始流行。這便是對漢字的豐富和發展。
兩表的調整表明我國語言文字規范的一個立場:“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的規范化、標準化是一個不斷進行不斷完善的過程,不可能一毗而就,也沒有終止的時候,需要從語言文字的自身發展規律和我國的國情出發,因勢利導,循序漸進,使原則性與靈活性統一起來,使語言文字規范化、標準化的過程成為積極引導規范而又不斷豐富發展的過程”。
從這一立場出發,我們研究了目前作為字形規范的《現代漢語通用字表》,認為此表還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現在把我們的意見提出來。
1.1筆形的變化規律不夠統一
①末筆是橫的部件作左偏旁的橫變成提,“車”和“牛”作左偏旁時改變筆順把橫變成了提,按照這種變化規律,“革”字作左偏旁時也應改變筆順把橫變成提。另外“黑”字作左偏旁時末筆不是橫,四點上面部件的橫不應該就提。
②末筆是豎的部件用作左偏旁時,豎變成撇,如:翔、邦、等,按照這種變化規律,韓、鄲、韌等字也可以變,特別是“”變“艷”字,左邊部件與“邦”相同,理應變撇。
③“月”字用作下部件時撇變成豎,如:肖、胃、能、俞等,但在筋、崩、葫、萌、旅等字中卻沒變。
④“木”字做底時,如果上部是撇捺對稱且覆蓋“木”字的部件,要把捺變成點,如:條、茶等。如果上部不與撇捺對稱的部件為鄰,則不必改變捺的筆形,如:桌、梁、棠等。可是“雜、親、殺”三個字本屬后種情況,卻按前者的規律把捺變成了點。考查這三個字的來歷,原來它們在繁體字時代只是該字的左邊部件,簡化時把右邊簡掉,卻沒有把作為整字時“木”字該有的捺恢復過來。與此相反本應根據避重捺的原則把其中的“米”字的捺變成點,然而《現代漢語通用字表》中的“乘”字卻設計為兩個捺。
1.2筆順的規則也不夠統一
漢字的筆順基本上是按人體臂、腕、指的運動生理特點和視覺審美要求約定俗成的,這叫作自然筆順;規范筆順是在自然筆順的基礎上加以整理而制訂出來的。規范的筆順主要有從上到下、從左到右、先橫后豎、先撇后捺、從外到內和先外后內再封口等幾條,除此之處,還有一些特殊情況,但一般都應該符合人的臂、腕、指的運動生理特性。
漢字的歷史太久遠,形成的因素太復雜,要想通過幾條規律把它們統一起來,簡直是辦不到的。不過,作為漢字的規范標準,是文字繼續豐富和發展的基礎,這個基礎越有規律、越容易掌握,推廣起來就越有效率。我們應該從“有利于維護國家和民族尊嚴,有利于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有利于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的總原則出發,盡可能地使漢字難認、難寫、難記的現狀得到改善,使漢字構形及組合時的變化規律趨于統一,為語文教學、社會應用和對外漢語教學開創新局面。
2文字規范發展的方向和措施
漢字喜逢盛世,必須抓住機遇,盡快適應世界漢語熱的需要、中國加人WTO后因交際的需要、科技發展的需要,采取有效措施,加快發展速度。
2.1調動國家與民間兩個個積極性,加大漢字研究的力度
國家“支持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的教學和科學研究”,多年來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但是,民間的積極性調動得不夠充分。漢字產生于勞動人民的勞動生活,又服務于社會生活,如果只有國家主管部門的研究而沒有民間的研究,是遠遠不夠的。我們不能只盯著民間用字出現混亂現象的消極因素,而忽視人民群眾使用和創造文字的積極因素。語言文字的政策應該適當放寬,鼓勵民間建立語言文字研究機構,并積極征求漢字使用者特別是語文教師的意見,吸收民間漢字研究的成果,使語言文字政策的原則性與靈活性統一起來。
篇3
目前,世界上正在使用的文字以漢字為最古老,生命力最強。其他民族的原始象形文字早已隨著文化的進化而湮沒無傳。漢字所以能歷盡滄桑猶青春依舊,主要在其獨特的造字參照系,造字原則,造字方法;構字參照系,構字原則,構字技法;書寫參照系,書寫原則,書寫技法,書寫個性等。
漢字最大的特點是象形,具有鮮明的“繪畫性”,但它和繪畫——非邏輯的個體的以形寓意的藝術有質的區別。就結果看,繪畫重在“形”,漢字重在“象”。是忠實于對象的本來面目,通過集中、概括、加工等典型化的方法,抓住對象的典型特征,約定俗成地賦予對象特定的“含義”。字形上既有現實的“形似”,又帶浪漫的“神如”。從總的哲學方法而言,漢字遵循現實主義的創造方法,具體地說,“象形”、“指事”主要是現實主義的;“會意”、“形聲”是在現實主義的基礎上有機溶入浪漫主義的方法。這兩大方法相結合的創造方法,通過漫長的文字進化,潛移默化地作用于多維價值取向的漢文化,或者說,漢字創造所蘊含的這一方法論成為漢民族的集體元意識,使傳統藝術——美的創造明顯帶著以現實主義為主旋律,同時輔之以浪漫主義的色彩。
漢字以現實主義為方法形象地描繪對象,這個“對象系統”即是‘造’字參照系”。它決定著漢字的本質特征。許慎說:“古者庖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視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1]“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2]并據此推斷說:“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蹄迒之跡,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3]說“八卦”先于漢字產生,漢字為倉頡所造,都欠科學。若將二說有機綜合以論漢字,便可得到漢字的造字參照系:(附圖略)
天文、地理、動物、植物、人類社會,物質和精神界,其表象的特征和本質的規律正是創造漢字的參照系,是其師法的對象。以“天”、“地”、“人”三才,物質世界和精神世界為系統的參照系所創造的漢字,因能“以通神明之德”——表現精神世界,“以類萬物之情”——表現物質世界,所以帶有多學科意義的價值。作為文字,漢字首先也是為了交際的實用,但它是特殊參照系下的產物,漢字創造還兼顧識讀理解功能。因而漢字體現了直觀可辨,形、音、義有機結合,與對象同步進化的動態性原則。因其“象形”,所以其義顯得直觀,又因為以“形”為基礎進行有規律的邏輯組合,其義便“可辨”。不少漢字可因形見義,望文生義、依字辨義。這一原則大大縮短了漢字與識讀者的距離。漢字的識讀過程完全成為有意識記的智力主動參與的過程。字符可對大腦產生有機的信息刺激,因而比純符號化的拼音文字更易識讀、理解和記憶。
漢字音、形、義有機結合的原則,使每個漢字具有鮮明的個性特色。它們以“形”為內核,以“義”為靈魂,以“音”為外殼,有機地構成一個信息碼,這種以三維價值觀界定的對象,使其交際功能更具精確性、客觀現實性。音為形設,形因義存的獨特個性又使漢字的認讀理解帶來便利。而拼音文字的音、形、義三者是相互割裂的,靠約定俗成紐結在一起。其識記過程是機械的記憶過程。給大腦刺激的信息強度類似于電話號碼式的缺乏主動性和深度。
漢字的象形,不但象具體之形,還要象抽象之形,而且要描繪再現對象的典型特征,所以必然又和對象一起處于不斷進化的生命律動之中。無論是時間的遷移、空間的變化,還是形狀的異構,外力的干擾或是思想的革命,總有某一具體表現形式或抽象可變的本質特征的顯現,漢字依此來概括描畫對象。如果說藝術是永恒的,以象形為主色的漢字也是永恒的。即使以現代的“藝術標準”來看,漢字幾乎可作為完全意義的藝術品。每個漢字都包含著造字主體(可能是一時一人,更可能是一代或數代的多人)對對象(客體)全方位的文化意義的最優化把握。即是說,認識對象并形象或本質地描繪對象時,凝結了主體的意識能量、認識水平、思維能力、思想觀念、世界觀、審美觀、文化程度、品質修為以及當時背景下的整個自然與社會,物質與精神對主體的影響。尤其是其中的社會文化的各個學科體系對主體的綜合作用都烙印在每個漢字之中,從這個角度說,每個漢字都是廣義的文化意義的全息碼。它積淀著文字史前的文明信息,又蘊涵著文字史后的文明進化的韻律。
(二)造字法與思維科學
漢字造字方法有象形、指事、會意、形聲四種,核心是象形。這種造字方法循序漸進,自成體系,是系統思維科學高度發展的產物。
象形是“畫成其物,隨體詰詘”。[4]原始象形文字有的完全是圖畫般描繪對象,但由于賦予字音,旨在交際,其“義”要求從“形”中明示,使它從“畫”中分離出來。畫以表意,其義尚隱,字以表義,其意宜直。“直”的要求,使漢字只能用最典型的線條來勾勒。不少人認為象形文字是一種低級幼稚的文字,因而對漢字提出各種非難,甚至要用拼音文字來取代它。其理論的邏輯依據是原始的文字都是幼稚的象形字,漢字是象形字,所以也是幼稚的。所謂“物竟天擇,適者生存”,原始的象形文字只有漢字在漫長的文化進化中生存下來,并且在大時代的變革中能注入新的血液,以新的風姿呈現出來。與外界不斷進行能量交換,是一種不斷吐故納新的開放型文字。今知考古意義上的最早文字系統——殷墟甲骨文,是智慧高度發達下的成熟的文字系統。盡管同期別的民族也有類似的象形字,但只是個體的,非系統的巧合。所以它們最終成為“幼稚品”被淘汰。甲骨文不但成為具有活力的系統而且和當時的具有多維價值意義的文化同構,滲入社會文化各個層面,所以它并非低級文字。其實在殷周以前的千百年中,漢字已經歷了“從低級到高級”進化的準文字期。通常以文字系統的誕生來界定社會文明和人類智慧,認為史前是低級的,文字史后才是高級的。對拼音文字來說,其本身無法譯解被創造前的社會文明程度和主體智慧水平。在象形到拼音的質變中,割斷了譯解文明進化的鏈條。只有漢字才是譯解這些奧秘的全息碼。通過細致的剖析,漢字的象形之法,并非兒童式的涂鴉,而是對“天”、“地”、“人”三才如實的、系統的、典型的描摹。經過了由個別到一般,由個性到共性,由特殊性到普遍性的全部認識過程。并在具體的實踐中進行修正,使之進一步準確化、符號化、目的化。這是一種復雜的意識活動過程。
其次,寓“義”于“形”。形為義設,義依形存。無義則形同虛設,無形則義無以生。形與義之間以直觀對應的線性邏輯來貫通信息。“象形”字多用以指代事物的“名”,畫一物指一物,觀其形可知其義。可分為三類:一是個別特征稱代,用“窺斑見豹”的方法,完善其形,以求其義。(附圖略)法來描繪,在約定俗成的基礎上表現其義。形與義更帶外在強迫性的信息運載特點。
再次,以“形”、“義”、“音”稱代事物是系統定義法的表現。“音”是一維的,“音”與“義”有機結合是二維認識,“形”與“義”與“音”三者辨證相因界定對象是三維(多維)的系統認識論,是智慧高度結晶的產物。
指事一法是“視而可識,察而見意。”[5]通過直觀辨識就知其義。拼音文字充其量是“視而可讀,察而見音”。其義得自機械的記憶。指事字邏輯上是以象形為基礎的,離開“形”、“事”無從指起,是在形的基礎上注入抽象的成份。其形象性較強,比較直觀,從字形本身的特點可大致推知其義。是以形似為基礎,神會為創造的具體的抽象符。通過這種辯證思維,得到三類指事字:一類是在原象形字——參照符上增加一個指示符——正補充符;二是原象形字——參照符上刪除部分符號——負補充符;三是原象形字——參照符的方向改變——零補充符。但無論指事字的創造經歷了多復雜的思維活動,仍然是源于形象,回歸形象,以形象思維為主色的思維活動的結果,是一個完整的思維創造系統。顯示了系統思維的第二個層面——初級中介層面的特征。具體的形加上抽象的指示符,表示一種既非原象形字義,又非指示符本身含義的新義。這類字在“形”與“義”之間用曲折勾連的線性邏輯通道來勾通其信息,昭示字義。
會意是“比類合宜,以見指撝”。[6]它是以象形字和指事字為基礎,由兩個以上象形字或指事字構成。其義有一定直觀性,可審字知義,望文生義。它不同于指事字只是在參照符形之上進行指稱,而是多符多形間的結合。它雖以形為緣起,但不能直接因形而定義。如果說象形字多數是單獨名物的“畫”,指事字是因義設標的“象意”之“符”,會意字便是“有情節和主題的藝術之詩”了。在表象上,古漢字頗似畢加索的現代派繪畫,但更具體而實用的是這些既形象又抽象的“藝術符號”,僅毫厘之差,便會使整個“情節”和“主題”都發生變化——字義變化。識讀者在審字以求義的思維活動中須通過想象去豐富、補充符與符之間的意義中介環。其“形”與“義”之間靠空間交叉的邏輯通道來勾通其信息。呈現了思維認識的第三個層面——高級中介層的特征。認知的最重要方法是“得意忘形”。
最后是形聲字——“以事為名,取譬相成”。[7]即按事物意思取個名稱,再用一個讀音相同或相近的字來表其讀音。它是以象形、指事、會意字為基礎,通過系統的邏輯思維來進行的高級造字法。抽象性最強。這一點雖然類同于拼音文字,但拼音文字的形與義與音的聯系是人為強制的,僅靠約定俗成,不存在內在邏輯關系。作為純抽象的符號,拼音文字本身無法顯示其運載的信息,只表其音。所以,無法通過創造性的思維活動來求其字義。拼音文字的造字法建立的是靜態的載體模式;漢字所建立的是動態的載體模式,它有自身的內在規律。拼音文字唯一趨勢動因是“拼”,但拼的是“音”。對整個識字過程來說是“初級階段”,“終極階段”的“義”是拼不出來的,只能靠硬記;漢字唯一的靜態因是“音”,音是約定好的。其識字過程也是“拼”,但拼的是“義”。猶其是形聲字,音、形、義甚至可“一拼而就”。三者的關系是有機的邏輯關系,由音形義的思維過程,需經過思維活動的全過程:分析和綜合,抽象和概括,比較,分類,系統化和具體化。通過這一系列的思維活動,音、形、義之間的信息得以貫通,但依據的是復雜的主體網絡的系統邏輯。
漢字通過這四種造字法,在建立完整的文字系統的同時,建立了交際功能以外的多值文化功能系統,這是拼音文字所不能具備的。
首先,它構建了一個思維方法進化的系統模式。漢字的造字法從象形指事會意形聲,在“認識”的角度上,它提供了一個對對象的形象描述形神兼顧得意忘形抽象概括的系統認識方法的進化模式。不論哪一種造字法其核心都是“象形”,都有一個“自在”的意義發生源,通過它不同程度地注入抽象成分,“形象”與“抽象”逆動消長,由象形指事會意形聲,抽象成分逐漸遞增,形象成分逐漸減少。是始于形象,終于抽象的連續思維的認識過程。人們在反復的識字過程中,除了知識人獲得,還本能地受到認識方法的教育,使我們在認識對象時,善于通過對象的外在特征,從感性材料入手,經過反復抽象的思維過程,正確的分析問題,揭示問題,解決問題。
其次,漢字系統還構建了思維發展進化的系統模式:四大造字法下的漢字系統構建了具體可感的象形系統,形神兼備的指事系統,得意忘形的會意系統,抽象概括的形聲系統。它們既獨立又相因。無高度發展的抽象能力,便不能將對象的總特征作典型化處理,優選出出神入化的線條來形象地刻畫對象——象形字,又由于形象思維的高度發展,而能天衣無縫地融匯到抽象的特征指稱之中。通過對漢字由表入里的深刻認識,由于系統的交互作用,漢字既能有效的培養形象思維的能力,還能培養辯證系統的思維能力,而且形象思維和抽象思維之間的中介思維被認識并得到培養。
此外,還建立了思維邏輯的系統模式:象形字培養直觀線性的邏輯思維;指事字培養曲折勾連的邏輯思維;會意字培養空間交叉的邏輯思維;形聲字培養立體網絡的邏輯思維。從而對不同性質的事物運用不同的邏輯思維,使邏輯思維能力得到提高。四大造字法本身就隱含著極為嚴密的邏輯關系:感性認識模糊思辯抽象認識的連續性的邏輯關系。由于“指事”、“會意”兩個既形象又抽象的中間環的運用,使的“模糊邏輯思維”得到揭示,并有著重大的現實意義和實踐意義。傳統的思維科學單純研究“形象”與“抽象”兩種端性思維,沒有對介乎二者之間的連續的“模糊思維”的認識,這是經典哲學及其邏輯研究的產物,是不完善的。
漢字造字法正是上述高度智慧下的辯證系統思維的產物。這種思維水平和方法體系通過具體的文字創造,濃縮在每個漢字中,使我們通過漢字的使用,自覺或不自覺地吸收其全部能量,譯解其全部信息,體現其多維的文化價值。
轉貼于 二 構字法之文化學價值
構字法指的是具體建構漢字的技法。它是造字法的一個子系統,由構字參照系、構字原則、構字技巧三個有機關聯的層次組成。
(一)構字參照系的文化學價值
構字參照系是漢字具體的線條構建的技巧之師法體系。造字方法的參照系是天、地、人三才,物質態與精神態的自在客體,師法其“然”,是客體在一定時空背景中某一條件下的存在態或特征。構字法參照系是對象的這種存在態或特征的構成邏輯或規律,即師法其“所以然”。
在系統的哲學與自然科學的基礎上師法其“所以然”的參照系。
西方哲學及其他科學的原始面貌只能考諸有關著述;中國哲學及其他科學的早期特征即使無書可考,也能從文字的構造中窺探其靈魂。因為漢字界定對象是主觀見諸客觀的精神活動,它能呈現“是什么”、“為什么”、“怎么樣”的三維價值意義。
首先,物質世界及其事理是無限多樣、個性各異的,為了準確地描述這些對象,只能采用與對象同構的思維邏輯來構造漢字,得到同樣多樣而個性各異的漢字系統。隨著認識能力的不斷提高,對對象的個性認識更加深入,使共性較強的記事或指稱方法——結繩記事、積石為記等再也無法準確描繪對象以供交流時,促使了文字的產生。但漢字的現實主義方法的造字原則,使它同構于對象世界,呈現出與自然對象世界及相關事物一樣的豐富和千姿百態。
無限紛繁而復雜的自然界并非無機的雜亂,是可以分門別類的。“物以類聚,人以群分”。通過對對象各有機系統的共性與個性關系的把握,對不同事物進行科學分類,并按其特征作形象指稱。要對整個自然界的萬事萬物及相關事理作種屬分明的文字指稱,就要具備不同系統事物的自然科學知識。要對飛禽進行指稱,就必須有對整個動物界的系統認識,進而將飛行動物分離出來。又通過對飛行動物從形狀到解剖特點的全面認識以確定類型。《說文解字》:“鳥,長尾禽總名也,象形”,“凡鳥之屬皆從鳥”。有明確的“屬”的概念,形象有其共性,解剖可見個性。《說文解字》收有120個“鳥”旁的字,多數用來稱代不同的“鳥”。此外,還有:“隹,鳥之短尾總名也,象形”,“凡佳之屬皆從佳”。《說文》中收“隹”旁字46個,包含了多數短尾鳥在內,是鳥類的又一種。憑此我們便能了解這些文字被創造時,上古先民的自然科學及其他科學的水平。《說文》共收9353個篆文,歸納為540個部首,以這些部首為定義根,將物質與精神世界的的無限復雜的對象進行分類,使各得其所,屬性分明。可見漢字是自然科學及其他相關科學高度發展的產物。使識讀者在漢字認知過程中,不但掌握字符本身指的“是什么”,而且知其“為什么”——得到學科意義的方法論教育。拼音文字的“類”、“屬”僅是語法意義的,非表義對象本身。其分類的目的不是為準確的表意,而是服從語法的形式邏輯。
基于自然對象世界組構的無限性但非無理性,使漢字有限的偏旁與部首在合理的無限組合下與對象共構,并結合字與字的語法關系的組合,描述出整個自然與社會甚至思維領域的一切,且隨對象的衍化而衍化。
個性各異的自然對象卻有其形象組構的共性,它們都由點、線、面構成,漢字則按對象自身的特性進行點、線、面(偏旁)的有機組構,創造出千變萬化的漢字系統。這是對參照系“所以然”的最本質的把握。最能體現造字時代人民認識自然的能力和征服自然的特征。
此外,自然萬物存在的一個共同態是受地心引力的作用,重心垂直指向地面。古人雖不能認識萬有引力,但處處感受到了這種現象。如實描繪對象的象形文字便本能地將萬有引力作用下的事物的特征描繪下來,使得每個漢字呈方塊狀的合理布局,每個字都有其重心,重心是否當位、合理,決定著這一漢字的形體的線條布置是否合理和具有美感。盡管每個漢字都有明確的重心,但其線條的設置并非簡單機械的組合,而是變化多端的有機構建。是由千差萬別的不對稱性、不均衡性構成整體的對稱與均衡,從而組成方正結構體式的重心。這一點楷體表現得最突出,其他各體也明顯遵循這種重心居中的對稱組構原則。
以人類行為科學為參照系。漢字線條的構組還以人類行為科學為參照,將人類關系態的邏輯運用到點、線、面組合的邏輯中。人類以各種規范來協調相處,從而構組了各種秩序下的人際關系態。漢字的構造也明顯帶著這種協調相處的特點。上下左右,內外先后,大小長短等等都有嚴格規定,秩序井然,不失規矩。表現在上下關系中以上為先,自上而下;左右關系中以左為先,從左到右;內外關系中以內為先,先內后外。這些無疑具有人類行為科學價值。拼音文字的字母書寫是無左、右、上、下、內、外的規則。既可自左向右,也可從右而左,既可從上到下,又能自下而上。字母與字母組合成文字時,只有單一的自左而右作線性橫向排列。
人倫講究秩序,但這種秩序并非一維的單向趨動,而是雙向逆動的。這種原則體現在漢字構造上雖講究上下、左右、內外的先后,但優先者并不能越位強占,更不可獨霸,而是按自身的特點占據一定位置,進行合理分配。如“忠”,在上的“中”不宜過大過長占據“心”的位置,使在下者無法立足。同樣,左右關系中,左先但不可欺后。如“林”,左“木”之捺宜短,右“木”之撇要收,在互讓的關系中,協調構建,不過分夸張任何一方。
此外,在群體與個體的關系中,漢字構造強調共性,群體大于個體,個性服從共性。具體地說是點、線、面(偏旁部首)的獨立意義小,共構意義大。部首的存在主要是為了共構,而且往往是帶有共性意義的部首偏旁放在優先位置,或在上、在左、在先。拼音文字的字母獨立性強,不同字母擺在一起無內在的必然共構性。顯示以個性為中心的行為價值特點。漢字完全是由筆劃(元素)偏旁部首(層次)單字(子系統)整個漢字系統,從個性到共性的邏輯組合,這種“共性優先”的原則,展示了傳統行為科學的價值取向。漢字構造以上述各學科對象為參照系并與之發生價值同構關系,凝固著他們的信息,所以帶有多維的文化價值。
(二)構字原則的文化學價值
構字原則是指漢字構建的具體技巧和手法所遵循的準則。它包括默記對象的模仿原則;辯證相生的組構原則:中正和平的美學原則。
默記對象的模仿原則與中國繪畫:從西安半坡出土的幾件著名的人面魚紋陶碗看,形象極生動,這種線條勾勒的畫竟如西方現代派一般。然而,這種早就很成熟的藝術,后來沒有得到應有的發展,直到南北朝以后才中興起來。但以線條勾勒為特征的象形字卻得到充分發展,到南北朝時已走完了由甲骨金文、大小篆、隸書、正楷、草書等全部的進化過程。在漫長的文字創造過程中,漢字的構造方法和書寫技法反而大大地影響和促進中國畫的發展,并匡定了中國畫的基本特征。
中國畫不是西歐式的寫生來再現對象,而是以默記對象的方法來再現客體。默寫是先經過心智活動,將對象留在記憶中的典型特征(往往是點或線的)繪寫出來,結果是“眼中竹”與“心中竹”與“筆下竹”俱不相同,愈加典型,愈加簡練。呈現出特征線條勾勒的繪畫特征。與象形字以特征線條刻畫對象有共同的價值取向。
以特征線條默畫對象會因人而異,不同繪畫者的思維水平、修養能力有差異,記住對象的特征也不盡同,所默畫的同一對象也有區別,只能求得大致的相似,本質特征趨同——神似。中國畫重神似而不拘于形似,東坡先生說:“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追求“詩中有畫,畫中有詩”的神妙境界。與漢字一樣是現實主義基礎上溶入浪漫的理想主義的成分。
以線條勾勒默畫對象,而不是面對面的寫生,使中國畫忽視了“光”和“色”的變化及立體透視的科學性。這也是追求“神似”的必然結果。中國畫以“散點透視法”的線條來構組對象,這與漢字以特征線條全方位地(必然是散點透視式地)設置也具有共同的價值取向。
工筆與寫意,篆楷與行草;繪畫與書法在傳統的文化中實有異曲同工之妙。
辯證生克的組構原則與古代哲學。文字史前哲學無稽可考卻能從漢字構造的邏輯中得到破譯。作為系統世界觀的哲學是很晚才誕生的,作為人類的世界觀甚至于初步的哲學體系在文字產生之前就存在于上古先民的物質與精神的文化生活中,既烙印在打制的石器中,陶器上,也凝固在千百年來群體集體創造的漢字中。因為漢字是主觀見之于客觀,如實地描述對象的交際符號。它有著客觀存在性,還有第二位的主觀性,而且是群體共同的主觀性——文字只能是群體的創造,這與畫有區別。這一群體性——社會共同性所表現出來的世界觀、哲學等文化特征能從漢字中譯解出來。
早期漢字的線條由直筆和曲筆這一對矛盾體組成。它們相生相克,相反相成。直有“橫”“豎”;曲帶“方”、“圓”。或橫豎相接,方圓相依;或直曲成方,斜曲成圓。有左彎右拐,有上折下勾……。生克變化,無盡無窮,完全體現了對立統一的法則。漢字按不同規律不同原則,以幾組簡潔的符號組成無限復雜的文字系統。并共同體現著陰陽生克同構的特征。橫一、再二、而三,但不可再四;一豎、二豎、三豎,而四豎不成字。橫而太過制以豎;豎而不節抑以橫。直筆添曲,曲筆加直;方中見圓,圓內生方。相依相斥,互為呼應;生克變化,渾然天成。
上述為“點”與“線”的哲學,進而由線構成面(偏旁)又由面構成“塊”(文字)時,更顯示了辯證法的熟練運用。這從偏旁與偏旁互相組構成字時的位置變化排列上,貫穿了辯證的甚至系統的哲學邏輯:左右結構,右左結構;上下結構;內外結構,外內結構;左中右結構,上中下結構;(上下)左右結構,左右(上下)結構,(上下)左右(上下)結構;(左右)上下結構,上下(左右)結構,(左右)上下(左右)結構;左右(內外)結構,(內外)右左結構;(左右)內外結構,外內(左右)結構;(上下)內外結構,(內外)上下結構;混合結構。
這種排列結構邏輯,還顯示了數學的排列組合的理論價值。
在偏旁與偏旁或筆劃的組合中,雖然是全方位的,但決不是無序的,有特定的邏輯性,并體現了共性與個性,特殊性與普遍性的辯證關系。同一偏旁(共性)的字群中,每個個體不同別的個體,有著自身的特殊性。共同的偏旁是其普遍性,是各個個體共同的組織信息塊,但它是寓于各個個體的特殊性之中。無共性則無個性,無普遍性亦無特殊性。
在點、線構面,面與點與線或面構成塊(字)時,還體現著系統論的五大原則:一、系統的整體性原則。點線面塊(字)是元素層次子系統系統的關系,同樣單個漢字同旁漢字漢字系統也是由元素到系統的有機構成關系。它們既獨立又有機關聯。二是系統整體的動態性原則。就漢字的構成看它們是由幾個基本筆劃——元素組合起來的,作為基本符號本身無多大意義,但按一定邏輯組合后,元素與元素進行了信息交換、構成了偏旁進而構成字便帶有了實際意義,起了質變。雖然各部分(偏旁)進行了能量交換,但并不破壞它們,而是保持了整體各部分的一定聯系。就整個漢字系統而言,是不斷與外在環境進行信息、能量交換的,不斷進化,注入新的活力。三是系統整體的結構性原則。指在一定層次中形成結構的基礎上的整體性。這在漢字的結構中體現的尤為鮮明。四是系統整體的層次性原則,即有序性原則。指任何有機整體都是按一定的秩序和等級組織起來的。漢字正典型地體現了這一原則。五是系統整體的相關性原則。任何系統都是存在于一定環境中,也是與外界其他系統進行聯系或交換。漢字既是現實主義式描繪對象,是以三才為參照系,自然是處在一定環境中與對象不斷交換信息和能量,隨文化(廣義)進化而進化。
通過剖析,傳統哲學的特點是能夠從漢字中得到合理破譯的。并且我們可以清晰見到漢字筆劃的有機組合所蘊涵的陰陽辨證的哲學精神孕育了中國傳統哲學的胚胎。
中正和平的美學原則。中正和平的美學原則是整個東方藝術的核心原則,它源于儒家哲學,但這一哲學本身在文字史前就已受孕。漢字摹仿三才,有典型的建筑美。它重心居正,不偏不倚。不作畸形之態,常呈中正之貌,柔和協調之狀。表現為一種自在美。早期漢字大致也呈方塊狀,端莊嚴正,重心穩實。但它并不呆板,其方正的總貌是由萬法紛呈、千姿百態、個性各異的形體組成。中正生自偏曲,端方來于圓折,平和協調起于變化律動。正是這一辯證的矛盾運動,最后形成美的形態。中正和平是漢字構建的總的美學原則,每一具體的漢字組構又體現了不同的美學技巧,它包括:陰陽相接。其方位以上為陽,下為陰;左為陽,右為陰;內為陽,外為陰。它們互相依存,和諧相交,合為一體。線條以直為陽,曲為陰,方為陽,圓為陰。多數漢字是曲直方圓交互連綴。節奏分明,韻律生動。剛柔相濟。線條以直為剛,曲為柔;線塊以方正為剛,以斜曲為柔。斜直曲方,陽剛陰柔,既對立相克,又溶于一體。虛實相間。是對線塊而言。筆劃少而空疏為虛,多而綿密為實。漢字總是虛實相間,上空則下實,左空則右實。線條分布朗列均衡,充盈一體。動靜相生。線條以方直為靜,以圓曲為動。漢字多數是以曲直相交,動靜相生。在平直方正的穩定靜態之中,輔之以曲折園斜的變動之姿。動中見靜,靜中生動,并在這一矛盾運動中服從整體的中正和平之態,給人以完善獨立,穩重端莊又充盈流轉的變動的美感。在這些辨證關系的美學處理中,在線條的具體設置上,既富于變化,又不走極端,是高則低之,長則短之,大則小之,寬則窄之,實則虛之。有余則削,不足便補,盈虧相濟,柔和協調,無不貫穿自然的美的法則。前面已論及漢字是呈方塊狀的總貌,盡管線條變化萬法紛呈,但總體效果是對稱分布的,重心位于方塊的對角線交點上。顯得端正典雅。而各個層次、各個角度不同性質的線條的辨證呼應,使穩重方正的外形展示于多姿多態的變化之中。這一中正和平的美學特征和傳統哲學、美學價值、對象世界的內在韻律是有機統一的。
(三)構字技法的文化學價值
構字技法是指線條安排的具體技巧和手法。由點線、面的組織,方位座標的確定,結構安排等三個層次構成。
點線面組織的邏輯學價值。每個漢字都是系統態下的符號塊、定義塊,也是凝固各學科文化價值的信息塊,所以其線條的組合要有一定的邏輯。在形狀的象形上,除了藝術化的邏輯,形式上還有獨特的組織方法。它是由點、線、面循序漸進,各自獨立又配合共構的邏輯來進行。由點到線到面,點線構面,小面構大面。點、線、面又各有獨立的功能,共構時互相以形式上的算術法相加,其功能卻起了質的變化。一點與兩點三點的含義絕不相同,丶冫氵灬——它們在組織上是相加,本質卻完全有區別。但它們都是漢字系統中的一個功能項,獨立是相對的,與其他功能項再構是絕對的。點與線、線與線、線與面、面與面的組構也遵循這一系統邏輯。
方位座標的確定。漢字的線條安排多設定在多維空間的立體坐標系中。因其象形性,所以在描摹對象時要在一定時空背景下進行,雖作散點透視但符合空間組構原則。因此漢字的(附圖略)
現中漢字的粗細、明暗、濃淡等具有主體意義的方位特征尤為明顯。漢字和國畫一樣是多視點的,呈視點移動組建的方位特色。因線條的座標方位的決定,線條便可進行全方位的辨證系統的組合。
結構安排。有了方位座標,在象形寫真與中正和平的原則下,對線條作優化安排。安排技巧須按照自然科學、人文科學,物質與精神態的價值取向進行,將文字創造時期的文化價值積淀在具體的布置中。
漢字是漢文化的全息碼,是文字史前文化的信息載體,又是孕育史后文明的基因。人們用考古的方法,見鐵而論冶煉,指鼎以說青銅,刀槍劍戟以談軍事。那么“文字”豈不正是史前文明留下的“文物”嗎?漢字的功能不但在其外殼,它是遠古文明的價值載體,同時提供塑造中華民族精神與性格的原動力!
【注】
[1][3]許慎《說文解字》十五
篇4
《左傳·成公·十三年》中說:“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其中“祀”就是古代的祭祀活動,“戎”就是軍事活動。可見在古時候,軍事活動在先民的生產生活中具有重要的意義,這一點也可以從現今出土的甲骨文得到印證,大部分的甲骨文內容都是圍繞祭祀和戰爭的。
戰爭既然對先民的生活有至關重要的影響,那么戰爭中的一些信息也會滲透到先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文字是記錄先民生活的重要工具,那么從古文字的字形中我們也可以探索到一些古代戰爭的文化信息。
一、漢字與古代軍事戰爭思想
在生產極為落后的上古時期,生產單位都是以血緣關系為基礎建立起來的氏族公社,人民都生活在相互協作緊密的群體之中,個體與個體,群體與群體之間難免不起摩擦,從繁體的斗字可以形象地看到兩個人相互廝打的場面。甲骨文中“斗”字作 [XCz1.TIF;%50%50,XQ],左右兩個符號代表兩個人,一副怒發沖冠,徒手相搏的樣子。葉玉森認:“古斗字像怒發相搏形。”字形中可以看出在“斗”字產生的時代,人與人,部落與部落之間的矛盾并不十分尖銳,打斗中并不使用器械,一般也不會造成致命的傷害。
隨著部落經濟的進一步地發展,生產工具的進一步改進和創造,部落間的矛盾也進一步的激化和升級,用于戰斗的工具也就應運而生,從此就出現了武器。從“戰”字的字形來看,它是由兩個部件構成的,繁體的戰作“戰”。許慎在《說文解字》中認為它是一個形聲字,“單”表音,“戈”表意義。其實這種說法有失準確性,“單”字不僅僅是表音部件那么簡單,他與“戰”字本身的意義十分密切,在甲古文中“單”字作等幾種字形,從字形上看是一個捆綁著石塊的樹杈,這很有可能是狩獵時使用的一種防衛型工具,用于人與人之間的戰斗時很可能就是一種防衛型武器。段玉裁在《說文解字注》中說:“經典謂之干…。所以捍身蔽目。用捍身,故謂之干。”由此可見,“干”就是一種防衛器械。春秋時期的一個鐘上鑄有“攻占無敵”的銘文。其中的“戰”就寫作,其中的“攻”和“戰”應當理解為一對反義詞,即進攻和防衛。
隨著金屬冶煉技術的提高和戰爭規模的擴大,出現了專門用于戰場上格斗使用的武器,戈是一種具有強大殺傷力的攻擊性武器,所以“干”和“戈”結合,有攻有防,才形成了“戰”的本意。可以說“戰”字的出現時古代戰爭殘酷性加劇的集中體現,群體之間的沖突已經不再停留在“斗”的水平,而是你死我活的殺戮。由此可以推斷“戰”字的出現應當晚于“斗”字。
關于“爭”甲骨文中它是一個會意符號,左右兩只手,中間一豎。意為兩只手爭奪某物,這其實是一個抽象意義,兩只手既可以表示兩個人,也可以表示兩股勢力,中間的一豎,更加的抽象,它有可能是具體的事物,如財物﹑配偶,也有可能是權力﹑地位等。《說文解字》對它的解釋是“爭,引也。”,“引”就是拉弓緊張的一種狀態,發生“爭”這種狀況只有一種可能,那就是資源相對缺少,而兩種力量又勢均力敵的時候。資源豐富,就不會去爭奪了,力量相差懸殊也不會發生爭斗。資源不足,兩派又實力相差不大,人們就會為有限的資源而爭,在“爭”的同時可能會“斗”,甚至會因此而“戰”。
一旦發生戰爭,參戰的雙方一般都是軍隊,“軍”字在甲骨文中作。許慎在《說文解字》中對它的解釋是:“軍,圜圍也。四千人為軍。從車從包省。車,兵車也。”從造字法角度來看,“軍”字是一個會意字,即用兵車圍起來。從這里我可以看到在古代軍隊在止宿時,為防止敵人的偷襲,往往用兵車圍城圓圍,啟到類似于城墻的防御作用。《說文解字》中所說的“四千人為軍。”古代軍隊大約是以軍為單位圍城一圈。因此軍事編制單位便與保衛共用一字。《銀雀山漢墓竹簡·孫臏兵法·十陣》:“疏而不可蹙,數而不可軍者,在于慎。”文中“軍”的意思就是包圍,又此圓圍乃軍隊止宿之圓圍,故有引申出駐扎﹑營壘等意義。《銀雀山漢墓竹簡,孫子兵法,行軍》:“凡軍好高而惡下,貴陽而賤陰。”這里的“軍”指的就是營壘。可見“軍”在最初的時候并不是直接指代軍隊。
篇5
漢字與文化的關系曾經并不為人們所重視,但是最近20年,隨著漢字文化學學科的建立和發展,已經成為一個熱門話題。漢字作為世界上唯一使用至今的以表意為主體的文字,“構形的最大特點是它要根據漢語中與之相應的某一個詞的意義構形,因此,漢字的形體總是攜帶著可供分析的意義信息。”雖然說世界上各民族文字無不凝結著一定的文化信息,但漢字在它自身的結構中包含著豐富的文化因素,反映了漢民族的文化特征,這一點在象形意味濃厚的古代文字中表現得更加明顯,是其他表音體系文字無法比擬的。因此,漢字與文化的關系越來越為人們所樂道,再加上歷史底蘊的深厚,我們在認識漢字、更深層次理解漢字方面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一、漢字與文化的關系
在漢字沒有產生之前,先人通過口語進行交流,憑借記憶一代一代往下傳,但記憶容易遺忘或走樣,同時還受到時間和空間的局限,不能長遠流傳。因而,我們的祖先在生存、發展的過程中,經過很長時間的努力,逐漸創造了漢字。從沒有語言到語言的產生,是人類進化史上的一大飛躍;從沒有文字到文字的產生,是人類進化史上的又一大飛躍。某種程度上可以這么說,由于漢字的產生和發展,自古以來漢民族長期積累的哲學、文化、科技和歷史才得以記載和流傳至今;我們祖先的思想、文化藝術和科學技術才得以廣泛傳播和日益提高。所以漢字是既反映文化又與文化相互依存的文字體系。
二、漢字推動漢文化的發展
(一)漢字推動了書法藝術的發展
漢字推動了漢文化中書法藝術的產生和發展。“中國書法藝術是以中國漢字的文義為內容,以某種字體的書寫為形式,書寫出來的有章、有法的一種藝術形式。”它是隨著中國漢字的產生、發展而產生和發展起來的。
(二)漢字推動了篆刻藝術的發展
漢字推動了漢文化中篆刻藝術的產生和發展。篆刻是我國特有的一種漢字、書法雕刻相結合的藝術。在紙張發明之前,人們的書寫材料為龜甲獸骨,青銅器,石器,木簡等。人們是將漢字刻在材料之上,這為篆刻藝術的產生奠定了基礎。而漢字的以形表意所具有的圖畫性、藝術性及字體多變性又是其產生發展的條件。
篆刻藝術起源于實用,開始只是作為商業上交流貨物時的憑證,及當權者表示象征權利的證物,后來發展成為一種獨立的,作為欣賞的藝術。
(三)漢字推動了修辭藝術的發展
漢字推動了漢文化中修辭藝術的發展。在古漢語中,詞匯多為單音詞,即一音一詞一字,這樣字與詞就建立起一對一的關系。而漢語表義是靠語序排列的,這就為同一語句的順讀,倒讀皆可誦提供了可能,而這種同一語句的順讀,倒讀皆可表義就是回文。
三、研究漢字與漢文化關系的意義
(一)有利于正確認識漢字的地位和作用
首先漢字不是落后的。有人認為漢字是落后的。漢字是漢文化的一部分,其形成與發展都要受到漢文化的制約和影響,甚至可以說什么樣的文化決定什么樣的文字。如果棄之不用,人們就不能通過研究漢字來考察遠古已逝的文化。
其次,漢字不是萬能的。漢字負載著大量的文化信息,但并不是所有的漢字都與漢文化有關,二者并不是一對一的對應關系。漢字是反映一定的歷史文化,人文信息,但絕不是每個字“都是一頁恢宏的歷史”。
(二)有利于拓寬漢語言研究的廣度和深度
現今中國漢語的研究,多用國外研究拼音文字的方法加以研究,且不說這種方法是否適合漢語,但可以肯定地說,研究漢語只用這種方法是完全不夠的。因為漢字與拼音文字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文字,漢字有自己獨特的特點,這需要人們用符合其特點的方法加以研究,這需要人們不斷地探討,深入地研究。而將漢字與漢文化聯系在一起,一并研究,從漢文化的角度看漢字的產生和發展,及漢字是如何構形等,這可以說是漢語研究的一部分,擴大了漢語的研究范圍。
四、結論
篇6
一、韓資銀行本土化進程及經營現狀
2006年12月,中國加入WTO后5年過渡期結束,中國金融業進入全面開放時期。隨后,銀監會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外資銀行管理條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外資銀行管理條例實施細則》,貫穿了以外資銀行法人為導向的監管理念。自此,外資銀行開始實施法人改制,成立本地注冊法人。本地注冊法人的成立,其管理架構與經營理念的巨大變化成為外資銀行本土化進程的里程碑。外資銀行本土化進程由此也分法人成立前時期和法人成立后時期兩個階段,不同的階段其本土化路徑體現出了不同的特征。以筆者所調查的煙臺市2家韓資銀行為例,在2007年和2009年,兩家銀行分別轉制為本地注冊法人銀行,成功翻牌并開辦了人民幣業務,邁出了本土化的關鍵一步。在華法人成立前,韓資銀行沒有統一的管理行,經營管理以韓國母行為主,采取業務跟進式的發展方式,主要經營戰略為服務本國企業。這一時期,韓資銀行缺乏統一、明確的本土化戰略,業務范圍局限于外幣業務,絕大多數客戶為韓資企業或合資企業,外籍員工占比較高,銀行自身的本土化意愿與程度均不強。法人銀行成立以后,韓資銀行結合自身優勢,提出了統一、明確的本土化發展戰略,大力開拓中國市場,如H銀行(中國)確定以私人銀行業務和財富管理經驗及技術引入中國市場,在東北三省和山東省大力拓展個人零售業務的發展戰略,Q銀行(中國)確定結合中小企業金融業務優勢,努力拓展中國市場的戰略;獲準開辦人民幣業務,業務范圍實現本土化;公司治理結構不斷完善,對業務、資金等實施了集中化管理,建立了統一的內部審計模式;不斷開發本土化產品,非韓資客戶占比逐步提高(見表1)。
明確、統一的本土化發展戰略的確立及實施,也推動業務的快速發展,截至2010年6月末,H銀行(中國)貸款余額89.12億元,較年初增加23.57%;各項存款70.18億元,較年初增加15.09%。Q銀行總資產為56.53億元,較年初增加13%;各項存款23.04億元,較年初增加108%(見表2)。
二、本土化問題與瓶頸
篇7
一、“字”在中文表達理解中的核心作用
在漢語的句子組織中,句法的基點是“字”。“因字而生句,積句而成章,積章而成篇”(《文心雕龍?章句》)是中國古代語言學對“字”和“句”關系的基本認識。在“字”和“句”中間,完全沒有“詞”的位置。即無須“詞”的轉換,漢字天然就是一個基本的語言單位。而“詞”這個觀念,在漢語中原來是一種文學樣式,是將詩文配上曲調加以演唱的形式。“詞”的word含義,是由翻譯外來詞而產生的,它并不是一個中文的概念。在現代漢語的分析范疇中,“單音詞”和“字”對應,兩者并無沖突。“雙音詞”把兩個字的較為穩定的組合視為一個基本單位,并非沒有道理。首先,單個漢字字義豐富,卻不夠明確。雖然中文高度依賴語境,但當我們僅僅指稱一個概念的時候,指稱本身的明晰就成了概念清晰的一個基本條件。中文不斷創造新的概念、新的指稱,其方法就是將有限的漢字靈活組合,產生新的組合義,從而創新了語匯。由此,新的組合義(1+1>2或1+1≠2的組合義),是雙字組結構“合法性”即“詞化”的必要條件。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明”表示bright,“白”表示white,而兩者組合后的“明白”表示understand(組合義)。其次,中文的表達喜好單雙音節交錯的節律,因此新的概念的產生,即字的組合和“意會”,大都發生在一個穩定的雙字組范圍內。甚至即使在意義上是1+1=2的字組,也會因雙音化而“凝固”起來,成為一個基本單位。前者如“然則”,王力分析說:“‘然’是‘如此’,‘則’是‘那么’,‘然則’本來是兩個詞,即‘既然如此,那么……就’的意思。后來由于它們常常結合在一起,就凝固起來,成為一個連詞了。”
又如“所以”,“在上古時期,‘所以’應該認為是兩個詞,‘以’字有它表示工具語的本來意義。”“‘所以’這個仂語,在古代漢語里是最常見的凝固形式之一。”更有些1+1=1的字組,其組合不惜以意義的冗余去湊足一個雙音節。例如,古代漢語中大量的“偏義復詞”,諸如用“吉兇”指“兇”,用“國家”指“國”。“有孫母未去,出入無完裙”(杜甫《石壕吏》),“出入”實指“入”;“備他盜之出入與非常也”(《史記?項羽本紀》),“出入”實指“出”。又如古代漢語中大量的“同義并行復合詞”,“涕淚”同義,“誅殺”同義,“憂虞”同義,“愿望”同義,“愛憐”同義。“吾既已言之王矣”(《墨子?公輸》)的“既已”、“斧斤以時入山林”(《孟子?梁惠王上》)的“斧斤”,都是十分典型的1+1=1的組合。在漢語史的發展中,基本表達單位的雙音節化是一個長期的趨勢。然而,即使受雙音化的影響,漢語的“雙音詞”仍然與歐洲語言的“word”有根本的不同。其關鍵在于漢語的雙音組合是“字”組,漢字在組合中有很大的分析性。這就造成了中國語言學的一個世紀糾結:當兩個漢字組合起來的時候,我們無法清晰地判斷哪些組合是“word”,哪些組合不是。即使是那些很有把握判斷為“詞”的字組,只要提供合適的語境,組合中的字就有可能獨立表意,由此形成漢語表達中十分獨特的“組義分合二重性”。經典的例子如“非常”,合則為“很”,分則為“不尋常”;又如“半天”,合則為“好久”,分則為“白天的一半”。漢字的分析性使得“字”即使在一個成熟的組合中都潛藏著很大的游離性,這種游離性甚至能轉換結構的性質。一個引人注目的現象就是“動賓強勢轉換”。例如,聯合結構“唱歌”強勢轉換為動賓結構(“唱了一個歌”),聯合結構“睡覺”強勢轉換為動賓結構(“睡好覺”),偏正結構“小便”強勢轉換為動賓結構(“小便小不出來”),甚至貌似不可分析的連綿詞、音譯詞也難擋漢字的游離,連綿詞“慷慨”強勢轉換為動賓結構(“慷他人之慨”),音譯詞“幽默”強勢轉換為動賓結構(“幽他一默”)。這一因漢字特點而造成的理解上的分合二重性,稍加擴展就成為漢語表達中習以為常的“結構重新分析”。
在漢語的句子組織中,音韻節律的基點也是“字”。“一句之中,或多一字,或少一字;一字之中,或用平聲,或用仄聲;同一平字、仄字,或用陰平、陽平、上聲、去聲、入聲,則音節迥異。故字句為音節之矩。積字成句,積句成章,積章成篇。合而讀之,音節見矣;歌而詠之,神氣出矣。”(劉大櫆《論文偶記》)漢語的表達,天然講究對稱與和諧。這種講究,在口語中粗放地表現為單雙音節的配合,而一旦要深究其規律,必須推敲書面語中每一個字的音韻表現,所謂“神氣不可見,于音節見之;音節無可準,由字句準之。”(《論文偶記》)“字正”才能“腔圓”,字音是句子音律的基礎。在漢語的句子組織中,意義的基點也是“字”。漢語是一種高度依賴語境的語言。漢語的說話人奉行“聽話人負責”的言說策略,對聽話人的默契有很深的信任。因此漢語句子的建構講究“人詳我略”。句子的意義依靠有限的文字作充分的意會,這樣的文字在句子的理解中就成了一個一個的意義支點,在多方意會中靈活地組合起來,字義成為句義乃至篇章之義的基礎。漢語句子的理解,在“字斟句酌”和“字里行間”展開,形成“文字有意以立句,句有數以連章,章有體以成篇”(王充《論衡?正說》)的意義格局。這樣一個特點,造成了中文簡潔凝練、靈活自由的風格,這也是為什么唐詩和宋詞成為中國古代文學的高峰。正如張新所說:“中國文字這種高度凝聚力,對短小的抒情能勝任,而對需要鋪張展開描述的敘事卻反而顯得太凝重與累贅。所以中國詩向來注重含蓄。所謂練字、詩眼,其實質就是詩人企望在有限的文字中凝聚更大的信息量即意象容量。”[3]漢字的凝練是中國文學充滿詩意、中國人的思維充滿豐富的意象和詩意的重要原因。中國語文研究傳統高度評價“字”在漢語結構的組織和理解中作為基本要素的功用。劉勰指出:“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積句而成章,積章而成篇。……句之精英,字不妄也。振本而末從,知一而萬畢矣。”(《文心雕龍?章句》)我在上世紀80年代的博士論文《〈左傳〉句型研究》中曾指出:“(劉勰)強調‘因字而生句’,這是同西方形態語言的因‘框架’(形態配合關系)而生句完全異質的一種組織方略。因‘框架’而生句,以大統小,以虛攝實,是先有句法關系模式,然后在這個圖式內的各條‘透視線’上刻意經營。這是一種靜態的空間體造句。因字而生句,是以小組大,散點經營,以流程見局勢。這是一種動態的時間流造句。劉勰所謂‘正本而末從,知一而萬畢’,其中的‘本’、‘一’,都體現出漢語句子以‘字’為立足點的建構而非‘填構’的語言組織方略。”
當然,就漢語句子的格局而言,僅僅有字的立足點還是不夠的,字的運用必須和“氣”聯系起來,并且渾然一體,形成句讀段,才能產生強大的鋪排延宕能力,使漢語的思維和表達流動起來,在語境的觀照下形成生發語義的整體(這一點,正是后來有人提出的“字本位”語法的很大的局限)。而“氣”的形成,依然是“字”的有節律的組合。汪曾祺曾提出過一個觀點:作為漢字書面語的詩歌和小說,用口語朗誦,甚至配樂朗誦,聽上去就像隔靴搔癢,很不過癮,因為離開了漢字視覺,會損傷原作的意境。他以柯仲平的“人在冰上走,水在冰下流……”為例,指出:“這寫得很美。但是聽朗誦的都是識字的,并且大都是有一定的詩的素養的,他們還是把聽覺轉化成視覺的(人的感覺是相通的),實際還是在想象中看到了那幾個字。如果叫一個不識字的,沒有文學素養的普通農民來聽,大概不會感受到那樣的意境,那樣濃厚的詩意。‘老嫗都解’不難,叫老嫗都能欣賞就不那么容易。‘離離原上草’,老嫗未必都能擊節。”因此,漢字書面語的閱讀效果比耳聽更好。與其聽書,“不若直接看書痛快。”
篇8
(一)旅游資源的文化屬性建設是發展韓城旅游事業的必然之路。
當前,旅游業的市場競爭日趨激烈。回顧自開發旅游以來韓城的發展進程,可分為三個競爭階段:
第一階段是項目競爭。上世紀70年代中期,各個行業都開始快速發展。旅游業作為一個新興產業也借勢而發,在那時要是能開辟一個景點,就能夠吸引大量游客。只要是有一個像樣的景點,就有著絕對的優勢。
第二個階段是廣告競爭。當人們漸漸認識到旅游是一個利潤豐厚的新興產業時,于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只要是有一點自然或是人文資源的地方都建設為旅游景點。幾年之后,很多地方都有了初具規模的景點,為了游客,各個景點都不惜工本的打廣告,進而發展成了廣告的競爭。
第三階段是文化競爭。這么多年的發展,旅游業也漸漸成熟,游客的素質也不斷的提高,于是一個新的階段開始了,即文化競爭。景點是否蘊含著獨特文化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二)加強景點文化屬性建設是防止韓城景點趨同化的必然之路。
景點的長久發展與生命力關鍵是區別于其他景點的文化屬性。一個沒有文化特征,沒有個性特征的景點很難在日趨激烈的競爭中走的長遠。韓城目前的各個景點幾乎是一樣的,沒有鮮明的特色,黨家村與古城都打的是明清建筑的旗號,司馬遷祠墓、大禹廟是純粹的祭拜,其他的都是打著元代建筑的名號,這種幾乎是一樣的思維弱化了司馬故里的文化氛圍,讓游客多出了些許疑問,難道一個以歷史文化著稱的名城竟然只剩下這些?事實上韓城這么多景點,各個都有著不同的文化差異,各有各的特點。
多年的總結可以明白,韓城旅游這幾年的快速發展,是韓城這片富饒的土地上豐富的文化差異造就的。假如去除了韓城特有的文化,就很難依靠古建筑和文物形態給人以永久印象。景點的發展和長久不衰,就必須要在文化建設上下大力氣。
(三)文化屬性的建設是保存和延續歷史的必然之路。
西禹高速路在擁有2000多年歷史的魏長城橫穿而過的時候,引起了很多人的關注,也引發了很多爭論,從景點的文化屬性來看我們明白了歷史文化遺產是不可再生的稀缺資源,一次不經意的破壞,從此再也不會擁有。也許是魏長城無法擋住秦軍的鐵騎,又怎么能擋得住橫穿而過的高速路?如今只剩下斷了的長城和橫穿而去的路。歷史在這里也斷了層,因此建設的本質是營造有利于景點的生存發展環境,是保存和延續歷史文化遺產資源的有效舉措,也是科學發展觀的具體體現。
二、現階段韓城怎樣走景點文化屬性建設道路
(一)樹立景點文化的意識。韓城在旅游經濟的發展中已經走到了其他地區前面,理解了旅游經濟發展的好處,在景點建設上加大了投資力度,卻不知道景點的經濟價值的最主要部分早已經不在于設施建設,而在于景點所包含的文化內涵。沒有一個區別于其他景點的文化特色,不重視特色文化開發利用,面臨的將是一條不歸路。所以在思想上要牢固樹立景點文化屬性的建設,把文化屬性的建設放到景點建設的前面。
篇9
早在馬克思寫作《資本論》時,就曾直接用到“自然化”一詞。雖然馬克思筆下的“自然化”[1]還沒有深入到大眾文化、大眾傳播研究的領域,“自然化”的意義也還是抽象和模糊的,但他的這一提及深刻影響了以后研究大眾文化、大眾傳播理論的思想家們,為他們作相關“自然化”問題的討論注入了靈感和啟發,也提供了科學的視角和理論源泉。
霍克海默認為,“娛樂工業借助符咒的力量,確立了自己的語言、語法和詞匯,這是一種例行化的過程。”[2]用“符咒的力量”來形容,這種描述本身就帶有超驗色彩。他們又進一步指出,“演藝明星無論是第一次表演,還是再次登臺,都熱情自如地使用這種語言,似乎在很久以前,這種語言就以沉默的方式存在”。[3]這里的“語言”對應先前的“例行化的語法、詞匯”,這是霍克海默“自然化”問題的體現之一。在他們眼里,發達工業社會帶來了繁榮的大眾文化,電視肥皂劇、流行音樂等雖然形態各異,內容不同,但是其語言風格都遵循“模式化”、“慣例化”的規則和規律;雖然大眾選擇的形式不同,但實際上隱藏在這些背后的還是一種意識形態。
霍克海默認為,因為有了模式化的語言風格做基礎,所以“每當娛樂工業出現新的與之不吻合的苗頭時,這時就會進一步強化習俗的力量。”[4]因此,霍克海默他們的“自然化”還指“習俗的力量”。習俗是自然界傳承下來的經驗、習慣,被世人看作是天經地義、理所當然的“自然法則”。常人不會違背先人留下的傳統,更不會輕易冒險將其改變。
在他們看來,大眾是在選擇自己愛看的內容和消費娛樂、休閑方式,好像有了“隨意性”的追求,但這只不過是一種假象。為了讓公眾能順順當當地接受已規定好的標準,變化的風格、細節和人物就是充當掩護的“煙幕彈”,隱藏于這些現象當中的標準語言始終如一、自始自終沒有改變。對“隨意性的追求(自然而然)”是霍克海默、阿多諾“自然化”問題的又一個體現。
在他們眼里,所有大眾文化的載體都包含重復的因素,長久下來,通過電影院、電視等大眾媒介進行的傳播就是重復的傳播,包括電視娛樂節目、肥皂劇、流行音樂在內的大眾文化一起形成了“風格統一體”,變成了“非文化體系”,構成了野蠻風格的入侵。在他們眼里,統治階級就是憑借現代技術和大眾傳媒,行使意識形態的統治功能。技術帶來的規模化生產形成一個無處不在的天羅地網,人們無法逃避,只能被動接受,大眾的主體性逐漸消亡,當人的思想已被“自然化”麻痹,這時被動變為主動,強制變成習慣,大眾文化融入進生活,人們開始爭先恐后的要求重復的大眾文化內容。霍克海默、阿多諾“自然化”也得以完成。此刻沒有文化可言,凸顯出來的是野蠻和非文化。與其說是發達的文化工業社會,還不如說是野蠻的文化工業時代。
霍克海默、阿多諾“自然化”就等同于“非文化”即野蠻。姑且我們暫不評論霍克海默他們說的對不對,他們所處的戰后的那種惡劣的生活環境,讓他們極度擔憂個體的生存狀況,和整個社會發展的前景。從而也導致他們思考得出的“自然化”問題過度走向了極端。
二、羅蘭?巴特“自然化”:“人性化”等
法國符號學家羅蘭?巴特的“自然化”潛移默化地貫穿在他的整個文化研究中,無論是在符號學的理論中,還是闡釋神話學的過程里,“自然化”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并且“自然化”在巴特那里以各種豐富的形式出現,含義也是各式各樣的,可以看到任何借助“自然化”來建造的意義,都被巴特悉心的一一指出。無論如何,巴特的相關研究都是為了戳穿“自然化”的傳播詭計,對各種大眾文化、大眾傳播現象作出意識形態的揭示和批判。
巴特是在其1953年出版的《寫作的零度》一書中,最早詳細地談到“自然化”問題,他使用“自然化”(naturalization)概念來解析文學的神話現象。到了后來,“自然化”就成了巴特研討大眾文化“今日神話”(today myth)的一個重要命題,并在1957年出版的《神話――大眾文化的詮釋》中系統地出現和反映。[5]
具體看來,在《寫作的零度》中巴特把文學結構的某種“自我封閉”或“自我完滿”的情形稱作“自然化”,[6]這里巴特指的是:文章的一種程式化結構,例如我們所見的每篇文章都會有開頭、中間、結尾部分。這樣一種程式化的法則已經深深扎根在人們心中,無論是自己寫文章,還是閱讀文章,都會按照這樣一種程式化的法則進行,這樣一種程式化的文學結構是巴特眼中“自然化”問題的體現之一。
在《神話――大眾文化的詮釋》中巴特把大眾文化體現人的“本性”(即人的“七情六欲”)的一些關聯和關涉、也稱作一種“自然化”。馬克思曾說人的自然是“需要與欲望”的總體,著眼于人的“本性”,這也是屬自然的東西,在巴特看來,想要達到大眾文化、大眾傳播想要的效果,最直接的影響就是大眾需要什么,大眾文化、大眾傳播就一定得及時反饋和給予大眾想要和需要的“要求”,以此不斷來滿足人的需求與欲望。欲望是一種主觀心理現象,其強度和廣度可以通過媒介的作用來加強、擴張或膨脹。媒介通過“自然化”的掩護,把人們潛意識里需要的,甚至是沒有察覺到的“人性”給其喚醒、甚至培養締造出。沒有人愿意強迫地被要求完成事情,當所有的目的都是在精心巧妙地安排下走入自己的生活,大家就都會不知不覺、樂意地去完成。到最后“自然化”還會把大眾打造成一種自愿去做的狀態,當大眾爭著、搶著想要完成的時候,神話的效果便也隨之而來了。
此外,巴特相信大眾文化的“自然化”之所以能夠完美地形成意識形態方面的“假正當”,除了依據人性化以外,還立足于“自然法則”對社會、對大眾進行操控。這樣的“自然法則”觀念在巴特眼中是一種話語獨斷式的言論,沒有原因沒有理由,就是強加式的給出說明和解釋。就好比霍克海默、阿多諾所說的“習俗的力量”。正如中國文化中有“食、色性也”、“男大當婚女大當嫁”一類的說法,無論因由,自古人們認為自然方面的東西其存在就理所當然、天經地義、合理合法,這也就是人類“自然法則”方面的觀念。[7]這種“自然法則”在大眾的眼里就是惟命是從,好像只用給出“命令”,人們就會乖乖地照著去遵循和辦理,這是巴特大眾文化、大眾傳播理論存在“自然化”問題的又一個具體體現。
三、布爾迪厄“自然化”:“簡單化”
在羅蘭?巴特之后對大眾文化、大眾傳播理論存在“自然化”問題給予過較多關注的思想家之是法國的學者布爾迪厄。在布爾迪厄的《實踐與反思》里談到了現代文化產品的“自然化”問題,而布爾迪厄作為思想家時提到的“自然化”問題主要指的是文化產品當中的意識形態在一種“簡單化”的表述中有著對于大眾一種所謂自然而然的隱性的操控。
布爾迪厄曾經反復指出,在文化產品中意識形態是依托某種“自然化”來形成、實現它對大眾一種“潛移默化”的影響,此外,這種“自然化”也就是文化產品一種所謂“簡單明了”、 “自然而然”的表述形態、風格。值得注意的是,布爾迪厄的此種“自然化”已經出現在巴特相關的討論中。從這個意義來看,可以說,布氏的相關認識有著巴特的啟發。
布爾迪厄長久以來被學術界關注的是他的實踐理論,以及在實踐理論體系中占據中心位置的“習性”這個概念。從某種程度上,從“習性”這一概念入手,是解讀布爾迪厄“自然化”命題的起點。他是在對“習性”有關理論的創作過程中,流露出了他“自然化”命題風格的特點,或許他太過依賴“習性”的概念,導致他之后得出的“自然化”命題,也與他所下的“習性”概念一樣,充滿懸乎。“習性”與他的“自然化”問題這兩者間有著十分緊密和不可分割的聯系。
筆者認為,首先“習性”的概念就是布爾迪厄大眾文化、大眾傳播“自然化”問題的一個方面的具體體現。“習性是與世界的日常關聯。”[8] “與世界的日常關聯”這就是在與“自然”套近乎,試圖建立與“自然界”之間的聯系,得以形成“自然化”。
“習性”是布爾迪厄“自然化”命題的一個體現,如果說這種概念的給出讓我們對布爾迪厄的標新立異有了錯誤的解讀,那么在他的直接表明更能讓人信服。他曾直接說到:“大眾從一出生就認可、接受了世界的現狀,根本無需勸導和灌輸,因為他們的心智來自認知結構,認知結構又是依據世界結構來構建的,世界結構是一種原生態的順序,即‘事物的秩序’。”[9]這是布爾迪厄“自然化”問題最直接、最具體的體現。
布爾迪厄認為人是帶著“自然化”形成的意識出生的。“自然化”的意識是事物的秩序。“事物的秩序”又是最原始的自然狀態,存在于自然界里的萬事萬物,他們都有自己生長、生活、存在的規律。這些規律是客觀存在的“自然法則”,是自然本身的內涵,或者規律,因此也是最簡單,最基礎的“自然”是我們討論的最淺顯的“自然化”。布爾迪厄的“自然化”問題相當直接和激烈。他在《實踐理論綱要》,《實踐的邏輯》,《實踐與反思》等著作中都曾討論過事物的秩序,以及這種“自然化”的意識形態生成的支配問題。
除此以外,布爾迪厄曾經反復指出,大眾文化、大眾傳播的意識形態是依托“自然化”來具體形成的、實現意識形態對大眾悄無聲息、潛移默化的操控和影響。此外,布爾迪厄所說的這種“自然化”還指的是文化產品、大眾文化中一種所謂“簡單明了”、“自然而然”的表述形態和風格。[10]因此布爾迪厄的“自然化”還指語言表述形態呈現出的一種“簡單明了”、“自然而然”的風格和面貌。
上述這些構成的布爾迪厄的“自然化”問題都是在強調“簡單化”的意思和思想。
結 論
霍克海默、阿多諾,羅蘭?巴特,布爾迪厄這三位思想家或學者對大眾傳播、大眾文化“自然化”在“意義歸結”方面是一致的,批判現代社會極權主義。所謂“流變”,一是從對西方大眾傳播或大眾文化“自然化”問題的認識由“單一”(霍克海默和阿多諾)走向“多樣化”( 羅蘭?巴特),再是走向了關注“重點”(布爾迪厄);再是,對“自然化”極權主義的功能(對人的操控)認識,則由斷言式(霍克海默和阿多諾)走向了學理解說(巴特),再走向了生理、心理學層面的解釋(布爾迪厄),也就是其認識在走向學理化,同時一定意義上也走向了某種“深入”。
注釋:
[1]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第24卷
[2]霍克海默、阿多諾:《啟蒙辯證法》,梁渠東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3][4]約翰?費斯克:《傳播符號學理論》,張錦華譯,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版
篇10
目前,人們對于“漢字文化”概念的界定,雖然從不同角度揭示了漢字文化的某些特點,但總體的研究力度還不夠,挖掘還不太深刻,概括也不太全面。我們認為,界定“漢字文化”應該從宏觀和微觀兩個角度著眼。宏觀的漢字文化,是指漢字的起源、演變、構形等基本規律所體現的文化內涵;微觀的漢字文化,是指漢字自身所攜帶的、通過構意體現出來的各種文化信息。宏觀的漢字文化是建立在微觀的漢字文化基礎之上的,因而,在研究的步驟上,應從微觀起步,逐步積累材料,總結規律,然后再上升到宏觀的研究上。但微觀的研究并不是對單個字符的孤立分析,而是要從整個漢字系統出發,著眼于宏觀的背景,并以宏觀的研究為最終目的。無論是宏觀的漢字文化研究,還是微觀的漢字文化研究,都必須圍繞漢字這個中心,要以漢字的自身因素為根本的出發點,而不能脫離漢字,把本不屬于漢字的東西生拉硬扯進來。
科學解釋漢字與文化的關系,必須首先了解“漢字”和“文化”各自的本質。就漢字而言,它是記錄漢語的書寫符號體系,它的產生,主要是為了滿足有聲語言的不足。對此,清代陳澧曾做過精彩的描述:“蓋天下事物之眾,人日見之,則心有意;意欲達之,則口有聲。意者,象乎事物而構成之者也;聲者,象乎意而構成之者也。聲不能傳于異地,留于異時,于是乎書之為文字。文字者,所以為意與聲之跡也”。[1](P8)意義是抽象的,是感覺器官所不能感知的;聲音是一縱即失的,只能作用于聽覺器官,而不能作用于視覺器官,它雖然能夠成為意義的符號,但在技術落后的古代,卻無法傳之異地,留于異時。而人類社會的日益發展,迫切需要在更加廣泛的時空范圍內進行思想交流。這種需要,促成了文字符號的誕生。漢字作為記錄漢語的書寫符號,以一種特殊的符形將漢語的意義和聲音物化下來,從而擴大了漢語的交際功能。可見,漢字的最根本的功能是記錄漢語,是否與漢語的詞相對應,是判斷某一符形是否為漢字的決定性條件。漢語是各種社會文化的載體,漢字記錄了漢語,因而也就與文化發生了聯系。就文化而言,由于社會文化的復雜性,對“文化”概念的界定也就成為難題,各家之說竟多達幾百種。有人認為文化專指人類的精神活動,有人認為文化包括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兩個方面,也有人認為文化泛指人類社會的一切活動。我們比較傾向于17世紀德國法學家S·普芬多夫的說法。他認為,文化是社會人的活動所創造的東西和有賴于人和社會生活而存在的東西的總和。它是不斷向前發展的、使人得到完善的、社會生活的物質要素和精神要素的總和。根據這個定義,漢字本身也是一種文化現象,是整個社會文化體系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漢字”和“文化”這兩個概念,應該是上下位的種屬關系。然而,在社會文化結構中,漢字這一結構成分必定要跟其他成分發生關系,所以“漢字”與文化的關系,并不僅僅表現為漢字與整個文化體系的關系,而更多地表現為漢字與整個文化體系中除漢字之外的其他文化元素的關系。關于這一點,王寧先生曾作過明確的辯證:“‘漢字與文化’這個命題實際上屬于文化項之間的相互關系范疇,具體說,它是指漢字這種文化項與其他文化項之間的關系。文化項之間是彼此有關系的,在研究它們的相互關系時,一般應取得一個核心項,而把與之發生關系的其他文化項看作是核心項的環境;也就是說,應把核心項置于其他文化項所組成的巨系統之中心,來探討它在這個巨系統中的生存關系。如此說來,‘漢字與文化’這個命題,就是以漢字作為核心項,來探討它與其他文化項的關系。”[2](P78)許多學者談漢字與文化的關系時,總是籠統地將“漢字”和“文化”這兩個概念簡單地對應起來,讓人覺得漢字似乎是獨立于文化之外的,這種割裂“漢字”與“文化”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漢字在整個文化體系中的地位是十分特殊的,它既是各種文化項之一,又是書寫和表達其他文化項的載體。它通過記錄語言中詞的方式,保存了詞的意義所反映的各種文化信息,因而同其他文化項之間建立了極為密切的聯系。漢字的悠久歷史與其跨時代性的特點,更使它具有了很大的文化考古價值,成了研究歷史文化及其變遷的重要依據。漢字與文化的這種密切聯系,使得二者之間具有著特殊的互證關系。人們既可以從漢字的角度去研究文化,挖掘漢字的起源、演變及其構形等各種規律中所包含的整體文化特質和具體文化信息;又可從文化的角度去研究漢字,探討其他文化項對漢字自身發展規律的影響。漢字自古至今一直頑強地堅持自己獨特的表意性,始終沒有割斷同文化的聯系,這使漢字文化的研究對各個歷史階段都有一定的適用性。因此,漢字文化研究不僅在理論上具有合理性,而且在實踐上具有可行性。
二、“漢字文化”與“漢語文化”的區別
在漢字文化研究領域,一些人往往混淆“漢字文化”和“漢語文化”這兩個基本概念,將漢語中所表現出來的文化內涵當成漢字文化現象來研究,從而影響到漢字文化研究的科學性。
其實,“漢字文化”和“漢語文化”是兩個不同的概念,有著各自不同的內涵。漢字和漢語雖然同是文化的載體,但二者之間卻存在著本質差別。就其構成要素來說,語言只有音、義兩要素,而文字則有形、音、義三要素。漢字的音、義要素是從漢語那里承襲過來的,而形體要素才是它自身所獨有的。字形雖然與音義有關,但卻有著自己獨立的作用和價值,具有自身的構造規律和系統。這就決定了漢字既與漢語有密切關系,又與漢語有著本質的不同。漢字與文化發生關系,一方面是以漢語為中介的,即通過記錄漢語而成為文化的載體;另一方面,由于漢字形體的特殊性,使得漢字具有了漢語所不具備的文化功能。漢字是表意文字,特別是早期漢字,形體與所記事物之間的關系極為密切。人們可以從字形當中,窺探出與所記事物相關的文化信息,這些文化信息有些是詞義能夠反映的,有些是詞義所不能反映的。從主觀上講,漢字構形的主要目的是為了記錄漢語中的詞,它的表意特征是在字形和詞義之間建立聯系的一種手段和方式。也就是說,人們采用表意構字法的目的主要是為了據形知詞,而不是據形知物。但從客觀結果上看,漢字的表意構形不僅記錄了詞,而且還記錄了除詞以外的其他信息。如甲骨文中的“王”字,除了記錄了“王”這個詞外,還以其像斧頭之形的構形告訴人們,古代統治者是靠武力統治天下的。這些信息,由于遠古文獻的貧乏,我們無法從“王”的詞義本身獲得。在最初造字時,古人并不是有意識地要將這些信息保存在字形之中,而是由于當時統治者必然擁有武器,人們看到武器極易聯想到擁有武器的人,于是,便用武器之形作為記錄“王”這個詞的字形,以期在字形和詞義之間建立一種明確的聯系。后來,統治者的形象發生了變化,“王”的詞義也隨之改變,人們通過“王”的詞義本身已無法了解到古代統治者的特點,而“王”的字形則成了古代統治者形象的歷史見證,具有了十分重要的文化考古價值。由此可見,漢字的文化功能實際上有兩個來源:一個來源于漢語中的詞,一個來源于漢字的自身形體。前者是漢語的文化功能在漢字形體中的物化,是與漢語文化相重合的,因而仍應歸于漢語文化的范疇。后者是漢字自身所獨有的,因而才是真正的漢字文化。
在具體研究中,不少人把漢語文化貼上了漢字文化的標簽,把許多本屬詞匯范疇的現象也歸到漢字身上。如有人在名為漢字文化研究的文章中,用《說文》“牛”、“馬”二部字多的事實,去印證我國古代曾經歷過畜牧業時代。我們且不說這種印證有何實際價值,僅在理論上,就存在著混淆漢字文化與漢語文化的傾向。“牛”、“馬”二部的字多,只能反映出當時語言中與牛、馬有關的詞多,除此之外,漢字字形本身并不能提供更多的文化信息。因此,對“牛”、“馬”二部字所反映的文化現象的研究,只能算是詞匯文化問題,而不能稱為漢字文化。假如把屬于詞義的東西都歸于漢字,漢字的文化功能就確實無所不包了。如果這樣的話,任何文字都是記錄詞義的,因而也就必然記錄文化,那么,漢字與其他文字還有什么不同之處呢?我們研究漢字的文化功能,必須從漢字的特殊構形出發,只有這樣,才能發掘出漢字文化的本質特點。
三、漢字文化功能的量度
對漢字的文化功能把握不準,甚至隨意夸大,是目前漢字文化研究中存在的一個較嚴重的問題。不少學者受“漢字優越論”的影響,將漢字夸得神乎其神,說“漢字是一串怪異的密碼”,“是古代社會的活化石”,“每個漢字都成為了一定文化的鏡像”。這些說法明顯與漢字文化功能的實際量度不相符合。
漢字與文化之間雖然存在著互證關系,但這種互證關系并不是完全對等的。從總體上來講,文化對漢字的證明功能要大于漢字對文化的證明功能,因為漢字畢竟是一種記錄語言的符號,而且是歷史積淀的產物,盡管它與文化之間存在著密切的關系,但它并不具備細致描寫文化的功能,也不具備最終確認文化的功能,更不具備確認文化所屬時代的功能。這就要求我們在進行漢字文化研究時,一定要對漢字文化功能的有限性有清醒的認識,準確把握漢字文化功能的量度,而不能隨意加以夸大。在這方面,王寧先生等人所著的《〈說文解字〉與中國古代文化》可謂成功的典范。該書《前言》中明確表示:“漢字中所貯存的文化信息,只能從每個字的構形——一個小小的方寸之地,簡化了的線條、筆畫,以及字與字的關系中得到,所以是有限的,如果夸大它,從自己的主觀臆測出發,弄出許多玄之又玄,廣之又廣的新鮮事來,其實是難以說服人的,也就把《說文解字》與中國古代文化這個題目給糟蹋了。”[3](P2)
漢字創造的最初目的是為了記錄語言,而不是為了細致描寫文化。漢字字形所體現出的除詞義之外的其他文化信息,只是其創造過程中的副產品。如果將這種副產品上升為其主要功能,就會導致對漢字本質的誤解。受夸大漢字文化功能觀念的影響,一些學者不能正確擺放漢字的位置,不能正確看待漢字和文化的關系。他們不是把漢字看作記錄漢語的工具,而是把它當成了考證和確認文化的靈丹妙藥,試圖通過漢字構形去構建整個中國古代文化史。于是,他們任意夸大漢字的文化功能,將本來毫無聯系的漢字構形和文化現象牽強附會在一起。如有人說:“它的存在無疑是一個活化石,能使我們透過文字的靜態形體步入到古人動態的文化意識中去,把文字內蘊所包含的深刻的政治、經濟、宗教、藝術觀念以及古人的行為方式、價值觀念、認識事物的方式等揭示出來。漢字作為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象征,乃是中華民族文化的脊梁。”[4](P15)作者把漢字比喻成中華民族文化的“活化石”、“脊梁”,說它是中華民族文化的“象征”,似乎中華民族文化的所有方面都可以在漢字字形當中找到根據,這無疑是對漢字文化功能的過分夸張。我們認為,漢字構形當中確實保存著不少有關古代社會狀況的文化信息,但漢字并不具備細致描寫文化的功能,它對文化的反映是有限的,而不是面面俱到的,因而,僅靠漢字構形無法確認文化,更無法全面構建古代的文化系統。
漢字構形系統是歷史積淀的產物,是伴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逐步形成的,這就決定了它必然具有很強的歷史層次性。但當漢字積淀為一個完整的構形系統時,這種歷史層次性已深深地隱藏在整個構形系統的背后,變得很難甚至無法考察了,因而也就無法運用漢字去確認文化所屬的時代。漢字構形中包含的一些文化現象,究竟應歸屬于哪一歷史層面,是很難有確切的結論的。這就要求我們在運用漢字考證文化時,一定要持謹慎的態度,要盡可能排除主觀隨意性,在漢字構形和文化現象之間建立起客觀、真實的聯系。有人不了解這一點,而是籠統地不分時代層次地去考察漢字的文化功能,其結果只能導致錯誤的結論。如同樣是《說文·女部》字,有人根據從女的字多,認為“男女地位的不平等完全可以從漢字字形中得到充分的證明。《說文》中女部下面有258個字,可以看出早先婦女的社會地位是比較高的。”[5];又有人認為,女部中的“大量貶義詞,反映了古代社會女子地位低下,受歧視受侮辱”[6];為什么會有如此差異的結論呢?問題的關鍵在于《說文·女部》字本身的復雜性,它們決不可能是同一時代產生的,因而也就不可能反映某一個時代的社會觀念。究竟哪些漢字起源于母系社會,哪些漢字起源于父系社會,現在已無法考察,所以,單憑女部字,既不能證明“早先”婦女的社會地位高,也不能證明“古代”社會女子地位低。《從女偏旁字看古代婦女的尊卑嬗變》一文[7],更是試圖通過女部字去描述古代婦女地位的演變史。作者認為,我國古代婦女在母系氏族公社時期地位極尊,從商代開始由尊向卑轉化,到西周以后地位極卑,這種演變過程都可以在漢字構形中找到證據。作者似乎對哪個字起源于什么時代、反映哪個時代的文化現象胸有成竹,但實際上,他在證明母系氏族公社時期婦女地位高時,用的是商代的甲骨文;在證明商代是婦女地位的轉化期時,用的還是甲骨文;甚至在證明西周時期婦女地位低時,仍然用甲骨文就已產生的例字。那么,究竟哪些甲骨文反映的是母系氏族公社時期的現象,哪些甲骨文反映的是商代的現象,又有哪些甲骨文預先反映了西周時期的現象呢?這種缺乏歷史觀念的做法恐怕值得商榷。
漢字是一個符號系統,每個字符的存在都受著系統的制約,它既以某種方式與其他字符相聯系,又以不同的構形與其他字符相別異。聯系和別異是每個字符存在的兩個必要條件,是漢字符號的本質內涵。漢字符號的系統性特點要求我們在分析漢字構形時,一定要從系統性原則出發,而不能孤立地分析單個字符。有些學者受夸大漢字文化功能觀念的影響,總是戴著有色眼鏡去審視漢字字形,習慣于到字形當中去為某種文化現象尋求印證。如有人認為甲骨文“母”字中的兩個指事符號象征“胸前兩乳十分發達”,并據此論證原始社會存在女性生殖崇拜。[8]我們認為這種論證是十分牽強的。漢字造字最初采取的是依類象形的方法,而象形就是要突出事物的顯著特征,只有如此,才能將相類似的事物區分開來。如“牛”、“羊”二字的構形就突出了牛角和羊角一個向上彎、一個向下彎的特點,從而使二字的形體有了明顯的區別。“母”字的構形之所以突出兩乳,也是出于與其他字符相別異的考慮,因為“女”字所表示的母親和“女”字所表示的女子在外形上很難區別,除了母親的乳房比一般女子較為發達外,其他特征很難在字形中體現出來,于是,古人便在“女”字的基礎上加上表示乳房的兩點,作為“母”字的構形。這種構形,既保持了與“女”字的聯系,又體現了與“女”字的區別,顯然是為了滿足漢字構形系統性特征的需要,而不是為了表示什么生殖崇拜。可見,漢字是一個具有嚴密系統性的符號體系,每個字符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受整個系統制約的。因此,我們不能為了一時方便而胡亂講字,否則就會造成講了一個亂了一片的嚴重后果,給讀者造成困惑。
總之,“漢字文化必須建立在科學的基礎上,不能違背漢字的發展規律,也不能違背文化的發展規律。漢字文化學是科學,不是幻想,更不是個人無根據的聯想和猜測。”[9]漢字構形確實蘊涵著豐富的文化內涵,在文化研究方面具有極大的參考價值。但是,我們在研究漢字文化時,一定要用科學的理論來指導,用謹慎的態度去操作,要樹立正確的漢字文化觀念,準確把握漢字文化功能的量度,合理分析漢字的構形;要明確漢字文化研究所要達到的目的,弄清漢字文化研究所要解決的問題以及能夠解決什么問題,正確認識漢字文化學方法的適用對象,避免出于趕時髦心理的隨意濫用。只有這樣,才能使漢字的文化功能得到正確的體現。不過,要想做到這一點并不容易,既需要有堅實的漢字學功底,又需要有較高的文化學修養,兩個方面缺一不可。
【參考文獻】
[1]陳澧.東塾讀書記[M].上海:商務印書館,1930.
[2]王寧.漢字與文化[J].北京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1(6).
[3]王寧,等.《說文解字》與漢字學[M].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00.
[4]李逢甫.漢字的文化積淀[J].黔東南民族師專學報,1996(3).
[5]陳建民.語言與文化漫話[J].宏觀語言學,1992(1).
[6]何毓玲.從《說文·女部》窺古代社會之一斑[J].古漢語研究,1996(3).
[7]殷寄明.從女偏旁字看古代婦女的尊卑嬗變[J].杭州師范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3(5).
篇11
從歷史上的紫砂大家來看,紫砂壺從原創性和人文性都有著共同的起伏,每一件經典作品都有著它獨有的原創性和人文性,有著那個時代的時代氣息。隨著時代的變遷,對于紫砂設計的觀念也在不斷變化。以經典的“石瓢”壺為例,“石瓢”最早稱為“石銚”,“銚”在《辭海》中釋為“吊子,一種有柄,有流的小烹器”。“銚”從金屬器皿變為陶器,最早見于北宋大學士蘇軾《試院煎茶》詩:“且學公家作名欽,磚爐石銚行相隨”。坡把金屬“銚”改為石“銚”,這與當時的茶道有著密切的關系。因為在宋朝初期,飲茶方法依舊遵循唐朝時期的古法,多為烹茶或煮茶,而之后隨著時代的發展,宋朝茶肆文化盛行,茶肆成為了一種公共娛樂場所,甚至出現了專業的從業人員,《水滸》第十八回:“宋江便道‘茶博士,將兩杯茶來。其中的“茶博士”便是指的此類人員,飲茶大眾化導致了飲茶方式的改革,原本貴族式的金屬茶具自然衍變成平民化低成本并且容易批量生產的陶器,久而久之便造成了茶壺名稱的變化。由此可見,壺式造型的原創性,其實是與其中蘊含的文化內涵息息相關的。
篇12
一、引言
漢語文言作為國學的載體,在我國文化中有著重要而獨特的地位。在中國文化“走出去”的過程中,優化文言文的翻譯,對于讓世界更好地理解我國傳統文化有著極大的助益。但漢語文言作為一種在秦時就已經基本定型的書面語,與現代漢語差別較大,即使在古代,也更多的是一種身份,文化的象征。簡潔而注重對仗,駢驪,用典以及音律工整的漢語文言本身也有著其特有的魅力,很多漢語文言文讀來十分精彩,但譯成現代漢語便索然無味。一般對漢語文言文的英譯,基本與文言文譯成現代漢語之后,再對現代漢語譯本進行英譯并無二致。也即是說,文言本身的風神蕩然無存。讀者在閱讀這類英譯的時候,已經很難從文本上識別其是否屬于中國傳統文化的范疇。而在16-17世紀的早期現代英語(Early Modern English)與現代英語近似,卻又保留了一些古英語的特征,但在閱讀上不會產生嚴重障礙,將漢語文言文英譯成為早期現代英語,“以古譯古”,能夠體現出漢語文言古樸簡潔等特點,又能提高我國傳統文化在“走出去”過程中的辨識度,不失為一種有效的方法。
二、以《孟子》的英譯為例看當前文言文翻譯的現狀
位列“四書”之中的孟子是儒家極具代表性的一部經典,美國總統奧巴馬曾經在首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開幕式上引用了《孟子?盡心下》中的一句“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為間不用,則茅塞之矣。”而其選用的英譯為‘Mencius said to KauTzu: A trail through the mountains, if used, becomes a path in a short time,but, if unused, becomes Blocked by grass in an equally short time. Now your Heart is blocked by grass.’該版本的譯文是企鵝出版社于1970年首版,由香港學者劉殿爵(D.C.Lau)所翻譯。然而最早翻譯《孟子》的是意大利耶穌會士利瑪竇(Matteo Ricci, 1552 -1610),他于1594年(明萬歷二十二年)完成了《中國四書》的拉丁語翻譯,今已亡佚。最早英譯《孟子》的是英華書院第三任校長英國人柯大衛(David Collie, -1828)完成的,同利瑪竇一樣,他也完成了《四書》的翻譯,《孟子》作為其英譯《四書》其中的一章。此后英國著名漢學家理雅各(James Legge, 1814 -1897)的《孟子》英譯本于1861年出版。理雅各本人對于中國傳統典籍有較為系統的認識與較為深刻的理解,他英譯的《孟子》內容翔實,忠于原文,并添加了大量注釋輔以理解,目前是最具有權威的《孟子》英譯本。由加拿大多倫多大學中文教授杜百勝(W.A.C.H.Dobson)完成,1963年首版的英譯《孟子》被收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代表作品集/中國系列》。此外,20世紀,英國學者翟林奈(Lionel Giles),英國漢學家蘭雅(Leonard.A.Lyall),哈佛大學漢語副教授詹姆士? 威爾(James.R.Ware),翟楚(Ch'u Chai)、翟文伯(Winberg Chai)父子都曾英譯過《孟子》。
但在這些譯本中,無論譯者身份是中是外,雖然用詞,句式甚至風格各異,但是都達到了表意的效果。《孟子》中原句所要表達的意思,已經在譯文中充分得到了體現。但是源本中文言文的風格卻鮮有保留。如果將這些譯本回譯,恐怕結果更容易是“山間的小路,走的人多了,就成了路,一段時間走的人少了,就會遍布荊棘,現在你的心里便滿是荊棘”而與更為簡潔古樸的原文“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為間不用,則茅塞之矣。”相去甚遠。錢鐘書先生曾提出翻譯的“化境”之說,即“ 文學翻譯的最高理想可以說是‘化’。把作品從一國文字轉換成另一國文字, 既能不因語文習慣的差異而露出生硬牽強的痕跡,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風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 ”。以上幾種譯文,“信”“達”兼備,“雅”亦不差,雖沒有“露出生硬牽強的痕跡”,但在“完全保存原作的風味”上卻欠佳。已然美,但仍不至盡善盡美。
此外,中國傳統文化典籍中的一些觀念因為囿于年代的限制,有些已經不在適用于現代社會。而在全球化進程日益加快的今天,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的深度,廣度,頻率與理雅各等人所處的時代相比,已經不在一個量級。各語種之間轉譯的現象也頗為頻繁。英語作為世界上使用最廣泛的語言,通常在轉譯過程中充當兩種或多種文化交流的媒介。如斯賓諾莎(Baruch de Spinoza)《神、人及其幸福簡論》的轉譯過程是:拉丁文-荷蘭文-英文-中文;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夢的解析》的轉譯過程是:德文-英文-中文;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悲劇的誕生》的轉譯過程是:德文-英文-中文。因此,中國傳統典籍的英譯本在中國文化向世界傳播的過程中起著頗為重要的作用。而在漢語文言文的英譯過程中,由于自身風味的佚失,導致讀者不能根據像國內讀者一樣根據文本的風格判斷其時代,判斷其是否出自中國傳統文化。諸如“老而不死是為賊”“死生有命,富貴在天”等思想,如果在文化傳播過程中,讀者沒有正確地判斷這些思想產生的年代,誤以為這是中國當代人的思想觀念,則會造成不必要的誤解。因此,文言文英譯保留文言文本身的“風味”,在當今世界文化交流中的意義非凡。
三、“以古譯古”方法使用早期現代英語的優勢
1.早期現代英語與后期現代英語的區別
現代英語一般指從1500年至今的英語,其中又大致以1700年為界,十六,十七世紀的英語被稱為早期現代英語,其后則為后期現代英語,即當代英語,1700年之后英語的語法,語音已經較為穩定,只有詞匯在不斷地擴充。早期現代英語作為英語從古英語到現代英語的過渡階段,既保留了古英語的一些特點,又能夠為現代的讀者所理解。著名的英王詹姆斯欽定版圣經(KJV, King James Version)即是用早期現代英語寫成,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的戲劇也是早期現代英語的作品。由于《圣經》英譯本較多,且大多是當代英語譯本,如NIV(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RSV(Revised Standard Version)因此借助不同版本圣經的比較,能夠顯而易見地看到早期現代英語與當下我們使用的后期現代英語的區別。由于早期現代英語與后期現代英語細節上的區別較多,此處僅列舉一些早起現代英語較為明顯,在“以古譯古”方法中可以利用的部分特點。
1.1人稱多保留古英語形式
Saying, Thou wentest in to men uncircumcised...(KJV Act11:3)
and said, "You went into the house of uncircumcised men..."(NIV Act11:3)
...for great is the Holy One of Israel in the midst of thee.(KJV Isaiah12:6)
...for great is the Holy One of Israel among you.(NIV Isaiah12:6)
For ye have heard of my conversation in time past in the Jews' religion...(KJV Galatians 1:13)
For you have heard of my previous way of life in Judaism...(NIV Galatians 1:13)
上文中出現的Thou, Thee, Ye等是古英語,現代除了詩歌,贈言等之外,已基本不用。但早期現代英語還大量保存了這些用法。它與當代英語的區別主要體現在第二人稱上。早期現代英語中,第二人稱單數主格用thou,第二人稱復數主格用ye,第二人稱單復數賓格用thee,而當代英語中以上幾種情況都用you.第二人稱單數所有格用thy或thine,今為your.
1.2動詞詞尾屈折變化
When thou art bidden of any man to a wedding...(KJV Luke14:8)
"When you are invited by any one to a marriage feast...(RSV Luke14:8)
Thou hast indeed smitten Edom, and thine heart hath lifted thee up: glory of this, and tarry at home: for why shouldest thou meddle to thy hurt, that thou shouldest fall...(KJV 2Kings 14:10)
You have indeed smitten Edom, and your heart has lifted you up. Be content with your glory, and stay at home; for why should you provoke trouble so that you fall...(RSV 2Kings 14:10)
早期現代英語在動詞詞尾變化上與當代英語有較大的差別。當代英語只有在第三人稱單數作主語,動詞的現在分詞才會出現詞尾變化,且對情態動詞不適用。但在早期現代英語中,在第二人稱單數,第三人稱單數作主語時,動詞的現在分詞詞尾都會產生屈折變化,對情態動詞也適用,并且在第二人稱單數作主語的情況下,動詞的過去分詞也要產生相應的詞尾變化,如didst。接第二人稱單數主語動詞的詞尾變化一般為-st或-est,個別情況會出現-t,如hast(have),shouldest(should),shalt(shall)接第三人稱單數主語動詞的詞尾變化一般為-th或-eth,如hath(have), droppeth(drop)系動詞are的第二人稱單數現代分詞形式一般為art,形成一個固定搭配Thou art.
1.3否定句式
For the poor always ye have with you; but me ye have not always.(KJV john12:8)
The poor you always have with you, but you do not always have me."(RSV John 12:8)
當代英語的否定句式一般要借助助動詞do,而早期現代英語一般直接在動詞后加not來構成否定句。
1.4介詞Unto的使用
These things have I spoken unto you, that ye should not be offended. (KJV John16:1)
I have said all this to you to keep you from falling away.(RSV John16:1)
當代英語中的介詞to在有些情況下早期現代英語中用unto代替,出現固定搭配如say unto sb. speak unto sb.等
1.5一些常用詞的變化
And whither I go ye know, and the way ye know.(KJV John 14:4)
You know the way to the place where I am going. (NIV John 14:4)
早期現代英語中一些常用詞和習慣用法,現代已經很少見到,甚至不再通用。如behold,whosoever,whither等。
2.以早期現代英語英譯漢語文言文的優勢
2.1能更好保存原作的“風味”
正如提到文言文,人們首先會想起的是孔孟老莊一樣,提起早期現代英語,人們首先想到的會是文藝復興時期的那些文學大家與文學經典,如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斯賓塞(Edmund Spencer)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英語文藝復興在英語文化圈中的影響不亞于“百家爭鳴”時期對中國文化的影響。這一時期的英語已經確立了新的語法系統,但是還是保留了很多古英語的痕跡。讀早期現代英語,正如讀漢語文言文一樣,可以感受到一種古樸的風格,但又不至于產生閱讀障礙。借助早期現代英語,可以使文言文的英譯在“形似”上更進一步,更多地保留文言文原作的“風味”。
2.2提高文言文英譯本的辨識度
雖然早起現代英語今天閱讀上不像古英語那樣難以理解,但早期現代英語與當代英語的差別還是比較明顯。讀者在閱讀早期現代英語翻譯的文言文譯本的時候,無需注釋就可以自然地判定這些文本出自古代,避免了一些誤解的產生。
2.3有利于漢語文言的“走出去”
漢語文言雖然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有著很高的地位,是中國傳統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是作為一種文化的載體,在中國文化走向世界的過程中,文言卻難以向外推廣。這也導致很多漢學愛好者無法更多了解文言文(Classical Chinese),無法認識中國傳統文化之全貌。“以古譯古”的方法,借用與漢語文言文有更多相似性的早期現代英語,可以提高漢語文言的存在感,為向世界介紹漢語文言提供了一個契機。
四、“以古譯古”方法的具體運用
由于“以古譯古”的目的在于更多地在英譯時還原漢語文言的風味,而不是寫出嚴格符合早期現代英語語法,用詞習慣的文章,并且首先要注重的是譯文的“信”與“達”。因此在使用早期現代英語英譯文言文的時候,對早期現代英語的特點要有所保留。一些古英語詞語,今天不再通用的,譯文不宜采用。即要在保證譯文信實于原文,表達通暢,易于理解的基礎上來還原漢語文言的“風味”,切忌舍本逐末。
魯迅先生曾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提出“硬譯”與“寧信而不順”的歐化翻譯觀,旨在在特殊歷史時期“引進并吸收外國的東西, 完善中國的文法”“改變國民的思維方式, 促使國民覺醒, 從而實現救國的目的”而在全球化大背景下的今天,漢語文言的英譯,也可適當采取異化策略,進行“漢化”,以達到魯迅先生所說的“求其易解, 保持豐姿”的效果,更接近錢鐘書“完全保存原作的風味”的化境。
例如《孟子》開篇《梁惠王章句上》第一句“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更偏向于歸化策略的理雅各譯本的翻譯是:
Mencius went to see King Hui of Liang. The King said,‘Venerable sir, since you have not counted it far to come here, a distance of a thousand li, may I presume that you are provided with counsels to profit my kingdom?’
理雅各的譯文不僅信實于原文,而且歸化得生動形象。如果采用異化的翻譯策略,使用”以古譯古“的方法,則譯文大致為:
Mencius went to see King Hui of Liang. The King saith unto him,‘Thou hast traveled from afar to come here, a distance of a thousand li, broughtest thou anything to profit my kingdom?’
筆者翻譯水平有限,與理雅各自然不可同日而語。但可以看到“以古譯古”的英譯更為簡潔,也更加具有漢語文言古樸的風味。以錢鐘書的“化境”說為標準,以“以古譯古”方法英譯漢語文言文,在“保存原作的風味”方面將更勝一籌。
五、結語
在不同歷史時期,翻譯的手段由翻譯的目的決定,為了吸收西方文化,促使國人覺醒,魯迅先生提出了“歐化”的翻譯觀。而在今天各種文化交流日益的今天,如何克服文化之間的差異,讓中國文化以一種更“中國”的姿態走出去,是我們必須考慮的問題。“以古譯古”的方法目的就在與在信實,通暢,易懂的基礎上,拓展“異化”在文言文英譯上的使用,更多保留原文的風味,讓文言文的英譯也能體現出漢語文言的特色。
參考文獻
[1]楊伯峻. 中國古典名著譯注叢書:孟子譯注[ M ]. 北京:中華書局, 2010
[2]錢鐘書. 錢鐘書散文[ C ] . 杭州: 浙江文藝出版社, 1997
[3]Legge, James. The Chinese Classics[ M ]. Taipei:SMC Publishing Inc,1991
[4]Collie, David.The Chinese Classical Work Commonly Called The Four Books[ M ] . Florida: Gainesville,1828
[5]Dobson, W.A.C.H.Mencius[M] .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69
[6]楊穎育.從奧巴馬引用孟子看《孟子》英譯[A].西南科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12
篇13
(一)靜態美。追溯到緣故的倉頡,漢字就是依類象形,先有其形后有其聲。我們的祖先經過對萬事萬物仔細的觀察進而用“漢字”將其描述。漢字的靜態美我們來說說它的具象美。漢字的具象美可以包括音律美和字形美。首先我們來說一下音律美。漢字的音節相互之間非常獨立,有著很強的節奏感,音節與音節之間抑揚頓挫,另外漢字之間的清音重音相互交替,平仄變化有致,給人以很強的韻律感,很強的音樂美。另外是當漢字相互在一起構成句子和文章,那么音律美更是體現得淋漓盡致。對仗,押韻,疊印、排比等多種多樣的修辭手法的運用,更是增強了漢字的音律美。下面我們說說字形美。漢字筆畫橫豎撇捺等等筆畫千變萬化,相互結合之后如同一幅美麗的畫面。漢字的結構就充滿了美感,如同建筑結構一樣,既有結構美也有自然美,給人一種自然而然的享受。也正是漢字的這種充滿美感的節奏更是促生了書法這一充滿著藝術感的項目。漢字不僅僅有著象形之美,更是有著會意之美,通過給人以無限的遐想,給人以無盡的美的享受。我們就以“美”作為例子,一只肥嫩的羊羔,讓人想著就喜歡,這是多么美:視覺上聯想到了羊羔的肥壯,味覺上給人以羊肉肥膩的感覺,觸覺上也有著羊毛溫暖的感覺。漢字的字形美其實反映著中華民族的追求美的民族特性。
(二)說完漢字的靜態美我們再來說說漢字的動態美。我們將從字義美和生命美兩個方面進行說明。
漢字是對自然界萬物萬事進行抽象之后的結果,自然界的萬事萬物就是美的本身,毋庸置疑,漢字以自然界為基礎更是充滿了字形美。這是漢字字義美的基礎。漢字在經過千年的時間洗禮和沉淀,在歷史的前進中不斷的被賦予各種含義,其實在這個過程中漢字慢慢的被賦予了一種精神、被賦予了一種生命。漢字之中被賦予的文化內涵,就是體現著漢字的美。
二、漢字教學之中的漢字之美
(一)漢字本身的美感。漢字本身所帶有的美感我們在上文中其實已經有著較多的說明。在語文教學過程之中,學習漢字的字形之美,漢字的結構,漢字的變化,漢字的音律等等都可以給人以無限的聯想。我們在進行語文教學過程中,如果回避漢字的本身之美,那么這樣的語文是不完整的。
(二)漢字之中的文化美。漢字的本身之美是一方面,更有意思的是漢字之中的文化美。作為文化的載體,學習漢字之美其實就是學習文化之美。在語文教學過程中,怎么可能不談漢字的字里行間所流露的文化。
漢字之中其實流露中天人合一的思想。學習漢字的文化美,我們可以更好的把握中華文化。漢字的象形來源于自然,經過發展像自然界一樣勃勃生機,無限繁衍。中國歷史上雖然也經歷過大分裂時期,但是卻最終沒有四分五[專業提供論文寫作的服務,歡迎光臨 dylw.NET第一論文 網]裂,很大的原因就是中華文化將中華民族凝聚,漢字將中華民族聯系在一起,如同自然一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誰也離不開誰。
漢字所流露的文化美還有漢字所表現的意境。“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這些漢字之中并沒有寫離別,但是這卻給人營造了無限的離別的悲傷氛圍,這就是漢字的魅力,這就是漢字的魔力,可以創造無限的可能。我們在語文教學中怎么可能會忽略這些呢?
總之,漢字文化是漢字在自身的長期衍生中所形成的獨特品質,包括漢字本身所蘊涵的特征來源、形象意義及漢字所反映出來的社會生活和思維方式等一系列精神和物質上的東西與中華文明一脈相承。近三年漢字教學研究的成功經驗告訴我們,扎實有效的漢字教學不僅會讓我們的學生遠離錯別字,更會讓學生在充滿濃濃文化味的語文課堂上受到靈魂的浸染。我們可以設想,當閃爍著人性光芒的語言光照學生心底時,當語言成為流淌過學生心靈的音樂時,那正是我們民族的語文素養應該達到的高度。在語文的教學中,我們應該積極的挖掘漢字的魅力,發現其中蘊含的無限的美。當我們理解了漢字的美,也就理解了中華文化的美。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