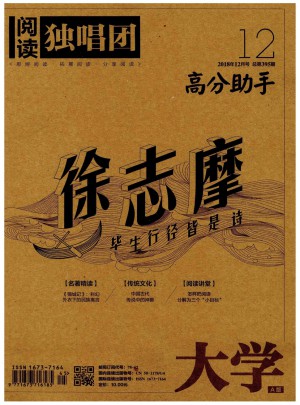引論:我們?yōu)槟砹?3篇大學生勞動教育論述范文,供您借鑒以豐富您的創(chuàng)作。它們是您寫作時的寶貴資源,期望它們能夠激發(fā)您的創(chuàng)作靈感,讓您的文章更具深度。
篇1
古往今來,許多西方大教育家將德育、智育、體育、美育、勞動教育并舉,表現(xiàn)出對體育教育和體育鍛煉的重視。古希臘三哲亞里士多德、蘇格拉底和柏拉圖對體育教育均有獨到的見解;而楊·阿姆司·夸美紐斯、讓·雅克·盧梭、約翰·洛克、裴斯泰洛齊、赫伯特·斯賓塞、伊·阿·凱洛夫等大教育家也有發(fā)人深省的體育教育思想。以上教育家的思想共識即為:體育應為“德育、智育、體育、美育、勞動教育”等“五育之首”,是人們生存、生活、工作、娛樂、發(fā)展的基石。
亞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公元前322)認為,體育鍛煉可以培養(yǎng)勇氣,身體的訓練應在智力訓練的前面。體育訓練的目的不是為了競技,不應該像斯巴達人那樣通過兒童勇敢地艱苦操練而變得殘忍,應該把高貴的東西而不是獸性的東西放在首位。體育在人們不同的教育階段包括不同的內容:在幼兒教育階段主要是通過游戲、飲食來發(fā)展兒童身體;初等教育階段主要是通過體操訓練形成人健美的體格、勇敢和良好的習慣。亞里士多德的觀點趨向于體育不能落后于智育。
蘇格拉底(Socrates,公元前469-公元前399)認為,身體健康在平時是有用的,因為人們做一切事情都需要用身體,要盡可能使身體保持健康的狀態(tài)。而在戰(zhàn)時,身體健康就更為重要。即使在思維活動中,健康的身體也是必要的,許多人“由于身體不好,健忘、憂郁、易怒,就會影響他們的神志,以致他們把已獲得的知識遺忘殆盡。”[1]蘇格拉底要求每個人的身體能忍受嚴寒、酷熱、饑渴、疲勞困頓,以便能適應各種環(huán)境;常常“竭力勸勉他的門人,要注意身體健康。一方面要盡量向那些知道怎樣保持健康的人學習,另一方面?zhèn)€人自己也要一生一世注意……”[1]蘇格拉底自己經常鍛煉身體,準備應付身體可能面臨的任何考驗。他每天早上都到廣場去體育鍛煉,因此培養(yǎng)了自己忍受饑餓寒冷、疲勞的驚人能力。[1]蘇格拉底能夠最終成為古希臘三哲之一,重視體育鍛煉,摸索健身方法起到了重要作用。
柏拉圖(Plato,公元前427-公元前347)曾提出“先音樂教育,后體育訓練”的主張,他把音樂和體育并舉,在當時是非常難能可貴的,也指明了體育鍛煉在人們個體發(fā)展中的重要性。“身體最強健的人不容易受飲食或勞作的影響,最茁壯的草木也不容易受風日的影響。”[2]
楊·阿姆司·夸美紐斯(JohannAmosComenius,1592-1670),17世紀捷克著名的愛國主義者,偉大的民主教育家。在論教育的作用和目的時,夸美紐斯強調人的身心是和諧的,他說:“人的本身,里外都只是一種和諧。[3]”教育的目的就是培養(yǎng)在身體、智慧、德行和信仰幾方面和諧發(fā)展的人。中世紀的基督教神學世界觀認為“肉體是靈魂的監(jiān)獄”,鼓吹實行禁欲主義,通過折磨肉體來拯救靈魂。夸美紐斯的觀點與此正好相反,他認為:“身體不獨是推理的靈魂的住所,而且也是靈魂的工具[3]”,因此十分重視保持身體的健康強壯,要求家庭和學校都應注意使兒童的生活與學習有規(guī)律、有節(jié)制,合理安排運動與休息。該觀點也符合現(xiàn)代運動訓練理論中的恢復機理。
約翰·洛克(JohnLock,1632-1704),17世紀英國著名的實科教育和紳士教育的倡導者。他在論述紳士教育時對體育非常重視,在《教育漫話》中一開篇就說:“有健康的身體,才有健康的精神。”“健康之精神寓于健康之身體……凡是身體精神都健康的人就不必再有什么別的奢望了;身體精神有一方面不健康的人,即使得到了別的種種,也是徒然。”“我們要能工作,要有幸福,必須先有健康;我們要能忍耐勞苦,要能出人頭地,也必須先有強健的身體。”[4]他為了培養(yǎng)健康的紳士,根據他的醫(yī)學知識,擬定了一個鍛煉紳士體格的體育保健制度,對兒童的衣、食、住、行都提出了具體要求,以此達到把紳士鍛煉成能拿起武器去當兵的標準,使他們能夠有一個忍耐勞苦的強健體魄。他所提出的各種保護與鍛煉身體的體育衛(wèi)生的要求,基本上是切合實際的;他關于體育的見解,內容十分豐富,新穎而系統(tǒng),對當今學校體育衛(wèi)生管理和家庭體育衛(wèi)生管理都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讓·雅克·盧梭(JeanJacquesRousseau,1712-1778),作為18世紀法國啟蒙運動中最激進的思想家,盧梭在《愛彌兒》中表達出了自然主義的教育思想,被譽為教育史上的哥白尼。盧梭想象的自然人是身心調和發(fā)達的人,是運動敏捷、身手協(xié)調的人,所以身體的養(yǎng)護和鍛煉被視為兒童教育最基本的組成部分,而這種養(yǎng)護和鍛煉其實質就是具有身體練習的體育。盧梭對于當時輕視身體健康的流俗主張給予無情的駁斥。首先,他認為惟有健康的體魄才能使人忍耐疾苦,勤于工作,獲得幸福和延長壽命。他說:“體質愈衰弱,欲求愈迫切;而體質愈強壯,便越能忍耐。一切肉體的都產生于體質軟弱的人;他們愈不能得到滿足,他們的痛苦也愈強烈。”[5]又說:“幾乎所有長壽者,都是出于從事多量體格鍛煉而能忍受疾勞和工作的人。”[5]其次,盧梭認為健康的身體是理性發(fā)達的基礎。他認為:“身體要相當的健康,以便聽從心靈的支配;正好似好的仆役必須是健康的。”[5]并指出:“以為身體的活動會妨礙心靈的活動,那是一樁絕大的錯誤。仿佛二者不能聯(lián)合并進,也仿佛心智活動不愿意去作行為的指導一般。”[5]所以“你假如要培養(yǎng)兒童的智力,你應當培養(yǎng)那智力所要控制的體力。為了使兒童良好而慧敏,你要給他的身體以不斷的鍛煉,使他的身體強壯而健康;你要讓他工作,讓他做事,讓他奔跑和喊叫,讓他永遠活動;使他成為有體力的人,他不久就成為有理性的人了。”[5]再次,好的身體是優(yōu)良品德的基礎。盧梭說:“霍布斯稱邪惡之徒是健壯的兒童,是不符合事實的。一切邪惡皆由體弱而生;兒童因為體弱才令人厭惡;設法使他們強壯,他就變好了;因為假如我們什么事都能做,我們一定不做壞事。”[5]盧梭把體育和鍛煉當作教育的主要內容,旗幟鮮明地指出了“體育先于智育”,有別于我國現(xiàn)在的“德育、智育、體育全面發(fā)展”。
裴斯泰洛齊(Johan Heinrich Pestalozzi,1746-1827),19世紀瑞士著名的民主主義教育家。裴斯泰洛齊認為,不僅要發(fā)展人的道德和智慧,還應發(fā)展人的身體力量,因為體育和德育、智育及勞動教育是緊密聯(lián)系的;人的認識能力、實踐能力的基礎都蘊含在人身體的發(fā)展之中。他認為體育的任務,就是要把所有潛藏在人身上的天賦的生理上的力量,全部發(fā)展出來。他說:“眼睛要看,耳朵要聽,腳要走路,手要抓物”,以致人的整個身體能要求通過各種活動得到發(fā)育成長。這種活動從小就在進行著,如從手抓、腳蹬、走動、伸舉到“打擊和搬運,戳刺和投擲,拖拉和旋轉,圍繞和擺動等等[6]”都可使體力得到發(fā)展。這些“體力表現(xiàn)形式雖各不相同,但是或合或分,都蘊含著一切可能的行動的基礎,乃至蘊含著構成人類的各種職業(yè)的最復雜的行動的基礎。”[7]而這些簡單的體力表現(xiàn)形式的基礎,則是自然所賦予的關節(jié)活動的能力。因而他提出了各種關節(jié)的活動應是體育最簡單的要素;體育應該從兒童的早期開始,學校的體育活動應該是多種多樣的。裴斯泰洛齊對體育的認識落腳于一個“力”字。
赫伯特·斯賓塞(HerbertSpencer,1820-1903)對體育也很重視,他是19世紀后半期至20世紀開始時期的英國著名社會學家、哲學家和教育家。他認為,由于每個人的利益(幸福)和現(xiàn)代生活日益增加的競爭,都需要體育;一個民族的繁榮、戰(zhàn)場上的勝負、商業(yè)上競爭的盈虧,都與人的身體強弱有關;女孩和男孩同樣需要體育。在《體育》一文中,他從體育理論論述到人體的養(yǎng)護與鍛煉:“身體即是心智的基礎,要發(fā)展心智就不能使身體吃虧。”“長期的身體毛病使最光明的前途蒙上陰暗,而強健的活力就使不幸的境遇也能放金光。”[8]因此,他要求讓兒童多運動、多游戲,他認為游戲和競技比體操更重要。他提倡自然的身體鍛煉,反對人為的體育制度,在學習方面,主張不能讓學生過分疲勞;改變當時學校那種兒童由于體力衰弱,時常被迫離開學校,功課繁多,教師苛求,以致學生不得不以一天12到13小時的時間致力于學習的現(xiàn)象。他說:“當用心大為過度的時候,結果就嚴重得更厲害,不只影響身體的健全,也影響到腦本身的健全。”“身體健康下降是學習過度的后果,……硬塞知識的辦法該受到多么嚴厲的譴責。”[8]斯賓塞對體育教育的重視也構成了他的五大部分課程體系的第一部分:開設生理學、解剖學。這是闡述生命和健康直接保全自己的知識。在斯賓塞看來,這是最重要的一部分。
伊·阿·凱洛夫(1893~1978),上世紀四五十年代很有影響的蘇聯(lián)教育家。他主編的《教育學》于蘇聯(lián)第二次教育改革時期問世。從那時起,他的教育理論一直成為蘇聯(lián)傳統(tǒng)的教育指導思想。凱洛夫在《教育學》第十六章《體育》中論述了體育教育的重要性:“體育是增進青年健康,發(fā)展他們的體力和各種能力的必要條件。”“體育的任務是使學生的身體獲得發(fā)育,使它變得結實健壯,有堅忍和持久的力量,并且要發(fā)展學生的靈活而美觀的動作。”[9]這已經從理論的高度提到了體育的概念、任務和外部條件,為后來體育基本概念的形成和發(fā)展奠定了基礎。
二、諸家體育思想對我國學校體育的啟示
通觀以上多位西方有代表性的教育大家的體育教育思想,不難發(fā)現(xiàn)體育對于他們一生的重要性。通過對他們主要體育思想的溯源和探析,可以得到以下幾點基本啟示。
1.學校體育教育應坐擁真正意義上的“五育之首”
以上多位著名教育家的教育思想中,無一例外地將體育教育列在“五育之首”。早在1917年4月1日,用筆名“二十八畫生”在《新青年》第三卷第二號上發(fā)表的《體育之研究》指出:“體育一道,配德育與智育,而德智皆寄于體,無體是無德智也。……體者,載知識之車而寓道德之舍也。”“體育于吾人實占第一之位置,體強壯而后學問道德之進修勇而收效遠。”[10]在這里,青年已將體育提至了德育、智育、體育、美育、勞動教育等“五育之首”,可見體育在教育環(huán)節(jié)中的重要地位。
2.學校體育教育中應改變重文輕武的辦學思想,嚴格按照國家有關規(guī)定重視和加強體育教學
在當代體育教學中,盡管《學校體育工作條例》、《學生體質健康標準》等法規(guī)文件對體育課、體育考試及體質健康標準測試都有明確規(guī)定與要求,但在實際操作中,規(guī)章制度形同虛設,沒有得到嚴格執(zhí)行。長此,學生間流傳“體育課學好學壞一個樣”,“學與不學一個樣”,這實質上既是我國學校體育教育的悲哀,更是整個教育制度的悲哀。學校乃至社會對體育教育的輕視,必然導致學生體育鍛煉意識的淡薄,更無法養(yǎng)成良好的體育鍛煉習慣。因此,要徹底改變此種現(xiàn)狀,學校應逐步廢止應試教育,根除淡化重文輕武現(xiàn)象;必須嚴格按照國家有關制度,制定具體落實細則。只有有了相應的規(guī)章制度的制約并嚴格規(guī)范管理,才能保證體育工作的質量,才能逐步規(guī)范和完善我國學校體育教育工作。
3.在學生鍛煉意識培養(yǎng)方面,應將提高學生的體育興趣
作為引導學生形成體育鍛煉意識的主要途徑。興趣是最好的老師,前面我們所列舉的西方大教育家的體育思想,無一例外地重視提高對體育的興趣,這對于我國今天的體育教學仍有非常積極的指導作用。但是這里所說的提高學生興趣并不僅僅停留在學生簡單地動一動就可以了,而是要求學生要較好地掌握運動技術,不斷提高運動技能,學習掌握鍛煉方法。在體育教學過程中,課程的內容和形式應進一步豐富和多樣化;要加大培養(yǎng)學生技能和技巧的力度,提高學生的運動能力。學生有著較好的運動能力和運動技術并且掌握2-3項特色和具有一定優(yōu)勢的運動項目,對他們在今后的生活中養(yǎng)成體育鍛煉的習慣有著重要的促進作用。此外,教師還要積極引導學生去觀察思考體育鍛煉對身心的各種功能,使其從根本上認識到體育鍛煉對增進健康、緩解壓力、塑造健全人格的重要作用,從而形成由自發(fā)到自覺的體育鍛煉習慣。
參考文獻
[1] 色諾芬.回憶蘇格拉底.北京:商務印書館,1986.
[2] 柏拉圖.文藝對話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3.
[3] 夸美紐斯.大教學論.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
[4] 洛克.教育漫話.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57.
[5] 盧梭.愛彌兒.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
[6] 張煥庭.西方資產階級教育論著選.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
[7] 裴斯泰洛齊.裴斯泰洛齊教育論著選.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