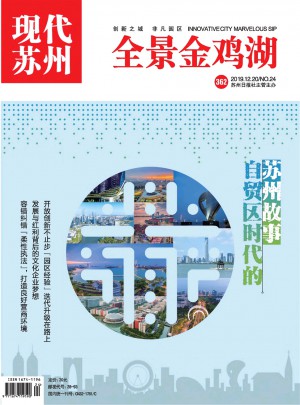引論:我們為您整理了13篇現代主義繪畫論文范文,供您借鑒以豐富您的創作。它們是您寫作時的寶貴資源,期望它們能夠激發您的創作靈感,讓您的文章更具深度。

篇1
人們過去并未意識到兒童隨意而愉快的涂抹有什么特殊意義,更談不上對兒童藝術的發現及關注,然而,隨著人類藝術史上對兒童藝術的發現及現代藝術的產生,兒童藝術在當代藝術世界的位置正日益凸顯。現在,“兒童藝術”已是被普遍接受的概念,兒童藝術中那種形象的簡化、畫面的和諧、富有表現力的線條、大膽的純色平涂以及那種無意識的創作狀態,使得西方現代藝術家懷著新奇的目光從兒童藝術中汲取營養。
二、西方現代主義藝術大師對兒童藝術的認識與評價
兒童的作品究竟有何魅力?為什么會吸引全世界藝術家的目光?在兒童藝術中,兒童常常以其天真率直的心態每每使我們拍手稱快,是任何人為的方法都無法企及的。兒童藝術是無意識下創作的作品,是兒童心智和心緒的自然流露,往往呈現著藝術創作最初的也是最純粹的源泉。其構圖造型稚拙有趣,似無法之法,有意想不到的生動。正如黑格爾所說:“兒童是最美好的,一切個別特殊性在他們身上好像都還沉睡在未展開的幼芽里,還沒有什么狹隘的東西在他們的胸中激動,在兒童還在變化的面貌上,還看不出承認繁復意圖所造成的煩惱,因而在兒童繪畫里表現出來的是他們對事物無意識的、天真率直的看法。”兒童藝術更具創造性和表現性,注重個人感受。兒童天性充滿熱情,能主動、自由地表現畫面,兒童看世界有他們自己的獨特眼光,他看起人來,只看到一個人的一個大頭,頭上的兩只眼睛,一個鼻子,一張嘴巴,什么耳朵、頭發、眉毛,他都沒有看見,所以他不畫一個人的身體,他看得不重要,只畫一條線來表示。這些入眼的觀察對象在兒童的心目中形象分外鮮明。兒童是畫其所想而非畫其所見,因此兒童畫出的作品往往想象豐富,用色大膽,富有生氣,有更多的靈性。西方現代派藝術中,反叛傳統,追求單純和質樸無華是其共同的目的和重要特征,因此,現代藝術家們不約而同地將目光投向了兒童藝術,而且給予兒童藝術以高度的評價,甚至對兒童的藝術狀態和兒童的藝術作品崇拜不已。現代藝術大師畢加索曾說過:“我曾經能像拉斐爾那樣作畫,但我卻花了畢生的時間去學會像兒童那樣作畫。”這在當時是很有代表性的。其實這種對兒童藝術的新的認識和評價在野獸派那里已有所表現。康定斯基崇拜兒童藝術是因為他認為兒童藝術是對事物內在本質的直覺表現,他說:“兒童除了描摹外觀的能力之外,還有力量使永久的內在真理處在它最能有力地得以表現的形式中。……兒童有一種巨大的無意識力量,它在此表達自身,并且使兒童的作品達到與成人一樣高(甚至更高)的水平。”畫家馬蒂斯、杜飛、夏加爾,尤其是克利、米羅和杜布菲等,同樣感到了兒童藝術的魅力。西方藝術家所向往的那種無意識的創作狀態、“信手涂抹”在兒童藝術那里得到了很好的詮釋。
三、西方現代主義繪畫對兒童藝術的借鑒與模仿
從19世紀后半葉起,西方畫壇發生了重大變化,眼花繚亂的西方現代畫派,既受到兒童繪畫在藝術形式上以及表現技巧方面的啟發,更受到兒童對待繪畫的基本態度無意識的強烈沖擊。對兒童藝術的推崇與模仿直接反映在他們作品的形式中。克利就一直崇拜兒童的這種天真狀態,并以自己的方式加以模仿。克利在繪畫技巧上使用兒童那種環繞的、粗陋的輪廓線,反應在作品《動物園》、《他喊叫,我們玩》和《女舞蹈家》中,這些畫中線條技法與兒童素描的線條技巧很接近,盡管它更細窄,更優美。《高架橋的革命》畫面上簡單的甚至笨拙的高架橋,表現出了克利對兒童畫天真稚拙的形象以及符號化形象的興趣。在米羅的繪畫世界中同樣可以感受到這位大師對兒童藝術的推崇,在他1948年至1953年的許多繪畫作品中,人物沒有身體表現,頭部直接安在以球形腳為末端的直腿上,整個臉像一個不規則的橢圓形或圓形,這種極端單純化的形象的變體,也就是兒童畫中的“蝌蚪人”樣式,如作品《在甲殼下部》、《黎明時瞪羚的哭叫》和《繪畫》以及早期最有名的作品《農場》都已呈現出一種兒童般稚拙的風格傾向。后來由于戰爭,米羅的作品表現出前所未有的恐怖之感,但畫面依然保持他那種天真、優美的風格。如系列《星座》及《女詩人》都是在戰爭的威脅之下創作出來的,但我們從中看不到任何血腥的痕跡。無怪乎有批評家說:“米羅的天才是一種返老還童的天才。”涂鴉和兒童藝術也是杜布菲的范例和靈感來源,他特別贊同用最簡單的正面和側面形象及兒童的輪廓線風格畫出大腦袋粗陋人物,也贊同兒童對記憶中傳達信息的細節的強調,杜布菲甚至希望以更加粗蠻、直接和確定的方式拋棄“后天學到的手段”,去探討一條回到“藝術基本的、形成的時期,記錄下兒童式的天真與好奇狀態的道路”。在他早期的作品中,如《街上的男人》畫面中描繪的是巴黎的景色與生活,具有一種天真稚拙的趣味。此后,他很快擺脫了克利藝術中那種幻想、略顯天真的氣質,而轉向一種獨特的、奠定自己在藝術史上地位的繪畫創作方法,創作出一些涂鴉形態的作品,如在《人間的聯歡節上》,我們可以看到的一種以此法創作出來的令人厭惡和不安的歡樂氛圍。
西方現代派藝術中的荒誕和隨意性與兒童藝術中的荒誕和隨意是一致的。“荒誕藝術比起優美、崇高的藝術更加深刻地表現了人之所以為人的內在生命力。”這是西方現代畫派對怪誕藝術的看法和推崇。現代派大師馬蒂斯、畢加索等人就從古代非洲的繪畫和雕塑中吸取怪異而又荒誕的特點,在我們的眼中極不符合常規,但這與兒童美術中的無意識荒誕的想法極為相似。西方現代主義繪畫對兒童藝術的接受主要表現在欣賞他們的天然和單純,使得他們的作品具有稚拙的面貌,法國評論家在觀看他們的畫展時,曾稱這些顏色不符合“客觀實際”,藝術形象難以理解。雖說在現在看來有點言過其實,然而的確在馬蒂斯等人的作品中反映出畫家進一步轉向表現內心情感,這也是近現代以來西方繪畫逐漸擺脫傳統上摹寫現實的主流畫法的新的一步,在野獸派繪畫中,馬蒂斯等畫家的一些人物畫有一個特點,人物的形象往往有彎曲的形態和封閉的輪廓線。如馬蒂斯的《浴者》和《海濱婦女》,這些作品使人想起兒童藝術的某些特點,人物的形象看起來“不準確”。上述這些對兒童藝術語言的模仿甚至直接挪用只是一個方面,更重要的是現代藝術家們從兒童那里重新獲得天真、純樸和清新的內在品質。
四、現代主義繪畫大巧若拙
現代主義繪畫在許多方面更借鑒兒童藝術,但他們的目的并非簡單地重創兒童繪畫,在技巧、表現形式上與兒童繪畫有很大差別。兒童繪畫是在生命之初對世界的探索嘗試,表達的是整個生命尚未展開的天性。而大師的繪畫則是在生命成熟階段對探索世界的提煉總結,表達出整個生命發展過程凝結出來的人格特征和藝術個性。所以,兒童畫一張張來看,大不相同,而大面積看起來,其面貌給人的感覺大同小異。大師繪畫則不同,都具有獨一無二性。克利、米羅和杜布菲等現代畫家在對兒童藝術的借鑒中充分展示了各自的藝術個性,他們使用兒童的符號和技法也并非偶然,而是他們比其他藝術家更需要這種敏銳的感覺力,帶著激情去感受兒童的繪畫世界。他們的繪畫有著精致的層次和精湛的技巧,雖然繪畫的最終效果有著明顯的隨意性,但與兒童天真的藝術并未完全融合,保持著各自的獨立性,又相得益彰。兒童的繪畫作品是“原始”形態的、天真純樸的,而又往往以“稚拙”的樣式表現出來。這在兒童是很可貴的,也是許多中外畫家所追求的藝術境界。那么藝術家追求的天真純樸和稚拙與兒童繪畫所表現出的天真純樸和稚拙是否如出一轍呢?這對于我們更深一步了解兒童藝術是至關重要的。審美創造一般都是由拙到巧、再由巧返拙的階段。開始之拙,是生疏幼稚的真拙,隨著審美創造技巧的提高,進入精巧工巧階段,有了豐富的經驗、功夫、素養,才能落盡繁華歸于樸淡,進入大巧若拙的境界。沒有深厚的功底,片面為拙而拙,只會粗陋低俗。戴復古說:“樸拙唯宜怕近村。”(《論詩十絕》)即使是巧后之拙,如果刻意追求拙的外在形式,則是一種造作,失去其真正的天然本質。拙樸絕非粗率平庸之輩所能達到的,它是審美創造高度成熟的標志。追求兒童趣味的藝術家在某些方面與兒童繪畫較為相似,例如:以線為主,平涂色彩,不講焦點透視及夸張變形手法等等。但兒童藝術中的那種天真稚拙的情趣被藝術家們加以發揮、拓展,成為嶄新的藝術形式。雖然他們畫中的“拙”與兒童繪畫中的“拙”有著形式上的相似,但卻又有著本質的區別:他們是老子所說的“大巧若拙”之“拙”。寫意大師崔子范也曾說:“一個沒有受過專業訓練的孩子只憑熱情作畫。在他長大之后,也應該注意使自己回到童年的心態,去重新發掘自己兒時的天性——自由地而不是造作地在畫中表現自己的感情。當一個成熟的畫家運用這種方式作畫時,當他將藝術大師的精湛技巧與孩子般的天真爛漫融合在一起時,會感到極大的快慰。”雖然西方的克利、米羅和杜布菲等畫家的作品源于兒童繪畫的造型符號,但他們靠熟練精深的技巧來完成。大體上都經歷了由開始的不成熟,到技法日趨精深,進而追求“返璞歸真”的過程。雖然也有追求兒童“拙味”的畫家未經過專門的訓練,但他們也難免經受藝術傳統的熏陶,前輩及同代畫家的影響與個人技巧的錘煉。克利雖曾說:“無需什么技巧”,但他畢竟經過了傳統藝術熏陶,其藝術風格必有傳統技巧的痕跡。可見兒童的稚拙是幼稚的拙,而畫家的稚拙是“拙中藏巧”之拙。“拙樸最難,拙近天真,樸近自然,能拙樸則渾厚不流為滯膩。”拙樸之拙,是大巧,不露痕跡,使人不覺其巧。它是“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實濃”(《東坡題跋》),在平實樸素粗散的形式中,蘊含著深厚的審美素養和豐富的情感意味。沒有一定技巧的錘煉,一味片面追求兒童“拙味”,只會流于粗俗淺薄,達不到自然渾化的拙樸之境。
五、結語
總之,現代藝術家們從兒童藝術中獲取到了造型符號的靈感,同時也通過自己的作品和言論促成了人們對兒童藝術的進一步關注、承認和了解。在現代藝術中,傳統的審美標準首先被打破,幾乎沒有什么尺度可以將兒童藝術與大師的作品相區別。當然,西方現代主義藝術家的作品與兒童的繪畫作品之間的相仿程度,也不能真正完全劃上等號,這些現代藝術大師的繪畫畢竟是落盡繁華歸于樸淡,大巧若拙,拙中藏巧。
參考文獻:
[1]羅伯特·戈德沃特.現代藝術中的原始主義[M].殷泓譯.南京:江蘇美術出版社1993:54.
[2]阿恩海姆.藝術與視知覺[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
篇2
[2]薛富興.文化轉型與當代審美[J].文藝研究.2001(03)
[3]肖鷹.青春偶像與當代文化[J].藝術廣角.2001(06)
[4]時宏宇.王爾德唯美主義的現代闡釋[J].齊魯藝苑.2003(01)
[5]余穎.Agora--廣場精神的復興[J].規劃師.2002(11)
[6]秦軍榮.漢語文學專業教育的學科體制化研究[D].武漢大學2014
[7]張寧.文化主義與意識形態幻象[D].武漢大學2011
[8]顧萍.淺談對繪畫藝術創作中的自律與他律的理解[J].皖西學院學報.2002(03)
[9]周小儀.“為藝術而藝術”口號的起源、發展和演變[J].外國文學.2002(02)
[10]陳剛.阿多諾對當代美學的意義[J].文藝研究.2001(05)
[11]伽茨,金經言.關于自律美學的若干批判性思考[J].南京藝術學院學報(音樂及表演版).2001(02)
藝術類論文參考文獻:
[1]趙雅妮,劉海.青年文化的變奏:從“青年的反叛”到“青春審美”的文化消費[J].北京青年政治學院學報.2012(01)
[2]衛華.波希米亞運動與歷史先鋒派的藝術行為理路[J].求索.2010(05)
[3]劉海.藝術自律與先鋒派--以彼得·比格爾的《先鋒派理論》為契機[J].文藝爭鳴.2011(17)
[4]劉海.城市廣場:城市制約中的空間政治[J].人文地理.2011(03)
[5]徐岱.藝術的自律與他律[J].東疆學刊.2006(03)
[6]陳劍瀾.從感性學到審美烏托邦--現代美學早期的一段問題史[J].江蘇社會科學.2010(06)
[7]劉海.倒塌的圍墻與崛起的讀者[J].長江學術.2010(04)
[8]杜吉剛.文學藝術自律--西方前浪漫主義、浪漫主義批評的一個詩學主題[J].大慶師范學院學報.2008(01)
[9]阿格妮絲·赫勒,傅其林.藝術自律或者藝術品的尊嚴[J].東方叢刊.2007(04)
[10]杜吉剛.唯美主義批評在英國的興起與消歇[J].青島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03)
藝術類論文參考文獻:
[1]陳文紅.在“藝術”之外思考藝術[J].文藝研究.2005(01)
[2]張相輪.當代審美文化發生發展的自律和他律[J].南京政治學院學報.2006(04)
[3]陶巧麗.在先鋒與自律的藝術之間[J].藝術界.2006(02)
[4]沈語冰.現代藝術研究中的范疇性區分:現代主義、前衛藝術、后現代主義[J].藝術百家.2006(04)
[5]施立峻.藝術自律性與當代中國語境--從法蘭克福學派批判美學的藝術自律性原則理論出發[J].上海交通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03)
[6]宋世明.“為藝術而藝術”:一場審美現代性的擴容運動[J].求是學刊.2006(03)
[7]呂景芳.自律與他律--文學在社會文化中的地位[J].寧波工程學院學報.2006(01)
篇3
1龐均簡介
龐均是我國現代藝術先驅、著名畫家、工藝美術家龐薰之子。江蘇省常熟市人,常熟龐美術館名譽館長。1936年生于上海。1939年考入杭州藝專,師承林風眠、潘天壽、黃賓虹、倪貽德、顏文梁等,1942年轉學北京中央美術學院,師承徐悲鴻、吳作人等前輩,1954年以優異成績畢業。從1954年到1980年步入專業創作的藝術生涯,1987年定居臺灣,任臺灣藝術大學專任教授。龐均避免了他長輩中的一些人堅守古典寫實藝術,摒棄現代藝術的偏頗態度,也沒有像另一些人一味盲目崇拜西方現代主義而全盤否定古典藝術那樣激進。他吸收古典與現代之長處,立足本民族的文化土壤,有機的融合文人畫精華,產生有創新意味和品格的中國油畫。他的油畫的特點有:線的加強(一波三折線的運用),空白處的采用(通過色彩關系來變現),書法體的簽名及畫出的具有個性特色的印章,淡雅的灰色調。
2意象油畫由來
意象是中國傳統美學體系中的一個重要概念,到底何為“意象”呢?最早的起源大約是《周易》的“圣人立象以盡意”。“意象”是可以感知的,它在表現客觀物象的基礎上,融入了作者的主觀情感, 滲透了作者的審美意識和人格情趣。意象油畫是屬于人類的精神產品,無法擺脫人的主觀元素即創作者的意識與感動,從而轉換成新的視覺現象而刺激他人。因此過分強調藝術的純客觀性、原始性是一種虛無,沒有價值的。對于有思想、有感受、有情感的觀眾來說,欣賞是一種主觀意識。當面對同一幅畫面,不同的觀眾會有不同的意境,有感覺傷感悲傷,有的卻感覺心曠神怡。
意象油畫的核心是寫意,寫意之意念在于“出新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意在筆先,為畫中要訣,不汲汲名利,把“百家風格”,“跟上時代”,“前衛”等等拋開,畫畫不過意思耳。這對意象油畫同樣適用,在落筆之前,心中必須要有構圖,有整體色彩之設想,對畫面要有全局性的感受――主次、空間、繁簡、色彩、趣味、黑白灰、厚薄、肌理、氣勢、情調、情緒、動靜、內力、外力等,瞬息之間統統涌上心頭,化作靈感,方可作畫。
3中國傳統美學的影響
意象油畫能夠在中國這篇土地上茁壯成長,與中國傳統文化對它的影響是分不開的。中國文化長期受老莊哲學及《周易》美學思想的影響與滲透,強調矛盾雙方的相互轉化,陰陽相互,有無相生。老子認為宇宙天道之妙用全在于陰陽動靜,宇宙萬物都包含著“陰”和“陽”這兩種對立的方面或傾向,萬物的變化都是由于陰和陽的相互轉化,它們最后都在“氣”中得到統一。“氣”是中國古代哲學中重要的范疇,影響十分廣泛。“氣”就是宇宙萬物的本體和生命,是萬物生命產生的根源,沒有“氣”就沒有萬物的生機與造化。老莊哲學理論中很多關于“氣”的論述,對后來產生了很大影響。“氣”和“韻”構成了物象表現的生命力,也是構成畫面耐人尋味的重要因素。中國畫追求空靈,講究“虛”和“空”的處理,其理論也是由陰陽觀演化而來的。 這些思想、理論深深地影響著龐均,影響著他的意象油畫。
4龐均意象油畫的技法特色
意象油畫筆觸書法化,講究筆性、筆意和筆韻,明顯可見是對中國傳統繪畫別講究的筆、墨形式感的借鑒與挪用。龐均追求中國繪畫的“一畫論”,所謂“一畫論”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萬物”認為“一畫”不止是“一條橫線”的意思, 也是“最原始最完整的線”的意思,是“最上大法也”。他在技法上以最簡單之筆,畫出最高之境界,必須每一筆都出自心田,用盡全身之氣,善用自我精神之高度、激動甚至“瘋癲狀態”,注入畫中。“宋人千筆萬筆,無筆不簡;元人三筆兩筆,無筆不繁”。簡筆比繁筆難,這個是需要不斷修養的,一畫比百花難,一人比群像難,一樹比森林難,就是這個道理。雖然龐均的意象油畫不可能三筆兩筆一蹴而就,但他也是極力避免在畫面上反復涂抹。因為他知道反復涂抹會使畫面變得光溜溜的,有一股“匠氣”缺少氣韻,所以龐均一改傳統油畫的“描”、“涂”、“抹”,在作畫時候的時候少用油,顏色厚,時而筆快速“拖拉”而上,時而快速逆筆推,或者快速左右拍打,重壓,滾卷,顫揉等等。用筆自如,使顏色通過他那手中的畫筆結合于畫布。自然而然的能夠做到“氣韻生動”、“一氣呵成”了意象油畫的色彩,既繼承了西方油畫藝術色彩的瑰麗之美,又傳承著中國特有的音韻之美,畫面的色彩主觀性比較強,同時也很生動,可能會表現出壯麗、淡雅、強烈等色彩。中國抽象油畫往往為了追求畫面的整體效果而削弱或是忽略形象的體積空間,使用更為單純、變化較簡單的色彩。
龐均的意象油畫直覺和對色彩所表現出的內涵,擺脫了單純的模仿,利用筆觸的交錯,就像從音樂中制造和弦一樣,來產生令人愉悅的色彩變化。他的畫面色彩有一種奇妙的文人情懷――即所謂的濃色不如淡色雅,淡色不如墨色高,在他獨有的灰色調的弱對比中追求妙趣。畫面上的色彩淡雅而不輕浮,厚重而不郁悶,處處洋溢出文人畫那種寧靜、相思、懷舊具有詩一般的思想境界與情懷。評論家們都說好的素描有色彩感,好的色彩有層次感、空間感,正所謂“色中有墨,墨中有色”。龐均的意象油畫,層次分明、空間感強,形、色肌理完美融合在畫面上,驚嘆之余感到妙不可言,具有震撼力、生命力,十分有趣。他在向中國傳統繪畫借鑒的過程中,沒有忘記油畫材料中光與色的優勢,這使得他的繪畫更加具有張力。在他那酣暢淋漓的油彩下,所蘊含的東方意韻令人沉醉,其筆端也自然地流露出海外生活所理解和滲透的西方浪漫主義色彩。
5結論
無論立意、氣韻,意象油畫走的路還很長,不僅僅技術磨練可達,更非油畫筆、刮刀、畫面之理之發,實屬品與格的觀念修養。誠然,觀念修養之高低可影響筆墨功力之優劣,油畫亦然,意象油畫更是如此。故民族油畫應向中國文人大家、數千年的文化精神學習,學習中國歷代書畫大家的文學修養與哲學思想。視油彩為一種精神內容,相信龐均的意象油畫不是中國民族油畫的終點,而是一個良好的起點。
參考文獻:
[1] 皮道堅.美術創作與論文指導[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9).
篇4
山水畫作為中國畫的一種分類,近百年來,正處于中國畫藝術由古典形態向現代形態變革的轉形時期,也就是表現性和再現性相互交替的階段,已取得了相當大的發展和成就。在二十世紀中后期還形成了以黃賓虹、傅抱石、李可染等為代表的歷史高峰。近些年來,山水畫的題材更加開闊,形式風格更加豐富,構思上也更富于創新。在我的畢業創作中體會深深得體會到了這個變化性―發展和變革傳統山水。表現性藝術性重視主體意識、重視創造個性,重視有意味的形式,在本世紀人類審美領域的開拓方面有它的積極作用和貢獻。東方人的思維方式帶有神秘的直覺性、感悟性,這種思維方式的特點和長時間形成的民族文化心理使中國藝術重性靈精神、重“意在象外”以非凡啟示和深遠影響。象外之意、象外之情的無盡妙處,如同點化的靈火,把藝術的審美對象由外部世界轉向內部世界,把藝術的傳導力由再現轉向表現。“外師造化、中法心源”,既是要求主客觀的契合統一,也是要求進一步把藝術的審美對象由外部世界遷入內部世界,把對客觀對象特征的認識轉型為對主觀感受、情意的抒發,帶有強烈的精神性、表現性和抽象意味。
主張中國畫變革的畫家鑒于歷史的經驗和自己藝術實踐的體會,并不主張拋棄山水畫傳統,而是主張學習、研究、繼承和發掘的態度。他們認為對傳統山水畫的變革要有一個基本態度和出發點,這就是繼承中國畫傳統,在繼承的前提下創新。所謂繼承傳統,就是要保留中國畫藝術本質的民族審美特征。中國畫的民族審美特征,是中國畫的本質特征和生命線。中國畫凝聚了數千年中國思想、文化、藝術的成分,作為中國人審美心理的一種最獨特、最合適的表征,對整個東方文化產生了巨大的、深遠的影響。它歷史的和現實的存在意義,全部在于它是東方的、中華民族的。山水畫作為中國傳統繪畫的重要組成部分,為我們后人留下了許多寶貴的經驗。近百年來,黃賓虹、齊白石、李可染、傅抱石、石魯等山水畫大家在繼承和變革山水畫傳統基礎上取得的成就,說明山水畫傳統在新的歷史時期中,仍然富有強勁的生命力。發掘山水畫傳統的精粹,使其服務于新的時代精神,是山水畫創作的畫家的重要課題。
1、溫故知新
“溫故知新”的觀念,即學習傳統全為了創造新意。在學習傳統的出發點解決了之后,方法也是很重要的。重要的是要從總體上把握傳統的精神本質,以宏觀的立意去體察傳統的博大和精深。學習傳統應該以現代精神為價值取向,以畫家的個性創造為主體,以現實生活為基礎。
作為封建農業社會經濟和古典文化背景的產物,古代山水畫賴以生存的時空已經消失,因此山水畫傳統的變革和向現代形態轉化是必然的。事實上,現代山水畫與傳統山水畫已經拉開了相當大的距離,從形式風格到精神內涵都有了許多不同。現代山水畫當然更符合現代人的審美心理,更適應現代社會的文化環境。現代山水畫的另一個時代表征是審美樣式的多樣性和技法語言的豐富性。改革開放的美術格局,與世界美術的頻繁交流以及日新月異的現代生活,提供了現代山水畫創造新的藝術語言的外部條件。傳統畫論中“外師造化”的涵義,正在被畫家們做更寬泛的理解。在重視畫家的個性和獨創性的新觀念中,在強調畫家發揚主體精神而又與大自然合諧觀照、天人合一的境界追求中,“中得心源”的傳統畫論正在啟發畫家們更大的創造精神。“外師造化,中得心源”的傳統中國畫創作法則,似乎永遠能煥發出新的時代精神,它堪稱是千古絕論。
致力于山水畫新的藝術語言的創造,體會這種創造不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新的山水畫藝術語言應該是傳統山水畫藝術語言的延續和革新。對傳統的再認識,已經成為最具現代意識的新觀念之一。
2、藝術語言
大陸畫壇在八十年代初期掀起現代主義思潮之后,中期就又流行了所謂“新文入畫”風。這種表面看起來很傳統文人品味,很講究傳統筆墨的畫風,正說明中國畫畫家已經從追求西方現代主義思潮的困頓中覺悟過來,又重新考慮自己藝術的民族基點,重新向民族藝術的傳統中探索謀求現展的因素。可惜所謂新文人畫的實踐算不得成功的實踐,因為它還是過于簡單地翻新了傳統文人畫的形式風格,基本限于形式上的以舊為新,而在精神內涵方面對傳統文人畫的革新和推進是有限的。新文人畫的另一個致命弱點是脫離社會和生活。藝術發展史上的經驗證明,任何藝術如果脫離社會和生活,是不可能有大發展和大成就的。它在藝術發展史上所能留下的痕跡,也是微乎其微的。
近年來畫壇出現了對黃賓虹積墨山水畫的研究熱和因此而出現的一批由積墨山水畫技法演繹而形成類形的畫家群。黃老的藝術雖然過去也曾受到高度的評價,但從沒有象今天這樣受到推崇和重視,以至形成風氣,理論家重新來解釋他的畫論,畫家紛紛跑到他的作品中去找感覺、尋出路。從這些現象中我們至少可以看出兩方面的問題。一是中國畫的傳統還煥發著強勁的生命力,它的資源還很有發掘的余地;二是以現代的價值取向和方法論,重新審視傳統,可能會有許多意想不到的發現。而這些發現也許正可以推動新型的、現代的中國畫藝術語言的形成。這種現象是否可以作為一種佐證,證明中國畫傳統中有些基本因素例如“筆墨”等是不可喪失的。在中國畫傳統藝術原則中,筆墨無疑是十分重要的,它集中體現了中國畫藝術的審美特色,深刻反映了中國傳統文化的精神實質。但是對筆墨的理解不應僅僅局限在形式和技法的層面上,更重要的是它的精神性方面。筆墨是一中國畫的基本藝術語言。用線用筆不僅是中國畫造型的基本手段,更重要的是 畫家胸懷、宣泄情感的重要體現,筆線是藝術形式,同時又是藝術內容,它是形式和內容的統一體,是一種具有意味的形式。傳統的中國畫藝術語言仍然是創造現代中國畫藝術語言不可脫離的背景和不可割斷的根源。
新的山水畫藝術語言應該廣為借鑒中外古今的一切藝術形式,因此它的形式風格也必然是豐富多采、不拘一格的。新的山水畫藝術語言的涵量和寬容度遠非傳統山水畫可比。
新的山水畫藝術語言,還應該從現實生活中去探求。從某種意義上說,藝術語言符號的創造是人在精神上對生活體驗的形象化。因此,畫家離不開生活,離不開對生活的體驗。中國古代文論中早有“登山則情滿于山,觀海則意溢于海”從藝術創造的角度論述人與自然關系的理論。強調人與自然觀照中“情”與“意”的意義。體現在山水畫中則是非常注重作品的意境。李可染先生認為:“畫山水,最重要的問題是‘意境’,意境是山水畫的靈魂。”“什么是意境?我認為,意境就是景與情的結合;寫景就是寫情。”“意境的產生,有賴于思想感情,而思想感情的產生,又與對客觀事物認識的深度有關。”我發現,當前有些山水畫畫家,受到西方現代主義的影響,過分強調作品中的觀念和哲理,從抽象理念到宇宙意識,弱化了山水畫藝術形象思維和表現的感染力。
3、類型化和風格化
山水畫創作中庸俗的類型化和簡單的風格化現象也令人憂慮。一方面是由于商品畫市場的影響,另一方面是某些畫家格調平庸,急功近利,不重視自己的藝術修養,他們的藝術語言從信息到信息,單看行情,照搬照抄,改頭換面。這種把藝術創作庸俗化的偽藝術現象,是山水畫健康發展的大敵。因此,強調畫家的修養,尊重畫家嚴肅的藝術勞動,使真正的藝術創作與偽藝術分出檔次,區別開來,是十分必要的。這是畫家自己、評論界和全社會應當重視的工作。
某一個時期理論界對純理論的鼓吹有些偏激,致使某些理論家完全脫離美術界的現狀和創作實踐,熱衷于引進和搬弄西方理論的所謂新觀念、新名詞。他們的文章空洞無物,晦澀難懂,必使讀者莫名其妙而后快。還有一些評論文章,慣于抑此揚彼,分派別類,大有指點畫壇、論定畫家之勢。而畫家更需要的是充分論述的,具體分析的和結合創作實踐的理論;更歡迎比較中肯、比較說理、比較切實、比較直率、比較與人為善的評論和批評。至于那些胡吹亂捧,不負責任的出于人情事故或商業考慮的所謂評論,則更為畫家們所深惡痛絕。有鑒于此,理論家和畫家們的平等對話,加強了解,互相探討是非常必要的。
某些創作中的具體問題 ,例如中國畫的展示問題,中國畫傳統的質材、工具、構圖、裝裱、展示等形式,大多源于古典形態的傳統需要。特別是文人畫的形式,正符合文人雅士的欣賞心理和生活需求。而現代中國畫的創作心態和展示環境等已經大別于古代。一幅畫并非僅供三兩友人茶余酒后展卷品味觀賞,而是陳列于展覽大廳,與周圍的環境構成了一個整體,展示給更多的觀眾。因此傳統中國畫的構圖和裝裱樣式以及展示方法已經明顯不符合現代的要求。當然這種表面形式上的問題也牽動著中國畫精神內涵的革新。總體來講,都是中國畫從古典形態向現代形態轉型的一個內容。
4、總結
總之無論是傳通還是現代山水畫的創作都是將“眼中自然”轉化為“心中自然”的過程。畫家從“眼中自然”到“心中自然”,都是要經過他獨特的情感、思想、意念、意志、審美胸襟的熔裁、孕化過程,將自然的形、色、線條整合為視覺意向,并賦與意象特定的精神內涵,實現以空間幻覺為特點的造型藝術生命。
[參考文獻]
篇5
一、回顧:百年中國文藝理論的基本性質
簡單地說,20世紀中國文藝理論的基本性質可以用一句話概括為主體性的建構和消解以及在此過程中形成的多元化格局。
建構主體性,首先需要確立人的個性主體(尤其是感性意志)的本體地位。盡管古典主義文論也講主體,但在古代社會生產力水平低下的情況下,主體自我的力量是微弱的,主體最終消融在外在的理性規范之中,或者消融在外在的倫理規范之中,或者消融在抽象的宇宙法則之中。因此,古典主義所講的和諧統一是以客體消融主體為前提的。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又可以稱古典主義美學為客體性美學。就中國傳統文化而言,雖然并沒有完全忽略人的感望,如《禮記?禮運篇》中說“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孟子?告子上》中說“食色,性也”,但卻將這種感望歸于“天理”,正所謂“有陰陽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婦,有夫婦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禮義有所措焉”,這樣,人的感性便完全被納入封建倫理規范之中,實際上等于取消了感性。特別是到了宋明理學,提出“存天理,滅人欲”,“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便更加明確地排斥了人的感望。因此,雖然中國古代文論追求情與理統一的和諧美,而且與古希臘一樣,也創造了光輝燦爛的體現著和諧美的古典文藝,但這種和諧美的實現常常是以壓抑和鉗制人的感性為代價的。
在確立感性意欲的本體地位方面,王國維的貢獻不可抹殺。他在《紅樓夢評論》中指出:“生活之本質何?欲而已矣。”在《叔本華與尼采》《古雅之在美學上之地位》等論文中,他一再申明“吾人之根本,欲而已矣”的觀點。確立感性意欲的本體地位,對于消解古典主義的客體性,建構近現代審美意識的主體性,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因為它使一個人在個性主體的意義上與古代倫理理性產生分離。
1902年,梁啟超在《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中,第一次將西方文學中“理想派”(浪漫主義)、“寫實派”(現實主義)的文學理論同時引進中國。他指出:“凡人之性,常非能以現境界而自滿足者也……故常欲于其直接以觸以受之外,而間接有所觸有所受,所謂身外之身,世界外之世界也……小說者,常導人游于他境界,而變換其常觸常受之空氣也。此其一。人之恒情,與其所懷抱之想象,所經閱之境界,往往有行之不知,習矣不察者……欲摹寫其情狀,而心不能自喻,口不能自宣,筆不能自傳。有人焉,和盤托出,澈底而發露之,則拍案叫絕……感人之深,莫此為甚。此其二……由前之說,則理想派小說尚焉;由后之說,則寫實派小說尚焉。小說種目雖多,未有能出此兩派范圍外者也。”①梁啟超的闡釋雖然有些原始、初級、粗糙,但這畢竟是中國文論史中首次對從西方移植而來的浪漫主義與現實主義的明確論述,其意義顯然要超出這種論述本身。后來,王國維又在《人間詞話》中再次提出“理想派”與“寫實派”的分別,他提出:“有造境,有寫境,此理想與寫實二派之所由分。”到五四時期,這種有關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抽象的理論提倡,終于演化為“文學研究會”與“創造社”兩種文藝流派的具體實踐。
在中國文論由古代向近現代的發展過程中,是一個重要的歷史事件。它的重要美學意義主要體現在對古代群體倫理理性的沖擊和反判,從而確立了個性主體的本體地位。無論是魯迅的“任個人而排眾數”,還是所斷言的“新文明之誕生……新文藝之勃興,尤必賴有一二哲人,犯當世之韙……為自我覺醒之絕叫,而后當時有眾之沉夢,賴以驚破”②,都將個人置于與社會群體尖銳對立的位置。中國近代文論的產生就是根植于這種人與社會的深刻的分裂之中。
到20世紀20年代后期,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則逐漸被“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和“革命浪漫主義”所取代。例如,郭沫若在他的《文藝論集序》中寫道:“我從前是尊重個性,敬仰自由的人,但在最近一兩年間與水平線下的悲慘社會略略有所接|,覺得在大多數人完全不自由地失掉了自由、失掉了個性的時代,有少數人要求主張個性,主張自由,未免出于僭妄。”“在大眾未得發展個性,未得享受自由之時,少數先覺者倒應該犧牲自己的個性,犧牲自己的自由,以為大眾請命,以爭回大眾人的個性與自由。”③基于這種認識,他開始拋棄主體的個性,轉而提倡“在精神上是徹底同情于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文藝”④。這預示著一種新的美學觀念正逐漸出現,標志著以崇尚主體性為主要特征的中國近代文論的發展已告一段落。
主體性理論也曾于20世紀80年代獲得復興,這主要體現在李澤厚的主體性哲學和劉再復的主體性文論中,但隨著90年代商品經濟大潮的沖擊,主體性的呼喚再次被淹沒。
作為近代文學理論,現實主義也講主體性,但浪漫主義主體與現實主義主體又存在著質的差異。浪漫主義文論追求個性主體的普遍性,現實主義文論則追求主體的特殊性。作為剛從社會倫理結構中分離出來的浪漫主體,浪漫主義尚缺乏一種社會內容的具體規定,顯得空泛而又抽象,往往表現為一種大人類主義,它將整個外在自然、宇宙一律看成是自我的表現。浪漫主義者提倡抽象普遍的人類之愛,主張以自我為中心,實行超階級差別的愛的推移。相對而言,現實主義文論則不像浪漫主義那樣特別關注自然,對于社會存在,他們也能采取較理智的態度,清醒地認識到人與人之間、個體與社會之間的矛盾沖突。一般來講,現實主義者反對浪漫主義抽象的人性論,而主張階級分析的社會學方法。
從浪漫主義到現實主義,主體性經歷了一個由抽象到具體的發展過程,而這一過程發展到現代主義那里才得以完成和終結。與浪漫主義強調主體的普遍性、現實主義強調主體的特殊性相比,現代主義則強調個性主體的個別性。其審美意識的結構方式主要表現為審美主體的感性意欲對理性目的的剝離,從而喪失了理性目的的總的統攝。在現代主義那里,整個外在世界都是異化的力量,主體感覺是破碎的、不完整的,他們特別表達了一種荒謬、無聊、空虛的純體驗的感覺。也就是說,現代主義處于主體性建構的臨界點,是主體性歷時發展的最后環節,可稱之為“主體性的黃昏”。
20世紀中國文藝理論的發展,不僅表現為主體性的建,也表現為主體性的消解。這具體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受到古典主義的消解。古典主義與現代主義的關系具有互動性,是作用與反作用的關系。古典主義不會只受到近代審美意識的沖擊,它也會對后者進行反擊。梁實秋曾在《古典的與浪漫的》一書中,從古典主義客體理性的角度,對中國新文學中所表現出的主體個性化傾向進行批駁與苛責。⑤
第二,受到“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理論的消解。“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作為現實主義的一種特殊形態,它理應充分尊重主體性,它所崇尚的主體群體性也必須以個性主體為前提,群體應由具有主體性的個體組成。然而在實際的歷史發展中,主體群體性卻時時表現出抹殺主體個性的傾向,這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表現得尤為突出。1958年提出“兩結合”創作方法,旨在把浪漫主義提到與現實主義同等重要的地位來加以確認,但由于受到當時社會氛圍的影響,極力膨脹人的主觀意愿,漠視客觀現實的規律,結果卻導致了“假浪漫主義”的出現。“假浪漫主義”與“革命浪漫主義”的區別在于,后者強調理性目的與理性認知的融合,前者則導致理性目的對理性認知的脫離。“”時期的文藝仍然標榜“兩結合”的創作方法,但在當時特殊的歷史環境中,文藝實質上成為“偽古典主義”的試驗場。“偽古典主義”是建立在虛假的客體性原則基礎上的,其中主體的理性目的外化為一種相當于古代倫理規范的所謂“根本任務”,并強制性地抑制和排斥主體的感性意欲、生命意志;主體的理性認知外化為一種相當于古代外在法則的所謂“三突出”原則,并對主體的感性體認進行了抽象化剝離。上述情況結合在一起,使現代審美意識主體性徹底解體。
第三,受到后現代主義的消解。這主要表現在20世紀90年代以來以“逃避崇高”為旗幟、以“調侃”為主題的王朔小說中,以及崇尚“零度情感”、追求純現象還原的新寫實主義小說中。后現代主義是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出現在中國的一種新型的審美意識。它雖然帶有從西方橫向移植的明顯特點,卻也有著深刻的現實文化背景。伴隨著商品經濟大潮的沖擊,知識分子的精英意識受到大眾文化的奚落和嘲諷,以“逃避崇高”為旗幟的王朔小說是這方面的集中體現。王朔小說中的“調侃”主題、對精英意識的棄置、對“崇高”的嘲諷以及他的大眾文化立場、寧愿流俗的態度,都構成了對審美主體性的致命一擊,使得還殘存在“先鋒派”小說中的一點點主體理性也蕩然無存了。在堅守大眾文化立場、放棄知識分子話語及寫作方式這一點上,新寫實主義小說與王朔小說有異曲同工之妙。與王朔小說不同的是,新寫實主義小說放棄了許多情緒化的東西,不再有意嘲諷精英意識,而是將這種態度貫穿在具體的純客觀的敘事與寫作之中。他們崇尚“零度情感”,追求純客體還原,將一切主體性的東西擱置在括號中,所剩下的就只能是一些瑣碎的帶有原貌性質的生活片段和生活場景。在注重客體這一點上,新寫實主義小說似乎與現實主義有著共同的傾向,但實際上兩者有著本質的區別。現實主義注重藝術形象的典型塑造,在審美主體的構成中,追求感性體認與理性認知的矛盾統一,其中感性體認為現實主義審美意識提供可感的生活素材,理性認知提供理性形式和藝術結構,它是對感性體認的藝術升華。這樣,現實主義藝術作品便可以再現社會生活的主流,反映宏大的社會場景,并具有嚴密的藝術結構。而新寫實主義小說卻放棄藝術典型的塑造,在審美主體構成中,擱置主體的理性認知因素,只專注于從感性體認得來的生活碎片,雖然有鮮明的形象可感性,但缺少宏偉的藝術氣魄。因此,我們決不能將新寫實主義小說歸入現實主義文論范疇之中。由于對主體情感的完全擱置,王朔小說和新寫實主義小說完成了對浪漫主義的最終解構。
主體性建構與消解的過程,也就是古典主義、浪漫主義、現實主義、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在20世紀中國文藝理論中交替發展的過程,從而形成了百年來中國文論發展的多元化格局。
二、反思:百年中國文論的話語轉型
百年來,中國文論的發展無疑受到外來文論特別是西方文論的影響。如何看待這種影響成為20多年來中國文論界的一個爭論焦點。從20世紀90年代的文論話語“失語癥”,到最近一兩年的“強制闡釋”,被越來越多的人所認同的一個觀點是:自近代以來,中國文化的激進主義和反傳統態度,過于偏激地對待自己的傳統,因而使得中國文化出現了某種斷裂。基于此,他們極力主張,在新的世界政治、經濟和文化格局中,身為“第二大世界經濟體”的中國的文論,應強調自己的文化傳統,建構自己的文論話語,避免西方話語的入侵。
然而,究竟什么才是真正的中國話語,論者迄今并沒有給出一個令人信服的解答和一個可資操作的方案。如果說,中國傳統文論中的“風骨”“神韻”等一系列的范疇可以作為我們中國文論建設的重要的文化資源的話,那么,我們必須進一步追問:這些范疇的確切含義究竟是什么?如果我們自己尚不能對它們的內涵達成共識的話,我們又如何讓文論初學者或者外國的文論研究者來掌握它們、接受它們?又如何實現論者所理想的避免中國文論“邊緣化”的目的?中國文論百年來的發展,已經初步形成了一套話語體系,盡管這套話語體系對西方有借鑒,但不可否認的是,它仍然主要是植根于中國的社會現實,是在中西文化的沖突與交融中成長發展起來的。文論話語轉型能否完全無視這一百年來形成的中國現代的文論傳統,是很值得懷疑的。
筆者深感有文論話語轉型的必要,但在實現轉型的目標和手段上卻有著自己的私見。筆者認同下列觀點:文論話語轉型的目標和方向,不應該是“向后看”,而應該是“向前看”,不應該是簡單地回到古代,而應該是對傳統進行“創造性轉換”;實現轉型的手段也不是簡單地采用中國古代的一些術語,而仍然需要立足現實和放眼未來,在中外文化的比較參照中,用現代人的思維方式去照亮和激活傳統,以一種批判的眼光去開發中國古代的文論資源,以一種審慎的態度對待中國現代的文論傳統,以一種寬廣的胸懷迎接西方文論話語的挑戰。
中國傳統文論,盡管具有豐富的價值資源,但其概念的構成形式、知識的生產和交換方式均基于特定的v史背景。主要表現在,關于文學藝術品評所操用的術語均局限在特定的文人社群之中,在這種文人圈中,人們的知識背景大致相同,審美趣味大體一致,因此其概念話語均帶有自明的共享性質,彼此之間不需要太多的解釋,對方肯定能聽得懂。作者在寫作的同時,已經將自己放置在讀者的位置上,他可以從自己作為讀者的立場上來對自己的作品進行評判;讀者也清楚作者的意圖,并以作者的身份來對作品做出反應。因此,作為中國古代文論重要資源的詩話、詞話、畫論、文論、曲論、樂論、傳奇評點等,往往三言兩語即能道破藝術的真諦,不需要太多的分析與論證。中國文論發展到近代,則逐漸喪失了這種特性。由于文藝要擔負重要的啟蒙職責,需要面對文人社群之外的廣大民眾,這在客觀上必然要求對其話語方式進行轉換,以彌合由于知識背景的不同而造成的差異。因此,要談論中國文論話語的現代轉型,必須首先從中國文論自身的發展歷史尋找轉型的動力。盡管在中國文論轉型的過程中,中國文論接受了西方文論的影響,但西方文論并不是唯一的、更不是最重要的起因。如果中國文論自身的發展是文論話語轉型的“內因”的話,那么外來文論的影響頂多可以看成是“外因”,內因和外因的共同作用,才促使中國文論從傳統走向現代。
中國現代文論話語的生成在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西方文論的啟迪,這在王國維、這兩位中國現代文論的締造者身上非常清楚地表現出來。不過我們在強調他們的“西學”知識背景的同時,同樣也不應該忽略他們深厚的“中學”知識背景。中國文論的“現代性”問題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問題,其中當然也有“反西方現代性的現代性”⑥問題。縱觀百年來中國文論的發展,其中有一個重要的理論價值取向,即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對于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文論的追求以及這種追求被主流意識形態的認可。作為文論思想的闡釋者,就曾明確地提出要“建立中國自己的文藝理論和批評”,反對“背誦馬列主義條文和硬搬外國經驗,而不結合中國實際”的做法,強調文藝理論“必須與我國的文藝傳統和創作實踐相結合”。⑦這種意見代表著主流意識形態的聲音,對中國現代文論的影響不可低估。
當然我們并不否認,20世紀中國文論的發展確實存在著外來文論話語橫向移植的傾向,但以下四個問題同樣不能否認。第一,這種分析性知識質態的移植或切換并非唯一的現代性知識的生成形式,如宗白華的文藝理論話語顯然是個例外。第二,中國文論發展中即使有對西學異質知識的移植,但它也不是某些理論家個人有意選擇的結果,而是中國現實發展的內在驅動使然,其中存在著“反傳統的中國傳統”問題。第三,我們對西學知識的接受存在文化“誤讀”的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我們在借用西方話語時,由于受到本土經驗的干擾,其“能指”與“所指”在西方原生意義上的關聯性有時會出現分裂的現象,我們借用的是西方話語符號的“能指”,而“所指”的卻常常是中國現實文本。西方話語在中國現代文論中的意義生成有著深刻的中國現實的文化背景,這也使得西方知識的全面置換打了折扣。第四,要將知識話語的建構與價值話語的建構進行區別,不能一概而論。從概念的外延上講,話語不僅僅是知識性話語,而且包括價值性話語。我們在接受西方知識性話語的同時,是否也接受了西方所有的價值性話語,這仍然是需要進一步論證的問題,并非不證自明。
從整體上看,20世紀中國文論的發展歷程反映了中西文化沖突與交融的現狀,其中有采納,也有拒絕;有借鑒,也有變異;有西方的知識話語形式,更有中國本土的現實經驗。中國現代性文論話語正是在這種沖突與融合中曲折地發生、發展的。這種現象可以首先從20世紀中國歷史發展的層面上去說明。“知識的現狀,與其說是根據它們本身的情況,還不如說是依其所追隨的事物來界定和解釋的。”⑧文論知識的增長,不僅是文論自身內部的知識調整,更是它所關注的現實經驗的回應。在中國文論的歷史發展中,話語系統的變換應該被看成是一種經常發生的情況,即使是被看成一個整體的中國古代文論,其自身依然存在著“不連續性”“斷裂”等現象。如果我們斷言,中國傳統在現代出現了斷層,我們就應該接著追問這種斷裂變換的判斷是否也適用于中國古代傳統。我們不應該只注意到傳統與現代的界限,而分別將傳統與現代看成是兩個互不相干的毫無變化的僵死實體,從而忽視和抹殺傳統和現代本身所具有的差異性。需要指出的是,所謂“不連續性”“斷裂”的論斷仍然是西方話語,這在米歇爾?福柯的著作中可以很容易地查找出來。但“中國傳統斷裂論”也同樣沒有將福柯的理論貫穿到底,其中仍然有“誤讀”。論者在傳統與現代的分界點上,采用斷裂的判斷,但當他們分析傳統這個概念的時候,卻給傳統賦予了“連續性”。在這里,我們非常有必要聽一聽福柯本人關于傳統是如何被構造出來的解說。他指出:“傳統這個概念,它是指賦予那些既是連續的又是同一(或者至少是相似)現象的整體以一個特殊的時間狀況;它使人們在同種形式中重新思考歷史的散落;它使人們縮小一切起始特有的差異,以便毫不間斷地回溯到對起源模糊的確定中去”,而這在福柯看來,不過是“以各自的方式變換連續性主題的概念游戲”,本身并不“具有一個十分嚴格的概念結構”。⑨不幸的是,“斷裂論”正是通過“變換連續性主題”、通過無限夸大現代與傳統的差異而極力縮小兩者本身中存在的差異的方式構造出來的,這里顯然使用了雙重標準。
我們必須承認一個基本事實,20世紀中國文論的發展格局是多元化的。中國百年來文論歷史發展的實踐表明,以單一模式來限定本身具有諸多差異性的中國現代文論,必然會顯露出自身的理論困境。
三、展望:間性研究與中國文論的未來發展
間性研究是當前文藝理論研究中出現的一種新的研究觀念和方法,它包括學科間性、文化間性、主體間性和文本間性四個方面,追求和強調的是學科之間、文化之間、主體之間、文本之間的綜合性、跨越性、開放性、互動性。間性研究對于文藝理論的學科建設和理論創新具有重要的價值與意義。通過學科間性研究,可以進一步明確文藝理論的學科定位與性質,促進文藝理論與相關學科的互動,密切文藝理論與當代審美實踐的P系。通過文化間性研究,可以突破以往中/西二元對立模式,避免中西方文化孰優孰劣的簡單對比和無謂糾纏,可以進一步發掘中國古代文藝理論資源,促進中外文學藝術的交流。通過主體間性研究,可以突破主客二元對立模式,進一步認識作者、作品、讀者之間的互動關系。通過文本間性研究,可以突破文學研究內外二元對立模式,促進文藝理論文本研究的開放性。所有這一切,顯然都有利于文藝理論的學科建設及理論創新。
文本間性(inter-textuality),又稱“互文性”,這一概念首先是由法國符號學家、女權主義批評家朱麗婭?克里斯蒂娃于1966年提出的。她在論文《巴赫金:詞、對話、小說》中說:“任何作品的本文都像許多行文的鑲嵌品那樣構成的,任何文本都是對另一文本的吸收和轉換。互文性這個概念取代了‘主體間性’的位置。詩性語言至少是作為雙重語言被閱讀的。”⑩在1974年出版的《詩歌語言的革命》一書中,她又指出:“互文性表示一個(或幾個)符號系統與另一個符號系統的互換;但是因為這個術語經常被理解成平常迂腐的‘淵源研究’,我們更喜歡用互換這個術語,因為它明確說明從一個指意系統到另一個指意系統的轉移需要闡明新的規定的位置性,即闡明的和表示出的位置性。”從克里斯蒂娃的解說中,我們可以看出,文本間性超越了主體間性研究和“淵源研究”,其基本內涵是,每一個文本都是其他文本的鏡子,每一文本都是對其他文本的吸收與轉化,它們相互參照,彼此牽連,形成一個潛力無限的開放網絡,以此構成文本過去、現在、將來的巨大開放體系和文學符號學的演變過程。這樣,閱讀成了在文本之間的游走過程,而意義則存在于文本與其他相關符號系統之間。應該說,克里斯蒂娃的文本間性理論并不是空穴來風,它是對巴赫金歷史詩學的對話思想和復調理論的繼承與發展,其學術背景則是結構主義理論向后結構主義理論的轉變。文本間性研究也可以看成是對以韋勒克為代表的美國新批評理論所提出來的文學內部研究與外部研究二分模式的超越,它強調的是在“符號系統的互換或文本意義的相互開放”基礎上文本與文本之間所達到的交融與會通。在這個意義上,再劃分文本之內與文本之外的所謂內部研究和外部研究就沒有多大意義了。中國古代文藝美學中所說的“文已盡而意有余”“文外之旨”“韻外之致”與“味外之旨”,其實都是非常重要的有關“互文性”問題的理論資源。
主體間性(inter-subjectivity)這個概念最早是由胡塞爾提出來的。對于胡塞爾而言,主體間性指的是在自我和經驗意識之間的本質結構中,自我同他人是聯系在一起的,因此為我的世界不僅是為我個人的,也是為他人的,是我與他人共同構成的。“在胡塞爾現象學中,‘交互主體性’(即主體間性――引者注)概念被用來標示多個先驗自我或多個世間自我之間所具有的所有交互作用。”因此,這一術語可以克服現象學還原后面臨的唯我論傾向。同時,主體間性還可以突破西方理性主義“主/客”二元對立的哲學和美學,“讓哲學和美學回到人的‘生活世界’,避免那種離開人類生活世界的客體與主體的隔絕與對立”。對于文學藝術問題而言,主體間性的概念則可以比較合理地解決作者、世界、文本、讀者之間的關系。也就是說,文藝美學的主體間性研究要側重研究的是作者與世界、作者與作品、讀者與作品之間的主體間性關系,即不再把作者對世界的感知、讀者對作品的解讀看成是主客體之間的關系,而是將其看成是主體與主體之間的關系。這樣,就可以使我們充分注意到作為主體的作家和作為主體的讀者之間的互動關系,從而使長期被忽視的讀者的地位得到重視;就可以使我們充分注意到作為主體的作家與作為主體的文本之間的關系,從而不僅注意到作家對文本的決定作用,而且也注意到文本對于作家的反作用或方向的決定作用;就可以使我們充分注意到作為主體的讀者與作為主體的文本之間的關系,從而不僅看到文本對讀者的決定作用,而且也看到讀者對作品的主動接受與變異;就可以使我們充分注意到作為主體的世界與作為主體的作者、讀者之間的關系,世界不再被看成是文學藝術反映的被動對象,而是與我們具有相互依存的密切互動關系,從而使我們對周圍的世界產生某種敬畏和依存感。與西方古典美學以主客二元對立論哲學為基礎不同,中國古代美學以“天人合一”的思想為基礎,以“致中和”為審美理想,完全以文學藝術為研究對象。中國古代美學可以成為今天文藝美學主體間性研究的重要資源,并與西方現代美學和后現代美學形成對話格局。
文藝理論的學科間性(inter-discipline)是指文藝理論與美學、文藝美學、藝術學的學科關聯性和交叉性。從這個意義上講,文藝理論是一門“間性”學科――這種認識對于文藝理論的學科定位和學科建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相對于自然科學而言,研究對象的模糊性和不確定性是人文學科的一大特點。我們關于文藝理論的學科定位的討論,總是試圖找到一個確定的文藝理論的研究對象,其結果總是讓人感到失望,原因就在于我們忽視了文藝理論作為一門人文學科的特征與品質。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區別于人文學科的一個明顯標志,就是其學科研究對象的相對確定性。用這樣的標準來要求人文科學,顯然是忽視了人文學科的特點,容易滑入理性主義、科學主義、本質主義的泥坑。文藝理論的學術生命力就在于它的跨學科性,這是文藝理論自產生之日起就具備的一種獨特的品質。文藝理論總是在自己與其他學科的相互關聯中來確立自己的學術形態、知識譜系、話語方式、精神皈依與價值取向,這其中主要是它與美學、文藝美學、藝術哲學、部門藝術美學的關系。正確地對待和處理這些關系問題,對于文藝理論的學科發展是內在性、本質性的問題。毫無疑義,文藝理論與美學、文藝美學、藝術哲學、部門藝術美學一樣,研究對象均脫離不了文學藝術,共同的研究對象使得上述各學科之間形成一個密切相關的相似于家族的學術部落。
談論文藝理論的學科間性,當然不是否認文藝理論的特殊性,否則文藝理論就失去了存在的價值。“文藝”作為文藝理論的對象,有“文學的藝術性”“文學與藝術的并列”和“文學與藝術的綜合”多種解釋的可能性。傳統意義上的文學是指詩歌、散文和小說,藝術是指音樂、繪畫、雕塑、舞蹈等,這些文學藝術形態之間是并列的,而當代大眾文化中新出現的文藝形態(如影視作品、網絡文學、多媒體動漫等),則具有文學與藝術的綜合性、兼容性,傳播的全球性、跨文化性,讀者觀眾與作品的互動性,閱讀接受的互文性,也可以說是一種間性文藝。文藝理論的研究應該適應當前審美實踐的主“場域”由過去小說、詩歌、散文到現在的影視作品、網絡寫作的變化。
文化間性研究,即跨文化研究。在英語中有三個詞都可以被翻譯為跨文化研究,即cross-cultural studies,inter-cultural studies,trans-cultural studies,有學者分別把它們解釋為“穿越式溝通”“互動式交叉”“會通式超越”。筆者認為,從總的方面來講,我們沒有必要過于拘泥于英文中這三個詞的細微差異。“跨文化”這個詞已經很好地將這三個詞的意義提煉了出來。所謂跨文化研究,就是跨越文化的界限,在兩個或兩個以上的文化之間進行比較,以便促進文化之間的理解、交流。在西方,希羅多德可能是最早的跨文化研究者,他在《歷史》中比較和分析了許多希臘世界的文化。19世紀,跨文化比較開始被進化論用來排列社會階段,如摩爾根在《古代社會》中所嘗試的那樣。在文學領域,根據德國著名理論家伊瑟爾的說法,跨文化話語的出現可以追溯到19世紀30年代托馬斯?卡萊爾的《拼湊的裁縫》這部作品。這是一部寫法非常獨特的書,既不是哲學,也不是小說和自傳,而是三者的結合。作者借助“衣服哲學家托爾夫斯德呂克先生的生平和觀點”,采用戲劇的手法,既對所涉哲學的原則作精要的敘述,又對哲學家的生平和性格進行描述,同時又扼要地闡釋了卡萊爾自己對人生的看法和觀點,而這正是對該書書名的解釋:衣服是指一切形式和慣例,裁縫則是指形式與慣例的創立者;裁縫是那位偉大的德國“衣服哲學家”,而將他的故事拼湊起來的另一位裁縫則是英國的卡萊爾。這就形成了一種溝通英德兩種不同文化的跨文化話語,作者也就成了一位將兩國不同的思想文化拼湊起來的文化的裁縫。伊瑟爾在《跨文化話語的出現:托馬斯?卡萊爾的〈拼湊的裁縫〉》這篇文章中指出:“卡萊爾在《拼湊的裁縫》中對跨文化話語的勾勒,是一個模式,而絕不是不同文化碰撞的縮影。不過,它倒確實提供了有關這種碰撞可能被確認的線索。跨文化話語不可能被確立為一種將不同文化之間的關系都包容進來的超驗的姿態,只有在此情形下,它才能成為模式。跨文化話語也不是一種凸現的第三維,它只能行使連結網絡之職,并將假定一種形態,其普遍特征不能等同于任何現存的類型。”也就是說,在伊瑟爾看來,跨文化研究也許不會關心不同文化碰撞和沖突的具體過程,但卻為理解和研究這種過程提供模式和線索。這種理解和研究并不是超越于F存文化之外的,而是在各種不同文化之間的,因而也可以說是一種文化間性。
目前,隨著全球一體化的趨勢,跨文化研究或者說文化間性研究會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重視,那種局限于一個國家和民族領域內的單純的文化研究會越來越難以進行。過去將世界文化簡單地分為東方和西方的二元對立的模式顯然已不合時宜,亨廷頓的世界七種或八種文明的劃分,也顯得粗糙。最理想的當然是在世界范圍內,不同的文化和文明都能得到同等的尊重和理解。在這一方面,筆者認為荷蘭跨文化研究學者霍夫斯戴德(G. Hofstede)的研究值得我們注意。從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霍夫斯戴德通過大規模的文化價值抽樣調查,得出了表現各國文化核心價值的五個層面:個人主義(IDV)、權力距離(PDI)、不確定性回避(UAI)、男性化(MAS)、長期傾向性(LTO),計算出了53個國家和3個地區在這五個層面上的數值,從而揭示了不同文化之間量的差異性。霍氏為跨文化研究創立了一個可操作的理論框架,文化價值五個層面的數值之間可以比較。不同文化之間的差異不再是質的差異,而表現為量的差異。這在文化比較研究方面是一個非常大的進步。例如在霍氏的量表上,中國的PDI為80,IDV為20,MAS為66,UAI為30,LTO為118,而澳大利亞相應的數值則分別為36、90、61、51。這表示,與澳大利亞相比,中國文化更能注重上下級在各方面的差異,不太注重個人主義傾向;在注重生活質量方面稍差,而在承受不確定性的能力方面以及在尊重傳統方面都要高于澳大利亞。而這樣的比較只是量的差異,并不是質的差異。也就是說,中國文化只是在量的意義上在注重個人權利方面低于澳大利亞,而這并不表示中國不注重個人權利。這就消除了以往異質文化論帶給我們的理論困惑。這樣的一種觀念,對于我們的美學研究也具有很大的啟發意義。過去我們有一種觀點,就是認為中國美學是表現美學,而西方美學是再現美學。這就容易將中西美學完全對立起來,消解了中外美學對話的可能性。實際上,中國美學中并不是沒有再現的因素,而西方文化中也并不是沒有美學表現的因素,中外美學的差異只是量的差異。這種量的差異性就為中外美學的跨文化研究提供了可能性,從而可以消解中西二元對立模式所造成的絕對論傾向。
在中國,最早的跨文化研究至少可以上溯到《史記》。《史記?大宛列傳》中記載:“安息長老傳聞條枝有弱水西王母,而未嘗見。”“西王母”是中國古代神話中的人物,司馬遷的這條記載說,在條枝(即今伊拉克)一帶也有類似的“西王母”的神話傳說,這可以被看成是中國跨文化研究的最初萌芽。王國維的《紅樓夢評論》(1904年),采用“取外來之觀念與中國固有之材料互相參證”方法,可以說是中國現代最早的跨文化研究的文藝美學著作。這種中外相互參證的跨文化闡釋法,也成為中國現代文藝學、文學批評的一個主要學術范式。
對于當代中國文藝理論建設而言,文化間性研究要超越中西二元模式,它以文化間的開放性為前提,要研究的是不同文化之間文學藝術的接觸、交流、相遇、傳播的運作方式,其中包括“文化翻譯”“跨國界傳播”及“跨語際欣賞”等問題。文化間性研究要達到的總體目標是實現“多元化的普遍主義”,既強調文藝創作的“地域性”“本土性”特征,又強調文學藝術欣賞與消費的超地域性,以及人文精神價值的普世性。
文化間性研究對于中國文藝理論未來發展的價值和意義,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第一,有利于促進中外學術的平等對話,有利于提升中國人文學科的國際形象和地位,有利于解決中外學術交流中中國學術話語缺失的問題,以真正做到中外學術的平等對話。第二,有利于發掘中國古代的文藝美學資源。相對于西方發達的哲學美學而言,中國古代則具有更加豐富的文論資源,從文化間性的角度,深入挖掘中國古代包括詩話、詞話、評點、畫論、書論在內的文論資源,可以使這些資源更好地走向當代,更易于被國外的研究者所接受。第三,有利于促進文藝理論對文化研究的積極回應。文化間性研究是對文化研究的超越,它強調的是審美研究與文化研究的結合,因而可以回應文化研究的沖擊和挑戰,并承擔起在市場經濟與信息化時代的新形勢下從審美的創造和接受的角度探索通俗性與審美性、娛樂性與陶冶性有機統一的問題,使得新時代的文學藝術(網絡文學、影視作品等)在適應大眾文化消費需求的同時,提高作品的審美品位。
注釋
①梁啟超:《飲冰室文集》卷十《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轉引自《中國美學史資料選編》下,中華書局,1981年,第424頁。②:《“晨鐘”之使命》,《晨鐘報》創刊號,1916年8月15日。③郭沫若:《文藝論集?序》,《沫若文集》第十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第3頁。④郭沫若:《革命與文學》,《沫若文集》第十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第321頁。⑤詳細論述請參見李慶本:《梁實秋與中國近代浪漫主義的終結》,《東方叢刊》1998年第2期。⑥具體論述參見汪暉的《當代中國的思想狀況與現代性問題》(《文藝爭鳴》1998年第6期)、《關于現代性問題問答》(《天涯》1999年第1期)、《傳統、現代性與民族主義》(《科學時報》1999年2月2日)。⑦參見《建立中國自己的文藝理論和批評》,《文藝報》1958年第17期。⑧[美]馬爾庫塞、費徹爾:《作為文化批評的人類學》,三聯書店,1998年,第24頁。⑨[法]米歇爾?福柯:《知識考古學》,三聯書店,1998年,第23―24頁。⑩Julia Kristeva.Word, Dialogue and Novel. The Kristeva Reader, edited by Toril Moi, Basil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1986, p37.[法]朱麗婭?克里斯蒂娃:《詩歌語言的革命》,《文學批評理論:從柏拉圖到現在》,[英]拉曼?賽爾登編,劉象愚、陳永國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422頁。倪梁康:《胡塞爾現象學概念通釋》,三聯書店,1999年,第255頁。張玉能:《主體間性與文學批評》,《文學批評與文化批判》,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73頁。王柯平:《走向跨文化美學》,中A書局,2002年,第2頁。程主編:《文化研究新詞典》,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78頁。Wolfgang Iser.The Range of Interpreta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0, p159.司馬遷:《史記》,中華書局,1959年,第3163―3164頁。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on The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Art in One Hundred Years
篇6
首先,對以明“四僧”為主的文人畫禪意傳統的承繼。
大千對于傳統文人畫禪意傳統的承繼,以研究和臨摹明“四僧”等人的繪畫作品為主,旁及徐青藤、陳白陽等諸名家。我們知道,“山人在清初是作為非正統,甚至以‘野狐禪’的面目出現的。……那極為簡潔、概括的造型,那白眼向人、孤獨瑟縮的鳥類形象,那省到不能再省的‘墨點無多淚點多’的筆墨處理,那高度抽象的形式表現,卻因為更符合中國繪畫美學的精義而具無限的生命力。……與相似,同為文人作花鳥畫的還有石濤、髡殘等,其品格孤高奇逸,筆墨縱橫捭闔,情意盎然,為文人寫意一路。”③可以說,由于作為明宗室后裔以及他做過和尚、道士等多重身份,使其畫作中傳達出簡淡、古雅、冷逸、蕭瑟等獨具特色的藝術風格。
張大千曾在《四十年回顧展自序》中說道:“予乃效為墨荷”。若以《荷石水禽圖》為例,似乎更可以探出幾分大千畫作中的禪意淵源。畫作中,以墨筆畫湖石臨塘,而疏荷斜掛處,兩只水鴨或昂首仰望,或縮頸漠視,怪石相伴而白眼天地;荷葉則奔放自如,蕭疏簡淡;整幅畫作以簡勝,以散出,意境空靈,意蘊豐澹,韻味無窮。
那么,觀張大千之《仿山人畫荷》,便足可以見出其對筆意的揣摩與超越:畫作以虛當實,把一大空白劈為一巨石,實筆之荷花、荷葉則圍著巨石宛然自若,或隱含或舒展。構圖似,又神貌皆逸出筆墨之外。可以說,張大千的畫作也正是其在靜觀“悟對”而“通神”處直接吸收了這種簡淡蕭疏禪意傳達的法心、筆式與意趣。因此,張大千荷之荷葉潑墨與渴筆兼用,舒卷自然,疏宕渾成,層次深厚;荷干亭亭玉立,氣勢挺拔,直可追之意,卻又不盡然。
一如張大千自己所言:“我花荷葉,就像漢朝人寫隸書,要逆入反出。”(《對臺灣記者蔡文怡的談話》)不僅如此,張大千也非常準確恰切地區分了和石G畫作中的筆墨精神,認為的用筆圓潤,用墨滋潤,并能夠在淡墨中顯精神,而石G的畫則圓筆中鋒,蒼茫渾厚,視其畫如見其人。(劉力上《博采眾長,勇于創新》)由此,張大千在《仿石濤山水》畫軸的題款中尊石G為“畫圣”,尊石濤為“畫佛”。在明確辨析各自風格特征的基礎上,各取二石之所長以融化于自己的神來之筆中。
尤其是對于石濤的學習和臨摹仿制,張大千在一個時期竟然使所臨之畫達到“似真”甚至是“亂真”的境界。以至于精于鑒別的陳半丁、羅振玉等幾乎都已上了他的“當”來。我們說,老子之道一論、莊子之自由意志、佛學本體論皆是構成石濤畫學體系的哲學基礎。那么,張大千畫作中對于石濤禪意的承繼也與石濤“出筆混沌開”之妙造自然的意趣直接相連,尤其是對于石濤潑墨潑彩技法的習染,更是張大千晚年與西畫印象主義、表現主義等藝術相融通而臻于化境的藝術風格得以形成的基礎。不過,張大千曾在《仿石濤山水》題款說中說:“此予三十年前所作,當時極意效法石濤,惟恐不入,今則惟恐不出,書畫事與年俱異,該有不期然而然者矣。”可見,張大千對于石濤的學習也是一個有入有出的過程。
石G之作則“蒼茫沉厚,或認為出于黃鶴山樵,殊不知玄宰空靈,石G變之以沉郁,不期與山樵比跡,則形相之論也。”(《明末四僧畫展序》)石G之畫意在“變”,把自然萬象變為自己的心象,于心象之外指向豐潤溫厚又奧妙靈秀的大自在。張大千對其畫意的承繼也在“變”,拿來豐潤之自然妙象,變為不拘成法,發揮個性,從而擁有不落前人窠臼的個人風格的言說符號。
對于漸江,張大千則認為他是“假和尚”,是“憂國憂民之士”,不過,他的用筆“剛健挺拔有英武之勢”。因而,從禪意承繼角度看,張大千或在用筆氣勢等方面對漸江的藝術技法有學習,但其畫意對張大千的影響并沒有明顯的印跡。
可以說,以對“四僧”的學習為基礎,張大千畫作又直接融匯儒釋道等多家思想,而呈現出“畫意禪心兩不分”(曉云法師語)的意境,雖畫意融懿雅淡而心性自出。這是因為,中國畫產生于多家哲學思想浸潤的土壤之中,作為在中國畫中有著重要地位的文人畫的發展,也是一個同多家思想緊密結合,一步一步走向成熟、走向“逸筆草草、不拘形似”而又妙合萬象以獨抒性靈之境界的過程。而張大千在對于前代不同藝術風格的藝術家的習染過程中,必然承繼了這種儒釋道屈等相融合的博大思想。一如徐悲鴻所說:“蓋以三代兩漢魏晉隋唐兩宋元明之奇,大千浸其中,放浪形骸,縱情揮霍,不盡世俗所謂金錢而已。雖其天才與其健康,亦揮霍之。生于二百年后,而友、石濤、金農、華巖,心與之契,不止發冬心之發,而髯新羅之髯。其登羅浮,早流苦瓜之汗;入蓮塘,忍剜朱耷之心。其言談嬉笑,手揮目送者,皆熔鑄古今;荒唐與現實,仙佛與妖魔,盡晶瑩洗練,光芒而無泥滓。”(《嗚呼,大千之畫美矣》)但張大千學某人并不拘于某人,并特別注重在暢游山水中尋找空明雅逸的情致與意趣,熔鑄成我自有我在的獨特藝術風格。
所以,如果說畫作中傳達的是一種簡淡、蕭散的禪境,石濤畫作中傳達的是一種造妙綿渺的禪境,石G畫作中傳達的是一種融懿渾厚的禪境的話(也可以說,石G的佛更是直指本心),那么,融合了多家思想之后,張大千畫作中傳達的則是一種超越前人而自有我之本心的圓融淵穆的禪意境界。
其次,對敦煌藝術中如來禪禪意傳統的承繼。
在1941年至1943年期間,張大千對敦煌壁畫進行了大量的臨摹,使其傳統繪畫之根直可追溯到魏晉南北朝至隋唐的如來禪時期。這就使大千荷具有獨特的深蘊著儒釋道合一又深受來自于敦煌壁畫影響的佛的圓融性風格。因而,自由的生命力量也就隨著如如禪意,悠然而來,又淡然地延宕于畫作之外。
這也使張大千畫作超越了平淡、蕭瑟禪意傳統,從而具有獨出機抒的禪趣之美:其一,莊靜深邃的意境美。敦煌壁畫中不變的佛教主題尤使其以后禪意畫綿邈的神韻傳達得以進一步的提升。及至20世紀60年代以后,張大千更是創造了顏色濃重、大幅連屏的潑墨潑彩技法,使作品表現出“蒼渾淵穆”的禪意境界。其二,流暢自由的線條美。張大千摹古并不擬古,而是能夠以“六經注我”之氣魄擷得古人之神髓來成就自己獨特的藝術面貌,使線超越了作為寫實的工具,以形寫神,從而具有了如佛光籠罩的自由性。其三,敦厚豐腴、闊大圓融的象喻風格。敦煌壁畫瑰麗多姿的藝術風格使張大千從盛唐人物中感受到重彩的復活。重要的是他不只得其貌,更是深得唐人精密與宏偉寫實精神的遺意,使畫作豐潤飽滿,極富感染力。由此,張大千畫作中更多了一層結合文人畫筆墨技法與唐人遺風而流露出的圓融嫻靜之韻致。
因此,在張大千的畫作中,似還可梳理出畫家在承繼禪意傳統的同時,也有著自己參悟“禪機”的不同發展階段。當然,這不過是強以名之而已。如較低一層,可定為“以色喻空”;再上一層,可定為“空即是色”;較高一層,可謂“空空,空空”,即色空的相對而生,皆成為不必要了,從非此非彼,亦此亦彼的“不二”法門來看,不管色還是空,都屬于執著,只有破除了這一層的對待,同時破除了對這一對待的否定的執著,才可領悟在時間之外的“真諦”。此時可超越三t,畫人之心胸灑脫,妙和無垠,默契神會,如王維《山水訣》云:“手親筆研之余,有時游戲三昧,歲月遙永,頗探幽微,妙悟者不在多言”。這是畫家游心物外而不被畫作牽制,可謂禪畫超越之機,“三品”而外之境。因而也就達到了“見山還是山,見水還是水”的禪悟境界。禪師所謂心身脫落,犖犖堂堂,畫家所謂如置身太空,了然無礙,“畫意禪心兩不分”時,心性亦自然顯現。不過,此種至境畢竟少之又少,因為,倘若真的至此至境,繪畫這一藝術門類也就毋須存在了。因為,任何一位畫家都會受繪畫符號的具象性特質所拘限,而難逃執著筆意之嫌。
二、對“無心之大心”禪機的天然體悟
“桃花紅、李華白,一塵一佛土,一葉一釋迦。”(《五燈會元》卷十七)這禪意就是包容一切又無跡象、不取不舍的本體性,也可稱為“無心之大心”。這也是張大千深深體悟到的,他的很多題款都顯示了自然這顆“無心之大心”對于我之本心帶來的怦然心動之觸碰,一如《飛泉圖》題款所云“絕壁過云開錦肅,疏松隔水奏笙簧”、《題白荷》所云“明月曾呼白玉盤,多情更照玉蘭桿。香吹一夜西風滿,水殿羅衣訝許寒”等,禪意也便在我與自然萬象、存在與存在相遇、相對時一瞬間的消息盈漲、彼此映照中嘩然落入筆下。所以,張大千的畫作雖然承繼了文人畫的禪意傳統,卻不乏榮榮生機而又別有逸趣。這是因為,對于張大千而言:
第一,空靈神秀的山水中自有之禪機。
“花開水流,鳥飛葉落,他們本身都是無意識、無目的、無思慮、無計劃的。也就是說,是‘無心’的。但就在這‘無心’中,在這無目的性中,卻似乎可以窺見那個使這一切所以然的‘大心’、大目的性―而這就是‘神’。”④那么,以荷花畫作為例,可以看出,作為虛實開合之構圖中靜觀悟對而通“神”的媒介,荷花就是了大千經過悉心的臨塘觀察、寫生以取法自然,長期捕捉荷花的特征和瞬間的動態,然后用跡化于筆墨之外的純然“本心”之心性加以浸潤,使之成為呈現某種平淡簡遠意趣的言說符號。至其潑墨、潑彩、潑墨彩畫作更將文人畫的筆墨拓展至另一境地,以傳達畫家靈通而空明的“無心”之“心”。正如大千自己在《與孫云生的談話》中所說:“我認為,繪畫是無法教的,必須靠自己去體會。只能意會,難以言傳”。這也是禪宗所謂“以心傳心,不立文字”之意。而這“難以言傳”之“意會”,便是“無我”之“本心”,因此,它無從說,無需說,自然也不必說。因而,在張大千的荷花系列畫作中,每一片渾然舒展的荷葉,每一個宛然自若的花苞,每一擎燦然盛開的花朵,每一枚艷麗豐腴的花瓣,都呈現出了這種“無心大心”以及“瞬間的永恒”的禪意境界。從而使人悟得:禪,就是那絕對無的無心,是心對境之時,了知境的本性是空,心的本性也是空,從而不染不離,又能以空為觀點來任運一切來去自由的無心之大心。
于是,荷花便非純粹的“本性是空”的境中絕對無心的符號,而是融合了“生機”的妙象。這也是大千深深體悟到的:“一切生物都是向上向陽的,即使下垂的枝葉,其末梢也必有一股向上之力。那崖壁上的樹木之所以向一旁猛烈伸張,乃是爭取生存的天地。”(王永年《大師攜我入畫門》)對于生命力量的表現是所有藝術家傾其一生都在逐求的美學理想。因此,“傳統士大夫文藝中的禪意由于與儒道屈的緊密交會,已經不是非常純粹了,它總是空幻中仍水天明媚,寂滅下卻生機宛如。”⑤這一點在張大千的畫作中表現得尤為突出,山山水水還是山山水水,荷花還是荷花,它們都是自然生命之本體,并不依附于禪悟在無禪體驗中的靜止,而是具有勃勃生命力量的自然存在。于此,對于張大千畫作中所含蘊的禪意而言,就是“人與自然冥合,將生命還原到藝人之生命中開放花朵”⑥,源于畫家自己的生命體驗與自然山水中豐沛的生命力量的天然契合。
第二,禪的秘密之一即在于“對時間的某種神秘的領悟”。
李澤厚認為,對時間的某種神秘的領悟,就是對所謂的“永恒的瞬刻”或“瞬刻即可永恒”的一種直覺感受。所以天地萬物無言而禪機無限、禪意自生,在心物相遇時本心之剎那觸動,在無始無終的時間中禪定為永恒。比如,張大千筆下的荷雖形態各異,多姿多彩,但多半以一開一合之荷來構圖,開合之間,有無相成,虛實相應。于是,禪意不在宛然“一笑”的荷花中,而在一切“無”有的花苞中,因為在開合之間的悟對中,一切都得到了超越。然而,又不僅僅止于此。可謂具象一層相對,超越一層靜觀,佛性正在那“瞬間即永恒”的有無突轉之間。當然,也由此而生成一種“于六塵中不離不染,來去自由”(慧能《壇經》)的令人瞬間可以聽得心響的禪悟體驗。
張大千在《潑墨鉤金紅荷》中有一題詩:“疏池種芙蕖,當軒開一萼。暗香風襟袖,涼月吹燈坐。”從中可以把捉到張大千對某種神秘的領悟、頓悟或了悟之頃刻:因風過而涼月吹燈,在自然給予的這一悄然動態中,“我”之“坐”這一靜態心境,在一瞬間完成了主體對生命本體所具有的不動之永動又永動而不動的神秘性的體驗和領悟。也所謂“萬象源生一念,一念照徹大千”(曉云法師語)矣。在此,禪意由畫借助詩的多重能指在由言荃而指向無的表達過程中亦虛亦實,層層延宕;同時,也由詩借助畫的具象在由象符而指向無的過程中亦實亦虛,畫作中處處流溢著一種禪悟的愉悅心境。
三、對于“不似之似”妙象之象喻傳統的超越
我們知道,“象”在我國傳統文學藝術中有著豐富的美學內涵,負載著多種哲學思想的綜合含義。《周易》中的象是對自然之象的效仿,所謂“象者像也”。莊子有“象罔”說,宗白華認為:“‘象’是境相,‘罔’是虛幻,藝術家創造虛幻的境相以象征宇宙人生的真際。真理閃耀于藝術形相里,玄珠的于象罔里。”⑦“妙”字最早見于老子《道德經》:“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而又玄,眾妙之門”。妙者,“微之極也”。郭璞《游仙詩》之八曰:“明道雖若昧,其中有妙象。”這里的“妙象”也就是指可以把“若昧”的“道”呈現出來的有無相生、虛實相合的境相。不過,對于自然本體來講,任何“象”都只是對自然的一種仿“像”,因而,真正的自然本體是無法顯象、無法言說出來。所謂“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但是,對于自然本體的認知又必須借助近取諸身、遠取諸物的“法象萬物”之象來觀象之妙而寓于變中,來“立象以盡意”,這樣,通過對于象的觀察與洞悉,始可達至“萬化在心”的境地。當然,即便是通過觀象于天地而實現了“萬化在心”,吾心終究還是與萬化隔著一層。因而,對于強調以明心見性之本心來直覺一切本相的祖師禪而言,就特別講求“掃象”、“泯跡”以悟入,而即心即佛。
于繪畫來說,就是不僅要否定以線造型的“形似”,而且反對“傳神”之滯于化跡;特別強調線條能夠“以不似之似,傳寫超脫灑然的畫外之意。這里的不似之似所似的是離一切相的實相,畫外之意的真意是無住生心。”⑧從而以線造型來構筑“不即不離”的“妙象”,以直達神秘頓悟之真心,同時也就可以以直覺的方式來認識宇宙自然之本相。那么,禪意畫中“不似之似”之妙象的象喻性本質上就是一種對自然本體之空無的隱喻。
從北宋坡詩句“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開始,到倪瓚所說“逸筆草草,不求形似”,再到黃賓虹說“惟絕似又絕不似于物象者,此乃真畫”,以至白石老人提出“妙在似與不似之間,太似為媚俗,不似為欺世”,這一過程中直接呈現出的是中國文人畫一直都在尋找的,以“不似之似”之妙象直指世界本相的象喻傳統。張大千不僅繼承而且超越了這一傳統,從而使其創作出的“不似之似”之妙象具有了中西合璧的美學意義與價值。
首先,妙象是畫家傳達有我之本心所直覺到的世界本相的隱喻符號。
我們說,妙象就是一種“超越具象而又融合于對象物當中的帶著藝術魅力的純粹心象”(賴賢宗語),也是一種象外象,它來自于渾化之境,必然要落于筆墨形跡之中,方能于“虛實相生合成妙象”的再現中化境為虛,而通于渾然之中。
其實,所有的藝術言說方式,從本質上講,都是一種隱喻。因為人類要言說的都是自然本體、人性、神性之所在,而我們不可能通過任何一種媒介就把自然存在的本體言說清楚,藝術言說本身只是一種通過觀看到的物象來表情達意的方式,而象本身也只是宇宙自然的仿像而已。所以,世界的本相與“真理和神性一樣,是永不肯讓我們直接識知的。我們只能在反光、譬喻、象征里面觀照它。”(歌德語)⑨而妙象正是賦予了世界本相以形象和生命,因此也增加了自身所寓含內容的深度與生命力。
正如張大千所說:“畫一種東西,不應當求太像,也不應當故意求不像。求它像,當然不如攝影,如求它不像,那又何必要畫它呢?所以一定要在像和不像之間,得到超物的天趣,方算是藝術。”⑩這就是對于藝術創作中著力創造出的妙合無垠又游心象外之妙象的最好注解。大千在創作中也是這樣做的,并且隨著藝術境界的開拓而日漸不著跡象。由此,以大千荷為例,我們可以說,荷花就是承載了張大千繪畫中所蘊涵的徐徐禪意之妙象―荷花之顯與荷葉之隱,花葉之實與飛白之虛,也即虛實相生之“象外象”。這樣,就充分發揮了妙象在似(即隱喻中的能喻)與“不似”(即隱喻中的所喻)之間創造相似性的功能,使妙象成為藝術言說的“指月”之指,直指世界之本相,或者說,妙象本身就是世界之本相,即所謂“一花一世界”也。
荷花是荷的“傳神阿堵”,關系著荷的神韻,因而“神韻”的主要來源當然離不開這一切心象所負載的筆墨。正如石濤《畫語錄•氤氳章第七》所云:“筆與墨會,是為氤氳。氤氳不分,是為渾沌。辟渾沌者,舍一畫而誰耶?……縱使筆不筆,墨不墨,畫不畫,自有我在。……化一而成氤氳,天下之能事畢矣。”“一畫之法”之“一”是“有”,也是“無”,也是“無無、無有”的筆墨形跡,也是由“有”通向“無”的筆墨之跡化。作為張大千筆下“虛實相生合成”的“妙象”,豐厚肥碩荷花花瓣筆(線)的勾勒即是“實”,它通向“虛”的渾然;闊大圓融荷葉墨的暈染則是“虛”,或是通向“虛無”之神秘。花瓣之鮮明“有形”漸漸渾入荷葉之“無跡”,從而給人一種自由自在的玄思空間,一時分明,又一時混沌,而本心似乎正在其中。并且,它因本心而鮮明,也因本心而跡化于這一意象的自由筆墨中。與此同時,本心正與與荷花一起指向自然本體之存在,靜穆、淡遠而澄澈。因之,荷花這一妙象也就成了張大千圓融淵穆禪意的得以傳達的具體符號。
其次,“不似之似”之妙象就是藝術再現與表現相融通的“有意味的形式”。“不似”是妙象的精神性之所在,也是妙象所再現的內容;“似”是妙象的具象性之所在,也是妙象所表現的對某種精神性內容的頓悟;由此,妙象也就成了抽象性與具象性,象征性與寫實性,意象性與逼真性,表現性與再現性等各種相反相成的本質性因素相融通的藝術言說的符號,具有著豐富的象喻功能。由此,妙象不再摹仿可見物,而是以半個造物主的氣魄創造出藝術品來指向世界之本相的。這樣,妙象之“不似”是對沾滯于傳統筆法與表現的否定,“似之”是對獨特藝術符號的活用,用以顯示“似之”的實相,用以傳達無限意蘊;“不似”是再現的內容,“似”是表現的頓悟。“不似之似”之妙象就是藝術再現與表現的相融通而生成的“有意味的形式”。
我們來看畫家故去前兩年所作之《清水出芙蓉》一畫:迷蒙的氤氳之氣中,淡然伸出數莖芰荷,舒卷的荷葉如佛家壁畫里諸佛、菩薩或者飛天腳下的祥云,荷也,云也,或皆不是,或皆是,抑或無所謂“是”與“不是”;而花瓣尖上鉤著嫩金的白花瓣,則象是佛祖座下的寶座蓮花。而正是在這“似”與“不似”交融的混沌中,整個畫面籠罩在一片祥和、寧靜、恬淡和從容中,甚至彌漫著神秘的佛家光輝,從而表達了一種靜穆的淵深之美。用筆隨意而精審,用墨淺淡而精奇,無一筆多,亦無一筆少,荷莖則兩筆扣合,絲絲入骨,毫無接痕,體現了再現之“不似之極似”,充分反映了畫家晚年從容的心境以及對人生世事的徹悟,鮮明地呈現出了藝術表現的“極似之不似”情狀。近觀之,仿佛置身佛光之中,如如禪意,又渾然若忘矣。同時,又飽含著西方現代主義藝術印象派在以光色暈染的瞬間真實來直面事物本質直觀的現代性之美,以及西方現代藝術哲性言說過程中顯示出來的張力美,卻又逐漸隱去了執著筆意之痕跡。
綜上,正如筆者在《張大千荷花系列畫作禪意研究》一文中所說:張大千一生畫風多變,但總體上所呈現出來的發展脈絡,深蘊著貫通于中國傳統文人畫流變過程中的徐徐禪意。這禪意源于其仿古臨古期對文人畫意境中禪意傳統的承繼,隱于荷花意象的禪意象征,漾于形而上玄思及表現、再現的中西融通之中,并呈現出深蘊著儒釋道屈合一、又深受來自于敦煌壁畫影響的佛的圓融性、藝術風格的疏淡簡遠的空逸性和藝術表達的非執著之執著性等鮮明的藝術特色。溯源來看,張大千畫作中所傳達出的圓融淵穆的禪意境界主要源自其對于文人畫禪意傳統的承繼、對于“無心之大心”禪機的天然體悟以及對于“不似之似”妙象的象喻傳統的承繼與超越。這三個方面有機地統一于張大千臻于化境的筆墨意趣中。
(作者為河南大學文學院教師、南京大學文學院博士生)
注釋:
①賴賢宗《禪的意境美學:以禪藝合流與石濤的一畫論為研究的主要對象》,《第四次儒佛會通學術研討論文集》第162頁,臺灣華梵大學。
②宗白華《美學散步》第129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③林木《中國古典畫鳥畫的總結與升華•清代畫鳥畫綜論》,見葛廣健等編《清代花鳥畫風》,重慶出版社1997年版。
④李澤厚《中國古代思想史論》第200~201頁,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3年版。
⑤李澤厚《李澤厚哲學文存》第717頁,安徽文藝出版社1999年版。
⑥曉云法師《禪畫禪語》第95頁,臺北原泉出版社1988年版。
⑦宗白華《藝境》第148頁,北京大學出版199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