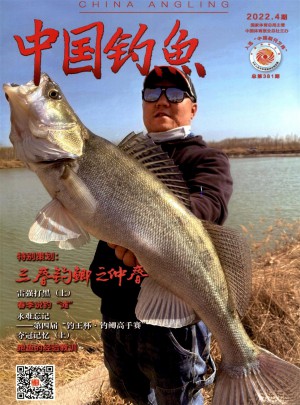引論:我們?yōu)槟砹?3篇中國歷史地理論文范文,供您借鑒以豐富您的創(chuàng)作。它們是您寫作時的寶貴資源,期望它們能夠激發(fā)您的創(chuàng)作靈感,讓您的文章更具深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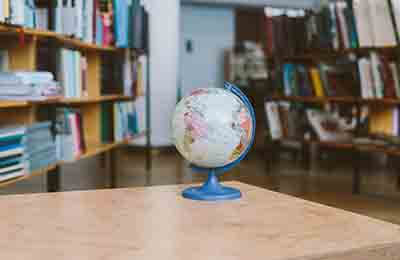
篇1
一、熵理論綜述。
1.國內(nèi)外研究綜述。
德國物理學(xué)家克勞修斯于1865年在《熱之唯動說》一書中首次定義了一個新的物理量———熵。這標(biāo)志著熵概念的正式誕生,但此時的熵理論的研究還局限于熱力學(xué)領(lǐng)域。20世紀(jì)50年代隨著信息論在美國的出現(xiàn),熵理論以“信息熵”的形式蔓延到非熱力學(xué)領(lǐng)域。經(jīng)過麥克斯韋、波爾茲曼、杰尼斯、維納、普利高津等人的努力研究,熵的泛化應(yīng)用迅速在經(jīng)濟(jì)、城市規(guī)劃、決策分析、人工智能與哲學(xué)方面展開。1923年科學(xué)家普蘭克首次將“熵”引入中國,隨后我國涌現(xiàn)出了許多熵理論的研究學(xué)者,很多學(xué)者開始嘗試著把這概念用在管理學(xué)的研究中,也有很多學(xué)者將熵應(yīng)用在企業(yè)的知識管理、品牌擴(kuò)散和企業(yè)效益評價等領(lǐng)域中,但是將熵應(yīng)用在競爭態(tài)勢和戰(zhàn)略分析中的并不多見。我們在前人研究基礎(chǔ)上,嘗試用熵理論來分析直國的快遞市場的競爭態(tài)勢。
2.熵思想概述。
熵是一個廣延量,是微觀態(tài)數(shù)大小,分子運(yùn)動混亂程度的度量,這就是熵的統(tǒng)計意義,從通俗的意義上來理解,熵的含義就是一個系統(tǒng)的混亂程度。對于任何一個系統(tǒng)的熵都遵循以下原理:
(1)基熵原理;(2)熵增原理與最大熵原理;(3)測準(zhǔn)原理。
二、基于基熵原理的市場競爭主體能力與分析。
任何系統(tǒng)都有個基熵,而每一個企業(yè)都有自己獨(dú)特的能力域。這里的能力域不僅僅是企業(yè)的業(yè)務(wù)領(lǐng)域和范圍,還包括一個企業(yè)未來的發(fā)展?jié)摿秃诵牡母偁幠芰λ凇S捎诿恳活惼髽I(yè)在發(fā)展歷程和能力的積累有所不同,因此每一個企業(yè)的核心業(yè)務(wù)領(lǐng)域有所不同。在這種快遞業(yè)重新洗牌的過程中,各種不同的競爭努力都在大舉攻城略地。根據(jù)它在經(jīng)營能力和業(yè)務(wù)范圍上的不同,我們將它們劃分為不同的能力域。
1.現(xiàn)有市場主題的能力域。
在我國的快遞市場中,競爭主體有以下三類:外貿(mào)快遞企業(yè)、中國郵政和國內(nèi)其他快遞企業(yè)。外貿(mào)快遞企業(yè)主要是以DHL,TNT,UPS,F(xiàn)EDXE四大巨頭為代表的跨國性快遞企業(yè)。部分是跟隨著他們的客戶來到中國,主要是將中國的貨物運(yùn)往海外,并將海外的商品運(yùn)抵中國。在中國境內(nèi)現(xiàn)有的快遞企業(yè)中,中國郵政無論從歷史規(guī)模還是影響力方面都是當(dāng)之無愧的龍頭。中國郵政在國內(nèi)快遞中建立了318個城市快遞郵件的查詢和跟蹤系統(tǒng),占有國內(nèi)快遞業(yè)務(wù)的70%左右的市場份額,占據(jù)了絕對領(lǐng)先的地位。而在國際快遞市場上,中國郵政大概僅僅占據(jù)了22%的市場份額。不僅如此,在服務(wù)的質(zhì)量和業(yè)務(wù)類型方面中國郵政主要承攬文件類和一般商品類快遞,而對于精細(xì)快遞和特殊要求的快遞大部分由外資企業(yè)來承攬。
在我國的快遞市場上,除了中國郵政之外,一些由傳統(tǒng)的運(yùn)輸業(yè)或者全儲企業(yè)轉(zhuǎn)型而來的國有物流企業(yè)如中鐵快運(yùn)、中外運(yùn)還有民航快遞等也是值得關(guān)注的國有快遞企業(yè)。它們因為擁有巨大網(wǎng)絡(luò)優(yōu)勢,在我國的區(qū)域快遞市場上也擁有很大的市場份額。但是這些快遞企業(yè)是從傳統(tǒng)的物流企業(yè)轉(zhuǎn)型而來的,所以在管理水平方面還有待加強(qiáng)。民營快遞每年的業(yè)務(wù)量以60%—120%的速度遞增,一大批中型民營快遞企業(yè)如東方萬幫、宅急送、申通、大田等都逐步發(fā)展壯大起來。目前我國從事快遞業(yè)的民營企業(yè)上萬家,從業(yè)人員已達(dá)百萬之眾,主要分布在以上海、廣州、深圳、北京為核心的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環(huán)渤海經(jīng)濟(jì)圈,業(yè)務(wù)也主要集中在同城快遞領(lǐng)域。
2.快遞企業(yè)能力域分析。
這是兩個不同的主體的業(yè)務(wù)交叉領(lǐng)域,其中中國郵政和外資快遞企業(yè)的競爭主要發(fā)生在海外網(wǎng)絡(luò)的快遞競爭中,而民營企業(yè)通過價格的競爭在城際快遞中和中國郵政展開了激烈的競爭。中國快遞企業(yè)和外資企業(yè)的交叉業(yè)務(wù)領(lǐng)域相比較少,主要在國內(nèi)的區(qū)域間的快遞業(yè)務(wù)。這部分是這三種市場主體都很關(guān)心和重視的領(lǐng)域,在高端的快遞業(yè)市場服務(wù)領(lǐng)域中,三家都不惜花費(fèi),奪取市場。
三、基于熵增原理和最大熵原理的市場競爭策略分析。
根據(jù)熵增原理和最大熵原理,要想保持物流市場競爭的有序和高效性,就要一方面通過在各自獨(dú)特的細(xì)分市場中提升企業(yè)的核心競爭能力,另一方面在交叉的細(xì)分市場中減少熵增,實(shí)現(xiàn)有序的、高效健康的市場發(fā)展模式。所以我們建議我國的快遞企業(yè)應(yīng)當(dāng)采取合縱連橫的市場策略。
四、基于測不準(zhǔn)原則的快遞企業(yè)服務(wù)創(chuàng)新管理。
面對復(fù)雜多變、競爭激烈、發(fā)展迅速的市場環(huán)境,快遞企業(yè)求生存與發(fā)展,僅僅靠對現(xiàn)有業(yè)務(wù)的有效管理是遠(yuǎn)遠(yuǎn)不夠的,要想獲得長期的競爭優(yōu)勢,實(shí)現(xiàn)持續(xù)健康的發(fā)展,必須牢牢抓住“服務(wù)創(chuàng)新”這根生命線。服務(wù)創(chuàng)新能夠提高企業(yè)經(jīng)營效率,創(chuàng)造當(dāng)期利潤,更重要的是它能夠培育企業(yè)的核心能力,從而贏得未來的競爭。
首先,要建立服務(wù)創(chuàng)新的企業(yè)文化。建立以客戶為導(dǎo)向的服務(wù)理念,能夠激發(fā)人員主動去探求和發(fā)現(xiàn)現(xiàn)有服務(wù)中的真空地帶和能夠改進(jìn)的方向。
其次,要建立鼓勵創(chuàng)新的企業(yè)制度。無論任何一種創(chuàng)新總是要充滿風(fēng)險的,同時創(chuàng)新就是一種對傳統(tǒng)的挑戰(zhàn),總是要面臨很多阻力和困擾。所以需要從公司的制度層面對于勇于創(chuàng)新的人進(jìn)行相應(yīng)的保護(hù)和支持。
最后,要建立良好的組織結(jié)構(gòu)促進(jìn)創(chuàng)新的發(fā)生機(jī)率。組織結(jié)構(gòu)是企業(yè)中人和人交往的基本框架,扁平化的、團(tuán)隊式的工作方式更加能夠促進(jìn)創(chuàng)新的發(fā)生。
隨著中國快遞業(yè)市場的不斷發(fā)展和成熟,市場中的競爭也變得日益激烈。通過在熵視角下對于我國快遞業(yè)市場的分析可以看出,在現(xiàn)有的市場競爭狀態(tài)下,我國的企業(yè)能夠通過合縱連橫和服務(wù)創(chuàng)新來提升自己的競爭力,突出重圍。
參考文獻(xiàn):
[1]任亞飛。民營快遞業(yè)的發(fā)展及其戰(zhàn)略選擇[J]。中國儲運(yùn),2006,(4):79-81.
[2]紫營輝。中國快遞業(yè)高局:四方勢力利益博弈再度升級[J]。北方經(jīng)濟(jì),2006,(2):55.
篇2
《中國文法要略》(以下簡稱《要略》)成書于上世紀(jì)四十年代,是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中國文法革新運(yùn)動后出現(xiàn)的一部漢語語法學(xué)力作。它打破了模仿西洋文法的舊框框,致力于探索漢語語法結(jié)構(gòu)的特點(diǎn)及規(guī)律,在中國語法學(xué)界產(chǎn)生了巨大影響。它的問世,在我國語言學(xué)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是革新探索時期漢語語法研究所取得的重大成果之一。
本文擬用歷史的眼光,從學(xué)術(shù)角度全面、客觀、公正地評價其歷史地位、價值,努力擺脫偏見,對其成功之處進(jìn)行充分肯定。
一、“動詞中心”說和動詞“向”的提出
所謂“動詞中心”是指在進(jìn)行語法分析時以動詞為中心的一種觀點(diǎn)和方法。這種語法分析方法己成為當(dāng)代多數(shù)語言研究者的共識。《要略》可以說是提出“動詞中心”理論的先聲之作。《要略》把單句分為四種:敘事句、表態(tài)句、判斷句、有無句。其中敘事句是“最常用的一種”。對于敘事句,《要略》指出,“這類句子的中心是一個動詞”。又說,“拿敘事句來說,既是敘述一件事情,句子的重心就在那個動詞上,此外凡動作之所由起,所于止,以及所關(guān)涉的各方面,都是補(bǔ)充這個動詞把句子的意義說明白,都可以稱為‘補(bǔ)詞’”。這些看法,可概括為“動詞中心”說。
基于這一觀點(diǎn),敘事句的基本格式為“起詞(動作起點(diǎn))—動詞—止詞(動作止點(diǎn))”,指出,起詞和止詞“這兩個名稱都是跟著動詞來的,沒有動作,就無所謂起和止。”之后,《要略》著重討論了兩個方面:(1)是否凡是敘事句都有起、動、止這三個成分;(2)這三個成分的次序是否都是“起—動—止”。通過詳盡描寫,《要略》勾勒了敘事句,即動詞謂語句的句型系統(tǒng)。
關(guān)于動詞“向”的概念,《要略》指出:有些句子只有“起”是因為許多動作只和一個人或物發(fā)生關(guān)系,所以有起詞而無止詞。“例如水的流,花的開和謝,以及行、止、坐、臥、來、去等等動作都是只有一個方向,沒有兩個方向的;說得更確切些,這些動作都是停留在起詞身上,不投射到外面去的。”動詞的“向”或“配價”的研究是現(xiàn)今語法界的熱點(diǎn)問題。1978年熙先生在《“的”字結(jié)構(gòu)和判斷句》中引入了國外關(guān)于動詞“價”的理論。經(jīng)過許多學(xué)者多年的研究,這一理論漸趨成熟,也己成為語言學(xué)界普遍接受。但是,在追尋這一理論源頭時,所關(guān)注的主要是國外語言學(xué)界。也有學(xué)者認(rèn)為:“80年代初我國漢語語法學(xué)界興起的關(guān)于動詞‘向’的研究熱,是舶來品和本土根的接通或殊途同歸的結(jié)果”,“中國傳統(tǒng)語法有一條粗壯的根,這就是重視語義分析和主張‘動詞中心’說”。它的突出代表可以溯源到呂叔湘的《中國文法要略》等著作。
二、轉(zhuǎn)換分析法的運(yùn)用
熙先生在《漢語語法叢書》序中說:“《要略》應(yīng)該說是研究漢語句法結(jié)構(gòu)變換關(guān)系的先驅(qū)。”在上卷“詞句論”里分別討論了句子和詞組、句子和句子之間的變換關(guān)系。尤其是句子和詞組之間的變換關(guān)系,其中有些觀察是相當(dāng)深入的。《要略》發(fā)展了傳統(tǒng)的轉(zhuǎn)換分析法,廣泛地使用轉(zhuǎn)換分析法來論證漢語的基本句型。
《要略》認(rèn)為“大概說來,相同的幾個概念,可以配合成句子,也可以配合成詞組;所以一句現(xiàn)成的句子大概可以改換成一個詞組,大多數(shù)的詞組也可以改換成句子。”《要略》設(shè)專章來討論句子與詞組的變換,從結(jié)構(gòu)類型和語義性質(zhì)上討論了句子和詞組的種種變換關(guān)系,指出哪類句子可以變換成詞組,哪些句子不能變換,說明變換的條件和規(guī)則以及不能變換的理由。如書中指出,敘事句一般都能轉(zhuǎn)化為名詞性詞組,而存在句、領(lǐng)屬句和判斷句則不能轉(zhuǎn)換成名詞性詞組。還指出,帶指人的“補(bǔ)詞”的敘事句轉(zhuǎn)換成詞組時必須補(bǔ)一個代詞復(fù)指成分“他”(你送花給一個人你送花給他的人)。
變換分析是一種有極大潛力的方法,可以揭示隱性關(guān)系。漢語是一種非形態(tài)語言,句子的各成分之間的關(guān)系往往是隱含的,缺乏顯露在外的形式標(biāo)志。根據(jù)這種特點(diǎn),變換分析法便成為非常有用的分析手段。通過變換可以把隱含的關(guān)系顯露出來,以便清楚地觀察語句構(gòu)造的類型和特點(diǎn)。例如:
水流流著的水/流水
她質(zhì)問她的質(zhì)問
星月光明星月的光明
老牛拉車?yán)吓@能?/p>
以上各例,從顯性角度看,都是“附加關(guān)系”,但從隱性角度看,它們又有不同的語義關(guān)系:①是動作和系事,②是動作和施事,③是事物和狀態(tài),④是動作和受事。可見,運(yùn)用變換能夠使我們顯性結(jié)構(gòu),看到其隱藏于內(nèi)的種種語義關(guān)系,從而揭示句法和語義間的聯(lián)系。
三、完整的“表達(dá)論”體系
呂叔湘在《重印題記》(1982年)中提到:“語法書可以有兩種寫法:或者從聽和讀的人的角度出發(fā),以語法形式(結(jié)構(gòu),語序,虛詞等)為綱,說明所表達(dá)的語法意義;或者從說和寫的人的角度出發(fā),以語法意義(各種范疇,各種關(guān)系)為綱,說明所賴以表達(dá)的語法形式。”前者是“從外到內(nèi)”,后者是“從內(nèi)到外”。《要略》第一次實(shí)踐了對漢語語法“從內(nèi)到外”的系統(tǒng)描寫。
《要略》的“表達(dá)論”部分占全書篇幅的三分之二,材料豐富、分析細(xì)致。根據(jù)漢語自身的特點(diǎn),“表達(dá)論”設(shè)立了多種“范疇”和“關(guān)系”。如“范疇”下設(shè):數(shù)量、指稱、方所、時間、正反、虛實(shí)、傳信、行動、感情等。“關(guān)系”下設(shè):離合·向背、異同·高下、同時·先后、釋因·紀(jì)效、假設(shè)·推論、擒縱·襯托。并從邏輯的角度(即以語義為綱),把各類范疇、各類關(guān)系聯(lián)系起來使整個“表達(dá)論”成為一個有機(jī)的整體。《要略》的論“關(guān)系”部分可以說是表達(dá)論的精華。這部分把表面上似乎不同的各種關(guān)系,用意念上的聯(lián)系、程度的差異、著重點(diǎn)的不同幾條線索串連起來,構(gòu)成了一個邏輯上有密切聯(lián)系的整體。
這是漢語語法學(xué)史上第一個完整的表達(dá)論體系。它以很強(qiáng)的實(shí)用性和體系的完整性,為《要略》也為漢語語法學(xué)史增輝不少,給今后的語法研究提供了一個重要的思路。
四、對比研究的提倡
篇3
對《水經(jīng)注》的研究一直是學(xué)術(shù)界研究的熱點(diǎn),自九零年以來出版的《水經(jīng)注》新版本及研究專著有14部,發(fā)表的相關(guān)論文近190篇,研究涉及到地理學(xué)、歷史學(xué)、文學(xué)、考據(jù)學(xué)等多個學(xué)科,還包括對《水經(jīng)注》版本、《水經(jīng)注》體例、歷代酈學(xué)家治酈過程、回歸原典等問題的探討,其中既有集大成的研究成果也有零散的查漏補(bǔ)缺。筆者現(xiàn)茲及所見,擇要作一綜述。
一、《水經(jīng)注》版本與專著
近二十年來研究《水經(jīng)注》的專著,最應(yīng)介紹的就是陳橋驛的著作。陳先生出身酈學(xué)世家,從事《水經(jīng)注》校釋工作也已四十多年,《水經(jīng)注校釋》是他畢生研究酈學(xué)厚積薄發(fā)的成果。該書以武英殿本為底本,參校各種《水經(jīng)注》版本33種,地方志120余種,其他文獻(xiàn)近300種,其中包括殘宋本《水經(jīng)注》等一批不易獲見的珍本或孤本,可以說是“《水經(jīng)注》眾多校釋版本中繼往開來、承先啟后之作”[1],該書問世后,在學(xué)界引起巨大的反響,評論文章也不斷問世。周筱云在《酈學(xué)研究的新成果――評陳橋驛〈水經(jīng)注校釋〉》(《浙江學(xué)報》,1999年06期)中高度贊揚(yáng)了《水經(jīng)注校釋》在版本校勘、歷史地理學(xué)上的成績,及在校記中對地名差異的重視和每卷卷末的《釋》,同時也指出該書沒有索引極大程度上降低了實(shí)用價值。《水經(jīng)注校證》則繼承了《水經(jīng)注校釋》的優(yōu)良學(xué)術(shù)品質(zhì),并增補(bǔ)了近代酈學(xué)研究成果及中外學(xué)術(shù)成果,是研究《水經(jīng)注》不可多得的佳本。當(dāng)然,任何一部著作,都不可能是完美無缺的,《水經(jīng)注校證》也不例外。宋震昊《陳橋驛〈水經(jīng)注校證〉校點(diǎn)商榷》(《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10年4月)擇出該書標(biāo)點(diǎn)錯誤二十余條,頗有補(bǔ)益之效。王先謙先生的《合校水經(jīng)注》則是便于一般讀者使用的版本,該書影印光緒十八年思賢講舍原刻本《合校水經(jīng)注》,彌補(bǔ)了1985年巴蜀書社以新化三味書室的翻刻本為底本,而沒有采用王氏原本的遺憾。但其沒有對校像殘宋本和《永樂大典》本等早期傳本,頗以為憾。
《酈道元評傳》、《水經(jīng)注研究四集》、《酈學(xué)札記》、《水經(jīng)注圖》、《水經(jīng)注論叢》等則是陳橋驛先生近二十年來的《水經(jīng)注》研究專著,分別從不同側(cè)面記述了作者的酈學(xué)成果。《酈道元評傳》從酈道元所處時代及其家世出發(fā),在《水經(jīng)注》中尋索酈氏業(yè)績,同時也闡發(fā)了《水經(jīng)注》中的愛國主義情懷。該書末附有按筆畫編排的索引,使得查找極為便利。《酈學(xué)札記》則匯集了陳先生多年的酈學(xué)心得。《水經(jīng)注圖》分為圖本和文本兩冊,校勘注釋,深入淺出,精思密致,經(jīng)緯厘然。《水經(jīng)注論叢》則精選了以往四集酈學(xué)論文中側(cè)重版本知識和酈學(xué)家兩方面的部分成果結(jié)集出版。此外陳先生還有一些版本方面的論文問世,如《〈水經(jīng)注〉版本和校勘的研究》(杭州師范學(xué)校學(xué)報,2000年01期)使讀者對《水經(jīng)注》各版本的源流以及校勘成果有了清楚的認(rèn)識。
此外,《水經(jīng)注全譯》、《水經(jīng)注選譯》、《水經(jīng)注選評》使得《水經(jīng)注》的可讀性大大增強(qiáng),起到了普及讀物的作用。《水經(jīng)注農(nóng)桑輯要》、《圖解水經(jīng)注》、《〈水經(jīng)注〉與北魏史學(xué)》則從農(nóng)桑、地理、史學(xué)的不同的角度對《水經(jīng)注》進(jìn)行了解讀。
二、考證與詮釋
因為時代、版本、傳抄等因素的影響,加上《水經(jīng)注》原書引用前代的典籍?dāng)?shù)量巨大,稍有不慎,就會發(fā)生差錯。陳橋驛《〈水經(jīng)注〉之誤》(《中國地名》,2001年04期)從河流水道方面列舉了《水經(jīng)注》中以黃河河源錯誤為代表的河流記載之誤,并闡述了產(chǎn)生這些錯誤的原因。金文明《〈水經(jīng)注〉標(biāo)點(diǎn)差錯舉偶》(《編輯學(xué)刊》,2001年03期)、王浩《三版〈水經(jīng)注〉標(biāo)點(diǎn)商兌》(《文教資料》,1996年05期)、以及前文提到的宋震昊《陳橋驛〈水經(jīng)注校證〉校點(diǎn)商榷》(《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10年04期)對不同版本中存在的標(biāo)點(diǎn)問題及錯誤予以分析考證。王勇《〈水經(jīng)注疏〉校讀札記(一)》(《中國典籍與文化》,2007年02期)、嘉昆《楊守敬〈水經(jīng)注疏〉糾謬一則》(《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9年04期)分別糾正了《水經(jīng)注》中有關(guān)文字和澧水縣的錯誤。楊世燦《楊守敬〈水經(jīng)注疏〉稿本辨?zhèn)巍罚ā度龒{大學(xué)學(xué)報》,1995年04期)對諸稿本源流及關(guān)系進(jìn)行了清理,并在此基礎(chǔ)上澄清了酈學(xué)研究中所謂“謄清正本”之訛。
關(guān)于《水經(jīng)注》中河流的考證也一直是學(xué)術(shù)的熱點(diǎn)。鮑善淳《〈水經(jīng)注〉“亂流”考釋》(《古漢語研究》,2001年03期)、劉茂真《〈水經(jīng)注〉記述西江水系一些河流的源頭和流向有謬誤》(《廣西地方志》,2002年04期)、朱圣鐘《〈水經(jīng)注〉所載土家族地區(qū)若干歷史水文地理問題考釋》(《中央民族大學(xué)學(xué)報》,2002年06期)、張曉東《〈水經(jīng)注〉所載漕運(yùn)史與運(yùn)河史資料及問題考述》(《重慶社會科學(xué)》,2007年06期)、朱士光《論〈水經(jīng)注〉對(溱)水之誤注兼論〈水經(jīng)注〉研究的幾個問題》(《史學(xué)集刊》,2009年01期)、羅平《〈水經(jīng)注〉中的白渠水即今洼陽河》(《文物春秋》,2004年01期)等文章通過史料的考證,指出了《水經(jīng)注》中詞匯、水文記載等的相關(guān)問題或存在的謬誤。
三、歷史地理學(xué)研究
《水經(jīng)注》是一部包羅廣泛的歷史名著,也是一部以水道為綱的地理著作,它對歷史人文地理及歷史自然地理的記載歷來受到酈學(xué)家的重視。劉不朽《〈水經(jīng)注?三峽〉之歷史地理、人文地理價值》(《中國三峽建設(shè)》,2004年05期)、梁中效《〈水經(jīng)注〉中的三國經(jīng)濟(jì)地理》(《漢中師范學(xué)院學(xué)報》,1997年第1期)、劉景純《〈水經(jīng)注〉流域地理的發(fā)現(xiàn)與撰述》(《西夏研究》,2011年02期)、汪一鳴《〈水經(jīng)注〉黃河銀川平原段若干歷史地理問題討論》(《寧夏社會科學(xué)》,2009年3月)、劉景純的《〈水經(jīng)注?漳水〉記載的區(qū)域山水地理》(《陜西師范大學(xué)繼續(xù)教育學(xué)報》,2001年第9期)等文章分別從不同流域、不同時間、不同角度論證了《水經(jīng)注》中所蘊(yùn)含的豐富的地理、歷史價值,一些文章頗有見地,如《〈水經(jīng)注〉黃河銀川平原段若干地理問題討論》討論了五個歷史地理問題,其中重點(diǎn)探討了黃河銀川平原段不同時期的古河道位置,指出所謂“東枝”實(shí)為人工灌渠。
劉景純《〈水經(jīng)注〉祠廟研究》(《中國歷史地理叢刊》,2000年04期)則對《水經(jīng)注》所載近二百個詞廟作了研究,從而對《古漢語常用字字典》的祠廟解釋作了進(jìn)一步說明。陳隆文《〈水經(jīng)注〉與祖國江河的生態(tài)危機(jī)》(《華北水利水電學(xué)院學(xué)報》,2010年02期),徐中原、王鳳《酈道元〈水經(jīng)注〉生態(tài)思想管窺》(《江南大學(xué)學(xué)報》,2010年04期)均從生態(tài)的角度出發(fā),探討了《水經(jīng)注》中表達(dá)的生態(tài)保護(hù)思想及今日的河流生態(tài)危機(jī)。
四、語言及文學(xué)價值
范文瀾先生說“《水經(jīng)注》不僅是水道變遷、地理沿革的重要記錄,就是敘事寫物,文章也極精美,讀來沒有枯燥繁雜的感覺”[2]對水經(jīng)注的文學(xué)價值作了很高的評價。
王東的《〈水經(jīng)注〉詞語拾零》(《古漢語研究》,2005年02期)、《〈水經(jīng)注〉詞匯性質(zhì)淺論》(《唐都學(xué)刊》,2006年09期)、《試論〈水經(jīng)注〉在中古漢語詞匯史研究上的語料價值》(《燕山大學(xué)學(xué)報》2010年03期)幾篇論文從漢語詞匯史研究的角度研究了《水經(jīng)注》中的詞匯系統(tǒng),為我們了解南北朝時期北方語言特色提供了重要參考。方向東教授的《〈水經(jīng)注〉詞語舉隅》(《語文研究》,2002年04期)、鮑善淳《〈水經(jīng)注〉詞語札記》(《古漢語研究》,2003年02期)則就《水經(jīng)注》中幾個多次出現(xiàn)而又意義較為特殊的詞語作出深層次的考釋,補(bǔ)充修訂大型辭書及現(xiàn)有校注本中存在的一些疏誤。
羅明月與王東的《〈水經(jīng)注〉地名反映的詞匯現(xiàn)象》(《學(xué)術(shù)探索》,2006年03期)、趙永慧《〈水經(jīng)注〉地名詞語淺析》(《渤海大學(xué)學(xué)報》,2011年03期)、劉建《〈水經(jīng)注〉復(fù)音形容詞研究》(《重慶師范大學(xué)優(yōu)秀碩士論文》,2011年)等分別從《水經(jīng)注》中的地名詞語、方位詞、復(fù)音形容詞入手,歸納中古時期漢語詞匯發(fā)展的諸多特點(diǎn)。同時也有一些學(xué)者注意到了句式的語法特征,如劉光明《〈水經(jīng)注〉“是”字判斷句考察》(《池州學(xué)院學(xué)報》,2010年02期)、張延俊《〈水經(jīng)注〉引文被動式語料研究》(《信陽師范學(xué)院學(xué)報》,2009年11期)就是這方面的代表。
陳橋驛《〈水經(jīng)注〉和它的文學(xué)價值》(《古典文學(xué)知識》,1994年03期)、錢光華《〈水經(jīng)注〉的文學(xué)價值》(《治淮》1997年12期)、張濤、羅明月《〈水經(jīng)注〉的語言藝術(shù)》(《南都學(xué)壇》,2006年11期)、黃華南《〈水經(jīng)注〉山水景物描寫的特點(diǎn)》(《韶關(guān)學(xué)院學(xué)報》,2006年07期)、張鵬飛《片言只字妙絕古今――〈水經(jīng)注〉山水文學(xué)價值探析》(《船山學(xué)刊》,2010年03期)均高度贊揚(yáng)了《水經(jīng)注》的文學(xué)價值。高建新《論〈水經(jīng)注〉對中國山水文學(xué)的獨(dú)特貢獻(xiàn)》(《內(nèi)蒙古師范大學(xué)學(xué)報》,2006年03期)則站在歷史的高度,頌揚(yáng)了《水經(jīng)注》人文景觀與自然景觀緊密結(jié)合的寫作觀,并認(rèn)為其直接導(dǎo)啟了柳宗元和徐霞客的山水游記。
五、概述類
對于“酈學(xué)”這樣一門宏博之學(xué),做總體研究確屬不易,即或做一全面介紹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陳橋驛《〈水經(jīng)注〉概論》(《華北水利水電學(xué)院學(xué)報》,2010年02期)則憑借深厚的酈學(xué)功底,深入簡出地介紹了《水經(jīng)注》的撰述與流傳、酈學(xué)的形成等情況。《酈學(xué)札記二》(《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3年02期)則通過對《水經(jīng)注》若干名本校勘次數(shù)、《水經(jīng)注疏》初稿、《水經(jīng)注圖》、方志等七個不同方面展開對《水經(jīng)注》的論述。
酈學(xué)的不斷發(fā)展,研究資料的不斷涌現(xiàn),也促使一些綜述文章的出現(xiàn)。陳橋驛《民國以來研究〈水經(jīng)注〉之總成績》(《中華文史論叢》53輯,1995年)賡續(xù)汪辟疆《明清兩代整理〈水經(jīng)注〉之總成績》,全面總結(jié)了民國以來八十余年酈學(xué)的成就,堪稱經(jīng)典之作。郗志群《最近十年來〈水經(jīng)注〉研究概述》(《中國史研究動態(tài)》,1996年05期)、徐中原《二十世紀(jì)以來〈水經(jīng)注〉研究綜述》(《湖南文理學(xué)院學(xué)報》,2008年09期)等文章則關(guān)注了不同時期的酈學(xué)研究。
六、其它
近二十年來研究《水經(jīng)注》的文章專著層出不窮,數(shù)量大、范圍廣,上文提到的五個方面并不能將其全部囊括其中,仍有一些文章從新角度闡釋《水經(jīng)注》中所蘊(yùn)含的價值。
張鵬飛《〈水經(jīng)注〉引〈詩〉考》(《文史博覽》,2006年09期)對酈道元引《詩》的獨(dú)到之處作了闡述和討論。鐘少華《電腦與考據(jù)學(xué)與〈水經(jīng)注〉》(《博覽群書》,2009年08期)論述了電腦考據(jù)帶給《水經(jīng)注》的便利與變革。李艷鳳、王嘉川《回歸原典:學(xué)術(shù)批評的必要與必須――由〈水經(jīng)注〉引發(fā)的一場學(xué)術(shù)爭論》(南京曉莊學(xué)院學(xué)報,2006年09期)以《水經(jīng)注》“萬城”之說而引發(fā)的千年聚訟為例,嚴(yán)肅指出回歸原典,重讀原典的必要與必須。嚴(yán)燕子的《〈水經(jīng)注〉案與現(xiàn)代思想史上兩條道路的爭論――重訂〈水經(jīng)注〉案的學(xué)術(shù)動機(jī)再探》(《湘潮》2009年03期)是對晚年重新考證趙戴相襲案的學(xué)術(shù)動機(jī)的探討。
基于以上介紹,筆者認(rèn)為近二十年來《水經(jīng)注》研究的成果是比較豐碩的,在許多重要問題上提出了新穎而富有啟發(fā)性的見解。版本與專著方面,盡管由于歷代學(xué)者的努力,已難以出現(xiàn)集大成之作,但仍有《水經(jīng)注校釋》、《水經(jīng)注校證》這樣的優(yōu)秀作品問世,不能不說是酈學(xué)界的一大喜事。考證與詮釋、歷史地理學(xué)研究、語言及文學(xué)價值、概論等方面的文章也層出不窮,有不少的考證文章來論述《水經(jīng)注》存在的問題,非常值得提倡。《水經(jīng)注》在語言及文學(xué)價值、編目特點(diǎn)、回歸原典等方面的研究基本是零散的查漏補(bǔ)缺。除此以外,《水經(jīng)注》的生態(tài)意識也引起了一些專家的重視,這對我們今天的生態(tài)保護(hù)、可持續(xù)發(fā)展都有著重要的指導(dǎo)意義。這些表明,《水經(jīng)注》研究正日趨完善,其空白與疏漏也在不斷減少。然而,如果從更為深刻而立體的層面對《水經(jīng)注》進(jìn)行闡釋,那么將會有更加廣闊的空間值得我們的去開拓。
篇4
自然環(huán)境是人類賴以生存的基本條件,其變遷必然會對人類社會經(jīng)濟(jì)產(chǎn)生影響。在自然環(huán)境諸要素中,與唐宋之際經(jīng)濟(jì)格局變遷關(guān)系至為密切的三方面當(dāng)是氣候變遷、森林植被變遷和水系變遷。
關(guān)于氣候變遷。氣候?qū)θ祟惿鏍顩r的影響重大而深遠(yuǎn).特別是氣溫升降和干濕狀況的變化對于人類經(jīng)濟(jì)行為的選擇之影響尤為突出.竺可楨《中國歷史上氣候之變遷》(《東方雜志》22:3.1925.2)為研究歷史時期氣溫變遷的較早成果。1972年.竺氏又在《考古學(xué)報》第1期發(fā)表《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認(rèn)為唐宋之際正處于物候時期由第三個溫暖期(公元600年到1000年)向第三個寒冷期(公元1000年到1200年)轉(zhuǎn)變的階段,年平均氣溫持續(xù)下降,致使生物分布亦出現(xiàn)較:丈變化。張家誠等《我國氣候變遷的初步探討》(《科學(xué)通報》19:4,1974)、任振球《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的異常期及其天文成因》(《農(nóng)業(yè)考古》1986.1)等文,又做進(jìn)一步申論.龔高法等《歷史時期我國氣候帶的變遷及生物分布界限的推移》(《歷史地理》第5輯.1987)認(rèn)為,隋唐溫暖時期,亞熱帶北界位置較之現(xiàn)代北移1個多緯度;而宋代寒冷時期,亞熱帶北界位置較之現(xiàn)在則南移1個緯度以上。
也有部分學(xué)者從區(qū)域研究角度對竺氏觀點(diǎn)作局部的修正和補(bǔ)充。張?zhí)祺搿堕L江三角洲歷史時期氣候的初步研究》(《華東師大學(xué)報》1982.4)認(rèn)為,長江三角洲在公元500年至850年處于暖期,公元850年至1200年處于冷期。王開發(fā)等《根據(jù)孢粉組合推斷上海西部三千年來的植被、氣候變化》(《歷史地理》第6輯,1988)認(rèn)為上海西部在公元550年至1100年期間氣溫處于上升階段。李一蘇《江西唐代以來的冷暖振動》(《農(nóng)業(yè)考古》1990.1)認(rèn)為,北宋初期的江西繼唐代之后更加溫暖。盛福堯《初探河南省歷史時期的寒暖》(《歷史地理》第7輯,1990)推斷河南省在隋唐時期以暖為主.自9世紀(jì)起轉(zhuǎn)寒;五代至宋初,暖情占優(yōu)勢,溫度有所回升;11世紀(jì)寒情顯著.滿志敏《唐代氣候冷暖分期及各期氣候冷暖特征的研究》、《黃淮海平原北宋至元中葉的氣候冷暖狀況》(分見《歷史地理》第8輯,1990;第11輯,1993)指出,唐代氣候以8世紀(jì)中葉為界可分為前后兩個時期.前期氣候冷暖的總體特征與現(xiàn)代相近,后期氣候明顯轉(zhuǎn)寒.氣候帶要比現(xiàn)代南退1個緯度。而在五代北宋之際至元中葉.包括黃淮海平原在內(nèi)的我國東部地區(qū)大部分時間都有偏暖的跡象.陳家其《江蘇近二千年來氣候變化研究》(《地理科學(xué)》1998.3)指出唐代中期以前很少有冷冬記載.何業(yè)恒《近五千年來華南氣候冷暖的變遷》(《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9.1)認(rèn)為,唐至北宋,華南氣溫較高,北宋末年氣溫逐漸降低.程遂營《唐宋開封的氣候和自然災(zāi)害》(《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02.1)認(rèn)為,在公元1000年以前,北宋東京仍處于隋唐以來的第三個溫暖期;但到了公元1000年以后,頻繁的雪災(zāi)預(yù)示著寒冷氣候的到來.
總體說來,竺可楨關(guān)于唐宋之際氣候變遷的論斷,迄今仍為學(xué)界的主流觀點(diǎn),并為眾多歷史地理教科書所采納,如王育民《中國歷史地理概論(上、下)》(人民教育,1987;1988),張步天《中國歷史地理(上、下)》(湖南大學(xué).1987;1988),史念海《中國歷史地理綱要(上、下)》(山西人民.1991),鄒逸麟《中國歷史地理概述》(福建人民.1993),張全明、張翼之《中國歷史地理論綱》(華中師范大學(xué).1995)等。
關(guān)于干濕狀況.竺可楨《中國歷史上氣候之變遷》(前揭)根據(jù)對比中國歷代旱災(zāi)和雨災(zāi)的統(tǒng)計資料,認(rèn)為唐代旱災(zāi)相對較少。徐近之《黃淮平原氣候歷史記載的初步整理》(《地理學(xué)報》1955.2)認(rèn)為長江流域一般較黃河流域濕潤.黃河中游早多于澇。1977年,鄭斯中等《我國東南地區(qū)近兩千年氣候濕潤狀況的變化》(《氣候變遷和超長期預(yù)報文集》,科學(xué))指出,自公元初以來,我國東部地區(qū)存在著水災(zāi)相對減少而旱災(zāi)相對增加的趨勢,公元1000年以前早期持續(xù)時間短,濕潤期持續(xù)時間長.其后則恰恰相反。王鄉(xiāng)、王松梅《近五千年我國中原氣候在降水量方面的變化》(《中國科學(xué)》B輯,1987,1)指出,公元630年到834年這200多年是中原地區(qū)近3000年來歷時最長的多雨期.張步天《中國歷史地理(下)》(前揭)認(rèn)為,東部地區(qū)的干濕狀況大致與氣溫對應(yīng),唐中期至北宋中葉為最長濕期.持續(xù)約240年(811年-1050年)。而且淮河以北地區(qū)旱多于撈,淮河以南地區(qū)則相反.劉俊文《唐代水災(zāi)史論》(《北大學(xué)報》1983.2)根據(jù)唐代降水旱情的統(tǒng)計分析,認(rèn)為氣候特征以溫濕為主。
關(guān)于森林植被。史念海《歷史時期黃河中游的森林》(《河三集·二集》,三聯(lián).1981)認(rèn)為,唐宋時期黃河中游的森林地區(qū)繼續(xù)縮小.山地森林受到嚴(yán)重破壞,丘陵地區(qū)的森林也有變化。宋代的破壞更遠(yuǎn)較隋唐時期劇烈,所破壞的地區(qū)也更為廣泛。林鴻榮《歷史時期四川森林的變遷(續(xù))》(《農(nóng)業(yè)考古》]985.2)指出,唐宋時期四川森林的變遷進(jìn)入漸變時期,表現(xiàn)為盆地、丘陵的原始森林基本消失.偏遠(yuǎn)山區(qū)森林受到一定程度摧殘,部分地區(qū)手工業(yè)的發(fā)展也使林區(qū)受到破壞。張靖濤《甘肅森林的歷史變遷》(《農(nóng)業(yè)考古》1986.2)指出.唐宋時期森林采伐的規(guī)模很大,時為農(nóng)耕區(qū)的黃土高原上的森林日益遭到嚴(yán)重破壞.隴南山地森林覆蓋率仍然較高.李繼華《山東森林的歷史演變》(《農(nóng)業(yè)考古》1987.1)認(rèn)為唐宋時期山東森林日益減少。朱士光《歷史時期我國東北地區(qū)的植被變遷》(《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2.4)認(rèn)為唐宋時期該地區(qū)森林未受明顯破壞。植被方面。朱士光《歷史時期農(nóng)業(yè)生態(tài)環(huán)境變遷初探》(《地理學(xué)與國土研究》1990.2)認(rèn)為,黃土高原上植被的嚴(yán)重破壞是唐宋以來的事.其后果是助長或促進(jìn)了鄂爾多斯高原和河套西部的三個沙漠的形成與發(fā)展.史念海《歷史時期森林變遷的研究》(《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88.3)和《論歷史時期我國植被的分布及其變遷》(《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1.2)兩文,認(rèn)為黃河流域、長江流域、珠江流域及東北地區(qū)的森林植被的減少大多始于唐宋之際。趙永復(fù)《歷史時期黃淮平原南部的地理環(huán)境變遷》(《歷史地理研究》第2輯,1991)指出,唐宋以后,隨本地區(qū)植被的銳減.湖澤陂塘逐漸淤成一片平陸。水早災(zāi)害加重.鄒逸麟《前揭書》認(rèn)為,唐宋之際華北平原的次生草地和灌木叢漸為大片栽培植被替代,黃河中游地區(qū)植被破壞嚴(yán)重,太行山區(qū)森林至北宋已為童山.秦嶺大巴山區(qū)森林仍然茂密。林鴻榮《隋唐五代森林述略》(《農(nóng)業(yè)考古》1995.1)指出,唐代北方森林面積進(jìn)一步縮小,不少林區(qū)殘敗,生態(tài)后果遠(yuǎn)遠(yuǎn)高于南方.而南方自然條件優(yōu)越,生態(tài)環(huán)境良好.程民生《宋代林業(yè)簡論》(《農(nóng)業(yè)考古》1995.1)指出.宋代的天然林帶主要分布于山區(qū).如南方的四川、湖南、江東和兩廣、福建北部,北方則主要集中于秦嶺山脈和京西路的部分地區(qū)以及太行山區(qū).
關(guān)于水系和湖泊。唐宋之際東部平原水系變遷較大,而尤以黃河中下游水系和長江中下游水系變遷對經(jīng)濟(jì)格局影響至為明顯。鄭肇經(jīng){中國水利史)(商務(wù),1.939)較早涉足水系變遷問題。岑仲勉《黃河變遷史》(人民,1957)為探討黃河變遷的最早專著。譚其驤《何以黃河在東漢以后會出現(xiàn)一個長期安流的局面》(《學(xué)術(shù)月刊》1962.2)認(rèn)為.安史亂后,由于生態(tài)環(huán)境的惡化,黃河下游河患增多.五代以降,河患更是愈演愈烈.史念海《由歷史時期黃河的變遷探討今后治河的方略》(《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81.1)指出.唐代后期黃河中下游河道泥沙大量增多.宋代淤泥更為嚴(yán)重,河道頻繁改易.張含英《歷代治河方略探討》(水利.1982)介紹了黃河下游在北宋初至中葉前后的五次改道情況.周魁一《隋唐五代時期黃河的一些情況》(見《黃河史論叢》.復(fù)旦大學(xué),1986)認(rèn)為.唐末下游河道漸趨淤高,曾于河口段改道,五代時期53年內(nèi)決溢19次,11世紀(jì)初又出現(xiàn)了懸河現(xiàn)象。鄒逸麟(前揭)認(rèn)為至唐末以前黃河下游河道相對穩(wěn)定.此后黃河下游進(jìn)入變遷紊亂時期.湖泊方面,鄒逸麟《歷史時期華北大平原湖沼變遷述略》(《歷史地理》第5輯,1987)認(rèn)為,從6世紀(jì)至]o世紀(jì),華北大平原上的湖沼雖有一部分消失或縮小,但整個湖招的布局似無根本性的變化。北宋時期,由于主要河流頻繁改道,華北大平原湖沼逐漸發(fā)生了較大的變遷.部分湖泊開始淤廢。
關(guān)于長江中下游水系的變遷.王育民、張步天、鄒逸麟(前揭)在學(xué)界研究成果的基礎(chǔ)上.分別進(jìn)行了概述。他們認(rèn)為,唐宋時代云夢澤已淤成平陸;下荊江統(tǒng)一河床形成,河床不斷淤積.逐步深化為河曲,北宋河患始見頻仍;洞庭湖進(jìn)一步下沉,湖面向西部擴(kuò)展;鄱陽湖因彭蠡澤迅速向東南方向擴(kuò)展,迫近鄱陽縣城。太湖平原湖泊廣布,太湖水系中之太湖至北宋復(fù)歸淤淺.泛濫時有發(fā)生,而吳淞江雖在人宋以后漸淤,但經(jīng)北宋中葉整治,情形有所改觀.李文瀾《唐代長江中游水患與生態(tài)環(huán)境諸問題的歷史啟示》(《江漢論壇》1999.1)認(rèn)為唐代是長江中游水患頻率最低的歷史時期.湖泊方面,張修桂《洞庭湖演變的歷史過程》(《歷史地理》創(chuàng)刊號,1982年)認(rèn)為,唐宋時期洞庭湖仍處于沉降擴(kuò)展之中.譚其驤、張修桂《鄱陽湖演變的歷史過程》(《復(fù)旦學(xué)報》1982.2)指出,唐末五代至北宋初期大體奠定了鄱陽湖未來的范圍和形態(tài).
二,農(nóng)牧業(yè)經(jīng)濟(jì)板塊錯動研究
在自然環(huán)境諸要素中,氣候變遷是影響我國北部農(nóng)牧業(yè)經(jīng)濟(jì)板塊發(fā)生錯動的重要原因之一。張家誠《氣候變化對中國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影響的初探》(《地理學(xué)報》1982.2)認(rèn)為,若其他條件不變,年均氣溫下降1℃,糧食單位產(chǎn)量即會較常年下降10%;年均降水量下降100毫米,糧食產(chǎn)量也會下降10%。程洪《新史學(xué)一一來自自然科學(xué)的挑戰(zhàn)》(《晉陽學(xué)刊》1982.6)認(rèn)為,若其他因素不變,某地區(qū)平均氣溫降低1℃,相當(dāng)于將該地區(qū)向高緯度推進(jìn)200到300公里;若年降水量減少100毫米.我國北方農(nóng)業(yè)區(qū)則將向南退縮100到500公里。龔高法等《氣候寒暖變化及其對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的影響》(《紀(jì)念科學(xué)家竺可楨論文集》,科學(xué)普及,1982)認(rèn)為,唐五代溫暖濕潤期農(nóng)作物的生長期比現(xiàn)在長10天以上.翁經(jīng)方等《中國歷史上民族遷徙的氣候背景》(《華東師大學(xué)報》1987.4)認(rèn)為,如果年平均氣溫下降2℃,生物的分布區(qū)域就要向南移緯度2‘至40C,反之亦然.倪根全《論氣候變遷對中國古代北方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jì)的影響》(《農(nóng)業(yè)考古》1988.1)認(rèn)為,歷史時期氣候變冷變干造成我國北方濕潤區(qū)和半濕潤區(qū)由北向南退縮,農(nóng)業(yè)地區(qū)隨之不斷南退。
關(guān)于唐宋之際的農(nóng)牧業(yè)分布,史念海《黃土高原及其農(nóng)林牧分布地區(qū)的變遷》(《歷史地理》創(chuàng)刊號,1982)指出.隴東、陜北和晉西北地區(qū),從隋唐開始逐漸由牧區(qū)轉(zhuǎn)變?yōu)檗r(nóng)區(qū),農(nóng)牧區(qū)之間的界限則處在變動之中。趙永復(fù)《歷史時期河西走廊的農(nóng)牧業(yè)變遷》(《歷史地理》第4輯.1986)認(rèn)為,河西走廊自唐安史亂后至北宋,處于畜牧業(yè)生產(chǎn)占優(yōu)勢的歷史時期。史念海《隋唐時期黃河上中游的農(nóng)牧業(yè)地區(qū)》(《唐史論叢》第2輯,陜西人民,1987)指出,唐初牧馬地原在隴右,鄂爾多斯高原也在唐初開始成為游牧區(qū).河隴各地在吐蕃占領(lǐng)時,也均為牧場.唐后期馬政漸趨廢弛,原牧馬區(qū)仍為半農(nóng)半牧區(qū)。史念海《唐代河北道北部農(nóng)牧地區(qū)的分布》(《唐史論叢》第3輯,陜西人民.1987)說,“燕山以南,在唐代已經(jīng)都成為農(nóng)耕地區(qū),司馬遷所規(guī)定的碣石龍門間的農(nóng)牧地區(qū)分界線,這時應(yīng)北移到燕山之上”。“燕山北的桑干河中游和玄水、白狼河流域。就是當(dāng)時的媯州和營州。仍當(dāng)是半農(nóng)半牧地區(qū)”。韓茂莉《唐宋牧馬業(yè)地理分布論析》(《中國歷史地理論叢》,987.2)和《宋代農(nóng)業(yè)地理》(山西古籍,1993)指出,唐后期牧馬區(qū)由前期的集中于隴右、關(guān)內(nèi)、河?xùn)|三道,轉(zhuǎn)向河淮一帶分散。而且牧馬區(qū)域穩(wěn)定程度漸差.人宋以來,河牧監(jiān)內(nèi)移,良田被占,河北路農(nóng)耕地僅為該地區(qū)總土地面積的十分之四.河?xùn)|路山區(qū)及澤、潞、遼等州軍,農(nóng)牧混雜。陜西路地處農(nóng)耕區(qū)西界,西、北兩面均為半農(nóng)半牧區(qū).程民生《宋代畜牧業(yè)略述》(《河北學(xué)刊》1990.4)指出,因失去北方及西北牧場.宋代畜牧業(yè)總量較唐代為小,但在其他地域畜牧業(yè)的發(fā)展卻超過唐代。杜瑜《甘肅、寧夏黃土高原歷史時期農(nóng)牧業(yè)發(fā)展研究》(《黃河流域地理環(huán)境演變與水沙運(yùn)行規(guī)律研究文集》第五集,海洋,1993)認(rèn)為,自唐宋時期開始,該地區(qū)由以往的半農(nóng)半牧狀態(tài)向農(nóng)業(yè)地區(qū)轉(zhuǎn)化。雍際春《宋代以前隴中黃土高原農(nóng)牧業(yè)的分布及其變遷》(《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5.2)認(rèn)為.中唐以后,隴中牧業(yè)衰退,農(nóng)業(yè)也呈不平衡發(fā)展。唐代后期肇始的濫墾之風(fēng)更使草原牧場加速退化。張澤咸認(rèn)為,西域在吐蕃占領(lǐng)期間,畜牧業(yè)有顯著振興,農(nóng)業(yè)亦未見衰落;歸義軍時代河西農(nóng)業(yè)仍稱發(fā)達(dá)(分見《漢唐間西域地區(qū)的農(nóng)牧生產(chǎn)述略》。《唐研究》四,1998;《漢唐間河西走廊地區(qū)農(nóng)牧生產(chǎn)述略》,《中國史研究》1998.1).史念海《隋唐時期農(nóng)牧地區(qū)的變遷及其對王朝盛衰的影響》(見《唐代歷史地理研究》,中國社科.1999)認(rèn)為,唐代農(nóng)牧業(yè)界線為農(nóng)耕區(qū)與半農(nóng)半牧區(qū)的界線.較漢代有所北移.東段北移到燕山山脈以上,西南端達(dá)至隴山之西,東北端伸向遼水下游.而半農(nóng)半牧區(qū)的界線則由陰山山脈西達(dá)居延海,東達(dá)燕山山脈.葛金芳《中國經(jīng)濟(jì)通史(第五卷)》(湖南人民,2002)指出.宋遼夏金時期的農(nóng)牧分界線由從外長城(即秦漢所建長城)退縮到內(nèi)長城(即明代長城)一線,即從位于東北方向的碣石向西南蜿蜒伸到龍門一線.此線以西以北,大片農(nóng)田化為牧地,除燕云一帶的部分地區(qū)外,多以畜牧業(yè)為主。就是此線以東以南的農(nóng)耕區(qū)中.草場牧監(jiān)也為數(shù)不少.
研究唐宋之際北部中國的農(nóng)牧業(yè)分布情況.尚須關(guān)注遼和西夏轄區(qū)。契丹(遼朝)南境之南京道(治今北京)、西京道(治今山西大同)地處今河北北部和山西北部,屬華北大平原的北半部。陳述《契丹社會經(jīng)濟(jì)史稿》(三聯(lián),1963)認(rèn)為。契丹北境草原以牧業(yè)居多,分布著“插花田”;而毗鄰漢區(qū)的南部地帶定居放牧的成分也逐漸增加,燕山以南則是傳統(tǒng)農(nóng)耕區(qū).鄒逸麟《遼代西遼河流域的農(nóng)業(yè)開發(fā)》(《遼金史論集》第2輯.書目文獻(xiàn),1987)認(rèn)為.自10世紀(jì)始.西遼河流域分布著墨點(diǎn)農(nóng)家村莊.遼代以后.該地成為半農(nóng)半牧區(qū),或稱農(nóng)牧交錯區(qū)。林榮貴《遼朝經(jīng)營與開發(fā)北疆》(中國社科.1988)指出,北部、西北地區(qū)和潢河(西拉木倫河)流域一帶為傳統(tǒng)畜牧業(yè)區(qū);潢河與土河(老哈河)匯流處及其周圍地區(qū).分布著零星的墾殖點(diǎn);在上京道的東部、南部和中部還分布著一些草原式的“插花田”.由于在草原地區(qū)開辟農(nóng)業(yè)區(qū),又在農(nóng)業(yè)地區(qū)開辟牧場或放牧點(diǎn).故遼代農(nóng)牧業(yè)的總體發(fā)展方向是,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向北拓展,畜牧業(yè)生產(chǎn)向南推進(jìn)。顏亞玉《契丹統(tǒng)治下的燕云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jì)》(《中國社會經(jīng)濟(jì)史研究》1989.3)指出,唐末至五代初該地區(qū)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jì)堪稱發(fā)達(dá),其后又有起伏,但仍以增長為主。鄭川水等《歷史時期遼河流域的開發(fā)與地理環(huán)境關(guān)系》(《歷史地理》第10輯.1992)認(rèn)為.在10世紀(jì)初遼河中下游平原重新出現(xiàn)點(diǎn)線分布的農(nóng)田與居民點(diǎn)。漆俠、喬幼梅《遼夏金經(jīng)濟(jì)史》(河北大學(xué),1994)指出,契丹人所在的草原地區(qū)以畜牧業(yè)為主,穿插一點(diǎn)農(nóng)業(yè);大定府以南奚人居住的部分草原和燕山山區(qū).畜牧業(yè)與農(nóng)業(yè)相間.燕山以南至白溝以北.西達(dá)東北.東至遼東.則以農(nóng)業(yè)為主,雜以部分畜牧業(yè)和果樹業(yè)。鄧輝《遼代燕北地區(qū)農(nóng)牧業(yè)的空間分布特點(diǎn)》(《歷史地理》第14輯.1998)認(rèn)為.遼代燕山以北到大興安嶺東南麓.是一個非常寬闊的農(nóng)牧交錯地帶,農(nóng)業(yè)集中于赤峰市以南的中京地區(qū),赤峰以北的上京地區(qū)則以游牧為主.農(nóng)業(yè)區(qū)的北界大約位于隆化縣北到赤峰市一帶,再向東穿過奈曼、庫倫二旗南部的黃土臺地北緣。韓茂莉《遼金農(nóng)業(yè)地理》(中國社科,1999)指出契丹立國之前以畜牧業(yè)為主,還未形成固定的農(nóng)業(yè)墾殖區(qū),漢城主要分布于西拉木倫河、大凌河、灤河流域。遼建立后,主要農(nóng)業(yè)區(qū)分布于西拉木倫河流域、醫(yī)巫閶山北端以及中京周圍,遼東、燕云地區(qū)亦以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為主,畜牧業(yè)區(qū)以北疆和東北疆最為廣泛,半農(nóng)半牧區(qū)的典型區(qū)域為河?xùn)|、代北一帶。
西夏轄區(qū)在今甘肅、寧夏一帶。江一鳴《歷史時期寧夏地區(qū)農(nóng)林牧分布及其變遷》(《中國歷史地理論叢》]988.3)研究了寧夏地區(qū)或農(nóng)或牧的變遷過程。漆俠、喬幼梅(前揭)認(rèn)為,除夏州一帶的毛烏素沙漠地區(qū)外,西夏境內(nèi)皆適宜畜牧業(yè).農(nóng)業(yè)區(qū)集中于靈州、橫山天都山一帶的片段土地.以及河西走廊。韓茂莉《西夏農(nóng)業(yè)區(qū)域的形成及其發(fā)展》(《歷史地理》第l0輯.1992)指出,西夏農(nóng)耕業(yè)最為成熟與穩(wěn)固的地區(qū)是銀川平原及宋、夏交界處的丘陵山地,河西走廊附近的農(nóng)業(yè)亦有一定發(fā)展,但不占重要地位。杜建錄《西夏經(jīng)濟(jì)史》(中國社科,2002)認(rèn)為,西夏的農(nóng)業(yè)區(qū)為興靈平原和內(nèi)蒙古河套平原,荒漠與半荒漠牧區(qū)由鄂爾多斯與阿拉善兩大高原組成,農(nóng)牧相間的半農(nóng)半牧生態(tài)區(qū)主要分布在河西走廊與宋夏沿邊山界.
三、經(jīng)濟(jì)重心南移研究
唐宋經(jīng)濟(jì)重心南移問題的提出。始見于張家駒《中國社會中心的轉(zhuǎn)移》(《食貨》2:11,1935),其后張氏又相繼發(fā)表《宋室南渡前夕的中國南方社會》(《食貨》4:1,1936)和《宋代社會中心南遷史(上)》(商務(wù),1942)重申自己的觀點(diǎn)。半個多世紀(jì)以來.學(xué)術(shù)界就此進(jìn)行了激烈的討論,焦點(diǎn)主要集中于對經(jīng)濟(jì)重心的理解、南移完成的時間、南移的判定標(biāo)準(zhǔn),以及南移的具體內(nèi)容等方面.
在對經(jīng)濟(jì)重心的理解上,韓國磐《隋唐五代史綱》(人民.1977)提出安史亂后唐代財賦重心在江南的說法.冀胡鼎《中國歷史上的基本經(jīng)濟(jì)區(qū)與水利事業(yè)的發(fā)展》(中國社科,1981)提出基本經(jīng)濟(jì)區(qū)的概念,認(rèn)為隋唐時期,長江流域取代黃河流域.已取得了基本經(jīng)濟(jì)區(qū)的地位。袁莢光、李曉路《唐代財政重心的南移與兩稅法的產(chǎn)生》(《北京師院學(xué)報》1985.3)提出財政重心的說法,但認(rèn)為唐代后期財政重心的南移并不等同于經(jīng)濟(jì)重心的南移。鄭學(xué)檬《中國古代經(jīng)濟(jì)重心南移的若干問題探討》(《光明日報》1988.6.15;《農(nóng)業(yè)考古》1991.3)贊同.財賦重心”的提法.趙德馨《我們想寫一部怎樣的<中國經(jīng)濟(jì)通史<》(《中國社會經(jīng)濟(jì)史研究》1997.3),則區(qū)分了.經(jīng)濟(jì)重心地區(qū)”與.經(jīng)濟(jì)中心地區(qū)”的不同,認(rèn)為.經(jīng)濟(jì)重心地區(qū)”是指經(jīng)濟(jì)較其他地區(qū)發(fā)達(dá)、財富較其他地區(qū)多的地區(qū),是經(jīng)濟(jì)發(fā)展、財富分布不平衡的結(jié)果。
在南移時間的看法上.學(xué)界存有較大分歧。依各家意見提出的先后次序而盲,第一種是“南宋說”.張家駒(前揭文)認(rèn)為,中唐以后.南方社會的發(fā)達(dá)已漸漸超過北方。及至宋代.東南已完全成為國家根本。而南宋時代更為中國社會經(jīng)濟(jì)中心轉(zhuǎn)變的最大關(guān)鍵.其所撰《兩宋經(jīng)濟(jì)重心的南移》(湖北人民.1957)再次強(qiáng)調(diào),宋王朝的南渡標(biāo)志著南方經(jīng)濟(jì)的空前發(fā)展.這一時期是我國歷史上經(jīng)濟(jì)重心完成南移行程的時代。鄭學(xué)檬《中國古代經(jīng)濟(jì)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經(jīng)濟(jì)研究》(岳麓,1996)認(rèn)為.經(jīng)濟(jì)重心南移至北宋后期已接近完成.至南宋則全面實(shí)現(xiàn)。第二種是.隋代說”。全漢升《唐宋帝國與運(yùn)河》(重慶商務(wù),1944)認(rèn)為,中古之經(jīng)濟(jì)重心在隋代業(yè)已南移.第三種是“晚唐五代說.,韓國磐《五代時南中國的經(jīng)濟(jì)發(fā)展及其限度》(《廈門大學(xué)學(xué)報》1956.1)認(rèn)為,五代時南中國的農(nóng)業(yè)、手工業(yè)、商業(yè)的發(fā)展均較北方發(fā)達(dá).曹爾琴《唐代經(jīng)濟(jì)重心的轉(zhuǎn)移》(《歷史地理》第2輯,1982)認(rèn)為.唐代后期經(jīng)濟(jì)重心從我國北方轉(zhuǎn)向南方。童超《東晉南朝時期的移民浪潮與土地開發(fā)》(《歷史研究》1987.4)認(rèn)為。經(jīng)濟(jì)重心南移始于東晉南朝,終于唐五代。唐長孺《魏晉南北朝隋唐史三論》(武漢大學(xué),1992)認(rèn)為,安史亂后.經(jīng)濟(jì)重心加速向南方傾斜.終南移于長江流域。翁俊雄《唐代區(qū)域經(jīng)濟(jì)研究》(首都師大,2001)認(rèn)為唐代后期經(jīng)濟(jì)的總體水平大大超過唐前期。尤其是長江流域。寧可主編《隋唐五代經(jīng)濟(jì)卷》(經(jīng)濟(jì)日報,2000)指出。大體上從安史亂后,南方經(jīng)濟(jì)發(fā)展的水平超過北方,全國的經(jīng)濟(jì)重心轉(zhuǎn)移到南方。第四種是“宋代說”,李劍農(nóng)《宋元明經(jīng)濟(jì)史稿》(三聯(lián),1957)說,“宋以后之經(jīng)濟(jì)重心遂移于東南”。漆俠《宋代經(jīng)濟(jì)史(上、下)》(上海人民.1987,1988)認(rèn)為宋代經(jīng)濟(jì)水平整體上是“北不如南.西不如東”。葛金芳《宋遼夏金經(jīng)濟(jì)研析》(武漢,1991年)根據(jù)《元豐九域志》的統(tǒng)計數(shù)據(jù),認(rèn)為北宋熙豐年間(1068年-1085年)耕地和勞動力資源重心的南移過程已經(jīng)完成.近在《中國經(jīng)濟(jì)通史(第五卷)》(前揭)中又重申了這個觀點(diǎn).但程民生《宋代北方經(jīng)濟(jì)及其地位新探》(《中國經(jīng)濟(jì)史研究》1987.3)認(rèn)為,北宋時我國的經(jīng)濟(jì)重心似仍在北方。程撰《宋代糧食生產(chǎn)的地域差異》(《歷史研究》1991.2)中甚至認(rèn)為宋代“北方地位比南方有過之而無不及”。稍后又在專著《宋代地域經(jīng)濟(jì)》(河南大學(xué),1992)中說,”宋代南北經(jīng)濟(jì)各有特色。經(jīng)濟(jì)重心從發(fā)展趨勢上看正在南移,但從歷史現(xiàn)狀上看還未完成..五是“六朝說..羅宗真《六朝時期全國經(jīng)濟(jì)重心的南移》(《江海學(xué)刊》1984.3)為其代表。
在經(jīng)濟(jì)重心南移完成的判斷標(biāo)準(zhǔn)上.學(xué)界認(rèn)識有一個逐步深化的過程。多數(shù)學(xué)者是從人口分布人手,易曼暉《唐代的人口》(《食貨》3:6.1936)指出,天寶以后,北方南徙人口大抵集中于江南道.黃盛璋《唐代的戶口與分布》(《歷史研究》1980.6)認(rèn)為,安史亂后人口比重發(fā)生變化,黃河中下游讓位于長江中下游,汴河兩岸讓位于漢江襄鄂等州,沿海港市戶口猛增.林立平《唐后期的人口南遷及其影響》(《江漢論壇》1983.9)認(rèn)為,經(jīng)過安史之亂的人口南遷.江南人口密度已居各道之冠.我國古代的人口分布重心也由此基本上從黃河流域轉(zhuǎn)向了江南.胡煥庸《中國人口地理(上)》(華東師大,1984)指出,安史亂后.人口分布格局發(fā)生重大變化.南方遠(yuǎn)遠(yuǎn)超過北方。胡道修《開皇天寶之間人口的分布與變遷》(《中國史研究》1984.4)亦認(rèn)為安史之亂是南北人口升降的主要轉(zhuǎn)折點(diǎn).費(fèi)省《論唐代的人口分布》(《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88.2)認(rèn)為.元和時期的淮河以南及江南地區(qū)為大面積的人口密集區(qū).人口占全國三分之一。凍國棟《唐代人口問題研究》(武大,1993)指出,安史亂后人口南遷與經(jīng)濟(jì)重心南移同時發(fā)生,黃河中下游地區(qū)失去了傳統(tǒng)的人口重心地位。翁俊雄《唐后期政區(qū)與人口》(首都師大,1999)指出,安史亂后,長江流域民戶日趨增多.宋史領(lǐng)域,胡道修《宋代人口的分布與變遷》(《宋遼金史論叢》第2輯,中華,1991)認(rèn)為宋初人口分布的最大特點(diǎn)為北方人口的減少和南方人口的增加。人口增加之區(qū)主要分布在東南、江淮一帶,這是南方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中國經(jīng)濟(jì)重心南移的表現(xiàn)。吳松弟《中國人口史(第三卷)》(復(fù)旦大學(xué),2000)指出,遼宋初期無疑是南北人口分布的一個轉(zhuǎn)折點(diǎn),此前北方人口占優(yōu),此后南方人口逐漸確立了絕對優(yōu)勢,并一直維持到明清時期。
后來漸涉農(nóng)田水利、蠶絲紡織、自然生產(chǎn)力和城市分布等諸多方面。論者們普遍認(rèn)為,南方水利事業(yè)在中唐以后的大規(guī)模興修,是促使南方經(jīng)濟(jì)趕超北方經(jīng)濟(jì)的重要原因之一.鄒逸麟《從唐代水利建設(shè)看與當(dāng)時社會經(jīng)濟(jì)有關(guān)的兩個問題》(《歷史教學(xué)問題》1959.3)指出.在唐前期138興修的163項水利建設(shè)中,北方五道有101項,占全數(shù)三分之二.唐后期101項工程中,南方五道就有76項,以江南道為最多,竟占49項.因此安史亂后,是我國古代經(jīng)濟(jì)重心南移局面的初步形成期,至于其鞏固與發(fā)展.則在10世紀(jì)以后的宋代。闡明同一主旨的成果極多.其中頗具代表性的有:李燦文《唐代水利事業(yè)與南北經(jīng)濟(jì)重心的轉(zhuǎn)移》(《新亞書院歷史系系刊》4.1978).黃耀能《隋唐時代農(nóng)業(yè)水利事業(yè)經(jīng)營的歷史意義》(《中山學(xué)術(shù)文化集刊》30.1983).周魁一《中國古代的農(nóng)田水利(續(xù))》(《農(nóng)業(yè)考古》1986.2),楊蔭樓《秦漢隋唐間我國水利事業(yè)的發(fā)展趨勢與經(jīng)濟(jì)區(qū)域重心的轉(zhuǎn)移》(《中國農(nóng)史》1989.2),鈕海燕《唐代水利發(fā)展的因素及其影響》(《歷史地理》第10輯.1992),屈弓《關(guān)于唐代水利工程的統(tǒng)計》(《西南師大學(xué)報》1994.1)等.
紡織業(yè)方面,孫運(yùn)郅從絲織業(yè)角度考察,認(rèn)為絲織業(yè)中心的南移完成于唐宋之交(《絲綢之路和我國絲織業(yè)中心的遷移》。《華東師大學(xué)報》1981.1).黃世瑞《我國歷史上蠶業(yè)中心南移問題的探討》(《農(nóng)業(yè)考古》]985.2;1986.1)認(rèn)為我國蠶業(yè)中心的南移開始于唐末五代.完成于南宋.陶緒《論宋代私營絲織業(yè)的生產(chǎn)形態(tài)及地理分布》(《中國經(jīng)擠史研究》1990.2)認(rèn)為宋代南方私營絲織業(yè)的發(fā)展速度高于北方.邢鐵《我國古代絲織業(yè)重心南移的原因分析》(《中國經(jīng)濟(jì)史研究》1991.2)認(rèn)為,在兩宋三百年間絲織業(yè)的生產(chǎn)重心尚未轉(zhuǎn)移.鄒逸麟亦指出,唐宋以后我國絲織業(yè)南盛北衰的局面逐漸形成(《有關(guān)我國歷史上蠶桑業(yè)的幾個歷史地理問題》,《選堂文史論苑》,上海古籍.1994).
董咸明從自然生產(chǎn)力角度探討,認(rèn)為唐代北方自然災(zāi)害遠(yuǎn)較南方頻繁.對經(jīng)濟(jì)的破壞程度遠(yuǎn)遠(yuǎn)大于南方(《唐代自然生產(chǎn)力與經(jīng)濟(jì)重心南移》,《云南社會科學(xué)》1985.6)。鄭學(xué)檬、陳衍德《略論唐宋時期自然環(huán)境的變化對經(jīng)濟(jì)重心南移的影響》(《廈門大學(xué)學(xué)報》1991.4)認(rèn)為南方經(jīng)濟(jì)超過北方是自然環(huán)境的優(yōu)劣互為逆轉(zhuǎn)的結(jié)果。
林立平從城市分布角度加以闡述.認(rèn)為唐宋之際的中國都城已由長安而洛陽而開封地向東遷徙,中國城市分布重心也從黃河流域移到了長江下游的江淮及太湖區(qū)域,也表明全國的經(jīng)濟(jì)重心已移到長江下游地區(qū)(《試論唐宋之際城市分布重心的南移》,《暨南學(xué)報》1989.2).近有鄭學(xué)檬(前揭)將經(jīng)濟(jì)重心完成南移的判斷標(biāo)準(zhǔn)歸納為三個方面:第一,經(jīng)濟(jì)重心所在地區(qū)生產(chǎn)發(fā)展的廣度和深度超過其它地區(qū).表現(xiàn)為人口眾多.勞力充足;主要生產(chǎn)部門的產(chǎn)量與質(zhì)量名列前茅;商品經(jīng)濟(jì)發(fā)達(dá)。第二,經(jīng)濟(jì)重心所在地區(qū)生產(chǎn)發(fā)展具有持久性和穩(wěn)定性.不只是在一個較短的時期居優(yōu)勢地位.而是有持續(xù)占優(yōu)勢的趨勢.就是其優(yōu)勢為后世所繼承。第三,新的經(jīng)濟(jì)中心取代了舊的經(jīng)濟(jì)中心后.封建政府在經(jīng)濟(jì)上倚重新的經(jīng)濟(jì)中心,并在政治上有所反映。
四,交通網(wǎng)絡(luò)變遷研究
唐宋交通網(wǎng)絡(luò)由國內(nèi)陸路、水路和通向域外路線三方面組成.目前最具代表性的著述.仍是嚴(yán)耕望《唐代的交通與都市》(《大陸雜志》8:4,1954)、《隋唐五代人文地理(上、下)》(中華文化出版事業(yè)委員會.1954)、《唐代交通圖考》(《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83,1985.1986),和青山定雄《唐宋朝代的交通和地志圖研究》(吉川弘文館,1963),兩人對復(fù)原唐代、宋代的交通路線貢獻(xiàn)尤巨.日野開三郎對《五代時期南北中國的陸上交通道路》(《日野開三郎東洋史學(xué)論集》12.三一書房.1989)作過研究.王文楚《古代交通地理叢考》(中華,1997)中也有六篇關(guān)于唐宋交通道路的考證文章.
先看陸路。白壽彝《中國交通史》(商務(wù),1937)列舉出唐代以長安為中心向四周展開的六條陸路交通干線.在所開鑿的新道中.又以大庾嶺山路為最重要。宋代陸路干線改以開封為中心。陳偉明《唐五代嶺南道交通路線述略》、《宋代嶺南交通路線變化考略》(分見《學(xué)術(shù)研究》1987.1;1989.3)認(rèn)為,唐代以廣州為中心向四方延伸的各條交通路線中.北路較南路發(fā)達(dá),西路較東路發(fā)達(dá)。宋代嶺南交通基本格局除沿襲唐代,但其功能開始由唐代的政治型、軍事型向經(jīng)濟(jì)型轉(zhuǎn)變,嶺南道成為真正意義上的經(jīng)濟(jì)動脈.李孝聰《公元十一十二世紀(jì)華北平原北部亞區(qū)交通與城市地理的研究》(《歷史地理》第9輯,1990)認(rèn)為.宋遼驛道的開辟,使得大名府、澄州、澶州為代表的一批地方中心城市地位的上升.宋遼邊界形成了一條新的城市帶。蔡良軍《唐宋嶺南聯(lián)系內(nèi)地交通線路的變遷與該地區(qū)經(jīng)濟(jì)重心的轉(zhuǎn)移》(《中國社會經(jīng)濟(jì)史研究》1992.3)敘述了唐宋時期嶺南以廣州為中心聯(lián)系內(nèi)地的三條道路,即桂州路、郴州路和大庾嶺路,認(rèn)為自唐代完成對大庾新路的開鑿后,該路成為人嶺南的最佳線路,嶺南交通重心亦因此東移至郴州路和大庾嶺路.韓茂莉《宋代嶺南地區(qū)農(nóng)業(yè)地理初探》(《歷史地理》第l1輯,1993)指出,宋代由內(nèi)地進(jìn)入兩廣的道路自西向東主要有三條.湘桂道(水路)、騎田道、大庾道,而以后者路途較為通暢。張澤咸《唐代工商業(yè)》(中國社科,1995)指出,安史亂后西線中的荊襄段因汴水通航受阻而變得格外重要。曹家齊《唐宋時期南方地區(qū)交通研究》(《宋史研究通訊》2002.2)指出,唐代南北交通干線主要有兩條.一為長安東南行至嶺南道;一為洛陽東南行至汴州.經(jīng)運(yùn)河至福建、嶺南道.宋代人閩路進(jìn)一步開辟,幾條南北干線之間聯(lián)系進(jìn)一步加強(qiáng),杭州與淮西地區(qū)聯(lián)系進(jìn)一步密切。
再看水路。白壽彝(前揭)指出唐代的運(yùn)河較江河等水道所居地位要高,唐代中葉后大運(yùn)河南段地位更見重要.北宋汴河(通濟(jì)渠)在交通上居于睥睨一切的地位。而在唐宋之際,所開浚的河渠中作用較大的還有嘉陵江、新源水、蔡河、廣濟(jì)河、金水河、荊南漕河、深州新河等.但地位均無法與運(yùn)河相比。全漢升《唐宋帝國與運(yùn)河》(前揭)認(rèn)為.運(yùn)河聯(lián)結(jié)著北方的軍事政治重心和南方的經(jīng)濟(jì)重心。導(dǎo)致唐宋帝國的經(jīng)濟(jì)地理發(fā)生劇烈變動.李劍農(nóng)指出,安史亂后.除江淮汴道地位見重外.由湘、贛二水人江,溝通江以南與嶺表,又顧流人揚(yáng)州.經(jīng)汴淮以達(dá)于河,由湘出者至鄂州人漢、漢沔經(jīng)陸路至長安。此亦有唐一代內(nèi)河南北交通之要道.就沿海航線而言,唐代海舶,由交廣北航經(jīng)泉州.北以江都為終點(diǎn);揚(yáng)子江口以北至白河口之線.幾無定泊之港。然在宋時,已由交廣閩浙江淮擴(kuò)至密州(《魏晉南北朝隋唐經(jīng)濟(jì)史稿》,《宋元明經(jīng)濟(jì)史稿》,前揭)。《長江水利史略》(長江流域規(guī)劃辦公室《長江水利史略》編寫組,水利電力,1979)指出.北宋時期,與長江干流密切相關(guān)的運(yùn)河有三個系統(tǒng):其一為江北運(yùn)河,聯(lián)系黃河、長江的汴運(yùn)潁運(yùn)等;其二為江南運(yùn)河,聯(lián)系江浙;其三為荊襄運(yùn)河,聯(lián)系長江、漢水。馮漢鏞《宋代國內(nèi)海道考》(《文史》26.1986),對宋代沿海各地,包括長江口外、錢塘江口外、閩江口、珠江口外、黃淮以北的海道,進(jìn)行了詳細(xì)考察.王興淮《我國歷史上的江漢運(yùn)河》(《中國水運(yùn)史研究》專刊一,1987)指出,北宋是江漢運(yùn)河曾經(jīng)發(fā)揮過積極作用的歷史時期之一.王力平《唐肅、代、德時期的南路運(yùn)輸》(見《古代長江中游的經(jīng)濟(jì)開發(fā)》,武漢,1988)認(rèn)為,中晚唐水陸交通中。穿過秦嶺.經(jīng)漢、沔水系,溝通關(guān)中地區(qū)與江漢流域以及整個東南地區(qū)水陸聯(lián)系的南路,肅、代、德時期運(yùn)輸非常活躍.承平之際即告蕭條.王力平《唐后期淮潁(蔡)水運(yùn)的利用與影響》(《河北學(xué)刊》1991.2)說,“北宋的惠民河與唐時的淮穎(蔡)水運(yùn)相比,已不再是臨時性、替代性的運(yùn)道,而成為了固定運(yùn)輸線.”張澤咸(前揭)認(rèn)為,有唐一代,珠江、長江、淮河、黃河等都有商船通行,沿海自南海至渤海的海上交通亦有發(fā)展.
域外交通又分陸、海兩路。白壽彝(前揭)較早據(jù)《新唐書·地理志》列舉唐代通四夷的七條重要道路,除登州海行人高麗渤道、廣州通海夷道外,其余五條為陸路,自唐天寶亂后,西域交通漸形衰落,雖北宋盛時也不能完全恢復(fù)。烏廷玉《隋唐時期的國際貿(mào)易》(《歷史教學(xué)》1957.2)、陳守忠《北宋通西域四條道路的探索》(《西北師院學(xué)報》1988.1)分別考察了隋唐和北宋的通西域道路。藍(lán)勇《唐宋南方陸上“絲綢之路.的轉(zhuǎn)輸貿(mào)易》(《中國社會經(jīng)濟(jì)史研究》1990.4)認(rèn)為,南方陸路主要有川滇道、邕州道、滇緬印道.
港口與海上交通.開創(chuàng)者當(dāng)屬桑原騭藏《蒲壽庚考》(陳裕青譯.中華.1929)和《唐宋貿(mào)易港研究》(楊煉譯,商務(wù).1935).兩書據(jù)伊本.胡爾達(dá)茲比《道程及郡國志》記載,指出交州、廣州、泉州、揚(yáng)州為唐宋四大貿(mào)易港.此外潮州、福州、溫州、明州、松江亦為沿海貿(mào)易港。白壽彝(前揭)指出,隋唐宋時代的域外交通,較前為特別進(jìn)展并歷時最久的,是南海上的交通。烏廷玉(前揭文)認(rèn)為.唐代從廣州出發(fā)可至大食波斯及南洋諸國;對日本的商路則有兩條,一為北路,即由登州出海;一為南路.從明州出發(fā).兩宋海外貿(mào)易路線經(jīng)馮承鈞(《諸蕃志校注》,中華.1956)、蘇繼頃(《島夷志略校釋》.中華,1981)和章巽(《我國古代的海上交通》.商務(wù).1986)等諸多先生的持續(xù)努力,現(xiàn)已清楚有四條航線。東海起航線是從明、杭等州出發(fā)東渡高麗、日本;南海起航線是從廣、泉等州出發(fā).有三條.一是經(jīng)三佛齊(今蘇門答臘)轉(zhuǎn)航閹婆(今爪哇)、渤泥(今加里曼丹)、麻逸(今菲律賓群島)等地.二是經(jīng)蘭無里(今印尼亞齊)再橫渡印度洋去阿拉伯半島上的大食諸國.三是從蘭無里出發(fā)橫渡細(xì)蘭海到故臨(今印度奎隆).在此換乘小船,沿近海西北向駛?cè)氩ㄋ垢邸喍场Ec此同時,也有更多的沿海港口被發(fā)掘出來。陳高華、吳泰《宋元時期的海外貿(mào)易》(天津人民.1981)指出,宋代東海航路中有登州、密州、明州、杭州、華亭、溫州等港;南海航路中的廣州、雷州、徐聞、瓊州等港;介于東海和南海航路間的有泉州、福州、漳州等港。章巽(前揭)指出,北宋時期,長江口以北的通、楚、海諸州.以及長江口以南的越、臺、福、漳、潮、雷、瓊諸州,也都是通航的海港。沿渤海灣的登州、萊州、滄州、平州、都里鎮(zhèn)諸地,亦有海舶往來.關(guān)履權(quán)《宋代廣州的海外貿(mào)易》(廣東人民.1987)認(rèn)為,廣州是唐代最為繁榮的貿(mào)易港,宋代與之通商的海外國家較唐代為多.海外貿(mào)易也超過了唐代.蔣致潔《唐宋之際絲路貿(mào)易與海路貿(mào)易的消長變化》(《社會科學(xué)戰(zhàn)線》1993.5)認(rèn)為,自唐宋以降,在中國古代對外貿(mào)易中.陸路(絲路貿(mào)易)地位日趨下降。海路貿(mào)易逐漸占據(jù)優(yōu)勢.基本上處于主導(dǎo)、支配地位。陸韌《宋代廣西海外貿(mào)易興起初探》(《海交史研究》1997.1)認(rèn)為,宋代廣西海港得到了極好的發(fā)展機(jī)遇。一躍成為西南地區(qū)貿(mào)易重地和出海門戶。黃純艷《宋代海外貿(mào)易》(社會科學(xué)文獻(xiàn),2003)認(rèn)為,宋代貿(mào)易港較唐代有明顯增長,北自京東路.南至海南島.港口以十?dāng)?shù).形成多層次結(jié)構(gòu),大致可分為廣南、福建、兩浙三個相對而言自成體系的區(qū)域.
五、區(qū)域經(jīng)濟(jì)研究
此項研究源起于20世紀(jì)30年代的《食貨》雜志.進(jìn)入80年代后,關(guān)注者益多。漆俠對兩宋區(qū)域經(jīng)濟(jì)的研究堪稱詳盡具體.他認(rèn)為從整體看是“北不如南.西不如東”(《宋代經(jīng)濟(jì)史(下)》.上海人民。1988)。葛金芳在《中國經(jīng)濟(jì)通史(第五卷)》(前揭)中.從動態(tài)角度將其發(fā)展趨勢概括為“東強(qiáng)西弱.南升北降”,并將各區(qū)域經(jīng)濟(jì)的特色歸納為:中原經(jīng)濟(jì)頑強(qiáng)發(fā)展、一波三折,東南經(jīng)濟(jì)蓬勃興起、后來居上.西川經(jīng)濟(jì)不平衡發(fā)展,中南經(jīng)濟(jì)困頓停滯,廣南經(jīng)濟(jì)地曠人稀、起點(diǎn)過低。
中原經(jīng)濟(jì)區(qū)。該區(qū)位于黃河中下游地區(qū),唐代大體包括關(guān)內(nèi)、河?xùn)|、河北、河南四道,以及山南道北部地區(qū).宋代則為京畿、河北、京東、河?xùn)|、陜西、京西北路六路.學(xué)界普遍認(rèn)為,關(guān)中地區(qū)自唐中葉后經(jīng)濟(jì)發(fā)展遭受重創(chuàng),人宋以后漸次恢復(fù)。楊德泉《北宋關(guān)中社會經(jīng)濟(jì)試探》(《宋史研究論文集》,浙江人民.1987)指出,從農(nóng)業(yè)和手工業(yè)看,較之唐代.宋代陜西經(jīng)濟(jì)地位明顯低落。韓茂莉《北宋黃河中下游地區(qū)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的地域特征》(《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89.1)認(rèn)為,中原地區(qū)以河南的經(jīng)濟(jì)發(fā)展水平為高;陜西則次之.雖本地農(nóng)業(yè)區(qū)僅限于關(guān)中,但仍能達(dá)到較高水平;河?xùn)|略有余糧;唯河北一路糧食最為短缺。程民生《論宋代河北路經(jīng)濟(jì)》(《河北大學(xué)學(xué)報》]990.3)認(rèn)為.宋代河北路經(jīng)濟(jì)仍然發(fā)達(dá),實(shí)力雄厚.邢鐵《宋代河北的絲織業(yè)》(《河北學(xué)刊》1990.5)認(rèn)為河北的絲織業(yè)仍較發(fā)達(dá),絲織業(yè)的重心似仍在北方.程民生《論宋代陜西路經(jīng)濟(jì)》(《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4.1)認(rèn)為宋代陜西的經(jīng)濟(jì)發(fā)展屈從于國防利益,但手工業(yè)門類齊全.商業(yè)也異常活躍.
東南經(jīng)濟(jì)區(qū)。該區(qū)泛指長江下游地區(qū),尤其以太湖流域為重心.在唐代大致為淮南、江南道東部地區(qū).宋代大致為淮南東西路、江南東西路和福建沿海地區(qū)。該區(qū)在兩宋時期發(fā)展迅速,故成果較多.陶希圣《五代的都市與商業(yè)》(《食貨》1:10,1935)指出,五代時,各地商業(yè)繁榮.都市繁盛。尤以淮河以南最足稱道.楊章宏《歷史時期寧紹地區(qū)的土地開發(fā)及利用》(《歷史地理》第3輯.1983)認(rèn)為,唐后期,該地區(qū)已成為全國最富庶的地區(qū)之一。至宋代,更成為全國的糧食基地之一。方如金分析了《北宋兩浙社會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及其原因》(《漸江師范學(xué)院學(xué)報》1984.1).彭友良《兩宋時代福建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農(nóng)業(yè)考古》1985.1)指出兩宋時代福楚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jì)得到了很大的發(fā)展,表現(xiàn)為土地的墾辟,耕地迅速增加;水利的開發(fā)和興修;各種物產(chǎn)豐富;對外貿(mào)易的崛起。梁加龍《宋代江西蠶業(yè)發(fā)展初探》(《農(nóng)業(yè)考古》1985.2).文士丹、吳旭霞《試論北宋時期江西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jì)發(fā)展》(《農(nóng)業(yè)考古》1988.1)和吳旭霞《宋代江西農(nóng)村商品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江西社會科學(xué)》1990.6)等.分別從不同角度探討了江西的經(jīng)濟(jì)發(fā)展。謝元魯《論“揚(yáng)一益二”》(《唐史論叢》第3輯.陜西人民,1987年)認(rèn)為.揚(yáng)州在唐以后的衰落不過是東南地區(qū)內(nèi)部中心城市轉(zhuǎn)移的一種表現(xiàn).杜瑜《歷史地理變遷與揚(yáng)州城市興盛的關(guān)系》(《平準(zhǔn)學(xué)刊》第4輯上.光明日報.1989)指出.唐代后期江淮地區(qū)經(jīng)濟(jì)的迅速發(fā)展,為揚(yáng)州發(fā)展提供了物質(zhì)基礎(chǔ),揚(yáng)州亦因其優(yōu)越的地理條件很快發(fā)展為全國最大經(jīng)濟(jì)都市。楊希義《唐代絲綢織染業(yè)述論》(《中國社會經(jīng)濟(jì)史研究》l990.3)指出江南地區(qū)的絲織業(yè)到唐代后期已超過北方.林汀水《兩宋期間福建的礦冶業(yè)》(《中國社會經(jīng)濟(jì)史研究》1992.1)認(rèn)為福建的礦冶業(yè)初興于唐代.至宋極盛.成為全國重要的礦區(qū)之一,出產(chǎn)金、銀、鋼、鐵、水銀、錫和礬等礦。方亞光《論唐代江蘇地區(qū)的經(jīng)濟(jì)實(shí)力》(《中國史研究》1993.1)認(rèn)為,唐代中葉以后,從生產(chǎn)工具水平、手工業(yè)技術(shù)、商品經(jīng)濟(jì)發(fā)展程度而盲,該地區(qū)均處于全國領(lǐng)先地位.韓茂莉論述了《宋代東南丘陵地區(qū)的農(nóng)業(yè)開發(fā)》(《農(nóng)業(yè)考古》1993.3)。方健《唐宋茶產(chǎn)地和產(chǎn)量考》(《中國經(jīng)濟(jì)史研究》1993.2)認(rèn)為,若從唐宋茶的產(chǎn)量而言,江南路居首位,次則四川,荊湖第三,兩浙第四,淮南13山場至北宋盛極,福建茶產(chǎn)量雖遜于以上各路.但以品質(zhì)優(yōu)良著稱.兩廣產(chǎn)量甚微.周生春《論宋代太湖地區(qū)農(nóng)業(yè)的發(fā)展》(《中國史研究》1993.3)認(rèn)為北宋崇寧以后太湖地區(qū)農(nóng)業(yè)發(fā)展達(dá)到北宋后期最高水平.龍登高《宋代東南市場研究》(云南大學(xué),1994年)通過分析和比較,認(rèn)為宋代的經(jīng)濟(jì)與市場發(fā)展程度最高的地區(qū)在東南的兩浙、福建、江東、江西四路。鄭學(xué)檬《中國古代經(jīng)濟(jì)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經(jīng)濟(jì)研究》(前揭)指出.太湖地區(qū)自晚唐五代以來,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最為突出;手工業(yè)以制茶、制鹽、紡織、竹編、葦編、瓷器、釀酒、造紙、藥材等為主.水平較高。江西經(jīng)濟(jì)開發(fā)自五代始大大加速,有特色的產(chǎn)品主要是稻米、豬、牛、禽、魚等副食品資源、木材、礦產(chǎn)、蔬果、烏血等經(jīng)濟(jì)林等等;手工業(yè)品則以瓷器最出名。宋代福建農(nóng)業(yè)發(fā)展最快的地區(qū)是沿海平原,在許多方面與兩浙有共同之處,它也代表當(dāng)時中國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jì)的水平。而從總體來看,五代時期南北方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jì)發(fā)展不平衡.長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區(qū)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jì)無論在深度和廣度上,都超過了北方,但本地區(qū)內(nèi)部亦不平衡。方健《兩宋蘇州經(jīng)濟(jì)考略》(《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8.4)一文,認(rèn)為宋代蘇州經(jīng)濟(jì)居當(dāng)時全國的領(lǐng)先地位,與中唐以來經(jīng)濟(jì)重心南移的趨勢相一致.周懷宇《論隋唐五代淮河流域城市的發(fā)展》(《安徽大學(xué)學(xué)報》2001.3)認(rèn)為,隋唐五代是淮河流域城市發(fā)展史上的一個快速成長期,揚(yáng)州、開封為兩大龍頭城市,而沿運(yùn)河相繼涌現(xiàn)出的新城市中較為突出的有宋、楚、泗、壽、潁、濠、宿、廬等州.陳國燦《宋代江南城市研究》(中華,2002)認(rèn)為.北宋時期,兩浙路的城鎮(zhèn)發(fā)展最為顯著,已達(dá)到乃至超過了北方發(fā)達(dá)地區(qū)的水平;江南東路次之.接近北方發(fā)達(dá)地區(qū)的水平;江南西路雖較宋代以前有顯著的發(fā)展,但由于起點(diǎn)較低,直到北宋中后期,仍與兩浙、江東地區(qū)有相當(dāng)大的差距.葛金芳《兩宋東南沿海地區(qū)海洋發(fā)展路向論略》(《湖北大學(xué)學(xué)報》2003.3)認(rèn)為,人宋以后,隨著商品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海外貿(mào)易的興盛,促使東南沿海地區(qū)開放型市場崛起,進(jìn)而在本地區(qū)出現(xiàn)海洋發(fā)展路向,其具體表征有五:其一.東南沿海眾多外貿(mào)港口,從南到北連成一片;其二,海外貿(mào)易范圍大為擴(kuò)展,構(gòu)成當(dāng)日世界性貿(mào)易圈的兩大軸心之一;其三.進(jìn)出口商品中,分別以初級產(chǎn)品和工業(yè)制成品為主;其四,中外商人隊伍壯大,出海經(jīng)商風(fēng)氣盛行;其五,對域外世界的認(rèn)識遠(yuǎn)較漢唐豐寓詳贍。此前,也有專文討論福建地區(qū)的海外貿(mào)易問?,如林汀水《略談泉州港興衰的主要原因》(《廈門大學(xué)學(xué)報》1984.1),韓振華《五代福建對外貿(mào)易》(《中國社會經(jīng)濟(jì)史研究》1986.3).胡滄澤《宋代福建海外貿(mào)易的興起及其對社會生活的影響》(《中國社會經(jīng)濟(jì)史研究》1995.1).廖大珂《唐代福州的對外交通和貿(mào)易》(《海交史研究》1994.2)等.
西川經(jīng)濟(jì)區(qū)。該區(qū)大致指唐代的劍南道,北宋的成都府和梓州、利州、羹州這四路.關(guān)于唐宋時期四川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先后有兩部專著予以討論,賈大泉《宋代四川經(jīng)濟(jì)述論》(四川省社會科學(xué)院.1985)認(rèn)為,自10世紀(jì)后期至北宋中葉,本地經(jīng)濟(jì)發(fā)展迅猛,在全國占有重要地位。李敬洵《唐代四川經(jīng)濟(jì)》(四川省社會科學(xué)院。1988)指出中唐以后四川成為全國經(jīng)濟(jì)最發(fā)達(dá)的兩個地區(qū)之一。賈大泉《宋代四川的紡織業(yè)》、《宋代農(nóng)村商品生產(chǎn)》、《宋代四川城市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分見《宋史研究論文集》1982年年會會刊.河南人民,1984;《西南師范學(xué)院學(xué)報》1985.1;《四川師范大學(xué)學(xué)報》1986.2)認(rèn)為,宋代本地的紡織業(yè)在前代的基礎(chǔ)上又有長足發(fā)展,農(nóng)村地區(qū)的商品化生產(chǎn)的專業(yè)分工現(xiàn)象極為普遍.在蠶桑紡織業(yè)、茶葉種植業(yè)、甘蔗種植業(yè)和制糖業(yè)、藥材種植業(yè)、釀酒業(yè)、井鹽業(yè)、水果生產(chǎn)方面均有體現(xiàn),從而促進(jìn)了本地區(qū)商品經(jīng)濟(jì)的日趨活躍。城市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貌似繁榮。但在封建勢力的干擾和戰(zhàn)爭的沖擊下,很難持續(xù).謝元魯《宋代成都經(jīng)濟(jì)特點(diǎn)試探》(《中國社會經(jīng)濟(jì)史研究》1983.3)、《論“揚(yáng)一益二”》(前揭)認(rèn)為,宋代成都的經(jīng)濟(jì)十分繁榮.在全國占有重要地位.韓茂莉《宋代川峽地區(qū)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述論》(《中國史研究》1992.4)認(rèn)為.川峽四路的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發(fā)展很不平街,川西成都平原是全國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最發(fā)達(dá)的地區(qū)之一,川東地區(qū)卻仍然較為落后.林文勛《宋代四川與中原內(nèi)地的貿(mào)易》(《宋代經(jīng)濟(jì)史研究》,云南大學(xué).1994)認(rèn)為.時至宋代,四川地區(qū)已發(fā)展成為我國西部區(qū)域的經(jīng)濟(jì)中心區(qū).
中南經(jīng)濟(jì)區(qū).該區(qū)大致措庸代山甫道南部和江南道西部一帶,宋代的京西南路和荊湖南北路。鄭學(xué)檬《試論唐五代長江中游經(jīng)濟(jì)發(fā)晨的動向》(見《古代長江中游的經(jīng)濟(jì)開發(fā)》,武漢。1988)指出,唐五代長江中游(今湖北、湖南、江西三省)地區(qū)經(jīng)濟(jì)發(fā)展加速.使地區(qū)聯(lián)系日趨緊密,由此江南經(jīng)濟(jì)正在向超過北方的方向發(fā)展。韓茂莉《宋代荊湖地區(qū)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述論》(《歷史地理》第12輯.1995)認(rèn)為,宋代荊湖南、北路尚未得到全面開發(fā).尚未處于粗放經(jīng)營階段。楊果《宋代兩湖平原地理研究》(湖北人民,2001)認(rèn)為.兩宋時期是兩湖平原市鎮(zhèn)在空間上迅速擴(kuò)展的一個重要時期,其中值得特別注意的又是縣以下鎮(zhèn)、市的擴(kuò)展.
廣南經(jīng)擠區(qū).該區(qū)大致指唐代的嶺南道,北宋的廣南東西二路.徐俊鳴《古代廣州及其附近地區(qū)的手工業(yè)》(《歷史地理》創(chuàng)刊號,1982)認(rèn)為,唐宋時期本地區(qū)手工業(yè)較為發(fā)達(dá).諸如造船、紡織、食品加工、陶瓷、制紙、礦冶等均帶有濃厚的地方特色。陳偉明《宋代嶺南主棱與經(jīng)濟(jì)作物的生產(chǎn)經(jīng)營》(《中國農(nóng)史》1990.1)認(rèn)為宋代嶺南地區(qū)初步形成了獨(dú)立的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區(qū)。關(guān)履權(quán)《宋代廣東歷史發(fā)晨趨向與農(nóng)業(yè)商品化》(《廣東社會科學(xué)》1991.1)認(rèn)為工商業(yè)和海外貿(mào)易對廣東歷史發(fā)展起了催化劑作用.韓茂莉《宋代嶺南地區(qū)農(nóng)業(yè)地理初探》(《歷史地理》第11輯.1993)分析了宋代嶺南地區(qū)的人口構(gòu)成及其分布,認(rèn)為蠻人集中分布的廣西和海南島生產(chǎn)方式還很落后.指出宋代內(nèi)地移民是嶺南地區(qū)重要的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勞動力。內(nèi)地移民集中的南嶺南坡地帶,以及珠江三角洲,是嶺南農(nóng)業(yè)開發(fā)程度較高的地區(qū).也是嶺南最重要的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jì)區(qū).但與內(nèi)地相比.嶺南大多地區(qū)的生產(chǎn)方式仍很落后.
筆者自知,對于學(xué)界在長達(dá)近一個世紀(jì)的時段中所做的有關(guān)唐宋經(jīng)濟(jì)格局研究的成果,是無論如何也不可能在此文中一一盡述的.因取舍眼光和目的所限.即使部分較為重要的成果,間或亦有遺漏.在對經(jīng)濟(jì)格局的研究成果進(jìn)行了上述梳理后.筆者認(rèn)為要使此課題的研究進(jìn)一步走向深入,還須從如下幾方面著手:
第一,確立貫遇研究的思路,打破朝代分野.即以唐宋變革期學(xué)說為指導(dǎo).改變過去以朝代為中心的敘述模式,將晚唐至宋的經(jīng)濟(jì)格局變動視作整體予以考察,關(guān)注趨勢的演變特征,以期反映出其時經(jīng)濟(jì)格局變動的總體面貌。
篇5
1.歷史地理學(xué)的涵義
歷史地理學(xué)是研究歷史時期的地理環(huán)境及其演變規(guī)律的一門學(xué)科,既具有地理學(xué)科的特點(diǎn),又具有歷史學(xué)科的特征,歷史地理學(xué)是地理學(xué)的一門分支學(xué)科。
2.歷史地理學(xué)的重要地位
歷史地理學(xué)和地理學(xué)科一樣,在培養(yǎng)學(xué)生的人文素養(yǎng)和綜合能力方面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歷史地理學(xué)在很多省份的高考中都占有一席之地。在高考文科綜合中,歷史地理知識的份量也較大。文科綜合地理試卷中滲透的歷史地理知識主要有:中國季風(fēng)氣候與歷代水利建設(shè);經(jīng)濟(jì)結(jié)構(gòu)戰(zhàn)略調(diào)整;黃河流域自然資源的開發(fā)利用與經(jīng)濟(jì)發(fā)展;長江流域經(jīng)濟(jì)發(fā)展;我國東部沿海地區(qū)經(jīng)濟(jì)發(fā)展;維護(hù)祖國統(tǒng)一,反對外來勢力侵略等。尤其是氣候與歷史、地理環(huán)境與人類文明等內(nèi)容都是重點(diǎn)考查的歷史地理知識。
例1:當(dāng)時(北宋)經(jīng)汴河運(yùn)往東京的稻米主要產(chǎn)自( )
A.華北平原 B.漢中平原 C、.太湖平原 D.江漢平原
分析:本題的題干是歷史知識而選項是明顯的地理術(shù)語,同時題干又強(qiáng)調(diào)了“水路”運(yùn)輸,所以學(xué)生既要根據(jù)一定的歷史事實(shí)(如京杭運(yùn)河連通淮河與長江、宋代太湖流域的稻米產(chǎn)量最高),又要熟悉地理因素中的河網(wǎng)水系(汴河經(jīng)運(yùn)河與淮河、長江聯(lián)連,又經(jīng)運(yùn)河中的江南河與太湖流域聯(lián)通) ,才能正確得出正確選項為 C。
例2:北宋后,黃河多次泛濫,汴河河道淤淺,漸至涸廢。試分析黃河該河段(黃河中游地區(qū))經(jīng)常泛濫的原因( )。
分析:本題設(shè)問在歷史教材中是沒有絲毫講述的,但如用歷史地理知識或方法進(jìn)行分析,就不難得出正確的結(jié)論:黃河流經(jīng)黃土高原后,挾大量的泥沙,進(jìn)入中游,由于水勢減緩,泥沙淤積,形成“地上河”;且黃河所經(jīng)地區(qū),降水集中,多有暴雨,易成泛濫。古今黃河流經(jīng)地區(qū)的地理環(huán)境的主體沒有什么大的變化,現(xiàn)代的原因也應(yīng)是古代的原因,所以這一原因也正是北宋后黃河該河段經(jīng)常泛濫的原因。
例3:宋代海上(貿(mào)易)往來大多是三、四月從日本駛往中國的江浙沿海,五、六月從江浙沿海駛向日本。這樣選擇航行的時間主要是為了( )
A.避開倭寇的活動 B.遵守朝廷有關(guān)海禁的規(guī)定
C.利用海洋回流 D.利用季風(fēng)
分析:該題題干是典型的歷史情景,而備選項則是以歷史情景與地理情景相混雜或單一的地理情景方式來迷惑考生,是一種較好的史地綜合題。由于時間季節(jié)的變化,區(qū)域地理自然現(xiàn)象的特性也隨之而變,人類的社會活動就是根據(jù)這些特性的變化,或躲避或利用。因此,宋代海上貿(mào)易的往返時間正是利用了區(qū)域地理因素中,處于溫帶和亞熱帶季風(fēng)氣候中的東亞地區(qū),隨季節(jié)變化而風(fēng)向變化的自然規(guī)律,以便于以風(fēng)力作為動力的帆船航行來選擇時間的。故正確答案為D。
分析現(xiàn)有教材,歷史地理知識在中學(xué)地理教材中非常欠缺。所以,文科綜合考試地理科的復(fù)習(xí),不但要引導(dǎo)考生關(guān)注現(xiàn)實(shí)的發(fā)展,也要從歷史地理知識中吸取營養(yǎng),從歷史中吸取經(jīng)驗教訓(xùn),為現(xiàn)實(shí)發(fā)展提供借鑒。不僅在文科綜合中如此,在一些地理單科試題中,也出現(xiàn)了相關(guān)的歷史地理知識。因此,無論從提高學(xué)生的學(xué)習(xí)興趣還是從在高考中取得優(yōu)異的成績來看,在中學(xué)地理教材中增添相關(guān)的歷史地理知識內(nèi)容都是必須的。
二、在中學(xué)地理教學(xué)中滲透歷史地理知識
(一)挖掘地理教材中的歷史知識,建立史理知識的有機(jī)聯(lián)系
1.在學(xué)習(xí)我國六大古都的地理知識中滲入其悠久的歷史
六大古都至少都已有二千年以上的歷史。北京始于西周薊城、春秋時代即成為燕國的國都,以后成為金、元、明、清各朝代的首都。西安始于西周的鎬京,以后成為秦、漢、隋、唐各朝首都。洛陽始建于西周初期,自東周以來,先后有東漢、曹魏 、西晉、北魏、隋(煬帝)、唐(武后)以及五代的后梁、后唐、后周等九個朝代在這里建都。開封在戰(zhàn)國時代是魏國的國都,以后又成為五代的后梁、后晉、后漢、后周、北宋、金等朝代的首都。南京始于戰(zhàn)國金陵邑 ,以后成為六朝(三國吳、東晉、南朝的宋、齊、梁、陳)首都,此外,明朝初年、和中華民國也定都于此。杭州始于秦錢唐縣,到五代成為吳越國的國都,以后又成為南宋的首都。
2.在講解中國地理中滲透歷史地理知識
如講到黃河流域的城市西安時,可介紹西安坐落在號稱“八百里秦川”的關(guān)中平原上,平原周圍群山環(huán)繞,形勢險要;河水(黃河)的支流渭水(渭河)橫貫關(guān)中平原,且流經(jīng)西安城北,為西安提供了灌溉和舟楫之利,并通過河水、渭水向長安城北運(yùn)送漕糧。因此西安成為中國歷史上重要的古都之一,現(xiàn)在又成為西北地區(qū)經(jīng)濟(jì)發(fā)展最快的城市之一。
3.在地理教學(xué)中增加一些與時俱進(jìn)的話題
如環(huán)境與發(fā)展的關(guān)系問題,如何在發(fā)展經(jīng)濟(jì)的同時保護(hù)人類賴以存在的自然和生態(tài)環(huán)境。又如可持續(xù)發(fā)展是我國的一項基本國策,在可持續(xù)發(fā)展教育方面歷史地理學(xué)等人文學(xué)科具有獨(dú)特的優(yōu)勢,諸如歷史上黃河的決溢改道、經(jīng)濟(jì)中心的南移、古都名城的興廢等等案例,均可成為揭示人地關(guān)系的極好例證,都可成為中學(xué)地理教學(xué)中進(jìn)行環(huán)保教育的良好素材。
(二)在地理教學(xué)中注意運(yùn)用歷史地圖
歷史教學(xué)地圖以簡明的、特定的地圖語言再現(xiàn)歷史,其載負(fù)的圖形信息能收到文字表達(dá)難以實(shí)現(xiàn)的直觀效果,與課本緊密結(jié)合,是取得最優(yōu)教學(xué)效果的重要工具之一。歷史地圖的重點(diǎn)不在于表現(xiàn)靜態(tài)的地理學(xué)信息,而在于表現(xiàn)動態(tài)的、發(fā)展的歷史學(xué)信息。在地理地圖教學(xué)中,教師可配合歷史地圖,設(shè)計有情有味的讀圖活動,以激發(fā)學(xué)生的讀圖興趣。如講到我國的行政區(qū)劃時,可結(jié)合地名的由來講授歷史上我國政區(qū)的演變,使學(xué)生能理解政區(qū)演變與自然環(huán)境、政治制度、經(jīng)濟(jì)發(fā)展和文化發(fā)展密切相關(guān)。再如講授鄱陽湖與洞庭湖時,可運(yùn)用它們的變遷圖,通過湖泊面積的對比使學(xué)生了解人類活動對自然環(huán)境的影響,從而更好地理解洪澇災(zāi)害的原因。總之,讓歷史地理地圖走進(jìn)地理課堂,符合時代的要求及考試方式的改革,不僅可活躍課堂氣氛,激發(fā)學(xué)生學(xué)習(xí)興趣,提高課堂教學(xué)效果,而且是歷史地理學(xué)滲透進(jìn)中學(xué)地理課的有效途徑。
三、史地結(jié)合教學(xué)對地理教師提出了更高要求
教師是課堂的設(shè)計者和指揮者,是學(xué)生智慧的啟迪者和挖掘者,更是學(xué)生心靈的塑造者和培養(yǎng)者。在中學(xué)地理教學(xué)中滲透歷史地理知識,對地理教師的自身素質(zh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要提高對跨學(xué)科教學(xué)的認(rèn)識
歷史學(xué)科與地理學(xué)科雖分屬社會學(xué)科、自然學(xué)科,但它們間的聯(lián)系十分廣泛。地理學(xué)科引導(dǎo)學(xué)生認(rèn)識今天的地理現(xiàn)象,著重探索地理現(xiàn)象的現(xiàn)狀和特點(diǎn)。而今天的地理實(shí)際上是過去地理的延續(xù),了解歷史上的地理情況,有助于探究地理現(xiàn)象演變的過程和規(guī)律,有助于人類更好地協(xié)調(diào)與自然的關(guān)系。因此,地理教師要盡可能在教學(xué)中有效利用歷史地理知識。
2.要努力學(xué)習(xí)一些交叉學(xué)科的知識
由于中學(xué)教材中歷史地理學(xué)知識還不成體系,文字與地圖尚沒很好的配合,加上相關(guān)教師中大多數(shù)缺少歷史地理知識的系統(tǒng)學(xué)習(xí),在教學(xué)中很難做到得心應(yīng)手。所以要求教師必須勤奮學(xué)習(xí),廣泛涉獵,善于積累,努力了解一些基本的歷史地理知識。要在教學(xué)實(shí)踐中,掌握一些學(xué)科交叉的知識,了解其發(fā)展趨勢,要從整體上把握地理學(xué)科與相關(guān)學(xué)科間的指示交叉點(diǎn),并且能夠融會貫通。
3.要處理好教學(xué)內(nèi)容的主次關(guān)系
雖然歷史地理知識在地理教學(xué)中有著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教師在補(bǔ)充、充實(shí)教學(xué)內(nèi)容時,必須擺正教學(xué)內(nèi)容的主次關(guān)系。必須從教學(xué)目的出發(fā),緊扣教材,突出重點(diǎn),突破難點(diǎn);必須有科學(xué)依據(jù),史料真實(shí),觀點(diǎn)正確;地理教師要把握好歷史地理知識滲透的合適時機(jī)和恰當(dāng)?shù)臄?shù)量,千萬不要喧賓奪主。
4.要進(jìn)行一些邊緣學(xué)科的教學(xué)法研究
教師不僅要有豐富的學(xué)科知識,具有廣闊的文化視野和深厚的文化底蘊(yùn),更要搞一些學(xué)術(shù)研究和教育科學(xué)研究,撰寫發(fā)表一些教學(xué)法研究論文,為成為學(xué)者型教師打下堅實(shí)的基礎(chǔ)。為此,教師要關(guān)注國際、國內(nèi)的時事動態(tài),了解社會熱點(diǎn)問題,以充實(shí)教材相關(guān)內(nèi)容,豐富教學(xué);要掌握先進(jìn)的教育理論和現(xiàn)代化教學(xué)手段;要研究文科綜合能力培養(yǎng)的方法,尋求教學(xué)的最佳方案,實(shí)現(xiàn)知識和能力、方法和過程、情感態(tài)度價值觀的三維教學(xué)目標(biāo),促進(jìn)全體學(xué)生的全面發(fā)展。
【參考文獻(xiàn)】
篇6
一、中國生態(tài)史學(xué)的本土淵源
從世界范圍來說,生態(tài)環(huán)境史研究大約興起于上個世紀(jì)七十年代;中國學(xué)者開始進(jìn)行這方面的專門研究稍晚一些,80年代初開始出現(xiàn)在題目上標(biāo)注“生態(tài)環(huán)境”一詞的史學(xué)論文,90年代中期以后、特別是最近幾年來逐漸成為熱門課題,一些學(xué)者相繼呼吁建立中國環(huán)境史學(xué),筆者甚為贊同,但更愿意稱之為“中國生態(tài)史學(xué)”。
中國生態(tài)環(huán)境史研究的興起,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國外環(huán)境史學(xué)的影響,這一點(diǎn)毋須諱言。近三十余年來,歐美國家的環(huán)境史研究不斷發(fā)展,新論迭出,漸成熱門之學(xué),并且有的外國學(xué)者還致力于研究中國歷史上的環(huán)境問題[2],令國內(nèi)學(xué)者聞風(fēng)聳動。不過,根據(jù)筆者的觀察,直至今日,除臺灣學(xué)者之外,國內(nèi)對西方環(huán)境史學(xué)的了解仍然很少,有關(guān)方面的理論方法尚處于初步引進(jìn)的階段[3]。也就是說,迄今為止,國內(nèi)的中國生態(tài)環(huán)境史研究,在思想理論和技術(shù)方法上并未受到歐美環(huán)境史學(xué)的顯著影響,而主要是依憑本國的學(xué)術(shù)基礎(chǔ)。換言之,由于“歐風(fēng)美雨”的刺激,中國生態(tài)環(huán)境史研究在較短時間里快速興起,以致最近若干年來標(biāo)榜“環(huán)境史”或“生態(tài)史”的研究課題日益增多,但無論就問題意識還是就理論方法來說,它都具有不可否認(rèn)的“本土性”[4],可從上個世紀(jì)中國史學(xué)自身發(fā)展的脈絡(luò)中找出它的學(xué)術(shù)淵源和軌跡。只不過早先的相關(guān)研究是在不同學(xué)科中分頭進(jìn)行的,顯得非常零散,也沒有明確打出“生態(tài)史”或者“環(huán)境史”的旗號。筆者以為:構(gòu)建中國生態(tài)史學(xué),固須積極引進(jìn)和學(xué)習(xí)國外相關(guān)理論和方法,對國內(nèi)學(xué)者所作的前期努力及其所取得的成績進(jìn)行一番認(rèn)真清理亦是十分必要的。唯有如此,中國生態(tài)史學(xué)方能建立在更加堅實(shí)的學(xué)術(shù)基礎(chǔ)之上,更好地結(jié)合本國實(shí)際開展研究工作,并免受“邯鄲學(xué)步”之譏。為此,筆者先對大陸學(xué)者以往的相關(guān)研究作一個簡要的評述。
1.考古學(xué)和古生物學(xué)者的相關(guān)研究
在中國學(xué)術(shù)界,最早關(guān)注歷史生態(tài)環(huán)境的是考古學(xué)和古生物學(xué)家。考古學(xué)向以歷史早期的物質(zhì)文化遺存為主要研究對象,考古工作者在清理出土文化遺存時,除了關(guān)心人體骨骸、人造事物(如器具、建筑、墓葬、手工業(yè)場所等)之外,也注意動物骨骸、植物籽粒或核殼等。出土動物骨骸、植物籽粒和核殼,指示著遠(yuǎn)古時代各地動植物種類的構(gòu)成乃至整個生態(tài)系統(tǒng)的構(gòu)造。上個世紀(jì)前期,當(dāng)考古學(xué)家在殷墟遺址中清理出大象的遺骨和古文字學(xué)家從甲骨文中發(fā)現(xiàn)“獲象”、“來象”之類的記載時,學(xué)者逐漸認(rèn)識到這種動物曾在華北地區(qū)棲息,也很自然地想象當(dāng)?shù)毓沤裆鷳B(tài)環(huán)境發(fā)生了巨大變化。隨著其它多種喜溫動植物遺存(如犀牛和竹鼠的遺骸、水蕨孢子等)亦在華北各地不斷出土,學(xué)者做出了遠(yuǎn)古中國氣候和動植物構(gòu)成與現(xiàn)代迥然不同的判斷[5]。
上世紀(jì)末期以來,日益嚴(yán)重的生態(tài)環(huán)境危機(jī)受到社會的普遍關(guān)切,考古學(xué)者也深受震撼,在國外考古學(xué)的影響下,大陸和臺灣都有一批學(xué)者積極著手建立中國的環(huán)境(生態(tài))考古學(xué),試圖對遠(yuǎn)古人類聚落的生態(tài)環(huán)境進(jìn)行某種程度的重建,并考察特定區(qū)域的生態(tài)環(huán)境因素對遠(yuǎn)古社會組織、經(jīng)濟(jì)生產(chǎn)和生活方式的影響。與此同時,古生物學(xué)家也不再孤立地認(rèn)識某些野生動植物,而是逐漸采用生態(tài)變遷的大視野,根據(jù)動物和植物考古資料,考察某個區(qū)域動植物區(qū)系和物種構(gòu)成和特定動植物種類分布區(qū)域的歷史變化及其原因。應(yīng)該說,考古學(xué)和古生物學(xué)家所開展的工作是非常有意義的,至少為我們長時段地考察中國生態(tài)環(huán)境變遷提供了豐富的和古今對比強(qiáng)烈的歷史信息。
2.歷史地理學(xué)和氣候史學(xué)者的相關(guān)研究
歷史地理學(xué)以自然和社會現(xiàn)象的歷史空間分布為主要研究內(nèi)容,致力于探討人地關(guān)系演變的過程和規(guī)律,與生態(tài)環(huán)境史研究有著天然的密切聯(lián)系。由于特殊的專業(yè)優(yōu)勢,歷史地理學(xué)者具有令人贊嘆的廣闊思維空間,他們不僅注意到了歷史上的森林破壞、河湖變遷、沙漠?dāng)U張和一些珍稀野生動植物分布區(qū)域的歷史變化,也注意到了歷史上聚落、城市及經(jīng)濟(jì)產(chǎn)業(yè)的分布與生態(tài)環(huán)境的關(guān)系。雖然他們的思想框架和研究方法是歷史地理學(xué)的,但前輩學(xué)者如史念海、譚其驤、侯仁之、文煥然、何業(yè)恒等人的不少論著實(shí)堪稱生態(tài)史研究的經(jīng)典。
氣候史方面,早在民國時期,竺可楨就已注意到中國歷史上氣候的冷暖變遷問題。1972年,他在早年研究的基礎(chǔ)上,發(fā)表了題為《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4]的著名論文,對中國東部氣候的周期性寒暖波動進(jìn)行了系統(tǒng)論述,成為學(xué)者引用頻率最高的史學(xué)論文。繼他之后,有一批學(xué)者先后在這方面開展了系統(tǒng)的研究,出版了數(shù)量可觀的論著[5]。
從最近10多年的成果來看,歷史地理學(xué)者顯然不再滿足于考察和描繪某些自然和社會文化現(xiàn)象的歷史空間分布,而是日益關(guān)注自然現(xiàn)象與社會文化現(xiàn)象之間的彼此聯(lián)系,在人口與環(huán)境、經(jīng)濟(jì)生產(chǎn)和生活方式與環(huán)境、社會變動與氣候變遷、疾疫和災(zāi)害與環(huán)境、民俗與環(huán)境等諸多方面,都進(jìn)行了卓有成績的探討;一些研究其實(shí)已不再是傳統(tǒng)意義上的歷史地理學(xué)課題了[6]。假如它們?nèi)匀槐仨毐环Q為歷史地理學(xué)的話,那么只能說生態(tài)史學(xué)和歷史地理學(xué)的研究對象本來即有很大的重疊,兩者間的界線事實(shí)上非常模糊,幾乎無法斷然劃清。直到目前,我們所進(jìn)行的許多生態(tài)史課題,往往是由歷史地理學(xué)者提出并率先開展研究的。如果說中國生態(tài)環(huán)境史研究主要是從歷史地理學(xué)中生長出來的,也不算言過其實(shí)。我們要想特別標(biāo)立一種與歷史地理學(xué)相區(qū)別的生態(tài)史學(xué),必須從學(xué)理上進(jìn)行認(rèn)真辨別,對兩者的理論方法和學(xué)術(shù)指向做出必要的判分[7]。
3.農(nóng)牧林業(yè)史學(xué)者的研究
農(nóng)業(yè)、牧業(yè)和林業(yè)的本質(zhì),是充分利用各種自然條件如水、土、光、熱和物種資源,干預(yù)動植物的生命過程,促進(jìn)那些經(jīng)濟(jì)動物和經(jīng)濟(jì)植物的再生產(chǎn),獲得以衣食原料為主的各種產(chǎn)品。任何一個類型的農(nóng)牧林業(yè)生產(chǎn)都不可能離開特定的生態(tài)環(huán)境,它們的歷史發(fā)展,與生態(tài)環(huán)境變遷有著不可分割的密切聯(lián)系,因此農(nóng)牧林業(yè)史家比較早地關(guān)注到歷史生態(tài)環(huán)境問題,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
我國農(nóng)牧林業(yè)史家關(guān)注生態(tài)環(huán)境,大約是從上個世紀(jì)80年代初開始的[8]。在此之前,個別學(xué)者已發(fā)表過若干相關(guān)論文,如雷海宗先生在1950年代曾發(fā)表《古今華北的氣候與農(nóng)事》[9],根據(jù)古書記載概述華北氣候的變遷及其對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的影響。但并未形成一種群體性的學(xué)術(shù)傾向。20世紀(jì)80年代前后,東西方農(nóng)業(yè)科學(xué)界都在反思“石油農(nóng)業(yè)”和過量使用化肥、農(nóng)藥對農(nóng)業(yè)生態(tài)系統(tǒng)的危害,提倡所謂“有機(jī)農(nóng)業(yè)”(后來又提出“生態(tài)農(nóng)業(yè)”,再往后則是“可持續(xù)農(nóng)業(yè)”;日本則有人基于道家思想提倡所謂“自然農(nóng)法”),不少中外農(nóng)學(xué)家稱贊中國傳統(tǒng)農(nóng)業(yè)技術(shù)方法的合理性和優(yōu)越性,使中國農(nóng)史學(xué)家受到了鼓舞,于是有人開始論說傳統(tǒng)農(nóng)作方式對維持生態(tài)平衡的積極作用,比如重視水土保持和積肥施肥、實(shí)行作物輪作間作套種、種植與飼養(yǎng)相結(jié)合、采用生物防治等等,對促進(jìn)有機(jī)物質(zhì)循環(huán)和保持農(nóng)業(yè)生態(tài)平衡的作用和意義,試圖闡發(fā)傳統(tǒng)農(nóng)學(xué)的現(xiàn)代價值,其中江南和珠江三角洲地區(qū)的“桑基魚塘”、“蔗基魚塘”生態(tài)農(nóng)業(yè)模式被賦予了典范意義。農(nóng)田水利作為農(nóng)史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面,向來受到重視,有大量的論著發(fā)表,學(xué)者很早就關(guān)注農(nóng)田水利建設(shè)對水資源調(diào)配的重要作用,及其對農(nóng)業(yè)生態(tài)環(huán)境正反兩方面的影響。與考古學(xué)家和歷史地理學(xué)家相比,農(nóng)牧林業(yè)史家對歷史生態(tài)問題的論說顯得更加專業(yè),這一方面由于他們具備良好的自然科學(xué)特別是生物學(xué)基礎(chǔ),另一方面則由于他們一開始就注重對生態(tài)學(xué)(特別是農(nóng)業(yè)生態(tài)學(xué))理論方法的運(yùn)用。
90年代以后,農(nóng)牧林業(yè)史家的研究思路漸趨開闊,對于中國歷史上農(nóng)牧林業(yè)與生態(tài)環(huán)境的關(guān)系,漸漸不再只是強(qiáng)調(diào)好的一面,而是開始反思傳統(tǒng)的農(nóng)業(yè)資源開發(fā)利用方式的弊病及其所造成的生態(tài)惡果,例如關(guān)于黃土高原過度開墾所造成的嚴(yán)重后果、宋代以后長江中下游的圍湖造田和明清以來山區(qū)墾殖對生態(tài)環(huán)境的破壞等問題,均取得了不少有深度的研究成果;一批學(xué)者從農(nóng)業(yè)史和經(jīng)濟(jì)史入手探討中國歷史上的“天人關(guān)系”,也取得了相當(dāng)可喜的成績[10]。盡管農(nóng)林牧業(yè)史學(xué)者的研究范圍大抵局限于對產(chǎn)業(yè)內(nèi)部歷史問題的探討,但由于中國是一個典型的農(nóng)業(yè)大國,直到上個世紀(jì)才開始走上工業(yè)化道路,此前人類活動對生態(tài)環(huán)境的影響,其實(shí)也主要表現(xiàn)在農(nóng)牧林業(yè)生產(chǎn)方面,離開了這些方面的基礎(chǔ)研究,想要真正認(rèn)清中國生態(tài)環(huán)境變遷的歷史,殆無可能。事實(shí)上,自譚其驤、史念海以來,歷史地理學(xué)家探討中國古代生態(tài)環(huán)境問題,亦主要從農(nóng)、林、牧業(yè)入手。
由上所述,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在中國,與生態(tài)環(huán)境史有關(guān)的學(xué)術(shù)研究可以追溯到上個世紀(jì)前期,并且已經(jīng)取得了不少成績,為進(jìn)一步考察中國生態(tài)環(huán)境變遷史打下了良好的基礎(chǔ),也為我們著手建立中國生態(tài)史學(xué)積累了較為豐富的學(xué)術(shù)資源。
然而,已有的研究尚不足以構(gòu)成中國生態(tài)史學(xué)。首先,以往相關(guān)探討大抵只是考古學(xué)、古生物學(xué)、歷史地理學(xué)和農(nóng)牧林業(yè)史等學(xué)科研究的外向拓展和延伸,而非以系統(tǒng)繪制中國歷史生態(tài)環(huán)境圖像為學(xué)術(shù)指歸。研究者對生態(tài)歷史問題的考察仍是立足于各自不同的專業(yè),并沒有凸現(xiàn)出全面認(rèn)識中國歷史生態(tài)環(huán)境、最終對之進(jìn)行某種程度的系統(tǒng)重建的意向,更沒有從開始生態(tài)環(huán)境出發(fā)對社會歷史運(yùn)動進(jìn)行系統(tǒng)解釋的努力,這就造成相關(guān)研究與主流史學(xué)之間存在相當(dāng)大的隔膜,其成果也未能很好地被一般史學(xué)著述所吸收;其次,盡管以往已經(jīng)探討了許多重要論題,在研究思路和技術(shù)方法上也作了諸多有益的探索,為中國生態(tài)史學(xué)的建立準(zhǔn)備了一些重要的構(gòu)件。但是,這些論題、思路和技術(shù)方法顯得相當(dāng)零碎和分散,彼此之間互不關(guān)聯(lián),尚不足以構(gòu)成學(xué)術(shù)界域分明、結(jié)構(gòu)層次清晰并具有內(nèi)在整體性和統(tǒng)一性的生態(tài)史學(xué)框架;其三,由于“自然”與“社會”二元分立的思想觀念根深蒂固,以往對生態(tài)環(huán)境史研究的理解和定位存在著不容回避的嚴(yán)重偏差:人們普遍將它視為社會歷史之外的另一學(xué)術(shù)領(lǐng)域。傳統(tǒng)史學(xué)一向重人事、輕自然,對自然的歷史用力甚少,對許多問題的認(rèn)識幾乎是一片空白,生態(tài)環(huán)境史研究者立志加以填補(bǔ),這是可以理解的。但矯枉未免過正,早先的生態(tài)環(huán)境史研究明顯偏重對自然層面的考察,社會層面的問題則被嚴(yán)重忽視了,從而造成了新的偏頗,以致許多人以為生態(tài)環(huán)境史的研究目標(biāo)只是考察古今自然環(huán)境之變;其四、與以上幾個方面相聯(lián)系,盡管越來越多的學(xué)者逐漸認(rèn)識到了開展環(huán)境史研究的必要性,實(shí)際介入這一領(lǐng)域者亦已不可謂少,但極少有人對這一新研究進(jìn)行學(xué)理上的論說。迄今為止,國內(nèi)的生態(tài)環(huán)境史研究仍局限于具體問題的探研,附屬在不同的相關(guān)學(xué)科之下,如果上升到“專門之學(xué)”這個層次加以考量,則仍存在著嚴(yán)重的學(xué)科理論缺失。正因為如此,在一些人的眼里,生態(tài)環(huán)境史研究只不過是探討一些邊邊角角的歷史問題,算不上什么專門的學(xué)問,至多只能充當(dāng)歷史著述的“緣飾”和“花邊”,難登史學(xué)的大雅之堂。這種狀況必須改變。
[1] “生態(tài)史”又稱“環(huán)境史”,中外學(xué)者都往往混用,但“環(huán)境史”的叫法更加流行。個人認(rèn)為:這一研究的基本理論框架應(yīng)是生態(tài)學(xué),因此更愿采用“生態(tài)史”一詞。另外,“環(huán)境史”仍有將社會文化與生態(tài)環(huán)境人為分割的嫌疑,而在我所主張的生態(tài)史學(xué)中,兩者是一個彼此影響、相互作用、協(xié)同演變的整體,人類(社會、文化)系統(tǒng)應(yīng)被視為地球生態(tài)大系統(tǒng)的一部分。
[2]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澳大利亞著名中國經(jīng)濟(jì)史和環(huán)境史家Mark Elvin (伊懋可),他在多年前即開始了系統(tǒng)的中國生態(tài)環(huán)境史研究,其中包括對洱海、巢湖、杭州灣、近代結(jié)核病與環(huán)境等問題的專門研究。伊氏曾與臺灣學(xué)者劉翠溶合作主編會議論文集——《積漸所止:中國環(huán)境史論文集》(上、下冊),由臺灣中央研究院經(jīng)濟(jì)研究所2000年出版中文版,劍橋大學(xué)出版社出版英文版(Sediments of Time: Environment and Society in Chinese History,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與中文版所收論文略有不同),在中西方學(xué)術(shù)界產(chǎn)生了廣泛的影響。最近,伊懋可又以《大象的退卻:中國環(huán)境史》(The Retreat of the Elephants: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China,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4.)為題,對中國環(huán)境史的一系列問題進(jìn)行了系統(tǒng)論述。
[3] 近年來,一些研究外國史的學(xué)者如侯文蕙、、包茂宏、梅雪芹、高國榮等做了不少這方面的譯介工作,提供了相當(dāng)豐富的學(xué)術(shù)信息,令人欽佩。
[4] 筆者這里使用“本土性”一詞意在說明:中國生態(tài)環(huán)境史研究的問題意識和研究方法,主要并非導(dǎo)源于近30年來在國外興起的環(huán)境史學(xué),而是基于本國學(xué)者在相關(guān)領(lǐng)域的前期研究。請切勿作過分寬泛的理解。
[5] 例如關(guān)于遠(yuǎn)古動物,徐中舒早在1930年就發(fā)表了題為《殷人服象及象之南遷》的長文[1](pp.51~71),根據(jù)殷墟出土甲骨卜辭中“獲象”、“來象”之文,參以其它文獻(xiàn)記載和出土實(shí)物,對商代河南產(chǎn)象及象之南遷事實(shí)進(jìn)行了論述。其后,德日進(jìn)、楊鐘健、劉東生等人又先后,對殷墟出土哺乳動物群進(jìn)行了系統(tǒng)研究[2][3]。這些均可視為中國生態(tài)環(huán)境史研究的先聲。
[6] 例如青年歷史地理學(xué)者王建革關(guān)于華北平原和內(nèi)蒙古草原生態(tài)、經(jīng)濟(jì)與社會史研究的系列論文,其實(shí)更多地采用了生態(tài)學(xué)而非歷史地理學(xué)的理論方法,與傳統(tǒng)的歷史地理學(xué)研究大異其趣,可為顯著的例證。
[7] 關(guān)于環(huán)境史學(xué)與歷史地理學(xué)的關(guān)系,同行學(xué)者時有議論,但對兩者究竟如何判分,并未形成成熟的意見。個人認(rèn)為:環(huán)境史(生態(tài)史)的理論基礎(chǔ)是生態(tài)學(xué),它的主要著眼點(diǎn)是“生命系統(tǒng)”,重在考察生物(特別是人類)與環(huán)境、生物與生物之間的歷史關(guān)系;歷史地理學(xué)雖然一向強(qiáng)調(diào)人地關(guān)系,但其理論基礎(chǔ)是地理學(xué),主要著眼點(diǎn)是“空間構(gòu)造”和“空間運(yùn)動”。因此,歷史地理學(xué)并不能包辦環(huán)境史學(xué)的研究工作。
[8] 從上個世紀(jì)80年代初開始,《中國農(nóng)史》、《農(nóng)史研究》和《農(nóng)業(yè)考古》等幾家農(nóng)業(yè)史刊物,均陸續(xù)刊載有題目上出現(xiàn)“生態(tài)”一詞的論文。在同一時期的農(nóng)業(yè)史著作中,更時常見有“生態(tài)農(nóng)業(yè)”、“生態(tài)平衡”、“生態(tài)破壞”等詞句,有關(guān)論述也不斷增多。
[9] 該文收入氏著《中國文化與中國的兵》,商務(wù)印書館2001年版。
[10] 上世紀(jì)80年代以來,在中國農(nóng)業(yè)史研究中,“風(fēng)土”和天、地、人“三才”觀一直是學(xué)者關(guān)注的重要課題,先后有不少論著發(fā)表。1999年12月,中國農(nóng)業(yè)歷史學(xué)會、中國經(jīng)濟(jì)史學(xué)會古代史分會和《中國經(jīng)濟(jì)史研究》編輯部聯(lián)合召開了“中國經(jīng)濟(jì)史上的天人關(guān)系” 學(xué)術(shù)討論會,分別從天人哲學(xué)、農(nóng)林牧業(yè)生產(chǎn)實(shí)踐、資源保護(hù)等多方面探討人類經(jīng)濟(jì)活動與生態(tài)環(huán)境之間的關(guān)系。會議論文由李根蟠、原宗子和曹幸穗等結(jié)集為《中國經(jīng)濟(jì)史上的天人關(guān)系》,由中國農(nóng)業(yè)出版社于2002年出版。 二、作為一個獨(dú)立學(xué)科的中國生態(tài)史學(xué)
誠然,從不同學(xué)科出發(fā)考察歷史生態(tài)環(huán)境的具體問題,是非常有意義、也是十分必要的,但相關(guān)研究必須加以有機(jī)整合。若欲改變目前的“零打碎敲”局面,開展全面系統(tǒng)的中國生態(tài)環(huán)境史研究,以獲得對環(huán)境歷史變遷的貫通認(rèn)識,并由此取得對社會歷史的更加透徹的理解,就必須建立一種專門之學(xué)——生態(tài)史學(xué),使之成為中國史學(xué)中的一個獨(dú)立分支學(xué)科。
毫無疑問,生態(tài)環(huán)境史研究要想提升為一個專門獨(dú)立的史學(xué)分支,必須具備獨(dú)特的思想框架和理論方法。然而,完成生態(tài)史學(xué)框架體系的構(gòu)建工作,恐怕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西方學(xué)者已就“什么是環(huán)境史”、“環(huán)境史主要研究什么”這些基本問題討論了數(shù)十年,并提出了多種定義和構(gòu)想,但各家的意見并不是很一致的;國內(nèi)雖也有個別學(xué)者提出了一些設(shè)想[1],但事實(shí)上還沒有人真正著手進(jìn)行這方面的努力。在此,筆者也只能提出自己的一點(diǎn)粗淺見解。
我們認(rèn)為:生態(tài)史學(xué)作為一個新的史學(xué)分支,其新穎和獨(dú)特之處,不僅僅在于它的研究對象,更重要的是它的思想理論和方法,首先(應(yīng)當(dāng))體現(xiàn)在它將現(xiàn)代生態(tài)學(xué)理論方法應(yīng)用于歷史研究,以生態(tài)學(xué)以及它的分支學(xué)科——人類生態(tài)學(xué)(生態(tài)人類學(xué))、人口生態(tài)學(xué)、社會生態(tài)學(xué)和文化生態(tài)學(xué)等,作為觀察和解釋歷史的思想導(dǎo)引和分析工具。簡要地說,生態(tài)史學(xué)是運(yùn)用生態(tài)學(xué)理論方法來處理史料、解釋歷史現(xiàn)象和歷史運(yùn)動(既包括自然現(xiàn)象和自然運(yùn)動,也包括社會現(xiàn)象和社會運(yùn)動)的一種新史學(xué)。它的基本學(xué)術(shù)指向是采用廣泛聯(lián)系、彼此作用、互相反饋和協(xié)同演化的生態(tài)系統(tǒng)思想,陳述和剖析人類社會與生態(tài)環(huán)境互動變遷的歷史經(jīng)驗事實(shí),并就如何協(xié)調(diào)人類與環(huán)境之間的關(guān)系發(fā)表自己的觀點(diǎn)和看法。
與一般的歷史研究不同,生態(tài)史學(xué)的觀察視野不局限于社會和人事,而是將目光較多地投向人類的生物屬性和與人類社會活動發(fā)生過種種聯(lián)系的那些自然事物和現(xiàn)象;但生態(tài)史學(xué)又非寬泛意義上的自然史研究,它事實(shí)上只著眼于自然界(特別是地球生物圈)中與人類活動發(fā)生過關(guān)聯(lián)的那些方面。也就是說,生態(tài)史學(xué)的學(xué)科特點(diǎn)表現(xiàn)在研究對象上,是它立足于自然生態(tài)與社會文化的中間界面開展學(xué)術(shù)探討,對于這個中間界面,我們或許可以借用“天人之際”一詞加以概括。[2]在生態(tài)史學(xué)者看來,社會文化與生態(tài)環(huán)境乃是一個彼此影響、互動作用、協(xié)同演變的統(tǒng)一整體,自然環(huán)境和人類活動彼此施加于對方的歷史作用,人們對這種彼此作用的認(rèn)識和反應(yīng),以及這些認(rèn)識和反應(yīng)的道德、價值、符號、組織、制度和各種行為體現(xiàn),都是生態(tài)史研究者理應(yīng)探討的內(nèi)容。了解生態(tài)環(huán)境的歷史面貌和變遷過程,固然是生態(tài)史學(xué)的一個重要目標(biāo),但考察生態(tài)環(huán)境及其變遷作用下的社會文化運(yùn)動亦應(yīng)作為它的基本任務(wù)之一,而正確認(rèn)識兩者之間的歷史互動關(guān)系和過程,則是這一新興學(xué)科的最高追求[3]。
很顯然,生態(tài)史學(xué)雖然看起來應(yīng)當(dāng)集中考察歷史“自然”問題(這既是先前的研究所造成的錯覺,也是一種矯枉過正的結(jié)果),事實(shí)上卻堅決反對將社會和文化排除在觀察視野之外。不過,生態(tài)史學(xué)者之關(guān)注社會和文化,與一般歷史學(xué)者關(guān)注社會和文化相比,在視角上有較大區(qū)別——生態(tài)史學(xué)強(qiáng)調(diào)人類的生物屬性,以及社會現(xiàn)象與環(huán)境因素的歷史關(guān)聯(lián),文化則被視為人類這種特殊生物同周遭環(huán)境(在這里,“環(huán)境”既包括自然環(huán)境,也包括社會環(huán)境)打交道的方式和方法體系。也許可以不甚恰當(dāng)?shù)卣f,生態(tài)史學(xué)在一定程度上有意將人類還原為一種動物——同其它動物一樣需要空氣、食物、水和各種其它資源,人類的繁衍方式、人口密度、生命維持體系和社會組織形式等等,同樣深受特定生態(tài)條件的影響和制約。所不同的是,人類具有創(chuàng)造、學(xué)習(xí)和傳承文化的能力,在應(yīng)對環(huán)境的過程中,構(gòu)建了復(fù)雜的工具、技術(shù)、組織、規(guī)范、價值觀念和意義象征體系,而一般動物只是渾渾噩噩的寄居者;人類依靠其所創(chuàng)造的文化而生存,一般動物只是憑著本能而已。
在生態(tài)史學(xué)看來:人類的任何一種社會歷史活動,都是在一定的空間中進(jìn)行的,離不開特定的環(huán)境條件,都直接或間接地受到種種生態(tài)因素的影響,如將生態(tài)環(huán)境排除在觀察視野之外,就難以全面揭示人類社會發(fā)展的真正秘密。因此,具體(而非抽象)、實(shí)證(而非玄學(xué)化)地考察生態(tài)環(huán)境因素對人類社會發(fā)展的歷史影響,理應(yīng)成為歷史學(xué)的一項重要任務(wù)。
與一般歷史學(xué)相比,生態(tài)史學(xué)不但有其特定的觀察視野和理論方法,而且具有獨(dú)特的社會歷史觀。它特別強(qiáng)調(diào):無論文明怎樣發(fā)達(dá)、社會如何進(jìn)步,人類始終都是動物界中的一員,人類的歷史始終都是地球生物圈中生命系統(tǒng)流轉(zhuǎn)的一部分。正如其它物種因生態(tài)環(huán)境的區(qū)域差異和時代變遷不斷發(fā)生變化一樣,人類社會和文化亦因所處環(huán)境的地域和時代不同而千差萬別。因此,社會和文化的許多歷史變異和差別,不但需從其自身的發(fā)生、演化過程中尋找答案,而且應(yīng)從其所處的生態(tài)環(huán)境中求索根源。生態(tài)史學(xué)將告訴我們:在不同的時代和區(qū)域,社會文化如何受到各種生態(tài)環(huán)境因素的影響,并且在這些影響之下不斷發(fā)展演變?
另一方面,與自然史研究不同,生態(tài)史學(xué)雖然重視考察各種歷史自然現(xiàn)象,但時空界域圈定在人類誕生以來、與人類活動發(fā)生了關(guān)聯(lián)的那些部分。而在這一時空界域內(nèi)的生態(tài)環(huán)境變遷,并不是一個純粹的自然過程,人類的各種活動及其方式和結(jié)果,都是生態(tài)環(huán)境變遷的重要影響因子和表現(xiàn)。隨著人類實(shí)踐能力的不斷增強(qiáng),人類活動在生態(tài)變遷中所發(fā)揮的作用也越來越大。生態(tài)史研究的另一重要目標(biāo),就是要弄清生態(tài)環(huán)境在歷史上究竟發(fā)生了哪些變化,人類在其中發(fā)揮了什么樣的作用?從一定的意義上說,它事實(shí)上想要搞清楚:由人類活動所造成的“第二自然”是如何逐步形成、并且不斷發(fā)生改變的?這些改變又如何對社會產(chǎn)生反饋?zhàn)饔茫绊懭祟惖睦^續(xù)生存和發(fā)展?
要之,在生態(tài)史學(xué)的思想框架中,環(huán)境是有人類的環(huán)境,人類活動是生態(tài)環(huán)境變遷的重要促發(fā)和推動因素;社會是一定生態(tài)條件下的社會,許多生態(tài)因素都是社會歷史運(yùn)動的重要參與要素——從總體上說,人類社會文化系統(tǒng)是地球生態(tài)大系統(tǒng)中的一個組成部分。雖然在具體研究實(shí)踐中,我們既可側(cè)重探討人類活動影響下的環(huán)境變遷,亦可側(cè)重考察環(huán)境影響下的社會文化發(fā)展——這兩個側(cè)重構(gòu)成生態(tài)史學(xué)研究的兩種學(xué)術(shù)指向,但兩者事實(shí)上是不可分割的整體。如果割裂了兩者之間的聯(lián)系,就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生態(tài)史學(xué)。
根據(jù)以上想法,我們對自己所設(shè)想的中國生態(tài)史學(xué)的基本框架作如下幾點(diǎn)歸納:
一、生態(tài)史學(xué)作為一種新史學(xué),并非刻意拋棄傳統(tǒng)的史學(xué)理論、方法和命題,而是要在歷史觀察中引入生態(tài)學(xué)的理論方法,強(qiáng)化對生態(tài)環(huán)境與人類活動相互關(guān)系的歷史探討;
二、生態(tài)史學(xué)擯棄“人類中心主義”,人類及其社會和文化的歷史被視為地球大生態(tài)系統(tǒng)演變歷史的一個組成部分;但也不是簡單地主張“生態(tài)中心主義”,雖然生態(tài)史學(xué)的一個重要目標(biāo)是對生態(tài)環(huán)境的歷史進(jìn)行系統(tǒng)描述和某種程度的“重建”,但人類活動及其方式和成果仍然被放置在關(guān)鍵的位置。因此,生態(tài)史學(xué)的歷史觀既非“文化決定論”,亦非“環(huán)境決定論”,而是“人類——環(huán)境互動論”;
三、生態(tài)史學(xué)從社會文化和生態(tài)環(huán)境的中間界面尋找和選擇論題,它的基本內(nèi)容(根據(jù)側(cè)重點(diǎn)不同)包括兩大方面:一是歷史時期的生態(tài)環(huán)境面貌及其在人為作用下所發(fā)生的種種變遷;二是在人類(社會文化)的歷史發(fā)展進(jìn)程中,生態(tài)環(huán)境及其諸要素所發(fā)揮的重要影響和作用[4];
四、生態(tài)史學(xué)研究的最終目標(biāo),是探索人類與其所處環(huán)境之間的歷史互動關(guān)系與過程,系統(tǒng)地描繪社會文化與生態(tài)環(huán)境彼此影響、相互作用和協(xié)同變遷的歷史圖式。
顯而易見,生態(tài)史學(xué)是一種真正意義上的跨學(xué)科研究,它所要考察的,不僅僅是社會現(xiàn)象和文化現(xiàn)象,也不僅僅是自然現(xiàn)象和環(huán)境因素,并且也不是兩者的簡單堆砌和相加,而是自然和社會兩大領(lǐng)域眾多現(xiàn)象和因素之間的有機(jī)、互動的歷史關(guān)系與過程。
毫無疑問,開展生態(tài)史學(xué)研究是一項極為艱巨的工作,研究者需要具備復(fù)雜、綜合和廣泛聯(lián)系的思想方法,需要具備廣博的知識——最好兼受過自然科學(xué)和社會科學(xué)兩個方面的訓(xùn)練,并且需要具備超越于兩個學(xué)科領(lǐng)域之上的進(jìn)行綜合、整體思辨的能力。由于以往學(xué)科劃分和教學(xué)方式的局限,一般中國學(xué)者在知識結(jié)構(gòu)和思維訓(xùn)練上都存在不可忽視的缺陷和不足。正因為如此,盡管目前生態(tài)環(huán)境史研究越來越熱門,已經(jīng)觸及了非常廣泛的問題,但就所見的成果來看,多數(shù)論著的學(xué)術(shù)水平并不很高,總體上說,研究深度仍未超出1993年香港“中國生態(tài)環(huán)境歷史學(xué)術(shù)討論會”的會議論文[5]。我們注意到:一般歷史學(xué)者的相關(guān)論著中時或出現(xiàn)一些常識性的錯誤,而由具備不同自然科學(xué)背景的學(xué)者所進(jìn)行的研究,又往往局限于各自的專業(yè)領(lǐng)域,彼此之間缺少必要的聯(lián)結(jié)和貫通,未能有機(jī)地整合起來形成系統(tǒng)的歷史認(rèn)識。要想很好地開展這一研究,不僅需要有豐富的知識貯備、系統(tǒng)的理論方法訓(xùn)練,而且要求不同專業(yè)領(lǐng)域的學(xué)者密切交流、通力協(xié)作。
[1] 例如,包茂宏在《環(huán)境史:歷史、理論和方法》一文(載《史學(xué)理論研究》2000年第4期)曾就此提出了若干值得重視的設(shè)想。
[2] 之所以特別指出“借用”,是因為筆者并不認(rèn)為“天人之際”的歷史含義并非今天所說的“人類與自然之間”。一些學(xué)者將“天”理解為“自然”,將“天人之際”、“天人合一”解釋為“人類與自然的關(guān)系”、“人類與自然環(huán)境的統(tǒng)一”是很不恰當(dāng)?shù)摹5珡臍v史文獻(xiàn)中,我們一時還找不到一個更簡約的詞匯來表達(dá)這種關(guān)系,只好暫且借用。
[3]景愛《環(huán)境史:定義、內(nèi)容與方法》[6]一文認(rèn)為:環(huán)境史是研究人類與自然的關(guān)系史,研究人類社會與自然環(huán)境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的歷史過程。顯然,在景先生看來,環(huán)境史所關(guān)注的“環(huán)境”并非寬泛意義上的“自然”,而是與人類發(fā)生了關(guān)系的自然環(huán)境。在這一點(diǎn)上,我們的觀點(diǎn)是一致的。不過,雖然他所主張的環(huán)境史研究強(qiáng)調(diào)人類與自然的“關(guān)系”,但觀察的重點(diǎn)仍在于“環(huán)境”,而筆者所主張的生態(tài)史學(xué)是從生態(tài)學(xué)立場出發(fā)的,更強(qiáng)調(diào)人類與環(huán)境的整體性和統(tǒng)一性,不僅為了理解環(huán)境的歷史,同時更是為了理解人類和社會的歷史。
[4]景愛認(rèn)為環(huán)境史研究應(yīng)主要圍繞三個方面進(jìn)行:第一,要研究自然環(huán)境的初始狀態(tài);第二要研究人類對自然環(huán)境的影響;第三,要研究探索人類開發(fā)利用自然的新途徑[6]。梅雪芹在吸收西方學(xué)者觀點(diǎn)的基礎(chǔ)上,將環(huán)境史研究分為四個層次:一是探討自然生態(tài)系統(tǒng)的歷史,二是探討社會經(jīng)濟(jì)領(lǐng)域和環(huán)境之間的相互作用,三是研究一個社會和國家的環(huán)境政治和政策,四是研究關(guān)于人類的環(huán)境意識,即人類概述周圍的世界及其自然資源的思想史[7](pp.10~11)。盡管他們都強(qiáng)調(diào)人類與環(huán)境的相互影響,但基本學(xué)術(shù)指向仍是理解“環(huán)境”,仍不能包容我們所設(shè)想的生態(tài)史學(xué)。
[5] 這次會議的絕大多數(shù)論文均收入前揭伊懋可、劉翠溶主編論文集。其中中文版除《序》和《導(dǎo)論》之外,設(shè)立了《比較的觀點(diǎn)》、《對自然環(huán)境的詮解》、《人類的聚落》、《邊疆地區(qū)》、《水文與水利》、《氣候》、《疾病》、《環(huán)境的形象-官方的心態(tài)》、《環(huán)境的形象-文學(xué)的和通俗的感受》和《環(huán)境與近代經(jīng)濟(jì)發(fā)展-臺灣和日本》等欄目,一些論文視角之新穎、論說之深入十分值得贊嘆。 三、中國生態(tài)史學(xué)研究的兩種理路
如上所言,我們所主張的生態(tài)史學(xué),將社會文化與生態(tài)環(huán)境視為統(tǒng)一的整體,致力于探索兩者之間的歷史互動關(guān)系與過程,它所研究的是“天人之際”的歷史問題。這就決定了它既不能像傳統(tǒng)史學(xué)那樣只重視歷史上的社會和人事,曾被嚴(yán)重忽視的自然歷史變動將被當(dāng)作重點(diǎn)突破的對象;亦不能像先前的相關(guān)研究那樣只對自然層面的問題情有獨(dú)鐘,眾多的社會歷史問題同樣需要認(rèn)真加以考察,傳統(tǒng)史學(xué)所探討的諸多重要問題,仍將成為生態(tài)史學(xué)的重要論題,只是采用了新的思想方法,變換了論說的角度。換句話說,生態(tài)史學(xué)研究的對象,既包括自然歷史現(xiàn)象和問題,也包括社會現(xiàn)象和問題,橫跨自然科學(xué)和社會科學(xué)兩大領(lǐng)域,是一種典型的交叉學(xué)科。
與多數(shù)成熟的史學(xué)分支相比,生態(tài)史學(xué)具有顯著的“邊緣學(xué)科”性質(zhì)。然而,在這里,“邊緣”意指它的思想空間是在多個多科領(lǐng)域的聯(lián)結(jié)和交匯部分,而不是說它應(yīng)該被定位在歷史學(xué)科的邊緣位置——盡管它目前仍然多少有些尷尬地被視為一種邊角的學(xué)問。事實(shí)上,只要稍微回顧一下學(xué)術(shù)史,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一種學(xué)術(shù)究竟屬于“主流”還是“邊緣”,未必就是命定的,而是既取決于相關(guān)成果的積累,更取決于不同時期的學(xué)術(shù)興奮點(diǎn)——而學(xué)術(shù)的興奮點(diǎn)總是與人類社會的現(xiàn)實(shí)問題密切關(guān)聯(lián)。隨著歷史條件和社會情境的改變,曾經(jīng)的主流學(xué)術(shù)可能被邊緣化,邊緣學(xué)術(shù)亦可能向中心位移而成為顯學(xué)。筆者大膽預(yù)測:生態(tài)環(huán)境史研究將逐漸登上中國史學(xué)的大堂正殿[1]。
當(dāng)然,這仍需生態(tài)環(huán)境史學(xué)者做出持續(xù)不斷的努力,開展更扎實(shí)系統(tǒng)的研究并取得更多、更好的成果。為了達(dá)到這個目標(biāo),還必須努力改變研究理路,具體來說,需要更多地關(guān)注人與社會的歷史,從生態(tài)史學(xué)的立場出發(fā)切入主流史學(xué)所長期關(guān)注的那些相關(guān)歷史命題,即在一定程度上向主流史學(xué)、特別是目前居于顯學(xué)地位的社會史研究靠攏。這不僅僅是一種爭取學(xué)術(shù)地位的“技巧”,同時也是推進(jìn)社會歷史認(rèn)識的需要——觀察社會歷史運(yùn)動和解釋社會歷史現(xiàn)象,原本即是生態(tài)史學(xué)的“應(yīng)有之義”,只是路徑和方法有所不同而已。
回顧過去一個時期生態(tài)史和社會史研究的發(fā)展,我們不難注意到:不論從學(xué)術(shù)動機(jī)還是從實(shí)際研究情況來看,兩者之間都似乎少有瓜葛。直到最近10余年來,情況才發(fā)生了可喜的變化:這兩種分途發(fā)展的學(xué)術(shù)研究逐漸出現(xiàn)了互相交融、彼此會通的趨勢。這是一個非常值得重視和努力推進(jìn)的學(xué)術(shù)走向,向來重人事、輕自然和將自然與社會相分離的史學(xué)傳統(tǒng),將可能因此發(fā)生根本性的變化。應(yīng)該說,互相溝通和彼此聯(lián)結(jié)乃是生態(tài)史和社會史研究不斷深入而產(chǎn)生的共同學(xué)術(shù)訴求。
試細(xì)言之。
按照先前的觀念,生態(tài)環(huán)境史研究的目標(biāo)是認(rèn)識自然環(huán)境、而非社會文化的歷史。如前所述,中國學(xué)者早先的相關(guān)研究,正集中于歷史上的氣候、森林、野生動物、沙漠化和水土流失、河流湖泊、海岸變遷和農(nóng)業(yè)生態(tài)平衡等方面,研究者大多具有一定自然科學(xué)背景,如氣象學(xué)、地理學(xué)、農(nóng)(牧、林)學(xué)、文水(水利)學(xué)等等[2]。歐美早期的生態(tài)史研究大抵也是如此,美國的生態(tài)環(huán)境史研究,雖然早期的研究已多與環(huán)保、邊疆和拓殖的歷史相聯(lián)系,但重點(diǎn)仍在于自然方面[3],目前這一領(lǐng)域的權(quán)威雜志——《環(huán)境史》是由美國環(huán)境史學(xué)會與森林史學(xué)會合辦的。但是,隨著相關(guān)研究不斷深入,學(xué)者日益意識到:生態(tài)變遷并不是一個純粹的自然過程,至少自農(nóng)業(yè)時代以來,生態(tài)環(huán)境的諸多變遷與種種人為因素有著密不可分的聯(lián)系,無視人類活動的影響,就無法理解生態(tài)環(huán)境的歷史變化。正因為如此,最近一個時期以來,關(guān)于生態(tài)環(huán)境的歷史著述愈來愈重視社會性因素的影響和作用。美國“進(jìn)入90年代以后,環(huán)境史與社會史合流成為一種趨勢,性別、種族都被納入環(huán)境史的研究內(nèi)容。”[4]歐洲的環(huán)境史研究視野也在不斷擴(kuò)展,從歐洲環(huán)境史學(xué)會網(wǎng)所刊1976-2004年間的相關(guān)論著目錄看,雖然近年的論著從數(shù)量上說仍以討論氣候、水源、森林、景觀、污染、災(zāi)害疾病等問題者居多,但經(jīng)濟(jì)、社會和文化與環(huán)境的歷史關(guān)系愈來愈受到重視[5]。在我國,關(guān)于近一萬年來(農(nóng)業(yè)起源以來)生態(tài)環(huán)境變遷是否主要由于人類活動所致,學(xué)者尚有不同的看法,但生態(tài)破壞的社會原因日益受到重點(diǎn)關(guān)注卻是無可爭議的事實(shí),譚其驤、史念海等著名歷史地理學(xué)家其實(shí)已經(jīng)率先做了若干十分精湛的開創(chuàng)性研究[6]。
社會史研究致力于考察人類群體(即社會)發(fā)展的既往經(jīng)歷,理所當(dāng)然應(yīng)以解釋社會歷史現(xiàn)象為鵠的。然而,單純從社會來解釋社會、或者僅將生態(tài)環(huán)境視為社會發(fā)展的“背景”,顯然無法對眾多社會歷史現(xiàn)象做出圓融的解釋[7]。從年鑒學(xué)派開始,法國的社會史家逐漸不再只是在理論上承認(rèn)環(huán)境對社會的影響,而是將生態(tài)環(huán)境視為影響社會歷史進(jìn)程的結(jié)構(gòu)性要素,通過實(shí)證研究探索其影響的具體機(jī)制,成為社會歷史觀察的一個新視角,并對歐美社會史、文化史和經(jīng)濟(jì)史研究的發(fā)展發(fā)揮了重要引導(dǎo)作用。最近若干年來,中國社會史研究者特別是地域社會史、災(zāi)害疾病社會史和社會生活史研究者,也開始將生態(tài)環(huán)境作為能動因素納入各自研究思考的范圍[8];在經(jīng)濟(jì)史和文化史研究中,也出現(xiàn)了同樣的學(xué)術(shù)趨向。
雖然國內(nèi)迄今仍無人對生態(tài)史和社會史研究相互結(jié)合的可能性與必要性作專門系統(tǒng)的探討,但在我們看來,這兩個看似互不相干的研究領(lǐng)域發(fā)生關(guān)聯(lián),互相對話、借取和觀照,走向匯流融通,卻是一種必然的學(xué)術(shù)發(fā)展走向和趨勢。這既是兩者均取得重大突破的可能途徑,更是生態(tài)史學(xué)研究應(yīng)取的理路。
站在目前主流史學(xué)的立場,人們也許會提出這樣的問題:生態(tài)史研究對于認(rèn)識中國歷史究竟有何意義?最容易得到認(rèn)同的回答是:有助于認(rèn)識社會發(fā)展演變的自然背景。這樣的回答自然并沒有錯,但從生態(tài)史學(xué)的立場來看,則仍然是不全面的,甚至是很偏頗的。這是因為,在生態(tài)史學(xué)觀念中,生態(tài)環(huán)境不僅是社會發(fā)展演變的自然背景,而且是非常重要的能動參與因素。對生態(tài)史研究進(jìn)行合理的學(xué)術(shù)定位并與社會史研究真正有機(jī)地結(jié)合起來,完全可能為深化中國社會歷史認(rèn)識做出更多貢獻(xiàn),而不僅僅是為演繹社會歷史戲劇鋪設(shè)一個“自然的布景”。
筆者曾經(jīng)指出:生態(tài)史與社會史研究互相滲透和結(jié)合,可能導(dǎo)致新的學(xué)科交叉,根據(jù)側(cè)重點(diǎn)不同,形成兩個學(xué)術(shù)分支:一是生態(tài)社會史,二是社會生態(tài)史[8]。前者的目標(biāo)主要是了解自然生態(tài)環(huán)境的歷史變遷,但與某些生態(tài)史研究相比,它特別強(qiáng)調(diào)并具體論證生態(tài)變遷過程中人類活動和社會(及其文化)因素的影響;后者則試圖采用生態(tài)學(xué)理論來研究歷史上的社會,強(qiáng)調(diào)自然環(huán)境因素的能動作用和影響,以期更好地認(rèn)識人類社會及其發(fā)展演變,目的在于理解社會的歷史運(yùn)動。簡而言之,前者是研究人類活動作用下的生態(tài)環(huán)境的歷史,后者則是研究生態(tài)環(huán)境參與下的人類社會的歷史。
為了進(jìn)一步闡明我們的想法,且將自人類誕生以來的歷史不恰當(dāng)?shù)貪饪s為一個童話式的簡短故事:“很久、很久以前,有一片茂密的叢林,林中有一個小村,村里居住著幾戶人家。村民們世世代代在這里勞作和生息……。”生態(tài)社會史家主要講述這片叢林的故事,談?wù)撨@片叢林曾經(jīng)有多大,生長過哪些樹木,棲息過哪些動物?進(jìn)一步,會談?wù)撨@片叢林逐步縮小、或至消失的歷史過程及其社會原因,如由于村莊的人口不斷增長,需要開墾更多土地、搭建更多房屋、樵采更多燃料等等,樹木因此不斷遭到砍伐,叢林面積逐漸縮小,原先棲息在這片叢林中的許多動物,也因無處藏匿和覓食逐漸逃逸、終至絕跡……等等;社會生態(tài)史家則主要講述這個村莊中的人的故事,亦即描述由這幾戶人家所組成的社會的歷史,談?wù)撝T如村落社會結(jié)構(gòu)、經(jīng)濟(jì)狀況、生活習(xí)慣、婚姻風(fēng)俗、文化娛樂、生老病死……等等問題。如果想把故事說得更加清晰和完整,就要進(jìn)一步談?wù)搮擦趾蛥擦种衅渌锓N的變化,以及這些變化對村民的謀生方式、利益分配、權(quán)力結(jié)構(gòu)、生育死亡、安全保障、娛樂活動,乃至信息交流、觀念情感等各個方面曾經(jīng)發(fā)揮過的作用和影響。很顯然,由于歷史關(guān)注的側(cè)重點(diǎn)不同,可能分別做出不同的歷史敘述。而歷史的真實(shí)情況是,叢林與村莊乃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彼此互為變化的因果,任一方面的變化都是促使另一方面發(fā)生改變的能動因素。
側(cè)重“自然”一面的生態(tài)社會史研究,基于這樣一個預(yù)設(shè):人類活動、特別是經(jīng)濟(jì)活動,至少從農(nóng)業(yè)時代以來就是生態(tài)變遷的主因之一。因此,有關(guān)研究雖然著眼于生態(tài)環(huán)境變遷,但強(qiáng)調(diào)人類活動的影響,對生態(tài)變遷的討論不是從生態(tài)環(huán)境到生態(tài)環(huán)境,而是將人口、技術(shù)、生產(chǎn)與生活方式、風(fēng)俗習(xí)慣乃至意識形態(tài)等等社會性因素,與水、土、光、熱、生物、礦物等自然因素,一同視為參與物質(zhì)循環(huán)、能量流動、信息傳遞乃至整個生態(tài)系統(tǒng)演變的重要因子,在特定情況下,甚至視為比自然因素更加重要的歷史變量。沿著這種思路所展開的生態(tài)史研究,實(shí)際上差不多是考察人類改變生態(tài)環(huán)境的歷史。
社會生態(tài)史研究,則將人類社會視為地球生物圈內(nèi)的一個特殊生命系統(tǒng),它一方面承認(rèn)人類與其它動物相比具有極為特殊的智能,即創(chuàng)造、傳播、積累和更新文化的能力,承認(rèn)由于這種能力,人類社會具有高度的復(fù)雜性;另一方面,它同時認(rèn)為:人類必須服從生態(tài)規(guī)律的最終支配,社會發(fā)展變遷的歷史過程,從根本上說,乃是人類不斷調(diào)整與生態(tài)環(huán)境關(guān)系(包括經(jīng)過自己改造的生態(tài)環(huán)境)的過程——技術(shù)體系的進(jìn)步、生業(yè)方式的改變、社會組織的變遷,乃至風(fēng)俗習(xí)慣和思想觀念的嬗變,都在很大程度上歸因于社會對生態(tài)變遷的適應(yīng)性調(diào)整,或者間接地跟從于這些調(diào)整;經(jīng)濟(jì)類型、社會結(jié)構(gòu)、生活方式乃至精神風(fēng)貌等等許多方面的地域差異,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生態(tài)環(huán)境差異所造成的;生態(tài)環(huán)境的歷史變遷,同樣導(dǎo)致上述方面發(fā)生種種改變。正由于人類社會在地球生態(tài)大系統(tǒng)中與周圍環(huán)境存在著廣泛的物質(zhì)、能量和信息交流,是其中的一個特殊生命系統(tǒng),因此人類社會的歷史,也就存在著采用生態(tài)學(xué)理論方法加以認(rèn)識的可能性。
社會生態(tài)史的主要研究對象,仍然是歷史上形形的社會現(xiàn)象、錯綜復(fù)雜的人際關(guān)系和流轉(zhuǎn)不息的生命運(yùn)動。但與一般的社會史研究相比,它更側(cè)重探討社會現(xiàn)象的生物性質(zhì)和自然基礎(chǔ),致力于尋找社會系統(tǒng)與生態(tài)系統(tǒng)、社會現(xiàn)象與自然現(xiàn)象、社會因子與生態(tài)因子之間的歷史聯(lián)系。在這里,紛繁復(fù)雜的社會歷史現(xiàn)象,諸如衣、食、住、行、生產(chǎn)、消費(fèi)、婚姻、生育、疾病、死亡、遷徙、社交、娛樂、戰(zhàn)爭等等,以及因之所產(chǎn)生的技術(shù)、組織、結(jié)構(gòu)、制度、規(guī)范、習(xí)俗、思想意識,就不單純地被理解為“社會的”或者“文化的”,同時還被理解為“生物的”,是在特定“自然”和“生態(tài)”影響下產(chǎn)生、并反映特定自然生態(tài)環(huán)境的;家庭、宗族、村落、城邑等等,也就不應(yīng)只是被理解為社會的單元或聚落,同時還是大小不同的生態(tài)單位或系統(tǒng),可以采用生態(tài)學(xué)方法加以考察。要之,社會生態(tài)史學(xué)者承認(rèn)文化因素的生衍變異和社會系統(tǒng)的發(fā)展演化具有自己的內(nèi)在邏輯,但卻不認(rèn)為它們是(至少不完全是)封閉、自限和自我決定的過程,而是與生態(tài)環(huán)境及其眾多因素彼此影響、協(xié)同演進(jìn)的過程。
這樣一來,生態(tài)史學(xué)研究就有了兩個側(cè)重點(diǎn)不同的可取理路:即生態(tài)社會史和社會生態(tài)史研究。如果選取前者,即使在具體實(shí)踐中十分強(qiáng)調(diào)人類社會活動的影響作用,也仍然屬于社會史之外的另一學(xué)術(shù)領(lǐng)域,它的學(xué)術(shù)目標(biāo)是系統(tǒng)地描繪生態(tài)環(huán)境及其變遷的歷史圖像,當(dāng)然客觀上也可為講述人類社會的歷史故事增添一個“布景”和“底圖”;如果選取后一種理路,則不僅是生態(tài)史學(xué)研究的一部分,而且可以視為社會歷史觀察的一個新的思想框架。這種新的思想框架,將社會及其所處的環(huán)境視作一個有機(jī)、統(tǒng)一和整體的生命系統(tǒng)納入考察范圍,不僅考慮各種社會因素的相互作用,而且將各種生態(tài)因素視為重要的參與變量,從而呈顯出一種新的社會歷史觀,我們姑且稱之為“社會(文化)——生態(tài)史觀”。一旦采用了這種新的框架,史家對“叢林中的村落社會”的觀察,既可能提出許多新的問題,對一些老問題的認(rèn)識也可能會發(fā)生根本性的改變,而不僅僅是在敘述故事時簡單地添加一些在過去看來無關(guān)緊要的內(nèi)容。生態(tài)史家有信心為社會歷史觀察提供新的視角、問題意識、解釋途徑乃至新的歷史觀念,并對推進(jìn)中國社會歷史認(rèn)識做出獨(dú)特的貢獻(xiàn)。
從生態(tài)史學(xué)的視角來觀察社會歷史可能會提出哪些新的論題,現(xiàn)在還難以預(yù)料。但可以肯定的是,它必定會提出并討論許多從前不曾思考的歷史問題;以往曾經(jīng)探討的不少論題,包括一些長期爭辯的重大問題,亦完全可以、而且應(yīng)當(dāng)重新研究,并可望做出新的解釋。事實(shí)上,已經(jīng)有些學(xué)者開始了這方面的嘗試。比如關(guān)于歷史上中國南北文明進(jìn)程的差異、胡漢民族的沖突與融合、周期性的社會動蕩、經(jīng)濟(jì)重心的轉(zhuǎn)移、水利與專制政體的關(guān)系[9]等等,已陸續(xù)出現(xiàn)了一些結(jié)合生態(tài)環(huán)境而重作思考的新論。還有不少重大問題,例如中國“封建社會”何以長期延續(xù)、何以歷史上漢文化不斷成功地向南擴(kuò)張卻難以向長城以北推進(jìn)?……等等,亦都可從人類——環(huán)境的互動關(guān)系和過程中重新求索。微觀層面上的許多歷史問題,同樣可以采用這一思想框架加以考察。當(dāng)我們?nèi)婵疾炷硞€地域社會的歷史時,決不能置當(dāng)?shù)氐纳酱ㄐ蝿荨夂颉⑺摹⑼寥馈⑸铮ㄌ貏e是經(jīng)濟(jì)動、植物)構(gòu)成乃至礦產(chǎn)資源于不顧,因為當(dāng)?shù)厣鐣谏a(chǎn)模式、飲食結(jié)構(gòu)、服飾式樣、居處方式、交通設(shè)施、疾病、災(zāi)害以及娛樂、信仰、知識等眾多方面所呈現(xiàn)出來的地方特色,都毫無疑問是根植于其獨(dú)特的生態(tài)環(huán)境和自然資源。舉例來說,一個地方的水資源環(huán)境,必然要影響當(dāng)?shù)氐纳a(chǎn)結(jié)構(gòu)和生活習(xí)慣,迫使人們圍繞水源控制管理和水旱災(zāi)害防治形成某些特殊的組織、制度和秩序,甚至進(jìn)一步影響到當(dāng)?shù)孛癖姷男膽B(tài),形成某些特殊巫術(shù)、禁忌和神靈信仰。如果不充分生態(tài)環(huán)境因素對社會文化發(fā)展的能動作用,許多宏觀和微觀層面的歷史現(xiàn)象都將無法得到合理圓融的解釋。
當(dāng)然,筆者也曾指出:采用社會生態(tài)史的框架來認(rèn)識社會,只是社會歷史觀察的一個特殊途徑,不能期望所有問題都能由此得到圓滿的回答。這是因為,社會生態(tài)史研究并不能完全取代一般的社會史研究,有些社會歷史問題并不在它的觀察范圍;更重要的是,現(xiàn)代生態(tài)學(xué)畢竟導(dǎo)源于生物學(xué),而人類不僅具有生物屬性,同時還具有文化屬性(特別強(qiáng)調(diào)一點(diǎn):文化具有自我演繹性),擁有復(fù)雜文化和思想情感的人類畢竟不同于其它動物,人類社會系統(tǒng)與其它生命系統(tǒng)的差距很大,其系統(tǒng)結(jié)構(gòu)、系統(tǒng)功能與運(yùn)行機(jī)制的復(fù)雜性遠(yuǎn)遠(yuǎn)超過其它任何生命系統(tǒng),在觀察社會歷史問題方面,現(xiàn)有生態(tài)學(xué)理論方法的解釋力仍然有所不足,對于現(xiàn)代生態(tài)學(xué)概念、術(shù)語和技術(shù)方法在社會歷史研究中的適用程度,不能期望過高,更不能簡單機(jī)械地套用,而應(yīng)在認(rèn)真披揀、選擇和改造其適用部分的基礎(chǔ)上,努力構(gòu)建符合中國歷史研究需要的新的理論方法體系[8]。如果將人類社會簡單類同于一般動物系統(tǒng),而忽略它的特殊性和復(fù)雜性,所得出的結(jié)論將可能是十分荒謬可笑的。
參考文獻(xiàn):
[1]徐中舒.徐中舒歷史論文選輯[M].北京:中華書局,1998.
[2]德日進(jìn)、楊鐘健.安陽殷墟之哺乳動物群[J].北京:中國古生物志(丙種第12號第1期),1936.
[3]楊鐘健、劉東生.安陽殷墟之哺乳動物群補(bǔ)遺[J].北京:中國考古學(xué)報(中國科學(xué)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十三第4冊),1949.
[4]竺可楨.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J].北京: 考古學(xué)報,1972,(1).
[5]葛劍雄、華林甫.二十世紀(jì)的中國歷史地理研究——回顧與展望[J].北京:歷史研究,2002,(3).
[6]景愛.環(huán)境史:定義、內(nèi)容與方法[J].開封:史學(xué)月刊,2004,(3).
[7]梅雪芹.環(huán)境史學(xué)與環(huán)境問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8]王利華.社會生態(tài)史——一個新的研究框架[J].天津:社會史研究通訊(內(nèi)部交流刊),2000,(3).
[1] 這一點(diǎn)可由《中國社會科學(xué)》、《歷史研究》、《史學(xué)理論研究》、《中國史研究》、《史學(xué)月刊》、《歷史地理》和《中國歷史地理論叢》等權(quán)威學(xué)術(shù)期刊頻繁刊載有關(guān)方面的學(xué)術(shù)論文可以看出。
[2] 關(guān)于過去一個時期中國生態(tài)環(huán)境史研究的發(fā)展情況,張國旺:《近年來中國環(huán)境史研究綜述》(載《中國史研究動態(tài)》2003年第6期)、佳宏偉:《近十年來生態(tài)環(huán)境變遷史研究綜述》(載《史學(xué)月刊》2004年第6期)分別作了較系統(tǒng)的回顧;王子今:《中國生態(tài)史學(xué)的進(jìn)步及其意義——以秦漢生態(tài)史研究為中心的考察》(載《歷史研究》2003年第1期)也提供了一些線索,可參閱。
[3]關(guān)于西方環(huán)境史學(xué)的發(fā)展,曾華壁《論環(huán)境史研究的源起、意義與迷思:以美國的論著為例之探討》(臺灣《臺大歷史學(xué)報》1999年第23期)、包茂宏《環(huán)境史:歷史、理論和方法》及《美國環(huán)境史研究的新進(jìn)展》(載《中國學(xué)術(shù)》2002年第4期)和梅雪芹《20世紀(jì)晚期的環(huán)境史及其學(xué)術(shù)意義》(收入氏著《環(huán)境史學(xué)與環(huán)境問題》,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等文分別有所介紹,可參閱。
[4]高國榮《美國環(huán)境史學(xué)研究綜述》(“中華文史網(wǎng)”2004年9月22日刊發(fā))。對于這一轉(zhuǎn)變,包茂宏《美國環(huán)境史研究的新進(jìn)展》一文也提供了不少信息。此外,J.R.McNeill“Observations on the nature and culture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載 History and Theory, Theme Issue 42,December 2003,5-42。茲據(jù)historyandtheory.org/McNeill.pdf)一文也有專門的論述。
[5] 由于筆者不懂英語以外的其它西方語言,以上印象只是根據(jù) European Society for Environmental History (Eseh)網(wǎng)“Bibliography”英文部分得出的,讀者若欲了解詳細(xì),請登錄 eseh.de/bibliography.html 。
[6] 例如譚其驤《何以黃河在東漢以后會出現(xiàn)一個長期安流的局面》(收入《長水集》下冊,人民出版社,1987年)、史念海《隋唐時期重要的自然環(huán)境的變遷及其與人為作用的關(guān)系》(收入所著《河山集》5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均為經(jīng)典之作。
篇7
《山海經(jīng)》堪稱天下奇書。它是一部具有獨(dú)特風(fēng)格的中華古代典籍,從此書內(nèi)容涉及之廣泛,文化沉積之深厚,歷代學(xué)者研究成果之豐碩,以及當(dāng)今《山海經(jīng)》影響之不斷擴(kuò)大等方面進(jìn)行考察,可以說,把《山海經(jīng)》稱之為世界文化寶庫中之瑰玉是當(dāng)之無愧的。
一
20年紀(jì)以來,從事《山海經(jīng)》研究的學(xué)者逐漸增多,成果迭出。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本世紀(jì)(截至各正式學(xué)刊發(fā)表論題含有“山海經(jīng)”或其篇目名的學(xué)術(shù)論文就有172篇,其中外國學(xué)者6篇。至于論題未直接標(biāo)明書名而涉及《山海經(jīng)》研究的則更多。
專著的推出標(biāo)志著《山海經(jīng)》研究的深化。1980年和1985年,袁珂《山海經(jīng)校注》、《山海經(jīng)校譯》先后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90年代出版的《山海經(jīng)》研究專著則有徐顯之《山海經(jīng)探原》(武漢出版社1991年出版)和扶永發(fā)《神州的發(fā)現(xiàn)》(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
《山海經(jīng)校注》包括《山海經(jīng)山經(jīng)柬釋》和《山海經(jīng)海經(jīng)新釋》兩部份,后附“《山海經(jīng)》敘錄”,全錄漢劉歆(秀)《上〈山海經(jīng)〉表》、晉敦璞《注〈山海經(jīng)〉敘》、舊本《山海經(jīng)》目錄和清郝懿行《山海經(jīng)箋疏敘》,另附“所據(jù)版本及諸家舊經(jīng)書目”與“引用書目”,書后另有《山海經(jīng)》索引,由張明華編。袁珂《山海經(jīng)校注》的主體部分是《山經(jīng)柬釋》和《海經(jīng)新釋》,后者完成于1963年,“著重對神話傳說部分的注釋,蒐羅豐富,征引詳博,頗有發(fā)明,其它部分也作了詮解和校勘”(注:《〈山海經(jīng)〉校注》出版說明,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山經(jīng)柬釋》完成于80年代。袁氏在序中指出的“《山海經(jīng)》匪特史地之權(quán)輿,乃亦神話之淵府”(注:《〈山海經(jīng)〉校注》序。)是對《山海經(jīng)》一書內(nèi)容的概括,很有見地。
《山海經(jīng)校譯》的最大成果在于校勘方面。作者認(rèn)為“須首先整理出一個《山海經(jīng)》的新校本來”(注:《〈山海經(jīng)〉校譯》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該書校勘是從十個方面著手的,即錯、脫、衍、倒、經(jīng)文入注、注入經(jīng)文、脫簡和錯簡、它書竄入、篡改、其它。在校勘的基礎(chǔ)上,此書按郭璞注《山海經(jīng)》18卷順序作了全譯。
《山海經(jīng)》研究的地理學(xué)派、歷史學(xué)派和文學(xué)神話派發(fā)端甚早。地理學(xué)派認(rèn)為《山海經(jīng)》是一部主要記述地理事物的著作,歷史學(xué)派認(rèn)為《山海經(jīng)》是反映中國上古時代的史籍,文學(xué)神話派認(rèn)為此書是神話匯集。本世紀(jì)中,由于不同學(xué)者對《山海經(jīng)》性質(zhì)的認(rèn)定和研究側(cè)面各有不同,各學(xué)派的流派特征逐漸明朗。值得注意的是,許多從事自然科技史研究的學(xué)者也參加治《山海經(jīng)》學(xué)人隊伍,他們的研究側(cè)重于《山海經(jīng)》科學(xué)價值和經(jīng)文破譯。近年來,各學(xué)派已在一些研究領(lǐng)域取得共識,形成了研究合力。
為適應(yīng)《山海經(jīng)》研究發(fā)展形勢,1983年12月在成都舉辦了“中國《山海經(jīng)》學(xué)術(shù)討論會”,有10多個省區(qū)的60多位學(xué)者參加。這是第一次《山海經(jīng)》專題研究會議,標(biāo)志著《山海經(jīng)》研究隊伍已經(jīng)形成。
“中國《山海經(jīng)》學(xué)術(shù)討論會”后,1986年1月,四川省社會科學(xué)院出版社出版了論文集《山海經(jīng)新探》,該論文集共收論文27篇,“大致依照地理、民族、神話、科技、綜論的順序進(jìn)行編排”,“各篇論文均從不同角度對《山海經(jīng)》及其所反映的中國古史諸問題進(jìn)行了探索,對于研究和了解我國上古的社會和自然狀況均有參考意義”(注:《〈山海經(jīng)〉新探》前言,四川省社會科學(xué)院出版社1986年版。)。
二
20世紀(jì)以來,《山海經(jīng)》研究在本書性質(zhì)、篇目、作者和成書年代、地理范圍等傳統(tǒng)論題上取得很大進(jìn)展。
關(guān)于《山海經(jīng)》的性質(zhì),學(xué)者的論點(diǎn)很不一致。30年代前,幾個主要論點(diǎn)先后提出。廖平《〈山海經(jīng)〉為〈詩經(jīng)〉舊傳考》(載《地學(xué)雜志》14卷第3期、第4期,1923年)認(rèn)為《山海經(jīng)》是《詩經(jīng)》之傳注,這大概是本世紀(jì)最早涉足《山海經(jīng)》性質(zhì)討論的論文。著名的《山海經(jīng)》研究日本學(xué)者小川琢治重提史地書說,他在《〈山海經(jīng)〉的考證及補(bǔ)遺》(《支那歷史地理研究》,1928年)一文中指出:“《山海經(jīng)》一書遠(yuǎn)比一向認(rèn)為金科玉律之地理書《禹貢》為可靠,其于中國歷史及地理之研究為唯一重要之典籍”。魯迅則提出巫書說,受到一些學(xué)者的贊同。
80年代以后,《山海經(jīng)》性質(zhì)的討論更為活躍。從歷史學(xué)角度研究《山海經(jīng)》的學(xué)者主張《山海經(jīng)》是一部“側(cè)重反映上古歷史的珍貴古籍,雖有許多神話傳說,但應(yīng)與史實(shí)區(qū)分開來,通過此書可以看出人類社會由原始蒙昧向高級階段漸次前進(jìn)的發(fā)展總過程”(注:段瑜:《中國〈山海經(jīng)〉討論會爭議的問題》,《新華文摘》1985年第4期。)。胡欽甫《從〈山海經(jīng)〉的神話中所得到的古史觀》(《中國文學(xué)季刊》1928年8月)、朱希祖《〈山海經(jīng)〉內(nèi)大荒海內(nèi)二經(jīng)古代帝世系傳說》(《民俗》第116期—118期,1933年5月)、鄧慕維《〈山海經(jīng)〉古史考》(《勵學(xué)(山東大學(xué))》第4期,1934年)和80年表的《〈山海經(jīng)〉及其史料價值》(《北京社會科學(xué)》1988年第3期)等文都傾向于認(rèn)定《山海經(jīng)》為歷史書。
側(cè)重于探討《山海經(jīng)》地理價值或認(rèn)定其為地理書的學(xué)者仍占多數(shù)。主要論文有顧頡剛《〈五藏山經(jīng)〉試探》(《史學(xué)論叢》第1期,1934年)、徐旭生《〈山海經(jīng)〉的地理意義》(《地理知識》1955年第8期)、曹婉如《〈五藏山經(jīng)〉和〈禹貢〉中的地理知識》(《科學(xué)史集刊》1958年第1期)、譚其驤《〈山經(jīng)〉河水下游及其支流考》(《中華文史論叢》第7輯,1978年)等。劉起釪認(rèn)為,“保存了豐富的地理素材而附麗以高度神話的《山海經(jīng)》,它開了幻想的一派”,但“不能把這一派這些著作認(rèn)真當(dāng)作嚴(yán)肅的地理書看待”(注:《〈禹貢〉作者》,《中國歷代地理學(xué)家評傳》,山東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1頁。)。近年一些探討《山海經(jīng)》地域范圍的學(xué)者大多也主張地理書說。
支持《山海經(jīng)》巫書說的學(xué)者也不少,在1983年成都學(xué)術(shù)會議上,有些學(xué)者又提出了這一主張。僅1985年一年就發(fā)表了三篇明確主張巫書說的論文:翁銀陶《〈山海經(jīng)〉性質(zhì)考》(《福建師范大學(xué)學(xué)報》,1985年第4期)、袁珂《〈山海經(jīng)〉蓋古之巫書試探》(《社會科學(xué)研究》1985年第6期)、孫致中《〈山海經(jīng)〉的性質(zhì)》(《貴州文史叢刊》,1985年第3期)。
關(guān)于《山海經(jīng)》篇目與版本討論的論文也很多,主要有蔣經(jīng)三《〈山海經(jīng)〉篇目考》(《語歷所周刊百期紀(jì)念號》,1929年)、賀次君《〈山海經(jīng)〉之版本及關(guān)于〈山海經(jīng)〉之著述》(《禹貢》第1卷第10期,1934年)、周士琦《論元代曹善抄本〈山海經(jīng)〉》(《歷史文獻(xiàn)集刊》第1集,1980年9月)等文,袁珂《〈山海經(jīng)〉產(chǎn)生地域及篇目考》(《中華文史論叢》第7輯,1978年)也討論了《山海經(jīng)》篇目。通過討論,目前對《山海經(jīng)》篇目的認(rèn)定已接近取得共識,至于《山海經(jīng)》版本學(xué)探討尚處于初始階段。
關(guān)于《山海經(jīng)》作者,論者的分歧很大。何觀洲主張鄒衍縣《山海經(jīng)》的作者(《〈山海經(jīng)〉在科學(xué)上之批判及作者之時代考》,載《燕京學(xué)報》第7期,1930年);顧頡剛等主張非一人之所作,作者為秦人(如顧頡剛《禹貢全文注釋》:“《禹貢》作者的籍貫同《山經(jīng)》作者一樣,可能是秦國人。”)袁珂等主張《山海經(jīng)》作者為楚人或楚地人(如袁珂《〈山海經(jīng)〉寫作的時地及篇目考》);呂子方、蒙文通等認(rèn)為有巴蜀人的手筆(如呂子方《山海經(jīng)雜記》等)。另外,衛(wèi)聚賢主張“戰(zhàn)國中年”的“楚以南人所著”,并進(jìn)而推演為墨子弟子隨巢子寫定;李行之認(rèn)為《山海經(jīng)》作者是楚國南部一位少數(shù)民族士人,其籍貫之地望為今湖南省常寧縣(《〈山海經(jīng)〉作者考》,《求索》1989年第6期);還有人主張《山海經(jīng)》有北方齊國、燕國人的手筆。
討論《山海經(jīng)》成書時代的論文很多,主要有何定生《〈山海經(jīng)〉成書時代》(《語歷所周刊》第2卷第20期,1928年)、陸侃如《論〈山海經(jīng)〉著作年代》(《新月》第1卷第5期,1928年)、蒙文通《略論〈山海經(jīng)〉的寫作時代及其產(chǎn)生地域》(《中華文史論叢》第1輯,1962年)、翁銀陶《〈山海經(jīng)〉作于楚懷王末年考》(《求索》1987年第5期)。通過論討,大多數(shù)學(xué)者認(rèn)定的《山海經(jīng)》成書時間在東周至漢代之間。不過,也有人認(rèn)為“本書成書年代可上溯至夏商。”有的認(rèn)為“《山海經(jīng)》的相對年代以儒家所說堯舜時期較為準(zhǔn)確,即夏代建立以前,約在公元前21世紀(jì)”(注:段瑜:《中國〈山海經(jīng)〉討論會爭議的問題》,《新華文摘》1985年第4期。)。
《山海經(jīng)》地理范圍的討論十分活躍,眾說迭起且相差驚人。大致說來,本世紀(jì)發(fā)表的論點(diǎn)可以歸納為三類:一是傳統(tǒng)的華夏說,二是局部小區(qū)說,三是世界圈說。
傳統(tǒng)的華夏說認(rèn)為,《五藏山經(jīng)》的地理范圍,“從所提到的山名來看,東邊達(dá)到東海之濱的會稽山,西邊提到了新疆的天山;從所描述的地理環(huán)境來看,北邊似乎越過了蒙古高原,到了西伯利亞,南邊似乎到了江南”(注:赫維人:《淺談〈五藏山經(jīng)〉》,《云南師大學(xué)報》1985年第1期。)。《海經(jīng)》描述的地理范圍則可遠(yuǎn)及朝鮮、日本、中南半島和阿富汗、俄羅斯等鄰國。持傳統(tǒng)觀點(diǎn)的學(xué)者對《山海經(jīng)》的地理內(nèi)容作了詳細(xì)的考訂,如譚其驤《〈山經(jīng)〉河水下游及其支流考》、衛(wèi)挺生《南山經(jīng)地理考釋》等五篇(載《東方雜志》1969年至1973年)等就是如此。
有些學(xué)者認(rèn)為《山海經(jīng)》描述的地域范圍很小,只及中國境內(nèi)某一局部地域。何幼琦《海經(jīng)新探》(《歷史研究》1985年第2期)認(rèn)為《海經(jīng)》的山川疆域只在今山東省中南部以泰山為中心的地域。扶永發(fā)《神州的發(fā)現(xiàn)》一書認(rèn)為,《山海經(jīng)》記述的是云南西部東經(jīng)101度以西,北緯23度以北縱谷地區(qū)的地理,書中的古昆侖山即今云南納溪河和毗雄河——苴力河以西、云縣縣城以北、高黎貢山以東、金沙江以南橫斷山脈地區(qū)。作者還利用地圖比例,換算出《山海經(jīng)》里距為今日華里的3.4%左右(注:扶永發(fā):《神州的發(fā)現(xiàn)》,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和局部小區(qū)說相反,有些學(xué)者認(rèn)為《山海經(jīng)》描述的地理事物遠(yuǎn)及非洲、歐洲、大洋洲和美洲,不少國外學(xué)者也持這一觀點(diǎn)。
國人《山海經(jīng)》地理范圍世界圈說可能發(fā)端于梁啟超、蘇雪林的中亞西亞說,本世紀(jì)70年代一些國外學(xué)者認(rèn)定《山海經(jīng)》某些部分相當(dāng)準(zhǔn)確地描寫了北美大陸,以及近年來在南美洲等地發(fā)現(xiàn)中華古文化遺物從而推論中國人最早到達(dá)美洲,這些事實(shí)支持并推動了世界圈說的提出。
梁啟超很早就曾提出“此經(jīng)蓋我族在中亞細(xì)亞時相傳之神話,至戰(zhàn)國秦漢間始寫以華言”(注:梁啟超:《翻譯文學(xué)與佛典》,《佛教與中國文學(xué)》,臺北大乘文化出版社1981年版。)。蘇雪林認(rèn)為《山海經(jīng)》所述海內(nèi)外的海實(shí)際指黑海、里海、阿拉伯海、印度海、地中海,《山海經(jīng)》“是兩河流域的地理書”,在戰(zhàn)國時由波斯學(xué)者攜來中國(注:《屈原與〈九歌〉》,《屈原評傳》1978年版第107頁。)。國外有的學(xué)者也主張世界圈說,如法國學(xué)者維寧認(rèn)為《海外東經(jīng)》、《大荒東經(jīng)》所寫“好象都是圍繞著科羅拉多大峽谷的地區(qū),但沒有計算里程”,“第四卷《東山經(jīng)》的記述與北美洲、中美洲及墨西哥灣地區(qū)有關(guān),有明確里數(shù)”(注:《無名的哥倫布或慧深與阿富汗族之佛教團(tuán)于五世紀(jì)發(fā)見美洲之證據(jù)》。)。為世界圈說注入活力的還有考古發(fā)現(xiàn)。近幾年,在美洲發(fā)現(xiàn)了反映軒轅氏的虎皮畫和殷商文化遺跡乃至寫有漢字的實(shí)物。
《山海經(jīng)》地理范圍世界圈說推出了不少論著。宮玉海《談?wù)勅绾谓议_〈山海經(jīng)〉奧秘》(《長白論壇》1994年第3期)是這一主張的代表作,該文對《山海經(jīng)》一些地名作了闡釋,地域涉及今歐洲、非洲、大洋洲、美洲等地。該文還認(rèn)為,“整個世界只有一個大陸時,就是《海內(nèi)經(jīng)》時代”。此外,胡遠(yuǎn)鵬《〈山海經(jīng)〉揭開中國及世界文化之謎》(《淮陰師專學(xué)報》1995年第3期)朱兆明《〈山海經(jīng)〉和中華文化圈》(《東北師范大學(xué)學(xué)報》1994年第5期)等文也表達(dá)了與宮文相同的觀點(diǎn)。焦國標(biāo)《〈山海經(jīng)〉空間之謎解析》(《信陽師范學(xué)院學(xué)報》1993年第2期)一文為《山海經(jīng)》蘊(yùn)涵的國外地理信息作出解釋,認(rèn)為《山海經(jīng)》是“我們民族自其初始至?xí)伤袝r代中保留于記憶里的經(jīng)歷(歷史、地理、聞見、見解等)的殘存者,漫長時代中繁復(fù)的經(jīng)歷代代相傳至《山海經(jīng)》成書時的‘記憶’,必然有久遠(yuǎn)和錯雜兩大特點(diǎn)”,該文認(rèn)為《山海經(jīng)》中的包括地理事物在內(nèi)的“記憶”材料是先民東遷時帶來的。
轉(zhuǎn)貼于
三
除了上述《山海經(jīng)》性質(zhì)、篇目、作者和成書時代、《山海經(jīng)》的地理范圍等傳統(tǒng)論題外,本世紀(jì)《山海經(jīng)》全方位研究還涉及到天文學(xué)、氣象學(xué)、氣候?qū)W、歷學(xué)、醫(yī)藥學(xué)、生物學(xué)、古人類學(xué)、考古學(xué)乃至音樂學(xué)等方面的新論題。
1905年,劉光漢在《〈山海經(jīng)〉不可疑》(《國粹學(xué)報》第1卷第10期)一文中就指出此書的科學(xué)性。30年代,學(xué)者已開始探討《山海經(jīng)》的科學(xué)價值。何觀洲《〈山海經(jīng)〉在科學(xué)上之批判及作者之時代考》(《燕京學(xué)報》第7期,1930年6月)、鄭德坤(《〈山海經(jīng)在科學(xué)上之批判及作者之時代考〉書后》(《燕京學(xué)報》第7期,1930年6月)等文涉及了《山海經(jīng)》一書某些科學(xué)解釋問題,鐘敬文《〈山海經(jīng)〉的醫(yī)藥學(xué)》則是從醫(yī)藥學(xué)角度探討《山海經(jīng)》科學(xué)價值的論文。到了60年代,又有張貽俠《〈山海經(jīng)〉——世界上最古老的礦產(chǎn)地質(zhì)文獻(xiàn)》(《光明日報》1961年3月29日)和伊藜清司《〈山海經(jīng)〉與鐵》(《社會經(jīng)濟(jì)史的諸問題》,《森嘉兵衛(wèi)教授退官紀(jì)念論文集》1969年6月)等。
80年代以后,探討《山海經(jīng)》科學(xué)價值的論文題材逐漸廣闊,學(xué)者的注意力已涉及到天文學(xué)、氣象學(xué)、氣候?qū)W、歷學(xué)、生物學(xué)、古人類學(xué)、考古學(xué)、音樂學(xué)等各個方面。孫培良《〈山海經(jīng)〉拾證》(《文史集林》1985年第4期)、尚志鈞《〈山海經(jīng)〉榮草釋》(《中華文史論叢》第15輯,1980年3月)、蓋山林《陰山巖畫與〈山海經(jīng)〉》(《內(nèi)蒙古社會科學(xué)》1981年第3期)、全祖孟《〈山海經(jīng)〉中的渾天說》(《歷史地理》第8輯,1990年)、陳國生、黃蔭歧《〈五藏山經(jīng)〉記載的植物地理學(xué)》(《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5年第3期)、劉恭德《試論〈山海經(jīng)〉與遠(yuǎn)古氣候史關(guān)系的若干問題》(《大自然探索》1993年第4期)、謝因《〈山海經(jīng)〉與現(xiàn)代科學(xué)》(《讀書》1981年第8期)、吉聯(lián)杭《〈山海經(jīng)〉遠(yuǎn)古音樂材料初探》(《中國音樂》1981年第2期)、王守春《〈山海經(jīng)〉與古代新疆歷史地理相關(guān)問題的研究》(《西域研究》1997年第3期)等是這一類論文的代表。
篇8
北京師范大學(xué)成立的全國高校第一個研究所――古籍研究所,經(jīng)過長時間的經(jīng)營承擔(dān)起了《全元文》這套書的編輯重任,由李修生主編,在大規(guī)模文獻(xiàn)普查基礎(chǔ)上于1999年由江蘇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第一冊。歷時15載編纂成功,其中收錄了大量元人別集中的著作和散篇文章,匯集了諸多不易見的材料。《全元文》共61冊,1880卷,收文35000多篇,總字?jǐn)?shù)約2800萬,涉及元代作者3200余人,是有元一代全部漢文文章的總匯,在收集過程中對誤收和漏收作了大量甄別工作,這是一個巨大的貢獻(xiàn)。
本文將以此書為基礎(chǔ),對書中收錄的江西人物進(jìn)行全面的統(tǒng)計與分析,以期從一個側(cè)面深入了解元代的江西文化。
二、《全元文》所收江西文人的地域分布
經(jīng)過統(tǒng)計,《全元文》所收江西13路人數(shù)多寡依次為:吉安路(57人)、饒州路(48人)、撫州路(39人)、龍興路(36人)、信州路(19人)、臨江路(17人)、建昌路(10人)、江州路(9人)、瑞州路(7人)、南康路(4人)、袁州路(3人)、南安路(2人)、贛州路(1人),另有4位永豐人,不明是吉安之永豐,還是信州之永豐,還有3位只注明籍貫江西,具體地望不明。達(dá)到10人以上的單個州縣有:徽州路婺源州(27人)、饒州路鄱陽縣(24人)、吉安路廬陵縣(22人)、龍興路南昌縣(22人)、撫州路臨川縣(14人)和金溪(13人)以及吉安路吉水州(11人)。
三、元代江西文化地域差異分析
元明清時期,“運(yùn)河──長江──贛江──北江――珠江則成為國內(nèi)最為重要的南北通道。這條通道全長兩千多公里,貫穿北京、河北、山東、江蘇、安徽、江西、廣東七省市,在江西境內(nèi)則占三分之一。”中國東南半壁賴以溝通江湖陸海,縱貫?zāi)媳闭呤獯艘煌荆瑥亩纬闪私鲄^(qū)域文化上的重要特點(diǎn)。這就很好地說明元代江西的文化必定在全國發(fā)揮著重大的影響。筆者從交通方面來詳細(xì)分析元代江西出現(xiàn)以上五個文化富集區(qū)的原因。
1.徽州路婺源州文化亞區(qū)
元代昌江和婺水是使用頻率較高的兩條水道,連接徽州與鄱陽湖。元人丁復(fù)有詩:“荒涼秋浦時時酒, 仿佛番江夜夜船。” 番江, 通“鄱江”, 即婺水, 今名樂安河, 由婺源流經(jīng)饒州路治鄱陽入鄱陽湖, 是聯(lián)系婺源與龍興經(jīng)濟(jì)中心區(qū)的重要交通線。昌江在鄱陽附近與婺水匯合后流入鄱陽湖, 是祁門茶等經(jīng)濟(jì)作物與浮梁瓷器外銷的重要水上通道。位于婺水與昌江交匯處的鄱陽成為發(fā)達(dá)的商業(yè)中級市鎮(zhèn)。
2.饒州――信州文化亞區(qū)
饒州、信州兩路還是江西省通往江浙及福建地區(qū)的長廊。信江整個河段在元時都是可以通航的。元政府在信江沿線設(shè)有水驛, 由鄱陽湖溯信江水路, 經(jīng)余干、安仁、貴溪、弋陽、信州(今上饒市)、沙溪抵玉山。由這可抵杭州, 往南可到武夷山, 至福建省境。信江邊的貴溪縣西南八十里的道教勝地龍虎山, 顯赫的宗教地位加上信江驛道的便捷交通,促進(jìn)了當(dāng)?shù)亟?jīng)濟(jì)和文化的發(fā)展。
3.豫章文化亞區(qū)
治所龍興地處廣大贛江腹地與鄱陽湖的連接點(diǎn),“南接五嶺, 北帶九江”、“襟帶江湖, 控引荊越”, 南北溝通珠江與長江兩大水系, 東西連接兩湖與浙閩兩大經(jīng)濟(jì)區(qū), 人稱“吳頭楚尾”。據(jù)載, 當(dāng)時的龍興城“緣江而為城”,“受江右諸江之水, 而衍迤寬廣, 安而有容”。優(yōu)越的商業(yè)交通中心地位使龍興城四方百貨云集, 商賈匯萃,“官鹽法茗有饒乏, 市利商功無算籌”, 商品交易量相當(dāng)可觀。“浮梁(今江西景德鎮(zhèn))、吉水(今江西吉水) 的瓷器, 袁州(今江西宜春) 的木材, 分寧(今江西修水) 的茶葉, 永豐(今江西永豐)、撫州(今江西撫州) 的棉產(chǎn)品”。所以南昌的文化依賴自身良好的交通優(yōu)勢,相應(yīng)地也很發(fā)達(dá),從表一中可以看到南昌籍貫的人數(shù)達(dá)到22人,而龍興路共達(dá)到36人。
4.廬陵文化亞區(qū)和臨川文化亞區(qū)
臨川境內(nèi)河流交錯,水系成網(wǎng),10平方公里以上流域面積的河流就有467條。 本市河流均屬長江流域,有撫河、贛江、信河三大水系。撫河干流全長317公里,為全市最大河流,也是江西省第三大河流。本市流域面積為1.59萬平方公里,占全流域面積的91.9%。沿汝水(今撫江, 上游為盱江) 過撫州、建昌,在建昌、邵武交界處度杉關(guān),可連接由邵武下汀州到潮州的驛道;也可由麻沙至建陽,上建溪,連接閩江干線。在贛東臨川、贛中吉安也相繼出現(xiàn)諸多“臨川才子”及著名文學(xué)家。
這兩個文化富集區(qū)的發(fā)展主要都是依靠贛江這條重要航道,撫河、贛江、信河航運(yùn)網(wǎng)絡(luò)的構(gòu)建,促進(jìn)了廬陵地區(qū)和臨川地區(qū)的信息流、物資流、文化流的形成。對江西經(jīng)濟(jì)文化的開發(fā)和發(fā)展關(guān)系甚巨。
本文通過對被收入《全元文》的江西文人地域分布做統(tǒng)計分析,可以了解江西文化與人才的歷史地域特征,對江西文化地域差異形成原因的探究,有助于進(jìn)一步了解元代江西文化。
參考文獻(xiàn):
[1] 鄭建明.試論江西進(jìn)士的地理分布[J].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9,(4):205-226.
[2] 謝宏維.論明清時期江西進(jìn)士的數(shù)量變化與地區(qū)分布[J].江西師范大學(xué)學(xué)報(哲學(xué)社會科學(xué)版),2000,(4):23-28.
[3 方志遠(yuǎn),孫莉莉.地域文化與江西傳統(tǒng)商業(yè)盛衰論[J].江西師范大學(xué)學(xué)報(哲學(xué)社會科學(xué)版),2007,(2):54.
[4] 劉錫濤.宋代江西文化地理研究[D].陜西:陜西師范大學(xué)博士學(xué)位論文,2001.
[5] 宋濂.元史[Z].北京:中華書局,1976.4-1491.
[6] 脫脫.宋史[Z].北京:中華書局,1977.11-2187.
[7] 劉錫濤.吉安宋代文化發(fā)展成就略說[J].井岡山師范學(xué)院學(xué)報(哲學(xué)社會科學(xué)版),2005,(1):61-64.
[8] 李才棟.江西古代書院研究[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3.10-213.
[9] 楊濂.元詩史[M].北京: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2003.8―412.
[10] 王秀麗,元代江西行省的商業(yè)交通[J].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04.9,vol 19,No.3:75―79.
[11] 謝廬明.論江西唐宋文化名人群體崛起的社會條件及其影響[J].萍鄉(xiāng)高等專科學(xué)校學(xué)報,1997,(3):41-45.
[12] [宋]王象之.輿地紀(jì)勝[M].臺北:文海出版社,1971.10.
篇9
考慮到下個世紀(jì)初人口高峰到來時中國農(nóng)業(yè)所面臨的壓力,耕地資源的變化無疑是影響中國可持續(xù)發(fā)展的關(guān)鍵問題。
1耕地數(shù)量變化的總體趨勢
與淡水資源一樣,土地資源屬于典型的多功能性自然資源,隨著人口和經(jīng)濟(jì)社會的發(fā)展,受到來自各方面需求的壓力不斷增大。特別是在經(jīng)濟(jì)高速增長的中國,土地資源,尤其是耕地資源,在這種需求的壓力下經(jīng)歷著前所未有的利用方式和質(zhì)量的變化。中國改革開放以來耕地資源變化總體趨勢表現(xiàn)為向其他利用方式的轉(zhuǎn)變,總面積持續(xù)減少。在“誰來養(yǎng)活中國”
的論爭和全球食物安全危機(jī)之背景下,耕地?fù)p失的問題引起了政府和社會各界廣泛的關(guān)注[2、3].我國政府為了遏制耕地持續(xù)減少的勢頭,提出了以行政區(qū)“耕地總量平衡”為目標(biāo)的耕地保護(hù)政策。
對于我國耕地總量,一直缺乏權(quán)威的數(shù)據(jù)。比較長的時間序列數(shù)據(jù)是國家統(tǒng)計局的統(tǒng)計資料[4].根據(jù)統(tǒng)計局的資料,我國耕地面積在1957年達(dá)到高峰,其后經(jīng)歷了一次大幅度的減少。第二次大的滑坡發(fā)生在1965~1977年;第三次1980~1988年;第四次從1992年持續(xù)至今。
改革開放以來耕地減少的速度是60年代至今最快的一段時間。根據(jù)原國家土地管理局和國家統(tǒng)計局的資料計算[5],1978~1997年累計增加耕地1140萬hm2,累計減少1605萬hm2,兩者相抵,凈減少465萬hm2,占耕地總面積的3.5%,相當(dāng)于整個江蘇省的耕地面積。這段時間平均每年凈減少耕地25萬hm2,而在此前的10年(1968~1978)間,平均每年凈減少16萬hm2,速度明顯加快。
在改革開放以來的20年間,耕地總量平衡中只有1979、1990、1995和1996年新增耕地面積超過了減少的耕地面積。但凈增面積有限,不超過10萬hm2.凈減少最快的是1984~1988年,年均減少55萬hm2,其中1985年是減少最多的一年,達(dá)100萬hm2.1993~1995三年也很突出,每年凈減少近40萬hm2.
如果僅從全國尺度考察耕地總量變化,會忽視一些重要的現(xiàn)象。從耕地面積變化的空間分布上看,凈減少最快的一是廣東、福建、上海、江蘇、浙江、山東、北京、天津及遼寧等沿海省份;二是陜西、湖北、四川、湖南、山西等中部省份。盡管從全國的趨勢看個別年份耕地面積是凈增加的,但這些自然條件較好的省份自1978年以來一直維持著凈減少的趨勢。
那些自然條件較差的邊遠(yuǎn)省份,如內(nèi)蒙古、黑龍江、新疆、云南、廣西、貴州、甘肅、寧夏等省,1988年以后耕地卻基本上是凈增加的。個別省份,如內(nèi)蒙古和黑龍江等,增加的幅度還比較大。耕地面積變化的這種區(qū)域差異,說明在我國耕地總量的動態(tài)平衡中,生產(chǎn)力較低的耕地面積的增加,在數(shù)量上部分地抵消了優(yōu)質(zhì)良田的減少,因而掩蓋了問題的實(shí)質(zhì)。
2耕地數(shù)量變化的構(gòu)成和分布
1988年以來,原國家土地管理局每年公布耕地增減的統(tǒng)計資料,被認(rèn)為是這方面比較權(quán)威的數(shù)據(jù)。根據(jù)該局1988~1995年的數(shù)據(jù)分析,8年中增加的耕地主要來源于荒地開墾,占76%;農(nóng)業(yè)結(jié)構(gòu)調(diào)整和復(fù)墾所占的比例較小,分別為13%和11%.在損失耕地的構(gòu)成中,農(nóng)業(yè)結(jié)構(gòu)調(diào)整,包括轉(zhuǎn)變?yōu)楣麍@、魚塘、林地及草地的耕地,占有最大的份額,為62%.其次為非農(nóng)建設(shè)占地,占20%.自然災(zāi)害損毀(風(fēng)蝕、水蝕、沙壓、洪澇)的耕地面積占18%.
新開墾的耕地主要來于自然條件較為惡劣的東北、西北和西南地區(qū)。新疆、云南、黑龍江、內(nèi)蒙古及廣西等省8年間荒地開墾面積最大,占全國開荒總面積的60%.有趣的是,這幾個省份也正是災(zāi)害毀損耕地最為嚴(yán)重的地區(qū)。從結(jié)構(gòu)調(diào)整占地的情況看,果園和魚塘占地問題較為嚴(yán)重的省份包括廣東、江蘇、遼,全國公務(wù)員共同天地寧、湖北及陜西等,主要是東部和中部地區(qū);而退耕還林還草的耕地占總耕地面積最大的省份有內(nèi)蒙古、陜西、新疆、和云南,主要分布在西部地區(qū)。非農(nóng)建設(shè)占地比較嚴(yán)重的地區(qū)明顯地分布在以珠江三角洲、長江三角洲和京津為中心的東部沿海地區(qū),此外,湖北、河南及安徽等中部省份也比較嚴(yán)重。值得注意的是,在1988~1991年期間,沿海12個省份非農(nóng)建設(shè)占地在全國此類占地中的比重維持在40%左右,而在此后的4年,比重上升到50%~55%.
中國近20年來耕地面積的變化及其政策啟示來自:免費(fèi)
3增減耕地的質(zhì)量差異
如果只從數(shù)量上比較耕地面積的增減,不能充分說明目前發(fā)生在我國的耕地問題的實(shí)質(zhì)。
實(shí)際上,在我們這個有著幾千年農(nóng)業(yè)文明而且人多地少的國度,尚存的可開墾宜農(nóng)荒地資源已十分有限。因此,近年來新增加的耕地主要是生產(chǎn)力較低的邊際土地。這些耕地產(chǎn)量低而不穩(wěn),退耕的危險很大。此外,由于人口與耕地在空間分布上高度相關(guān),損失的耕地,尤其是非農(nóng)建設(shè)占用的耕地,主要是優(yōu)質(zhì)的農(nóng)田。這些耕地往往含有很高的物化資本。從以上所述耕地面積變化的地理分布上,也可以看出這些問題。
為了說明近年來我國耕地變化造成的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力的損失,我們按增、減耕地所在地區(qū)的糧食單位面積平均產(chǎn)量進(jìn)行了大致的估算[6].1988~1995年間,我國新增加的耕地面積為39萬hm2/a,減少60萬hm2/a,比例為1∶1.54.按增減耕地所在省份和所發(fā)生的年份糧食平均產(chǎn)量水平估算,新增加耕地貢獻(xiàn)的糧食為143萬t/a,減少的耕地造成的糧食損失為236萬t/a,比例為1∶1.65.假如將空間尺度縮小到縣,這種估算就更加接近于實(shí)際情況。1980~1994年間,我國耕地凈增加縣份增加的耕地總計為10萬hm2/a,凈減少的縣份減少共44萬hm2/a,比例為1∶4.4.按增減耕地所在縣份1990年糧食平均產(chǎn)量水平估算,耕地凈增加縣份貢獻(xiàn)的糧食約424萬t/a,耕地凈減少縣份的糧食損失為3216萬t/a,比例為1∶7.6.實(shí)際上,采用所在地區(qū)平均產(chǎn)量水平來計算,多數(shù)情況下是過高地估計了新增耕地而過低地估計了損失的耕地的生產(chǎn)水平。但無論如何,這一估算說明,假如只是從總量增減平衡上來衡量我國的耕地問題,可能會舍本求末。
論文中國近20年來耕地面積的變化及其政策啟示來自
4耕地變化的驅(qū)動力分析
在改革開放后的20年中,我國耕地面積的變化與經(jīng)濟(jì)波動有著較為密切的聯(lián)系(圖1)。
首先,從全國耕地總量的變化曲線上看,以固定資產(chǎn)投資大幅度提高為特征的經(jīng)濟(jì)鼓動期都伴隨著新一輪的耕地總量滑坡,而經(jīng)濟(jì)調(diào)整期則出現(xiàn)耕地?fù)p失減緩的勢頭。與固定資產(chǎn)投資關(guān)系最為密切的是非農(nóng)建設(shè)占用耕地的情況。以這個時期中耕地減少幅度較大的1992~1995年為例,以省級數(shù)據(jù)計算的兩者的相關(guān)系數(shù)高達(dá)0.85.非農(nóng)建設(shè)占地對固定資產(chǎn)投資較為敏感,某種程度上說明我國城鄉(xiāng)的建設(shè)用地效率低,不夠集約。如果把單位固定資產(chǎn)投資占用耕地的面積作為評價用地效率的指標(biāo),我們發(fā)現(xiàn),用地效率較高的省份大都分布在城市化水平高的地區(qū),如京、津、滬、吉、粵、魯、閩等;城市化水平低的省份往往用地效率也低,如藏、皖、豫、黔、滇、桂、陜等(表1)。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在空間布局上的分散是造成非農(nóng)建設(shè)占地多的一個主要方面。全國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集聚在城鎮(zhèn)的只占8%,其余分散在農(nóng)村[7].以省級資料做比較,發(fā)現(xiàn)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分散程度高的省份用地效率就低(表1)。
*資料來源:建設(shè)占地為1992~1995年數(shù)據(jù),來源于文獻(xiàn)5;固定資產(chǎn)投資為1992~1995年數(shù)據(jù),來源于文獻(xiàn)4;工業(yè)企業(yè)數(shù)和城市化程度為1995年數(shù)據(jù),來源于文獻(xiàn)4.
在1988~1995年間,農(nóng)業(yè)結(jié)構(gòu)調(diào)整造成的耕地?fù)p失占總耕地?fù)p失的一半以上。這部分占地主要有兩種情況,一是退耕還林還草,二是開辟果園或開挖魚塘。前者主要是在政府有關(guān)環(huán)境和生態(tài)保護(hù)政策和十大防護(hù)林工程的指導(dǎo)和帶動下進(jìn)行的;后者主要是農(nóng)民在比較經(jīng)濟(jì)效益的驅(qū)使下發(fā)生的①。1979~1996年,我國的果園面積增加了近4倍。從增長曲線上來看,與糧食產(chǎn)量的增長有密切的關(guān)系。果園面積的兩個快速擴(kuò)大期(1985~1988年和1993~1996年)都是在糧食總產(chǎn)上了一個臺階之后。1985~1988年是果園面積擴(kuò)大最快的時期,它是在1983年糧食產(chǎn)量達(dá)到一個高峰之后,農(nóng)民人均占有糧食得到了迅速提高,人們開始尋找提高收入的新的土地經(jīng)營方式。同時,我國3種主要糧食作物的單位面積產(chǎn)量也是在1984年前后達(dá)到歷史新高,為農(nóng)業(yè)的多種經(jīng)營提供了可能。
土地退化構(gòu)成我國耕地?fù)p失的另一個重要的驅(qū)動因子。我國每年因災(zāi)害毀損的耕地面積平均為4.5萬hm2左右,主要發(fā)生在東北、西北和西南各省。災(zāi)損耕地嚴(yán)重的省份也是開荒面積最多的地區(qū),兩者的相關(guān)系數(shù)為0.75.這些地區(qū)自然條件均較惡劣,環(huán)境十分脆弱。一般來講,受沙漠化威脅大的東北和西北地區(qū),因災(zāi)損而棄耕的面積較大;受水土流失威脅較大的西南地區(qū),因災(zāi)損而棄耕的面積相對較小,但造成的耕地生產(chǎn)力損失也是不可忽視的。
5政策啟示
根據(jù)以上分析,作者認(rèn)為在我國目前耕地保護(hù)的政策和管理上,應(yīng)強(qiáng)調(diào)以下幾點(diǎn):
中國近20年來耕地面積的變化及其政策啟示(1)在耕地的保護(hù)上,數(shù)量和質(zhì)量應(yīng)并重。政府在有關(guān)政策的宣傳和掌握上,應(yīng)盡快從行政區(qū)“耕地總量平衡”向“基本農(nóng)田的有效保護(hù)”和“用途管制”轉(zhuǎn)移。從本文的分析可以看出,片面強(qiáng)調(diào)總量平衡,不僅造成該保護(hù)的良田沒有保護(hù)好,還間接地鼓勵地方開墾那些不適宜耕種的土地,造成環(huán)境和生態(tài)的惡化;
篇10
一、中國地理學(xué)的開先河之作
1858年(咸豐三年),英國人慕維廉(W.Muirhead)所著《地理全志》由上海的江南制造總局出版。該書是中國最早的一部用中文所寫的地學(xué)文獻(xiàn)。慕維廉是英國傳教士,1846年來華,居住上海。他和洪仁軒有交往,曾到南京考察的政治、經(jīng)濟(jì)、宗教。他的中文著述還有:《大英國志》、《天文地理》及《知識五門》。《地理全志》由“廣學(xué)會”發(fā)行,是適應(yīng)維新運(yùn)動而出版的科學(xué)著作。該書分上、下編,共十五卷,線裝木刻本。上編主要講地理,除總論外,分別論述亞西亞、歐羅巴、阿菲利加、亞墨利加、大洋群島等五個地域,“分文、質(zhì)、政三等”論述。下編主要講地質(zhì),標(biāo)題是:地質(zhì)論、地勢論、水論、氣論、光論、草本總論、生物總論、地文論、地史論〔1〕。 將世界地理的知識介紹給了中國。之后,上海還陸續(xù)出版了《繪地法要》(著者不詳,金楷理、王德均譯,1875年江南制造總局出版)、《測地繪圖》(富路瑪著,傅蘭雅、徐壽譯,1876年江南制造總局出版)、《測候叢談》(著者不詳,金楷理、華衡芳譯,1876年江南制造總局出版)《測繪海圖全法》(華爾敦著,傅蘭雅、趙元益譯,1901年江南制造總局出版)等介紹西方地理學(xué)方法技術(shù)的著作以及《八省沿海圖》、《平園地球圖》(兩圖均為江南制造總局出版,年代不詳)等地圖。
1901年,在上海南洋中學(xué)任教的張相文編寫了《初等地理教科書》(二冊,上海南洋公學(xué)印,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初版)和《中等本國地理教科書》(四冊,上海蘭陵社印,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四月初版)。此兩書是我國最早的地理教科書,印行總數(shù)達(dá)二百萬部以上,為地理學(xué)知識在我國的普及做出了重要貢獻(xiàn)〔2〕。
1908年,張相文著中國第一本自然地理學(xué)著作——《地文學(xué)》(地文學(xué)一詞來自日本,即自然地理學(xué)),由上海文明書局印發(fā),至民國二年(1913年)已發(fā)行了第三版〔3〕。 作者鑒于當(dāng)時一般的地文學(xué)著作不是譯自東洋就是西洋,故撰此書,“會萃各大家學(xué)說,博引旁搜,一切證例悉以中國之事實(shí)為本”,力求“親切詳瞻”〔4〕。 這在當(dāng)時也是一個可貴的創(chuàng)舉。
張相文在《地文學(xué)》緒論中,一開始就說:“地文學(xué)者,地理學(xué)之精髓也。言地理必濟(jì)地文,其旨趣始深,乃不病於枯寂無味,而於他學(xué)科亦多互相關(guān)聯(lián),如天文學(xué)、地質(zhì)學(xué)、動植物學(xué)、人種學(xué)、氣象學(xué)、物理學(xué)、化學(xué),莫不兼容并包,以為裨益人生之助。……于以統(tǒng)合各科,而蘄進(jìn)于實(shí)用,此地文學(xué)所以為最重要之學(xué)科也。”此言時至今日仍有參考價值。
《地文學(xué)》一書,篇幅不多,全書共197頁, 附中西對照表長達(dá)13頁,附彩色圖十余幅。該書的特點(diǎn)主要有:
(1)內(nèi)容分星界、陸界、水界、氣界、生物界五編。
(2)“參酌東西各大家學(xué)說”。如講到太陽系的形成時, 介紹了康德及拉普拉斯的星云說。
(3)對于舊地學(xué)家迷惑不解地許多自然地理方面的事物, 均能科學(xué)地闡明其形成原因與發(fā)展規(guī)律。例如,在講到片麻巖的形成時說:“原始界(太古界)巖石,層理清晰,乍見兒如水成巖,而其成分則為結(jié)晶質(zhì);又與火成巖無異,是為化形巖(變質(zhì)巖),大抵受地下之熱力與壓力,使最古之水成巖,悉數(shù)融解,再為凝結(jié),逐變?yōu)槠閹r。”
(4)重視聯(lián)系中國實(shí)際。“舉為例證,以本國為宗, 其為中國所無,或調(diào)查未晰,而于地文有切要之關(guān)系者,兼及他國”如講到地質(zhì)時代各界、系地層時,就指出其在我國的分布,講到河口泥沙沉積時,則以崇明島為例而加以說明。
(5)“尤時時注意實(shí)用,如防霜、避電、培植森林、 改良土壤等,各舉其要,以為實(shí)地應(yīng)用之資”。
二、活躍的地理學(xué)術(shù)組織及刊物
后,上海地理學(xué)的發(fā)展出現(xiàn)一段頗為繁榮的時期。除了繼續(xù)介紹國外地理學(xué)的知識和思想外,中國人自己的研究活動逐漸地活躍了起來,研究人員不斷增加,研究活動向有組織的方向發(fā)展。在這段時期先后出現(xiàn)“中華地學(xué)會”、“建國地學(xué)社”和“中華地理教育研究會”三個地理學(xué)術(shù)組織,并發(fā)行了《地學(xué)季刊》和《地理之友》兩個地理學(xué)術(shù)刊物。
1.中華地學(xué)會及《地學(xué)季刊》
中華地學(xué)會于1931年1月成立,由葛綏成(中華書局編輯)、 盛敘功(暨南大學(xué)教授)、李長傅(東方輿地學(xué)社兼暨南大學(xué)南洋文化事業(yè)部編輯)、丁紹恒(大同大學(xué)教授)、劉虎如(商務(wù)印書館編輯)等人發(fā)起,先后參加會員約80人,其中大部分系上海方面的會員,外地會員約20余人,分布在江蘇、浙江、安徽、湖北、湖南、四川、福建、河南及遼寧等地。
該會成立后的主要工作是編輯出版《地學(xué)季刊》。1932年1 月創(chuàng)刊號出版,共刊載18篇文章,合計約20余萬字,由大東書局印行。“發(fā)刊詞”稱:“地學(xué)之宗旨,在于研究人地相互關(guān)系,使吾人于世界各處之風(fēng)土人情,能詳釋其因果,尋求其系統(tǒng),以明今后應(yīng)如何改造之途徑。……同仁有鑒于此,組織中華地學(xué)會,以期交換知識,發(fā)展地學(xué)。內(nèi)而國計民生,外而國際概況,俾有真確之認(rèn)識。期有裨益于中華之建設(shè),固意中之事也”。至1934年底,《地學(xué)季刊》一卷四期出齊,共80余萬字,此時由于印刷困難,1935年2月2日舉行第三次年會,討論季刊的繼續(xù)出版工作,并修改會章,改選職員,聘請丁文江、王云五、何炳松、竺可楨、金兆梓、翁文灝、費(fèi)伯鴻、舒新城、為名譽(yù)會員,選舉葛綏成、李長傅、盛敘功、丁紹恒、顧因明、董文、楚曾、洪懋熙、褚紹唐為執(zhí)行委員、葛綏成為總務(wù)主任、李長傅為編輯主任、褚紹唐為干事。《地學(xué)季刊》第二卷起改由學(xué)會自行印發(fā),每期約15萬字,內(nèi)容理論與實(shí)際并重,著重系統(tǒng)研究和現(xiàn)代趨向,至1936年底后又出版了四期,共約50余萬字,由上海中國科學(xué)公司總經(jīng)售,各大城市均有特約代售處。
1937年抗戰(zhàn)開始,因會員分散,季刊無法繼續(xù)出刊,學(xué)會工作也告停止。至此,《地學(xué)季刊》共出刊了2卷8期,合計約130萬字, 刊載各類文章124篇(其中包括續(xù)載7篇,譯文24篇,如不計續(xù)載則為117 篇)。其類別為:1.介紹辯證唯物主義的地理學(xué)思想的論文6篇;2. 經(jīng)濟(jì)地理及人文地理10篇;3.自然地理12篇;4.中國地理28篇;5.歷史地理(包括邊疆地理、地名學(xué)及地理學(xué)家)19篇;6.外國地理6篇;7. 地理教學(xué)9篇;8.游記及考察9篇;9.地方志17篇;10.書目及書刊評介3篇;11.國外地理動態(tài)及會務(wù)報告5篇。
三十年代的上海各種思潮都在此匯聚。當(dāng)時上海地理學(xué)的領(lǐng)域中部分人士開始接受辯證唯物主義觀點(diǎn)并介紹新哲學(xué)觀點(diǎn)的地學(xué)刊物。這方面的文章計有楚圖南的“人文地理學(xué)的發(fā)達(dá)及其流派”、李長傅的“地理學(xué)研究的新階段”(2卷1期、2期)、“轉(zhuǎn)形期的地理學(xué)”(2卷4 期)等約10多篇。
楚圖南在“人文地理學(xué)的發(fā)達(dá)及其流派”一文最早介紹了新社會派的人文地理學(xué)的基本思想:“這個學(xué)派最先的淵源,當(dāng)然要從嘉爾(即馬克思)算起,他的《資本論》的名著里已經(jīng)提出了經(jīng)濟(jì)怎樣為一切歷史建筑或社會建筑的基礎(chǔ)。由于經(jīng)濟(jì)手段或經(jīng)濟(jì)關(guān)系的變化,而歷史或社會也不能不隨之而變化。將這個原則應(yīng)用于地理學(xué)上的問題,即人地相關(guān)的問題。于是發(fā)生了人類歷史的發(fā)展即人類文化的發(fā)展是自然契機(jī)(因素)規(guī)定了呢?還是社會契機(jī)(因素)規(guī)定了呢?據(jù)蒲列哈諾夫的意見,自然環(huán)境是最終的規(guī)定。但自然環(huán)境對于人類的影響,則以在自己的作用之下所發(fā)生的經(jīng)濟(jì)關(guān)系為媒介而主要地影響人類,這便是這派人文地理學(xué)的最基本見解或根本原則。這個原則的最初應(yīng)用,始于墨西尼可夫的《文明與歷史上的大河》,其方法和體系的大致規(guī)定,則始于威特福噶爾諸人的《地理學(xué)批判》。”李長傅在該刊二卷中連續(xù)發(fā)表了四篇介紹辯證唯物主義地學(xué)觀的文章。他在“科學(xué)的地理學(xué)的新轉(zhuǎn)向”一文中批判了當(dāng)時流行的人地關(guān)系論后指出:“人地關(guān)系的缺憾,據(jù)威特福噶爾之說,陷于速成推理法,把人與地的中間項的勞動過程漏掉了,其結(jié)論是任意規(guī)定,雖有時正確,但常常半正確,甚至完全錯誤。要救濟(jì)這缺憾只有利用辯證法的唯物論”。他又在“轉(zhuǎn)形期的地理學(xué)淺釋”一文中認(rèn)為:“正確的地理方法應(yīng)是辯證唯物論,它應(yīng)用于社會科學(xué)即唯物史觀,應(yīng)用于自然科學(xué)即自然辯證法。人對自然的活動不是個人的而是集體的,因此發(fā)生人對自然、人對人們二種活動……,自然以勞動過程為媒介,才能在人類之社會生活中發(fā)生作用。所以,一切人文地理學(xué)的現(xiàn)象,其主動力不在自然、不在人類,而在生產(chǎn)力和生產(chǎn)關(guān)系”。該文還引介威特福噶爾的圖式,說明在不同社會制度下,勞動力、勞動手段和勞動對象的不同特點(diǎn)由此形成不同類型的人地關(guān)系,這也就是辯證唯物主義地理學(xué)的中心思想。在當(dāng)時特定的歷史條件下,他們的文章不得不用隱晦的詞句論述,如資產(chǎn)階級為“布爾喬”,馬克思為“馬卡爾”、“嘉爾”等巧妙地躲避當(dāng)時政府的審查。
《地學(xué)季刊》中關(guān)于中國地理方面的文章,李長傅的“中國地理區(qū)域論”(1 卷1期和3期)兩篇文章是比較系統(tǒng)的中國地理的區(qū)劃研究。前文介紹了中國各種地理分區(qū)(如張其昀、翁文灝、香川干一、葛德石、博克斯頓、洛克斯比的分區(qū)和田中季作的東北分區(qū)等),并加以評論,最后提出作者的意見,分全國為25個地理區(qū)。后文分為緒論和本論兩段。緒論歷述地形區(qū)(野田勢次郎、史密斯、李長傅)、氣候區(qū)(竺可楨、甘德樓)、生物地理區(qū)(鄒樹文、錢崇澍)等部門分區(qū)及綜合分區(qū)(張其昀、葛德石、香川干一及李長傅等)。作者將全國分為北部、南部、東北及西北四大區(qū),26個分區(qū),并論述了各分區(qū)的特征。以上兩文是我國三十年代較系統(tǒng)的地理區(qū)劃研究論文。
李長傅的“中國湖泊的研究”(1卷4期)論述了湖泊的意義、分類、成因、變動與人生的關(guān)系及我國湖泊的分布等。此文亦為我國早期系統(tǒng)的全國湖泊研究論述。
褚紹唐的“中國都市的地理因素”(1卷2期)對我國205 個較大的城市,從地理位置、腹地條件、水運(yùn)和氣候條件及經(jīng)濟(jì)基礎(chǔ)分析了我國都市的地理因素,為我國較早研究都市地理因素的文章。
《地學(xué)季刊》在歷史地理方面主要有楚圖南的“中國歷史地理學(xué)的發(fā)展”(2卷3期)。該文討論了歷史地理學(xué)的定義、發(fā)展史略、研究的重要性、有關(guān)的科學(xué)、歷史地理學(xué)與唯物辯證法、中國歷史地理學(xué)的目的等。作者還提出了必需以唯物辯證法的方法來研究歷史地理,同時指出中國歷史地理學(xué)的最終目的不僅是說明歷代疆域沿革,最重要的是在中國這塊土地上,以歷史的地理因素或條件,來闡發(fā)中華民族、中國社會文化的發(fā)展的性質(zhì)和發(fā)展的過程。
在地名學(xué)方面,葛綏成的“地名的研究”(2卷1期),論述了地名的意義、種類、構(gòu)造、變化、同地異名及別稱、地名和國語、翻譯地名應(yīng)注意的事項等等,是我國最早較系統(tǒng)的地名研究論述。李長傅的“揚(yáng)子江名稱考”(1卷2期)指出在隋唐時即有揚(yáng)子橋,揚(yáng)子津之名,唐永淳元年(682年)曾在揚(yáng)子橋設(shè)揚(yáng)子縣, 揚(yáng)子津揚(yáng)子江之名已散于詩歌文章中。當(dāng)時揚(yáng)子江僅指揚(yáng)州以南的大江。至1658年(順治十五年)馬尼刺大學(xué)教授D.F.Navarette始稱中國最有名的大河洋子江, 意為“大洋之子”(Son of Ocean),后又譯為揚(yáng)子江,并謂此江發(fā)源于云南。至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英國使者馬卡尼(Marcartney)至揚(yáng)州,稱自此至揚(yáng)子江巖約二英里,此后在國外的文獻(xiàn)中,遂多稱全江為揚(yáng)子江。
關(guān)于地理景觀方面的論述,葛綏成的“景觀研究(1卷4期)論述了文化景觀、空中攝影、景觀綜合、景觀論等內(nèi)容,主要根據(jù)日文材料,此文為我國介紹景觀論的早期論述。
轉(zhuǎn)貼于 此外,還有盛敘功譯介的日本黑正巖的“科學(xué)的經(jīng)濟(jì)地理學(xué)”( 1卷1期、2期),德國威特噶爾的“中國農(nóng)地的灌溉問題”(2卷2期)和“中國治水事業(yè)與水利事業(yè)”、丁紹恒的“中俄界約桌原委與邊防之危機(jī)”(1卷1期)、葛綏成的“十年來的中國疆域和政治區(qū)劃的變遷”(2卷1、2期)、褚紹唐的“中國地圖史略”(1卷4期)、 楚圖南譯的“近代地理測量及繪圖學(xué)之發(fā)達(dá)”(2卷2期)、何錫昌的“自然科學(xué)體系所見地理學(xué)之地位及其本質(zhì)”(1卷3期)、張淪波的“地理科學(xué)之解釋及其代表作”(1卷3期)、周宋康的“地理環(huán)境決定論”(2卷3期)、葛綏成譯Taylor.G的“環(huán)境和人種”(2卷 3、4期)等較重要的文章。以上說明,30年代上海中華地學(xué)會編輯的《地學(xué)季刊》站在時代的前列,起到了推動我國地理科學(xué)發(fā)展的作用。
2.建國地學(xué)社
建國地學(xué)社由盧材禾(社長、復(fù)旦大學(xué)教授)、樂漢英(上海藝術(shù)研究社出版部主任)、陳聞遠(yuǎn)(南京朝報編輯)、盧毅(復(fù)旦大學(xué)教授)、黃望平(中華鐵工廠工程師)、莊國鈞(立達(dá)圖書公司經(jīng)理)、王成祖(大夏大學(xué)文學(xué)院院長、圣約翰、東吳大學(xué)教授)、黃國璋(清華大學(xué)、中央大學(xué)、北平師范學(xué)院地理系主任)、陸承蔭(中華輿地學(xué)社繪圖組長)、蔣天任(蘇州中學(xué)講師)、申廣霆(暨南大學(xué)助教)12人發(fā)起。據(jù)他們向當(dāng)時社會局申請備案〔5〕的理由稱:(1)集合地理學(xué)者,研究專科學(xué)術(shù);(2)聯(lián)絡(luò)會員感情,增進(jìn)工作效能;(3)協(xié)助政府推進(jìn)地理教育,并研究地理建國方案,以為政府之參考;(4 )促進(jìn)國民理解地理建國之重要,以養(yǎng)成正確之國家觀與世界觀。他們準(zhǔn)備做的工作有:(1 )聘請專家編輯地理教材,地圖以及各種專門著作;(2 )計劃制作地理模型、儀器、照片,以應(yīng)一般教學(xué)與普及之需要;(3 )對本國各區(qū)域作精密之實(shí)地調(diào)查(注重土地利用),出版報告;(4)舉行學(xué)術(shù)演講;(5)搜集地學(xué)資料,會員約30至50人。據(jù)筆者訪問當(dāng)時活躍在上海地學(xué)界的現(xiàn)華東師大地理系褚紹唐教授和西歐北美地理研究所的錢今昔教授,該學(xué)會在上海雖未開展較有影響的活動,但當(dāng)時的地理學(xué)工作者積極以地理學(xué)參加抗戰(zhàn)后國家重建的精神由此可見一斑。
3.中華地理教育研究會
1947年8月31日,中國地理學(xué)會在上海召集年會, 討論中學(xué)地理課程問題,因時間匆促,一時未能獲結(jié)果,乃推舉葛綏成、許逸超、褚紹唐三人負(fù)責(zé)召集上海中學(xué)地理教師作一討論。9月10日, 中學(xué)地理討論會在曉光中學(xué)開會,各大中學(xué)地理教師共二十九人出席,由葛綏成報告開會宗旨,許逸超講述地理學(xué)教育的趨勢。旋即討論地理教學(xué)實(shí)際問題,如教學(xué)時間問題、高中自然地理教學(xué)問題、高中本國地理區(qū)域問題、各省區(qū)域面積問題、外國地名譯音問題。討論結(jié)果由于問題頗大,需較長時間討論與研究,乃決定籌備上海地理教育研究會,推舉葛綏成、許逸超、王文元、邱祖謀、盧材禾、褚紹唐、陳爾壽、陳大森、朱jǐng@①琳九人為籌略委員。10月5 日上海地理教育研究會在市立育才中學(xué)成立,到會會員四十七八,會上洪紱先生作了中國省區(qū)改造問題報告,最后逐條討論章程并選定第一屆理監(jiān)事。推舉翁文灝為名譽(yù)理事長、王成祖為名譽(yù)副理事長、許逸超為理事長、葛綏成、盧材禾等14人為監(jiān)事,褚紹唐為總干事、葛綏成為總編輯、洪紱、丁錫祉等11人為研究委員。該會成立后為了使外地同行加入便利而更名為“中華地理教育研究會”,同時在國內(nèi)各重要城市均進(jìn)行組織分會。武漢分會由鄒新垓主持;北平分會由王成祖、李良驥二人主持;東南分會由李式金(廈門大學(xué))主持;南京分會由孫承烈(南京中國地理研究所)主持,西北分會由馮繩武(蘭州大學(xué))主持;昆明分會由王立本主持,貴陽分會由王鐘山(貴陽師范學(xué)院)主持;臺灣分會由任德庚(臺北師范學(xué)院)主持。中華地理教育研究會已成一全國性的地理學(xué)術(shù)組織〔6〕。 中華地理教育研究會“其旨趣擬本純學(xué)術(shù)之立場,探討新地學(xué)之真義,以效之方法,使達(dá)成教育之目的,并期待群策群力,搜輯地學(xué)之新資料,以謀有所貢獻(xiàn)于我國之地理教育”。〔7〕
中國地理教育研究會成立后,會務(wù)積極進(jìn)行,1947年10月21日召開首界理監(jiān)事會,并歡迎中央大學(xué)李旭旦教授由美國返國,開會時由李先生報告了美國地理教育狀況,并決定該會刊物名稱為《地理之友》,創(chuàng)刊號于1948年3月出版〔6〕。該研究會的主要活動是編輯出版《地理之友》。翁文灝在其發(fā)刊詞中稱:“地理研究對于國民思想,民族前途,以及人類文化等,都有莫大的關(guān)系。……我國科學(xué)地理師資的缺乏,教材和教法的欠當(dāng),是人所共曉的事,以至三十年來的地理教育,始終在非驢非馬的狀態(tài)中。……但補(bǔ)救之道不外兩點(diǎn):一是普及地理教育灌輸正確觀念和知識;二是服務(wù)地理界的同志,要從今后下決心訓(xùn)練自己,同時放棄一味室內(nèi)埋首陳書的陋習(xí),各就所在各地做實(shí)地考察。這樣時日一久,自有相當(dāng)滿意的收獲。我希望‘地理之友’的同志,能負(fù)起這等使命!”
至1949年前,《地理之友》共出版兩期,第1 期文章有:許逸超“地理學(xué)的因素和原則”、洪紱“地理教育之目的”、葛綏成“記清代地圖學(xué)家鄒代鈞”、丁錫祉“地理基圖”、李震明“中國地形的區(qū)分”、楊景雄“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領(lǐng)土之變更”、馬湘泳“錢唐江下游地形實(shí)察與今后潮汐之影響”、李震明書評“南海諸島地理志略”、任德庚“新生的菲律賓共和國”、褚紹唐“修正高級中學(xué)課程標(biāo)準(zhǔn)草案意見書”、章生道“北行紀(jì)要”。第2 期文章有:劉恩蘭“我國疆土拓殖的地理背景”、王成祖“地理教材的適用”,劉德生“臺島地形隨筆”、盧材禾、秦華麟“臺北區(qū)域地理”、徐俊鳴“河南的地理形勢和軍略價值”、陳爾壽“當(dāng)前我國水利建設(shè)的三大要務(wù)”、章生道“佘山地形考察”、唐永鑾“東北地理景觀”、秦華麟“〔新書介紹〕諶譯中國區(qū)域地理”、陳大森譯“剛果河之游”。許逸超在“地理學(xué)的因素和原則一文中認(rèn)為研究地理的因素可分為兩組九個,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各占四個半因素。研究地理要根據(jù)因果原則、通論原則、分布原則。分布原則是地理學(xué)特有的原則。“地面上任何現(xiàn)象涉及到分布,就含有地理的意義。火山的原因和現(xiàn)象,個別敘述,地質(zhì)的意味很濃,但尋求火山的分布,并問為什么地球上的火山帶要環(huán)繞著太平洋沿岸,這就是地理了。”很好地表述了地理學(xué)的特質(zhì)。但文中也存在著當(dāng)時地理學(xué)者將自然現(xiàn)象同人文現(xiàn)象簡單類比的問題,“至于我們中國,有人說是老而不死的一個國家;早晚能否大地回春很難推料。我們知道,這種由幼而壯而老而返老還童的輪回哲學(xué),本是地形學(xué)的基本原則,今日人文地理的許多現(xiàn)象,也都可以引用了。”洪紱在“地理教育的目的”一文中提倡了地理的愛國主義教育功能,“地理學(xué)為中學(xué)初級教育重要之一門,應(yīng)使學(xué)生認(rèn)識中國大好河山,無盡之富源,與我刻苦耐勞之人民,從而引起愛國愛鄉(xiāng)之念。學(xué)地理始知中國之偉大,其在世界之使命,并藉以明晰中國文化之地理基礎(chǔ),以冀從因襲的,傳統(tǒng)的文化根基上,創(chuàng)造一個有意識的,合理化的新文化。在物質(zhì)方面,由目前在崩潰中的傳統(tǒng)的經(jīng)濟(jì)重建科學(xué)的技術(shù)的經(jīng)濟(jì),……。”李震明在“中國地形的區(qū)分”一文中闡述了中國地形的要點(diǎn)、分布、界線、幾種特殊的地形(黃土、赭色砂巖、石灰?guī)r地形、沙漠)和五大地形區(qū)(青藏高原、蒙新沙漠草原地域、北部地域、中部南部地域、東北地域)。王成祖在“地理教材的適用”一文中講述了區(qū)域的順序、位置的意義、地形氣候的比較、分布范圍的確定、統(tǒng)計數(shù)字的應(yīng)用、時事發(fā)展的詮釋、風(fēng)土人情的影證、風(fēng)景區(qū)的描摹、圖解的補(bǔ)充、中外地理的差別十個地理教材適用的問題。陳爾壽在“當(dāng)前我國水利建設(shè)的三大要務(wù)”一文中論述了當(dāng)時我國黃泛區(qū)的復(fù)興問題,YVA (長江上游水利計劃)的夢想和南北兩大港口(北方塘沽港的繼續(xù)修筑和南方黃浦港的正式開辟)三大水利建設(shè)要務(wù)。在黃泛區(qū)的復(fù)興問題中提出“不僅是希望這個區(qū)域能夠恢復(fù)昔日的舊觀,并且可以將‘工業(yè)農(nóng)’的理想在這里作為試驗,……”。它們反映了當(dāng)時上海地理學(xué)和地理教育研究的水平。上海解放后,中華地理教育研究會繼編了一期《新地理之友》。1951年,上海地理學(xué)會成立,中華地理教育研究會逐并入其中,刊物停辦。
三、地理教育事業(yè)與地理學(xué)著作和地圖的出版
上海的地理教育在中國也是較早開始的。1870年,上海同文館開設(shè)了地理課〔8〕;1876年創(chuàng)辦的格致書院也開設(shè)有地理課〔8〕。1897年創(chuàng)辦的南洋公學(xué)也開設(shè)了地理課〔8〕,1899年至1903 年中國近代地學(xué)大師張相文在此教授國文與地理〔9〕。
1929年,大夏大學(xué)高等師范專科開設(shè)了史地組,后在文學(xué)院下設(shè)史地系。開設(shè)有人生地理、中國地理、外國地理、地理繪圖、地理教學(xué)法、自然地理等課程。主要任課教師有:葛綏成、李長傅、鄔翰芳、孟壽椿、王成祖等〔10〕。1931年,暨南大學(xué)史地系成立,先后開設(shè)了中國地理、歷史地理、地理學(xué)史、氣象學(xué)、地形學(xué)、經(jīng)濟(jì)地理、人文地理、世界地理、政治地理、地圖學(xué)等課程。楚圖南、王庸、王勤@②、王成祖、姚明輝、許逸超、盛敘功、洪紱、王文元、褚紹唐、葛綏成等先后在此開課〔11〕。復(fù)旦大學(xué)在抗戰(zhàn)期間成立了史地系,其設(shè)立的目的是:“養(yǎng)成能獨(dú)立研究史地之人材”;“培養(yǎng)中等學(xué)院史地課之良好師資”;“灌輸全校學(xué)生以史地知識”〔12〕。開的地理課程有:中國地理、氣候?qū)W、地圖學(xué)、經(jīng)濟(jì)地理、地學(xué)概論、人文地理、亞洲地理、美洲地理、歐洲地理、政治地理。任美鍔、葉粟如、顧頡剛等曾在此任教。〔13〕
這一時期,上海憑借其雄厚的研究、出版力量,出版了許多地理學(xué)著述,它們中較有影響的有:葛綏成編著《世界文化地理》、《地理數(shù)學(xué)法》、《中國近代邊疆沿革考》、《地形學(xué)》等書;李長傅的《人文地理學(xué)》、《地理政治學(xué)》、《轉(zhuǎn)形期的地理學(xué)》、《南洋地理志略》等書;盛敘功的《農(nóng)業(yè)地理》、《交通地理》;丁紹恒的《近代本國地理沿革志》;張資平的《地圖繪法和繪制》;楚圖南的《地理學(xué)發(fā)達(dá)史》等書。地圖出版在國內(nèi)更是一枝獨(dú)秀,大量的地圖出版機(jī)構(gòu)(如世界輿地學(xué)社、東方輿地學(xué)社、大眾輿地學(xué)社、中華輿地學(xué)社等)出版了大量的地圖。其中《申報地圖》為我國的地圖出版做出了重要貢獻(xiàn)。《申報地圖》是上海《中華民國新地圖》和《中國分省新地圖》的習(xí)慣統(tǒng)稱,是上海《申報》為創(chuàng)刊六十周年而于1930年秋由丁文江、翁文灝、曾世英開始編繪的。它在地學(xué)上的貢獻(xiàn)主要是根據(jù)古今中外經(jīng)緯測量成果,運(yùn)用等高線,并采用分層設(shè)色法編繪,具有很強(qiáng)的科學(xué)性。它為我國地學(xué)所做的另一貢獻(xiàn)是為我國培植了地圖印刷力量。(原有人主張到日本小林又株式會社膠印廠印刷,印價較便宜,但丁文江等人最終確定在上海出版)。至1949年后,我國印刷質(zhì)量較高的地圖大都由當(dāng)時《申報地圖》培植起來的上海中華廠承印〔14〕。
解放前上海地學(xué)一百年的發(fā)展過程中,呈現(xiàn)出了從譯介到獨(dú)立研究不斷發(fā)展;研究力量從個體到形成組織;內(nèi)容逐漸與中國國情相結(jié)合;地理教育較發(fā)達(dá);地理出版興旺等特征。上海是我國近代地理學(xué)研究、教育和傳播的一個重要中心,為我國地理學(xué)的發(fā)展作出了重要的貢獻(xiàn)。
參考文獻(xiàn)
〔1〕王子賢:《簡明地質(zhì)學(xué)史》,河南科技出版社,1985年出版,第202至206頁。
〔 2〕林超:《中國現(xiàn)代地理學(xué)萌芽時期的張相文和中國地學(xué)會》, 會議資料,存河南大學(xué)地理系資料室。
〔3 〕張?zhí)祺耄骸稄埾辔膶χ袊乩韺W(xué)發(fā)展的貢獻(xiàn)——紀(jì)念“中國地學(xué)會”成立七十周年》,會議資料,存河南大學(xué)地理系資料室。作者為張相文堂兄弟。
〔4〕《地學(xué)雜志》創(chuàng)刊號:紹介圖書。
〔5〕上海市社會局第五科36組55號(上海檔案局全宗號6、目錄號5、案卷號1807,該資料現(xiàn)藏上海檔案館。)
〔6〕“中華地理教育研究會務(wù)概況”,《地理之友》1卷1期。
〔7〕“中華地理教育研究會緣起”,《地理之友》1卷1期。
〔8〕唐振唐:《上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91頁。
〔9 〕張?zhí)祺耄骸皬埾辔膶χ袊乩韺W(xué)發(fā)展的貢獻(xiàn)——紀(jì)念‘中國地學(xué)會’成立七十周年”。
〔10〕《大夏大學(xué)年鑒》民國十八年,藏華東師大檔案館。
〔11〕據(jù)華東師大地理系褚紹唐教授和西歐北美地理研究所錢今昔教授回憶。
篇11
福建省泉州市惠安高級中學(xué)
貴州省赤水市第二小學(xué)
吉林省梅河口市第三中學(xué)
二、先進(jìn)個人名單
一等獎
安徽 徐曉玲 福建 林秀欽 廣東 鄧紹宏 廣西 許媛 貴州 范本艷 河北 趙 欣 湖北 龔倫軍 云南 楊紅 浙江 范源清 顧俊芳
江蘇 周國偉 王建忠 孟 軍
二等獎
安徽 梁 好 福建 林 盛 廖友國 柯碧田 唐惠煌 莊春鳳 陳建杰
廣東 鄧 旭 廣西 許 媛 何 珍 馮 平 陳賀允
貴州 穆 菁 羅 艷 曾利和 河北 付會玉 趙 欣
河南 羅保愛 湖北 龔倫軍 方蓮英
湖南 王菊紅 吉林 蘇麗華 張 碩 李和義
江蘇 陳 楓 束麗文 謝鴻瑾 山東 黃艷艷 程顯龍 孫 娜
上海 劉金艷 四川 徐小瓊 梁 崗
天津 劉 越 浙江 吳樟英 王軍女
三等獎
福建 林 盛 肖婷婷 柯碧田 莊進(jìn)平 楊蒼洲 王建鵬 陳佳民 陳姍菁
康麗芳 許長安
甘肅 劉曉峰 王紅萍 周根旺 廣東 陳少貞 鄧紹宏
廣西 許 媛 陳賀允 馮 平 何 珍 貴州 王高良 陳 英 羅利瓊
河北 郭海紅 秦 梅 史建勛 河南 朱 麗 莊鳳平 羅保愛
黑龍江 張雪梅 李翠敏 李 萍 湖北 萬 晶 王鳳英 張建新
湖南 黃明勛 吉林 李偉芳 王文娟
江蘇 張 珊 遼寧 趙艷英
山東 陳立功 四川 梁 崗 徐小瓊
云南 余曉潔 楊曉玉 重慶 盧 璐 唐 英
浙江 范源清 聞洪波 方祝發(fā) 宋偉仙 許偉澤
北京地區(qū)獲獎名單
一等獎
白 敬 畢小芊 柴振榮 陳麗輝 程 芬 崔長友 崔 琳 鄧麗群 范寶東 范秀清 馮 帆 高奇越 高 穎 龔學(xué)志 郭俊彬 韓沁彤 韓向華 郝梅梅 郝向榮 何麗芳 胡文杰 胡玉強(qiáng) 黃小梅 賈慧蓉 賈 婷 姜 畔 解 薇 康菁菁 亢學(xué)麗 李 超 李海燕 李海穎 李浩敬 李 婕 李 靜 李 磊 李 曉 李學(xué)會 李永輝 劉海娜 劉 靜 劉俊鳳 劉 凱 劉 麗 劉 沙 劉 舒 劉學(xué)惠 劉一成 樓 樺 馬文麗 潘雪飛 彭玉華 祁永博 秦山丹 任 薈 邵立平 沈景娟 宋 輝 宋子男 孫鐵民 孫 薇 孫雪梅 孫雪巍 孫 艷 孫治英 唐 燕 陶小蘇 田 虹 田 彤 佟會敏 王愛國 王長青 王東紅 王建富 王 晶 王 靜 王麗娜 王 楠 王榮海 王 瑞 王世華 王香玲 王曉菁 王曉菁 王曉靜 王曉瓊 王秀琴 王 艷 魏賀淼 魏 然 吳恭平 武 月 席蓉蓉 晏 潔 楊 洋 易 靜 尹紅芳 于淑敏 苑 靜 張貝迪 張慧萍 張景芳 張留英 張偉華 張曉軍 張彥華 張依雯 張玉梅 趙立伶 趙明勇 趙榮旺 趙鑫馨 趙 燕 朱 彤 莊春妹
二等獎
艾天燕 愛 丹 安晶卉 安欣穎 安雪飛 白鳳穩(wěn) 白秀梅 白雪梅 鮑 瑋 薄淑紅 蔡明艷 曹冬生 陳彩霞 陳海芳 陳金成 陳 瑾 陳立娟 陳麗輝 陳麗娟 陳 雪 陳玉梅 程 旭 仇鳳霞 崔婷婷 代 瑩 鄧 晶 鄧科軍 狄永杰 丁 燕 董金鳳 董淑萍 竇長穎 杜艷艷 段海娟 方春梅 馮 琦 付海紅 高貴平 高海伶 高 靜 高 梅 郭春梅 郭海波 郭紅兵 郭新剛 郭迎濱 郭 穎 韓春霞 韓 鵬 韓曉慧 郝婉華 何 淼 何 偉 胡秀杰 胡 燕 黃 杰 黃小梅 黃秀英 黃 英 霍永躍 紀(jì)愛朋 賈娜娣 金 迎 康夢蘭 賴妙瓊 郎海英 雷米新 雷米新 李寶蘭 李赤瑜 李東穎 李 端 李方亮 李國青 李海波 李海霞 李 浩 李浩敬 李宏爽 李建敏 李金梅 李金榮 李 靜 李 黎 李 同 李雪玲 李雪梅 李雅娟 李 巖 李艷輝 李艷軍 李燕云 李一佳 李 影 李永蓮 李子路 厲江南 梁 好 梁秀敏 林翔宇 藺玉松 劉東芬 劉鳳艷 劉 福 劉洪發(fā) 劉鴻雁 劉 輝 劉建萍 劉進(jìn)波 劉 軍 劉麗娜 劉 敏 劉 銘 劉守宏 劉 碩 劉艷萍 劉 穎 劉元元 劉 震 路鳳敏 路 寧 呂 媛 馬 芳 馬加良子 馬立紅 馬 薔 馬穩(wěn)盼 馬穩(wěn)盼 門衛(wèi)華 孟祥陽 孟雪蓮 孟 灼 閔 敏 那 敏 牛衛(wèi)忠 牛彥芳 牛 彥 龐 暉 祁金花 祁有娟 錢磊俊 邱立君 榮 旭 茹建偉 芮愛忠 沙 莎 邵立平 申秀紅 沈嘉煜 沈金瑞 沈景娟 石京麗 史天慧 舒 芳 宋麗榮 宋應(yīng)富 宋正紅 蘇 晶 蘇 珂 蘇 娜 孫 浩 孫紅梅 孫樂芩 孫佩琴 孫 萍 孫婷婷 孫治英 孫 忠 譚 強(qiáng) 湯 平 唐鳳萍 田光華 田亞軍 脫國梅 萬 靜 王 哲 王彩蓮 王長青 王 超 王 琛 王翠菊 王桂鳳 王 涵 王好生 王會紅 王建華 王 建 王 靜 王 娟 王 蕾 王 麗 王麗娜 王連長 王琳娜 王 楠 王 琪 王 茜 王 清 王群英 王世強(qiáng) 王栓保 王 維 王香玲 王小平 王曉燕 王 新 王雪麗 王亞玫 王彥軍 王 英 王園園 王月青 王躍梅 王 蘊(yùn) 魏秀娟 文春宇 吳 然 吳 雙 吳 思 吳雅麗 夏換龍 肖光耀 熊麗平 徐 靜 徐 平 徐學(xué)宏 徐峪森 徐志欽 薛長浩 閆立娟 閆艷華 晏玉香 楊 斌 楊海濤 楊 潔 楊 靜 楊麗蘋 楊 敏 楊 銘 楊松珍 楊小麗 楊秀艷 楊云華 姚靜薇 殷 毅 尤 飛 尤曉宏 于大哲 于 瀾 于麗萍 于姍姍 苑 靜 臧超英 曾 莉 張愛軍 張春梅 張改蓮 張海燕 張 健 張 杰 張金朋 張 昆 張莉萍 張 利 張 慶 張 蓉 張如燕 張升軍 張素艷 張 威 張文娜 張小剛 張曉紅 張亞坤 張 艷 張艷霞 張 燕 張倚天 張 穎 張 蕓 趙海娜 趙繼蓮 趙麗華 趙 瓊 趙 蕊 趙婉麗 趙萬超 趙雪嬌 趙 艷 趙艷梅 趙燕武 趙玉娟 趙云紅 鄭紅麗 鄭云杰 周 蕾 周蘇平 周衛(wèi)東 周宗文 朱 紅 朱建玲 朱 莉 朱 迎
三等獎:(略)
關(guān)于獲獎名單的說明:
1.獲獎名單中省份、人名均按拼音順序排列。
篇12
一、商鞅的“重農(nóng)”政策及成效
公元前359年,秦孝公任命商鞅為左庶長,開始推行“重農(nóng)”政策。商鞅的“重農(nóng)”政策大體有三個方面;一個是對農(nóng)民的限制;第二個是對商人的限制;第三個是國家對糧食、鐵器等重要戰(zhàn)略物資進(jìn)行壟斷經(jīng)營。對農(nóng)民的限制表現(xiàn)在嚴(yán)禁農(nóng)民棄農(nóng)經(jīng)商還要對因懶惰務(wù)農(nóng)導(dǎo)致的貧窮者,施予嚴(yán)懲。對商人的限制表現(xiàn)在,嚴(yán)禁商人從事影響國家戰(zhàn)略物資的買賣,如糧食,鐵器等等。商鞅曾下令“使商無得糴,農(nóng)無得糶”,還對商業(yè)活動征收重稅,據(jù)史料記載說“貴酒肉之價,重其租,令十倍其樸”。此外“令商賈、技巧之人無繁”,即嚴(yán)格限制行商之人的數(shù)量和規(guī)模;國家參與對與國計民生相關(guān)的物資都嚴(yán)加控制,禁止私商經(jīng)營。
此法對秦國產(chǎn)生了重要影響。對農(nóng)民的限制,不但使秦國原有的農(nóng)民被束縛在土地上,而且還用法律對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進(jìn)行嚴(yán)格要求,對棄農(nóng)經(jīng)商或因懶惰而使自己變窮者,一律變?yōu)榕`。這種規(guī)定使農(nóng)民專心于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這樣即會增加農(nóng)民的數(shù)量也增加了國家的糧食儲備,有利于秦國的爭霸戰(zhàn)爭的需要。商鞅曾認(rèn)為“國之所以興者,農(nóng)戰(zhàn)也。”。商鞅來自衛(wèi)國,而當(dāng)時衛(wèi)國的工商業(yè)十分發(fā)達(dá),所以在衛(wèi)國的所見所聞使他十分明白人民從事商業(yè)的流動性,不利于國家的鞏固和爭霸戰(zhàn)爭地進(jìn)行。尤其是在當(dāng)時生產(chǎn)力水平很低的情況下,各國之間的爭霸戰(zhàn)爭打的是“兵源”和“糧草”。誰擁有雄厚的兵源和充足的糧草,誰就能傲視群雄,君臨天下。商鞅深知其中的道理,所以他告訴秦國的百姓說“……國待農(nóng)戰(zhàn)而興,主待農(nóng)戰(zhàn)而尊”,生活中只有兩件事,耕田和打仗,只有強(qiáng)大的農(nóng)業(yè)才能支持不斷擴(kuò)大的戰(zhàn)爭。從某種意義上講,耕戰(zhàn)策略最終成就了秦國統(tǒng)一天下的宏愿。“重農(nóng)”政策的實(shí)施的確讓秦國受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行之十年,秦民大悅,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于公戰(zhàn),怯于私斗,鄉(xiāng)邑大治”。糧食充裕,人口猛增,綜合國力迅速提升,使秦國在短時間內(nèi)就發(fā)展成為七國中實(shí)力最強(qiáng)的一個,從此秦國發(fā)動了一系列吞并戰(zhàn)爭,僅僅用了大至十年時間,就滅掉了韓、趙、魏、楚、燕、齊,統(tǒng)一天下,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統(tǒng)一的多民族國家,“重農(nóng)”政策在秦國統(tǒng)一的過程中起了重要作用。這一政策之所以在秦國得以成功推行,與秦國在政治上秦孝公的大力支持、經(jīng)濟(jì)上發(fā)達(dá)的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jì)、文化上悠久的農(nóng)業(yè)文明等多方面因素是分不開的,但重要的是秦國優(yōu)越的地理環(huán)境,為“重農(nóng)”政策的實(shí)施提供了良好的客觀條件,這才是秦國選擇和推行“重農(nóng)”政策的重要因素。
二、秦國重農(nóng)政策的地理因素分析
“重農(nóng)”政策最早并不是產(chǎn)生在秦國,但是卻在秦國重大的成功,這主要得益于當(dāng)時秦國優(yōu)越的地理環(huán)境,這為“重農(nóng)”政策的實(shí)施提供了良好的客觀條件,這決定了秦國要選擇“重農(nóng)”政策而不是“重商”政策,因為要推行這一政策必須有地可分,有資源可用。下面筆者就從秦國優(yōu)越的自然地理條件和該地域深厚的農(nóng)業(yè)文化積淀這兩個方面來分析秦國選擇“重農(nóng)”政策的原因。
(一)優(yōu)越的自然地理條件:
秦國是七國中唯一在地形上處在第二階梯的國家(大興安嶺、太行山脈、巫山、雪峰山是地勢二、三級階梯的分界線),其它六國均處在第三階梯。秦國境內(nèi)擁有有當(dāng)時重要的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jì)區(qū),如黃土高原、關(guān)中平原等適于耕種的地理單元,特別是關(guān)中地區(qū)平原廣闊,土壤肥沃,據(jù)史料記載“關(guān)中自汧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貢,以為上田”,渭 河水長期沖擊泛濫,逐漸形成了肥沃的平原,號稱“八百里秦川”。為了更好的實(shí)行“重農(nóng)”政策,秦惠文王時發(fā)動了對巴蜀的千里用兵,其目的就是要奪取那里的產(chǎn)糧區(qū),把那里變成秦國的天然糧倉和進(jìn)攻勁敵楚國的跳板。另外秦境內(nèi)也有面積廣大的丘陵和山地,例如“秦巴山地氣候溫暖濕潤,地勢高峻,垂直地帶性顯著也是我國東部山地垂直地帶譜系最完好的山地”。從整體地形上講,無論是中原的韓、趙、魏、東方的齊國、南邊的楚國還是北面的燕國,即使六國中有的擁有這些的地理類型,也遠(yuǎn)不及秦國的豐厚。在這樣的地形條件下,農(nóng)牧皆宜。司馬遷曾分析春秋四霸興起的原因說:“晉阻三河,齊負(fù)東海,楚介江淮,秦因擁雍州之地,四海迭興更為”。由此可見三晉之地受三條大河所阻,發(fā)展空間狹小,齊國三面環(huán)海,楚國地域廣闊但氣候濕熱,湖泊縱橫,再加上燕國位置靠北,氣溫低下,多山和沙漠,都不利于農(nóng)業(yè)的發(fā)展,所以六國在地理方面與秦國相比,在發(fā)展農(nóng)業(yè)上都沒有優(yōu)勢。因此,秦國的地形優(yōu)勢在一定程度上促進(jìn)了秦國“重農(nóng)”政策的選擇。
另外從氣候上講,戰(zhàn)國七雄大致處在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以北的地區(qū)。當(dāng)時在這個范圍的南北兩面氣候不適于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南面高溫濕熱、北面寒冷,以當(dāng)時的生產(chǎn)力水平來說還難以開發(fā),秦時的關(guān)中地區(qū)可謂是天時地利。秦時的關(guān)中地區(qū)氣候溫暖濕潤,據(jù)研究,“當(dāng)時的氣溫要比今天溫暖”。從“公元前770年到西漢,是中國歷史上第二個溫暖期,關(guān)中地區(qū)的平均溫度比現(xiàn)在還要高出1-2攝氏度,降水量也比現(xiàn)在大”。據(jù)史料上記載:“……渭川千畒竹”。這可以說明喜高溫、濕熱的竹子曾經(jīng)能在關(guān)中平原生長,也可以側(cè)面反映出這一地區(qū)當(dāng)時的氣候溫暖濕潤,非常適合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水資源是發(fā)展農(nóng)業(yè)的必要條件之一,黃土高原和四川盆地是當(dāng)時水資源十分充足的地區(qū),在渭河、涇水的南北兩岸集中了大小數(shù)十條河流,有雍水、褒水、洛水、沛水、石川水、灞水、零水、戲水、馬連河、黑河等,水資源十分豐富,四川盆地更是河流縱橫、水網(wǎng)發(fā)達(dá),很大程度上減少了農(nóng)民對自然降雨的依賴,既提高了抵御自然災(zāi)害的能力,也有便利的灌溉。還有秦國對國內(nèi)的水力資源進(jìn)行科學(xué)合理的開發(fā),鄭國渠能灌溉農(nóng)田4萬余傾,都江堰使蜀地沃野千里,水旱無災(zāi),對秦國農(nóng)業(yè)的發(fā)展有很大的貢獻(xiàn)。
此外,秦國有面積廣大的丘陵和山地,森林、植被非常茂盛,“有戶、杜竹林,南山檀柘,號稱陸海”。除了渭河南面的秦嶺和北面的山地有茂密的樹木,即使是在關(guān)中平原上也有眾多的森林。物種繁雜眾多,有數(shù)不盡的林木、草場資源,這就為秦國的畜牧業(yè)發(fā)展提供了便利的條件,使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和軍事上得到充足的耕牛和戰(zhàn)馬,而當(dāng)時恰好是鐵器和耕牛的普遍應(yīng)用被認(rèn)為是生產(chǎn)力進(jìn)步的標(biāo)志。秦國境內(nèi)還有豐富的礦藏資源,如玉石、銅、鐵、美玉等等。有“天府之國”之稱的四川盆地不但有肥沃的土地,礦產(chǎn)也十分豐富,據(jù)史料記載“地饒卮、姜、丹砂、銅、鐵、竹、木之器”。
秦國處在偏邦一隅的隴西一帶,地理位置相對偏僻。由于地處偏遠(yuǎn),與中原各國交往相對較少,遠(yuǎn)離先進(jìn)的中原文化,“秦國的經(jīng)濟(jì)以農(nóng)為主以牧為輔”,而商品經(jīng)濟(jì)并不發(fā)達(dá),與其它六國相比秦國的生產(chǎn)、生活都相對落后,但是這對于“重農(nóng)”政策的實(shí)施來說是個有利的條件,因商品經(jīng)濟(jì)的落后就意味著商人階層的力量不大,同時對秦國的政治、經(jīng)濟(jì)的影響力也微乎其微,所以在推行“重農(nóng)”政策的過程中的阻力就小。
秦國最初興起于陜西,后通過征戰(zhàn)逐漸興起于關(guān)中地區(qū),北部是黃土高原,東面是函谷關(guān),南面是四川盆地和成都平原,四面都是高原高山,基本處于我國的第二階梯,形成了一個獨(dú)立的實(shí)體這能使秦攻守自如,占盡了地利的優(yōu)勢。如果國內(nèi)的商人集團(tuán)勾引外來勢力,或者消極抵抗,那么秦國可以關(guān)閉函谷關(guān),在秦孝公的大力支持下,將反對勢力一舉殲滅。如果有外來勢力干涉變法,秦國只需要派兵把住函谷關(guān)口,外來勢力就很難插手。司馬遷也曾說過:秦孝公據(jù)“關(guān)中之固,金城千里,君臣同守而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nèi)、囊據(jù)四海、并吞八荒之心”。有如此優(yōu)勢的戰(zhàn)略地形,六國別說干涉秦的改革,就是自保都是一種奢求。現(xiàn)代地理軍事專家宋杰指出:“秦……有黃河以拒晉,有秦嶺、商洛以隔楚。……地理形勢利于守險,退可以保國土不失,進(jìn)則能蠶食諸侯,假以時日,遂愈戰(zhàn)愈強(qiáng),得以傲視諸侯”。縱觀整個戰(zhàn)國時期的戰(zhàn)爭史,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秦與六國的征戰(zhàn)中,東方六國極少能攻入秦國國境之內(nèi)。數(shù)次合縱的聯(lián)軍,除最后一次之外,其余都是僅僅到達(dá)函谷關(guān)便叩關(guān)而還。而秦國則是充分利用自己的地型上的優(yōu)勢,攻城掠地,頻頻發(fā)動對六國的進(jìn)攻,直到最終掃平六國統(tǒng)一天下。
秦國偏處一隅地理位置,使秦國的商品經(jīng)濟(jì)發(fā)展相對落后,商人階層的力量有限,還無力阻撓這一政策的推行。自成一體的獨(dú)特地理結(jié)構(gòu),它可以為秦國的國防安全提供保障,使其“重農(nóng)”政策的實(shí)行有了安定的環(huán)境,避免國內(nèi)或國外反對勢力的干涉,因此秦國得天獨(dú)厚的地理位置使“重農(nóng)”政策在安全上有了保證。秦國擁有優(yōu)越的自然地理條件,國土面積廣大,土地肥沃,還有物產(chǎn)豐富的山地、水草風(fēng)美的草原,農(nóng)牧都可以發(fā)展。氣候溫暖濕潤,降雨充足,植被物種齊全,礦藏資源眾多。有這樣優(yōu)越的自然環(huán)境與豐富的自然資源,綜上所述,可以看出秦國選擇“重農(nóng)”政策從自然條件上將有很很大的優(yōu)勢。
(二)深厚的農(nóng)業(yè)文化積淀
秦人從很早的時候就已經(jīng)在我國西部定居。在商代末期,他們就已經(jīng)在西部逐漸發(fā)展壯大,據(jù)史料記載秦“在西戎,保西垂”。秦當(dāng)時是處在偏邦一隅的隴西一帶的西部小國,建都西犬丘(今甘肅天水市西南),后來隨著實(shí)力增強(qiáng)逐漸向東發(fā)展,直到西周末年在周平王東遷洛邑中秦襄公護(hù)送有功,被封為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后來經(jīng)秦襄公、秦穆公、孝公和惠文王等歷代國君的征戰(zhàn)和擴(kuò)張,到秦始皇即位時,秦國大致的版圖是“北抵秦昭襄王所修建的長城(由今甘肅臨洮經(jīng)陜北吳旗、靖邊、神木等縣),南到巴、蜀與楚相接,東過嘉峪關(guān)與三晉為鄰,西及北西戎、胡林、樓煩諸部交界”,大概就是今天的陜西全部,甘肅東部,四川大部,河南的中西部,還有山西和湖南、湖北的部分地區(qū),也就是占有黃土高原與四川盆地兩個地理單元之大部及其東緣部分區(qū)域。應(yīng)該說,這一國土范圍,地域廣闊,地勢險固,而且地理環(huán)境優(yōu)越,自然資源豐富,宜農(nóng)宜林宜牧,對秦國“重農(nóng)”政策提供了良好的物質(zhì)基礎(chǔ)。
秦國立國的時間相對比較晚,而且國內(nèi)氏族雜居十分雜亂,西方的戎族“自隴以西有綿諸、犬戎、翟、獂之戎、岐、梁山、涇,漆之北有義渠、大荔、吳氏、衍之戎”。秦國的先王為了擺脫戎族的威脅,擴(kuò)大疆域不斷向西、向北發(fā)動擴(kuò)張戰(zhàn)爭。歷經(jīng)幾世征戰(zhàn),“公元前5世紀(jì)中葉到公元前4世紀(jì)中葉綿諸、犬戎、翟、獂先后為秦所滅,其他戎族方國大都?xì)w附于秦”。據(jù)史料記載:“西戎八國服于秦”。兩個民族也在戰(zhàn)爭的過程中逐漸融合,相互影響,所以到戰(zhàn)國初期,秦國仍是“戎翟之教,父子無別,同室而居”。在生活習(xí)慣上,更是與中原各國存在著較大的差異,由于受戎文化的影響,還保持著與六國不同的少數(shù)民族風(fēng)俗的獨(dú)立的社會結(jié)構(gòu),這樣使秦國內(nèi)的氏族組織結(jié)構(gòu)沒有受到較大的沖擊和影響,經(jīng)商逐利的觀念還沒有形成風(fēng)氣,仍以農(nóng)耕思想為主。后來,商鞅根據(jù)秦國地廣人稀的國情,提出了“徠民”政策。這既可以增加農(nóng)業(yè)勞動人口也可以加速秦國土地的開發(fā)利用,商鞅曾對秦孝公說:“秦之所與鄰者,三晉也。所欲用兵者,韓、魏也。彼土狹而民眾,其宅參居面并處,其寡萌賈息,民上無通名,下無田宅,此其土不足以生其民也”,他建議秦孝公利用秦國廣袤的土地和優(yōu)厚的政策來吸引三晉之民,于是秦孝公即以賜其田宅三世不變和復(fù)及子孫的優(yōu)厚政策引來三晉之民,一方面使秦國大量的荒蕪?fù)恋氐靡蚤_辟為良田,提高了糧食產(chǎn)量。另一方面也使秦人有足夠的兵源,來應(yīng)付外敵,收到強(qiáng)兵富國之效用。實(shí)行了吸引三晉之民的“徠民政策”,吸引大批有生產(chǎn)經(jīng)驗的勞動力,在一定程度上促進(jìn)了秦國土地的開發(fā)和農(nóng)業(yè)的發(fā)展。
其實(shí)早在80萬年至75萬年前人類就開始在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藍(lán)田人、大荔人距今已有幾十萬年的歷史,母系氏族的半坡人、姜寨人在這里以堅硬的石器作為生產(chǎn)工具,創(chuàng)造了輝煌的原始農(nóng)業(yè)文化,是我國最早的農(nóng)業(yè)發(fā)源地之一。到新石器時代,這里的農(nóng)業(yè)就已經(jīng)很發(fā)達(dá) 了。1963年在位于中國西北部陜西省的藍(lán)田縣發(fā)現(xiàn)了藍(lán)田人遺址,出土的以三棱大尖狀器為特色的石器,被認(rèn)為是藍(lán)田人文化的特征之一,此外還發(fā)現(xiàn)了用火的遺跡。由此可見,在這片土地上,早在舊石器時代就開始了原始的農(nóng)業(yè)文明。到了周朝時期,進(jìn)一步發(fā)揚(yáng)重視農(nóng)業(yè)的傳統(tǒng),并吸收了商朝發(fā)展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的經(jīng)驗,使農(nóng)業(yè)發(fā)展很快,成就也頗大,尤其是創(chuàng)造了“輪荒制”和“休閑制”。是我國農(nóng)業(yè)發(fā)展的重要里程碑,奠定了傳統(tǒng)農(nóng)業(yè)的基礎(chǔ)。隨著生產(chǎn)力的進(jìn)步,農(nóng)業(yè)的不斷發(fā)展,此時全國形成了幾大區(qū)域經(jīng)濟(jì)區(qū)。秦國版圖包括有大部分的“中部農(nóng)業(yè)區(qū)”是指夏、商、周時期的文明中心區(qū)域,大體上“東及東夷分布區(qū),西達(dá)秦隴,南抵漢水、淮水流域,北到晉北、陜北高原腳下”。該區(qū)的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發(fā)展較快,最先步入文明社會。后來被秦國征服的巴蜀地區(qū)也是重要的農(nóng)業(yè)區(qū),很早就有“天府之國”的美稱。三星堆文化遺址存分布區(qū)出土石質(zhì)等生產(chǎn)工具有斧、錛、鑿、鋤、鏟和少量銅農(nóng)具。結(jié)合出土的大量陶制酒器和食器來看,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以達(dá)到了相當(dāng)高的水平。說明以三星堆為代表的古蜀文明是一種農(nóng)業(yè)文明。
秦國當(dāng)時的疆域擁有渭河流域、關(guān)中平原和四川盆地,沃野千里,但是人口稀少。司馬遷曾指出:“故關(guān)中之地,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眾不過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其意思是,關(guān)中的耕地占到當(dāng)時全國總耕地面積的三分之一,人口占到全國總?cè)丝诘氖种?而其財富卻占全國總財富的十分之六。商鞅認(rèn)為秦國的土地人口比例關(guān)系是“今秦之地方千里者五,而谷土不能處二,田數(shù)不滿百萬,其藪澤、溪谷、名山、大川之才物寶,又不盡為用此人不稱土地也”。所以“重農(nóng)抑商”政策在這樣的國情下推行就顯得十分容易,農(nóng)民可以分到大量土地,既提高了勞動積極性,同時也提高了土地利用率和單位產(chǎn)量。而與之相比地處中原的韓、趙、魏的土地情況卻正好與之相反,這三國都是山地多,平地少,人口稠密,其民無地可耕。商鞅針對三晉的土地情況這樣說過:“彼土狹而民眾,其宅參居而并處,其寡蔭賈息民,民上無通名,下無田宅,而恃奸務(wù)末作以處,人之復(fù)陰陽澤水者過其半,此其土不足以生其民”。如果在這樣的地理條件下選擇“重農(nóng)”政策,必將會民不聊生,造成內(nèi)亂不止,局勢不穩(wěn),影響國家的安定發(fā)展,所以它允許國內(nèi)民眾以行商謀出路,以解決因土地不足造成的困境。因此從它的國情來看,這樣的國家不具備選擇“重農(nóng)”政策的自然條件。另一方面,秦國統(tǒng)治者重視農(nóng)業(yè)的發(fā)展,采取了一系列的重農(nóng)政策和豐富的農(nóng)耕經(jīng)驗來保護(hù)和促進(jìn)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的發(fā)展還立法保護(hù)農(nóng)業(yè),考古學(xué)家再進(jìn)湖北夢縣的睡虎地秦墓中發(fā)現(xiàn)了一名叫喜的人所抄的1100多枚竹簡,為我們了解秦國的農(nóng)業(yè)提供了線索,原文如下,“種:稻、麻畝用二斗大半斗,禾、麥一斗,黍、荅畝大半斗,叔(菽)畝半。利田疇,其有不盡此數(shù)者,可(也)其有本者,稱議種之”。這些法律條文清清楚楚的顯示了2000多年前,秦國是如何保護(hù)農(nóng)業(yè)耕種的。其意思是播種時水稻種子每畝用二又三分之二斗,谷子和小麥用一斗,小豆用三分之二斗,大豆半斗,如土地肥沃,每畝播撒的種子可以適當(dāng)減少。此外秦國還有對耕牛保護(hù)的法律,從這里可以看到秦國的所有的農(nóng)戶播種莊稼的方法都是用國家用法律來保障,由此可見秦國對土地的管理竟然具體到如此地步。秦國有悠久的農(nóng)業(yè)傳統(tǒng)、良好農(nóng)業(yè)基礎(chǔ)加上有法律上的保障,對推行“重農(nóng)”來說有了客觀上和法律上的保障。
牧業(yè)是農(nóng)業(yè)的重要支撐,特別是在戰(zhàn)國時期耕牛的使用,被看作是生產(chǎn)力進(jìn)步的標(biāo)志,而秦國在畜牧業(yè)的發(fā)展上更是讓其它六國難以比及,秦的先人主要活動在渭水河上游一帶以游牧為主。“非子居犬丘,好馬及畜,善養(yǎng)息之”。由此可見秦人的祖先早就開始養(yǎng)牧的歷史,加上秦國境內(nèi)有面積廣大的山地丘陵,這里氣候暖溫,雨水充沛,水草豐美。適合于畜牧業(yè)的發(fā)展,到了西周時期已經(jīng)形成了以畜牧為主的西部經(jīng)濟(jì)區(qū),畜牧業(yè)的發(fā)展,為秦國的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提供了充足的蓄力,有利于秦國農(nóng)業(yè)的發(fā)展。
秦國的疆域廣闊擁有黃土高原、四川盆地、關(guān)中平原等重要的農(nóng)業(yè)區(qū)。境內(nèi)的民族主要是秦人和被征服戎族,他們相互雜居、融合,使傳統(tǒng)的農(nóng)業(yè)文化保存較好,商品經(jīng)濟(jì)思想對秦國的“重農(nóng)”思想沖擊不大,后來從三晉吸引的“徠民”,給秦國的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帶來充足的勞動力,秦國的農(nóng)業(yè)歷史悠久,開發(fā)較早,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jì)十分發(fā)達(dá),畜牧業(yè)的發(fā)達(dá),這些為“重農(nóng)”政策的選擇和推行奠定了基礎(chǔ)。
三、地理因素與政策的選擇兩者之間的關(guān)系
影響一個國家制定政策的影響因素有很多,但是地理環(huán)境因素應(yīng)該排在前列。一個國家,無論是大國還是小國,是強(qiáng)國還是富國,也無論采用何種政治制度,它的地理環(huán)境因素,首先影響了它的基本政策的制定。政治學(xué)中有一句話說得好,“你坐在那兒,決定你站在那兒”,一國政策的選擇也不例外。你擁有什么樣的地理環(huán)境因素,也同樣決定一個國家將選擇和制定什么樣的政策。“疆域、氣候、地理位置以及人文特征,這些自然環(huán)境因素對政策的制定和選擇所發(fā)揮的作用,以及由此而產(chǎn)生的關(guān)系模式構(gòu)和關(guān)鍵性成分,地緣政治學(xué)用整體論的研究方法,其目的是把不同的現(xiàn)象結(jié)合起來,并把它看成一個整體而加以描述”。地理因素是制定適合國情政策的客觀依據(jù)而正確的政策又有助于地理因素的優(yōu)勢充分發(fā)揮。秦國有廣袤肥沃的土地、溫暖濕潤的氣候等優(yōu)越的自然環(huán)境因素,這些能為重農(nóng)政策推行,提供了良好成長環(huán)境和生存空間,從另一個方面講,秦國采用適合國情的重農(nóng)政策,充分發(fā)揮了秦國地理環(huán)境因素的優(yōu)勢,短短數(shù)十年時間,秦國的綜合國力簡直可以用,擊水三千,扶搖直上來形容。兵強(qiáng)馬壯,糧草充足并且秦王嬴政最終完成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大統(tǒng)一,創(chuàng)立了前無古人的千秋偉業(yè)。
結(jié)論
地理環(huán)境對政策的選擇和走向會有一定的影響作用,但不是決定作用,所以我們要避免陷入“地理環(huán)境決定論”的誤區(qū)。秦國選擇“重農(nóng)”政策有著它優(yōu)越的自然地理條件和深厚的農(nóng)業(yè)文化積淀,這些因素能為“重農(nóng)”政策的推行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發(fā)展空間。再加上秦國政治、經(jīng)濟(jì)、文化的發(fā)展和商鞅、秦孝公等的努力,共同促使了“重農(nóng)”政策在秦國推行并取得了成功,為秦國統(tǒng)一天下奠定了基礎(chǔ)。終于在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統(tǒng)一天下,結(jié)束了長期以來諸侯爭霸的局面,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統(tǒng)一的多民族國家。由此可見,地理環(huán)境對一個國家的政策的選擇和制定有一定的制約作用。
參考文獻(xiàn):
[1] 戚曉輝,地理標(biāo)志的特征及其完善途徑[J],齊齊哈爾大學(xué)學(xué)報(哲學(xué)社會科學(xué)版),2007(3):183-184
[2] 高敏.秦漢史探究[M].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9
[3] 張金光.秦制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12
[4] 黃仁宇.中國大歷史[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03.3
[5] 史念海.黃土高原歷史地理研究[M].鄭州,黃河水利出版社,2001.8
[6] 上海社會科學(xué)院經(jīng)濟(jì)研究所經(jīng)濟(jì)思想史研究室著.秦漢經(jīng)濟(jì)思想史[M].中華書局,1989.7
[7] 范文瀾.中國通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0
[8] 林劍鳴.秦史稿[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底
[9] 史念海.山河集[M].北京,三聯(lián)書店出版社,1963
[10] 史念海.黃土高原歷史地理研究[M].鄭州,黃河水利出版社,2001
[11] 祝中熹.早期秦史[M].蘭州,敦煌文藝出版社,2004.2
[12] 藍(lán)勇.中國歷史地理學(xué)[M].北京,高等 教育出版社,2002.8
[13] 郝懿行.山海經(jīng)箋蔬[M].成都,巴蜀書社,1958.6
[14] 廖幼華.歷史地理學(xué)的應(yīng)用[M].臺北,文津出版社,2004.8
[15] 胡渭.禹貢錐指[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7
[16] 何清谷.三輔黃圖校釋[M].北京,中華書局,2005.6
[17] 史念海.中國歷史地理論叢[M].陜西,陜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6
[18] 陜西師范大學(xué)西北歷史環(huán)境與經(jīng)濟(jì)社會發(fā)展研究中心編.歷史環(huán)境與文明演進(jìn)[C].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6
[19] 中國古都學(xué)會,新鄭古都學(xué)會編.中國古都研究[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4.8
[20] 上海社會科學(xué)學(xué)院經(jīng)濟(jì)研究所經(jīng)濟(jì)思想史研究室.秦漢經(jīng)濟(jì)思想史[M].北京,中華書局,1989.7
[21] 王勇.東周秦漢關(guān)中農(nóng)業(yè)變遷研究[M].湖南,岳麓出版社,2004
[22] 王子今.秦漢時期生態(tài)環(huán)境研究[M].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07
[23] 雷虹霽.秦漢歷史地理與文化分區(qū)研究[M].北京,中央民族大學(xué)出版社,2007
[24] 宋杰.先秦戰(zhàn)略地理研究[M].北京,首都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1999.7
[25] 李源澄.秦漢史[M].上海,商務(wù)印書館,1947
[26] 常璩,劉琳校注.華陽國志校注[M].四川:巴蜀書社,1984.7.
[27] 孫詒讓.十三經(jīng)注疏校記[M].山東:齊魯書社,1983.9
篇13
一、寬口徑、厚基礎(chǔ):模塊化的課程設(shè)置
我校歷史學(xué)門類由歷史教育、基地班、文化遺產(chǎn)與文化產(chǎn)業(yè)三個專業(yè)構(gòu)成,以歷史教育專業(yè)學(xué)生為主,全部為免費(fèi)師范生。三個專業(yè)的課程體系均由三大模塊構(gòu)成,即通識類、專業(yè)必修類、專業(yè)選修類。通識類課程除、英語、高等數(shù)學(xué)、計算機(jī)、數(shù)據(jù)庫等基礎(chǔ)課外,還規(guī)定學(xué)生必須自主選修理科類、藝術(shù)類課程,提高學(xué)生的科學(xué)素質(zhì)與藝術(shù)素質(zhì)。專業(yè)必修類包括歷史學(xué)專業(yè)基礎(chǔ)課和教師教育課程,前者主要有中國通史(古代史、近現(xiàn)代史、當(dāng)代史)、世界通史(古代中世紀(jì)史、近代史、現(xiàn)當(dāng)代史)、中國歷史文選、歷史科學(xué)概論等。教師教育課程除教育學(xué)、心理學(xué)、歷史學(xué)科教學(xué)論外,我們還特意設(shè)置了教師口語、教師書法、現(xiàn)代教育技術(shù)、歷史教學(xué)技能訓(xùn)練等課程,使學(xué)生掌握必備的技能與藝術(shù)。專業(yè)選修類則結(jié)合本院教師研究狀況,開設(shè)各種課程多達(dá)105門。這類課程旨在加深、拓寬學(xué)生已有歷史知識,注重學(xué)生研究能力的培養(yǎng)。在三大模塊中,歷史教育專業(yè)更加重視基礎(chǔ)課程,學(xué)分分布依次為47、67、34,共計148學(xué)分,學(xué)分分布比例分別為32.9%、44.7%和22.4%。基地班更加注重培養(yǎng)學(xué)生更為寬闊的視野和較強(qiáng)的研究能力,其中,通識課、選修課的學(xué)分達(dá)到47和48,在總學(xué)分中的比例分別為34.8%和35.6%。相比之下,專業(yè)基礎(chǔ)課的學(xué)分及比例分別為40和29.6%。
為強(qiáng)化基礎(chǔ)教學(xué),我們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是大力加強(qiáng)精品課程建設(shè)。近年來,我們圍繞歷史學(xué)人才培養(yǎng)模式改革,積極申報國家級精品課程,先后獲得“中國近代史”、“中國歷史文選”、“中國近代史綱要”、“中國古代史”等四門國家級精品課程,并由知名教授領(lǐng)銜組成強(qiáng)大的師資隊伍。如中國近代史教學(xué)團(tuán)隊由馬敏、朱英、劉偉、彭南生等教授加盟,中國歷史文選以周國林、劉韶軍、董恩林、張固也等教授為主體組織教學(xué)力量。中國古代史教研室通過長期不懈的努力,在教學(xué)團(tuán)隊、課程群、網(wǎng)絡(luò)教學(xué)資源、教學(xué)改革等方面取得了明顯進(jìn)步,終于在2010年獲國家級精品課程立項建設(shè)。截至目前,中國近代史國家級精品課程已通過專家驗收,并被評定為優(yōu)秀,其他精品課程建設(shè)扎實(shí)向前推進(jìn)。除此之外,我院還有世界近代史等省級精品課程。
二是開發(fā)具有本校特點(diǎn)的系列化教材,在課堂教學(xué)中深受學(xué)生歡迎。近幾年來,我們先后組織編寫了《中國文化概論》、《中國近現(xiàn)代史》、《中國當(dāng)代史》、《世界通史(古代中世紀(jì)卷)》、《世界通史(近代史)》、《世界通史(現(xiàn)代卷)》、《中國歷史地理學(xué)導(dǎo)論》、《文化學(xué)》等系列教材。這些教材不僅深受學(xué)生歡迎,而且產(chǎn)生了廣泛影響。有些教材被多所大學(xué)采用,如周國林主編的、由中華書局出版的《中國歷史文選》,在“選目的新穎性”、“解題的立意”、“編排格式的講究”、“適當(dāng)?shù)膱D文配合”以及“附錄的采用”等方面具有鮮明的特點(diǎn)。章開沅、朱英主編的《中國近現(xiàn)代史》2009年由河南大學(xué)出版社推出,該教材邀請了國內(nèi)武漢大學(xué)、中山大學(xué)、湖南師大、南開大學(xué)、中山大學(xué)、北京師大、鄭州大學(xué)等多位從事中國近代史教學(xué)與研究的學(xué)者參與編寫。不僅突破了傳統(tǒng)的中國近、現(xiàn)代史分界線,將1840-1949年間的歷史作為一個整體,而且多有創(chuàng)新,如“注意歷史新知識的增補(bǔ)、傳授,也注意新理論、新觀點(diǎn)、新方法的介紹,史實(shí)的敘述盡是精練,減少篇幅,學(xué)術(shù)研究的介紹則加大篇幅,不僅向?qū)W生講授什么是近代史,同時也引導(dǎo)學(xué)生學(xué)習(xí)怎樣認(rèn)識近代史。”同時,每章正文后“列本章小結(jié)、學(xué)術(shù)綜述、參考書目和思考題,目的是開闊學(xué)生視野,促使學(xué)生將課內(nèi)學(xué)習(xí)與課外學(xué)習(xí)有機(jī)結(jié)合,激發(fā)學(xué)生的思考與研究興趣。”該教材出版后,深受授課教師和學(xué)生的喜愛,“是反映史學(xué)發(fā)展趨勢和適合閱讀對象的成功之作”,已陸續(xù)被南開大學(xué)、中山大學(xué)等國內(nèi)著名高校歷史專業(yè)作為教材使用。
三是堅持教授授課制。我院現(xiàn)有教授38人,是教師隊伍的主體,他們教學(xué)經(jīng)驗豐富,學(xué)術(shù)造詣深厚,教學(xué)藝術(shù)高超,課堂深受學(xué)生的歡迎。但教授們課題多,科研壓力大,加之時下科研工作的量化考核機(jī)制,使得教授們給本科生上課的積極性不高。為了鼓勵教授上本科講臺,我們將教學(xué)與科研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在聘任制下,如果教授的本科生教學(xué)工作不達(dá)到一定的課時,將會影響其下一輪聘任,在年度考核中,如果教授沒有本科生教學(xué)課時工作量,則教學(xué)考核為不合格,進(jìn)而影響其績效工資。這樣的制度設(shè)計旨在確保每位教授每一學(xué)年至少為本科生開設(shè)一門課程。
二、師為導(dǎo)、生為主:研討式的課堂教學(xué)
傳統(tǒng)教學(xué)突出“一言堂”或“滿堂灌”,不給學(xué)生思考的余地,久而久之,養(yǎng)成了學(xué)生學(xué)習(xí)上的惰性,形成上課做筆記、下課整理筆記、考試背筆記(有些懶惰的學(xué)生甚至省去了前兩個環(huán)節(jié),只是到了考試的時候才匆忙復(fù)印同學(xué)的筆記)的學(xué)習(xí)模式。創(chuàng)新型人才不僅需要知識的積累,更需要寬廣的視野,發(fā)散性的思維,因此,傳統(tǒng)教學(xué)模式難以滿足創(chuàng)新型人才培養(yǎng)的需求。大學(xué)教學(xué)不再只是知識的傳授,而是一種能力的養(yǎng)成,研討式教學(xué)的特點(diǎn)旨在強(qiáng)調(diào)學(xué)生學(xué)習(xí)的主動性和教師授課的引導(dǎo)性,改變學(xué)生被動接受的角色。
為加強(qiáng)研討式教學(xué),在“研教雙優(yōu)”人才培養(yǎng)模式創(chuàng)新實(shí)驗區(qū)內(nèi),我們鼓勵各專業(yè)、各課程積極探索,并采取課題立項形式加強(qiáng)研究,大膽實(shí)踐,及時進(jìn)行理論總結(jié)、提煉與升華。如周國林主持的《教學(xué)與人文素質(zhì)培養(yǎng)》、洪振強(qiáng)的《研教雙優(yōu)教育模式下的課堂建設(shè)——以“中國現(xiàn)代史”課程為例》、江滿情的《課程探究式教學(xué)研究》、尤學(xué)工的《理論的位置——研究型教學(xué)探研》、吳琦的《學(xué)生學(xué)術(shù)前沿意識的培養(yǎng)與訓(xùn)練——以為平臺的教學(xué)探索》、李曉明的《中國歷史文選與其他相關(guān)學(xué)科的溝通融合研究》、馬良懷的《授課實(shí)錄》、劉固盛的《課程教學(xué)改革與大學(xué)生人文精神培育》、魏文享的《方法與經(jīng)驗:中國近代史教學(xué)中學(xué)生研究意識的培養(yǎng)路徑》、馮玉榮的《免費(fèi)師范生歷史教育專業(yè)課程建設(shè)——以為例》、黃尚明的《文化遺產(chǎn)與文化產(chǎn)業(yè)專業(yè)實(shí)踐教學(xué)探討》、杜芳的《高師歷史專業(yè)師范生職業(yè)素養(yǎng)培養(yǎng)的實(shí)踐探索與創(chuàng)新研究》、張明生的《構(gòu)建第二課堂,提升學(xué)生綜合素質(zhì)》等。通過上述課題立項研究,教師們不僅提出了很多創(chuàng)見,如建議在院系網(wǎng)頁上開辟交流平臺,用于師生交流和在線答疑,根據(jù)學(xué)生興趣愛好,建立QQ群,交流學(xué)習(xí)心得體會等,而且在教學(xué)中付諸實(shí)踐,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近年來,研究型課堂實(shí)踐在實(shí)驗區(qū)內(nèi)逐漸推廣,如中國古代史課堂“以問題為中心,注重專題討論”,如“從新儒學(xué)的復(fù)興和文化下移的角度、貴族政治向官僚政治轉(zhuǎn)變的角度、商業(yè)革命的角度、科技進(jìn)步的角度探討轉(zhuǎn)型時期的社會問題”,并將學(xué)生分成若干個興趣小組,每一小組重點(diǎn)圍繞一兩個專題作主題發(fā)言,其他學(xué)生補(bǔ)充,主講教師點(diǎn)評。這種以“問題”為中心的教學(xué)方式,“充分調(diào)動了學(xué)生的學(xué)習(xí)興趣,充分發(fā)揮學(xué)生的主體性、積極性和創(chuàng)造性,大大活躍了課堂氣氛和學(xué)生思維。”中國當(dāng)代史課程嘗試開展“輪流式”互動教學(xué),依據(jù)基本內(nèi)容及發(fā)展階段分為24~26個專題,開列相關(guān)論著目錄,每個專題的討論以一個學(xué)習(xí)小組為核心,輪流進(jìn)行,各小組圍繞問題精心準(zhǔn)備,重點(diǎn)發(fā)言,相互啟發(fā),通過爭論,學(xué)生發(fā)現(xiàn)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提高了。世界近代史課堂長期堅持本科生的科研能力訓(xùn)練,探索五步法,即布置、選題、輔導(dǎo)、寫作、交流、點(diǎn)評,“激發(fā)了大學(xué)生的未知欲與想象力,培養(yǎng)了他們的求異思維和探索精神,培養(yǎng)了學(xué)生的學(xué)習(xí)能力、創(chuàng)新能力、交流能力。”專業(yè)選修課更多地采取了研討式的教學(xué)方式,在“宋史”課堂上,“形成‘對話式’、‘商討式’或‘答辯式’的教學(xué)氛圍,經(jīng)常保持課堂中具有教與學(xué)的雙向交流”。通過研討式教學(xué),建立起“師生參與互動—座談研討—科研實(shí)踐一體化的復(fù)合型的多樣化的教學(xué)模式”。這種教學(xué)模式就是把課堂教學(xué)與學(xué)生的課堂內(nèi)外實(shí)踐、科學(xué)研究融為一體。
在“中國近代史研究專題”教學(xué)中,任課教師朱英教授充分運(yùn)用現(xiàn)代網(wǎng)絡(luò)手段,在學(xué)院網(wǎng)站專業(yè)論壇.開設(shè)網(wǎng)絡(luò)論壇。由教師、助教擔(dān)任論壇版主,加強(qiáng)師生之間的聯(lián)絡(luò)和溝通。通過網(wǎng)絡(luò)論壇向?qū)W生提供必要的專業(yè)學(xué)習(xí)資料,并輔助課堂討論,網(wǎng)絡(luò)論壇有效地拓展了課堂,收效顯著。據(jù)悉,“在一個學(xué)期中,本論壇共發(fā)有近百個專題帖,跟帖也達(dá)到近五百個,點(diǎn)擊量更高達(dá)逾萬之?dāng)?shù),很快就一舉超過在該網(wǎng)絡(luò)社區(qū)原已開設(shè)多年的眾多論壇,成為主題帖,跟帖數(shù)量、點(diǎn)擊次數(shù)最多的一個論壇。”研討式教學(xué)取得了明顯的效果,“中國近代史研究專題”的課堂討論使得學(xué)生“學(xué)習(xí)積極性變強(qiáng)”、“表達(dá)概括能力、文獻(xiàn)檢索能力以及分析能力提高顯著”、“專業(yè)認(rèn)同感增強(qiáng)”、“發(fā)現(xiàn)問題、思考問題的能力增強(qiáng)”等。
多元化的考核是檢驗研究型課堂效果的有效手段,也是克服一張試卷論優(yōu)劣的重要方式。研討式課程大多采取了多元化的考核。如在世界近代史課堂上,任課教師對學(xué)生成績的評價主要包括“學(xué)生的課堂參與程度、小組課題合作程度、課堂的語言表達(dá)以及課程論文的研究質(zhì)量等方面”。中國古代史課程成績的評定“由討論、作業(yè)、論文撰寫、課題研究、社會調(diào)查、考試等多種檢測指標(biāo)來決定”。
可見,研討式教學(xué)將學(xué)生的課前準(zhǔn)備、課堂討論、課后論文有機(jī)地連為一個整體。在這個過程中,通過課前準(zhǔn)備,學(xué)生提前進(jìn)入角色,學(xué)術(shù)視野擴(kuò)大了。發(fā)現(xiàn)問題的能力提高了,文獻(xiàn)檢索能力增強(qiáng)了,在課堂討論中,同學(xué)們的交流互動能力、語言表達(dá)能力、即興思維能力等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提升。課后論文則是培養(yǎng)學(xué)生科研能力的一個關(guān)鍵環(huán)節(jié),是學(xué)生選題、資料搜集、解讀與運(yùn)用、寫作技巧與規(guī)范訓(xùn)練的一種綜合實(shí)踐。總之。研討式教學(xué)的大力開展是研教雙優(yōu)型人才培養(yǎng)模式的一個主要特色。
三、重藝術(shù)、強(qiáng)技能:課堂延伸與實(shí)踐教學(xué)
教學(xué)是一門藝術(shù),涉及到課堂組織、演講技巧、板書設(shè)計、粉筆藝術(shù)等多個環(huán)節(jié),優(yōu)秀教師的課堂對學(xué)生來說是一種藝術(shù)的享受,往往能產(chǎn)生事半功倍的效果。要當(dāng)好一名優(yōu)秀的中學(xué)歷史教師,不僅既要擅長粉筆字、板書等傳統(tǒng)教學(xué)藝術(shù),更要懂得計算機(jī)、多媒體、數(shù)據(jù)庫、網(wǎng)絡(luò)等現(xiàn)代教學(xué)技能。這是在長期的教學(xué)實(shí)踐中熏陶養(yǎng)成的,但大學(xué)階段教學(xué)藝術(shù)和技能的理論修養(yǎng)與必要的訓(xùn)練對教師的成長十分重要。為了培養(yǎng)“重藝術(shù)、強(qiáng)技能”的中學(xué)歷史教師,一方面,我們在課程設(shè)置中將計算機(jī)基礎(chǔ)、高等數(shù)學(xué)、多媒體技術(shù)與應(yīng)用等必備的現(xiàn)代教學(xué)技能作為通識必修課,將教師口語(普通話)、教師書法、歷史教學(xué)技能訓(xùn)練、現(xiàn)代教育技術(shù)等作為專業(yè)必修課,強(qiáng)化學(xué)生在教學(xué)藝術(shù)與技能上的理論素養(yǎng);另一方面,我們有效延伸課堂,通過豐富多彩的課外活動,使勤動手、善動腦、敢開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