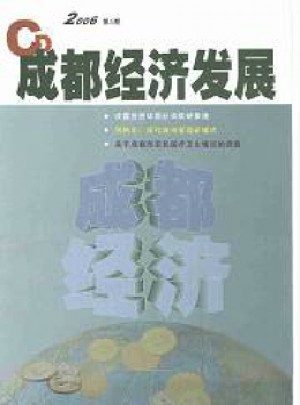引論:我們為您整理了1篇低碳經濟發展思考研究范文,供您借鑒以豐富您的創作。它們是您寫作時的寶貴資源,期望它們能夠激發您的創作靈感,讓您的文章更具深度。

國務院于2021年10月26日印發《2030年前碳達峰行動方案》,強調要堅持“總體部署、分類施策,系統推進、重點突破,雙輪驅動、兩手發力,穩妥有序、安全降碳”的工作原則,強化頂層設計和各方統籌。全面準確地認識碳達峰行動對經濟社會發展的深遠影響,提高政策的系統性、協同性。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大力推進綠色低碳科技創新,深化能源和相關領域改革。但在我國仍然以煤炭主導能源結構的背景下,如何實現“碳達峰、碳中和”,實現低碳經濟發展,兌現莊嚴承諾?能源消費結構如何在低碳經濟發展中實現轉型?相關能源產業又如何實現進一步的優化升級?厘清上述問題,對于幫助我們明晰“碳達峰、碳中和”實現社會低碳經濟發展具有研判意義。
一、中國低碳經濟的發展路徑分析
(一)中國實現低碳社會的目標《巴黎協定》代表了全球綠色和低碳發展的總方向,也是對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行動做出的統一安排。中國將努力擴大國家貢獻,制定更有效的政策,采取更有效的措施,到2030年達到碳峰值,到2060年實現碳中和。這意味著我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將完成全球最高碳排放強度降幅,用全球歷史上最短的時間實現“碳達峰、碳中和”。西方主要發達國家預計用80年實現碳達峰向碳中和的過渡,而我國有信心在短短30年的時間內實現碳達峰向碳中和的巨大跨越。碳達峰是實現碳中和的關鍵節點,更是實現經濟發展模式轉變的重要標志。
(二)中國目前低碳經濟的發展狀況我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2022年我國人均GDP為1.05萬美元,而按正常情況,人均GDP在1萬~2萬美元的國家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會持續增加,人均GDP在2萬~4萬美元的國家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會緩慢增加,我國仍然會存在明顯的耗能增加。但是我國經濟發展進入低碳新常態以來,轉變能源使用方式,優化發展動能使碳排放量得到了一定的控制,碳排放的年均增長率已經由10年前的5.4%下降到近兩年的1.2%,增長速度已經趨于平緩,為我國到2030年實現碳達峰提供了堅實基礎(國家統計局,2020)。[1]而在保障社會經濟持續增長的情況下實現碳排放量達峰,其核心是降低單位GDP的碳排放量(何建坤,2013)。[2]第十九屆五中全會中黨和政府提出2020—2035年中國GDP總量有望翻一番。到2030年,中國單位GDP的碳排放量下降率要由“十三五規劃”中的4.1%提升到4.5%的水平,以維持穩定的社會經濟增長率,在保障社會經濟穩定發展的同時實現2030年的碳達峰目標。同時,習近平在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上提出要大幅度提高原來自主承諾的單位GDP碳排放率下降幅度,實現碳排放下降幅度由60%~65%提升到65%以上的跨越,這為在2030年實現碳達峰提供了有力保障。
(三)低碳排放量與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關系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實現碳達峰、碳中和是一場廣泛而深刻的經濟社會系統性變革,要把碳達峰、碳中和納入生態文明建設整體布局。發展低碳經濟是中國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途徑之一。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主要來自煤炭和石油等化石能源的生產和使用,“多煤少油”的能源結構限制了中國能源結構的轉型升級。中國是世界上“以碳為基礎”的國家,而碳豐富的能源結構是中國碳排放增加的主要原因。我國能源結構過于依賴煤炭資源,已成為制約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因素。首先,有效減少和緩解我國高碳能源依賴和二氧化碳減排壓力,可為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提供基本保障。其次,發展低碳經濟,更多的是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促進我國經濟產業結構優化升級。低碳經濟的核心是通過提高能源利用率和開發新的清潔能源,促進低碳經濟的發展,實現低碳經濟和綠色社會的發展。
二、中國目前實現“雙碳”目標面臨的困難
(一)中國整體仍然處于工業化的中后期階段中國既不具備老牌發達國家美國在碳達峰時具備的較高工業生產技術水平與經濟發展水平,也不具備日本、德國在碳達峰時達到的較高的城市化率。[3]中國傳統的“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益”產業占比較高,有很大一部分的制造業在國際產業鏈中仍然處于中低端,存在能耗大、高碳燃料使用量大等問題,在如今“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國際形勢下,我國產業結構轉型升級面臨著高尖技術型應用人才不足、自主創新不足、各類能源成本上升等挑戰。我國現如今很大程度上仍然依靠以化石能源為基礎的工業體系和以勞動密集型為主導產業的傳統經濟增長方式,經濟發展新動能在產業轉型升級與穩經濟、保就業的宏觀經濟背景下面臨許多客觀壓力,經濟結構與傳統產業優化升級的任務艱巨,想要在短時間內實現碳排放量與社會經濟增長脫鉤壓力巨大。
(二)中國目前能源結構與低碳經濟建設存在明顯矛盾中國目前以煤為主的能源結構不符合當今世界能源發展的主流趨勢。但是我國煤炭資源豐富、煤炭能源使用成本低的實際情況也決定了我國的能源結構轉型困難,不能一蹴而就,“碳達峰、碳中和”的深層次問題便是能源結構問題,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能源是實現“雙碳”目標的重要方向標,但我國的能源結構一直以來存在著“富煤貧油少氣”的情況,嚴重制約了碳減排進程。經國家統計局核算,2020年我國全年能源消費中,煤消費總量占能源消費總量的56.8%。我國煤炭消費量與煤炭能源生產量都位居世界第一,石油和天然氣等能源消費對外依賴度高,能源供給壓力大(莊貴陽,2021)。[4]截至2019年底,中國煤電裝機容量達到10.4億千瓦,占世界煤電總裝機容量的一半,煤電占中國煤炭消費量的50%以上。考慮到低碳減排的要求,大量以化石為主燃料的傳統基礎設施將在中國產生巨大的退出成本。減少二氧化碳排放將鼓勵逐步淘汰煤炭和電力,這將加劇相關行業的動蕩,而以密集勞動力生產為主的煤電行業動蕩會造成大量失業,會給社會保障體系和社會穩定帶來一定影響。
(三)中國目前低碳減排相關技術有待完善脫碳是實現碳達峰和碳中和的關鍵。相較于大多數發達國家,我國的脫碳發展起步較晚,相關政策尚未完善。從各國脫碳戰略的舉措來看,優化產業結構、科技創新和設定碳定價機制是脫碳的戰略核心,而化工能源產業和鋼鐵冶煉業更是低碳減排的重要領域。從資金投入的角度來看,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我國脫碳技術的研發工作起步較晚,投入也遠低于發達國家,部分領域的核心技術主要由發達國家掌握。從科技創新的角度來看,我國脫碳技術的發展有待成熟,各種技術難以整合,技術種類多,成本高。目前,投資和實現減排目標仍在繼續,現有的脫碳技術很難幫助中國在2030年和2060年分別實現碳達峰和碳中和,目前已有數十億元人民幣投資于碳捕獲、利用與封存(CCUS),但效果并不明顯,影響了CCUS技術的開發和推廣。此外,我國目前的碳減排技術仍然較為單一,能源系統的優化技術,低能耗、高選擇性的加工技術,以及CCUS等技術研發進度較慢,推廣難度較高,缺乏完善的理論支撐和豐富的國際實踐經驗輔助,低碳減排發展阻力明顯。
三、多措并舉推動我國低碳經濟目標的實現
我國要用短短30年時間實現從碳達峰到碳中和,這一過程無疑是困難的。實現碳達峰、碳中和這一艱巨任務,需要有強有力的政策和制度保障,更要有超前的部署和行動。
(一)積極推動綠色“碳賬戶”的建立建立綠色“碳賬戶”是市場在綠色資源配置中發揮重要乃至決定性作用的基礎。因為無論是通過政府還是市場實現低碳減排,都需要核算明細,因此也就需要以“碳賬戶”為輔助。碳賬戶首先要解決核算問題,包括碳核算和環境核算,這是綠色發展的基礎。在此基礎上,創建碳賬戶,以形成各級政府、企業和個人實現二氧化碳減排目標的環境責任成本。明確所有公司減少排放的責任,以實現國家雙碳目標。除了建立碳賬戶外,還應該探索建立企業ESG(環境、社會、公司治理)評估體系和制度。確定更多的企業減排責任,將其作為企業的一種評價體系,讓更多的國內外企業參與其中。
(二)推動碳排放權交易市場健康發展從整體來看,綠色經濟發展轉型將是一場深刻的經濟社會變革,需要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經濟體系的穩固支撐。從國際經驗來看,擁有一個充分發揮優化資源配置機制作用的碳排放交易市場是必不可少的。近年來,碳排放權交易市場的建設進程正在穩步推進,但總體來看,要想切實發揮綠色減排的調節功能,還需要針對短板精準發力。當前,碳排放權交易市場還處于建設階段,制度體系既缺少部門之間的協調聯動,在關鍵環節也缺少明確的規范和標準,制度缺陷日益明顯。此后,一是要加快在更高層級建立部門聯系的步伐,強調系統性、重視整體性,提高政策的可執行性。二是要將碳排放權交易體系積極融入現如今人工智能、大數據、數字化的發展新趨勢中,將數字化作為提高管理精細化水平的核心,將數字化技術更大規模地應用在能源及其相關產業中,通過對數字化技術在各個環節的深度運用,持續降低企業碳排放量。只有政府與市場協同發力,才能實現更為有效的低碳減排。
(三)加大對低碳技術研發創新的支持力度對低碳技術的創新推廣可以進一步增強低碳產品的競爭力,也能加快低碳市場經濟系統的建立與完善。[5]“雙碳”目標的實現,離不開技術的支持,我國政府在脫碳關鍵技術領域應當積極建立產學研創新體系,發揮各大高校優質科研資源與相關產業界配套設備和管理經驗的聯動作用,以研促產,加快碳中和核心技術如CCUS的市場化運用。政府還應該通過財政補貼等方式加大對碳中和相關核心技術研究人員的激勵,促進相關技術的研發與落地,政府加大財政資金投入可以充分鼓勵市場上的相關科技企業圍繞碳中和實施相關市場措施,同時進一步吸引國內外投資者加大對低碳技術領域的投資力度。
(四)加快推動能源產業結構綠色轉型與升級能源是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物質基礎,也是碳排放的最主要來源。能源系統種類繁多,要推動能源結構轉型升級,必須加強能源風險控制,確保穩定低碳。還要合理限制石油消費,優化新能源的消費結構,積極推動能源加工技術的升級,深入開展CCUS技術的規模應用。同時,要樹立低碳減排的風向標,堅定不移地推進能源結構轉型升級,完成推動綠色低碳發展這一關鍵任務,推動我國能源結構轉型實現飛躍。[6]結合索洛經濟增長模型和對碳排放強度進行的實證研究發現,雖然低碳減排在短期內造成了少量經濟損失,降低了社會經濟發展速度,但低碳減排相關技術投資等提高能效的方式在長期顯現出日益提高經濟效益的趨勢,能源結構優化是碳減排目標實現的關鍵。[7]由此可見,能源結構的進一步轉型升級對我國綠色低碳減排事業的發展具有重要的推動作用。
結語
總體來說,我國在專注發展經濟建設的同時,關注碳排量的降低,警惕日益嚴重的環境污染,并向世界做出2030年實現“碳達峰”、2060年實現“碳中和”的莊嚴承諾,展現了一個負責任的大國形象。而我國在實現綠色低碳經濟發展的過程中遇到的是挑戰更是機遇,抓住綠色低碳經濟模式發展的機遇,推動社會能源消費結構轉型升級,將賦予中國社會更多的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潛力。
參考文獻:
[1]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摘要2020[M].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20.
[2]何建坤.CO2排放峰值分析:中國的減排目標與對策[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3,23(12):1-9.
[3]叢建輝,王曉培,劉婷,等.CO2排放峰值問題探究:國別比較、歷史經驗與研究進展[J].資源開發與市場,2018(6):774-780.
[4]莊貴陽.我國實現“雙碳”目標面臨的挑戰及對策[J].人民論壇,2021(18):50-53.
[5]石敏俊,袁永娜,周晟呂,等.碳減排政策:碳稅、碳交易還是兩者兼之?[J].管理科學學報,2013(9):9-19.
作者:甘宇飛 單位:江西師范大學財政金融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