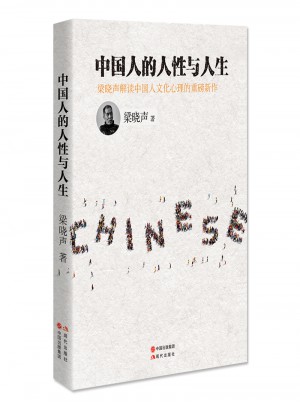
中國(guó)人的人性與人生
- 所屬分類(lèi):圖書(shū) >文化>文化評(píng)述
- 作者:[梁曉聲]
- 產(chǎn)品參數(shù):
- 叢書(shū)名:--
- 國(guó)際刊號(hào):9787514344103
- 出版社:現(xiàn)代出版社
- 出版時(shí)間:2017-01
- 印刷時(shí)間:2017-01-16
- 版次:1
- 開(kāi)本:16開(kāi)
- 頁(yè)數(shù):--
- 紙張:膠版紙
- 包裝:平裝-膠訂
- 套裝: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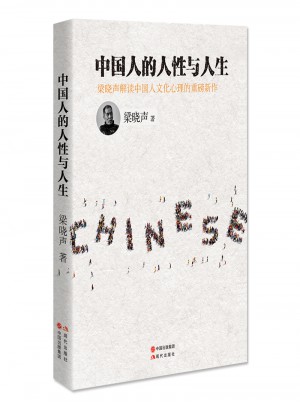
本書(shū)是梁曉聲先生深度解剖當(dāng)代中國(guó)人的文化心理與國(guó)民性的重磅力作。
作者以一如繼往的冷峻而智慧的筆調(diào)、滲及骨髓的透視深度,以及充滿(mǎn)人文理性的文字,對(duì)當(dāng)代的中國(guó)人的文化心理狀況,普通人人生的尷尬,以及關(guān)于中國(guó)的文化與文化人,給出了自己的觀察與評(píng)述,可以說(shuō)是一部關(guān)于中國(guó)社會(huì)人文現(xiàn)狀的“田野調(diào)查”,也是一部深度的社會(huì)觀察筆記。在本書(shū)中,作者直視人性的軟弱,頌揚(yáng)人性的閃光與良知的自省,由此,我們才能獲得改變與進(jìn)步的勇氣,并期許與擁抱光輝的未來(lái)。
1、梁曉聲2017年重磅新作,繼《中國(guó)社會(huì)各階層分析》《郁悶的中國(guó)人》之后,全新深度解剖當(dāng)代中國(guó)人的文化心理和國(guó)民性!
2、滲及骨髓的人性透視,在梁曉聲筆下,人性的偽裝被一層層地?zé)o情剝?nèi)ィx后令人冷汗淋淋、連連呼痛。
3、一部充滿(mǎn)人文理性的社會(huì)觀察實(shí)錄。道德尷尬、影視亂象、職業(yè)角色錯(cuò)位、青年人的出路問(wèn)題、文化不自信問(wèn)題……作者以冷峻而智慧的文字予以解說(shuō),一針見(jiàn)血,卻又深慰人心。
4、中國(guó)社會(huì)各色人等的人生百態(tài)的記錄,直視人性的弱點(diǎn),見(jiàn)證人性的光輝、溫暖與尊嚴(yán)。
梁曉聲,當(dāng)代著名作家、教授、全國(guó)政協(xié)委員。創(chuàng)作過(guò)大量具有影響的小說(shuō)、散文、隨筆及影視作品。主要作品有《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風(fēng)雪》《雪城》《知青》《中國(guó)社會(huì)各階層分析》《郁悶的中國(guó)人》等。他的文字兼具作家、學(xué)者、思想者等多個(gè)維度,深受廣大讀者喜愛(ài)與推崇。
需要安放的人心
論中國(guó)特色之“存在主義” / 003
你想成為吸血鬼嗎? / 009
語(yǔ)說(shuō)“寒門(mén)”與“貴子” / 016
蘋(píng)果樹(shù)下》與“廣告扶貧” / 023
論“吸血鬼”策略 / 028
千年病灶:撼山易,撼奴性難 / 033
培養(yǎng)一個(gè)“貴族”是容易的 / 041
當(dāng)懷才不遇者遭遇暴發(fā)戶(hù) / 044
猴子 / 048
真話(huà)的尷尬處境 / 052
報(bào)復(fù)的尺度 / 055
我們的社會(huì)
一條小街的GDP現(xiàn)象 / 063
中國(guó)影視那些事 / 069
實(shí)難為續(xù)的收視率 / 080
那些老美電影中的臺(tái)詞(之二) / 089
當(dāng)今中國(guó)青年階層分析 / 092
僅僅譴責(zé)是不夠的 / 103
醫(yī)生的位置 / 108
法理與情理 / 112
世界的丑陋 / 116
我的一點(diǎn)人生經(jīng)驗(yàn)
梁曉聲答讀者問(wèn) / 125
我的“人生經(jīng)驗(yàn)” / 134
書(shū)、女人和瓶 / 147
七彩茉莉 / 155
禪機(jī)可無(wú),靈犀當(dāng)有 / 164
做竹須空,做人須直 / 169
老嫗 / 174
狡猾是一種冒險(xiǎn) / 176
人性似水 / 184
人生真相 / 191
中國(guó)的文化修行
關(guān)于邵洵美之雜感 / 205
知識(shí)分子與“轉(zhuǎn)基因” / 210
敬讀靜好心靈 / 220
巴金的啟示 / 225
沉思聞一多 / 231
中國(guó)人文文化的現(xiàn)狀 / 236
拒做儒家思想的生 / 246
中國(guó)“尼采綜合癥”批判 / 250
文化的報(bào)應(yīng) / 277
只想當(dāng)“小知識(shí)分子” / 280
知識(shí)分子與“轉(zhuǎn)基因”
這里談的是中國(guó)知識(shí)分子,且限于文化知識(shí)分子,即自身所學(xué)專(zhuān)業(yè)及后來(lái)乃至終生職業(yè)與文、史、哲領(lǐng)域密不可分的一類(lèi)知識(shí)分子。
科技知識(shí)分子是另一類(lèi)人。除了在人類(lèi)處于科學(xué)知識(shí)蒙昧的時(shí)期,這一類(lèi)人的發(fā)現(xiàn)、發(fā)明、創(chuàng)造曾與當(dāng)局的意識(shí)形態(tài)控制尺度產(chǎn)生沖突,因而受到迫害——在歷史的多數(shù)時(shí)期,他們實(shí)際上是任何一個(gè)國(guó)家的任何性質(zhì)的當(dāng)局所愿倚重的人,因?yàn)樗麄兊难芯砍晒蟮謺?huì)使國(guó)家和代表國(guó)家的當(dāng)局大受其益而不是反過(guò)來(lái)。故他們的人生,通常不致過(guò)于可悲。這乃是人類(lèi)歷史上的一種事實(shí),無(wú)須贅言的。
這里談的“轉(zhuǎn)基因”,與崔永元與方舟子之間爭(zhēng)論是非的“轉(zhuǎn)基因”毫無(wú)關(guān)系,只不過(guò)是借以比喻。他們爭(zhēng)得特別激烈之時(shí),有記者要我表態(tài),我拒絕了,由于當(dāng)時(shí)我對(duì)“轉(zhuǎn)基因”食物的知識(shí)空白。現(xiàn)在,我也有了一些這方面的知識(shí),故可以表態(tài)站在崔永元一邊了。入口之物無(wú)小事,危害與否尚不明確的東西,當(dāng)然以慎食為好。
言歸正題——僅舉蔡元培、魯迅、胡適、郭沫若為例,淺析中國(guó)文化知識(shí)分子之群體的思想“基因”的守與失,試看我們中國(guó)半個(gè)多世紀(jì)以來(lái)的文化成色的嬗變。
一、1940年蔡元培逝后,國(guó)內(nèi)曾有報(bào)道言及聯(lián)合國(guó)亦表示了哀悼,充分肯定其在中國(guó)教育事業(yè)方面所做的貢獻(xiàn),認(rèn)為對(duì)于教育落后的國(guó)家有示范性的作用。未經(jīng)核實(shí),姑且存歟。但以上兩點(diǎn)確合事實(shí),當(dāng)無(wú)爭(zhēng)議。
這里且不談他的貢獻(xiàn),單論其德。
當(dāng)年國(guó)民政府褒揚(yáng)令(非尋常哀悼),頌其“道德文章,夙負(fù)時(shí)望”,“推行主義,啟導(dǎo)新規(guī)、士氣昌明,萬(wàn)流景仰”。
以上懇詞包含以下諸意:
蔡元培是一位“士”,其“士”的精神磊落坦蕩;
他是一個(gè)為主義而鞠躬盡瘁的人,他推行的自然是三民主義;
他在人格方面,具有極其本色的而非企圖靠作秀贏得的強(qiáng)大魅力,即使反對(duì)他的人也由衷折服。
所以全國(guó)不分政治派別,“萬(wàn)流景仰”。
馮友蘭認(rèn)為他“是近代確合乎君子標(biāo)準(zhǔn)的一個(gè)人”。
儒家文化論及個(gè)人道德修養(yǎng)的全部?jī)?nèi)容,無(wú)非“君子”二字而已。
“可以托六尺之軀,可以寄百里之命”“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可辱也”,“身可危也,志不可奪也”,“可欺以其方,難枉以非道”——這些中國(guó)古代關(guān)于君子的標(biāo)準(zhǔn),在蔡元培人生的不同階段,幾乎都不同程度地證明了。
馮友蘭由是稱(chēng)贊他的人格“是儒家教育理想的較高表現(xiàn)”。
傅斯年的評(píng)價(jià)更些,他說(shuō):“蔡元培先生實(shí)在代表兩種偉大文化:一曰,中國(guó)傳統(tǒng)圣賢之修養(yǎng);一曰,西歐自由博愛(ài)之理想。此兩種文化,具其一難,兼?zhèn)溆炔豢捎M。先生歿后,此兩種文化,在中國(guó)之氣象已亡矣!”
魯迅兄弟的業(yè)師壽洙鄰說(shuō):“孑民道德學(xué)問(wèn),集古今中外之大成,而實(shí)踐之,加以不擇壤流,不恥下問(wèn)之大度,可謂偉大矣。”
正因其具有“不擇壤流”,兼容并包之襟懷,連辜鴻銘也說(shuō):“現(xiàn)在中國(guó)只有兩個(gè)好人,一個(gè)是蔡元培,一個(gè)是我。因?yàn)椴滔壬c(diǎn)了翰林之后不肯做官就去革命。我呢,自從跟張文襄(之洞)做了前清的官之后,到現(xiàn)在還是保皇”。
不肯做官的蔡元培托病離朝,回到家鄉(xiāng)興辦新式學(xué)堂,先后主辦、創(chuàng)建了中西學(xué)堂、紹興府學(xué)堂、越郡公學(xué)、明道女校、稽山中學(xué)、嵊縣剡山書(shū)院、南陽(yáng)公學(xué)。1902年,創(chuàng)建中國(guó)教育會(huì)、愛(ài)國(guó)學(xué)社、愛(ài)國(guó)民校。1904年組織光復(fù)會(huì),1905年參加同盟會(huì)。謙謙君子而研制炸藥,每欲以文人之軀換清廷大佬之狗命——想來(lái)真真令人心疼。
今日之國(guó)人,特別是青年,若對(duì)魯迅知之甚多,對(duì)蔡元培僅知一二,或全然陌生,實(shí)在是不應(yīng)該的,也實(shí)在是知識(shí)方面的遺憾。
同在紹興,同在一條街上,魯迅故居車(chē)水馬龍,蔡元培故居門(mén)可羅雀,可謂國(guó)人一大羞恥也。
蔡元培者,可謂中國(guó)近代史上文化知識(shí)分子中的孫逸仙啊!
世負(fù)斯人!世負(fù)斯人!
若有青年讀了我此書(shū),且又去了紹興,我勸你們也前往蔡元培故居參觀。比之于魯迅故居,那里未免冷清、寒酸。而比之于魯迅,蔡元培則尤可崇敬也!
你們?nèi)艄チ耍鹜疑罹弦还?/p>
你們須知,你們中人所津津樂(lè)道的近代中國(guó)歷史上那些大師級(jí)的文化知識(shí)分子,幾乎都是受到過(guò)蔡元培人格與精神的感召的!
二、關(guān)于魯迅,我以為蔡元培為魯迅全集所做之序中的評(píng)語(yǔ),甚為中懇:“先生閱世既深,有種種之不忍見(jiàn)不忍聞的事實(shí),而自己又有一種理想的世界,蘊(yùn)積既久,非一吐不快。”——這實(shí)際上等于替泉下的魯迅辯了“帶病態(tài)的人物”這一貶識(shí)。對(duì)于魯迅的文學(xué)成就,蔡元培推崇備至:“蹊往獨(dú)辟,為后學(xué)開(kāi)示無(wú)數(shù)法門(mén),所以鄙人敢以新文學(xué)開(kāi)山目之。”
魯迅生前,對(duì)是同鄉(xiāng)的蔡元培亦不乏文字譏諷。其逝后,蔡元培毫不計(jì)較,誠(chéng)受其夫人重托,兩個(gè)月內(nèi)遍閱魯迅遺著,潛心析思,方落筆墨,足見(jiàn)他的人格之可敬絕非虛名。
后來(lái)的魯迅研究者,每將其與胡適相比較,以拔高他的偉大。此種比較之法的失當(dāng)之處在于,仿佛胡適很矮小,只可做偉大之魯迅的陪襯人。我年輕時(shí)深受此種比較的影響,深信不疑。后來(lái)讀書(shū)漸多,始覺(jué)受蒙蔽矣。
我倒是每將魯迅與郭沫若相比較,結(jié)果一次又一次產(chǎn)生這樣的印象——魯迅與郭沫若在人格上肯定是不同的,在思想上卻曾十分地近似過(guò)。
我產(chǎn)生這樣的印象,乃因魯迅是格外贊賞尼采的。
尼采的所謂哲學(xué),在我看來(lái),無(wú)非便是“造反有理”那一套而已。又在我看來(lái),他的“超人妄想”,分明是反眾生的。他幾乎一切都反,包括對(duì)宗教也乏敬意。但卻從不以文字或語(yǔ)言冒犯德皇——因其母親的家族中,有人深受皇恩,而且那恩澤及其身。僅此一點(diǎn),作為“哲學(xué)家”便甚不靠譜了。
魯迅贊賞尼采的文學(xué),不引也罷。
其雜文《這樣的戰(zhàn)士》中,有幾行字是:“那些頭上有各種旗幟,繡出各樣好名稱(chēng):慈善家、學(xué)者、文士、長(zhǎng)者、青年、雅人、君子……頭下有各樣外套,繡出各式好花樣:學(xué)問(wèn)、道德、國(guó)粹、民意、邏輯、公義、東方文明……
但他舉起了投槍。
……
他微笑,偏側(cè)一擲,卻正中了他們心窩。”
在《復(fù)仇》二篇中,魯迅一如既往地表達(dá)了他對(duì)看客們的極強(qiáng)烈的憎惡,不,那其實(shí)是憎恨,因極厭惡而極強(qiáng)烈的與痛苦同在的憎恨。
因憎恨而痛苦,這是魯迅那個(gè)時(shí)代幾乎唯他獨(dú)有的一種痛苦。他憎恨別人的悲運(yùn)變成看客圍娛的現(xiàn)象,自己卻往往陷于同樣境況。
然而,無(wú)論我們對(duì)魯迅多么理解,都難以否認(rèn)他有思想特別偏激的方面,如他對(duì)中國(guó)歷史、中國(guó)字以及中醫(yī)而徹底地否定的言論。
如果說(shuō)這也是一種“左”,那么他與尼采可算是“國(guó)際戰(zhàn)友”;而與郭沫若,則可謂是思想上的“同志”,盡管他們彼此同等程度地排斥。
1949年前的郭沫若的“左”,尚在可以兼容并包的范圍;1949年后,郭的“左”的激昂優(yōu)越感逐年熾烈。不但打倒任何曾屬同一陣營(yíng)的人都是他必帶頭歡呼的,而且往往也親自口誅筆伐。
故,到“”時(shí)期,死了的魯迅的語(yǔ)錄,也有殊榮被印成“小紅書(shū)”,在紅衛(wèi)兵和造反派中廣為流傳;活著的郭沫若的表態(tài),往往意味著是代表中國(guó)全體文化知識(shí)分子宣告立場(chǎng)了。
兩個(gè)互無(wú)好感的人,因他們思想中的“左”的共同點(diǎn),便都起了身不由己的作用。
在魯迅,那是無(wú)奈的,因?yàn)橐褵o(wú)法抗議了。
在郭沫若,卻是另外一回事,起初出于自我證明,后來(lái)出于趨利避害的“明智”。
魯迅的“左”是由衷的,剛烈的,寧折不彎的,無(wú)絲毫取悅心理的正大光明的“左”;他極其鄙視利用的勾當(dāng)和情愿被利用的偽態(tài)。
所以魯迅在人格上與許多別的中國(guó)文化知識(shí)分子的“左”是不一樣的。
在我看來(lái),魯迅之“氣象”,寶貴而可敬的方面,似乎也終結(jié)于中國(guó)某些70年代文化知識(shí)分子身上了;不那么可取的方面,卻反而似乎成了后人身上的“基因”現(xiàn)象……
三、相對(duì)于魯迅,胡適一向被大陸的歷史定義為近代以降“右翼”中國(guó)文化知識(shí)分子的領(lǐng)袖人物。
這么定義自有其道理,因?yàn)檫B中國(guó)共產(chǎn)黨的同路人都不曾是過(guò)一日,并且一向“效忠”于國(guó)民黨。
確乎,在國(guó)共兩黨之間,胡適是選邊站的。
但對(duì)他的態(tài)度卻也任性得可以——倘他肯留在大陸,那么北京圖書(shū)館館長(zhǎng)的位置便是他的;他選擇去了美國(guó),于是上了“戰(zhàn)犯”名單,且排名極為靠前。
姑且不論他的政治立場(chǎng)選擇之對(duì)錯(cuò),單論其歷史作用與人格美點(diǎn),我以為周、胡二人身上實(shí)在是有諸多相同之點(diǎn)。
“魯迅是中國(guó)文化革命的主將”,那么胡適就不是了嗎?肯定應(yīng)該說(shuō)更是的吧?他毫無(wú)疑問(wèn)是中國(guó)新文化運(yùn)動(dòng)的旗手之一啊。今天漢字能在中國(guó)較容易地達(dá)到普及,越來(lái)越多的中國(guó)人能以現(xiàn)代漢字創(chuàng)作出越來(lái)越千姿百態(tài)的文學(xué)作品,能將越來(lái)越多的外國(guó)文學(xué)作品翻譯成人人讀起來(lái)輕松流暢的中文讀本,是不是應(yīng)該對(duì)胡適心懷感激呢?
那在當(dāng)年也是一件罵聲四起,很不容易取得成功的事。為其成功,他是不是也做到了“冷對(duì)千夫指,甘為孺子牛”呢?只不過(guò)他做得相當(dāng)?shù)ǎ丛?ldquo;橫眉”,也未曾“伏首”而已。他與志同道和者們所做那事,利益是超乎黨派、階級(jí),功在國(guó)家與民族的。
胡適是有奴顏和媚骨的嗎?
當(dāng)然也是絲毫沒(méi)有的——他與之間一向以諍言、逆言平等討論問(wèn)題的自尊自重的態(tài)度,足以說(shuō)明此點(diǎn)。
他雖算不上是什么“偉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但他于“國(guó)統(tǒng)”時(shí)期,一再大聲疾呼民主、法制、言論自由、人權(quán)平等,難道不也等于是在不遺余力地傳播進(jìn)步思想嗎?
與魯迅的四處樹(shù)敵相反,胡適是團(tuán)結(jié)每一個(gè)正派的好人而唯恐不及的——連瞧著他大不順眼的辜鴻銘,他也不愿與其真的形成交惡關(guān)系,而且最終辜鴻銘基本上也算是被他團(tuán)結(jié)了——因?yàn)楣鉴欍懺谒哪恐胁⒉皇且粋€(gè)壞人。
當(dāng)時(shí)及以后曾有某些人士貶損胡適“是個(gè)大鄉(xiāng)愿”,在我這兒,視為“訾嗷”蔡元培的同類(lèi)。
唐德剛說(shuō):胡適是“傳統(tǒng)中國(guó)”向“現(xiàn)代中國(guó)”發(fā)展過(guò)程中,繼往開(kāi)來(lái)的一位啟蒙大師。
我認(rèn)為此評(píng)恰當(dāng),毫不過(guò)分。
但我更喜歡徐復(fù)觀評(píng)胡適的——“一個(gè)偉大的書(shū)生”。
此“書(shū)生”在社會(huì)學(xué)的主張方面堅(jiān)決反對(duì)暴力革命,但又與堅(jiān)決實(shí)行武裝奪取政權(quán)的共產(chǎn)黨的兩位高級(jí)領(lǐng)導(dǎo)人與陳獨(dú)秀友誼深焉。
他之反對(duì)暴力革命純粹是站在社會(huì)學(xué)的立場(chǎng)上而非站在國(guó)民黨的立場(chǎng)上;李、陳二位逝后,他將對(duì)他們的真摯的悼念文字印在自己新出版的書(shū)上。
他“書(shū)生”到寫(xiě)信勸解散共產(chǎn)黨的武裝,以不流血的參與議會(huì)斗爭(zhēng)的方式對(duì)抗國(guó)民黨的一黨獨(dú)大、,促進(jìn)中國(guó)的民主化進(jìn)程。這當(dāng)然是天真的,站著說(shuō)話(huà)不嫌腰疼的——不流的只會(huì)是國(guó)民黨的血,許多共產(chǎn)黨人卻肯定會(huì)肝腦涂地。
他也很反感搞黨天下,反對(duì)“剿共”,認(rèn)為共產(chǎn)黨當(dāng)然不是“匪”,而是國(guó)民黨的公開(kāi)的,有政治綱領(lǐng)、組織系統(tǒng)和軍隊(duì)的“政敵”而矣;所以國(guó)民黨不但應(yīng)該允許共產(chǎn)黨的合法存在,還應(yīng)劃分給共產(chǎn)黨至少一個(gè)省,任其搞共產(chǎn)主義試驗(yàn)——倘效果好,其他省有權(quán)力效仿。
因?yàn)樗且粋€(gè)影響力“偉大”的書(shū)生,而且又是由于真性情驅(qū)使的真天真,國(guó)、共兩黨才都不忍心滅他。
他也真的憤慨于國(guó)民黨的腐敗無(wú)能,曾斥曰:“所以老百姓才紛紛投奔共產(chǎn)黨,拿起槍來(lái)反抗!”
他也會(huì)天真得相信謠言,見(jiàn)報(bào)上說(shuō)共產(chǎn)黨入川后“大開(kāi)殺戒”,致使幾十萬(wàn)人頭落地,迫不及待地催促?lài)?guó)民黨拯救四川,“該出手時(shí)就出手”——待明白自己上當(dāng)了,復(fù)而對(duì)共產(chǎn)黨人所受的迫害表示同情。
共產(chǎn)黨逐漸擁有了大陸,天下定局分明,他卻偏要忠于他的政治主張一條道走到黑。
國(guó)民黨退至臺(tái)灣,他也不跟隨求安,于是“流亡”于美國(guó)。
請(qǐng)他去臺(tái)灣出任“科學(xué)院”院長(zhǎng),一向清高的他反而去了。
他的想法是——知道你在利用我,但我正可利用你對(duì)我的利用,做我最想做的弘揚(yáng)文化民主之事。
已被共產(chǎn)黨宣布為戰(zhàn)犯了;也一再名列國(guó)民黨的黑名單榜首。
他對(duì)自己的處境心知肚明,卻終生無(wú)怨無(wú)悔。
大陸大張旗鼓地批他,他坦然面對(duì)。
其實(shí)也巴不得他早點(diǎn)兒死,他也猜得到。
但他對(duì)兩邊任何一邊都絕無(wú)屈膝之態(tài)。
這是否稱(chēng)得上具有“獨(dú)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呢?
當(dāng)然的!
也正是在這一點(diǎn)上,我認(rèn)為蔡元培、魯迅、胡適,他們其實(shí)有著一樣的骨質(zhì),并列于同一人格高度——不同的是他們的性格和思想主張。
蔡元培和胡適,都是一定要以“君子”風(fēng)范立人做事的。
而魯迅不愿做“君子”——如絕不行小人勾當(dāng)和反感成為人格榜樣——這乃是由于他之甚缺兼容并包的襟懷和長(zhǎng)期糾纏他的“憎恨的痛苦”所決定的。
他們都是只有在特定歷史條件下才能僥幸存在的人物。
胡適的千年唯此一“書(shū)生”的文化“氣象”也是不可復(fù)制的——以我的眼看來(lái),中國(guó)以后相當(dāng)長(zhǎng)時(shí)期內(nèi),胡適那種自由知識(shí)分子的“基因”,在文化知識(shí)分子們身上不會(huì)再現(xiàn)特征。
四、關(guān)于郭沫若,便沒(méi)有多說(shuō)的必要了。
但郭沫若式的文化知識(shí)分子的“基因”,在中國(guó)當(dāng)下及以后幾代文化知識(shí)分子身上,將還會(huì)是特征之一,由不同的人對(duì)當(dāng)官(其實(shí)大抵是當(dāng)管文化知識(shí)分子的官)這件事的不同感覺(jué)而決定體現(xiàn)得明顯與不明顯。普遍規(guī)律是,官位越高,特征越鮮明。
總體而言,中國(guó)文化知識(shí)分子之素質(zhì)還是進(jìn)步多了的,表現(xiàn)如下:
1、凡需表態(tài)(除非事關(guān)國(guó)土完整、國(guó)家分裂與否),都更愿以低調(diào)為好。高調(diào)的、激揚(yáng)文字的、嘩眾取寵意圖分明的表態(tài),已基本上為文化知識(shí)分子所不恥。偏演此技者,定遭同類(lèi)側(cè)目。
2、倘同類(lèi)又上什么名單,落井下石者鮮見(jiàn)矣。即或其言行的確與自己之見(jiàn)解或主張相左,也只不過(guò)表示遺憾而已。若并未被要求表態(tài),則大抵沉默。趁機(jī)充當(dāng)棍棒,采取誅心之法,置同類(lèi)于雪霜之境以博青睞者,更是少之又少了,近年鮮聞。并未絕種,但繁殖力大不如前了。
3、濾掉具體語(yǔ)境,對(duì)某同類(lèi)之發(fā)言斷章取義,歸納成“黑話(huà)”,匿名或?qū)嵜蛴嘘P(guān)機(jī)構(gòu)打小報(bào)告,目的在于表忠取寵的現(xiàn)象也少了。我從青年時(shí)期便深受此種現(xiàn)象之苦,極厭之。如今此現(xiàn)象也并未消除,但同類(lèi)之間的出賣(mài)確已被公認(rèn)是卑鄙行徑了。工作性質(zhì)的匯報(bào)卻還是常態(tài)——既是某些同志的工作,也就只有理解萬(wàn)歲。有的話(huà)別當(dāng)人家面說(shuō)才好,你說(shuō)了,使人家為難。不匯報(bào),人家失職,可能要被問(wèn)責(zé);匯報(bào)了,人家覺(jué)對(duì)不起你。所以須懂事。這點(diǎn)道理,越來(lái)越多的文化知識(shí)分子開(kāi)始認(rèn)同。
在胡適們的時(shí)代,文化知識(shí)分子們最為關(guān)注的乃是民族與民權(quán)問(wèn)題。民生雖哀鴻遍野,文化知識(shí)分子們發(fā)聲的重點(diǎn)倒不在斯。不同的時(shí)代有不同的國(guó)情,不同時(shí)代的文化知識(shí)分子有不同的甘愿自授的使命。
民生、民權(quán)——中國(guó)之文化知識(shí)分子,倘肩上的使命感怎么也卸不下來(lái),那么在這兩方面還是有些作用可以發(fā)揮的。
寫(xiě)到這里,我更加理解蔡元培和胡適了——他們之教育興國(guó)、法制醫(yī)國(guó),民主改良的努力路徑,不是幼稚,是不逢其時(shí)耳。
現(xiàn)在之中國(guó),當(dāng)然還是需要魯迅精神的;而我卻希望蔡元培和胡適的“基因”,在自己和同類(lèi)們的言行中也有所現(xiàn)——人格上可敬起來(lái),話(huà)語(yǔ)權(quán)便更大些……
自二十世紀(jì)九十年代以來(lái)中國(guó)和世界的變化讓人們改變得很多,但梁曉聲式的慷慨陳詞依然有自己的力量在。人們?nèi)匀豢梢詮牧簳月曔@里得到一種真正的滿(mǎn)足,梁曉聲仍然能夠給他的讀者想要的東西,是一位關(guān)愛(ài)學(xué)生的教授。(文學(xué)評(píng)論家張頤武)
知識(shí)分子歷來(lái)就有矯正社會(huì)惡疾和喚醒民眾的使命,包括基本概念的重建。在這一點(diǎn)上,作家梁曉聲先生是令人尊敬的。(龍應(yīng)臺(tái))
他的寫(xiě)作始終堅(jiān)持自己的立場(chǎng),始終秉持知識(shí)分子的良知和情懷,始終高揚(yáng)人文主義的旗幟,他從不因?yàn)樗^純文學(xué)的原因而放棄對(duì)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的思考與批判。(中國(guó)現(xiàn)代文學(xué)館館長(zhǎng) 吳義勤)
從新時(shí)期之初的知青文學(xué),到后新時(shí)期的市場(chǎng)批判,同代人都轉(zhuǎn)身離去,只有梁曉聲以筆為旗,始終不渝,呼喊、堅(jiān)守、承擔(dān)。因?yàn)橛姓嬲娜柿x之道,他才可以那么愛(ài)憎分明,那么不留余地。(中國(guó)人民大學(xué)教授 程光煒)
作家分兩類(lèi):一類(lèi)服務(wù)于社會(huì),一類(lèi)服務(wù)于心靈。用心靈發(fā)展出的智識(shí),又反哺于社會(huì),或從社會(huì)發(fā)展出的智識(shí),透浸于心靈。梁曉聲有他那一代作家的顯著特點(diǎn),既勤奮又悲憫,在社會(huì)與心靈的總作用下替我們發(fā)聲,這尤要致以敬謝。我為其常識(shí)與智識(shí)所感動(dòng)。(《新周刊》主筆 胡赳赳)
作家梁曉聲是中國(guó)文壇的常青樹(shù),他開(kāi)了知青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先河,出版的一系列文學(xué)作品,深刻地展示了知青群體的痛苦與快樂(lè)、求索與夢(mèng)想,真誠(chéng)地禮贊他們?cè)谀婢持斜憩F(xiàn)出來(lái)的美好心靈與情操,為知青一代樹(shù)立起不屈的精神豐碑。 (人民日?qǐng)?bào)海外版)
生活中的梁曉聲低調(diào)、充滿(mǎn)溫情,但在爭(zhēng)取公權(quán)上,作為政協(xié)委員的梁曉聲是個(gè)斗士,聲色俱厲,直言上書(shū)。(《南方人物周刊》)
還沒(méi)有看但期待精彩內(nèi)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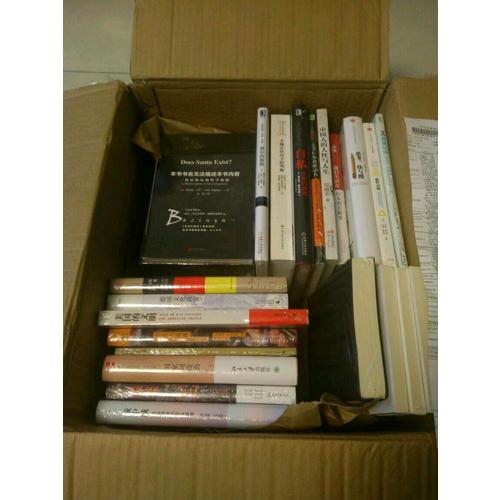 太棒了喜歡
太棒了喜歡
正版好書(shū),快遞給力,包裝好無(wú)破損,5分好評(píng)!
喜歡梁曉聲 作品
梁曉聲2017年重磅新作,深度解剖當(dāng)代中國(guó)人的文化心理與國(guó)民性!一部充滿(mǎn)人文理性的社會(huì)觀察實(shí)錄,直視人性的軟弱,更相信人性的尊嚴(yán)!
看完了收獲很多,可是自己的水平有限,有些內(nèi)容需要慢慢吸收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