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穿越西域前往天竺取經,歐洲中古學者為了意大利修道院的一卷珍本,要橫穿英吉利海峽,翻越阿爾卑斯山。如今,網絡提供了一種人類無法抗拒的便利,在彈指之間接近無窮的閱讀可能。
數(shù)碼時代,以"書"為載體的人類文明將走向何方?我們找來了這個星球上或許最有資格談論這一話題的兩人:安貝托?艾柯,讓–克洛德?卡里埃爾。一位是耀眼的百科全書式學者,享譽世界的意大利哲學家、符號學家、小說家;一位是電影泰斗、著名編劇、法國國家電影學院創(chuàng)始人。他們同是藏書家和珍本追蹤者,對書籍有深刻的理解,對各種文化載體在技術革命中的變局有敏銳的洞察。
當人類的一切視聽遺產都消失了,我們還可以在白天讀書,在夜里點根蠟燭繼續(xù)。書是人類的起點和終點,是世界的場景,乃至世界的末日。在過濾和傳承中,我們的文化是幸存下來的東西,還是所有從此消失的書的墓園?那些經世流傳的書,就是最值得留下來的嗎?我們如何為后代做出選擇?為什么說人對過去的認知歸功于傻子、呆子和敵人?互聯(lián)網時代我們將如何面臨知識的改變?……
歐洲兩位最重要的知識分子,充滿奇思異想的淵博對談。關于書籍的秘密,關于知識的真相。
[兩位重量級知識分子,充滿奇思的淵博對談]當艾柯遇上卡里埃爾,這兩顆博學驚人的頭腦必得上天入地,暢所欲言,碰撞出眼花繚亂的精彩觀點。從史前洞穴壁畫到達芬奇的奧秘,從各種象形文字到計算機編碼,從17世紀的真人版"萬維網"、德國天才學者基爾歇到丹?布朗,從耶穌、佛陀到狂熱異教徒的教義……展開一場富于機智、充滿創(chuàng)見、熱情洋溢的書籍歷史之旅。
[關于書籍的秘密,關于知識的真相]我們架子上的書,全世界圖書館里的書,包含了人類自書寫以來積累的知識與夢想的書,究竟是什么?書一定是進步的象征嗎?它究竟在對我們說些什么?兩位藏書家、珍本獵取者和知識分子,探索書籍這一文化載體在人類文明進程中的前世、今生和未來。透過書的歷史,尋訪文明的歷史。
[數(shù)字閱讀時代,書的命運與變局]玄奘穿越西域前往天竺取經,歐洲中古學者翻過阿爾卑斯山求取珍本,今天我們如何看待網絡時代的閱讀便利?書寫的普遍數(shù)字化和電子閱讀給書籍帶來極大挑戰(zhàn),艾柯與卡里埃爾將書籍看作倔強的幸存者,在淵博學識的輕松外衣之下,討論人類面臨的深刻劇變。他們對書籍的幸與不幸的揭示,有助于我們深刻理解這些眾所周知的變化。
[向人類這一半天才、半愚昧的造物致敬]若要對人類的奇遇有所領悟,就不僅要通過人類的輝煌,還要通過人類的失敗。在這里,兩位對談者圍繞記憶展開出色的即興言談,從各種難以彌補的失敗、缺陷、遺忘和損失說起,從虛假、錯誤甚至愚蠢的書籍說起——所有這一切,與我們的杰作一起,成就了人類的記憶。他們津津樂道地揭示,書籍盡管遭到各種審查的迫害,終還是得以穿過那張開的大網,這有時是好事,有時卻可能是壞事。
安貝托·艾柯(Umberto Eco),享譽世界的哲學家、符號學家、文藝批評家和小說家,21世紀最耀眼的一位百科全書式學者,少有的將精深學術與玄奧著作變成暢銷書的作家,作品被翻譯成30多種文字。代表作有《玫瑰之名》、《福柯擺》、《布拉格墓園》、《美的歷史》、《無限的清單》,等等。1992–1993年任哈佛大學諾頓講座教授,其講演結集為《一個年輕小說家的自白》出版。
讓-克洛德·卡里埃爾(Jean-Claude Carrière),法國著名作家、電影泰斗、國家電影學院創(chuàng)始人,《布拉格之戀》、《鐵皮鼓》、《大鼻子情圣》、《屋頂上的輕騎兵》、《白日美人》等80多部經典電影劇本的創(chuàng)作者,電影大師布努埃爾最青睞的編劇,1972年龔古爾文學獎得主。
前言:艾柯與卡里埃爾相遇的意義
書永遠不死
長期載體最暫時
母雞用一世紀學會不過街
說出滑鐵盧所有參戰(zhàn)者的姓名
被過濾者的報復
今天出版的每本書都是后印刷初期珍本
那些非到我們手里不可的書
我們對過去的認知歸功于傻子、呆子和敵人
虛妄所向無敵
愚蠢頌
互聯(lián)網,或"除名毀憶"之不可能
火的查禁
所有我們沒讀過的書
圣壇的書和地獄的書
人死后他的藏書怎么辦
譯后記:網絡與書籍——蘇格拉底的預言
"電影和收音機,還有電視,絲毫沒有取代書,除了那些書"毫無損失地"丟掉了的用途。
在某個特定時刻,人類發(fā)明了書寫。我們可以把書寫視為手的延伸,這樣一來,書寫就是近乎天然的。它是直接與身體相連的交流技術。你一旦發(fā)明了它,就不可能再放棄它。這就好比發(fā)明輪子一般。今天的輪子與史前的輪子一模一樣。相比之下,我們的現(xiàn)明,電影、收音機、網絡,都不是天然的。
書就如勺子、斧頭、輪子或剪刀,一經造出,就不可能有進一步改善。你不能把一把勺子做得更像勺子。書多方證明了自身,我們看不出還有什么比書更適于實現(xiàn)書的用途。也許書的組成部分將有所演變,也許書不再是紙質的書。但書終將是書。
想想2006年7月紐約那次電力大故障吧。假設范圍擴大,時間延長。沒有電,一切都會消失,無可彌補。反過來,當人類的一切視聽遺產都消失了,我們還可以在白天讀書,在夜里點根蠟燭繼續(xù)。20世紀讓圖像自己動起來,有自己的歷史,并帶有錄音——只不過,我們的載體依然極不。
書寫載體多種多樣,石碑、長板、錦帛。書寫本身也多種多樣。然而,我們感興趣的不僅是載體,更是這些殘章斷篇所傳達的信息,從某個我們幾乎無法想象的古代流傳而來。
科技更新的速度迫使我們以一種難以忍受的節(jié)奏不斷重建我們的思維習慣。每兩年必須更新一次電腦,因為這些機器就是這么設計生產出來的:過時到了一定期限,維修比直接替換更昂貴。每種新科技都要求人們更新思維模式,不斷作出新的努力,而更新的周期也越來越短。母雞可是花了將近一個世紀才學會不去過街。它們最終適應了新的街道交通狀況。但我們沒有那么多時間。
我們處于運動、變化、更新和轉瞬即逝之中,矛盾的是,我們的時代卻是一個越來越長壽的時代。
一位歷史學家也許可以查出滑鐵盧戰(zhàn)役所有參戰(zhàn)者的姓名,但中學和大學不會教這些,因為這樣的細節(jié)沒有必要,甚至可能很危險。
知識塞滿我們的腦袋,卻不總是有用。認識則是把一種知識轉化為生活經驗。也許我們可以把不斷更新知識這個任務交給機器,而把精力集中在認識之上。我們只剩下智慧——多么輕松!
一種文化若不懂得過濾過去幾個世紀的遺產,就會讓人想到博爾赫斯在《博聞強記的福內斯》中的人物福內斯,那個能記住一切的記憶專家。這恰恰與文化背道而馳。文化是所有從此消失的書和其他物件的墓園。
夏多布里昂的《墓中回憶錄》一開始是秘密寫的,在他生前只發(fā)表一小部分,而且是很久以后。當時給他帶來榮譽的小說如今都不堪卒讀。這是一個過濾的奇特例子:他為眾多讀者寫的東西被我們丟開,他單獨為自己寫下的作品,卻讓我們心醉神迷。
現(xiàn)在有一種葡萄酒,就是"沒過濾的"。它保留了所有殘渣,有時帶來一種非常獨特的風味,一經過濾就被去除。也許,我們在學校里品嘗了一種過度過濾的文學,以至于喪失了這種不純粹的風味。
一個作家若想避免被過濾,那么他好聯(lián)合、參與某個小群體,而不要保持孤立。莎士比亞之謎在于,人們不能明白,為何單單一個演員就能創(chuàng)造出如此天才的作品。
透過書的歷史,我們可以重建文明的歷史。對于"書的宗教"來說,書不僅是海納一切的容器,更是一只"廣角鏡頭",透過鏡頭我們可以觀察一切,講述一切,甚至決定一切。書是人類的起點和終點,是世界的場景,乃至世界的末日。
基爾歇的學問觸及那個時代的一切認知領域。我們甚至可以說,早在網絡產生以前,基爾歇就是某種形式的網絡。他無所不知,而在他的知識里,一半正確,另一半則是謬誤或空想——這種比例似乎接近我們在電腦屏幕上的搜索結果。
在《詩學》中,亞里士多德提起至少二十部悲劇,我們今天對它們一無所知。真正的問題在于:為什么只有索福克勒斯和歐里庇得斯的作品流傳下來?它們好、最值得流傳后世嗎?或者它們的作者費盡心思,以便取得同時代人的認可并淘汰其他競爭者,也就是亞里士多德提到的那些作者,而歷史本該記住這些人的名字?
達芬奇畫過比這個更美的作品,比如《巖間圣母》和《抱白貂的女子》。但《蒙娜麗莎》得到了更多的詮釋,這些詮釋猶如沉積層,和時光一起沉淀在畫里,并改變了畫作本身。
我們不要指望擺脫那些虛假、錯誤的書籍,甚至那些愚蠢的書籍。它們將如忠實的影子,追隨我們直到一刻,毫不欺瞞地講述我們曾經是——尤其我們現(xiàn)在還是——熱情、固執(zhí)但毫無顧忌的探索者。
從前玄奘要穿越西域,前往天竺取經,歐洲中古學者為了意大利修道院里的一卷珍本,要橫穿英吉利海峽,越過阿爾卑斯山;如今,網絡在彈指之間提供了近乎無窮的閱讀可能。古人在抄寫經文時會小心翼翼地依樣照抄前人筆誤,手抄本上的一個筆誤也會得到膜拜;如今人們一邊懷疑著網絡上未加分辨和過濾的信息,一邊又隨時隨地有條件添上新的信息。這是人類的進步還是退步呢?無論如何,謬誤和愚蠢像影子一般忠實地追隨著我們。但有一點大概可以確定,網絡與書籍并不是非對立不可。
我們通過艾提烏斯的作品了解了前蘇格拉底哲人的不少殘篇,艾提烏斯卻是個徹頭徹尾的傻瓜,只需讀一讀他的筆記就清楚了。因此,我們大可懷疑他的記載是否忠于前蘇格拉底哲人們的精神。還有愷撒筆下的高盧人、塔西陀筆下的日耳曼人,我們多少了解這些民族,恰恰是借助他們的敵人的記載。
我們對過去的認知往往來自書本,因此也就歸功于傻子、呆子和狂熱的敵人。仿佛過去的痕跡消失,要重建過去,只能借助這些文學瘋子的作品,這些不可信的天才。
我們當年發(fā)現(xiàn)了亞述人最早的圖書館,但對楔形文字一無所知。人類始終面臨丟失和毀滅的問題。挽救什么?傳達什么?如何傳達?如何確保今天使用的語言能在明天、后天依然被理解?一種文明若不向自身提出這個問題將是不可想象的。
這是愚昧史上的另一篇章。"也許是我理解力有限,但我不明白為什么要花三十頁的篇幅描述一個人在床上輾轉難眠"——這是普魯斯特《追憶逝水年華》的及時份閱讀報告。對《白鯨》:"這類作品很難有機會吸引年輕讀者。"對福樓拜的《包法利夫人》:"先生,您把您的小說埋藏在一堆雜亂的細節(jié)之中,這些細節(jié)雖然描寫得不錯,卻純屬多余。"對艾米莉?狄金森:"您押的韻全錯了。"對喬治?奧威爾的《動物莊園》:"在美國根本賣不動一本動物故事書。"
我們對書總是有一種崇高的理念,我們自愿將書神圣化。然而,事實上,只要認真觀察我們的書架,就會發(fā)現(xiàn)有相當驚人的一部分書出自毫無才華的人之手,要不就是傻瓜或瘋子。
人類是一種不可思議的造物。他發(fā)現(xiàn)火,建就城市,創(chuàng)作美妙詩篇,解釋世界萬物,創(chuàng)造神話形象,等等。然而,與此同時,他從未停止與同類戰(zhàn)爭,鑄下大錯,毀壞環(huán)境。在高等心智與低級愚蠢之間的平衡,最終形成某種近乎不好不壞的結果。因此,當我們決定談論愚蠢,從某種意義來說,我們在向人類這一半天才、半愚昧的造物致敬。
為什么只關注智慧、杰作和精神豐碑的歷史?在我們看來,福樓拜所珍視的人類的愚蠢要普遍得多,這是顯而易見的。愚蠢更豐富多產,更具啟發(fā)性,在某種意義上,更公正。
比如古羅馬人想出來的"除名毀憶"之刑。"除名毀憶"由元老院投票表決,判處某人在死后處于默默無聞和徹底遺忘之中,也就是將他從官方名錄中刪除,銷毀他在公共場所的雕像,或將他的出生日宣布為兇日。話說回來,在斯大林時代,人們也干過類似的事,把某個被放逐或遭暗殺的領導人從照片里抹掉。今天要想讓某個人從某張照片上消失可就困難多了,人們很快就能在網上找到原本的老照片。消失者不可能消失很久。
某個"輝煌一時"的人物被我們不知不覺地淡忘。他自行消失,毫不引人注意,去了黑暗王國。某個人走出我們的記憶,被緩緩驅逐出我們的歷史書,我們的談話,我們的紀念,就好像他從來不曾存在過一樣。
沒有文字書寫的人就是沒有被命名的人。沒有被傳述(即便是錯誤地傳述)的人,他們沒有存在,即便他們的黃金精美絕倫。要想讓人記住你,就必須寫下東西。書寫,同時謹防寫下的東西消失在某個火堆之中。我有時會想,納粹在焚燒猶太人的書時腦子里都想些什么。他們會以為自己能把這些書全部銷毀,一本不剩嗎?這樣的行為除了是犯罪,豈非也是一種烏托邦的空想?
我走上前去,想看看他在燒什么書,只在那些翻開的書頁里辨認出數(shù)學圖形和公式。這也許是剛剛改變信仰的奴仆在焚燒古希臘的科學書籍。這個場景實在觸目驚心。信仰到來了,人們開始焚燒科學。這不只是過濾,這是用火焰來清算。直角三角形斜邊的平方必須永遠消失。
當有人問我是否讀過這本或那本書時,我出于謹慎總是這么回答:"您知道,我不讀書,我寫書。"這樣一來,所有人都會閉嘴。但有時還會有人堅持不懈地提問。"您讀過薩克雷的小說《名利場》嗎?"我最終屈服了。連續(xù)三次我試著讀這本小說,每次都半途而廢。
我直到四十歲才讀了《戰(zhàn)爭與和平》。但我在閱讀以前就了解這部小說的精髓。你剛才提到《摩訶婆羅多》:我從沒讀過,雖然我收藏了三種語言的三個版本。誰從頭到尾讀過《一千零一夜》?誰真正讀過《愛經》?但人人都在談論它,有一些還加以實踐。這個世界上充滿我們沒讀過卻幾乎無所不知的書。
無知就在我們四周,無處不在,往往還狂妄自大。無知甚至滋生使人瘋狂的熱忱。它充滿自信,借政客的小嘴慷慨陳詞,儼然勝券在握。相形之下,知識脆弱,易變,永遠受威脅,懷疑自我。知識無疑是烏托邦式理想的一處避難所。你認為知識真的重要嗎?
在這些公共大圖書館里,有一樣東西總讓我著迷:綠色的燈罩投射出一個明亮的光圈,光圈的中心總是有一本書。你有你自己的書,與此同時,你還被全世界的書所包圍。
我很少把藏書展示給別人看。藏書是一種手淫現(xiàn)象,只屬于個人,很難找到能夠分享同一激情的人。你若收藏美輪美奐的畫,人們會紛紛前來欣賞。但沒有人會真的對你的舊書藏品感興趣。他們不理解你為什么要如此看重一本毫無吸引力的小書,并傾注多年心血去尋找它。
……
梁文道——我看到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別想擺脫書》,這本書是歐洲兩個重量級的知識分子意大利的艾柯和法國的卡里埃爾的對話,談的是書的歷史和命運。艾柯是一個超級的書迷,而且艾柯本身是很出名的藏書家,他在意大利的大學里面,他的研究室里面的書多到嚇人的地步,而且古籍收藏非常成名。另外一位也是法國有名的作家。這兩位聚在一起談話,大家開始覺得書這個東西快完蛋了……到底電子書會怎么樣改變紙質書的命運?
梁文道——艾柯認為,即使我們會有越來越多的電子閱讀器,但書這個東西是一個非常好的發(fā)明,是不能被改進、不會被替代的發(fā)明。就像剪刀、車輪或者勺子一樣,這些東西自從問世之后,就幾乎沒怎么變過,我們一直在使用,也不嫌它們落伍,也許需要小修小補,但整個形態(tài)上的大規(guī)模的變化是不必要的。
楊葵——聽不少人夸一本書好,說是越讀越慢,因為舍不得讀完。我想分享一下自己對待好書的讀法:非但不能慢,反而需越讀越快,快速讀完及時遍,翻回頭再讀第二遍,第三遍。如此能讀到蕩氣回腸。不妨試試。二十多年前,哥倫比亞作家馬爾克斯和記者門多薩的對話錄《番石榴飄香》,曾享受我這一讀法。最近又有一本對話錄,被我照此閱讀,就是意大利作家艾柯和法國編劇卡里埃爾的談話錄《別想擺脫書》。
楊葵—— 一直覺得,好書的一大特點是不拿讀者當學生,跟你玩填鴨式教學;它會拿你當朋友,和你一起討論、商議,觸發(fā)你去反思自己一些早已固定的思維,進而可能就會先破后立,建立起對事物全新的、更通達自如的一些認識。《別想擺說書》里,這類的段落太多了。
陳平原——坊間有不少"閱讀學"方面的書籍,熱衷于討論閱讀的起源、意志、目標、心境、方法、品質等,在我看來,這些書意義不大。還不如讀一點"關于書的書",略具紙張、印刷、書籍、古書版本、歷代藏書,以及現(xiàn)代報刊和圖書館業(yè)的知識,那樣對于養(yǎng)成讀書習慣更有好處。安貝托?艾柯與讓–克洛德?卡里埃爾對話,討論書籍對人類文明進程的影響,以及網絡時代紙本書的未來,結集成了《別想擺脫書》。這兩位嗜書如命的古書珍本愛好者,其對話及時部分的標題是"書永遠不死"。
外觀感覺一般吧 本來以為很大的一本書 結果這么小 而且有一股濃烈的味道 表面有壓痕和劃痕
值得一看,方法論,世界觀,可以得到不同的補充,修正。
兩個老人,在敘敘舊的時候會不經意間聊起了對當今文化的感想。那是老一代人對文化的看法了。卻是整個時代都要去看重的一頁思想史。
最近迷上了對話錄,發(fā)現(xiàn)人的智慧火花都是在與人討(爭)論(辯)中產生,古有百家爭鳴、舌戰(zhàn)群儒,西有各種XX談,對話錄,中外古代先哲似乎都有提個問題就讓學生各抒己見的教育習慣,現(xiàn)在的很多大學也開始引入這種討論式的教學模式,比起先入為主的單一學派的理論著作,能夠采納百家之長但并非漫漫而談的書實在少見。當然,被這本書吸引的理由只有一個:別想擺脫書——偉大的書永遠活著,和人類一起成長和衰老,但從不死去。類似的格言也有:法律有時入睡,但絕不死亡。文明也是如此。雖然網絡提供了人類無法擺脫甚至上癮的便利,很多書也漸漸從現(xiàn)實里消失,越來越多的…
艾科的書必需的,感覺相當不錯,需要慢慢地閱讀和欣賞
靈魂大師們的對話,在大師們的對話中思考書的世界。
西方文論老師推薦的,不過看起來難度挺大的,需要一定的西方文化知識
世界兩大作家的對話,我們永遠不可能離開書籍!
理想國的這類書都是我喜愛的,基本都買了,不知道給不給我這種忠實粉絲送送書或者交流交流啥的。
看了書名,得到安慰,我的滿屋子書,都有了存在的理由
對于和書相關的書,一下子買了幾本來看。這本文學理論性稍稍強些,需要靜下心來好好看的哦
通過兩位大師的對話,我們真的能夠體會,書籍我們是無法擺脫的了……很受啟發(fā)……
我很關注有關讀書方面的書籍,看看讀書人是如何看待讀書的。
別想擺脫書:艾柯&卡里埃爾對話錄(精譯版)(陳丹青、陳平原、楊葵、梁文道、熊培云都在讀的書)
自買書以來就一直在當當,發(fā)貨快,一般都是當日下單次日送達。書質量也很好,買了很多還沒有閱讀,留著慢慢看。
艾柯說,書像勺子、輪子一樣,一旦造出來就臻于完美,不必改善。這句話說得智慧、深情,深深地感染了我,給了我信心。
剛拿到手里比想象中的小,但翻書頁的時候又覺得就該是這樣,像是本小記事本,我看著里面睿智的對話
艾柯和卡里埃爾的對談錄。讀過《玫瑰的名字》的人應該都想讀一下艾柯其他作品吧。
讓-克洛德·卡里埃爾和安貝托·艾柯作為這些探索過程中的意外事件的饒有興趣的觀察者和記錄者,深信我們若要對人類的奇遇有所領悟,將不僅通過人類的輝煌,也將通過人類的失敗。在此,他們圍繞記憶展開出色的即興言談,從各種難以彌補的失敗、缺陷、遺忘和損失說起——所有這一切和我們的杰作一起成就了人類的記憶。他們津津樂道地揭示,書籍盡管遭到各種審查的迫害,最終還是得以穿過那張開的大網,這有時是好事,但有時卻可能
別想擺脫書,對這個書名很感興趣呢,應該還不錯吧。
關于書的書也真是很好看,一直在買各類相關的書話
無論從哪一點來看這本書,都無可挑剔的好!只是,我擔心國內的讀者對于本書種的觀點會形成一個小眾化的群體認知!這是因為中國的普遍民族文化素質并不是很高決定的!
在談論紙質書籍方面,最能給我信心的正是這本艾柯和卡里埃爾的對話集。我一直喜歡紙質書,現(xiàn)在是越看越領略到傳統(tǒng)書籍的魅力。書是不會消亡的,它給我的遠超電子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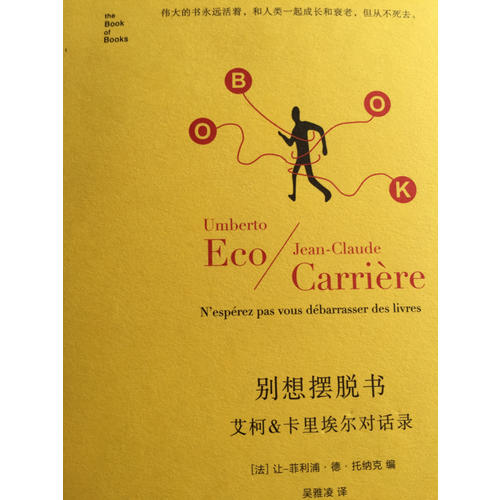 喜歡~ 我女神推薦的書啊,偉大的書永遠活著,和人類一起成和衰老,但從不死去。書真的重要么?知識真的重要么?重要啊!超級喜歡 ~紙質一般 。
喜歡~ 我女神推薦的書啊,偉大的書永遠活著,和人類一起成和衰老,但從不死去。書真的重要么?知識真的重要么?重要啊!超級喜歡 ~紙質一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