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諾反復出入《左傳》的世界,一次次試圖走入子產、趙武、申公巫臣乃至孔子、左丘明等歷史人物的內心世界,探索春秋時代杰出的頭腦在其時其地究竟看到、想到了什么,他們某一言行究竟有著何種深遠的積淀與思考,從而認出藏在歷史縫隙里好的人好的事,也讓春秋時代呈現出一個更為復雜深邃、立體可感的世界。情欲之事、鬼神之說、弭兵之會、小國家的大靈魂、兩千多年前的夢、春秋戰國的繁花般思維……由此出發,作者旁征博引,以文學的視角,圍繞八個問題進行叩問和延伸,令人驚嘆地將實然歷史變成哲學思索的場域,陳舊的千年文本開始蕩漾進此時此刻,是為《眼前》。
像是安排一趟遠行,設定的目標是《左傳》,想辦法在那里生活一整年,不一樣的人,不一樣的話語,不一樣的周遭世界及其經常處境,不一樣的憂煩和希望……遠游回來,就是這本《眼前》了,我的讀《左傳》之書。
我設想每個人的視線都是一道道光、一次次的直線,孤獨的,能穿透也會被遮擋,能照亮開來某個點、某條路徑卻也總是迷途于廣漠的幽深暗黑空間里時間里——春秋時日那些人的眼前,《左傳》作者的眼前,我的眼前,我希望能把它們疊放一起;我想象這些縱橫四散的直線能相交駁,這樣我們就可望得到一個一個珍罕的定點,知道自己身在何時何處,這也是基本簡單的“定位”方式。
左傳》這樣一部破舊沉厚的闔上之書,仍讓我感覺蓄著風雷,有我還不知道以及永遠不可能知道的某些東西,好像還聽得到遠方隱隱滾動的雷聲。
——唐諾
談NBA、談推理、談文字、談文學之后,唐諾回歸歷史書寫。當唐諾看球,他寫出的球評讓他一炮而紅,連不看球的人也讀;當唐諾讀枯燥的文字學,寫出《文字的故事》,浩瀚篇幅天馬行空讓人無法自拔;當唐諾看推理,他的推理導讀風靡海峽兩岸,“借由用腦子、秀的小說,把讀者誘拐上另一個層次”。這次,臺大歷史系畢業的唐諾終于回歸“本行”,用一年時間漫游在《左傳》的世界,這位“專業讀者”會看出什么?史書從來就不只是事實的倉庫,書寫者與被書寫者都有其特定的處境、思考乃至不得已,當文字空間只剩下一枚竹簡的大小,強調與忽略之間的抉擇,本身就意味非常。
以文學眼光讀史,認出藏在歷史縫隙里的人與事。人類的歷史是一本瘋子的日記,人類所曾擁有的東西、人的樣子都不會在這里,愈認真讀史,愈讓人滿心沮喪荒敗。而文學有著“可以說一些稍稍過火的話”的寬待,唐諾以文學的眼光讀史,講出獨特的進一步話語,把眼光從歷史的主線移開來,離開政治、現實成敗的焦點,去發現那些微光閃爍于各個角落的的人與事。
一樣的唐諾,不一樣的歷史散文書寫。唐諾的文字素有博議體、大散文、信馬由韁、旁征博引等等標簽,它自有一種力量把人帶到遠方再拉回來。此次重讀《左傳》,唐諾用八篇散文,二十萬字,探究春秋時代杰出的頭腦,他們的視野和想象,他們的處境、選擇以及限制。路途雖然遙遠,唐諾的文字依然從遠方傳遞微光至當下,同時擊碎當下直抵遠方。
唐諾
本名謝材俊,一九五八年生于臺灣宜蘭,畢業于臺灣大學歷史系。
曾與朱天文、朱天心等共組著名文學團體“三三集刊”,后任職出版公司數年。
近年專事寫作,曾獲多種文學獎項,朱天文譽之為“一個謙遜的博學者、聆聽者和發想者”。
2013年出版散文力作《盡頭》,探索極限和人的現實處境,獲評《亞洲周刊》年度十大好書與臺灣金鼎獎。
(自序)信它為真,至少先這樣
為什么會是子產?
來想象一個作者
兩千多年前的一個夢
左傳》的情欲亂倫之事
一場盟會、一個國君和一個老人
很荒唐的戰爭
音樂,或者,樂
船身上的刻痕
(自序)信它為真,至少先這樣
上一本書《盡頭》,整整用掉兩年半時間,寫得很疲憊,也有某種出清之感,好像會的東西全部講完了(我每寫完一本書都有這一感覺,只是這回特別強烈特別真實),所以當時我說,接下來我要很輕快地寫出“小書”,看看還能否愉悅地叫喚出不同的什么—像是安排一趟遠行,設定的目標是《左傳》,想辦法在那里生活一整年,不一樣的人,不一樣的話語,不一樣的周遭世界及其經常處境,不一樣的憂煩和希望。我預想共八個篇章,八個話題,每個話題用一萬字左右講完。
所以,遠游回來,就是這本《眼前》了,我的讀《左傳》之書——惟一出錯的是字數,每一篇章都陡然地膨脹一倍有余,遂成為一本稍厚的小書。丟臉的是,我的一干友人對此好像全不意外,每個人都是那種“早就曉得一定會這樣”的有點氣人的漠然表情。
這本書有一參照之書,那就是博爾赫斯寫《神曲》的《有關但丁的隨筆九篇》,他五十歲左右的作品。我仿用的不只是他的書寫體例而已,更重要是他的書寫和《神曲》這一文本的“關系”,尤其是其中的信任關系。也就是博爾赫斯多次引用的詩人柯勒律治名言:“詩的信念,就是自愿地把不肯輕信的念頭高高掛起。”進一步明說便是:“當你下定決心不再懷疑,你就能讀到一本好書了。”——《神曲》寫出了我們今天或更不愿相信就是那樣的地獄、凈界(煉獄)和天堂,我們當然可以就此大大爭辯一番,但這勢必把我們困在這個可能是無止無休的話題里,而這只是《神曲》的設定或說背景而已,也就是我們根本還沒出發還沒真正開始,也就是詩本身;而且,當我們的心思集中在這樣的真假分辨上,我們就很難去聽但丁實際上說了什么,這是一定的。所以博爾赫斯說他寧可先相信但丁所講都是真的,好真的進入,“我認為有這種天真的觀念,即我們正在閱讀一個真實故事的想法還是合適的,它可以讓閱讀把我們牽住……至少在開始的時候應該這樣,好能跟上故事的線索。我想誰也不會拒絕這么做。”
這一回再讀《左傳》,我(已經過了五十五歲,比當時的博爾赫斯再老一些,及時次讀《左傳》是三十五年前,已經又多知道了不少事情,也清楚很多所謂的“事實”其實都是脆弱不堪的,更多時候只是一堆事件隨機的、暫時的搭建)也試著信《左傳》為真,先努力跟上書寫者的想法,以及他看到的、看著的世界變化。
信《左傳》為真,極可能比信《神曲》要稍微困難些而且多有顧慮,只因為《左傳》畢竟仍是歷史,有實人實地實事的更大抓地力及其種種緊張和要求;但我想,這也恰恰好意味著,人們更容易懷疑它從而遠離它,錯失掉它的大部分內容,更不必說那些必須認真一點、看著它久一點才會注意到、會浮現出來的東西。
懷疑是有益的健康的,當然如此,但懷疑跟所有的東西一樣,仍受制于邊際效益遞減這一無情的法則,時間一久(比方持續一百年兩百年),其效益會逐漸窮盡、歸零,甚至成為負數,并顯露出一種蒼老的殘暴(如“思想初生時是溫柔的,當它蒼老時卻總是殘暴的”);而懷疑另一個通則般的特質是,它一向比較容易,人甚至不必準備什么,只要學會說“不”就行了。容易的東西不見得不對,但總是一下子來得太多需要打掃清理,還往往固著為一種習慣,也僅僅只是個習慣而已。
信《左傳》為真,倒不是拒絕日后歷史研究(包括人類學考古學的有益加入)對這本書,以及它所講述那個時代的更正確發見及其必要更正(事實上這已不知不覺成為一個認知基礎,我們都站在這一修正過的基礎上),只是除此而外不急著懷疑而已——對所有未經證實為誤的東西,對那一整塊最該要人沉靜下來的寬廣灰色地帶,最有意思的東西都在這里。還有,就是不讓無謂的懷疑分神,不讓懷疑弄得自己寸步難行,扯毀掉一整個圖像、一個時代的可能完整面貌。
真假對錯自有其更深沉的意思和更多面向,尤其在縱橫交錯的歷史里,更多時候它只是不足、不完整以及人不那么恰當又難以遏止的想象力而已。理論(基于某種一以貫之的基本要求)往往容納不下它,甚至文字都還裝不住它們,只有人心、夠堅韌的人心還勉強可以,因此成為必要,否則,在最終的揭示到來之前(也許永遠不會來),我們就再找不到另外的地方完整地存留住它。于此,惠特曼愉快地宣稱,也許太輕快了些:“你說我自相矛盾,我當然是矛盾的,因為我心胸寬闊。”但也正因為惠特曼的如此興高采烈,讓我們頗清楚看出來,這里面,有一種很特別的自由,一種不被懷疑倒過來抓住、限制的自由,一種不必動輒舍棄、得以窺見世界較完整形貌的自由,一種人可往四面八方而去、向各種遠方各個深處的昂然自由。
把《左傳》當一個文本,信任這本書,讓書寫向著這本書而不直接是那個時代,連同它的選擇,連同它的所有限制,這一轉折因此也有多出來的可貴東西——如列維-斯特勞斯說的,不只是人們做了什么,還有他們相信什么,或者認為什么是必須做的。“它可以是發生在實證領域中的事物,也可以是一些人在思想上經驗著的東西,盡管這些人在觀察他們自己的感性材料時不免有失偏頗,但他們的意愿在于發現什么是恰當行為的規定性。”
也可以這么說,較完整的人乃至于人的歷史,應該包括他所做的和他所想的(“在思想上經驗著的東西”,說得真好);還有,在“做”與“想”的反復交錯之間出現的種種參差、延遲、落差和背反;還有,對此結果又再發生的進一步感受、反省和思維。
人究竟在想什么?能想什么?
這本書,反反復復想過不少書名(我一直是那種認為書名不是太重要、認為書名總有虛張聲勢之嫌的人),最終才決定就叫它《眼前》——復數的眼前,眼前加s,眼前們。很多人,包括站不同空間位置乃至于不同時間里的人,子產的、趙武的、叔向的、夏姬和申公巫臣的、宋襄公秦穆公楚莊王的,以及孔子的云云;還包括《左傳》作者的眼前、兩千多年后我自己此時此地的眼前。每個人都有他看著的東西,有他想望和擔心憂煩的東西,有他對自身處境的種種察知和猜測,不得不做的猜測。
楊照,這位我愈來愈佩服的書寫者、不懼也不懈的解說者,和我是高中和大學歷史系的前后期,后來還去了哈佛繼續史學之路,擁有我缺乏的嚴謹史學根基。《盡頭》寫完后,楊照曾在他的廣播談話時問我:“為什么從不考慮寫歷史方面的東西?”現在回想起來,楊照應該是已知道我打算以《左傳》為下本書的對象,做球給我,是主持人的技巧。我當時魯鈍地不察覺,只模糊地回答他,當然也都是真心話:也許,如今寫實然世界的東西太多了,實存變得太理所當然,也占去了幾乎所有的可能空間,我趨向于多想一些應然層面的東西;還有,也許年紀大了,讀人類歷史愈來愈不愉快……
今天,依我自己看,這本《眼前》仍是“文學類”的。
書寫規范上,我們給了文學多點寬待,允許它說一些稍稍過火的話,但這并非沒代價;我們會追討其成果,要求文學講出進一步的話語,提出它獨特的、通常是一個個具體而專注的發見——每一種書寫體例都有它的“報稱性”,這在書寫各自進行的漫長如河時間里自自然然地形成,其實仍是公平的。
我設想每個人的視線都是一道道光、一次次的直線,孤獨的,能穿透也會被遮擋,能照亮開來某個點、某條路徑卻也總是迷途于廣漠的幽深暗黑空間里時間里——春秋時日那些人的眼前,《左傳》作者的眼前,我的眼前,我希望能把它們疊放一起;我想象這些縱橫四散的直線能相交駁,這樣我們就可望得到一個一個珍罕的定點,知道自己身在何時何處,這也是最基本最簡單的“定位”方式。
每寫完一本書都不得不緩緩告別自己一些東西,像雷蒙德 錢德勒所說的“漫長的告別”那樣。我的這本《左傳》,墨綠色布面精裝,是完整《十三經注疏》的其中一冊,我大學二年級時發狠一次買齊,存了不少時候的錢,在那個比較窮的時代和年紀。我還記得它的嶄新模樣,“嶄新得如一個新月,一副新牌”。三十幾年后,它已開始解體了,靠著布質纖維不絕如縷才讓封面不致脫落。還會像從前那樣一而再地讀它嗎?這樣一部破舊沉厚的闔上之書,仍讓我感覺蓄著風雷,有我還不知道以及永遠不可能知道的某些東西,好像還聽得到遠方隱隱滾動的雷聲。現在它就躺在咖啡館桌上我的手邊,不知道是巧合而已還是有著另外的奇妙原因,我最近幾本書總是結束在這樣天氣轉涼的時日,我無來由地想起這一句歌詞:“時間像開玩笑一樣地過去了。”真的,時間的確像開玩笑一樣地過去了。
我今天已經很少見到有人這么純粹、這么用心地來經營散文。
——梁文道
唐諾所依恃的,是他近乎無涯岸的雜學知識,出入不同文本的綜理能力,一次又一次找來或熟悉或陌生的引文例證,如海浪般彼此推擠涌動,構成一幅幅教人目不暇接的風景。
——楊照
不錯的書籍,全家行動,大人小孩一起看書。
左傳系列 非常好的書籍 有意思 推薦給大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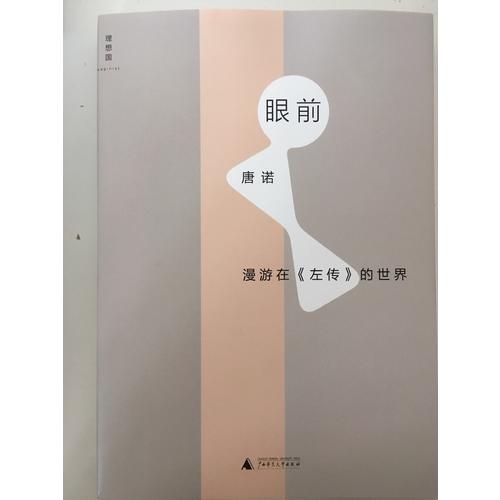 好好好好好
好好好好好
很好,喜歡
像是安排一趟遠行,設定的目標是《左傳》,想辦法在那里生活一整年,不一樣的人,不一樣的話語,不一樣的周遭世界及其經常處境,不一樣的憂煩和希望……遠游回來,就是這本《眼前》了,我的讀《左傳》之書。
Satisfied
值得一看呀,
依舊是唐諾式的“文字轟炸”,信息量爆炸;唐諾的書是無論看多少遍,都能發現你需要繼續補習解的信息。
到貨時書脊處有磕碰,換了一本還可以。初次看帶有臺灣腔的作品,雖不習慣,但是正好開開眼界
內容和角度很有結合度,將故事的前后左右,描述的剔透,同時,還有一定的考慮和思考
活動入,書籍素雅,廣西師大出版社的書還是有品質保證的。
在難懂的文言中看到有趣的細節,讓人欲罷不能,值得一讀
唐諾的文字不太接地氣,博學有見識,也給人以啟迪,但這種表述方式,我是不喜歡。臺灣的幾位作家我都不喜歡,朱家三姐妹等
 以前大學時就喜歡《左傳》,此書我一定會細細品味。隨后再來分析一下
以前大學時就喜歡《左傳》,此書我一定會細細品味。隨后再來分析一下
好看!好看!超級好看!重要的事要說三遍,文學少女們買起來啊
從書城看了文章才來買的,果然收獲頗豐,眼前一亮
唐諾的書,非常值得一看,推薦大家閱讀,祝大家閱讀愉快
其實,很多內容陸陸續續看過,但是還是值得擁有。贊!
唐諾的散文從不錯過。有些繞和啰嗦,但是他的特點。
還沒有看完,感覺開不下去了,注水嚴重,只能跳躍性翻閱!
左傳不錯,書很不錯,活動很給力,作者的深度不錯,中華文化博大精深,下次還來
一年時光,一次重讀,八篇隨筆,八次綿延曲折的叩問與思索
唐諾的書總是非常讓人期待。這是第一次讀到他的歷史書。
前陣子唐諾來了廣州方所,雖然主要是陪妻子天心作新書宣傳。唐諾的書值得推薦
以哲學家的視角看左傳,入于其中,出乎其外,思想性、知識性、藝術性兼備。不能更贊了!!
文筆優美,行文流暢,但并非歷史科普書,而應是屬于歷史讀后感,適合大眾讀物,需要有一定歷史知識積累,建議配合《左傳》閱讀。
唐諾的書,沒有看過幾本。主要是對暢銷書有抵觸。因為《左傳》,買了這本。感覺內容有新意,是讀《左傳》的另一個角度。語言雖生澀,也很有特點。
一樣的唐諾,不一樣的歷史散文書寫。唐諾的文字素有博議體、大散文、信馬由韁、旁征博引等等標簽,它自有一種力量把人帶到遠方再拉回來。此次重讀《左傳》,唐諾用八篇散文,二十萬字,探究春秋時代*杰出的頭腦,他們的視野和想象,他們的處境、選擇以及限制。路途雖然遙遠,唐諾的文字依然從遠方傳遞微光至當下,同時擊碎當下直抵遠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