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論文集共收錄14篇講演稿和1篇附錄。講演稿是羅蘭教授于2006年至2014年間,在北京、成都、泉州、貴陽、大理等地參加會議、舉辦講座、參與國家外國專家局項目的主要論文與講稿的譯稿;附錄是對羅蘭教授的學術專訪。這些文章盡顯羅蘭教授多年來在長時段史的人類學、物質文化與博物館研究等領域的研究心得。
邁克爾 羅蘭教授在人類學和物質文化研究領域聲名顯著,他對西方人類學文明研究做出了深刻的反思,并同中國學者一道在“文明”“物質性”等領域討論互動,進行了一系列深入對話。
聚焦“歷史、物質性與遺產”主題,契合我國當下已蔚然成風的物質與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運動,推動對我國博物館方向轉型的理解。
扎實的人類學知識,豐富的援引資料,一窺英國人類學務實而又進取之風范。
邁克爾 羅蘭,在1972年獲得倫敦大學考古學博士學位后,至倫敦大學學院任人類學講師,后于1992年成為物質文化研究教授,曾擔任倫敦大學學院人類學系主任。羅蘭教授的研究突破了民族、國家與區域的視野局限,并注重對各種文明體系的比較研究工作。作為一位卓有建樹的人類學家,羅蘭教授的學術成果豐富,著有《考古學中的社會轉型》《物質文化研究手冊》等。
自序
編譯者說明
上編 歷史、文明與人類學
從民族學到物質文化(再到民族學)
文明與非洲的一體性
長時段過去和斷裂
超越封閉文化: 中國境外的文明、區域和長時段的延續與斷裂
文明作為對照的宇宙秩序:西非與中國
作為宇宙統治之比照的文明
新石器化:從非洲到歐亞以及更遠之處
下編 物質性、遺產與博物館
器物之用:物質性的人類學探究
獻祭行為:對世界“之間性”的物質化
遺產、記憶與后殖民時代的博物館
對遺產與記憶的再思考
重新定義博物館中的物品:中國遺產的井噴
中國的新博物館時代到來了嗎?
“新型”民族志博物館:數字化遺產技術、社區參與及文化還原
附錄 物質文化與人類學:英國人類學家邁克爾 羅蘭專訪
從民族學到物質文化(再到民族學)
導論
1923年, 英國社會人類學奠基人之一——拉德克利夫-布朗(Radcliffe-Brown),撰寫了一篇在當時被認為劃時代的文章,他認為,民族學與社會人類學的區別,類似歷史與科學的區別。德英美三國的民族學,以歷史化(historicizing)或意象化(ideographic)的方式研究文化多樣性。新的社會人類學,則是一門對社會體系進行共時性、比較性、一般性研究的自然科學。
眾所周知,涂爾干的社會學讓社會人類學家脫離進化論和傳播論的人類文化起源說,并拒絕“原始遺存說”和歷史猜測。與任何奠基故事相仿,今天的人可能覺得那場分裂很嚴重。可是,研究“野蠻他者”的民族學,并沒有像人們想象的那樣迅速消失——尤其在東歐。民族學盡管不符合人類學的“社會學化”進程,但它在某些方面仍繼續發展。在斯堪的納維亞國家和德國的某些院系,民族學仍是一門研究民俗和農民遺存的學科。即使經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劫難,它也并未中斷,且延續至今,研究“日常生活”、國民身份、民俗(Volkskunde),并轉向流行文化a 研究。在美國,博厄斯派的人類學,從傳播論、歷史具體主義轉向了文化的心理學綜合。在20世紀60年代美國考古學實證主義的支持下,美國人類學經弗里德(Morton Fried)、斯圖瓦德(Julian Steward)和薩林斯(Marshall Sahlins)之手,演變為獨領風騷的新進化論。
但是在戰后歐洲,人類學卻發生了重大的轉向,非歷史化和民族志化消解了多數方法,民族學就是其中之一,以至于今天很多人類學家聽說民族學還是一個獨立學科,都會感到意外。今天的民族學,恰恰是拉德克利夫-布朗這樣的人類學家眼中的民族學。它通過博物館和人造物的收集,而不是民族志的方法,研究文化的多樣性。斯特拉森(Marilyn Strathern)曾令人信服地指出,社會人類學的興起使“物”的研究衰落,其結果就是,物不得不被放在社會語境中理解。她強調說,新幾內亞高原的哈根人,是用人造物創造語境的,人的存在并非理解意義的前提條件。同理,“原始藝術”的研究之所以在20 世紀60 年代變成了“藝術人類學”,就是為了突出田野工作的重要性,為了突出在社會與文化語境中觀察物品的重要性,而將處理博物館藏品的技能與理解藏品的技能分開。賓尼(Christopher Pinney)曾提出所謂的“金斯博格問題”(Ginzburg problem)——在視覺分析中,“歷史學家解讀通過其他手段了解的意象”。
民族學研究作為民族一體性資源之一的“民間文化”,并因此在歐洲某些地方得以保留,這背后顯然存在有趣的歷史。研究民眾生活的學者,受命收集和保存那些日常的、被忽視的物品,如烤鏟、鋤頭、擠奶凳。從農業工具、農場建筑,到家庭陳設,他們不知疲倦地為一切物件創造科學術語。他們相信,搶救正在消失的農民文化的任務十分緊迫:在廢棄的谷倉崩塌之前,要抓緊測量;在一塊公用地被圈占之前,要抓緊研究村落;在閣樓和棚屋的物品被遺忘之前,要趕緊收藏。他們插手每一個領域,尤其是與農民社會有關的物質文化。對于舊的人文學科如藝術、歷史、文學的同行來說,這種雄心很容易被視為可笑的或微不足道的。但是,對于印度“部落人群”和中國、前蘇聯少數民族研究來說,則未必如此。民族學對于19世紀印度種姓的種族化,或前蘇聯的民族發生學(ethnogenesis)一直有貢獻。但是,到了20世紀60年代,在歐洲社會人類學的核心地帶,民族學已經被分解成一個個最小單位,要么被“社會學化”,要么被排擠到博物館研究領域。在博物館研究中,1870 年到及時次世界大戰期間(即及時個博物館時代)收集的大量民族志物質文化藏品,已經喪失了傳播論或進化論的框架,物質文化和技術的研究于是發生了一場描述轉向。所以,物質文化和歷時性研究淡出人類學,并不一定是民族學受到了整體的學術批評,而是因為民族學作為一個有價值的研究領域消失了。
物質性怎么了?
在下面的講座中,我將回歸并重建民族學對大規模時空轉型和長時段歷史變遷的興趣。但是,我的討論將以物質文化為題。物質文化是民族學事業的另一個強有力的支撐,是對人造物的表象特征進行博物館收藏、分類和研究的工作。
眾所周知,雖然對博物館藏品的類型學研究與新興的社會人類學互不相干,但社會人類學并未忽視技術和物質文化,前提是要用田野工作的三棱鏡改造一番,使技術和物質獲得語境,如拉德克利夫-布朗對安達曼島人的觀察,或馬林諾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對珊瑚園圃及其魔法的觀察。但這意味著,要理解物品世界的物質性,就必須知道它們的社會語境,即人如何言說物品。因此,像哈登(Alfred Haddon)等人關于太平洋地區的魚鉤
或者旋架獨木舟的研究,只好躺在圖書館里無人問津。民族學成果(傳播論者眼中的人造物的時空形態變異)無非是“臆測歷史”,對于理解“社會如何整合”這樣的功能主義問題沒有貢獻。
當前物質文化研究在人類學和更大范圍的復興,并沒有保障要重新研究宏大的時空變異。例如,米勒(Daniel Miller)在一本研究物質性的專著的導論中,這樣定位物質文化研究的主旨:理解物的世界如何制造人,以及人制作了什么a。他將物品化(objectification)的研究與布迪厄的著作聯系起來,批評社會人類學將物質世界簡化為社會的解釋。他強調,社會區隔(socialdistinction)實際是對物質做選擇的后果。他對消費的研究,很大程度上遵循這一觀點,且不無偏見地反對理性行動者的算計說(拉圖爾(BrunoLatour),卡龍(Michel Callon)等)。他著力理解物質世界如何通過從無到有,實現某些特定的理想。許多物質文化研究關心群體如何理解自身并通過盜用汽車、時裝、家具等貨物成為自身。該觀點認為:如果貨物不存在,身份就不能實現——年輕并非擁有時裝、音樂或生活方式的先決條件,而是它們的后果。而且,人也可以失去物質性——貧困,即失去自我,恰好是這樣的例子。拉圖爾提出“偶像沖突”(iconoclash)的概念,形容一種混雜的反應:既沉溺于意象,又渴望破壞意象。實際上,米勒的觀點并不完善,因為在邏輯上,他從物質性移向文化性,但文化性卻由人化的語境來定義,即穿一件印度紗麗或買一杯特立尼達“飲品”之所以使身份成為現實,取決于附著在物上的、布迪厄式的傳遞和慣習。拉圖爾的出發點較為偏激:因為沒有“自然”,所以就不可能有“文化”,只有混雜或“自然加文化”(nature-cultures),人和非人糾合在一起。因此,大氣中的臭氧空洞既不是自然的也不是文化的,而是兩者糾合的產物。提姆 英格爾德(Tim Ingold)批評米勒沒有注意到物品在技術上的物質性。米勒畢竟認為,物品的意義和形式要從人們對物品的態度理解,就是說,焦點仍在文化而不在物質性。提姆 英格爾德在一篇《制造文化與編織世界》的文章中,宣稱他對物質性的研究取得了突破。他將通常的秩序顛倒過來,將制作視為熟練操作的產物。一件物品成為現實,體現的是有節奏的制作過程,例如編一個籃子或者造一口鍋。這個過程的特點,在于將想法變成現實,并將之帶入慣習或日常行動之中。我猜,我們更接近哈登和他的魚鉤了。當然,嚴肅地研究物品,讓我們可以重新利用博物館藏品,讓藏品虛擬地回歸田野工作的語境,并推進人造物的物質性研究,而不再僅僅做文本或口述形式的視覺驗證。吉爾(Alfred Gell)將人類學的藝術爭論從文化決定論的邊緣拯救回來。他以20世紀80年代在紐約展出的贊德人(Zande)獵網所引起的爭議為例,將藝術理解為思想的對象。獵網用打結的繩子編成,繩結和繩索承載了復雜的觀念。此處的觀念,類似鄧肯(IsadoraDuncan) 的說法:“如果我能告訴你它是什么意思,我就不會把它跳成舞了。”庫奇勒(Susanne Kuechler)說,繩結不僅激發了一系列個人思想和情緒,還構成了太平洋作為文化區的特征。她研究了繩結的類型與結繩的本體論之間的關系,并以此理解南太平洋的身體政治及其各種表述。她研究太平洋地區的物品,一種是用辮形繩索捆扎的物品,另一種是用特殊的打結方式捆扎的物品。結果發現,捆扎動作與酋長繼承有關。她認為捆扎的物質性與知識的技術有關。技術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技術的轉型。新愛爾蘭的馬朗根雕塑(Malanggan sculpture)木框上的繩結或者夏威夷斗篷和物品上的過度捆扎,與當年哈登筆下的魚鉤有直接的關系——在太平洋地區,人們極為重視魚鉤系在魚線上的方式,它大大超出了捕魚本身的需要。
過去的“文化區”觀念和當下的商品觀念,在這里形成一個矛盾。前者認為,世界可以根據某種延續性和實質性特征分成區域,無需顧及具體的政治和經濟變化;后者認為,商品從一個文化進入另一個文化,會越來越失去其物質性。就這個問題,賓尼提出,可以存在不同的“汽車文化”。這里又是一個循環論證:汽車文化僅僅是不同文化中的汽車文化。
“物品看似敘述的焦點,僅僅成為搭建不同文化(乃至于人)的方式。作為物的社會生活的敘事,物品再次肯定了它們穿梭于其中的人的能動性。”
后來,他遵循馬丁 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的觀察,提出了一個更深刻的悖論,“物品越是客觀,主體就越主觀地凸顯出來,我們所講的有關世界的知識就越發變成關于人的主張,越變成人類學。物品作為非人領域的誕生,與人類作為人的誕生是同步的”。
僅僅強調“客體(物品)凌駕于主體”,換言之,修正涂爾干式社會學對人類學的影響,只能繼續陷入主體-客體的悖論,繼續讓物品和意象附屬于我們已經熟識的文化和歷史,我們希望擺脫這個悖論。
我提出的解決辦法是,在混雜的復合體中,追蹤在實際上將物品和人聯系起來的通道和網絡。如果文化和物質性不能分開,人與物品是它們互動的產物,那么文化將物品人化的觀念,或者物品和技術制作人的觀念,都將消解到一個更為基本的問題,即這些不同的潛力如何傳遞或如何繼承。在后面兩講中,我將更細致地追究這些問題。
研究論著,值得細讀。。。
意外很好
zhengtihenhao
試讀
推薦!
真心不錯,太好了!非常棒!紙質和印刷都沒的說,絕對正版!關鍵便宜,過年有事做了!
贊贊贊贊贊贊贊贊贊贊贊贊贊贊贊贊贊贊贊贊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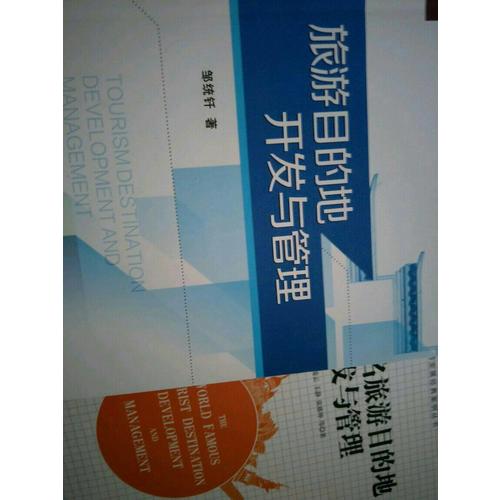 這本書沒什么問題,關鍵是快遞打了電話確認家里有人,但結果就放到柜子里,天熱不愿意爬樓也可以理解,但是某東的小哥為什么每次都能送上門,對比一下,服務看就出來了
這本書沒什么問題,關鍵是快遞打了電話確認家里有人,但結果就放到柜子里,天熱不愿意爬樓也可以理解,但是某東的小哥為什么每次都能送上門,對比一下,服務看就出來了
大家的大作,確實值得細讀!
這是一部學術論文集,內容非常專業扎實,對社會學、人類學和歷史有興趣者不妨一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