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盡了,渺渺途程,漠漠平林,壘壘高山,滾滾大江”……
戰亂烽火下的弦歌不輟,薄暮余暉中的驪歌永別。
教會大學——在近代中國發軔于民國初年,至1920年代中后期,漸成蓬勃之勢,以燕京、輔仁等為代表的十數所教會大學散落于北京、上海、山東,與國立大學及其他私立大學交相輝映,成為民國高等教育不可忽略的一支。20世紀30年代,日本侵略步伐加速,隨即全國進入長達八年的抗戰階段,全國向大后方遷移,教會大學亦漸次遷移、聚集在成都華西壩等地篳路藍縷復課興學。1945年抗戰勝利后不久,四年內戰再起,至1949年新中國成立,1952年中國大陸實行高校改革,教會大學旋遭解散,西方各國傳教人員及各方面專家盡數離境。作為近現代中國教育史中一種短暫存在而有重要影響的教育機構,教會大學其歷時不足半世紀,對近現代高等教育及學術研究卻影響深遠。因其“輝煌”,故有“弦誦”;嘆其短暫,亦復“驪歌”。
作者岱峻將書寫對象聚焦“教會大學學人往事”,展示出20世紀30年代到50年代初期,教會大學的幾度折轉經歷,尤其是一代學人的精神氣質與人世遭際。這其中既包括齊魯大學國學所的顧頡剛、錢穆等著名學者的曲折經歷,也包括許多或顯赫一時或學術影響深遠卻因種種原因被歷史湮沒少為人知的學者(如人類學家李安宅、哲學家羅忠恕等)、以傳教身份來華的海外學者(如農經學家卜凱、金陵大學教授芮陶庵等)、因卷入政治之爭而經歷曲折的媒體人(畢業于燕京大學的“新聞四杰”唐振常、嚴慶澍等)。
九篇文章,有特寫也有群像,各自獨立,又彼此關聯,猶如一部同氣連聲的短篇小說集,又似一本此起彼落的折子戲。
從《李濟傳》到《發現李莊》,再到《民國衣冠》《風過華西壩》,作者岱峻一直堅持細碎處鉤沉歷史,在細節中觸摸歷史的方式,這一本《弦誦復驪歌》同樣是嚴謹而不乏溫情的筆調,講述一段教會大學的學人往事。
岱峻,本名陳代俊,原籍四川資陽,現定居成都。1982年畢業于重慶師大中文系,執業媒體,業余文學創作,曾獲全國及四川省多項文學獎。20世紀90年代轉入民國學術史及學人研究,著有《發現李莊》《消失的學術城》《民國衣冠》《李濟傳》等。
目錄
烽火弦誦 斜陽驪歌(代自序)
大地雄心:卜凱與賽珍珠及其弟子1
錦官城送別2
宿州洋夫婦3
石頭城勞燕分飛8
中國土地利用調查18
弟子們25
大地徘徊的幽靈33
顧頡剛、錢穆與齊魯國學研究所43
“有眾一族,可以中興”44
崇義橋賴家園子52
顧老板篳路藍縷59
瑜亮之憾64
錢穆得其所哉72
顧頡剛渝州受困78
胡厚宣探驪得珠84
曲終月在天88
丹楓報秋意93
長著青稞、飄著經幡的田野100
——戰時成都的藏地研究
李安宅與華西邊疆研究所102
任乃強與康藏研究社135
格薩爾—共同的研究課題148
老樹逢春吐芳華156
羅忠恕:民間外交的布衣學者175
攪動大洋暖流的一只蝴蝶176
壩上的東西文化學社184
再度西游:光榮與夢想194
獲新生昏鏡重明204
文章報國披肝膽 筆削褒貶著春秋209
——記燕大新聞系暨大公報四杰
拔萃芳草地211
不做羅亭,要做英沙羅夫218
大公報:堂堂之鼓,正正之旗230
遠望紅旗 心潮難平236
風正時濟待揚帆247
在這個沸騰的時代258
以筆為槍,轉戰香港267
新聞是歷史的初稿273
我在“遠東好的牙醫學院”291
——醫學家王翰章口述史
家鄉淪陷 遠去成都291
插讀齊魯 轉學牙科298
林則與華西牙醫學院301
一棵稻穗逐漸飽滿306
特殊的牙病患者309
只是當時已惘然312
象牙罐,紫檀蓋,里面坐了棵小白菜318
——革故鼎新的吳貽芳
內心要有光319
及時小姐與及時夫人323
開明領袖 保守校長329
吳貽芳意欲何為? 337
夕陽山外山344
一種不舒服的蟲子348
1948:齊魯大學再度南遷記354
萍飄蓬轉 命運多舛355
背運校長吳克明359
離開濟南 再度播遷 363
弦誦云棲寺366
在福州的醫學院371
最是橙黃橘綠時379
他者的文化鄉愁387
——芮氏三父子的未了情
患難與共388
的圣餐395
中西方文化的擺渡人404
后記416
顧頡剛、錢穆與齊魯國學研究所(節選)
辦國學所,只有幾位當事者的熱情,主管部門多不支持。1940 年 9 月 9 日,史社系主任張維華向顧頡剛轉達,教育部批復齊大“設研 究所事緩議”,理由是經費匱缺,房舍圖書全是借華大的,故“抗戰 期內,充實內部,不圖擴張”。顧頡剛則表示,“予決不灰心,要做 好事,未免不盤根錯節者也。” 教育部“緩議”并非停辦,況且他 們不管經費。
另一“老板”哈佛燕京學社(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簡稱“哈 燕社”)的態度卻成敗攸關。哈燕社于 1928 年在哈佛大學成立,在北 平燕大設立辦事處。依據美國鋁業大王查爾斯 馬丁 霍爾遺愿,決 定拿一筆錢,為在華的基督教大學提供漢學研究經費,齊魯國學所即 其中的受益者。此時,哈燕社社長葉理綏(Serge Elisse?eff) 認為, 齊大辦國學所是好高騖遠,應該按計劃先辦好本科教育。自 1939 年 12 月起,葉理綏在致齊大的信中,即對國學所有微詞。1941 年 1 月 9 日, 張維華到賴家園子,出示哈燕社來信,要求顧頡剛解釋 1939 年 4 月接 受哈燕社資助 2000 美元所擔負的《尚書學》編刻課題的進展情況,信 末追問:“交稿抑或退錢?” 1942 年 12 月 4 日葉理綏致信劉世傳, 指示齊大“除非專修課程組織完善,教學質量崇高”,否則“不應從 事研究工作”,而“違反本社董事會政策及未和本社商量就組織的國 學研究所開支太大”,已“大大的越出教務費用所占的比例......”
戰爭牽制學術的發展。齊大原有的學術刊物《齊魯學報》《齊大國學季刊》被停辦。顧頡剛自籌經費辦了一份學術半月刊《責善》。 為向學生示范讀書筆記,他索性在雜志上連載原在昆明寫的《浪口村 隨筆》。老師領進門,修行靠各人。弟子們也把《責善》當成向師長 匯報、與同窗交流的園地。魏洪禎的《契丹之文學》,杜光簡的《烏 地也拔勤豆可汗墓志考釋》,錢樹棠《秦治馳道雜論》諸文,皆獲顧 頡剛與錢穆的賞識。
顧頡剛此時的學術興趣,重在關注歷史地理與民俗。避亂蜀地,他 有清理四川上古史的計劃。1940 年 12 月中旬,他帶弟子李為衡外出考 察。先到雙流縣,查考文廟、薰風塔、瞿上城遺址、商瞿墓、應天寺等。 后轉新津縣,游覽“宋太子少保張商英故里”。再雇船沿南河下行 15 里, 上岸西行,觀摩一座座漢代崖墓群。后來到九蓮山觀音寺,“可惜元 末毀于兵燹。到明代中葉,又由和尚們興建起來,清代再加幾次培修, 才成十重殿宇,與舊址相較,已經縮小了大半。中間一殿還保存明成化以來的壁畫,莊嚴肅穆,因系膠漆所繪,不易剝蝕。諸殿佛像也各極 其妙,顏色凝湛......” 再赴邛崍,盤桓數日,考察天慶寺、楊伸花 園遺址及文君井及邛窯遺址等,瞻仰魏了翁讀書臺、點易洞。12 月 31 日,轉道大邑,游覽灌口悅來場、鶴鳴山。“鶴鳴山之中峰曰天柱山, 上老君殿甚陡,聞張道陵即在此間仙去。其后迎仙閣則永樂帝所遣道 士在此迎張三豐者。” 乘坐滑竿離開大邑,再到崇州、溫江、郫縣, 順路考察魚鳧城、望帝叢帝陵。1 月 5 日回到賴家園子。
這趟環成都周邊,由南向西朝北的半月形考察,“對于古代的蜀 國也浮動了重重的幻想。”顧頡剛重新調閱《元和郡縣制》《嘉慶四 川通志》《路史》《華陽國志》《蜀中名勝記》《新津鄉土志》《清代邊政通考》等地方文獻,結合原有積累與此次踏訪的所獲,開始撰 寫《蜀國史實之分析》—
三皇之一的人皇,“分九州為九囿”,《華陽國志》說巴蜀之為國, “肇于人皇”,“梁岷之域是其一囿”;五帝之后即夏禹,《史記》說“禹 興于西羌”,《華陽國志》說禹治水后,大會諸侯,巴蜀作為梁州的侯國參加了大會;桀是夏代最末一王,《竹書紀年》說“后桀伐岷山”, 可見他曾對蜀國用兵......縱觀巴蜀古史,左絀右支,疑竇叢生。顧頡 剛提出,須先做徹底的破壞,才有合理的建設。“不幸歷代人士為秦 漢的大一統思想所陶冶,論古代也是一模一樣的,終不肯說這一塊地 土的文化在古代獨立發展,偏要設法把它和中原的歷史混同攪和起 來,于是處處勉強拍合,成為一大堆亂絲。一班修史的人難以考核, 把這些假史料編進許多史書里去,彼此糾纏,把人們的腦筋弄迷糊了, 古蜀國的真相再也看不清了。” 弟子方詩銘談道:“這篇文章寫好 后,頡剛先生翻覽群書,又得到許多資料,準備寫‘拾補’,還打算 遍稔四川方志,系統研究四川的古史傳說。” 因時間不逮,原定的 目標終未實現,唯將構思中的及時部分完成,題為《古代巴蜀與中原 的關系說及其批判》,刊載《中國文化研究匯刊》創刊號上。1942 年, 再完成《秦漢時代的四川》一文。
顧頡剛曾總結此期的學術科研活動:
一、春秋史材料集— 前年本擬作古代史材料集,嗣以 范圍過大,先從春秋史入手。此一年中,讀《春秋經》《左傳》 《國語》《公羊傳》《穀梁傳》等書,寫筆記約 4 萬言,又 令書記抄寫《春秋經》,編輯《春秋經通檢》。
二、研究古蜀史— 四川古代史,去年已與楊向奎君合 力從事于李冰治水之故事。本年又研究古蜀國之傳說,寫成《古 代巴蜀與中原之關系說及其批判》一文,約三萬五千言,刊 入《三大學研究所中國文化匯刊》。并游歷雙流、新津、邛崍、 大邑等縣,實地搜集資料。
顧頡剛的四川上古史研究雖未完成,但后來的三星堆、金沙等眾 多文化遺址,證明了他當年的預見。華夏文明起源已從單一的“黃河 文明中心論”,演變成當今國內學界大致認同的“中華文明一體多元 論”,顧頡剛先聲奪人。
瑜亮之憾
初到賴家園子,錢穆曾語顧頡剛:“兄任外,余任內,賴家園環 境良好,假以年月,庶可為國家培植少許學術后起人才。” 這番“雙 峰并峙,二水分流”的愿景,顧氏內心未必認同。
1941 年 1 月 5 日,顧頡剛外出考察返回賴家園子,即發現情況大 異于前,“予出門不及二旬,而所中紀律已歸松懈,所中時間較城中 已遲一小時,而猶七時不搖起身鈴,則早飯開時必近九時矣。聞開早 飯時尚有不起身者,可見人情向下甚易,向上絕難。賓四在此乃一切 不問,我真不能作長期旅行矣。” 于是,顧頡剛連續數日“晨,喚 老周搖鈴”。
當初,顧頡剛對錢穆有舉薦之恩,而“有為”與“無為”,是二 人之思想分野,這會不會也是立在他們之間的界石?
錢家乃江蘇無錫望族。錢穆早年喪父,中學肄業即去小學中學教 書自給。他精通經史,博聞強記,早有著述。1929 年顧頡剛回蘇州養病, 偶然讀到錢穆《先秦諸子系年》,大為驚嘆,即去無錫訪錢穆,告訴他,“你應該到大學去教歷史。”還邀他為《燕京學報》撰文。經顧氏推薦, 錢穆的《劉向歆父子年譜》在《燕京學報》上發表。他考證偽造經書 問題,與康有為的觀點大相徑庭,引起軒然大波,也因此卓然成名。 顧頡剛還向北大文科學長胡適力薦錢穆,“我所能教之功課他無不能 教也,且他為學比我篤實”。從此錢穆登上大學講壇。晚年錢穆猶記: “頡剛不介意,既刊余文,又特推薦余至燕京任教。此種胸懷,尤為 余特所欣賞。固非專為余私人之感知遇而已。”
此一時彼一時。賴家園子的研究員需在齊大文學院兼課,兩位老 友無異于同臺打擂。顧頡剛為齊大史社系學生講授“中國古代史”等 課。他常著寬大長袍,戴一副白色金邊眼鏡,背微駝,不茍言笑,蘇 州口音重且略顯口吃,學生不易聽懂。他除了發給學生大量資料外, 大部分時間都在寫板書,通常寫滿三四黑板,下課的鈴聲也就響了。
錢穆為之嘆:“頡剛長于文,而拙于口語,下筆千言,汩汩不休,對 賓客則訥訥如不能吐一辭。聞其在講臺亦惟多寫黑板。”
中小學教員出身的錢穆,在史社系教中國通史、中國文化史課, 則大受歡迎——
時《國史大綱》甫問世,授課即以此為講義,并多所發揮。 班中同學甚眾,多有來自外校者。賓四先生善言辭,長于演 講,......講課時頗帶鄉音,蜀人初聽之下,頗有茫然之感。久之, 我對先生的鄉音漸有所悉。再久之,更不覺先生言辭中有鄉 音,如聽一般的普通話。先生授課,于興至之處,時高舉雙臂, 慷慨激昂,間更縱聲而笑。
錢穆教授教我們的中國通史,他在課堂中總喜歡拿些小 故事串聯歷史中的大事件,生動有趣歷久不忘。那時大學生 已經很多,對社會似乎發揮不了什么作用,更甭說帶動的力 量了。錢教授就舉了一個東漢時大學生的故事,......在漢代 有個大學生叫郭林宗的,24小時正在街上走著的時候,忽然下 起雨來了,雨點把他的四角帽的一角打垂了下來,變成了五 角帽。第二天,長安市上,就有很多人模仿他戴起了五角帽 來了。現在的大學生會有這么大的影響力嗎?
登堂執掌教鞭,化育莘莘學子,誠人生之樂也。嚴耕望曾轉述老師錢穆的感受:
“一登上講壇,發言講論,講到得意處,不但不見下面 有大群人,也渾忘天地人世,連自己都忘掉了。只是上下古 今毫無顧忌的任性盡情的發揮,淋漓盡致,其樂無比!”他 說得興高采烈,得意的大笑“哈哈!好痛快!”那狀貌 神情真像個天真的老小孩,我也被逗得大笑!
顧頡剛的不快是人之常情,而較大的不快是要在人前若無其事。
1941 年 1 月 11 日,顧頡剛收到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部長朱家驊信函,邀他到重慶去辦《文史雜志》,許以每月經費 5000 元。“數非不多, 無如我精力不濟,且抓不到工作人員何!” 動心的不獨待遇,還有 他與朱家驊的交情。1926 年,留學德國的礦科博士朱家驊主政廣州中 山大學,即邀顧頡剛前往辦東方語言歷史科學研究所。1933 年,顧頡 剛與同事在北平組建“三戶書社”,出版通俗讀物,遭人舉報宣傳赤 色思想。陳立夫以此為由要查封書社。1936 年 1 月,顧頡剛攜所出書 刊去南京面晤朱家驊。朱翻閱讀物后,公開表態支持,隨即介紹顧頡 剛加入國民黨。顧頡剛并未推辭,卻未辦入黨手續,回到北平后也未 與市黨部接洽,卻收到朱家驊寄來的入黨證書,還收到中央黨部寄來 的“三戶書社贊助費”2 萬元......追憶前事,俯瞰今日,顧頡剛心緒 難平,他在 1941 年 1 月 31 日的日記中補寫:“校長于二月一日召見, 謂西山自崇義橋歸,謂錢、胡二先生對于研究所極熱心,極有意見, 擬此后照文學院例,開所務會議云云。所務會議當自開,惟錢、胡二 位有意見何以不對我說而向西山說,西山何以亦不對我說而對校長 說,必由校長以傳達于我乎?此中之謎,不猜亦曉。予太負責,致使 西山無插足地,故渠必欲破壞之。渠對賓四,忠順萬狀,其目的則聯 甲倒乙而已。”錢是錢穆,胡即胡厚宣,“西山”指張維華,皆與之 有隙。到了 5 月,“劉校長必不讓我辭職,但行心既動,已按捺不住。 誰教他和西山在此兩年之內處處束縛我乎!我即緩行,當使此一機關 漸變為賓四所有,予則漸漸退出也。”
6 月 5 日,顧頡剛以臨時有事為名,先去重慶探路。此行,他既 有蒙蔣公召見且賜宴的寵幸,也有財物遭敵機轟炸的損失。7 月 9 日, “我所住室落一燒夷彈,自己帶去的零碎東西全沒有了。唯衣服籃子 為工友張某取藏防空洞,尚得保全。我的日記、賬目、信件,以及別 人的稿件托我看的,一切成為灰燼了。”
7 月 19 日,顧頡剛回到成都,趕上西南聯大的梅貽琦、鄭天挺及 羅常培等人訪問壩上。羅常培寫道:“至于三大學的中國文化研究所: 齊魯由顧頡剛主持,另外還有錢賓四、張維華、張維思、胡福林、孫 次舟幾位......這三個研究院的風格,大致齊魯偏重歷史,金陵偏重考 古,華西偏重語言,不過中間也沒有嚴格的分野;經費的來源都是由 哈佛燕京社供給的。”
9 月 13 日,顧頡剛回到賴家園子,“整理書物,為人寫字五件, 出布告三通,與賓四、厚宣、洪楨等談所事。二時半開茶話會,與所 中同人作臨別贈言,五時半畢。......連日,將經費、組織系統、房屋, 都作一分配。”14 日午飯后,就此離去。“北平傳說予與西山不合, 憤而走渝,學界之人何消息之靈也?”
顧頡剛出走的原因,胡厚宣有不同的解釋:
錢先生來齊魯,顧先生本應高興,但錢先生又會講又會說, 學生非常擁護,顧先生名義上受不了。錢先生學生都是好學生, 顧先生學生卻有些沒出息的學生,加之顧先生用人不成,無 象樣的人,固“不可一日留”,非到重慶不成。顧先生至渝做事, 與朱家驊編《文史雜志》,國學研究所主任所長職不交錢先 生。錢先生非常不滿,同我抱怨道— 不來又不交。顧先生 曾想讓我他,我只是研究所秘書,我說我雖是研究員, 但是給你們當助教,先生是我的老師,錢先生亦是我的老師, 有錢先生在,我怎么能,這是給我為難。
1942 年 3 月 4 日,在重慶的顧頡剛致信錢穆說,“研究所者,弟 費了兩年心力所建設者也,自身雖去,終不忍其倒塌。去年時,所以 仍擔任主任名義者,即恐因弟一走而致人心渙散,故欲請假延長時間, 使兄之力量可漸深入,則至弟正式辭職時可無解之憂也。”5 月 4 日, 他在致鄭德坤的信中說,“我在重慶忙得不(得)了。......成都事, 我已不能擔任,去函辭職......”查閱顧氏當年日記:8 月 5 日從到渝 的劉世傳處得知:“賓四態度頗模棱,究否留齊魯;如留,究否主研 究所。均不可知。”9 月 25 日,“劉書銘來,謂賓四對我有誤會,我 想,我是竭誠要賓四作研究所主任者,若賓四真對我誤會,則賓四為 不智矣。”10 月 4 日,“前日書銘來,謂我寫與彼信有‘只要錢先生 任主任,將來剛幸能擺脫塵世,必仍有為齊大專任研究員之一日’等 語,使賓四對我起誤會。今日丁山來,又謂在三臺時,(蒙)文通適來, 談及錢先生對我有不滿意處,而文通謂是賓四對。丁山又云,楊拱辰 得崇義橋信,謂錢先生對我不高興,不欲我回去。三人成市虎,得非 賓四對我確有不滿意處乎?我對賓四盡力提攜,彼來蓉后,要什么便 給他什么,且我自知將行,盡力造成以他為主體之國學研究所,我對 他如此推心置腹,彼乃以此相報乎?人事難處,至矣盡矣!”
人師也是人,同樣不離七情六欲。顧頡剛不愿撒手,錢穆不能接手, 此或是問題關鍵。當事人胡厚宣證明:
湯吉禾被解職后,顧先生又回研究所來,但顧先生始終 未辭所長主任職,始終未交權給錢。錢先生《八十憶雙親 師 友雜憶》說交錢穆,事實未交,顧錢兩先生講的都不對。我 身歷其境。在兩位老師之間,我誠實,忠實,兩位 都是我的老師,對我都很好,我不敢說一句假話。
錢穆先生做學問,主張“學以致用”,講“內圣外王”之道。與顧先生相比,錢先生以主立為主而顧先生以主破為主,顧 先生是要弄清事實真偽,錢先生則是講事實是怎樣,同時錢 先生講做人、人生應該怎樣。這大概是二人的區別所在。
事實真相就像“羅生門”,歷史敘述的意義或在于揭示人性的復雜性, 人情物理的豐富性。
這個商品很不錯
弦誦復驪歌——教會大學學人往事,好書推薦 。
一段值得回味的歷史
這是一本非常棒的書籍。
很好的書,書的裝禎好,質量好,書很喜歡!
內容好,很喜歡
單位買的書,不錯。
整體感覺不錯
好書好好讀啊
書皮有部分破損,分撿的時候能不能小心點!
太好了,這書太好了
非常好的書
 不錯不錯不錯不錯不錯不錯不錯不錯
不錯不錯不錯不錯不錯不錯不錯不錯
民國現在己成熱詞,民國大師令人景仰
趁著活動買了存著,慢慢讀。
講述一段教會大學的學人往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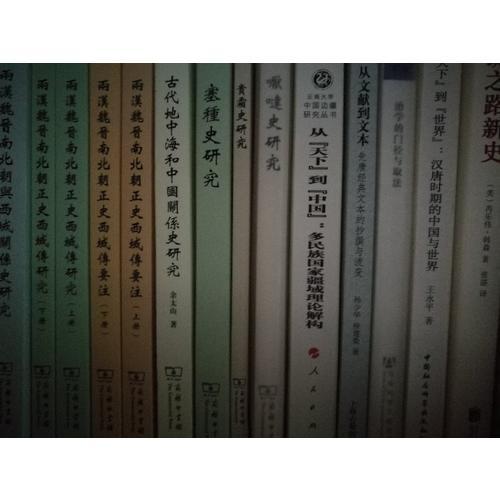 “既怕有負先生,更怕有誤后生”,在于丹式的文化網紅盛行的年代,岱峻先生這種田野考古的治學方法尤顯可貴,十余年的持續采訪,大量的一手資料,三年時間的反復打磨,使教會大學這一歷史的旁支細節同樣成為挖掘的豐盈偏倉,有料,也有趣,更令人深思。鄭重推薦。
“既怕有負先生,更怕有誤后生”,在于丹式的文化網紅盛行的年代,岱峻先生這種田野考古的治學方法尤顯可貴,十余年的持續采訪,大量的一手資料,三年時間的反復打磨,使教會大學這一歷史的旁支細節同樣成為挖掘的豐盈偏倉,有料,也有趣,更令人深思。鄭重推薦。
經典圖書,很好。
6049通知:請各位家長告知學生及家長,請按照以上要求準備好辦理社保金融卡的材料,但辦理時間要另行通知!
喜歡作者的風過華西壩,也買了這本
那一段舊時光令人難忘
大開眼界,值得一讀
很好的一本書,值得慢慢讀來,喜歡。
很好的一本書,值得慢慢讀來,喜歡
教會學校似乎在被刻意遺忘,為此,尤需要感佩作者的用心!
非常好的書 關于華西壩 四川人不可以忘記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