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讓我們成為人類?
我們怎么發展出了語言、思維和文化?
為什么我們存活下來,而其他的人科物種卻滅絕了?
人類演化的故事,比任何其他故事都更讓我們著迷。我們的好奇心永不滿足,總是不斷在問:我們是誰?來自哪里?本書對人類演化歷程提出了全新的疑問,也給出了嶄新的研究方式和回答。
“這是一個偵查的過程,呈現在我們面前的,是一個由考古學記錄組成的犯罪現場。和通常的犯罪現場一樣,證據很不完善,讓人激動,也讓人抓狂,我們的任務就是試圖推演出在什么時間,發生了什么,以及背后的動機。”牛津大學人類學家羅賓•鄧巴,著名的“鄧巴數字”提出者,以社會大腦假說和時間分配模型為偵破工具,猶如最敏銳的偵探,一步一步拼接出人類演化的完整圖像。
是什么讓我們成為人類?
我們怎么發展出了語言、思維和文化?
為什么我們存活下來,而其他的人科物種卻滅絕了?
人類演化的故事,比任何其他故事都更讓我們著迷。我們的好奇心永不滿足,總是不斷在問:我們是誰?來自哪里?本書對人類演化歷程提出了全新的疑問,也給出了嶄新的研究方式和回答。
“這是一個偵查的過程,呈現在我們面前的,是一個由考古學記錄組成的犯罪現場。和通常的犯罪現場一樣,證據很不完善,讓人激動,也讓人抓狂,我們的任務就是試圖推演出在什么時間,發生了什么,以及背后的動機。”牛津大學人類學家羅賓•鄧巴,著名的“鄧巴數字”提出者,以社會大腦假說和時間分配模型為偵破工具,猶如最敏銳的偵探,一步一步拼接出人類演化的完整圖像。
“半個世紀以來,成千上萬的讀者選了鵜鶘叢書作為他們的自學方式。這些藍封面小書,代表了的思想潮流,閱讀它們就如置身好的大學課堂之中。”鵜鶘有一種特殊的魔力,它吸引社會學家、經濟學家、數學家、歷史學家、物理學家等各領域知名學者迫不及待發表的研究成果,同時也鼓勵普通民眾躍躍欲試,探索不息。“鵜鶘”圖書是真正意義上的“公民大學”:沒有入學的門檻、沒有選擇的約束。
牛津演化心理學家鄧巴談論人類演化:我們是誰?我們來自何方?一直以來,一說起這個故事,總離不開考古學中的那些冷冰冰的石頭和骨頭。可單憑這些骨頭和化石,也許并不能完整地講述人類演化過程中的真實故事,這里所說的演化,指的是社會和認知的演化。那是一個漫長的進程,步履緩慢而猶疑,但是,它卻是人類進化到現代人的真實路徑。其實,我們真正想探尋的答案,就隱藏于這段進程之中,它會告訴我們,人類何以成為人類?人類何以走到今天?
羅賓•鄧巴 (Robin Dunbar)
演化心理學家,牛津大學認知及演化人類學學院前院長。作品被馬爾科姆•格拉德威爾譽為“大眾科學的神作”。
另著有《我們到底需要幾個朋友》(How Many Friends Does One Person Need?)和《梳理、八卦及語言的進化》(Grooming, Gossip and the Evolution of Language)。
致謝 及時章 幾個事先的說明 第二章 靈長類社會化的基礎 第三章 基本的架構 第四章 及時次過渡:南方古猿 第五章 第二次過渡:早期古人 第六章 第三次過渡:古人 第七章 第四次過渡:解剖學意義上的現代人 第八章 血緣關系、語言和文化是怎么來的 第九章 第五次過渡:新石器時代及以后 參考文獻
及時章 幾個事先的說明
人類進化的故事,比任何其他故事都更讓我們著迷。我們的好奇心,似乎永遠得不到滿足,我們總是在不斷地叩問:我們是誰?我們來自何方?一直以來,一說起這個故事,總離不開考古學中的那些冷冰冰的石頭和骨頭。這也不是沒道理,因為只有這些看得見摸得著的實物,給我們提供了確定性,給了我們可以依循的憑據。近半個世紀以來,考古學家們輕易不敢繞過這些“鐵證”,因為他們可不想被說成是在憑空編故事。可是,單憑這些骨頭和化石,也許并不能完整地講述人類進化過程中的真實故事,這里所說的進化,指的是社會和認知的進化。那是一個漫長的進程,步履緩慢而猶疑,但是,它卻是人類進化到現代人的真實路徑。其實,我們真正想探尋的答案,就隱藏于這段進程之中,它會告訴我們,人類何以成為人類(相對猿類而言)?人類何以走到今天?
我們人類屬于大猿猴科(great apes),因為我們身上所攜帶的生物學、基因學和生態學上的特質,大體上和猿猴共享。如今,比較統一的觀點是,與我們屬于同科的還有兩種黑猩猩(genus Pan,黑猩猩屬)、兩種(抑或四種)大猩猩(genus Gorilla,大猩猩屬)和兩種(抑或三種)紅猩猩(genus Pongo,猩猩屬)。在它們中,只有紅猩猩不是生活在非洲大陸上。現在,只有在東南亞的婆羅洲和蘇門答臘島上,才能發現它們的身影。而在一萬多年前的上一個冰河紀結束時,它們還廣泛分布于印度支那和中國大陸的南部。
直到1980年前后,依照傳統的概念,我們人類還是會被毫無爭議地和猿猴歸為同一科(family)。但事實上,我們和我們祖先的種類屬于一個有別于其它猿類的亞科(subfamily),因為和猿類相比,我們有著一系列很明顯的不同之處:我們直立行走,猿猴四肢著地行走;猿猴的腦容量以靈長類的標準來衡量已經算很大,但是,我們的腦容量更是大得多;我們有文化,而猿猴只有行為。這些區別顯示了在早期猿類即有不同的分支,一條通向現代人類,另一條通向現代的其它猿類。紅猩猩的這條分支能通過化石追溯到大約一千六百萬年前,如果由此類推,我們和猿類的共同祖先應該至少也有那么久遠的歷史。
但是,在1980年代,這個故事出現了戲劇性的轉折。因為從這個時期開始,生物科技的發展使得我們能夠從基因上分析不同物種之間的相似度(相對于僅僅依賴解剖學的結果)。不久我們就發現,從基因的角度來看,人類和黑猩猩的相似度明顯高于其它猿類,大猩猩緊跟其后排在第二。但是,從一千六百年前開始就居住在東南亞的紅猩猩和我們的相似度卻并不高。而在非洲生活的幾種猿類(類人猿、大猩猩和黑猩猩)形成了一條共同的支線,這條支線的分叉點離現在要近得多,大約是在六百萬到八百萬年前(圖1.1)。我們并不是大猿猴科之下一個獨立的亞科,而是從屬于非洲猿類亞科。由于我們和黑猩猩擁有共同的祖先,所以,黑猩猩(而不是第三紀中新世的隨便某種猿類)就成了人類支線十分恰當的類比參照物,從很多角度來講,黑猩猩是早期的人類支線,也就是南方古猿(australopithecine)及其前輩中好的模版。
為了把故事講清楚,讓我來簡單重復一下非洲猿科的進化過程,以及我們在這個過程中所處的位置。有了這些背景知識,我再進而描述我們人類的支線從非洲猿亞科分離出來之后的五個重要進化階段。這些階段,或可稱為轉變過程,構成了我所要講述的這個人類進化故事的框架。
非洲猿猴的故事
現存的大猿猴(其中包括紅猩猩),其祖先是生活在中新世時期(Miocene era)的猿類。那是大約在兩千萬年前,各類猿猴突然大量繁衍,這種現象起初發生在非洲,而后又蔓延到歐洲和亞洲(圖1.1)。到了大約一千萬年前,由于氣候日益干燥,濕潤溫暖的熱帶森林面積大大減少,而這些森林就是當時種類繁多的中新世時期大猿猴的家園。數十種活躍于當時的猿類因此滅絕,取而代之的是生存能力更強的猿猴,這些猿猴在之前的亞非大陸靈長類中并不起眼。隨后,非洲猿類中的一條支線頑強地存活了下來,并且成為了現存非洲猿類的共同祖先。之后,大約在八百萬年前,成為大猩猩的那條支線分離了出來。又過了大約兩百萬年,最終誕生現代人類的支線開始形成,人類和黑猩猩的祖先同屬于這條支線(這就是通常所說的共同祖先,Last Common Ancestor,簡稱為LCA)。這條支線,之后走上了它獨自的進化軌道。又過了很久,大約在兩百萬年前,差不多就是在人屬(genus Homo)現身于東非的時候,黑猩猩的支線開始一分為二,演化成普通的黑猩猩和倭黑猩猩(bonobo,也就是pygmy chimpanzee)。按照慣例,分類學學者現在把猿科動物(包括人類)稱為人科(hominids),在LCA后分離出來的成為人類的支線中所有動物稱為人亞科(hominins)。在早期文獻中,出現的是homininoids和hominids這兩個相應的詞,不過,我使用的是目前學界通用的術語。
而人類的祖先,當時還毫不起眼地混跡于各種猿類之中,在大約六百萬年前,默默地開始了進化歷程。在非洲中部,殘留著大片中新世的大森林,我們的祖先就在那個時候開始進入這片森林邊緣更為開闊的平地。雖然猿類有時候也能在平地上活動,但是,以它們的天性,是生活在樹上的動物,習慣于手腳并用地竄上參天大樹,或者在林地上的樹枝間攀爬和悠蕩。而我們這條支線的決定性特點,也就是雙足行走(bipedalism)的特點,在和黑猩猩分開后不久就形成了,據推測,可能就是為了適應在沒有大樹的廣闊平地上行走。
我們人類的祖先是雙足行走的猿類,古人類學家就是利用了這個物種在解剖學上的特征,來尋找我們最早的祖先。現在,普遍的看法是,最早的人亞科化石屬于乍得沙赫人(Sahelanthropus tchadensis),但也有人懷疑,它們并不屬于人亞科,而“僅僅是另一種猿類”。這只幾乎完整的頭骨是在德乍臘沙漠(Djurab desert)發現的,那里是西非乍得撒哈拉沙漠的南部邊緣。這個頭骨的發現有兩大重要性,一是在于它的年代(距今約七百萬年前,所以非常接近于LCA),二是在于它的發現地距離其它早期人亞科發現地的東非有數千公里,且距離現代猿類在西非居住區域的北方也有數千公里(這表明森林和林地一度向更北面的方向延伸,切入了當今撒哈拉沙漠所在的地域)。雖然一些古人類學家認為,這只頭骨屬于某一種猿類,但更多人則依據它的枕骨大孔(頭骨中脊柱穿過的孔)的位置,確認了頭骨主人雙足行走的姿式,以此推斷應該把它歸入人亞科。越是接近猿類和人亞科分開的時期,其化石標本的界限越是模糊,難以區分,所以很難將那個時期的化石歸類。
圖根原人(Orrorin tugenensis)化石是目前已知的第二古老的人亞科化石,距今大約六百萬年,發現于東非肯尼亞的圖根山。這個發現不同于沙赫人的頭骨化石,原人的化石主要包括四肢骨骼、頜骨以及數顆牙齒。從原人的大腿骨和髖關節的角度來看(注1),幾乎可以確定無疑地判斷出原人是雙足行走的,雖然同時也表現出非常善于攀爬的特征。從這點說,原人好像和一百萬年后在東非和南非大量出現的南方古猿有很多共同點,可以確認它是人亞科中最早期的一員。接著,來到了距今大約四百五十萬年前,這個時期的化石被大量發掘,證明了人亞科支線在這個時期又衍生了更多不同的種類,于是南方古猿的時代來臨了。在當時,很有可能同時出現了多達六種南方古猿,它們中的大多數都散居在非洲的不同區域(圖1.2)。
南方古猿的繁衍非常成功,一時間,它們的生活空間覆蓋了撒哈拉沙漠南部的大部分區域。雖然在它們被發現之初曾經引發了考古界的轟動,在當時被確認為人類支線的祖先成員。然而,后來的研究證明它們無非是雙足行走的猿類,就大腦容量來說和現代的黑猩猩幾無差別。和黑猩猩一樣,它們很可能也屬于食果類動物(frugivore),即使在能弄到肉類的情況下也吃得很少。它們后來很有可能也開始使用石頭工具,在這一點上它們往往讓人聯想起能人(Homo habilis),后者現在被認為是一種過渡期的南方古猿。但是,這些工具充其量就是原始粗陋的趁手石塊,拿這些石塊做工具,類似于現在西非的黑猩猩也會拿著石頭當錘子用。
在距今一百八十萬年的一百五十年萬中,稱雄的是直立人(Homo erectus),這是一個人亞科物種,在所有人亞科類動物中,這個物種很可能生存了最長的時間。嚴格意義上來講,這個物種屬于生物學家口中的年代物種(chronospecies),意思是一種隨時間的推進而變化的物種。考慮到這個物種在地球上超長的生存時間,這種提法倒是合情合理。在它的早期,也就是匠人期(Homo eraster)前后,這個物種基本上在非洲生活,而到了后期(也就是進入了真正意義上的直立人時期),這個物種已經遍布于歐亞大陸。這個階段(距今約一百五十萬年前或更早)演化的意義,在于人亞科物種及時次走出非洲,進入了歐亞大陸,也是及時次出現了加工過的工具(1859年,在法國北部圣阿舍爾,出土了屬于阿舍利文化的手持斧頭)。這一時期的特別之處,在于它的穩定性。在將近一百五十萬年中,直立人腦容量的增加相當有限,而他們所使用的石頭工具,在形狀的變化上更是乏善可陳。這種長期的穩定性,在人亞科演化的歷史上是很獨特的。
而后,在距今約五十萬年前的某個時段里,一個新的物種從非洲匠人和直立人中脫穎而出,最終,它們成為了及時批古人(archaic humans),也就是海德堡人(Homo heidelbergensis)。它們的出現,標志著大腦容量的爆發性增加以及物質文化多樣化的起點。當然,從匠人到海德堡人之間也有過不同的過渡性物種,但是從細節上來看,其中的差別可以忽略不計。匠人群體漸漸淡出非洲和歐洲,被古人所替代,但是在東亞,直立人群體頑強地生存了下來,直到六萬年前仍然在這個區域生存著。被稱為霍比特人的弗洛勒斯人(Homo floresiensis)就是它在形體上較為矮小的變種,直到一萬兩千年前,這個群體仍然生活在印尼群島上,以地質學的時間概念來講,那就像發生在昨天。
這個階段的演化還有另一層重大的意義,這批古人的遷徙,推動了第二波向歐洲和西亞進發的行程,從而最終造就了歐洲人的原型尼安德特人(或稱尼人,Homo neanderthalensis)。尼安德特人長了一副特別適應高緯度生存環境的身板,在歐洲和北亞的冰河紀寒冷氣候中,得以生存下來。他們四肢短小,身體結實,這種體征有助于他們較大限度地減少從四肢手腳散失熱量,這一點和生活在北極圈的現代因紐特人(或稱為愛斯基摩人)很像。不同的是,因紐特人和他們在西伯利亞的同胞是近期才來到這樣的生存環境的,而尼安德特人將這樣的特征的優勢發揮到,從而在冰河紀的歐亞大陸生存了大約二十五萬年。
與此同時,在距今約二十萬年前,在更南面的非洲,古人正在經歷著另一種演化,這種演化的結果最終造就了我們自身的物種,被稱為解剖學意義上現代人(anatomically modern human, AMH現代人,或可簡稱為現代人),更科學的命名是智人(Homo sapiens)。解剖學意義上的現代人和古人相比,身材變得纖細(gracile),而且,大腦容量在持續增加。現代基因學的發展,使得我們可以利用俗稱的分子時鐘(molecular clock)來測算某條支線進化的時間。分子時鐘的原理,是利用兩個物種之間DNA的不同數量及自然變異的速率,來計算兩條支線分開了多少時間。觀測的重點是自然選擇范圍之外的基因組,也就是說,分子時鐘測算的只是DNA中自然變異部分的穩定速率。這一點很重要,決定我們的身體特征的那部分DNA,會在自然選擇的過濾下,發生急速的變化。通過對線粒體DNA(mtDNA)的研究(注2),有基因證據顯示,AMH現代人的起源來自于一個相對較小的族群,那是生活在距今二十萬年前后的大約五千名女性。當然這并不是說在那個時候那個族群的總數只有五千名女性,它只是表明,現代人類的基因都是由那五千名女性貢獻的。
至于是一股什么力量推動了這種全新的演化,到目前為止還沒有找到明確的答案。比較容易達成共識的是,氣候的變化是導致新物種形成的重要原因,智人的形成,很有可能也不外乎這個原因。不管怎樣,我們的物種迅速地在非洲各地繁衍開來,取代了古人的位置。至于古人為什么會這么快速地被智人取代,仍然是個謎。要知道,在被智人取代之前,古人在非洲還有歐洲至少已經生存了三十萬年。
之后,在距今約十萬年前,AMH現代人在非洲東北部的一條支線迅速在地域上擴展,到距今七萬年前,已經跨過紅海,占據了亞洲的南部海岸,最終在距今約四萬年前到達了澳洲(注3)。抵達澳洲這件事,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成就,因為這個旅程必須跨越從巽他陸架(Sunda Shelf,現代印尼和婆羅洲)到莎湖陸架(Sahul Shelf,新幾內亞,再連接到澳洲大陸)(注4)之間九十公里的深海海溝,這說明他們應該已經擁有了較大的船只。在我們要講述的這個故事中,解剖學意義上的現代人開啟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轉變階段,因為伴隨著他們的出現而來的文化是前所未有的。在距今約五萬年前的這段時期里,武器、工具、首飾及工藝品等在數量和質量方面相比以前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更不要說在那個時期還出現了諸如帳篷、燈具等等一系列實用性的物件,以及大型的船只。
現代人離開非洲向亞洲進發,在途中的黎凡特(Levant)及時次遭遇尼安德特人。在這次的正面交鋒中,現代人很有可能遭到了尼安德特人的抵制而不能進入歐洲,迫使他們沿著阿拉伯半島的南部海岸,往東進入了亞洲。在東亞,他們很有可能與直立人的殘余相遇,更為確定的是,在亞洲,他們和另一種叫做丹尼索瓦人(Denisovan)的古人相遇,因為他們有與之雜交的跡象。關于丹尼索瓦人,我們對他們的了解只能憑借幾根骨頭化石,那是在南西伯利亞的阿爾泰山的一處洞穴中發現的幾根骨頭,距今約有四萬一千年。這個洞穴,在不同的時期,還有尼安德特人和現代人居住過。通過對丹尼索瓦人的基因組的分析,可以得知他們和尼安德特人有著共同的祖先,這個洞穴的所在之處,很可能是在尼安德特人之前的早期古人往東擴張的一個終點。
讓我們再回到歐洲,此時,古人族群漸漸地變得越來越適應北方寒冷的氣候,進而演化成了尼安德特人。在距今約二十五萬年前到四萬年前,尼安德特人毫無爭議地成為歐洲的主宰,直到現代人的出現。和后來歷史上其他的入侵族群一樣,現代人也是從俄羅斯草原進入歐洲的東部,抵達西歐不過在三萬兩千年前后。這兩個族群共同生存了很長一段時間,直到大約兩萬八千年前,尼安德特人最終在伊比利亞半島消亡。尼安德特人或許是人類進化史上較大的謎團,在時間上和基因上他們都和我們最接近,消亡的時點離現在也不遠,這一切都讓我們費解又著迷。何況,他們已經適應了北方的氣候,比起我們的祖先AMH解剖學上的現代人,他們在歐洲生存的時間更長,可是到底是什么原因讓他們消失了蹤影?關于這個問題,我們現在先按下不表,在以后的章節中再展開深入的探究。
為什么說我們不是猿猴
首先,讓我回到本書的主題:我們和其他猿類共享一段漫長的進化歷史,我們有著相似程度極高的遺傳基因以及相似的體型外貌,我們都有發達的認知能力使得我們能夠學習和交流,我們也共同擁有群居狩獵的生活方式,但是,所有這一切都不能說明我們就是猿猴,我們和猿猴之間存在著一系列巨大的差異。幾乎所有人都會把關注的重點放在生理解剖的差異之上,也就是我們雙足行走的站姿,這當然是最一目了然的差異,但同時也是最無趣的差異。中新世氣候的變化導致了熱帶森林的退行和消失,為了避免物種消亡,行走方式的改變是必須的,這些早期的細小變化積累到一定程度之后最終形成了人類在形體上的種種特征。其余的爭論糾纏于工具的制造和使用,但事實上這些只是認知上不值一提之處,即使腦容量只是黑猩猩一個零頭的烏鴉也能制造和使用工具。本質的區別在于我們的認知,也就是我們的大腦所能夠產生的意識,是這些意識賦予了我們的Culture(文化)一個大寫的C,而文化才是人類文學和藝術的根源。
在過去的二十年里,人類對動物文化做了很多深入的研究,著述頗豐。尤其是針對猿類的文化,甚至有了一個專門的學科,被命名為猿類學(panthropology),也就是關于猿猴的人類學(注5)。在近親中找到類似于人類的某些行為和認知能力,這并不奇怪,人類的特征不可能毫無來由地從天而降,相反,這些特征是不斷適應和進化的結果。在大多數情況下,原有的一些特征,因為選擇壓力的加重而逐漸演變為新的特征。以后我們還會回到這個話題上,但是目前我需要明確的重點是:是的,人和猩猩都具備通過學習,社會性地傳遞行為方式的能力;而且,是的,我們也確實可以說黑猩猩和其它猿類擁有它們自己的文化。但事實上,和人類相比,猿類的文化能力簡直太微不足道了。這樣說不是要貶低猿猴的能力,而是為了點明一個在混亂和激動中幾乎被忽視的重點:是人類把這種文化能力提高了一大截,從猿類的文化到人類的文化,發生了一個質的飛躍而不是緩步向前。那么,問題來了,他們是怎么做到的?又為什么要這么做?
文化中有兩個關鍵的特性,顯然為人類所獨有。這兩個特性一個是宗教另一個是故事講述。其他任何生物,無論是猿類還是烏鴉,它們都不可能擁有這樣的文化特性。這兩種特性,完全屬于人類,而且只屬于人類。我們說這兩種特性是人類所特有的,是因為這兩種特性都需要用語言來執行和傳遞,而只有人類的語言擁有這種作為媒介的質地。對于這兩種特性來說,很重要的一點是它們都要求人類能夠生活在虛擬的世界之中。這是一個存在于人們的思想意識之中的虛擬世界,它并不真實存在,所以我們必須能夠憑借想象在頭腦中幻化出另一個世界,并將這個世界和我們每24小時都生存其中的現實世界分離開來。為了做到這一點,我們必須能夠把自己從現實世界中抽離出來,也就是說,從思想意識上和眼前的現實世界保持一段距離。只有當我們做到這一點,我們才有可能用超然的眼光去打量置身其中的現實世界,去思考它的緣起和合理性以及必然性,或者,去想象另一個平行世界的存在,那是屬于虛擬甚或是超虛擬(para-fictional)(注6)的精神世界。這些特殊的認知行為不是無關緊要的進化副產品,相反,在人類的進化過程中,這些行為能力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在以后的章節中,我會進一步解釋做出這個判斷的理由所在。
此外,人類文化中,還有其它一些特性,也已經被證明是非常重要的。特性之一是作為社會活動的音樂演奏,誠然,很多其它物種也會表現出樂感,比如鳥和鯨魚。但是,只有人類是把音樂表演當作一種社交性的活動,對于鳥類來說,制造音樂主要是為了引起異性的關注,是出自于交配的本能。因而,在人類社會中,音樂在社會關系上起到的作用,是非常特殊的。如今的現代社會,我們時常端坐在音樂廳里,溫文爾雅地欣賞音樂。但是在傳統社會里,音樂的制作和歌唱以及舞蹈幾乎是不可分割的,而且在人類的生活中顯得異常重要。這個現象值得我們深思和探究。
毋庸置疑的是,所有這些文化活動的起點當然就是我們發達的大腦,說到底這里就是我們和其他猿類產生根本性區別的所在。在圖1.3(注7)中,列出了所有人亞科物種的大腦容量,這張圖為本書提供了一個基本的框架。以過去的六百萬年為時間維度,我們可以看到,人亞科的大腦容量在不斷地穩步增加,今天的現代人類,腦容量已經是當初南方古猿的三倍。這個數據似乎在向我們暗示,隨著時間的推移,大腦承受著不斷長大的壓力。然而,這并不意味著是選擇的壓力使大腦穩步加大,這種和地理時間的推移相伴的增長,其實只是一個由不同物種樣本拼起來后呈現出的假象。如果把它們分開來看,更加明顯的是間斷性平衡的特點,也就是說,伴隨著每個新物種的出現,腦容量的增加會有一個跳躍,產生類似于爆發性增長的現象,但在隨后的一段時間里,腦容量的增長又恢復到平穩的狀態。
在本書接下來的章節中,我會一一描述人類進化過程中的五次重大轉變,或稱為五個進化階段。把這五個階段聯接在一起,就形成了們要描繪的人類進化路徑圖,而每一次轉變,都是由于大腦容量或生存環境的重大變化。及時次轉變是從猿類到南方古猿,主要是外部生態和解剖生理上的變化,并無大腦容量或認知上重大變化的證據;此后,從距今約兩百萬年前開始,經歷了三次大腦進化。及時次發生在距今約一百八十萬年前,人屬物種伴隨大腦容量的躍升而出現,雖然在此之前,伴隨著能人(Homo habilis)的出現,預告了一次微弱的增長,或許這是一個過渡性的階段。第二次伴隨著距今約五十萬年前的古人海德堡人的出現。一次是腦容量更為急速的飛躍,這個發生于距今約二十萬年前的巨變,直接催生了我們的物種,也就是解剖學意義上的現代人(也就是智人,Homo sapiens)的出現。與此同時,尼安德特人在大腦容量方面也有著平行的進化,相比它們在古時候的基準線,已經發生了可觀的增加,關于這一點,我們會在第六章里再次展開探討。每一次的轉變,都會帶來與相關物種有關聯的兩個問題:一是如何償付因為腦容量的增加而產生的額外支出,因為從能量的角度來說,大腦活動的消耗量非常驚人;二是如何把越來越大的社會群體緊密地聯合在一起,龐大的社會群體伴隨著腦容量的增加而來,腦容量越大,越能組成更大的社會群體。社會群體的規模,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社會成員的腦容量,如果群體過大,小容量的大腦在處理多出來的問題時就會顯得捉襟見肘。在每一個時間都已經被占用的日子里,能否找到更好更高效的解決問題的方法,對每一個社會群體來說都是嚴峻的考驗。如果沒有更大的腦容量的支持,在每個階段,群體的較大數量就會遇到瓶頸。
在上述的四個最根本的轉變之外,我還要增添一個和腦容量無任何關系的轉變,也就是本書要講述的第五次轉變。那就是發生在近東的新石器革命,距今大約有八千到一萬兩千年。關于新石器時代,尤為讓人疑惑好奇的一點是,它幾乎是對過去發生的一切的顛覆。兩大主要的更新是這個時期的標志,首先,由游牧過渡到定居,然后,逐步實現了農耕。雖然農業革命總是更加令人感興趣,但事實上農業只是手段而非目的。真正意義上的革命,是人類能夠定居下來,不再四處游蕩。不管群體以什么原因聚居在一個固定的處所,必然會引起諸多的社會矛盾,只有在化解了這些矛盾之后,才有新石器時代的到來。一旦這些問題被解決,人類就有了新的可能性,有能力擁有更大的社會群體。也正因此如此,城邦以及小王國才會次第出現,并隨著歷史的發展,最終誕生了現代的國家。我們的此次行旅,一個重要的目標,就是試圖去尋覓和理解人類祖先是如何渡過這一系列的轉變。
前方的道路
我在本章一開始就說過,考古學家們是靠著石器工具和化石遺骨吃飯的,佐以那么一點點區域地質學。但是,這些傳統上被人們聚焦的石器和遺骨有其致命的缺陷,因為它們反映不出人類進化過程中的社會層面,至于人類的認知這一進化中更為重要的依托,更是不可避免地被疏忽了。當然,考古學家們的擔憂也不是沒有道理,他們總覺得,這些來自遠古時代的證據,并不完整,也不夠直接,試圖從中推斷出任何你想要證明的社會行為,是否過于輕率了。但是,正是我們這個生物物種的社會和認知行為,標刻出一條前行的道路,這條道路的起點是在六百到八百萬年前,由共同祖先(LCA)走向我們自己現在所代表的現代人類。這條道路曲折迂回,經常看不清前方。但是,如果我們想在迷霧中摸清這條道路,就必須緊緊貼住這個模糊不清的,隱藏著的社會性世界,無論這樣做將要面臨多么艱巨的困難。
在靈長類(包括現代人類)的社會中,每個群體都是高度結構性的網絡,個人和個人之間的關系由親情、友情和責任維系著。這種由親情和非親情組成的社會網絡,以及它們的分布方式,不僅會直接影響到個人是否能容易地得到幫助,也會影響到這個網絡賴以生存的凝聚力和持續性。
現在,我們已經有能力來面對這些問題了,因為我們已經對靈長類動物的社會行為和生存環境有了更多的認識。這些強化的認識和理解是非常關鍵的,我們因此能夠輕巧地繞過一個難關,避開有關重塑化石人行為這個長期以來讓我們為之困擾的問題。迄今為止,標準的研究方式是,找到一種和化石人共享某些關鍵特性的現存動物,然后再假設化石人和這些動物有著相似的生態和社會組織。曾經有過那么一些時期,黑猩猩、大猩猩、狒狒、獅子和鬣狗都做過早期人類的模板,甚至連非洲的野狗都曾享有過這種殊榮。正是出于這種原因,偉大的化石專家及考古學家路易斯•利基(Louis Leakey)派出珍妮•古道爾(Jane Goodall)和黛安&
“一部必讀之書!強悍地向我們展示了極富想象力的大腦的運作過程,同時又留下了自由思考的空間。”——《新科學家》New Scientist
包裝精美,內容豐富,值得購買
品質不錯,包裝也很好,紙張手感不錯,是正版,給個好評!!
送貨給力,圖書精美。推薦大家來當當買書!
內容有點深奧,但是讀起來很有意思,了解人類的發展與進步,是一本難得的好書
包裝很好,先入手
整體感覺很好,質量很好,很喜歡
做活動下來4折多點,喜歡
還沒開始看 據說還不錯
好好學習天天向上
性價比很高
最近對進化論感興趣,開始看書
挺好的 這次沒磕壞 還沒看
很有意思的書
質量好,性價比高,好書
很早就想入手了,這個價格還可以
好書
考據嚴謹,資料翔實
非常好的一本書,作者寫得深入人心。當當正版書
當當活動很給力,比以前好很多,繼續努力
非常喜歡的書,看國外的書有新的感受。9
這個商品不錯!!!!!這個商品不錯!
很好,收獲很大,知識點很多。很好,收獲很大,知識點很多。很好,收獲很大,知識點很多。
鵜鶘這是相當不錯的了
還可以!!!
還行,小開本,精裝,不好攜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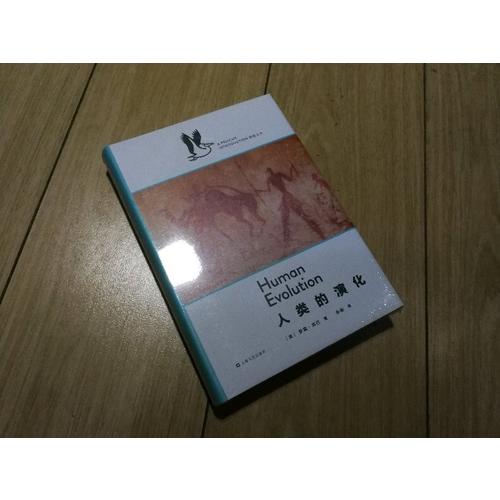 每個月都會來轉轉,收上幾本書。這次的書不錯,包裝完好,沒有破損與污漬。——【鍛煉與不鍛煉的人,隔一天看,沒有任何區別;隔一個月看,差異甚微;但是隔五年十年看,身體和精神狀況就有了巨大的差別。讀書也是一樣的道理,讀書與不讀書的人,日積月累,終成天淵之別。書籍是人類進步的階梯!你讀過的書其實早已融入你的靈魂,沉淀成你的智慧和情感,他會體現在你的談吐舉止里,體現在你的氣質中,體現在你的心態上,只要一個觸動點,就噴薄而出。】相對于國外,中國的書籍確實便宜,一頓飯的價錢可能買來的就是別人畢生的成果。所以,為了自己投資,永遠都不存在買…
每個月都會來轉轉,收上幾本書。這次的書不錯,包裝完好,沒有破損與污漬。——【鍛煉與不鍛煉的人,隔一天看,沒有任何區別;隔一個月看,差異甚微;但是隔五年十年看,身體和精神狀況就有了巨大的差別。讀書也是一樣的道理,讀書與不讀書的人,日積月累,終成天淵之別。書籍是人類進步的階梯!你讀過的書其實早已融入你的靈魂,沉淀成你的智慧和情感,他會體現在你的談吐舉止里,體現在你的氣質中,體現在你的心態上,只要一個觸動點,就噴薄而出。】相對于國外,中國的書籍確實便宜,一頓飯的價錢可能買來的就是別人畢生的成果。所以,為了自己投資,永遠都不存在買…
非常好,喜歡!
正在學習閱讀中
五星好評五星好評五星好評五星好評五星好評五星好評
這本書不錯
希望這套引進的叢書能帶來更多新觀點新視野,這本書應該說還不錯,內容新,有啟發
鵜鶘叢書的出版旨在傳播大眾能夠接受的知識,在購物車放了很久,打折終于買下來了。很心儀,封面好看,內容因為知識性會有點枯燥,但是真的獲益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