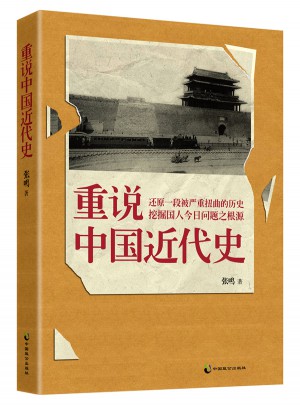
重說中國近代史
- 所屬分類:圖書 >歷史>中國史>近代史(1840-1919)
- 作者:[張鳴] 著
- 產品參數:
- 叢書名:--
- 國際刊號:9787514502022
- 出版社:中國致公出版社
- 出版時間:2012-02
- 印刷時間:2012-02-01
- 版次:1
- 開本:16開
- 頁數:--
- 紙張:膠版紙
- 包裝:平裝
- 套裝: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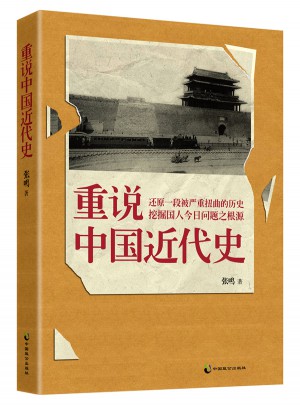
本書源自人大的一門熱門選修課,即張鳴老師開設的政治史公開課,它靠同學們口碑相傳而走紅校園,最終使更多的人對這段看起來枯燥無比的歷史重新認真審視起來。
這門課為什么如此受歡迎?原來在張鳴老師的還原下,中國近代史變得如此復雜、精彩,又是如此的顛覆,它與我們記憶里的古板印象迥然不同,絕非教科書上的忠奸兩列、黑白分明。當諸多人物與史實呈現在我們面前時,難以用一句簡單的是非作判定,在正視一段被扭曲的中國近代史的同時,我們也能發現國人今日問題的精神根源。
基于此,我們將這門課的講課稿集結成書,希望與更多的人分享這段充滿矛盾與悖論的真實歷史:中國與西方、清廷與民間、滿族與漢族士人、洋教與本土信仰、槍桿與筆桿、造反和維新、科舉與革命……是的,那段歷史,除去屈辱與仇恨,還有著太多的內容值得重新去回望和反思。
正如張鳴教授所說:如果我們不知道或者無視這個過程,就很難在歷史長河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很難安放好自己的位置,在世界格局中也定位不好自己的位置。誠如斯言。
還原一段被扭曲的歷史,挖掘國人今日問題之根源。
真實的歷史,只能由真誠的學者完成!
有料的大學歷史課,從大學校園流行出來的近代史!
更多歷史真相 政治暗殺簡史
推薦購買 : 馬云正傳:活著 就是為了顛覆世界、雪洞、覺醒課程、單身
張鳴:
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他個性鮮明,在嬉笑怒罵中藏著嚴肅的悲憫之心。社會責任感使然,張鳴以深厚的文化底蘊和深刻的人文關懷關注天下事,為歷史與當下人物事件虛華假面,使真相豁然,真知畢然。
主要學術著作有《辛亥:搖晃的中國》、《北洋裂變:軍閥與五四》、《武夫治國夢:中國軍閥勢力的形成及其社會作用》、《鄉土心路八十年:中國近代化過程中農民意識的變遷》、《鄉村社會權利和文化結構的變遷》等;歷史文化隨筆有《中國心絞痛》、《直截了當的獨白》、《歷史的壞脾氣:晚近中國的另類觀察》、《歷史的底稿》、《歷史的空白處》等。
及時講 中國近代政治史開場白
對于近代史的“三婦”心態
中西兩種體系
中國的抵抗
第二講兩個世界最初的碰撞
中西近代史的不同開端
中國和英國的及時次直接碰撞
鴉片——打破中英貿易結構的不平衡
第三講兩個世界最初的碰撞(續)
英國對中國政策的成本核算
中英的戰爭技術和戰略對比
開放教禁帶來了西方的輸入
傳統歷史締造的兩個神話
中國近代化的及時步
第二次鴉片戰爭
第四講帝國古老命題新解
關于太平天國起義原因的商榷
清末統治的主要問題
洪秀全創教史
太平軍起義
太平軍的問題
第五講帝國古老命題新解(續)
戰爭的天平開始傾斜
關于太平軍的幾個問題
湘淮兩軍——漢族士大夫的崛起
“同光中興”
第六講從自強到變法
洋務運動的起因
洋務運動的開展
北洋水師
洋務運動未必是場失敗運動
第七講從自強到變法(續一)
洋務運動存在的問題
甲午戰爭
第八講從自強到變法(續二)
戊戌維新的貢獻
清政府對于變法的態度
列強對于變法的態度
民眾對于變法的態度
第九講義和團運動
民教沖突的產生
天主教與中國民間傳統文化的沖突
清朝官府對于民教沖突的態度
清政府對于義和團的態度
第十講義和團運動(續)
義和團興起的原因
義和團的特點
東南互保
義和團失敗,八國聯軍攻入北京
第十一講清廷的新政
新政的成就
預備立憲
廢除科舉
滿族親貴收權
第十二講辛亥革命
革命的發生
會黨的特點
革命黨結緣幫會的原因
資產階級的軟弱性?
袁世凱這個人
第十三講袁世凱的悲劇
共和體制的問題
袁世凱與國民黨的對峙
袁世凱的悲劇
第十四講黯然北洋
段祺瑞與黎元洪
府院之爭
張勛復辟
南北交戰
第十五講眾說紛紜的“五四”
白話文運動
五月四日政治運動
的吊詭之處
的影響
后記
附錄:中國近代歷史大事年表
及時講 中國近代政治史開場白
我們為什么要學歷史?我的一個朋友曾提過一個很好的比喻:24小時早上你起來突然失憶了,忘記自己是誰了,想想看你今后該怎么生活——你誰都不認識,這意味著忘掉了自己的歷史。歷史看起來好像沒什么用,但實際上我們是離不開它的。其實對于一個民族,無論是其整體還是個人,記憶都是不可或缺的,歷史就是民族的記憶。很多人現在在某種程度上就是處于失憶狀態,所以一直安放不好自己的位置,在歷史長河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在世界格局中也定位不好自己的位置。
關于中國近代史的課,大學本科都在開,但是名義上講的是歷史,實際上卻不是當成歷史課開的,而是按政治課開的,即使在歷史系也是如此。這種課的主要目的是想給大家灌輸一種世界觀,一種意識形態,所以它其實是一個觀念史。所謂史實,是被要求服從某種觀念的。如果我們今天從一個常人的是非和真偽角度來看,這樣的歷史就是偽史。上這種政治課的時候,大家都興趣不大,經常睡覺或者看小說。但別看上課的時候不以為然,其實你還是或多或少會受它影響,一到在網上談某些事情的時候,只要涉及歷史,就不知不覺地把這套東西搬出來了。也就是說,我們會鄙視一個假的東西,但是我們依然依賴這個假的東西。這就令人很困惑。
我國的近代史,有一個范文瀾、胡繩的基本模式。這種模式通常有兩條線索,其中一條是帝國主義侵略論——自鴉片戰爭以來,西方列強總是侵略、欺負中國。強調這樣一條脈絡,由此證明我們這個民族是苦難深重的,同時說明我們的落后是因為別人侵略、欺負我們造成的。另一條線索就是革命線索——三大革命高潮,從太平天國、義和團然后到辛亥革命,總之就是一個反抗、革命的過程。這樣一段悲慘的近代史,一段總是折騰的歷史,很容易使我們忽略從晚清以來這么多豐富的變化,不知道該怎么走后面的路,不知道為什么要改革、要開放,為什么還要學洋人那一套東西。
事實上,如果我們不知道近代中國是怎樣融入世界的,或者無視這個過程,而只強調我們一直在革命,那么我們就不會明白為什么要放下革命搞建設,不會明白為什么要重新開放。結果也就只能是我們重來,再重來,重新開始鼓噪革命,重新開始鼓噪排外。可是這樣一來,我們會回到哪兒去呢?我們處在這樣一個過程之中,面臨著這樣的困惑。
對于近代史的“三婦”心態
以往我們對于中國近代史有三種慣常的態度。在此,請允許我打個不嚴謹的比方。及時種是怨婦心態,凡事以哭鬧為主,就是覺得你們總欺負我們,你們從頭到尾都欺負我們,我們冤得要死,我們苦大仇深,比竇娥還冤。總是在哭,總是在鬧。不僅哭鬧,還時不時要掀起衣襟給人看:我這傷疤就是當初你弄的。
圓明園那幾個水龍頭能賣出天價來,就是因為這種心態在作怪。那幾個水龍頭怎么可能是英法聯軍搶走的呢?當時圓明園珍寶如山,英法聯軍會搶這幾個按照西方的模式做出來的噴頭嗎?它們十有八九是在這個園子廢了以后,被中國人弄到外邊賣掉的。賣出去也就是當個擺設,當時仨瓜不值倆棗,現在卻賣給華人,賣到幾千萬,可見國人這種怨婦心態已經根深蒂固。
第二種是潑婦心態,凡事講打,打不過我撓。我要反抗,把整個近代史寫成僅僅是反抗的歷史,這個反抗的過程雖然可歌可泣,但畢竟沒打過什么勝仗,充其量就是撓人一把,還撓不到臉上。但是我們覺得很好,還很推崇,因而創造出很多神話。如果當時斗爭真有這么波瀾壯闊,那英國人根本進不來,我們也就根本不會有這段被稱為半殖民地的歷史。
第三種是情婦心態。它跟前面兩種心態正相反,在它看來,殖民歷史也是好歷史,不殖民我們怎么進步?但是被殖民的過程實際上是很屈辱的,不論在哪個國家都是如此,尤其對這個民族的上層精英來說。如果這些上層精英曾受過本民族悠久文化傳統的熏陶,他們就會感到更悲哀。但是情婦心態把這一層抹掉了——就覺得殖民是好事,能看到它給被殖民國家帶來文明,卻看不到殖民本身的掠奪和奴役。這種心態,其實有點變態。
“三婦”心態實際是我們國人對待近代歷史比較常見的心態。有人說,這好像都不大對頭啊,我們到底應該怎樣看待歷史和外來者呢?我說,我們能不能別在歷史和外國人面前當婦人。你可以將其當做朋友,也可以視為敵人,只要自己別像婦人一樣就成。關于心態問題,我覺得是在看待近代史的時候首先需要思考的問題。
中西兩種體系
所謂近代史,如果按中國傳統史學來說,就是晚清史。中國傳統史學,是朝代史,唐史、宋史、明史、清史這樣的。如果按世界史的劃分來說,晚清史只能算是中國近代史。我們怎么看待近代史,或者說怎么看待我們的晚清史,這個歷史過程到底意味著什么,這是我們首先要解決的問題。在我看來,晚清歷史的本質就是西方把中國拖入它們的世界體系的過程。西方有個世界體系,我們有一個天下體系,或者叫朝貢體系。但是我們這個天下體系(朝貢體系)是內斂的,是內縮的。就是說,并不是我去打了天下,征服了某塊殖民地,然后建立起一個朝貢體系讓其他人來服從我,而基本上是用一種文化的、一種以德服人的方式讓周邊國家來仰慕我的文化,然后向我進貢;或者以大國之威,讓周邊國家向我朝貢。有的朝代也會打一下,占了地方,不是當殖民地,而是直接占領。但往往控制不住,朝代末期又退了出來。在這個天下體系里,我呢,是中心,但并不知道世界周邊有多遠。朝貢體系就像一個圓,這個圓的中心是中國,而外延有多大不知道,多大都可以。你來不來我不管:你來朝貢,那是你向慕王化;如果你不來呢,隨你的便。顯然,這樣一個體系不是向外輸出的體系。但是西方自十八世紀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建立之后呢,實際便形成了一個輸出型的體系。它不斷地把這個體系向外輸出,把它所遇到的,能殖民的就殖民,不能殖民的也要把其納入自己的體系中來。在這兩種體系的碰撞中,我們的天下體系顯然崩潰了。
我們干不過人家,就得聽人家的。中國人開始是被動接受,人家兵臨城下,我們捏著鼻子忍受;后來有點主動性了,逐漸產生了解人家的欲望,開始學習《萬國公法》。我們在1860 年開始設置同文館的時候,主要學習的就是《萬國公法》。我們開始想了解這個世界體系是怎么回事——所謂的《萬國公法》,其實就是西方那個世界體系的規則。
開放口岸也是如此:開始是人家逼著我們開放,這次開放一些,下次再開放一些,后來我們就自己主動開放了。學習亦是如此:開始是被動學習,然后是半推半就、中體西用,是地學習。到了辛亥革命的時候就是地學習。不光是西學東漸,而且是西俗東漸。如果注意看一下那個時候的報紙,就會發現當時所有西洋的東西都被冠以“文明”兩個字。西式禮帽是文明帽,手杖是文明棍,自行車是文明車,連火柴都是文明火。話劇是文明戲,我們的京劇叫舊戲。凡是西洋的東西都意味著文明,都意味著是需要我們學習的。這說明什么呢?說明我們這個時候已經心悅誠服地被拖入了這個體系——我們認賬了。為何會這樣?因為西方世界迎合了人類創造和追求財富的需求,一旦這個世界的價值觀普及開來,會產生一種內在的驅動力驅使人們去進入它們的世界。這就是一個近代史的過程。
可能在我們今天看來,西方的世界體系不見得是什么好事情。它是在工業革命過程中建立的,跟工業革命息息相關。如果按考古學家張光直先生的說法,其實西方的發展道路是一個偶然,但是這個偶然卻造出了大事。為什么呢?因為工業革命創造出一個新工商文明,而現代工商文明這樣一個潘多拉之匣被打開后,世界就變了。這個地球上所有的人,或早或晚都得跟著走。
我覺得這個文明可能是不好的,它對資源掠奪和榨取得太厲害,對環境破壞得太快。就像《莊子》里那個故事,說是一個老頭在澆園子,園里有一口淺井,老頭每天拿個瓦罐跳到井里,打一罐水然后爬上來澆。子貢問他為什么不弄個桔槔(就是杠桿),那樣多方便。老人說他知道那個東西,但是他不用。為什么要用那玩意兒呢?它是機械,人用了機械就起機心了,就想著怎么取巧,從此天下就不得安寧了。其實道理就是如此,一旦把這個大工業文明喚出來之后,人們就天天想著怎么取巧——我們去發明創造,翻著花樣地想著怎樣去榨取資源——人類幾萬年的歷史都沒有弄出這么些事來,但這幾百年就都實現了,而且后面會怎么樣,人類還不知道。但是世界一旦進入這個軌道,潘多拉匣子一旦打開后,就回不去了。你想進去也罷,不想進也罷,都回不去了。你看這世界哪個地方還沒有進入這個體系?哪個地方還沒有受到工業文明的污染?哪個地方還是桃花源?沒有辦法。你只能在這個文明的基礎之上,想一點補救的辦法。比如出現了土壤板結、農藥污染問題,我們只能在工業文明基礎之上想辦法發明一種污染較小的農藥,以及使土地板結程度較低的化肥。我們只能在這個基礎之上往前走,不可能回去了。人類都不可能逃脫這個被工業化的命運,抗拒它是沒有用的。西方的發展道路或西方的世界給我們帶來這個東西,世界的命運已定,已然逃不過去了。
中國的抵抗
所謂中國的反抗史就是抗拒史,其中抗拒最激烈的就是義和團,他們把西方的一切都排斥掉了,把所有沾洋邊兒的東西全部干掉。從街上抓來一個長得像學生的人,搜搜包,如果發現里面有一張洋紙,那么那個人的腦袋就沒了。有一支鉛筆也不行,鋼筆更不行。當時他們盲目排外,排斥一切。而這樣做換來的是一個很悲慘的結果,我們被迫簽訂了《辛丑條約》。根據條約規定,外國可以在中國北京駐軍,從山海關到天津一線,中國軍隊不能駐軍,外國軍隊卻可以。天津也是如此。后來中國人要在這一帶駐軍,只能把軍隊服裝換成警服,以警察部隊的名義進駐。不僅如此,中國還賠了人家四億五千萬兩白銀。
這種抵抗是無效的,不僅中國的抵抗無效,其他地方,諸如奧斯曼帝國和非洲祖魯人的抵抗也是無效的。任何地方的這種抵抗都是無效的,因為這是大勢所趨。潘多拉的匣子一旦被打開,這個世界和人類的命運就已經被注定了。在西方的工業文明沒有出來之前,我們可能有很多種選擇。比如,我們可能還在慢慢地走,出門還騎驢。進京趕考的人給老婆寫封信,估計她三個月以后才能收到。過去的風俗,長久以來都這樣,或許現在某些地方還是這樣。因為中國兩千多年大體進步不大,拿秦朝和清朝比的話,我們的進步有限,尤其是技術進步有限。有人可能說,秦朝燒不出瓷器來,清朝可以燒出許多花樣的瓷器來。但秦朝的陶罐子也能頂用,一樣可以煮飯、打水。還有馬車,秦始皇那個時代的馬車,跟現在我們看到的馬車沒什么本質區別,除了現在的馬車是膠皮輪子而已,進步非常有限。
那個時候好不好呢?女性可能差點,只能待在家里,不能出去上學,婚姻大事都由別人做主,看上誰也不能直接嫁給他,除非你是卓文君。男性可能感覺還好,如果有本事就出來,考個秀才、中個舉人很爽的。很多人覺得我們在接受西方文明的過程中失去了一些東西。現在人們普遍活得比較緊張,文明越往后發展,人們越緊張,也就沒有閑暇去想其他的。一些有錢的讀書人閑下來,就會想現在的生活太沒意思、太乏味了,過去的日子多好啊,田園詩一樣的生活。吟吟詩,喝喝酒,談談風月,24小時到晚沒什么緊張事,一覺睡到自然醒,多舒服啊。人們會懷念這樣的生活。
實際上我們人類很難,作為人,很難有一種狀態是感覺非常好的。當我們回頭看歷史的時候就會發現,既然我們不可能逃脫這個命運,那么我們的感慨,我們的憤慨,或者我們的不滿意都只能是一種牢騷而已。那么我們干嗎要這么折騰呢?這樣想來,心情就會好一點,就會平和。我們可以設想,有沒有可能擺脫這條道路?其實歷史上很多人都在思考,是不是可以走一條有中國特色的新路。這個想法不是今天才有的,中國人一直都想走一條特色道路,一直都在想。
我們最早學日本。看上西方直接學西方就行了,干嗎學日本呢?日本納入西方是后來的事情,當時還不算西方呢。我們之所以學日本,是因為覺得日本好,學日本是捷徑。我們認為日本學西方是學了一條捷徑,我們如果直接學捷徑就更捷徑了。什么叫捷徑呢?就是抄小路。人家這么走,我們抄小路,抄近道,趕上去,走到前面去。后來我們又學俄國了,也是想抄近路。學俄國實際上也是學西方,看上去俄國人抄小路突然之間就富強了,就厲害了,就變成蘇聯可以跟美國人抗衡了。其實中間有一段時間我們還想學美國,辛亥革命以后成立了臨時政府,那就是美國模式。為什么學美國呢?因為當時我們認為美國是的,我們把的直接拿來用就行了。
抄近路學人家,是想把那些貌似是捷徑的東西學過來,這本質上就是想走一條中國自己的特色道路。這條道路無論怎樣,還是離不開工業文明。也就是說,無論怎么講中國特色,都不能回到孔子時代老牛破車的道路上去,都不能回避工業文明自搞一套。沙特是一個神權國家,但是它也接受西方文明。有時候接受得比較過分,一些大阿訇們會生氣抗議。國王一看大阿訇們抗議了,就悄悄令手下把大阿訇坐的高級轎車全部收走,封上封條。大阿訇們出來一看車被收了,就問為什么。得到的回答是:你們反對西方工業文明,而汽車那些玩意就是西方工業文明的產物,所以你們不能坐。大阿訇們想,不坐高級轎車,靠腿走路太難受了。于是之后再開會時,就同意了一些條例。也就是說,即使今天再保守的人,有一個問題也是能夠想通的:他會享受西方文明的成果,有小車就不坐大車,有電梯不會爬樓梯,如果爬一定是為了減肥。
我們現在能不能摸索出一條全新的路?我覺得很不容易,因為我們很難走出這個大框架,很難走出來一條跟這不一樣的道路。走自己的路,說說容易,做起來難。
還有,中國人能不能不挨打?說了,中國人學西方,但是為什么先生老打學生?的確,他們老打我們。但是回過頭來看,那個時候的中國人如果不挨打,能去向西方學習嗎?說實在話,我們走到今天也可以說是被打出來的。不挨打就學西方,日本人做到了。佩里艦隊去了,一看日本人沒什么大船,就遞上條約訂城下之盟,日本琢磨琢磨就軟了,就同意開放——日本的開放不是從明治維新時開始的,而是從幕府時代就開放了。還沒打,日本就開放了,然后在這個基礎上往前學。但是中國人做不到,這可能跟國民性或民族性有關。不挨打,就很難學人家,被打得很慘,才學得好一點。比如,在1901 年之后,那次被打得最慘,慈禧太后和光緒帝都從皇宮里逃了。大熱天的,太后那么大歲數了,化裝成農婦,坐著騾車,一路風餐露宿,還穿越苞米地,一身痱子,兩天兩夜連水都喝不上一口——這下可受苦了。所以我說帝王之尊得挨點餓,挨過餓后,施政、做事什么的就好一點。總這么養尊處優的話,根本沒法進步。
改革開放之后我們發現,日本的傳統其實維護得很好,西方看東方很多方面是看日本。日本的歷史和古代文化都不如我們悠久,但是為什么它在西方受到的評價那么高?就是因為它走出來了,它成功了。你現在成功了,人家才會重視你的過去。如果你現在什么也不是,那么你的過去就是一堆垃圾。就是你想發揚國粹、弘揚傳統,都沒機會。如果我們不能正確對待歷史,不能走出歷史,那么我們過去的歷史就什么都不是。
今天我們應該怎樣看這段歷史,又該怎么去做?很顯然,我們需要冷靜地審視過去,不能再當怨婦、潑婦、情婦。冷靜地審視過去,然后去看待我們的未來,盡早學得聰明些,不要總在一個坑里反復折騰、反復跌倒。如果我們不能很正確地看待這段歷史,就很難吸取教訓,很難避免過去的悲劇。我們必須從心理上走出我們的中世紀,才有前途,過去的輝煌歷史才有價值。
……
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
——克羅齊
冷靜地審視過去,然后去看待我們的未來,盡早學得聰明些,不要總在一個坑里反復折騰、反復跌倒。如果我們不能很正確地看待這段歷史,就很難吸取教訓,很難避免過去的悲劇。我們必須從心理上走出我們的中世紀,才有前途,過去的輝煌歷史才有價值。
——張鳴
以前讀張鳴老師的《歷史的底稿》的時候,沒怎么看上眼,覺得張老師寫短文看不出水平,這次讀了張教授的講課匯總,對張教授越來越高看了,不僅是那個在網絡世界“鐵肩擔道義”的功過知識分子,也是個在學術殿堂能夠“妙手著文章”的學者!
初高中的中國近代史,是從宏觀角度對這個時間段的歷史做一個講述,但是這本書,更多的是從某些微觀的角度進行陳述,從而甚至顛覆了我們以往對于中國近代史的宏觀認識!歷史就是這樣,應該從多角度,多方面進行研究和探討!不錯~贊!
非常不錯的一本歷史讀物,了解中國近代史,歷史對于一個國家來說就是一個國家的過去,正確面對歷史有助于今天的快速健康發展。以史為鑒,通過歷史了解國民的人生百態,舉一反三,更好把握人生。在歷史中,會對中國人整體的特性有所體現。
近來連續讀了兩本張鳴寫的有關辛亥年歷史的書,感覺以前對辛亥革命的了解近似于小時看電影時總要分出好人壞人一般幼稚,也許這不是個人的錯,是正統的宣傳造成的。讀書,歷史也許原本是這樣的,感謝那些告訴我們不一樣歷史的人。
張鳴,大鳴大放之年(1957)生人,注定敢曬觀點.在史學家高華的追悼會上,張鳴流淚道:“天要亮了”。你的書輕松而深沉,學問大,張教授的歷史知識融會貫通,文筆流暢,佩服。我買了兩本,送了一本給朋友,自己那本快看完了。感覺真好,愛不釋手。
買這本書是因為之前看過陳丹青老師的視頻里面有提到。買回來看完之后覺得,書的內容寫得比較客觀,確實寫得很吸引人。也顛覆了很多頭腦中錯誤的歷史知識。這樣的書籍,感覺收獲良多。所以,不管是沖著陳丹青還是張鳴,我覺得這本書值得一讀。
這本書不是一部正襟危坐的近代史,每次讀后之后都有一種輕松的感覺。可貌似不嚴肅的外表背后卻蘊含對于中國近代歷史的深層次思考,它沒有要求讀者在應然和實然之間選擇,只是告訴大家一些事實,這樣的學術態度,不禁叫人欽佩!
全書講了從鴉片戰爭到五四的這段歷史(尤其注意五四到建國這段時間的歷史是沒有的,購者慎選)。其實就是張鳴上課的講錄,其中對于很多歷史事件和人物倒真是“重說”了一次,能夠讓人有一些新的啟發和思考,對于辯證的史觀形成確有好處。
冷靜地審視過去,然后去看待我們的未來,盡早學得聰明些,不要總在一個坑里反復折騰、反復跌倒。如果我們不能很正確地看待這段歷史,就很難吸取教訓,很難避免過去的悲劇。我們必須從心理上走出我們的中世紀,才有前途,過去的輝煌歷史才有價值。
張鳴暢銷代表作,還原一段被扭曲的歷史,挖掘國人今日問題之根源,解讀張鳴、解讀完整的晚清七十年。一個寫史的“局外人”——《南方人物周刊》,竇文濤、易中天、梁文道等熱議與推崇)
此書讀罷,對晚清那段歷史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中學教育所知的零碎的歷史片段,由書中的前因后果分析串聯起來,明白了許多。此書的確做到了"還原一段被扭曲的歷史”,但談到"挖掘國人今日問題之根源”上,就有點過譽了。
真的很不錯的一本書,能讓我們重新更加理性的去反思這過去的一百多年,里面的人物并不像在課本上學到的一樣黑白分明,作者以一種十分客觀的角度去闡釋一段被扭曲的歷史,使近代史不再是一門避重就輕的“政治課”而成為原汁原味的歷史
重說中國近代史 英E國對中國政策的成本核算 中英的戰爭技術和戰略對2比 開放教禁帶來了西方的輸入O 傳統歷史W締造的兩個神這個人第十三講M 袁世凱的悲劇K 共和體制的問題 袁世凱與國民10黨的對4峙 8袁世凱的悲劇第E十四講2 黯然北洋A
又是張鳴教授的書,真的很好。從書中能看到些真實的歷史,比中學課本上講的好多了。讀起來也很痛快,不像課本那么枯燥。真希望能有更多的教授像張教授一樣,多說點真話。張鳴教授的書我基本都買了,強力推薦各位買來看一看。受益非淺
說實話,讀中國近代史,也是我第一次人是自己想去看這些歷史。近代史寫的不錯。從清朝末年講到中國近代。。也講了一些近代史發生的一些大事。。太平天國起義什么的。。都很詳細。寫的很好!
中國近代史可以說是沉重的歷史。我們都不想面對也不愿面對的歷史。可是我們要想在當今發展就必須正視這段歷史,對我們現在和今后都非常重要。而張鳴老師帶領我們重溫這段歷史,我們應當認真學習思考。感謝張鳴老師!
張鳴的這本書我很喜歡,可惜第一本被借走了,后來又買了馬勇的《坦然面對歷史的傷》,本想從不同的敘述中了解更多的信息和不同的觀點,只是實在難以下咽,馬勇的寫作風格絮絮叨叨讓人看不下去。還是懷念張鳴的書,才又買了第二次。
很有意思的中國近代史,鴉片戰爭、、辛亥革命、、太平天國、義和團、慈禧太后、袁世凱,都談了。不晦澀。加了不少個人邏輯分析。有些辟謠觀點。但也不能說這本書就一定是正確的。相對嚴肅些。盡信書不如無書了。應該看些更嚴肅的歷史。以史為鑒。
看了幾頁不想看下去了,作者作為人民大學的教授,對義和團的鼓吹和對傳教士的敵視,已刻上階級的烙印,后悔邁著本書了
在張鳴老師的還原下,中國近代史變得如此復雜、精彩,又是如此的顛覆,它與我們記憶里的古板印象迥然不同,絕非教科書上的忠奸兩列、黑白分明。當諸多人物與史實呈現在我們面前時,難以用一句簡單的是非作判定,在正視一段被扭曲的中國近代史的同時,我們也能發現國人今日問題的精神根源。
值得一讀,有自己的視角!推薦購買! 雖然不是嚴肅專著,但提供了一種新的視角和觀點,重新了解近代史的種種觀點和結論。其實作為一個脈絡挺好的,由此進去,更深入的基于史料和專業著作進一步了解這段歷史才是這本書的最大價值。
張鳴老師開篇對于歷史作用的比喻讓我耳目一新,比喻太貼切了。歷史如同一個人的記憶,看似無用。但當某一天我們完全失憶,我還是我嗎?我是誰,我走向哪里都沒有了意義。看不清歷史就看不到自己的未來,也喜歡張鳴老師有點憤青的感覺
中國近代史變得如此復雜、精彩,又是如此的顛覆,它與我們記憶里的古板印象迥然不同,絕非教科書上的忠奸兩列、黑白分明。當諸多人物與史實呈現在我們面前時,難以用一句簡單的是非作判定,在正視一段被扭曲的中國近代史的同時,我們也能發現國人今日問題的精神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