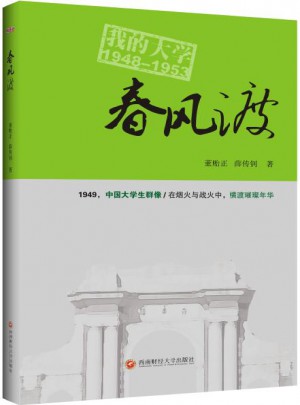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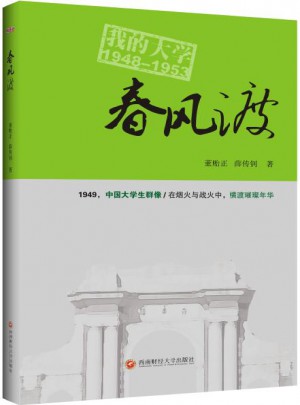
他們生于1930年代的中國,出身中產(chǎn)家庭,1948年進(jìn)入清華大學(xué),是當(dāng)時(shí)的學(xué)界精英。他們受業(yè)于中國最知名學(xué)者,近距離領(lǐng)略了王竹溪、錢三強(qiáng)、何成鈞、孫瑞藩、翦伯贊、嚴(yán)景耀、雷潔瓊、陳岱孫等大師的風(fēng)采。他們在求學(xué)期間親身經(jīng)歷了諸多歷史事件,見證了那個(gè)風(fēng)云變幻的大時(shí)代。本書既是個(gè)人大學(xué)生活的回顧,也是當(dāng)時(shí)社會(huì)和國運(yùn)的縮影與投射。
1.本書作者董貽正1948年從上海租界考入清華大學(xué);薛傳釗則1948年從香港考入燕京大學(xué),后轉(zhuǎn)入清華大學(xué);他們詳細(xì)回憶了以清華大學(xué)為代表的解放前的大學(xué)教育,與后來的大學(xué)狀態(tài)不同。這些敘述不僅給我們提供了珍貴史料,更讓我們了解曾經(jīng)有過的大學(xué)的風(fēng)貌。
2.1948-1953年,中國社會(huì)經(jīng)歷突變,清華大學(xué)不僅親自聆聽了現(xiàn)當(dāng)代著名的大師的授課,還經(jīng)歷了國民黨炮臺架進(jìn)校園、炮彈扔進(jìn)會(huì)堂、地下黨風(fēng)起云涌的組織活動(dòng),更經(jīng)歷了青年學(xué)子迎接北平解放、參加開國大典在天安門游行等重大歷史事件。這些來自親歷者一線的熱血經(jīng)歷和溫情回憶,是不可多得的口述歷史。
董貽正,男,1931年間月出生于上海市,漢族。1948—1952年就讀于清華大學(xué)電機(jī)系。
薛傳釗,女,原籍廣東中山,1930年生于上海,年幼時(shí)隨父母逃難,流離顛沛,輾轉(zhuǎn)數(shù)年。抗戰(zhàn)勝利后,在廣州培道女中念完高中。1949年夏從香港飄海北上,考入燕京大學(xué)社會(huì)系,1950年轉(zhuǎn)入清華大學(xué)經(jīng)濟(jì)系。
一路向北
我們當(dāng)年考大學(xué)
馬桶上聽到被清華錄取的消息
一路向北
來到北京,來到清華園
1949年的清華
國府末日
清華的學(xué)習(xí)生活和我的老師們
清華特色
特殊背景下的社團(tuán)"團(tuán)契"
新民主主義青年聯(lián)盟
國民黨走了,共產(chǎn)黨來了
參與迎接北平解放
三次申請入黨
在清華園參加的政治運(yùn)動(dòng)
在畢業(yè)證書上蓋章的兩位校務(wù)委員會(huì)主任
我們這個(gè)班
畢業(yè)奔赴東北
重返北京
用土辦法來測算所需各類專業(yè)人員的比例關(guān)系
學(xué)于天地間
奔赴解放區(qū)
穿越封鎖線
燕京一年
翦伯贊教我中國社會(huì)史
體育和音樂史的陶冶
燕京的課外生活
參加開國大典
到京郊參加
轉(zhuǎn)學(xué)去清華
清華的學(xué)風(fēng)與校訓(xùn)
大學(xué)有大師
馬約翰教授的體育課
課外的錘煉
多才多藝的清華學(xué)子
孫曉邨、張君秋和烏蘭諾娃的指導(dǎo)
到印度大使館借服裝
去廣西參加
董必武送行團(tuán)
前奏
進(jìn)駐山區(qū)"土匪村"
那些事兒
邕江江畔的彩虹
及時(shí)次參與"戰(zhàn)地手術(shù)"
一只掉出來的眼球
從看攤到接生
團(tuán)部工作剪影
向知名的人民藝術(shù)家學(xué)習(xí)
張定和的委屈
同安娥和田漢的接觸
巧遇詩人艾青和作家李又然
豐收中凱旋
畢業(yè)前
騎河樓老校舍和皂君廟新校
清華的學(xué)習(xí)生活和我的老師們
清華校長梅貽琦早就說過:"大學(xué)者,非有大樓之謂也,蓋有大師之謂也。"事實(shí)上,清華不僅有大樓(當(dāng)然,同現(xiàn)在幾萬人規(guī)模的大清華相比,這些樓顯得小了些,但即使現(xiàn)在,看到科學(xué)館、化學(xué)館等建筑,仍然會(huì)肅然起敬),但更重要的是,清華有聞名國內(nèi)外的大師們。這些大師,既是學(xué)術(shù)殿堂的締造者,也是民族堡壘的捍衛(wèi)者。清華在1952年"以蘇為師",進(jìn)行院系調(diào)整前,工學(xué)院固然在國內(nèi)外頗有影響,但文、法、理,甚至農(nóng)學(xué)院更有過之。看到清華如此學(xué)習(xí)環(huán)境,真是滿心歡喜。能夠在這樣大師云集的學(xué)校里求知,真是一生的幸事!
但是,我這個(gè)人資質(zhì)平庸,學(xué)習(xí)方法又不對頭,因此面對眾多大師如此豐富的知識寶藏,我卻未能從中汲取充分的營養(yǎng),更不能從他們智慧的腦袋中獲取探索科學(xué)門徑的密碼。但畢竟在這種強(qiáng)大氣場的影響下,也多少學(xué)到了為人、求知、做事的正道,使我以后在社會(huì)上能堅(jiān)守底線,奮發(fā)求知,雖然沒能為母校增添光彩,但也沒有辜負(fù)母校的期望。
回顧在清華4年的學(xué)習(xí)生活,確實(shí)是平平而已。所以,有的同事在向初次見面的朋友介紹我時(shí)往往會(huì)說:這是清華的高才生,我會(huì)立即否認(rèn)。這不是謙虛,而是實(shí)事求是。因?yàn)椋M(jìn)清華的,絕大多數(shù)確實(shí)都是高中學(xué)校的高才生;但出清華時(shí),就不一定是清華的高才生了。當(dāng)然,清華不乏高才生,他們善于思考,鉆研問題深,總結(jié)概括能力很強(qiáng)。
大一課程工學(xué)院各系基本相同,有國文、英文、微積分、普通物理、畫法幾何、經(jīng)濟(jì)學(xué)概論。普通物理是理、工學(xué)院學(xué)生的必修課,學(xué)生多,分4個(gè)大班,國文、英文、微積分則都是二三十人的小班,物理課分別由王竹溪、錢三強(qiáng)、何成鈞、孫瑞藩講授。其中,王竹溪和錢三強(qiáng)都是教授。按清華的規(guī)定,所有教授都要輪流講授基礎(chǔ)課,他們倆也不例外。1947年錢三強(qiáng)回國時(shí),已以其發(fā)現(xiàn)核反應(yīng)三裂變的重大研究成果轟動(dòng)世界科學(xué)界;王竹溪的資歷更深。1971年夏,楊振寧及時(shí)次回大陸探親訪友時(shí),曾向總理點(diǎn)名要求拜見的少數(shù)幾個(gè)人中,就有他在西南聯(lián)大做研究生時(shí)的導(dǎo)師王竹溪,王竹溪這才從北大在江西鯉魚洲的五七干校回到北京。但據(jù)高年級學(xué)長介紹,他們認(rèn)為講課講得好的還是何成鈞老師,工科的很多同學(xué)都選他的課,我也選了何老師的課。他用四川話講課,抑揚(yáng)頓挫,條理清晰。
物理課有兩位助教,其中一位是陳篪,中等個(gè)兒,長個(gè)娃娃臉,說話細(xì)聲細(xì)氣,對學(xué)生很客氣,但要求又很嚴(yán)格,對實(shí)驗(yàn)數(shù)據(jù)的處理就是從他哪兒學(xué)到的。新中國成立后他主動(dòng)要求去鞍鋼工作,這在當(dāng)時(shí)也是一種小潮流,認(rèn)為搞建設(shè)了,還是要以工為主。我們班上兩位女同學(xué)也是從物理系四年級轉(zhuǎn)到電機(jī)系二年級的。以后陳篪又調(diào)入鋼鐵研究院,任物理室主任。在他確診為甲狀腺癌癥后,住院期間,還堅(jiān)持看書學(xué)習(xí),進(jìn)行運(yùn)算,并表示要寫信給黨支部:"生命不息,戰(zhàn)斗不止。"但就是這樣一位好同志,被當(dāng)作"白專"典型來批判。粉碎""后,冶金部黨組把他樹為"冶金科技戰(zhàn)線的鐵人"。
數(shù)學(xué)課馬良老師講微積分。開學(xué)前,高年級學(xué)長就向我們介紹了一些老師的特點(diǎn),總的印象是學(xué)識淵博,要求嚴(yán)格,特別是會(huì)對新生來個(gè)"下馬威"。開學(xué)后,果真體驗(yàn)到了。馬老師上課時(shí)經(jīng)常來個(gè)10分鐘的小測驗(yàn),有的在講課前,有的在課程的10分鐘。本來,微積分我在中學(xué)時(shí)就自學(xué)過,覺得并不難,但幾堂課下來,把我"烤煳"了。好在老師們采取的方針是"考試從嚴(yán),給分從寬",有的老師按實(shí)際得分的開方乘以10,作為正式成績,這樣算來就是36分算及格,也算是放我們一馬。
畫法幾何由褚士荃老師主講。他是清華的訓(xùn)導(dǎo)長。在我印象里,訓(xùn)導(dǎo)長都是國民黨的黨團(tuán)骨干,是鎮(zhèn)壓學(xué)生運(yùn)動(dòng)的幫手。但褚老師是慈眉祥目的,聽說他還幫助黑名單上的學(xué)生逃離清華。但這門課一般安排在下午及時(shí)節(jié),那時(shí)有些發(fā)困,但主要是自己對三維圖像概念差,因此,這門課也沒學(xué)好。
好像也是在一年級,有一門金工實(shí)習(xí),由機(jī)械系強(qiáng)明倫教授主講。該實(shí)習(xí)課要求要親自動(dòng)手把一塊粗鋼加工成長方形的鋼塊,四周要挫得有棱有角。這又暴露出我的動(dòng)手能力差的弱點(diǎn)。至于車床等機(jī)器設(shè)備,也只是大概知其操作方法而已。
一年級下學(xué)期已是新中國成立后的新清華了,課程也多少有些變動(dòng)。原本要上的普通化學(xué)和工程測量課,電機(jī)系的學(xué)生就免修了。英文課,凡是考試合格的也免修了。
進(jìn)入二年級,有兩門重點(diǎn)課程:一是電工原理,二是材料力學(xué)。前者是電機(jī)系的專業(yè)基礎(chǔ)課,這才開始同電機(jī)系接觸了。清華電機(jī)系是1932年秋創(chuàng)立的,及時(shí)任系主任由工學(xué)院院長、美國麻省理工學(xué)院及時(shí)個(gè)中國博士顧毓琇教授兼任。電機(jī)系的辦學(xué)宗旨、課程設(shè)置、教學(xué)方法甚至教材選擇,都采用美國麻省理工學(xué)院電機(jī)工程系的模式。早在上海讀高中時(shí),我就久仰MIT(麻省理工學(xué)院英語的縮寫)的大名,有"世界理工大學(xué)之最"的稱號,有眾多的諾貝爾獎(jiǎng)獲得者(至2009年,先后有78位諾貝爾獎(jiǎng)得主曾在麻省理工學(xué)院學(xué)習(xí)或工作),在我的心目中MIT甚至超過了哈佛、耶魯。而在MIT的眾多專業(yè)中,尤其以電子工程系名聲最響。現(xiàn)在,在眾多大學(xué)排名榜里,麻省理工學(xué)院均位列世界前五位。
教"電工原理"的是孫紹先教授。新中國成立前這些課程都是英文講課,原版教材;可是到了二年級就是新中國成立后了,在新時(shí)期,在"一邊倒"的思想指導(dǎo)下,要肅清"親美、恐美、崇美"思想,教授們都是用中文講課,"電工原理"當(dāng)然不能例外,也是自編中文講義了。孫紹先是東北人,1945年獲麻省理工學(xué)院碩士學(xué)位。他講課語速較快,對所講內(nèi)容爛熟于心,十分重視概念的理解。但在""中,他被誣陷為美國特務(wù),曾兩次自殺未遂。有意思的是,他的兒子孫立哲卻被親自圈定為5名知青先進(jìn)典型之一。孫立哲""中從清華附中到延安插隊(duì),成了赤腳醫(yī)生,自學(xué)成才,在農(nóng)村做了上千例手術(shù),治愈了不少鄉(xiāng)親的病。1983年,他獲得美國西北大學(xué)博士學(xué)位。
這門課配了4名助教,足見其重要性。他們平時(shí)對學(xué)生進(jìn)行輔導(dǎo)、答疑、指導(dǎo)實(shí)驗(yàn)。考前幫助同學(xué)進(jìn)行復(fù)習(xí),對同學(xué)很關(guān)心,也很有耐心。四位助教都不是泛泛之輩,他們后來都是教授。其中王先沖當(dāng)時(shí)已是講師,是批博士研究生導(dǎo)師之一,還有一位吳佑壽,他們兩人后來都是中國工程院院士;另一位南德恒,我們給他起的外號叫"難得很";金蘭,同學(xué)們也是取其諧音,取外號"真難"。從中也可看出同學(xué)們對這門課程的敬畏之情。三位老師也回校參加慶典,竟然還能叫得出很多同學(xué)的名字。
遺憾的是,這門課我沒學(xué)好,學(xué)期末了的考試,我居然成為極少數(shù)幾個(gè)不及格的人員之一。雖然同學(xué)們沒有任何輕視之意,但這畢竟是我及時(shí)次在學(xué)習(xí)上遭遇滑鐵盧,當(dāng)時(shí)的心情可想而知。這年暑假,我沒有回家,我把這事寫信告訴了父親。從上學(xué)以來,父親從來不過問我的學(xué)習(xí)成績,我也從來沒有給他看過成績單。這次我把成績告訴了他之后,他回信毫無責(zé)備之意,只是要我總結(jié)學(xué)習(xí)方法,加以改進(jìn)而已。
這次滑鐵盧對我的影響還是很大的。過去中學(xué)那一套學(xué)習(xí)方法,主要是靠死記硬背,靠多做習(xí)題,對基本概念缺乏深刻理解,不能把各種觀念融會(huì)貫通。而有的同學(xué),老師講完一章,就把這章內(nèi)容歸納成一張圖表,各種概念之間的聯(lián)系說得一清二楚。于是第二年重修時(shí),也朝這個(gè)方向努力,這次得了80多分,多少有了些進(jìn)步。
二年級的另一重頭課是材料力學(xué),有兩個(gè)班,分別由錢偉長和張維教授講授。一般機(jī)械系的都安排在錢偉長的班上,非機(jī)械系的則是由張維教授講授。錢偉長是無錫人,個(gè)兒不高,戴副眼鏡,言談溫雅,風(fēng)流倜儻。雖然不擔(dān)任我們的課程,但他的名氣很大。他是有"火箭之父"美稱的美籍猶太人馮·卡門教授的弟子。1937年他考入清華時(shí),國文和歷史都是100分,而數(shù)學(xué)則是接近零分。九一八事變后,他決心棄文學(xué)工,經(jīng)過一番嚴(yán)格的考核,終于轉(zhuǎn)系成功,最終成為世界著名的科學(xué)家。張維教授是柏林工業(yè)大學(xué)的博士。他不僅講課講得好,而且關(guān)心同學(xué)的發(fā)展。雖然他是機(jī)械系的教授,但是在春假帶領(lǐng)我們電機(jī)系學(xué)生外出郊游的老師,記得地點(diǎn)是在黑龍?zhí)叮F(xiàn)在我們同學(xué)中還保存有郊游時(shí)的照片。他的夫人陸士嘉是航空系的教授,也是留德的博士,他們是在德國留學(xué)時(shí)結(jié)為伉儷的。他們夫婦都是中國科學(xué)院及時(shí)批院士。
三年級開始分組了。那時(shí)沒有專業(yè)之分,電機(jī)系下分三個(gè)組:電機(jī)制造、發(fā)電、電訊。我選擇了發(fā)電。三個(gè)組的課程不盡相同了。發(fā)電組的,本系的課程有章明濤教授的"交流電機(jī)"、鐘士模教授的"電機(jī)原理"、楊津基教授的"高壓工程"、黃眉的"輸配電工程",還有范崇武、唐統(tǒng)一教授等的課程。外系課有劉仙洲的"機(jī)械原理"、莊前鼎的"熱力學(xué)"、張光斗的"水力發(fā)電",都是這方面的。此后的課程,就不那么吃力了,分?jǐn)?shù)也上去了。
章明濤是電機(jī)系系主任,也是浙江鄞縣人,和我該是小同鄉(xiāng)吧。1929年22歲時(shí),他在英國獲得碩士學(xué)位。1932年清華電機(jī)系成立時(shí),25歲的他就被聘任為教授。新中國成立后,他當(dāng)選為及時(shí)批中國科學(xué)院學(xué)部委員。1992年,朱镕基的一篇短文《為學(xué)與為人》,就記錄了章先生的一段話:"你們來到清華,既要學(xué)習(xí)怎樣為學(xué),更要學(xué)會(huì)怎樣為人,青年人首先要學(xué)`為人`,然后才是學(xué)`為學(xué)`。為人不好,為學(xué)再好也可能成為害群之馬。學(xué)為人,首先是當(dāng)一個(gè)有骨氣的中國人。"這番話,擲地有聲,終生難忘。
鐘士模是MIT電機(jī)工程系的博士,教授"電路原理"。他身材比較魁梧,圓圓的臉,膚色黝黑,講課條理清晰,課后同學(xué)生互動(dòng)較多,是最受學(xué)生歡迎的教師之一。以后他奉命籌建全國及時(shí)個(gè)自動(dòng)控制系,并被任命為系主任。1971年5月11日在一次會(huì)議上,他心臟病突發(fā),經(jīng)搶救無效逝世,時(shí)年僅60歲。
楊津基教授是留德的,講授"高壓工程"。希特勒執(zhí)政時(shí),他正好在德國。他私底下同我們閑聊時(shí),說起當(dāng)時(shí)德國的經(jīng)濟(jì)發(fā)展,還是推崇有加。這些話,如果晚幾年被人聽到,肯定是"吃不了兜著走"。
劉仙洲教"機(jī)械原理",在這些教授中他的年齡較大,執(zhí)著于研究中國機(jī)械史。1952年春節(jié),我們幾個(gè)同學(xué)去他家拜年,他的書桌前攤放著一些線裝書,正在專心研究。他說,他年紀(jì)大了,過年的事無所謂了;他當(dāng)時(shí)是河北省人民政府的委員,我們談起剛被處決的劉青山、張子善,他也不加表態(tài),給人感覺是一位"只做學(xué)問,不問政治"的忠厚長者。1955年他加入了共產(chǎn)黨,在教授們中影響很大。
也有的教授因?yàn)樵趪顸h時(shí)擔(dān)任過一些職務(wù),以致在相當(dāng)長的時(shí)間里,得不到任用,未能發(fā)揮其專長。直到粉碎""后,才重新煥發(fā)其青春。
到四年級下學(xué)期時(shí),已經(jīng)是1952年,全國性的"三反""五反"開始了,四年級大部分同學(xué)都抽出來搞運(yùn)動(dòng),所以上半學(xué)期還是按正規(guī)上學(xué),下學(xué)期除還有極少的課程外,主要是做畢業(yè)論文。后來,課基本上都停了,畢業(yè)論文也免做了。
翦伯贊教我中國社會(huì)史
我不能忘懷的課程之一,就是翦伯贊老師的中國社會(huì)史的講授方法。他能把每一階段的社會(huì)狀態(tài),從政治、經(jīng)濟(jì)、文化等不同的角度來描述,當(dāng)然還要講述一些史實(shí)加以說明。因?yàn)闆]有課本,我比較注意做筆記。講到一定階段則組織討論,一般由他親自來主持。我記得及時(shí)次參加討論時(shí),人數(shù)不多。他要求每個(gè)同學(xué)在每個(gè)階段聽課后,要將自學(xué)中存在的問題都提出來,似乎希望每人都要提出一兩個(gè)問題。學(xué)歷史,一般地講,很少有聽不懂的問題,重要的是要求每個(gè)人開動(dòng)腦筋去想、去理解并從中發(fā)現(xiàn)問題。當(dāng)時(shí)我真不知提個(gè)什么問題好,迫于無奈,挖出一個(gè)莫明其妙的問題:"從猿到人,是先直立起來用手勞動(dòng)的呢?還是先會(huì)用手勞動(dòng),再直立起來的呢?""怎么證明人是從猿演變而來,而不是兩種不同的品種呢?"老師立刻笑著說:"哈哈,她提了一個(gè)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問題,大家討論吧!"每次討論會(huì),他都要求大家提問題、發(fā)言,然后由他做總結(jié)。這樣的討論會(huì)使我深知:必須認(rèn)真去消化課堂上的內(nèi)容,還要參閱一些資料之后,才能提出像樣的問題。平時(shí)討論的問題我已經(jīng)記不清楚了,但及時(shí)次討論會(huì)使我留下深深的印象,促使我認(rèn)真地去對待這門課程。不管怎么說,這種教學(xué)方法在中學(xué)里是沒有經(jīng)歷過的。新中國成立后一般的學(xué)習(xí)討論會(huì)是比較常見的,所不同的是并非所有討論會(huì)都像翦老師主持的那樣,參加的人從老師到同學(xué)都那么認(rèn)真,而且都能敞開思想進(jìn)行探索。時(shí)間長了,習(xí)慣了,探討的問題就更寬廣、更深入。有時(shí)我們會(huì)討論劃分封建社會(huì)(或奴隸社會(huì)等)的依據(jù)是什么?為什么歷史時(shí)期的劃分總是以朝代、君王為界線?勞動(dòng)人民創(chuàng)造歷史在歷史書中如何來體現(xiàn)?……除了在討論會(huì)上能探討學(xué)習(xí)中我遇到和想到的問題,每次考試的題目也是充滿了探索學(xué)術(shù)的氣息。一年的課程,確實(shí)使我學(xué)會(huì)了許多知識,學(xué)會(huì)一些研究問題的方法,學(xué)會(huì)了一點(diǎn)治學(xué)的應(yīng)有態(tài)度。這都是翦伯贊老師帶給我們的。我不僅對這門課產(chǎn)生了興趣,而且對翦老師的博學(xué)多聞,以及他那種平易近人、諄諄教導(dǎo)、啟發(fā)式的教學(xué)方法留下了難忘而深刻的印象。對他的治學(xué)、教學(xué)態(tài)度更是由衷地尊敬。他宅前有幾棵桃樹,當(dāng)桃子熟了的時(shí)候,他都會(huì)約請我們這幾個(gè)學(xué)生到他家聚會(huì)聊天,或一塊嘗嘗新鮮的桃子。一年學(xué)習(xí)結(jié)束時(shí),我整整做了兩大本筆記,還有一些大幅圖表。翦老師看了很高興。他為了編寫新書,向我借走了全部筆記和圖表。當(dāng)然,我非常樂意為他做一點(diǎn)對他有用的事情。我后來也沒有想到問他取回來。現(xiàn)在,我們每一想到這位大師級的恩師在中的悲慘遭遇,就免不了黯然傷神。
燕京的課外生活
1949—1950年燕園的風(fēng)物人情給我留下的回憶是如此深刻,如此激發(fā)著我的情感;然而燕園墻外的巨大變化卻震撼著我的思想,潛移默化地改造著我的價(jià)值觀、世界觀。新中國成立前后的許多重大歷史事件,震動(dòng)了神州大地,也震動(dòng)了整個(gè)世界。其實(shí),首都的變化早已引起燕園墻內(nèi)悄悄地變化,只不過我開始時(shí)也察覺不多罷了。但是后來發(fā)生的幾件大事,卻猛烈地沖擊著每一個(gè)青年的燕園學(xué)子和師長們,而且深深地吸引了我。
有24小時(shí),社會(huì)系的同學(xué)們聚在老師家中的客廳里,聚精會(huì)神地聆聽著翦伯贊老師,還有嚴(yán)景耀(注4)、雷潔瓊(注5)等老師的談話。他們是那么興奮,熱情向我們介紹1949年9月21日在北京召開的全國及時(shí)次政治協(xié)商會(huì)議的盛況。不但告訴我們參加會(huì)議的人物和討論的內(nèi)容,還拿出不同樣式的國旗、國徽方案,并詳細(xì)說明這些圖樣象征著什么?還解釋為什么采用"義勇軍進(jìn)行曲"作為國歌等,并告訴我們1949年10月1日將在天安門宣布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師生們十分興奮地度過了這難忘的一席夜談。這時(shí),我才知道,我們系里竟有這么多老師都是受國家、人民尊敬的政協(xié)委員,而且他們都曾為祖國的解放做出過許多貢獻(xiàn)。我及時(shí)次為國家大事而振奮,而激動(dòng)!
從那時(shí)起,我除了努力學(xué)好所選的課程外,開始擠出更多的時(shí)間關(guān)心課堂以外的事情,并開始閱讀各種有關(guān)抗戰(zhàn)時(shí)期、解放戰(zhàn)爭時(shí)期的小說和書籍,如《新兒女英雄傳》(注6)《趙一曼的故事》(注7)《青年近衛(wèi)軍》(注8)《西行漫記》(注9)……這些書過去沒有看過,從那時(shí)起就很快被我迷上了。一到周末我們還會(huì)同一些同學(xué)到清華大學(xué)看《白毛女》(注10)《劉胡蘭》(注11)等歌劇或話劇。它們嶄新的內(nèi)容、嶄新的唱腔和表演方式,使我覺得既樸實(shí)又感人,這一切生動(dòng)活潑而潛移默化的教育,也使我思想的深處在不斷地變化著。
與此同時(shí),還有兩件實(shí)事也在我們身邊發(fā)生了。1950年春天,學(xué)校里分了一塊菜地給我們社會(huì)系一年級的新生,讓我們五個(gè)人一塊在那片不算很大的地里種菜、種瓜,我們每周要到菜地里澆水、除草、施肥,勞動(dòng)一兩次。燕京大學(xué)其他的院系和鄰近的清華大學(xué)也都這樣地發(fā)動(dòng)和組織同學(xué)自己學(xué)種一部分蔬菜。這件事雖小,但對我們這些從未接觸過土地的年輕人來說,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也知道撒下種子,讓它發(fā)芽、長出來并不難,但要讓它長得"茁壯""像樣"倒并不容易。不僅要有一點(diǎn)種植的知識,更要我們精心地呵護(hù)它。我們要時(shí)刻惦記著它是"渴"啦,還是"澇"啦;是否會(huì)被風(fēng)刮倒,或是否被蟲子咬了?終于菜是長起來了,但都不那么"光彩奪目"。這讓我們知道干什么事,包括農(nóng)民、工人所干的"力氣活"都不是那么容易的。
另一件實(shí)事是讓我們到校園附近的農(nóng)民居住區(qū),給失學(xué)的農(nóng)家孩子上課。這是我生平及時(shí)次給別人上課。這些孩子家境貧困、衣衫襤褸、渾身臟兮兮的,還有些難聞的氣味。他們?nèi)藬?shù)不多,程度不齊,擠在一間破舊的土屋里,充滿好奇地、擠眉弄眼地等待著我們給他們上課。讓我教的是小學(xué)三年級和五年級的班,他們分開坐在兩側(cè),我只能給一側(cè)的孩子講算術(shù),讓另一側(cè)的孩子做作業(yè);隔一會(huì)兒再交換地講課和布置作業(yè),搞得我手忙腳亂。這雖然純粹是盡義務(wù),但我的確從心底里挺樂意為此而忙碌。因?yàn)檫@讓我有機(jī)會(huì)接觸社會(huì),認(rèn)識到一墻之隔的差異竟然這么大,老百姓要解決的困難實(shí)在太多了。
大學(xué)有大師
清華的老校長梅貽琦(注19)先生有一句論大學(xué)的名言:"所謂大學(xué)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我進(jìn)清華的時(shí)候,無論是理、工、文、法、農(nóng)學(xué)院,都是大師云集,舉國聞名者何止數(shù)十上百人。我們的法學(xué)院院長兼經(jīng)濟(jì)系主任陳岱孫老師就是一個(gè)經(jīng)濟(jì)學(xué)方面的泰斗。經(jīng)濟(jì)系的主要課程之一是"財(cái)政學(xué)",這就是當(dāng)時(shí)由陳岱孫(注20)教授開的課。這門課主要是為三年級同學(xué)開設(shè)的主課。我們這些長期向往名教授,又是剛轉(zhuǎn)學(xué)到清華的同學(xué),總惦記著去旁聽他的課,盡早親自體會(huì)他講課的風(fēng)采和魅力。當(dāng)時(shí),"財(cái)政學(xué)"對我來說還十分陌生,并認(rèn)為是一門非常深?yuàn)W、難懂的課程。到校不久,我們終于擠出了時(shí)間踏進(jìn)了陳先生講授財(cái)政學(xué)的大教室里,全神貫注地先聽為快,并努力記好筆記。陳老師講課十分嚴(yán)肅,他有理有據(jù),侃侃道來,既旁征博引,又闡述自己的獨(dú)立見解,內(nèi)容精煉而豐富,邏輯性強(qiáng),很有理論深度。可惜我當(dāng)時(shí)的經(jīng)濟(jì)學(xué)水平還缺乏根基,有些道理在課堂上一時(shí)消化不了。下課后,我再次細(xì)讀所記的筆記,我這才發(fā)現(xiàn)陳先生所講的課,都是一篇篇沒有任何多余詞句、內(nèi)容精彩、富有條理性的文章。如果用心去理解和運(yùn)用這些內(nèi)容,對經(jīng)濟(jì)學(xué)是可以較快升堂入室的,有些難點(diǎn)也可以迎刃而解。遺憾的是,由于我當(dāng)時(shí)的社會(huì)工作占去了較多的時(shí)間,最終不得不放棄這門重要的旁聽課,而集中精力去學(xué)習(xí)好規(guī)定的二年級的必修課。但陳岱孫大師的高大形象在我心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陳岱孫二三事
說起陳岱孫老先生,這里還有兩件事我必須提一下。一件事是陳老師不但是一個(gè)學(xué)富五車的學(xué)者,而且是一位關(guān)心弱小、仗義執(zhí)言的長者。記得1980年清華校慶時(shí),經(jīng)濟(jì)系的校友們在清華園聚會(huì),陳老師也去了。當(dāng)他問起我現(xiàn)在的工作情況時(shí),我如實(shí)匯報(bào),說我從干校回京后,已不在冶金部機(jī)關(guān)工作,而分配到一個(gè)有幾十名家屬的"五七工廠"去了。陳老師一聽就直言不諱地說"冶金部還沒有落實(shí)知識分子政策,怎么把清華培養(yǎng)的人才送到一個(gè)家屬工廠去了"。后來有別的同志把這個(gè)話傳給了冶金部唐部長。唐部長很看重陳老師的意見,立即批示人事司、辦公廳把我從家屬工廠調(diào)到冶金經(jīng)濟(jì)研究所去工作,以落實(shí)"學(xué)以致用"的政策。還有一件事是陳老師到晚年仍然孜孜不倦,為國操勞,體現(xiàn)出一種"老驥伏櫪、壯心不已"的精神。陳岱老生于1900年,逝于1997年,可謂是世紀(jì)老人。他青年時(shí)代留學(xué)美(哈佛)、歐,回國后即任清華教授。他不但培育了十幾代經(jīng)濟(jì)學(xué)人,而且在新中國為社會(huì)主義的建設(shè)做出過很多學(xué)術(shù)上、政策上的貢獻(xiàn)。在他晚年時(shí),黨和國家提出了建立中國社會(huì)主義市場經(jīng)濟(jì)的任務(wù),陳老師為此奔走呼號。他在親自主編了《中國經(jīng)濟(jì)百科全書》之后不久,立即著手組織力量,由他親自主編《市場經(jīng)濟(jì)百科全書》。這時(shí)他已年近九十,但他仍是老當(dāng)益壯、志在千里。他說,我是及時(shí)批到國外學(xué)市場經(jīng)濟(jì)的,現(xiàn)在祖國要建立社會(huì)主義的市場經(jīng)濟(jì),我對編撰好這部《市場經(jīng)濟(jì)百科全書》是義不容辭、責(zé)無旁貸的。他的豪言壯語感動(dòng)了全體編撰人員。他不但坐而言,而且起而行,親自出面籌備編寫和出版工作。在他的鼓舞下,我們單位和我也有幸參加了由他領(lǐng)導(dǎo)下的編撰和籌集出版資金的工作。我和我的同事們?nèi)鐚O立、侯書森等同志,為陳老師主編的這本書寫了關(guān)于有關(guān)"工業(yè)"和"生產(chǎn)率"等方面的幾十個(gè)條目。陳先生在生前還對這本書的主要部分多次批閱,提出修改意見,極為認(rèn)真。只可惜陳老師沒有來得及看到這本《市場經(jīng)濟(jì)百科全書》(1998年10月第1版,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出版,上下兩冊)的正式出版,就與世長辭了。他真正做到了鞠躬盡瘁、死而后已,成為我們這些晚輩學(xué)習(xí)的楷模和追思的德高望重的大師。
"統(tǒng)計(jì)學(xué)"和其他主課
當(dāng)年給我們上"統(tǒng)計(jì)學(xué)"的老師是戴世光(注21)教授。上課的及時(shí)天,他就給我們留下清晰的印象。一口流利的普通話,口齒是那樣地清楚,重點(diǎn)是那樣地突出,邏輯是那樣地嚴(yán)謹(jǐn),他的講課像磁石一般一下子吸引住課堂里每一個(gè)同學(xué)。他的課程總是安排得有條不紊,深入淺出地講述著。他從最基本的統(tǒng)計(jì)表如何劃,如何達(dá)到簡明,有邏輯地列表,一直到各種不同統(tǒng)計(jì)對象的統(tǒng)計(jì)原理,分析方法,如何從繁雜的現(xiàn)象中去蕪存精,表述清楚,都講解得入木三分。我在戴先生統(tǒng)計(jì)學(xué)課程的班上,整整學(xué)了兩個(gè)學(xué)期。他的教而不倦激起了我的學(xué)而不厭。一年中在上課時(shí),總能讓我在課堂里目不轉(zhuǎn)睛地盯在黑板上,務(wù)求聽個(gè)明白,記住要點(diǎn),甚至還要舉一反三,由淺入深地去理解。他講的每一章節(jié)都是那么簡明扼要、清晰有序、認(rèn)真嚴(yán)謹(jǐn)。這一年的統(tǒng)計(jì)學(xué)學(xué)習(xí)是我以后參加工作后一輩子都受用無窮的。
對少數(shù)教授講課"技巧"較差或條理不那么清晰的課程,我就感到有些費(fèi)勁了。我記得當(dāng)時(shí)學(xué)"貨幣與銀行"這門課時(shí),不知為什么總是不開竅,一處"卡"住,就環(huán)環(huán)不通,一時(shí)很難搞明白。直到放暑假時(shí),我到中國人民銀行總行短期放款處實(shí)習(xí)時(shí),才慢慢有所領(lǐng)悟。經(jīng)過實(shí)習(xí)和請教行家,再重新學(xué)一下課本,才算明白一些。實(shí)踐證明,我對一些理論性較強(qiáng)、抽象一些的知識,一直不善于消化、吸收,或者說吸收得比較慢。"貨幣與銀行"是我當(dāng)時(shí)學(xué)得比較糟的一門課程。
我是到清華后才開始學(xué)習(xí)俄文的。對于我們文法學(xué)院的學(xué)生來說,學(xué)俄文似乎是形勢的需要,而不是學(xué)習(xí)的需要。因?yàn)槲覀兊恼n本包括參考書都沒有俄文本,只有中文本和英文本。在當(dāng)時(shí)的氣氛下,老師們也不會(huì)再開英文參考書讓我們閱讀,而多數(shù)同學(xué)也不具備專業(yè)英語水平,閱讀起來也不容易。在那個(gè)年代,法學(xué)院的學(xué)生只有中文參考資料和中文課本。學(xué)生從大學(xué)二年級開始學(xué)俄文也不是一件容易事。當(dāng)時(shí)課時(shí)很少,老師也少,但是學(xué)生很多,一般在大教室,甚至在大禮堂里上課。我記得光是俄文字母就學(xué)了很長時(shí)間,一年下來,收獲有限。同學(xué)們似乎是在"隨大流",既不會(huì)不及格,但也沒有學(xué)會(huì)去看書。學(xué)一種新的文字、語言是比較艱辛的,要堅(jiān)持、積累,才會(huì)有成效,學(xué)了不用也會(huì)很快忘卻。果不其然,我這一輩子,除了在清華上了一年"大鍋飯"式的俄語課外,此后,在工作、學(xué)習(xí)中再也沒有機(jī)會(huì)接觸俄語。時(shí)至今日,連俄文的字母也記不全了。這就是我們那個(gè)年代法學(xué)院多數(shù)學(xué)生外語水平的狀況。
馬約翰教授的體育課
在清華給我留下記憶的另一門課程,居然還是體育課。可能我屬于對形象思維較為容易吸收而又感興趣的那一類型的學(xué)生吧。盡管我在體育方面沒有什么專長,運(yùn)動(dòng)時(shí)甚至是笨手笨腳的,但只要多留心、多練習(xí),也能學(xué)會(huì)。體育課當(dāng)時(shí)在學(xué)校里是作為一門不可缺席、不可不及格的課程。我想這是因?yàn)榍嗄陮W(xué)生正是長身體的時(shí)期,需要學(xué)會(huì)鍛煉身體的技巧,以便人人堅(jiān)持鍛煉、強(qiáng)身。不能光埋頭讀書,畢業(yè)后因?yàn)樯眢w差而成為"廢物"。因此,學(xué)校對體育的設(shè)施、體育的師資都是相當(dāng)重視的。那年,我的體育老師是全國頗有名望、白發(fā)蒼蒼的馬約翰教授。(注22)上課他只講英文,因?yàn)樗闹袊捠歉=ǚ窖裕覀兟牪欢K险n時(shí)有一位助教,為大家做翻譯,并做一些示范動(dòng)作,或幫助同學(xué)掌握各項(xiàng)運(yùn)動(dòng)的要領(lǐng)之類的工作。馬約翰老師雖然那時(shí)快滿70周歲了,但體格仍然健壯,冬天還能穿著白短褲、白襯衫在戶外活動(dòng),還經(jīng)常打打網(wǎng)球。他告訴我們,因?yàn)樗?jīng)常運(yùn)動(dòng),所以身體好。他每周要給我們(女生班)上兩節(jié)課,每天還要指導(dǎo)和督促我們進(jìn)行"勞衛(wèi)制"達(dá)標(biāo)鍛煉。工作非常認(rèn)真、熱情!
我們體育課的內(nèi)容是十分豐富而又比較獨(dú)特的。每節(jié)課的內(nèi)容是馬老師自己編排,自編自教,而且每節(jié)課的內(nèi)容幾乎都不相同。例如:為了鍛煉反應(yīng)能力,他事先會(huì)在墻上畫許多白色的圓圈,直徑不到半米,每個(gè)圈內(nèi)寫著不同數(shù)字,而且不按順序排列著。上課時(shí),讓你站在離圓圈若干米的地方,持著一個(gè)籃球,快速順時(shí)針自轉(zhuǎn)。待你轉(zhuǎn)得頭昏眼花時(shí),他發(fā)出命令,不許稍有定神的時(shí)間,叫你把球投向幾號圈。這樣連續(xù)做10次,記錄你投中次數(shù),加以計(jì)分。一直練到你"及格",再讓你去打籃球。同樣,在打排球之前要先練發(fā)球。在對方排球場地上劃
當(dāng)年一群有理想有道德有抱負(fù)的愛國青年,為了國家和民族大業(yè)付出了太多。今天的幸福生活來之不易。
好
新奇,書不錯(cuò),比較有趣,看看有收獲
還沒讀,無法對內(nèi)容做出評價(jià),待讀后再予以仔細(xì)評價(jià)吧
好
從細(xì)微處感受大時(shí)代的變遷
書不錯(cuò),物流快包裝還行,值得看。
值得一看吧,具體內(nèi)容不是很了解。
大家之作,很好
這本書,屬于稀世存書,又趕上滿減,買了
挺好看的。
不錯(cuò)的圖書。
讀本書可以了解那個(gè)年代大學(xué)生們的所思所想。
動(dòng)蕩的時(shí)代,充滿激情的學(xué)子……李四光、錢三強(qiáng)、翦伯贊、雷潔瓊、陳岱孫這些大師是如此親切。
50年代的大學(xué)生活讓人神往。十幾年前去過清華,北大則經(jīng)常在西門附近溜達(dá)。物是人非,很多東西只屬于那個(gè)時(shí)代。
新中國成立時(shí)候的大學(xué)充滿生機(jī),人們的精神面貌與我們所生活的這個(gè)凡事向錢看的社會(huì)的人有天壤之別。看完這本書,覺得應(yīng)該重溫一下《青春萬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