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師們的民族大義與家國情懷 大文人的悲壯遷徙和抗戰史詩
《民國清流1:那些遠去的大師們》入選《作家文摘》2015年度十大非虛構好書
葉辛、何建明、張抗抗、梁曉聲、李敬澤、葉廷芳、張頤武、王躍文、余世存、孫郁、解璽璋、李建軍、北村、岳南等名家傾情推薦!
聯合早報、南方都市報、鳳凰周刊、央廣、人民網、新華網、北京晚報、騰訊、新浪等全國百余家媒體廣泛報道。
本書系民國大師們的集體傳記系列之四。
本書沿襲《民國清流1:那些遠去的大師們》《民國清流2:大師們的“戰國”時代》《民國清流3:大師們的中興時代》的風格,承接前三部的歷史階段(1917年至1936年),呈現出1937年至1945年八年抗戰時期悲壯而慘烈的文化景觀。
七七事變之后,國難當頭,民國知識分子自覺站在統一戰線的大旗下,演繹了一部壯烈激越的抗戰史詩。無論是在國統區、解放區,還是在淪陷區,抑或上海的“孤島”,“民族”“救亡”的主流都激起了巨大的民族凝聚力,讓抗戰時期的文化思想界空前統一。胡適、郁達夫、老舍、沈從文、梁漱溟、茅盾、張恨水、聞一多、鄭振鐸、馬寅初、陳寅恪、吳宓、趙樹理、丁玲、蕭軍等,做著他們認為文人應當做的事情,在抗日救國的路上披肝瀝膽,以各自的姿態,演繹著知識分子的氣節、風骨與擔當。
作者不囿于故有定論,依據翔實的史料,書寫被遮蔽的歷史,刻畫真實生動而豐富的人物命運,立體式地彰顯了民國大師們獨特而復雜的文化品格和人格。
1.“民國清流”系列是民國大師集體演繹的史詩級傳記。《民國清流4:大師們的抗戰時代》系作者汪兆騫繼《民國清流1:那些遠去的大師們》《民國清流2:大師們的“戰國”時代》《民國清流3:大師們的中興時代》之后又一力作。
2.作者汪兆騫是文學界、出版界的老前輩,“朋友圈”俱為文學名家和文化精英,輻射了中國的當代文壇。汪老先生經手孵化的名作,大多讓人如雷貫耳;汪兆騫做過嫁衣的作家尤其是文學大家,幾乎占據中國當代文壇的半壁江山。更可敬的是,汪兆騫是一位秉持道義與良知的知識分子型作家。由汪兆騫以客觀公正的史家視角講述的民國時代的文壇,在剖析人物的性格與人格方面,自然是游刃有余,功力深厚。
3.《民國清流4:大師們的抗戰時代》中的時間節點,為1937年至1945年八年抗戰時期悲壯而慘烈的文化景觀。在大環境中,這些知識分子展現出來的風骨和氣節讓后人敬佩。他們沒有為亂世所裹挾,而是站在統一戰線的大旗下,在各自的領域中竭盡所能,救國救民,奏響一曲正能量爆棚的愛國主義贊歌。
4.《民國清流4:大師們的抗戰時代》中,作者汪兆騫同樣憑借翔實的史實與依據,實事求是地撰寫歷史,披露真相,還原歷史,對歷史人物客觀公正的講述與剖析,刻畫出民國大文人、大知識分子在大環境中呈現出來的多種文化品格,彰顯人性的光輝與卑微。
5.“民國清流”系列流暢優美的寫作風格,紀年體式集體傳記的寫法,讓這一系列的圖書既適合作為文學和文學家史料的補充,又能讓普通讀者獲得愉悅而充實的閱讀感受。 50%'>大時代成就大人物,大人物影響大時代。中國現代的源頭是怎么回事,那段時間關鍵。汪先生用跟王蒙等當代大文人交往的方式跟民國大文人對話、溝通,把大歷史關鍵時期的那些關鍵人物寫得特別生動,特別活,現場感很強,就像在我們旁邊一樣。像汪先生這樣對民國時代進行描述,對民國時代知識分子和20世紀中國的命運做探討,非常有價值。
著名作家王躍文:
汪兆騫老師深諳《左傳》筆法,其《民國清流》依照編年剪裁民國歷史,將人物置于云詭波譎的大事件大沖突中摹形刻畫,以史家手眼鉤沉實錄,以文學筆墨傳神寫照,于人物書寫中別嫌疑,于敘事中富褒貶,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援史明志,其為士人清流招魂之深情苦心,令人感佩。
著名作家梁曉聲:
前事不忘,后事之師。以史為鏡,躬身自照,可助當下文化知識分子警鑒省思,保持立言、立行、立書、立品之原則與底線。重要的是對史事、史人做的評說須力求公正客觀。而本書作者做到了,值得一贊,更值得一讀,有可敬的文史價值。
著名作家、中國作協副主席張抗抗:
汪先生近一連出了好幾本書,都是系統地梳理民國文化史、文學史和思想史的。打個比喻,民國就像一艘沉沒的豪華巨輪,上面有無數寶藏值得我們挖掘。汪先生的這套民國系列就在為我們打撈這些寶藏。
著名作家、中國作協副主席何建明:
汪兆騫
生于1941年,人民文學出版社編審,原《當代》副主編兼《文學故事報》主編。中國作協會員。著有《往事流光》《春明門內客》《記憶飄逝》《紫塞煙云》《張騫》等,新近出版有《民國清流1:那些遠去的大師們》《民國清流2:大師們的“戰國”時代》《民國清流3:大師們的中興時代》《文壇亦江湖:大師們的相重與相輕》,深受讀者好評。
及時章民國二十六年(1937 年) / 003
七七事變,抗日戰爭拉開序幕;胡適提出不要放棄河北;郁達夫、李叔同、張恨水、老舍擔起民族救亡的使命
“為誰萬里御風行”——胡適以非官方身份出訪歐美五十24小時,作五十六次演說 / 007
“燕山柳色太凄迷”——躲在苦雨齋觀望的周作人 / 017
“云何色殷紅”——弘一大師“為護法故,不怕炮彈” / 024
“讓詩人的聲音像高射炮一樣”——郭沫若、田漢參與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工作 / 032
第二章民國二十七年(1938 年) / 045
百城淪陷;叛國投敵;名校南遷,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組建;梁漱溟、周揚、徐懋庸來到延安
“做了過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胡適就任中國駐美大使首戰告捷 / 049
“中國的甘地”梁漱溟赴延安訪 / 058
“為全節概而免禍累”——陳寅恪在香港寧死不事倭督和汪偽 / 068
周揚、馮雪峰、徐懋庸的命運發生了轉折 / 078
第三章民國二十八年(1939 年) / 089
國共摩擦加劇;吳佩孚拒絕汪偽邀請;周作人淪為漢奸;張愛玲、蘇青和邵洵美與“孤島文學”
“一生真偽有誰知”——方圓、冰炭集于一身的周作人 / 093
“忽而普羅,忽而民主,忽而民族”——寫得一手漂亮小說的變節文人張資平 / 107
“孤島”中的張愛玲、蘇青和邵洵美 / 117
第四章民國二十九年(1940 年) / 137
發表《新民主主義論》;文化工作委員會正式成立;茅盾到延安;吳宓講授《紅樓夢》;老舍別婦拋雛,走上抗日
巴金說,“其實我并不理解他”——抗日戰爭中的茅盾 / 141
“聊報國家于萬一”——張恨水改寫抗戰小說 / 151
“血若停流定是灰”——老舍別婦拋雛,走上抗戰征程 / 162
現在是一切對外的時候——“對政治一向有興趣”的文人梁實秋 / 174
第五章民國三十年(1941 年) / 183
民國教育文化大遷徙已過去四年;全國文化精英、作家、學者與亟待學成救國的青年學子云集于西南地區
是夜,大雨方歇,胡適又和羅隆基、陶希圣等在胡宅商量于7 月9 日前往江西九江廬山開會事宜。他們吃過晚飯,坐在庭院中開會。羅隆基對國民黨應對七七事變態度不積極大為不滿,言道:“國民黨既不能不退出河北,何妨讓各黨各派來干一下。”胡適聽罷,不以為然。他批評羅隆基,堅稱此時此地只能跟著國民黨政府進退,不能只搞什么黨派活動(《胡適之先生二三事》,1962 年2 月6 日“中央日報”)。
胡適是當日離開南京的。他與兒子祖望乘船逆江而上,于11 日抵達漢口。安頓好兒子,胡適又于13 日與錢端升、張忠紱搭飛機離武漢,一路向南飛往香港。趕上臺風肆虐,那個讓胡適感到恥辱的九一八事變六周年紀念日,就在香港度過。胡適感慨地說:“今日總算是用飛機炮火來紀念九一八了。”
周作人盡管早已躲進苦雨齋,放棄對歷史和時代的責任,甘愿做一個“平凡的人”,但畢竟曾是新文化運動的開創者之一,其文學作品也成就了他在中國文壇的崇高地位。特別是他與日本及日本文化的特殊關系,使他無法避免成為當時中日各方政治力量可資利用的政治籌碼這一宿命。郭沫若寫的《國難聲中懷知堂》,其夸飾性的語言掩蓋不了其動機,那就是爭取周作人莫忘祖國,使他成為愛國的知識分子代表人物。
那是1906 年,李叔同在日留學,與日本姑娘福基邂逅。這是李叔同最諱莫如深的一段戀情。李叔同學習西洋畫,需要一位人體模特。不經意間,他發現常給他送飯的房東女兒福基身材窈窕,福基正是自己苦苦尋覓的模特人選。李叔同詢問姑娘是否愿做他的模特,姑娘大大方方同意了。合作是愉悅而有成就的,李叔同旅日期間畫的油畫《裸女》,便是他們合作的作品。接觸多了,兩個年輕人就有了感情。接下來就同居了。李叔同曾于1898 年,在母親安排下,與天津一茶商女兒俞氏成親。不久,舉家遷到上海。1901 年,李叔同與上海有“詩妓”之譽的李香一見傾心,二人常以詩詞相和。多年后,李叔同遁入空門,得李香所贈詩畫,送給好友夏丏尊,以示情緣已了斷。
1938 年2 月5 日,胡適結束一次演說,準備到他處演說,匆匆走下樓梯。這時,迎面一位美國人微笑著將他攔住,是位身著雜役制服的美國人。胡適也微笑著問他有什么要幫忙的,雜役從口袋里摸出三塊銀幣,說:“胡先生,聽了您的演說,知道中國抗戰太艱苦了,這三塊銀幣捐給貴國吧。”胡適聽罷,眼睛濕潤了。遠在中國萬里之遙的國度,一個毫不相干的美國工人,用自己辛苦賺來的血汗錢支援中國抗日,讓胡適感動莫名,久久難以忘懷。
梁漱溟自然記得,1918 年年初,他幾乎每晚都到楊懷中家里拜訪。每次開院門的,是一個高大英武的湖南青年,彼此總是點頭一笑,沒有互報姓名。梁與楊交談,這位青年從不在場。楊懷中告訴他,青年叫,是他在湖南及時師范教書時的學生,很有才華。此次到來,經他推薦,在北京大學圖書館謀得月薪八元的管理員一職。白天還到學校里當旁聽生,晚上回楊家住宿。
批評梁漱溟,認為要求照顧農民是小仁政,發展重工業,打美帝是大仁政。隨后幾天的會議上,還對梁漱溟說:“你雖沒有以刀殺人,卻是以筆殺人的”,“人家說你是好人,我說你是偽君子”,“你一生一世對人民有什么功?一絲也沒有,一毫也沒有。而自己卻把自己寫成了了不起的天下及時美人,比西施還美,比王昭君還美,還比得上楊貴妃”。說:“對你的此屆政協委員不撤銷,而且下一屆政協還要推你參加,因為你能欺騙人,有些人受你欺騙……”書呆子梁漱溟被老朋友氣頭上的話驚呆了,書生意氣又犯了,他不顧一切地要求發言,與發生了激辯,要求要有“雅量”,被轟下了臺。
在西南聯大,陳寅恪每次上課,都要步行一里多地。每天,昆華路上,都有一道這樣的風景:穿著藍布長衫的陳寅恪,腋下挾著用一塊花布或黑布裹著的一大包書,沉重地走向教室,晨陽照著他的滿是汗的額頭,亮晶晶的。那時,他的右眼視網膜已脫落。學生見他如此辛苦,多次提議輪流去家里接他上課,都被他婉拒。
錢夏是錢玄同在日留學時,為反抗清王朝而起的名字。此舉寓意打倒清王朝,恢復中華,不再亡國亡民的信念。日寇占領北平后,錢玄同致信老友周作人,說“我近來忽然抒懷舊之蓄念,發思古之幽情”。他寫信給遷到陜西城固的北京師范大學同事黎錦熙先生等人,表達出“錢玄同決不污偽命”的堅貞、磊落的胸襟。
張愛玲在1944 年發表了一篇并不大為人重視的小說《年青的時候》。內容是上海青年潘汝良,愛上了一位十月革命后逃離蘇俄,僑居上海的白俄姑娘。在侵略者的刺刀下,二位淪為難民的年輕人的異國之戀,本身就具的象征意義,給作家提供了廣闊的空間。但張愛玲把一切文學技巧都隱在了極樸素的敘述之中。可以發現,她的小說風格的悄然變化:從以前的繁復濃烈,向平淡自然轉化。看不到的技巧,是文學中較高超的技巧。
陳公博請并不熟悉的蘇青吃飯,推杯換盞之后,借著酒力,澆出心中塊壘,黯然說出自己的人生經歷:一介熱血文人,參加革命,但嚴酷的社會現實又使其希望幻滅,心灰意懶,為了友情,以自己的命相報。看著眼前堂堂男兒,聽著他內心流出的悲愴命運,一個涉世不深的弱女子動了惻隱之心,合乎人之常情。但世事的殘酷是,事物對錯,并不取決于常情,蘇青受到攻訐和付出的代價,是因她在重要的歷史關頭,堅持報知遇之恩的私人性選擇,是因她毫不掩飾地同情喪失民族氣節者之流。
邵洵美在《十日談》發表文章批判“文人無行”,說“有些‘沒有飯吃’或‘有了飯吃不飽’的人”,以為當文人是“無本生意”,就“人人想做”,“我們的文壇便是由這種文明人組成的”,“這般東西便永遠在文壇里胡鬧”。于是,就有人猜測,這是罵魯迅的,因此這種挑釁,勢必遭到魯迅的痛擊。有人還言之鑿鑿,說魯迅寫的《各種捐班》(1933年8 月26 日《申報 自由談》),就是回應邵洵美這篇文章的。似也無根據。依《魯迅全集》的編輯原則,大凡魯迅批評文字指向誰,都在注釋中說明。此論無非是說,邵洵美先惹了人家魯迅,魯迅為了自衛,才發動反擊批判邵洵美的。
6 月初,一個上午,茅盾在窯洞里正讀《中國文化》雜志,來到他的住處。進屋就說,實在太忙,一直沒看過你和夫人、孩子。說著,又拿出一本自己寫的,散發著油墨香氣的《新民主主義論》送給茅盾:“剛剛出版。你是大作家、評論家,請你看后多多批評啊!”兩個老朋友興致勃勃地從《新民主主義論》談到古典文學。對《紅樓夢》發表了許多精辟的見解,令人耳目一新,談到魯迅,也有獨特的見識,讓茅盾驚嘆不已,自愧弗如。
當時張恨水已搬到南京郊外上清河。他每天下午頂著酷暑烈日,匆匆步行十幾里地,趕到報社,然后就伏在辦公桌上,一直工作到第二天旭日東升,才疲憊地往城外趕。到了家里,倒頭便睡。有時,在半路上會碰上日本鬼子飛機的轟炸,聽到空襲警報響起,他不得不趴在田埂或伏在樹下。空襲之后,他即奔向報館,馬上撰寫夜里就要印刷的重要社論和時評。
那時的張恨水四十來歲,身材高大,胖墩墩的,為人和藹可親。其嗓門大,未見其人,已聞其聲,因在北京多年,便操一口京腔徽調。每次撩起長藍布衫,拿著折扇上得樓來,總是高喊:“今天真熱。”報社同人回憶,他一來編輯部,首先翻閱當日各家報紙,拆閱稿件和私人信件,然后與同人談談情況。等他坐下來,會全神貫注筆走龍蛇,不多久,漂亮的社論或時評就寫出來。
被人過度宣傳的老舍與沈從文的矛盾,更多地賦予意識形態的色彩,或故意挑撥二人的關系。事實是,老舍與沈從文并無芥蒂。早在1935 年1月5 日《人間世》征詢“一九三四年我所愛讀的書籍”時,老舍回答的及時本書就是沈從文的《從文自傳》。1946 年,老舍在《八方風雨》中回憶愉快的云南之行時,就說見到了聞一多、沈從文等人。“諸先生都見到或約我吃飯,或陪我游山逛景。這真是愉快的日子。”而沈從文在1952 年被迫逃離文壇,填寫《博物院工作人交待社會關系表》時,便將老舍列入“作家中較熟悉的”之人(沈從文《交待社會關系》)。在那特殊的政治背景下,沈從文依然將老舍引為朋友。
一次,日寇飛機來昆明轟炸,師生聽到警報后,紛紛跑向防空洞。劉文典忽見沈從文從身邊經過,甚是不悅,對身邊學生道:“我跑是為了保存國粹,學生跑是為了保留下一代的希望,可該死的,他跑什么呀!”劉文典素來看不起新文學作家,認為他們的創作不是真正的學問。劉文典的可愛,在于他敢于當面直言不諱地貶損他認為沒本事的人,對大人物同樣敢于犯顏,而對他服氣的人,不管年紀長幼、身份貴賤,總是十分謙恭,如他曾說:“陳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該拿四百塊錢,我該拿四十塊錢,朱自清該拿四塊,可我不給沈從文四毛錢!”
弟子汪曾祺在聯大寫的稿子,幾乎全部由沈從文修改后寄出去的。李霖燦在麗江畫玉龍雪山的畫,也多由沈從文代為出手。那時通貨膨脹,郵費上漲,有時信封上貼滿郵票。一兩封尚可,像沈從文幾乎天天都自費給學生寄稿件,那可是一筆相當可觀的票子堆起來的。是薪金不多的沈從文,從自己生活費里擠出來的。他毫無怨言,默默地這么做了多年。
據汪曾祺回憶,吳宓講《紅樓夢》,深受學生歡迎,常常尚未開課,教室已被學生坐滿。來遲的女生沒有椅子坐,吳宓見到,就轉身到其他教室去搬椅子,等到大家都有座位,才開始上課。此等騎士風度,感動了學生,遂有大量男士紛紛效仿,一時成為風氣,傳為美談。
昆明有家牛肉館,老板為招徠食客,以雅號“瀟湘館”為店名,生意果然不錯。一貫以“怡紅公子”自況,深愛林妹妹的吳宓聞之,認為這是一個俗商對《紅樓夢》的褻瀆,甚是惱怒。他選好時機,趁“瀟湘館”賓客盈門之時,提著一根很粗的黃藤文明棍登上門去,然后不由分說,一通亂砸。仍不解氣,還要老板立刻摘下“瀟湘館”匾額。
有次出游,吳宓見一軍官舉槍打鳥,遂上前勸阻:“子彈應留著打鬼子,打鳥豈不浪費。”軍官見吳宓西裝革履,不知是哪方神仙,只好收手。正巧這時西南聯大學生從此經過,齊向教授鞠躬問候。軍官知吳宓乃一窮書生,面生怒色,準備發難,學生見狀,拉起吳宓離去,避免一次激烈沖突一次,財政部部長孔祥熙,在中國經濟學社年會上講話。馬寅初突站起來,當面質問,孔被問得面紅耳赤,結結巴巴說:“我是孔子后人,不會貪污的。”有人見狀,給孔一個下臺階的機會,提議會議休息十分鐘。解了圍的孔祥熙落荒而逃。為了拉攏馬寅初,和孔祥熙曾派中央銀行會計處處長金國寶去馬寅初處,傳達政府恭請馬寅初出任財政部次長的命令。馬寅初識破蔣、孔之計,說:“你們想弄個官位把我嘴巴封住,怕辦不到。”此后,蔣、孔幾番派人游說,馬寅初終不改不予合作的初衷,令蔣、孔很丟面子。
一日清晨,在去往課堂的途中,白髯飄飛,手上拿著一個用印有太極八卦的藍布裹著的書包的馮友蘭,與一身舊西裝的金岳霖相遇。金故作認真狀:“老兄,修到什么境界了?”馮一本正經曰:“到天地境界矣!”二人大笑,各奔課堂而去。
1940 年,蕭軍由重慶再到延安,在魯迅藝術文學院當教員。1941 年出版了報告文學《側面》的續集《從臨汾到延安》。與蕭軍關系密切,交往多,通信多,喝酒碰杯多,談文學多。故蕭軍與朋友談天時,常狂妄且有江湖氣地放言:魯迅是我父親,是我大哥。說者大言不慚,聽者莫不瞠目。當時,除了丁玲,在延安的作家中,蕭軍算是重量級的了。
魯迅是喜歡蕭紅的。一次,蕭紅穿著火紅的上衣、咖啡色的裙子,請魯迅評價。魯迅坐在躺椅上,很有興味地看著她,微笑著說:“你這裙子是咖啡色的,還帶格子,顏色混濁得很,所以把紅衣裳弄得不漂亮了。”魯迅還對她以前穿過的短統靴子批評了一番,讓蕭紅很吃一驚。魯迅說,那短靴是軍人穿的,應把褲子塞在靴里。蕭紅問,為什么你以前不告訴我?魯迅說:“你不穿了,我才說的,你穿的時候,一說你該不穿了。”
在重慶時,高長虹儼然成為政論家。他寫的大量關于抗戰的時評,角度新穎,思想深刻,見解卓異,也引起國民黨的注意。一日,他的一個崇拜者,曾是狂飆社成員,現已成為閻錫山二戰區駐重慶辦事處任主任的梁武,突然到高長虹居住的旅館拜訪,特奉上白花花的大洋五百。高長虹微微一笑,搖頭拒不接受,并不無譏諷地道:“那是刮地皮的錢!”
嚴文井老人在他走后,講了不少趙樹理的趣聞,說老趙酷愛家鄉戲上黨梆子,常常主動“送戲上門”。有時天色已晚,他常會“推門而入”:“老嚴,我來給唱段上黨梆子!”接著,他不用等“老嚴”讓座,已一屁股坐在書桌邊,雙手并用,代替打板和鑼鼓,同時高亢地哼著過門。一段驚天動地的曲調,便大屋子里回響。還沒等醒過神,琢磨出意思,老趙又主動說:“還有一段更好的!”又是雙手并用,哼過過門,放聲高唱,又是聲高震屋,曲調飛揚。嚴老說:“這個晚上,老趙倒是盡了興,而我則有苦說不出。”
窮其四年,鄭振鐸竟收購珍貴古籍八百三十余種,并做大量整理工作,或寫題跋,或寫札記,并在日記中詳記版本、內容等。他的努力付出,艱苦備嘗,大類愚公移山,精衛填海。自云:“雖所耗時力,不可以數字計,然實為民族效微勞,則亦無悔!”
1949 年3 月,中共已將國民黨趕到臺灣,留在大陸的高級知識分子,在黨的安排下,從全國各地區集中到北平。在北平西郊機場舉行的歡迎等中央領導人從西柏坡遷至北平的儀式上,馬寅初突然見正乘坐在一輕吉普車上指揮大會,不顧會議秩序,在眾目睽睽之下,一人跑到身邊,大聲而激動地說:“遵照你的指示,我已平安來到北京。
1942 年2 月,日軍占領毫無抵抗能力的新加坡。郁達夫躲到蘇門答臘西部高原一個叫巴爺公務的偏僻小市鎮。24小時,化名趙廉的郁達夫,裝扮成工人模樣,登上市鎮的公共汽車。車子行在半路,突被一隊日本憲兵攔住。幾個憲兵沖上汽車,其中為首的日軍軍官哇啦哇啦說了一通。車上人聽不懂日語,以為大禍臨頭,都嚇得面色蒼白,驚恐萬狀。車上的郁達夫,早就聽懂,日本人只是上車問路。郁達夫用日語為他們指了路。日軍軍官臨走前,問了郁達夫的姓名、住址,向他舉手敬禮,然后帶兵走了。
日本人立即到東京、上海等地進行秘密調查。很多朋友聞之,都勸郁達夫趕緊躲到別處去,以防不測。郁達夫卻鎮靜地對胡愈之等人說:“我是躲避不了的,最近日本憲兵每天都到我家來喝酒閑談,雖沒說穿,顯然已被監視了。”
此后一段時間,日本人雖已改稱“趙先生”為“郁先生”,那張窗戶紙,已經捅破,但一切都維持原狀,常來喝酒,常來閑扯,常來借錢。日本人怎么想,郁達夫難以揣摸。他自己早就對結局有了心理準備。
1938 年,李劼人在成都近郊東沙河堡菱角堰購置土地,約兩畝。1939年,日軍轟炸成都時,建成一批泥墻草頂的簡易房舍。李劼人家自八世祖從湖北入川定居,從未有過自己的房子,很多書籍在遷徙中散失,有了“菱窠”,他可不再擔心自己多年置備的近萬部書籍和積存的大量報紙遺失。為了方便信件、圖書投遞,他在門楣題“菱窠”二字,意指此菱角堰之窠臼也。又因此地處于市郊,交通不便,人煙稀少,故可供進步作家棲身,一時成為成都文學界的一個據點,借機掩護了不少地下黨作家。作家唐山在其《李劼人,被忽略的“中國左拉”》一文中,曾說“馬識途(作家,電影《讓子彈飛》原著作者)被通緝時,就住在‘菱窠’”。葉圣陶多次到“菱窠”訪友。
好好看看這樣的作品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1234都買了喜歡
民國清流4:大師們的抗戰時代
好書推薦!
當當很給力當當很給力當當很給力當當很給力
我買了六本書,書一起發過來了,但是我要一個一個評價
包裝太差!!!!!!!!!!!!!!
前事不忘,后事之師。以史為鏡,躬身自照,可助當下文化知識分子警鑒省思,保持立言、立行、立書、立品之原則與底線。重要的是對史事、史人做的評說須力求公正客觀。而本書作者做到了,值得一贊,更值得一讀,有可敬的文史價值。
心儀已久的!不錯
看了第一部——遠去的大師們,便欲罷不能,雖然這套書不參加活動,價錢高,忍痛全買了。這些學富五車,才高八斗的大師們,用自己的一支筆去傳播新文化新思想,影響并推動社會發展進步。同時也比較客觀地披露了他們之間的友誼和:矛盾以及他們各自的人生觀世界觀的炯異。幫助我了解了某些歷史社會細節和大師們的人生細節。有味,有料。
剛開始讀,第一本以前買過。非常好!
這本書,作者很有水平,文筆不錯,知名出版社,排版印刷精美,包裝認真,快遞速度,我很滿意。謝謝作者,謝謝當當,謝謝快遞小哥,你們都辛苦了!真的挺好的!感恩有你們!
這本書加前三本是一套的。現在買齊了。
不錯,活動打折時買的,很便宜
商品沒問題,物流太爛。
寫得還可以,個別觀點有誤。
活動購入,性價比很高!
非常不錯的書
整體感覺還可以
非常滿意,能夠獲得新的認識
四本都收齊了,很高興,謝謝當當
不愧是大手筆,一定好好拜讀。
不錯,孩子很喜歡!
很不錯的書!
書好,送貨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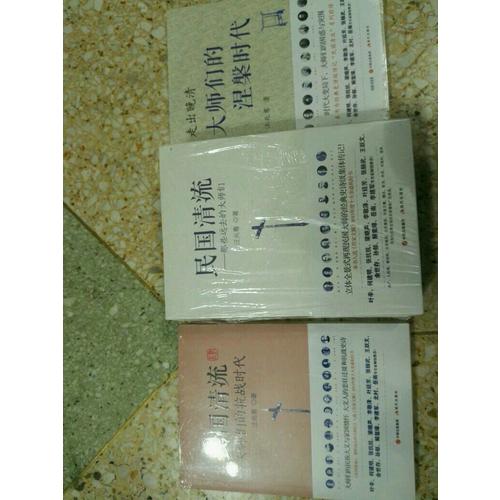 民國大師們的故事,汪老師的神作,值得讀
民國大師們的故事,汪老師的神作,值得讀
慢讀細品,走近大師們。
這書性價比高,內容詳實,給贊!非常好!值得推薦!
好書,值得一看
好書!!!!!
做讀書準備!
當當搭配韻達,速度簡直太快了,大大的贊好評!
民國清流這套書真是難得的好書啊,第三部還沒看完,先入手,寒假慢慢看吧
一套共五本,已經讀了四本,最后一本正在讀,讀完后再追加評價。
我喜歡看有良心的書籍,汪老的民國清流可以和岳南的《南渡》、《北歸》、《離別》對照著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