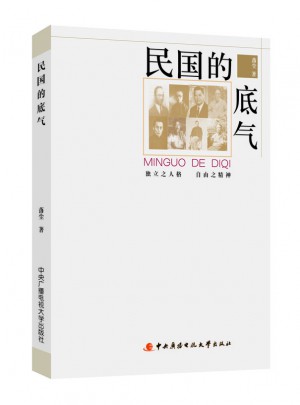
民國的底氣
- 所屬分類:圖書 >歷史>歷史普及讀物>中國近現代史
- 作者:[落塵]著
- 產品參數:
- 叢書名:--
- 國際刊號:9787304051518
- 出版社:中央廣播電視大學出版社
- 出版時間:2011-07
- 印刷時間:2011-07-01
- 版次:5
- 開本:12開
- 頁數:--
- 紙張:膠版紙
- 包裝:平裝
- 套裝: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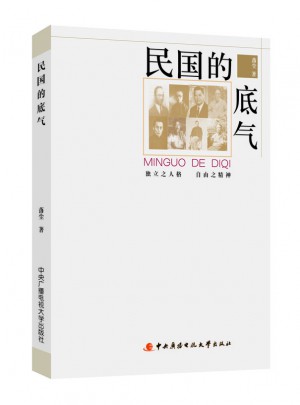
閱讀民國,不僅僅是在閱讀一段歷史和文化,更是在回望和追念一種精神。那是中國知識分子群體遠承魏晉之后,以獨立姿態演奏出的一個華彩樂章。
這是一本介于學術和通俗讀物之間的圖書,或者說,它力圖在兩者之間打通壁壘,架起一座橋梁。通俗讀物往往太缺乏根柢,學術書籍又常常艱深枯燥。既給人輕松愉悅的閱讀快感,又能給人以精神上的深度拓展和啟迪,這恐怕就是作者的寫作企圖。
2005年,病榻上的錢學森面對前來探望的,問道:“為什么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杰出人才?” 并說:“回過頭看,這么多年培養的學生,還沒有哪一個的學術成就,能和民國時期培養的大師相比!”這就是著名的“錢學森之問”,也被稱為“世紀之問”。
這同樣也是許多人心中的困惑。中國人怎么了?中國社會怎么了?六七十年的歲月在歷史長河中并不算長久,但在此過程中,我們究竟遺忘和失落了什么?
這本書以嚴肅而幽默的筆墨帶給我們的,正是一次笑與淚中的追問和思索。
落塵,70年代人,獨立譯著。目前專注于民國文化的研究與寫作。致力于讓美好的人物和思想流傳。
辜鴻銘:“菊殘猶有傲霜枝”
20世紀初,西方人曾流傳一句話:到中國可以不看紫禁城,不可不看辜鴻銘。英國作家毛姆來中國,想見辜鴻銘。毛姆的朋友給辜寫了一封信,等了好長時間也不見辜來。毛姆沒辦法,自己找到辜的小院,辜不客氣地說:“你的同胞以為,中國人不是苦力就是買辦,只要一招手,我們非來不可。”辜鴻銘學貫中西,但卻推崇儒家學說,反對新文化,他認為要估價一種文明,必須看它“能夠生產什么樣的男人和女人。”清亡后辜鴻銘堅持留長辮,著長袍,有人戲稱,“全世界只有一條男辮子保留在辜鴻銘頭上”。一次他因為裝扮如鄉下人被兩青年用英文嘲笑,便留下一張用拉丁文寫成的便條,上注英文:“你們若不認識上面寫的是哪種文字,可于明天下午到北京大學來請教辜鴻銘。”兩人看到紙條,聽說這個鄉下佬就是大名鼎鼎的辜鴻銘,嚇得抱頭鼠竄而去。
王國維:一種文化的背影
“凡一種文化,值其衰減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現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則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曾經透徹地將人生的事業和學問解析為三種境界的靜安先生,終于沒有看透自己人生的迷局;曾經輕易地出入于中學與西學、美學文學與史學的一代大家,卻如此輕易地跨越了死生的界限……這是時代的創痛,學者的悲歌,亦是曾經的文化轉身離去時,留下的一抹悲愴的背影。
黃侃:八部書外皆狗屁
黃侃是章太炎先生的大弟子,號稱“章門天王”。他任教于南京中央大學時,與校方約定“下雨不來,降雪不來,刮風不來”,綽號 “三不來教授”。黃侃嗜酒,喜美色、美食,其門上掛有一小木牌,上面寫“坐談不得超過五分鐘”。有一次,兩位女學生來借閱雜志,稍事閑談即準備離去,黃侃說:“女學生不在此限,可以多坐一會兒。”黃侃反對白話文,尊崇儒學,有“八部書外皆狗屁”之言。他對胡適說:“你提倡白話文,不是真心實意。”胡適問他何出此言。黃侃正色道:“你要是真心實意提倡白話文,就不應該名叫‘胡適’,而應該叫‘到哪里去’。”說罷此言,還仰天打三個哈哈,把胡適氣得臉都白了。
錢玄同:從不判卷子的教授
錢玄同從不批改學生們的考卷。北京大學為特意刻了一枚“及格”的木質圖章;錢玄同收到考卷后,就直接送到教務室,由教務統一蓋上“及格”二字。而后來到了燕京大學,校方警告他如果拒絕判卷,就將扣除相應薪金云云,而錢先生立即作書一封,言:“判卷恕不能從命,現將薪金全數奉還。”他是新文化運動的主將之一,曾與劉半農合作演出一場著名的“雙簧戲”。因為中年以上的人多固執而專制,錢玄同更說出一句名言:“人到四十就該死,不死也該槍斃。”當外在的壓力消失,個人也跨過激昂漸漸冷靜成熟,不惑之年的錢玄同說自己從前種種過激的言論“十之八九都成懺悔之資料”。
梅貽琦:寡言君子
“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這是梅貽琦的一句名言。他被譽為清華大學的“終身校長”。當年清華學生驅逐校長的運動此起彼伏,但是無論什么時候,學生們的口號都是“驅逐某某某,擁護梅校長”。有人問梅貽琦有何秘訣,梅貽琦說:“大家倒這個,倒那個,就沒有人愿意倒梅(霉)!”梅貽琦主持下的清華和西南聯大,可以說是中國近代教育史上的兩座高峰,后者更是在國土淪喪、內憂外患的情況下,創造出了 “物質上不得了,精神上了不得”的奇跡。梅貽琦一生清廉,死后沒有任何遺產。他去世后,人們將他病中一直帶在身邊的一個手提包打開后,里面原來是清華基金的歷年賬目,一筆一筆,分毫不爽。
陳寅恪:最是文人不自由
陳寅恪被譽為“活字典”、“教授的教授”,受聘為清華國學院四大導師之一時年僅36歲。他終生沒有獲得過一張大學文憑,但卻通曉英、法、德、希臘、拉丁、梵、蒙等22種文字。蘇聯考古學家發掘出三塊突厥文碑石,學者們莫衷一是,不懂不通,請教陳寅恪,才得到破譯。陳是1948年國民黨“搶運學人”計劃中的國寶級人物,但他最終卻選擇蟄居嶺南,晚年在目盲臏足的情況下,口述完成80余萬字的《柳如是別傳》。陳一生秉持“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1953年,對于勸說他出任中國科學院中古史研究所所長一事,陳寅恪提出兩個條件:一、允許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并不學習政治;二、請毛公或劉公給一允許證明書,以作擋箭牌。此事于20世紀80年代方始公布于世。
趙元任:多好玩兒的語
傅斯年:歸骨于田橫之島
傅斯年(1896-1950),字孟真,山東聊城人,祖籍江西永豐。著名教育家、歷史學家,的學生領袖之一,仿效《新青年》創辦《新潮》月刊,宣傳科學和民主思想。1919年底赴歐洲留學,先入英國愛丁堡大學,后轉入倫敦大學,研究實驗心理學、物理、化學和高等數學。1923年進入德國柏林大學哲學研究院,學習語言比較學等。歷任中山大學教授、北京大學教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等職,抗戰勝利時曾北京大學校長,直到胡適到任。1949年以后,他擔任臺灣大學校長。
在中國近代學術史上,傅斯年是一個不應被忽略,但由于特殊原因卻不為更多民眾所熟知的人物。他不僅是著名的歷史學家、教育家、的北大學生領袖、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創始人,還是北京大學校長、臺灣大學校長,一生富有傳奇色彩。傅斯年去世后,他的老師胡適一連用了十四個“最”字來表彰傅斯年,說他是“人間一個最稀有的天才。他的記憶力最強,理解力也最強。他能做最細密的繡花針工夫,他又有較大膽的大刀闊斧本領。他是最能做學問的學人,同時他又是最能辦事、最有組織才干的天生領袖人物。他的情感是最有熱力,往往帶有爆炸性的;同時,他又是最溫柔、最富于理智、最有條理的一個可愛可親的人。這都是人世最難得合并在一個人身上的才性,而我們的孟真確能一身兼有這些最難兼有的品性與才能。”
傅斯年1896年出生于山東聊城一個名門望族,其七世祖傅以漸是清代開國的及時位狀元,官至武英殿大學士、兵部尚書。曾叔祖傅繩勛為清嘉慶進士,官至武英殿協修、軍機處章京等職,后外放為浙江、江西、江蘇等省巡撫,晚年講學于濟南濼源書院和聊城啟文書院;其弟傅繼勛,亦即傅斯年的曾祖,在安徽為官多年,清末名臣李鴻章、丁寶珍等皆是他的門生。祖父傅淦少負才名,博通經史,工詩書畫,又精通醫道。同治十二年拔貢,但他自甘淡泊,不樂仕進,得到貢生資格后,便絕意仕途,終生不參加科試。傅斯年之父傅旭安,光緒甲午年舉人,曾任東平縣龍山書院山長。
傅斯年成人后,從不向人提及他的宰相先祖傅以漸,更不引以為榮,其原因是傅以漸在明清易鼎之際,出仕清朝,傅斯年認為他有違漢族士人的民族氣節。
傅斯年五歲時,祖父傅淦便迫不及待地送他進入當地好的私塾,放學后又在家督導傅斯年讀書習字,不準其有絲毫懈怠。傅斯年成年后曾對弟弟傅斯嚴深情地說:“祖父生前所教我兄弟的,盡是忠孝節義,從未灌輸絲毫不潔不正的思想,我兄弟得有今日,都是祖父所賜”。傅淦性情友善,重孝悌,且好交游,樂善好施,赴義唯恐后人,傅斯年一生堅持參政而不從政,為人常懷俠義之心,率直而有豪氣,這些都深受其祖父影響。
據傅斯年同鄉聶湘溪介紹:“孟真四歲即和祖父同床共寢,尚未起床,便口授歷史故事,從盤古開天辟地,系統地講到明朝,歷時四年,一部二十四史,就口授完畢了。在他幼小的心靈里早就埋下了研究歷史的興趣,其后能成為歷史學家是與其家學淵源分不開的。”
傅斯年9歲時,父傅旭安去世,當時傅斯年的弟弟剛出生7個月,兄弟二人由祖父和寡母李氏撫養成人。傅旭安生前為人仁厚,去世后,其友朋學生共同湊集一部分錢,以維持傅家生計。盡管如此,家用仍入不敷出,生活最窘迫時,傅母只得從房屋中拆一些磚瓦變賣,后來房屋破損無力修補,每逢下雨,李夫人便抱著幼子,頭上撐著一把雨傘遮蓋。盡管家道艱難,傅母仍嚴格督促傅斯年兄弟二人讀書,不使他們失學,而且教子甚嚴,兄弟二人如有過錯,立予責罰。
傅旭安出任龍山書院山長以前,有一次在聊城一家商店內見一青年學徒專心讀書。此人眉清目秀,談吐文雅,傅旭安與之攀談,知其姓侯,名延塽,因家境貧寒,奉后母之命來此當學徒。他酷愛讀書,利用一切空余時間刻苦自學,傅旭安對侯延塽的遭遇深懷同情,從此二人開始來往。1899年,傅旭安出任龍山書院山長時,讓侯延塽辭去商店差使,隨自己到龍山書院讀書,一切費用由自己代為解決。侯延塽意外得到這樣一個讀書的機會,自然更加刻苦自勵,苦讀了3年之后,參加光緒壬寅年鄉試,得中舉人;次年赴京會試,又中進士;經過朝考,被清廷授予刑部主事。侯延塽對恩師的提攜之恩銘記在心,及時次回鄉省親,便專去龍山書院拜望恩師,得知傅旭安已經去世后,又奔赴聊城看望師母。他在傅旭安墓前發誓,要把斯年、斯巖兄弟二人培養成才,以報恩師當年的知遇之恩。
侯延塽雖然是清末官僚,但思想并不保守,他深刻地意識到當時中國社會已經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新學興起,并且代表著時代的要求和中國發展的方向,聊城地處偏僻,傅斯年如長期呆在家鄉,接觸不到新事物,學不到新知識,因此,只資助他一些錢物是解決不了根本問題的。于是在侯延塽的安排下,1908年冬,12歲的傅斯年告別故鄉,進入天津府立中學堂,這是他人生的及時次轉折。
1913年,傅斯年考入北京大學預科,當時北大預科分甲乙兩部,甲部重數學及自然科學,乙部重文史,傅在乙部學習,由于國學底子好,四年考試三次全班及時。1916年,傅斯年入北京大學國學門。
初入北大時,傅斯年雖然只有十七八歲,但他的治學功底甚至強過了北大當時的某些教授。
北大同學聶湘濱回憶說:“據我了解他(傅斯年)很少上課,成天泡在圖書館里,博覽群書。當時有些教授就怕給他上課,往往在課堂上,他提出的問題,老師答不上來。使教師更難為情的是,他會當面指責教師講錯了,并有根據地說:這個問題某某書上是怎么講的,某某先生是怎么說的,我認為該怎么理解,經常把老師弄得張口結舌,下不了臺”。
傅的好友羅家倫回憶說:“在當時的北大,有一位朱蓬仙教授,也是太炎弟子,可是所教的《文心雕龍》卻非所長,在教室里不免出了好些錯誤……恰好有一位姓張的同學借到朱教授的講義全稿,交給孟真。孟真一夜看完,摘出三十幾條錯誤,由全班簽名上書校長蔡先生,請求補救,書中附列這錯誤的三十幾條。蔡先生對于這些問題是內行,看了自然明白……”可蔡元培不信這是學生們自己發現的,為防教授們互相攻訐,于是突然召見簽名的全班學生。同學們慌了,害怕蔡元培要考,又怕傅斯年一人承擔這責任未免太重。于是大家在見蔡先生之前,一人分擔了幾條,預備好了方才進去。果然蔡先生當面口試,同學們回答得頭頭是道。考完之后,蔡先生一聲不響,同學們也一聲不響,一一鞠躬魚貫退出。過后不久,朱蓬仙果然不再教這門課,而換成了黃侃。
傅斯年的天縱之才為同學極力推崇,甚至有人稱贊這位山東才俊是“孔子以后及時人”、“黃河流域的及時才子”。平日,某若問另一同學是中文系哪班,若對方回答是傅斯年那班的,彼此肯定會心一笑。因為有傅斯年“壓”著,別人休想翻身。后來,傅斯年到歐洲留學,被傅斯年譽為“中國最有希望的兩個讀書種子” 的俞大維竟也趕忙棄學文史而改擇理科,他說:“搞文史的人當中出了個傅胖子,我們就永無出頭之日了!”
當時,黃侃等人皆將傅斯年視為衣缽傳人,傅斯年也以其師為楷模,就連穿著打扮也刻意模仿黃侃:一襲長衫,一把大葵扇,一卷古書。但因為一個人的出現,傅斯年的人生再次發生了改變,這個人就是胡適。
1916年11月,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長,提出“兼容并包”的辦學方針。次年,胡適從海外歸來后,被聘為北大教授,講授中國哲學史,但其講授的內容和方法與眾不同,當時就讀于北大哲學系的顧頡剛后來說:“覺得他(胡適)講的雖是哲學,不啻講的史學,更不啻講的是治史學的方法。他用實驗主義的態度講學問,處處是出我意外,入我意中。”不過胡的授課方式卻在學生中引起不小的爭議。有人認為胡適遠不如國學大師陳漢章,想把他趕走;有人則認為,胡適讀的書雖然沒有陳漢章多,講課卻頗有新意。顧于是想起在學生中頗有威望的好友傅斯年,想讓傅去聽一聽胡適的課,傅斯年開始以自己不是哲學系的推脫,顧說:“你雖不是哲學系學生,又何妨去聽一聽呢?”傅斯年最終接受了顧的建議,專門去聽了幾堂胡適的課,并且做足功課,在課堂上以請教為名向胡適發問,胡適一一作答,傅則步步緊逼,一問一答之間,胡適的汗就下來了。胡適后來坦白地說,他當時就發現了,這批學生盡管“年輕但是卻相當成熟,而對傳統學術又頗有訓練”,有“幾個學生的學問比我強”。
后來回憶起這段日子時,胡適感慨地說:“那時北大中國哲學系的學生都感覺一個新的留學生叫做胡適之的,居然大膽地想紋斷中國的哲學史;因為原來講哲學史的先生們,講了兩年才講到商朝,而胡適之一來就把商朝以前的割斷,從西周晚年東周說起。這一班學生們都說這是思想造反;這樣的人怎么配來講授呢?那時候,孟真在學校中已經是一個力量。那些學生們就請他去聽聽我的課,看看是不是應該趕走。他聽了幾天以后,就告訴同學們說,‘這個人書雖然讀得不多,但他走的這一條路是對的。你們不能鬧。’我這個二十幾歲的留學生,在北京大學教書,面對著一般思想成熟的學生,沒有引起風波;過了十幾年以后,才曉得是孟真暗地里做了我的保護人。”
聽過胡適的課之后,傅斯年對胡適的治學方法很是認同,從此之后,便疏遠了黃侃等章氏門生,不時趨訪胡適,請教學問,縱論時局。在胡適的家里,傅斯年結識了同在北大讀書但并不在一個系里的羅家倫。對此羅家倫回憶說:
“我和孟真是1917年在北京大學認識的……我們開始有較深的了解,卻在胡適先生家里。那時我們常去,先則客客氣氣的請教受益,后來竟成為討論爭辯肆言無忌的地方。這時期還是適之先生發表了《文學改良芻議》以后,而尚未正式提出“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也就是未正式以文學革命主張作號召以前。適之先生甚驚異孟真中國學問之博與精,和他一接受以科學方法整理舊學以后的創獲之多與深。適之先生常是很謙虛地說,他初進北大做教授的時候,常常提心吊膽,加倍用功,因為他發現許多學生的學問比他強。(抗戰勝利后的第二年,適之先生于北大校慶之夕,在南京國際聯歡社聚餐時演講,就公開有此謙詞。)這就是指傅孟真、毛子水、顧頡剛等二三人說的。當時的真正國學大師劉申叔(師培)、黃季剛(侃)、陳伯弢(漢章)幾位先生,也非常之贊賞孟真,抱著老儒傳經的觀念,想他繼承儀征學統或是太炎學派等衣缽。孟真有徘徊歧路的資格,可是有革命性、有近代頭腦的孟真,決不徘徊歧路,竟一躍而投身文學革命的陣營了。以后文學革命的旗幟,因得孟真而大張。”
隨著與胡適交往日深,傅斯年盡棄舊學,轉而投向新文學陣營。1918年,傅斯年與同學羅家倫、顧頡剛等人組織新潮社,通過陳獨秀向蔡元培提出申請,蔡同意從北大每年4萬元的經費中撥出2000元作為辦刊經費,于是新潮社由胡適做顧問,創辦《新潮》月刊,與《新青年》同聲相呼。
周作人在《知堂回想錄》中說:“《新潮》的主干是傅斯年,羅家倫只是副手,才力也較差,傅在研究所也單認了一種黃侃的文章組的‘文’,可以想見一年之前還是黃派的中堅。但到七年十二月,就轉變了。所以陳獨秀雖自己在編《新青年》,卻不自信有這樣的法力,在那時候曾經問過我,‘他們可不是派來做細作的么?’我雖然教過他們這一班,但實在不知底細,只好成人之美說些好話,說他們既然有意學好,想是的吧。”
傅斯年在《新潮》上發表了40多篇文章,內容涉及文學語言、社會政治、道德倫理、哲學歷史等領域,隨著新文學運動影響日大,最初銷量不佳的《新青年》、《新潮》發行量大增,傅斯年也隨之蜚聲文壇,成為北京大學著名的學生領袖。胡適在《中國文藝復興運動》一文中說:“《新潮》雜志,在內容和見解方面,都比他們的先生們辦的《新青年》還成熟得多,內容也豐富得多,見解也成熟得多。”
1919年“”爆發,北京十三所學校學生3000余人在天安門集會后舉行游行,扛著大旗走在隊伍前面的,正是傅斯年。游行隊伍起初秩序良好,但在東交民巷使館區受阻后,學生的情緒開始失控,有人大喊:“大家往外交部去,大家往曹汝霖家里去!”傅斯年雖然平時性情急躁,容易激動,但每臨大事卻非常理智,他勸導眾人保持冷靜,不要過激,但他個人的聲音在群情激涌面前已經太過微小,阻擋不了事態的發展。此后的火燒趙家樓和群毆章宗祥,已超出了學生和平游行示威的初衷,32名學生因此被捕入獄。
在暴力事件上演后,傅斯年離開了鬧哄哄的現場。翌日,北大學生會開會,一位山西籍學生與傅斯年意見相左,由口角紛爭發展到武力毆斗,對方打掉了傅斯年的眼鏡。傅斯年怒不可遏,向好友賭咒發誓不再參與北大學生會的工作。
趙家樓的沖天火光映紅了古老的京都,朝野為之震動,北洋政府做出了查封北大,懲辦校長蔡元培的舉措。蔡元培一面沉著果敢地與政府官僚周旋,一面安撫學生,勸其復課,同時聯絡組織平津地區的國立大學校長為營救被當局逮捕的學生奔走呼號。當被捕學生全部被釋放,蔡元培于5月8日夜提交辭呈,悄然離京。
而作為學生領袖的傅斯年,也于這年夏天畢業離校,懷著百感交集的心情回到故鄉山東聊城。同年秋季,山東省教育廳招考本省籍官費留學生,傅斯年赴省會濟南應試,并以全省第二名的優異成績入選。盡管如此,主考方卻以傅是中的“激烈分子,不是循規蹈矩的學生”,且還是“兇惡多端的學生示威活動的頭頭”等為由,拒絕錄取。在這關乎傅斯年人生命運的緊要關頭,山東省教育廳一位以行俠仗義著稱的科長陳豫挺身而出,據理力爭:“如果成績這么優越的學生,都不讓他留學,還辦什么教育!”傅斯年終于涉險過關,1919年冬,他由北京起身去上海,乘輪船赴歐洲,開始了7年的留學生涯。
有人認為傅斯年在“”中所起的作用有些虎頭蛇尾,之后甚至與之漸行漸遠,但如果我們肯透過表象,更深地向下探尋,就可以看出傅斯年對于學生運動的思想脈絡,以及他選擇負笈留學的根源所在,而這也正是傅斯年之所以為傅斯年的地方。
在“五四”前一個月發表在《新潮》上的《白話文學與心理的改革》一文中,傅斯年指出:“凡是一種新主義、新事業,在西洋人手里,勝利未必很快,成功卻不是糊里糊涂。一到中國人手里,總是登時結個不熟的果子,登時落了。”“因為中國人遺傳性上有問題……因為中國人都以‘識時務’為應世上策。”傅斯年認為“自從以后,中國的新動機大見發露,頓使人勇氣十倍”,但是應該吸取此前的教訓,避免重蹈覆轍,使運動很快地興起,又快速地衰落。為了實現這一目的,思想界就要“厚蓄實力,不輕發泄”,通過長期的積累和持久的努力,使發軔的新動機能夠自然生長,結出成熟的果子,而不是再中途夭折。
對于學生動輒罷課,耽誤學業,尤其是使用暴力的做法,傅斯年是不認同的。學生運動的負面因素,如人心浮動,崇尚高談闊論,不肯踏踏實實地做學問,同樣引起了當時社會上的很多有識之士的警覺,如胡適、蔣夢麟等人,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先生在一年后回顧“”時也指出:“因群眾運動的緣故,引起虛榮心、依賴心,精神上的損失也著實不少。”
對于中國社會,傅斯年也有著頗有深刻的認識和剖析:“中國一般的社會,有社會實質的絕少,大多數的社會不過是群眾罷了。”在他看來,“凡名稱其實的社會——有能力的社會,有機體的社會——總要有個密細的組織,健全的活動力。若果僅僅散沙一盤,只好說是‘烏合之眾’。十個中國人所成就的,竟有時不敵一個西洋人。”而這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西洋人所憑托的社會,是健全的,所以個人的能力,有機會發展;中國人所憑托的社會只是群眾,只是有名無實。所以,個人的能力就無從發展。”
而在傅斯年看來,改造社會必須由下而上地進行。由上而下的改造,總會帶有幾分專制的臭味;而由下而上的改造,因為有社會基礎存在,才能有徹底的覺悟。
而這樣由下而上改造社會的及時步,就是要改造自己。在《歐游途中隨感錄》中,傅斯年寫道:“社會是個人造成的,所以改造社會的方法及時步是要改造自己。”又說:“我現在對于青年人的要求,只是找難題目先去改造自己。這自然不是人生的究竟,不過發軌必須在這個地方。若把這發軌的地方無端越過去,后來就有貌似的成就,也未必能倚賴得過。”他對新潮社同仁的期望是:(1) 切實的求學;(2) 畢業后再到國外讀書去;(3) 非到三十歲不在社會服務。而他自己決心要在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方面培植根底,認真讀書,認真研究,他在給北大畢業后任教于清華的好友袁同禮的信中說:“要把放洋的那24小時做我的生日。”
對于群眾運動,傅斯年也有自己的獨到見解:“我覺得若是青年人只知道有群眾運動,而不知道有個人運動,必有好幾種毛病。”一是,群眾運動雖然一時可以見效,但多因其中個人不健全的原故而不能支持。二是,改善需從個人始,若忘了個人,就是社會一時改的好了,之后也不免發生復舊的運動。三,沒有個人覺悟的群眾運動,其結果只會造就一批“神圣”,他們擁有崇高的威望和巨大的勢力、影響,以致權力集中到這少數人甚至一個人的手里,所成就的仍然不會是有機的社會,仍只是有群眾而無社會。
抵達英國后,傅斯年先入愛丁堡大學,后轉入倫敦大學,研究實驗心理學、物理、化學和高等數學。在傅斯年研究了三年心理學后,很多同學陸續來歐留學,其中陳寅恪、俞大維、徐志摩、金岳霖等先后聚集到德國柏林大學,他們多次來信勸說傅斯年到柏林。1923年秋,傅斯年終于下定決心,轉入柏林大學哲學院,學習哲學、物理、比較語言學等。
留學生在國外的物質生活大都非常清苦,但在私人生活方面,許多人卻比較放任,而在當時的德國留學生中,陳寅恪和傅斯年被譽為“寧國府大門口的一對石獅子,是最干凈的”。
趙元任、楊步偉夫婦游歷歐洲時曾到過柏林,楊在《雜憶趙家》中記述道:“孟真和元任最談得來,他走后元任總和我說此人不但學問廣博,而辦事才干和見解也深切得很,將來必有大用,所以以后凡有機會人家想到元任的,元任總推薦他,因元任自知不如也。”
一次當地留學生請趙氏夫婦去傅的住處吃茶點,定的下午三點,趙氏夫婦剛吃過午飯,“本以為只有一點點心和茶,豈知到了那兒一看,除點心外,滿桌的冷腸子肉等等一大些,我們雖喜歡,沒有能多吃,看他們大家狼吞虎咽地一下全吃完了。我說德國吃茶真講究,這一大些東西,在美國吃茶只一點糕什么連三名治都很少的。孟真不憤地回我:趙太太!你知道這都是我們給中飯省下湊起來請你們,你們不大吃所以我們大家現在才來吃午飯。”楊步偉感嘆說:“他們這一班人在德國有點錢都買了書了,有時常常地吃兩個小干面包就算一頓飯。”
有意思的是,傅斯年和陳寅恪一樣,學習廣博而刻苦,在國外卻沒有獲得任何學位。在傅斯年離開柏林大學的證明書上寫著:傅斯年,1896年5月26日生于中國聊城,在柏林大學讀到1926年夏季學期止,為哲學系學生。此人修過但在課冊中未被證明的還有人類學、梵文文法、普通語言學。
傅斯年返國后,本想回到北大任教。但就在他歸國之前,接連發生了幾件大事。
1926年3月18日,北京高校學生因為日本軍隊派軍艦炮擊天津大沽口,公然侵略、挑釁,紛紛組織起來向段祺瑞執政府請愿。當游行隊伍來到執政府門口時,遭到槍擊和暴力毆打,當場死傷數百人,這就是著名的“三一八慘案”。
慘案發生后,北洋政府擬定了一張通緝當時北京教育、文學界支持學生運動的50余名人士的名單,北京大學等幾所高校處于風雨飄搖之中,魯迅、劉半農、馬敘倫、高一涵、陳翰笙、馬寅初等被迫離開北平,留下者也多韜光養晦,不再出頭露面。
1926年4月15日,奉直聯軍從天津進入北平,京城內一時風聲鶴唳,北大的蔣夢麟、朱家驊、紛紛出逃,7月,胡適出走英國,北大陷入前所未有的凋零局面。7月9日,以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的名義,在廣州市東校場誓師北伐。
所以同年10月底,當傅斯年乘船返國時,前途還是一片渺茫。但就在他登陸香港時,一份來自廣州中山大學的聘書意外地出現在他面前,邀請他的是經戴季陶推薦,在光復后的廣州主持中山大學校務的朱家驊。接到聘書的傅斯年當即表示同意,但要先回山東拜望老母。 12月,傅斯年出任中山大學文科學長暨國文、史學兩系主任,半年多后,他又創辦了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
傅斯年回國之前,因為去北大一事已然無望,曾致信在清華任教的好友陳寅恪,陳極力想要在清華為其謀一職位,11月,梅貽琦在陳寅恪的極力推薦下,決定聘用傅斯年,不料中山大學捷足先登,傅因此與清華失之交臂。
1927年5月9日,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決定設立中央研究院籌備處,由已從歐洲考察歸國的蔡元培負責,中央研究院最初只設了理化實業、社會科學、地質、觀象四個研究所,但作為籌備委員之一的傅斯年認為,既然是中央研究院,就應該設立文史方面的學科,否則將有失偏頗,于是他召集“一部分熱心文史學的先進”,以“歷史語言研究的特別重要,現代的歷史學與語言學科是科學”等說詞,憑著北大時代與蔡元培校
絕對的好書,喜歡作者極富感染力的描寫。讓我們回到那個國家滿目瘡痍,但有識之士鞠躬盡瘁的年代。有他們的事跡告訴我們什么叫做有意義的生活,什么叫做忠實于自己的夢想,我們每位讀者都應珍視這次啟蒙的機會!中國需要更多的這種底氣的存在!
買前看來中評和差評,當時有些猶豫,買下之后,感覺很好。想想那些差評,可能閱讀者對這些故事早已熟知,希望得到深刻思想的描寫。對此段歷史略知一二或者不熟悉的人,確實是本不錯的書。
偶然間發現的這本書,讀了在線的幾段,覺得很好就買了。民國時期,確實有很多文人很有個性,又博學多才,值得世人敬仰的,我是中文出身,對書中寫的幾個人物,也有耳聞,這回可以詳細了解了。書的感覺很好,有淡淡得優雅氣息,還是讀紙質的書,有感覺~
買這本書之前看過別人的評論.說這本書文筆很好.買回來看了一下.覺得也沒有說很好.可能是因為我比較看習慣詩集.但是作為一般的文化類書籍.這本書的文筆還是挺不錯的.而且.里面的東西寫得很細膩.但是在細膩中又蕩氣回腸.值得一看再看.
看了民國的氣質再看的民國的底氣,不得不說民國的教育真的很好,出了很多大家。
亂世多人才,民國就是這樣一個時代,風云際會,人才輩出,在這本書中感受到何為民國底氣
版本設計典雅大方,內容很精彩,文字有溫度,很能打動我。介紹了辜鴻銘、黃侃、王國維、陳寅恪等民國重量級知識分子的故事,令人感慨,令人思考。
還沒細看,先大體翻了翻,一些非常熟悉的名字映入眼簾。一直想了解民國時期的故事,所以一口氣買了《民國的底氣》《國民的氣質》《民國范兒》《民國風度》四本書,相信這四本書看完了,我就會對民國時期的歷史有所了解了。
在線試讀完傅斯年就欲罷不能,作者的文筆和對人物的剖析都深深吸引著我,讓我看到真實的大師氣派,感動于書中人物傲人的才氣,嚴謹的學習態度,純粹的學術信仰,感嘆他們艱苦的條件、曲折的人生,在會心一笑中豁然明白大師何以堪稱大師!
很喜歡的一本書,講述的幾位大師的人生故事,有趣味性和閱讀性……、總體很好,但是作者少數觀點還是略有偏激的,讀的時候要回到那個時代的歷史擺正心態去思考,不要輕易被影響了,不然不小心就變成“憤青”了。
快遞能不能溫柔一點對待我們的書,書脊都磕破了,哼╭(╯^╰)╮差評。但是書很好哦!高考之前語文老師找了好多關于民國大家的趣事還有簡介,當作作文素材的。羨慕先生們的學識,佩服他們的氣度和風骨。
看了《民國的氣質》然后買的,感覺是快餐歷史里面不錯的書,用心去讀感受到民國學者的風華,即使在浮躁的現在社會里也能感受到一絲沉潛,那可真是一個精彩的年代~中國傳統博大精深的文化,和新思想新視野的西學,交匯碰撞,激蕩出許多大家學者,是一個學習學問的年代~
在當當購書這么久,第一次上來寫評論。這本書深入淺出,我看書過程中幾次落淚又幾次不禁大笑,實在是被書中的人物所感動。作者很神秘,我在網上都查不到相關的信息,但是看完這本書就能感覺到作者寫書的誠意。我還一次性購買了民國的氣質。
書中僅介紹了十位民國大師,包括辜鴻銘、王國維、趙元任和陳演恪等,但從他們的身上可見民國時學者治學之風采。他們多追尋學術獨立,認為做學術就要有自由獨立之精神。新中國成立六十余載,大師一個一個的離去。如今經濟似乎是搞上去了,可是卻不再有大師了。
我很喜歡民國的東西,無論是人或事物,無論是男人還是女人,在那個紛亂的年代仿佛都有著一種特別的氣質,很是迷人。旗袍,愛情,國家,民族,都是那個時代的主題,都是我們這些后人眼中的絕唱,幾乎每個人,在那個年代,都有著別樣的魅力
以前看過一本關于民國大師介紹的書籍,后來又買了一本南渡北歸。今天這個時代,很多人質疑民國的大師,也有人十分推崇民國時的教育。無論如何,在我看來,他們那種做學問的精神今天的人是無法比擬的。
拿到手就翻到趙元任那一章節,讀來酣暢淋漓。被小故事和事跡觸動,也不斷反思為什么民國時代的他們有如此成就,現在的自己如何能在時間的河流中留下什么。很好的人,很好的書,尤其對我這種受物質文化侵蝕很久的人來看看,為時不晚。
在我們這樣年齡的人中,民國往往是與軍閥混戰、民不聊生這些詞語聯在一起的。但是,果真如此的話,難以解釋短短37年的民國期間,大師輩出,燦如星斗。而近60年來,有幾個人堪與那些大家們比肩?還原一個真的民國吧。
民國的人物傳記中,這本寫的很好,展示了大師們的風骨和才情。我感覺現在的學者缺少獨立人格,思想不深刻,人云亦云,不敢提出自己的見解。真應該好好看看前人的思想軌跡。我尤其佩服民國時期的教育家和作家,如魯迅、蔡元培等人。
這群人在那個命運都輾轉零落的動蕩年代,遠承魏晉風骨,以獨立之姿態,演繹出中華最后之名士風度,說他們承載了民國的底氣,實不為過。閱讀這本書,其實就是帶我們閱讀了一段歷史和文化。
很愛這本書。書的文字是我非常喜歡的。介紹了民國時期的很多大師的趣事,也讓我們回憶起了那個時代的很多事情。對于人物的刻畫是非常深刻的,尤其是在書本中,關于其人物的學術成就以及生活性格上的描寫,是很仔細的。非常推介,有利于了解民國時的人物群像。
幾百幾千年后,民國那段歷史注定要被大書特書的!那是中華歷史上的一個閃光點,雖然只有一瞬間,但它的光芒是誰也掩蓋不了的!有種說法是亂世出大師,亂世的時候對知識分子的思想禁錮最輕,這種觀點用民國那段歷史來證明是再恰當不過的了!
君子固窮,文化人的骨氣傲氣在他們身上表現的淋漓盡致。在那戰火紛飛,國土淪陷的年代里,他們能夠安于貧窮,在最困頓的時候,安心學問,著述立學,不受外界影響,誘惑;他們有骨氣有傲氣有脾氣敢于直斥當權者,實在讓人折服!
喜歡民國那個年代,那個年代是自由的,是早就大師的年代。書中介紹了12位大師。被劉文典譽為“國粹”的“教授的教授”陳寅恪,語言之父趙元任,從不判卷子的教授錢玄同,清華大學終身教授梅貽琦,被甘地譽為"最尊貴的中國人”辜鴻銘......
書是不錯,只是紙質的出版書,“和諧”了好些內容,光一個人上就有好幾大段被刪節了,讓人很不舒服。不過書是好書,依舊值得推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