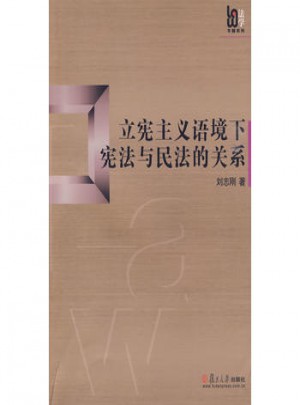
立憲主義語境下憲法與民法的關(guān)系
- 所屬分類:圖書 >法律>國家法/憲法
- 作者:[劉志剛] 著
- 產(chǎn)品參數(shù):
- 叢書名:法學專題系列
- 國際刊號:9787309068290
- 出版社:復(fù)旦大學出版社
- 出版時間:2009-09
- 印刷時間:2009-09-01
- 版次:1
- 開本:16開
- 頁數(shù):--
- 紙張:膠版紙
- 包裝:平裝
- 套裝: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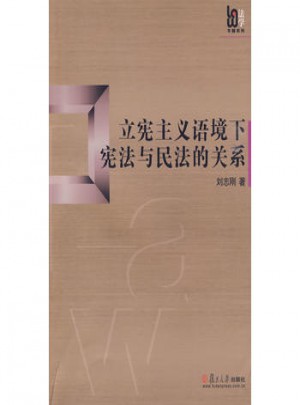
憲法與民法的關(guān)系是憲法學理論研究中的一個重要命題,對該命題的研究直接關(guān)涉到憲法學中一系列基礎(chǔ)理論的展開。作者將憲法與民法的關(guān)系置于立憲主義的語境之下,從憲法與民法的關(guān)系概說、憲法與民事立法的關(guān)系、憲法與民事法律行為的關(guān)系、憲法與民事司法的關(guān)系等四個方面系統(tǒng)地分析論證了憲法在私法領(lǐng)域中的作用。在這一過程中,作者依托相關(guān)的理論背景,對近年來我國立法和司法實踐中所發(fā)生的一些熱點問題進行了深人的分析,提出了一些個人的觀點。該書的內(nèi)容對于從跨學科的角度分析、解讀憲法與民法的關(guān)系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
劉志剛,男,原籍河北武安,1971年出生于河南安陽。1999年、2002年先后畢業(yè)于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獲得法學碩士、法學博士學位。2002年進入武漢大學法學院博士后流動站從事博士后研究。2004年博士后出站后于復(fù)旦大學法學院任教至今。自1996年以來,長期致力于憲法學與行政法
及時章 立憲主義語境下憲法與民法的關(guān)系概說
及時節(jié) 立憲主義的基本精神
一、古代社會的政治哲學
二、近代立憲主義政治哲學的產(chǎn)生
三、近代立憲主義政治哲學的成熟和完善
第二節(jié) 立憲主義由以存在的社會基礎(chǔ)
一、市民社會的基本含義
二、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的關(guān)系
三、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的分離和互動是立憲主義由以存在的社會基礎(chǔ)
第三節(jié) 國內(nèi)學者視野中的公法與私法關(guān)系問題
一、公、私法分類由以存在的社會基礎(chǔ)——市場經(jīng)濟目標模式的確立
二、國內(nèi)法學界關(guān)于公、私法分類問題的討論
三、國內(nèi)法學界關(guān)于公法與私法關(guān)系問題的討論
第四節(jié) 國內(nèi)法學界關(guān)于憲法與民法關(guān)系的論爭
一、中國傳統(tǒng)憲法學理論關(guān)于憲法與民法關(guān)系的觀點
二、20世紀90年代民法學界提出的"民法優(yōu)位論"、"民法與憲法平行論"與我國憲法學界對其所作的滯后回應(yīng)
三、"憲法司法化"及時案之后我國憲法學界對憲法與民法關(guān)系的自省與反思
四、鞏獻田教授公開信發(fā)表后憲法學者的針對性回應(yīng)和民法學者再度提出的"民法優(yōu)位論"和"憲法與民法平行論"
五、梁彗星教授文章 發(fā)表后憲法學界對憲法與民法關(guān)系問題的回應(yīng)
第二章 憲法與民事立法的關(guān)系
及時節(jié) 民法的性質(zhì)與調(diào)整對象概述
一、民法的性質(zhì)
二、民法的調(diào)整對象
第二節(jié) 憲法的性質(zhì)
一、憲法的公法性質(zhì)是確保作為現(xiàn)代法制之基礎(chǔ)的公、私法分類的前提
二、福利國家時代公法、私法的混合與交融不能抹殺憲法的公法性質(zhì)
第三節(jié) 憲法與民法關(guān)系在民法制定方面的話語基礎(chǔ)
一、"根本法"的內(nèi)涵
二、"母法"的實質(zhì)性內(nèi)涵
第四節(jié) 憲法與民事立法之間關(guān)系所發(fā)生的場域
一、憲法中的哪些內(nèi)容對民事立法具有影響
二、在民事立法方面,憲法對民法中的什么內(nèi)容具有影響
第五節(jié) 作為公法的憲法是私法的制定基礎(chǔ)
一、古典自然法理論不足以作為"私法優(yōu)位論"的基礎(chǔ)
二、民法典的功能不足以防范來自國家公權(quán)力的侵害,憲法是私法由以自治的基礎(chǔ)
第六節(jié) 憲法對民事立法的影響有不同的方式
一、憲法中應(yīng)該有關(guān)涉經(jīng)濟內(nèi)容的規(guī)定,但以憲法為制定根據(jù)的民法并不需要重復(fù)憲法中的相關(guān)內(nèi)容
二、憲法中關(guān)涉財產(chǎn)權(quán)的規(guī)定是民法的制定依據(jù),后者需要對其加以充實和具體化
第三章 憲法與民事法律行為的關(guān)系
及時節(jié) 基本權(quán)利與私法權(quán)利
一、權(quán)利的含義及其在近代的出現(xiàn)
二、權(quán)利由以存在的根據(jù)及基本權(quán)利作為私法權(quán)利存在根據(jù)的正當性
三、基本權(quán)利與包括私法權(quán)利在內(nèi)的法律權(quán)利的區(qū)別
第二節(jié) 民事法律行為概說與基本權(quán)利相較于民事行為的意義
一、民事法律行為的歷史沿革
二、民事法律行為的適用范圍及其調(diào)整方式
三、民事權(quán)利的功能與基本權(quán)利對民事行為的意義
第三節(jié) 基本權(quán)利在民事法律行為領(lǐng)域的適用
一、國家涉足民事行為領(lǐng)域的背景及原因
二、國家涉足民事行為的領(lǐng)域及基本權(quán)利在該領(lǐng)域的適用
三、基本權(quán)利對國家所為之民事法律行為的適用
四、基本權(quán)利對私人在傳統(tǒng)公共行政領(lǐng)域所為之私法行為的適用
第四章 憲法與民事司法的關(guān)系
及時節(jié) 憲法"司法"適用問題在中國的提出
一、"齊玉苓訴陳曉琪等侵犯姓名權(quán)、受教育權(quán)案"的案情
二、"齊玉苓"案引發(fā)的憲法司法適用方面的討論及學術(shù)界的相關(guān)觀點
第二節(jié) 憲法與民事司法關(guān)系的框架性分析
一、基本權(quán)利對司法機關(guān)效力的類型化分析
二、基本權(quán)利在民事審判中的適用問題的提出背景
三、基本權(quán)利在民事審判中原則上不能適用的原因
四、新形勢下,基本權(quán)利在民事審判中被適用的原因
五、基本權(quán)利在民事審判中適用的比較分析
第三節(jié) 基本權(quán)利在民事司法中適用的具體問題
一、民法的法律淵源與民事審判的法律依據(jù)
二、國內(nèi)語境下對民事審判中基本權(quán)利的適用及其范圍的分析
三、基本權(quán)利在民事審判中與其他規(guī)則形式的關(guān)系調(diào)適問題
四、基本權(quán)利在民事審判中的適用管道
后記
及時章立憲主義語境下憲法與民法的關(guān)系概說
及時節(jié)立憲主義的基本精神
憲法和立憲主義是憲法學的基礎(chǔ)概念,兩者從不同的側(cè)面反映了國家與社會生活之間的相互關(guān)系。"如果說憲法概念表現(xiàn)一種靜態(tài)的價值體系的話,立憲主義概念則反映一種指導社會生活的動態(tài)價值體系。"民主社會發(fā)展到今天,制定憲法、建構(gòu)立憲主義政體已經(jīng)成為世界各國的一種共性的價值追求,是否制定了一部具有正當性的憲法、是否以立憲主義為政治建構(gòu)的目標是民主化時代人們評判特定政體是否具有正當性的基本指標。基于憲法、立憲主義所具有的褒義性,二者被當作一個時髦的標簽隨意套用,以至于在外觀和性質(zhì)上截然不同的政體都能夠以立憲主義政體而自詡。然而,就在人們基于不同的目的而竟相使用上述兩個術(shù)語并近乎達到泛濫程度的時候,"憲法"和"立憲主義"的確切含義卻逐漸被人所淡忘。荷蘭學者馬爾塞文指出:"憲法和憲政之間的舊有的聯(lián)系正在受到懷疑……憲法逐漸地在各種不同的政治制度中發(fā)揮作用已經(jīng)變得很明顯了……再也沒有必要把憲法的存在看作從屬于特定的思想前提,看來憲法能夠為每一種政治思想服務(wù)。"此語可謂深刻!在憲法和立憲主義的大旗已經(jīng)插滿世界絕大多數(shù)國家并近乎"紅旗滿山"的時候,以立憲主義為制度依歸的我們不能滿足于立基于這種表面繁榮基礎(chǔ)之上的津津樂道,而應(yīng)該撥開這種不時清風拂面的立憲主義面紗,透視和探究特定制度背后所蘊藏的立憲主義本質(zhì)。誠然,語言是一種開放的結(jié)構(gòu)體系,隨著時代的變遷,特定名詞術(shù)語中不時會添附一些新鮮的語義。然而,這種基于時代的變幻而施加的添附并不意味著從根本上背離特定術(shù)語之先前的本意。如果那樣的話,還不如從根本上加以推翻或者以一個新的范疇加以取代。作為一種語言存儲系統(tǒng),特定名詞術(shù)語的含義是以往歷史經(jīng)驗的凝結(jié),它匯集了特定時代人們的精神理念和價值訴求,是延承過去、展望未來的一個載體。如果將這種匯集了特定價值訴求的載體隨意套用,甚至施加于與之秉性不同的事物的時候,這種原本清晰的話語體系就會在結(jié)構(gòu)上徹底坍塌。在政治層面,甚至會引發(fā)體制上的混亂。說到底,這是一種對民意的強奸和欺騙!就"憲法"和"立憲主義"而言,它們具有為時代所賦予的特定價值內(nèi)涵,這是人們反思過去、追求未來的精神支柱,只能指向于特定的政治內(nèi)容和物質(zhì)載體,而不能被當作一種政治標簽隨意套用,指向于任何一種思想觀念。因此,從詞源學的角度,探究立憲主義的歷史本義,以防止現(xiàn)實中這一概念在使用上的混亂和一些人的故意歪曲,就顯得非常有必要。
一、古代社會的政治哲學
(一)古希臘的政治哲學
立憲主義是近代西方的產(chǎn)物,但其思想源頭最早可以追溯至古希臘時期。成型于近代西方的立憲主義不是某種單一政治思想的發(fā)展結(jié)果,而是自古希臘以來各種政治哲學相互競爭和妥協(xié)的產(chǎn)物。因此,挖掘和梳理立憲主義產(chǎn)生的基本理路,就必須從西方政治傳統(tǒng)的始源地——古希臘開始。
古希臘是歐洲最早進入文明社會和最早產(chǎn)生國家與法的地區(qū)。與早期東方和歐洲大陸國家不同的是,古希臘建立的不是疆域性和專制性的帝國,而是城邦制國家,古希臘實際上就是由一系列面積不大、人口不多的城邦國家組成的。與春秋戰(zhàn)國時代的中國不同的是,古希臘地區(qū)的城邦統(tǒng)治者們所關(guān)注的不是在既定政治結(jié)構(gòu)形式下的統(tǒng)治方式,如禮治還是法治問題,而是在不同城邦相互競爭的背景之下,力求最適合于城邦統(tǒng)治的政體形式。這種不同于東方社會的政治關(guān)注就造成了不同城邦之間在政體形式上的競爭,以及同一城邦在不同歷史時期對不同政體形式的先后嘗試,由此催生出了不同于古東方社會的公民政治和理性思想,并在歷史的長河中積淀而成了古希臘政治哲學,為近代西方立憲主義的產(chǎn)生提供了思想的源泉。
古希臘政治哲學的內(nèi)容無疑是博大精深、豐富雋永的,但蘊涵于其思想體系中的邏輯主線卻是非常清晰的,事實上,也正是在這條邏輯主線的貫穿下,才形成了為后世所延承并進而豐富和發(fā)展的立憲主義思維基點。那么,貫穿于古希臘政治哲學的邏輯主線是什么呢?不言而喻,就是立基于對人性反思基礎(chǔ)之上的整體主義和個體主義的論爭。整體主義的方法論最早導源于公元前6世紀時的古希臘。當時,古希臘城邦特別是雅典正逐步走向繁榮。基于城邦政治的公開性特征,雅典城邦公民熱衷于對城邦事務(wù)的民主參與和集體決策,由此推動了古希臘早期以整體主義為典型特色的政治哲學的產(chǎn)生,其典型代表就是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柏拉圖強調(diào)人的社會性,認為人天生就是政治動物或社會動物,任何個人都不是自足的,只有通過城邦生活,人類才能獲得的自給自足,因此過一種整體的城邦生活是合乎自然的。柏拉圖指出:"我們的立法不是為城邦任何一個階級的特殊幸福,而是為了造成全國作為一個整體的幸福。它運用說服或強制,使全體公民彼此協(xié)調(diào)和諧,使他們把各自能向集體提供的利益讓大家分享。而它在城邦里造就這樣的人,其目的就在于讓他們不致各行其是,把他們團結(jié)成為一個不可分的城邦公民集體。"顯然,柏拉圖所奉行的是一種整體主義的人性觀,他的政治理論的核心就是探索能使整體的生活和目的影響個人的途徑,國家的使命就是積極地促進整體主義的善。亞里士多德繼承了柏拉圖那種整體主義的人性觀,并以命題的形式指出:人是合群的動物;人是社會性的動物;人是政治性的動物。亞里士多德在把人定為政治動物的時候,是說人是他那個特定社會整體的一部分,就是說,他深植于社會之中。與整體主義方法論相似,個體主義方法論在哲學上的源頭最早也可以回溯至古希臘。但與整體主義方法論不同的是,個體主義方法論主要興盛于古希臘晚期。當時,城邦政治已趨向于沒落,帝國逐步蠶食和取代了城邦政治,古希臘人逐漸喪失了先前城邦政治繁榮時期那種參與政治的權(quán)力,公民的職責只剩下單純的服從。個人由于不能參與公共生活,無法掌握自己的命運,也無力改變現(xiàn)狀,只好轉(zhuǎn)向個人的安身立命。在個體主義論者看來,國家的產(chǎn)生是個人自利的需要,法律是個人為了功利的目的而相互約定的產(chǎn)物。與整體主義論者鼓勵和支持個人參與政治不同,個體主義論者勸導個人遠離權(quán)力,退出公共生活,離群索居,親近知識和智慧,以此獲得內(nèi)心的平靜。與先前時期相比,城邦衰落時期的哲學不再追求城邦整體的至善,而是追求立足于排斥國家侵害的個體的善。這樣一來,先前城邦政治繁榮時期那種政治哲學就實現(xiàn)了結(jié)構(gòu)性的轉(zhuǎn)變,成為一種與政治相對分開的倫理哲學。
反觀古希臘時期政治哲學的發(fā)展軌跡,可以清楚地發(fā)現(xiàn),伴隨著古希臘城邦的繁榮和衰落,整體主義和個體主義的爭論一直持續(xù),并交替占據(jù)主導地位。這種爭論上升到政治層面,集中表現(xiàn)為對個人與國家之間關(guān)系的不同理解,由此為后世立憲主義的產(chǎn)生奠定了扎實的思想基礎(chǔ)。事實上,成為后世立憲主義思想基礎(chǔ)的"對個人權(quán)利的尊重和保障"、"契約論"、"自然法"、"民主制度與理念"以及關(guān)于政體的觀念等大名源生于此。
(二)古羅馬的政治哲學
與古希臘建立的城邦制國家不同,源起于羅馬城邦的古羅馬人奉行對外侵略擴張的政策,最終建立了一個以地中海為中心,橫跨歐、亞、非三大洲的帝國。這種不同于古希臘的政治實踐影響了古羅馬人對城邦政治的關(guān)注熱情,進而形成了一種不同于古希臘的法律文化。回顧歷史,可以清楚地發(fā)現(xiàn),古羅馬沒有產(chǎn)生出類同于柏拉圖、亞里士多德那樣的哲學大師,在政治哲學方面也沒有取得古希臘那樣的成就,它對后世的貢獻更多地表現(xiàn)在私法方面。然而,古羅馬人卻創(chuàng)造了帝國這樣的政治制度,建立了比古希臘城邦更為精致和穩(wěn)定的政治體制,并在較大程度上克服了古希臘城邦那種與生俱來的缺陷,即安全方面的不足以自保和政治層面的過于肥大。因此,相較于古希臘來說,古羅馬的政治成就更多地表現(xiàn)在政治實踐方面,而不是政治理論方面。由于缺乏類同于古希臘那樣的源出于自身的政治哲學,古羅馬人往往自覺不自覺地援引古希臘的政治哲學來解釋自身的政治法律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