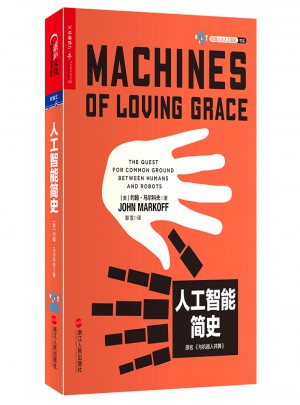
人工智能簡史
- 所屬分類:圖書 >經(jīng)濟>中國經(jīng)濟>中國經(jīng)濟概況
- 作者:[ 美] [約翰]· [馬爾科夫]([John] [Markoff])著
- 產(chǎn)品參數(shù):
- 叢書名:--
- 國際刊號:9787213084515
-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
- 出版時間:2017-11
- 印刷時間:2017-11-01
- 版次:1
- 開本:16開
- 頁數(shù):345
- 紙張:膠版紙
- 包裝:平裝-膠訂
- 套裝: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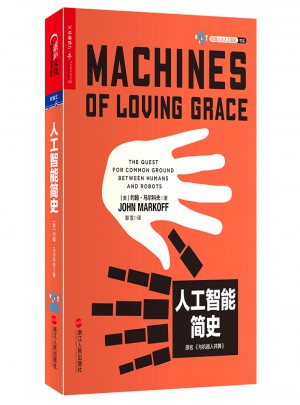
l 人工智能究竟是天使,還是魔鬼?
人工智能會像200年前的電力那樣顛覆世界嗎?
未來的機器人是否真的會像電影《Her》《機械姬》中那樣具備高超的人類智慧,進而取代人類?
奇點來臨時,人類將何去何從?
在《人工智能簡史》一書中,人工智能時代的科技預(yù)言家、普利策獎得主約翰 馬爾科夫?qū)ьI(lǐng)我們尋找答案。
l 約翰 馬爾科夫在他的重磅新作《人工智能簡史》一書里,從多個維度描繪了人工智能從爆發(fā)到遭遇寒冬再到野蠻生長的發(fā)展歷程,直擊了工業(yè)機器人、救援機器人、無人駕駛汽車、語音助手Siri等前沿領(lǐng)域,進而深入探討了人工智能(AI)與智能增強(IA)的密切關(guān)系,而馬爾科夫也會剖析“人與機器誰將擁有未來”這一機器時代的核心倫理問題。
l 《人工智能簡史》是國內(nèi)首套集、重磅、系統(tǒng)、實用于一體的“機器人與人工智能”書系之一!是迄今為止非常完整又具可讀性的人工智能史著作。約翰 馬爾科夫重新定位了人與機器的關(guān)系,是目前關(guān)于機器人與人工智能領(lǐng)域內(nèi)非常具有力度的深思之作。
l 《人工智能簡史》是首套集、重磅、系統(tǒng)、實用于一體的“機器人與人工智能”書系之一!
l 湛廬文化聯(lián)合機構(gòu)中國人工智能學(xué)會特設(shè)專家委員會!該專家委員會包括中國工程院院士李德毅、馭勢科技(北京)有限公司聯(lián)合創(chuàng)始人兼CEO吳甘沙、地平線機器人科技創(chuàng)始人余凱、IBM中國研究院院長沈曉衛(wèi)、國際人工智能大會(IJCAI)常務(wù)理事楊強、科大訊飛研究院院長胡郁、中國人工智能學(xué)會秘書長王衛(wèi)寧、達闥科技創(chuàng)始人兼CEO黃曉慶、清華大學(xué)教授朱小燕等專家學(xué)者,他們將以自身深厚的專業(yè)實力、的洞察力和深遠(yuǎn)的影響力,對這些圖書進行深度點評。
l 人工智能時代的科技預(yù)言家、普利策獎得主、喬布斯強力推崇的記者約翰 馬爾科夫重磅新作!
l 《人工智能簡史》是迄今為止非常完整又具可讀性的人工智能史著作,為我們描繪了一幅機器人與人工智能趨勢的宏大圖景!人工智能究竟是天使,還是魔鬼?人工智能為何在經(jīng)歷“寒冬”之后在今日迸發(fā)出野蠻生長的態(tài)勢?人工智能和智能增強終將走向何方?奇點來臨時,人還會是自身命運的主宰者嗎?本書將給你答案。
l 國際人工智能領(lǐng)域5大知名專家重磅推薦,《史蒂夫 喬布斯傳》作者沃爾特 艾薩克森傾情推薦!中國人工智能學(xué)會副理事長、國際人工智能大會(IJCAI)常務(wù)理事、騰訊微信事業(yè)群技術(shù)顧問楊強,中國人工智能學(xué)會副秘書長、地平線機器人科技創(chuàng)始人余凱,馭勢科技(北京)有限公司聯(lián)合創(chuàng)始人兼CEO吳甘沙,《史蒂夫 喬布斯傳》作者沃爾特 艾薩克森傾情推薦!Nest聯(lián)合創(chuàng)始人、iPod之父托尼 法德爾,美國艾倫人工智能研究所CEO奧倫 埃奇奧尼聯(lián)袂推薦!
l 湛廬文化出品。
約翰 馬爾科夫
n 《紐約時報》高級科技記者,普利策獎得主,被譽為“硅谷獨家大王”。他對互聯(lián)網(wǎng)發(fā)展有著驚人的洞察力與敏銳度,他是最早對互聯(lián)網(wǎng)進行報道的記者,將互聯(lián)網(wǎng)譽為“信息時代的藏寶圖”;并最早對首個通過互聯(lián)網(wǎng)傳播的蠕蟲病毒進行了報道。
n 有40多年的媒體從業(yè)經(jīng)歷,專注于機器人與人工智能領(lǐng)域的報道。他是報道谷歌無人駕駛汽車及時人,更是喬布斯等業(yè)界大咖極為信賴的記者。
中文版序 智能機器時代的抉擇
前言 是謙遜地生存,還是傲慢地死去
01 人與機器,誰將稱王
無論機器人是否在現(xiàn)實世界幫助了我們,人工智能已經(jīng)不可辯駁地日益成為我們生活的一部分。今時今日,麥卡錫和恩格爾巴特最為核心的沖突仍然懸而未決—— 一種方法要用日益強大的計算機硬件和軟件組合取代人類;另一種方法則要使用相同的工具,在腦力、經(jīng)濟、社會等方面拓展人類的能力。需要再次注意的是,若軟件和硬件機器人都足夠靈活,它們最終都會變成我們在程序中為它們設(shè)計的模樣。
◇ 比爾 杜瓦爾,在AI 和IA 中游走的及時人
◇ 兩大陣營的奇點之爭:主人、奴隸還是伙伴
◇ 人機交互,機器的終極智慧
◇ 懸而未決的倫理困境
02 無人駕駛汽車,將人類排除在外
DARPA 大賽是兩個世界的分界線——在一個世界中,機器人被視作玩具或研究人員的玩物;而在另一個世界中,人們開始接受機器人能夠在世界上自由移動的事實。如今,“半自動”汽車已經(jīng)在市場上出現(xiàn),它們給交通的未來開啟了兩條路—— 一條路配有更智慧、更安全的人類司機;而在另一條路上,人類將成為乘客。機器智能時代的到來
◇ 特瑟的自動駕駛汽車挑戰(zhàn)賽
◇ 問鼎冠軍,威廉 惠特克的復(fù)仇
◇ 塞巴斯蒂安 特龍,用科技重塑交通系統(tǒng)
◇ 谷歌無人駕駛汽車的誕生
◇ 2014,無人駕駛汽車商業(yè)化元年
◇ Mobileye,無人駕駛汽車的另一種可能
◇ 應(yīng)對分心,將人類排除在駕駛之外
◇ 手推車難題,是否選擇“更小的惡魔”
03 跨越2045 年,人類將去往何處
隨著機器學(xué)習(xí)能力的增強,它們?nèi)找娉尸F(xiàn)出了極強的獨立性,而這一新機器時代正掀起一場十分嚴(yán)酷的工業(yè)革命,可以將一名工廠工人置于不被雇用的地步。奇點臨近,到底誰才是人類命運的主宰者? 2045 年,對人類來說究竟將是艱難的一年,還是會掀起一場技術(shù)盛宴的一年,抑或是兩種可能同時發(fā)生的一年?
◇ 諾伯特 維納,一位科學(xué)家的反叛
◇ 技能錯配,技術(shù)性失業(yè)的元兇
◇ 奇點臨近,人類會否被機器取代
◇ 生產(chǎn)力之爭,回歸還是告別
04 從寒冬到野蠻生長,人工智能的前世今生
雖然很多人相信世界上及時個機器人Shakey 預(yù)示了人工智能的未來,但其商業(yè)化進程卻不甚理想。20 世紀(jì)80 年代初,人工智能公司一家接一家地走向崩潰。現(xiàn)如今,新一波人工智能技術(shù)預(yù)示著新“思維機器”的出現(xiàn)。而隨著微軟、谷歌等公司的加入,新一波人工智能浪潮再次被喚起。
◇ 世界首個機器人Shakey,引爆人工智能大爆炸
◇ 約翰 麥卡錫,“人工智能”概念之父
◇ 斯坦福大學(xué)人工智能實驗室,語音識別技術(shù)濫觴
◇ 漢斯 莫維拉克,人工智能最堅定的信徒
◇ 人工智能商業(yè)化的冬天
◇ 像人腦一樣思考,人工神經(jīng)網(wǎng)絡(luò)出現(xiàn)突破
◇ 機器學(xué)習(xí)重燃人工智能研究
◇ 人工智能再現(xiàn)巨浪
05 以人為本,重新定義“機器”智能
在交互式計算的前50 年中,計算機更多的是在增強而非取代人類,人工智能遭遇了“滑鐵盧”,很多人背離過往,將自己職業(yè)生涯的剩余時間貢獻給了“以人為本”的計算,也即智能增強。他們“遺棄”了人工智能圈,將注意力從建造智能機器轉(zhuǎn)到了讓人類變得更聰明上。
◇ 人機共生,AI 與IA 重塑的新世界
◇ AI vs. IA,數(shù)十年的科學(xué)家大戰(zhàn)
◇ “理性主義”與“以人為本”之爭
◇ 擬人化界面,來自人機交互的沖擊
◇ 軟件助手,數(shù)字化生存之道
06 學(xué)會協(xié)作,人類與機器共存
馬文 明斯基、杰夫 霍金斯和雷 庫茲韋爾等多位電子工程師都宣稱,實現(xiàn)人類級別的智能的方法是發(fā)現(xiàn)并整合那些人類大腦中隱藏著的認(rèn)知的簡單算法。這通常能制造出有用、有趣的系統(tǒng)。或許,與機器人交互的那種自由、放松之感,正是因為在連線的另一邊并不是一個令人難以捉摸的人類。也許,這根本與人際關(guān)系無關(guān),更多的在于是取得控制成為主人,或者,是成為奴隸。
◇ 讓工具變成玩具
◇ 是伙伴不是敵人
◇ 虛擬機器人,更自由、更放松的人機交互
07 救援機器人,從模擬智慧到智能增強
霍姆斯泰德 - 邁阿密舉行的機器人大賽讓一件事情變得清晰起來,那就是,有兩個不同的方向能夠定義即將到來的人類與機器人的世界:一個邁向人機共生的世界,而另一個則在向著機器取代人類的方向發(fā)展。正如諾伯特 維納在計算機和機器人的啟蒙時期所意識到的一樣,其中一種未來對于人類來說可能將是凄涼黯淡的,而走出這條死路的方法是將人類放置在設(shè)計環(huán)節(jié)的中心,重新塑造個人計算,把它作為增強人類智慧的終極工具。
◇ 從機械獸到機械展館
◇ 仿生機器人,進入極端環(huán)境作業(yè)
◇ 安迪 魯賓,移動機器人時代的預(yù)言家
◇ 谷歌的機器人帝國計劃
◇ 巔峰之戰(zhàn):DARPA 機器人挑戰(zhàn)賽
◇ 機械手,觸摸的科學(xué)
◇ 加里 布拉德斯基,將機器視覺技術(shù)融入機械手臂之中
◇ 智能增強,以人類為中心重塑計算
08 收購Siri,蘋果正式踏入智能增強陣營
收購Siri是喬布斯在為蘋果鋪平通向未來的道路——迎接將來人機交互的另一次重要轉(zhuǎn)換。在計算機世界的一幕,喬布斯選擇落地,徑直走進了智能增強陣營:讓人類控制他們自己的計算系統(tǒng),站在了增強和合作的陣營。
◇ 收購Siri,喬布斯的一件事情
◇ 湯姆 格魯伯,從建模知識到建模策略
◇ Intraspect,流星般的人機交互系統(tǒng)
◇ Web2.0,群體智慧改變一切
◇ 亞當(dāng) 奇耶,下一個恩格爾巴特
◇ Siri核心創(chuàng)始團隊的建立
◇ 攜手蘋果,讓人類與機器優(yōu)雅地合作
結(jié)語 選擇,一切與機器無關(guān)
致謝
譯者后記
是謙遜地生存,還是傲慢地死去
2014 年春天,我把汽車停在臨近斯坦福大學(xué)高爾夫球場的一家小咖啡館前。當(dāng)我從車?yán)锍鰜頃r,一位女士正將她的特斯拉電動汽車停進我旁邊的車位。她下了汽車,把自己的高爾夫球車拿了出來,然后徑直走向球場。這時,那輛球車就跟在她身后,請注意,是車“自己”跟著她前進。我有點兒吃驚,但當(dāng)我瘋狂地在谷歌上搜索“機器人高爾夫球車”時,卻發(fā)現(xiàn)這種“小家伙”并沒有什么新奇之處。這款名叫CaddyTrek 的機器人高爾夫球車的零售價是1 795 美元,而它不過是出現(xiàn)在硅谷高爾夫球場里眾多奢侈物件中的其中一個而已。
機器人在我們的生活中無處不在。便宜的傳感器、強大的電腦和人工智能軟件能確保這些機器人變得更加自主。它們將幫助我們,也將取代我們。它們會像改變戰(zhàn)爭方式一樣,改變醫(yī)療保健和老年人護理的現(xiàn)狀。無論是在文學(xué)作品還是在影視作品中,我們早已對機器人司空見慣了。但是,我們遠(yuǎn)沒有為這一孕育之中的新世界做好準(zhǔn)備。
撰寫本書的想法要追溯到1999 —2001 年,當(dāng)時我正在進行一系列采訪,,這些采訪匯成了《睡鼠說:20 世紀(jì)60 年代的反文化如何影響個人計算機產(chǎn)業(yè)》(What the Dormouse Said: How the sixties Counterculture Shaped the Personal Computer Industry)一書。我最初的研究是“反自傳”(anti-autobiography)的一個例子。20 世紀(jì)五六十年代,我在帕洛阿爾托(Palo Alto)附近長大,這里后來變成了硅谷的核心地帶,但當(dāng)一系列計算機和通信技術(shù)組合起來,形成個人計算和現(xiàn)代互聯(lián)網(wǎng)的基礎(chǔ)時,我卻搬走了。不過,我回來得很及時,見證了“將會席卷整個世界的計算時代的興起”,它所到之處,一切都被改變了。幾年以后,在進行睡鼠項目研究的時候,我發(fā)現(xiàn)了與早期的互動計算機系統(tǒng)設(shè)計者們的工作不同的內(nèi)容。在信息時代剛剛揭開序幕的幾年里,兩位研究人員開始獨立開發(fā)未來的計算形式,他們建立的實驗室離斯坦福大學(xué)校園不算很遠(yuǎn)。
人工智能里程碑
1964 年, 曾提出“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概念的數(shù)學(xué)家、計算機科學(xué)家約翰 麥卡錫(John McCarthy)開始著手研發(fā)一系列技術(shù),試圖模擬人類能力,他原以為這個項目在10 年內(nèi)就可以完成。與此同時,在校園的另一邊,一心打算“用自己的技術(shù)讓世界變得更美好”的夢想家道格拉斯 恩格爾巴特(Douglas Engelbart)堅信,計算機可以被用來加強或擴展人類的能力,而非模仿或取代這些能力。他開始構(gòu)建系統(tǒng),使小組內(nèi)的知識分子們可以快速地提高智力,協(xié)同工作。一位研究人員開始用智能機器取代人類,而另一位則開始擴展人類的能力。當(dāng)然,他們的研究既存在聯(lián)系,又互相排斥。這里存在的悖論是,同樣的技術(shù)既
有可能延伸人類智力,也有可能取代人類。
在本書中,我探索了科學(xué)家、工程師和黑客們研究的“如何深化人與計算機間的聯(lián)系”這一問題。在一些案例中我發(fā)現(xiàn),設(shè)計師們堅持認(rèn)為人工智能和“智能增強”(intelligence augmentation,IA)之間存在互相矛盾的關(guān)系。通常,這會被歸結(jié)為簡單的經(jīng)濟學(xué)問題。現(xiàn)在,對這種性能遠(yuǎn)超50 年前早期工業(yè)機器人的新機器人的需求正在不斷上升,甚至在一些早已高度自動化的行業(yè),比如農(nóng)業(yè)中,一大批新型“農(nóng)業(yè)機器人”正在駕駛拖拉機或收割機作業(yè),從空中監(jiān)管并提高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率。
關(guān)于前面提到的悖論,研究人員還有許多深入的思考。以埃里克 霍維茨(Eric Horvitz)為例,他是微軟人工智能項目的研究人員、醫(yī)學(xué)博士,也是美國人工智能協(xié)會(AAAI)的前主席,幾十年來一直致力于研究如何拓展人類的能力。他設(shè)計出了一些精密的機器人,它們可以充當(dāng)辦公室秘書,完成諸如追蹤日程安排、招待訪客的任務(wù),并可以管理終端和排除干擾。他制造的機器人在增強人類的同時也在取代人類。
另外,生于德國的塞巴斯蒂安 特龍(Sebastian Thrun)是一位人工智能研究人員和機器人專家(同時也是在線教育公司Udacity的聯(lián)合創(chuàng)始人),他們都在打造一個將充滿自動化機器的世界。作為谷歌自動駕駛汽車項目的創(chuàng)始人,特龍主導(dǎo)了無人駕駛汽車的設(shè)計,這項設(shè)計可能會在未來的某天取代數(shù)百萬人類駕駛員——也許只有那些被拯救的生命和被避免的傷害才能證明這個項目的價值。
本書的主題是辯證地看待這些設(shè)計者的工作。他們制造出的系統(tǒng)既可以讓人類變得更強大,也有可能取代人類。安迪 魯賓(Andy Rubin)和湯姆 格魯伯(Tom Gruber)的理論就體現(xiàn)出了最清晰的對比。魯賓是谷歌機器人帝國最初的架構(gòu)師,格魯伯則是蘋果Siri智能助手的主要設(shè)計師,他們都是硅谷最、最耀眼的明星,他們的工作都建立在前人成果的基礎(chǔ)之上:魯賓模仿了約翰 麥卡錫,格魯伯則追隨了道格拉斯 恩格爾巴特——或取代人類,或讓人類變得更強大。
今天,機器人學(xué)和人工智能軟件都在不斷喚起人們對個人計算時代早期的回憶。正如業(yè)余愛好者們締造了個人計算機產(chǎn)業(yè),人工智能設(shè)計師和機器人學(xué)家對技術(shù)進步、新產(chǎn)品和它們身后的科技公司都抱有極大的熱情。與此同時,多數(shù)軟件設(shè)計師和機器人工程師在被問到自己的發(fā)明會帶來什么潛在影響時都會感到不快,只能頻繁地以幽默來轉(zhuǎn)移話題,化解尷尬,但是,問題仍然是必要的。機器人發(fā)展中可沒有“盲眼鐘表匠”(blind watchmaker)。無論是增強還是自動化,都是由一個個人類設(shè)計師作出的設(shè)計決定。
盡管結(jié)果本身很是微妙,不容易分出黑白兩面,但將一組人當(dāng)作英雄、另一組人當(dāng)成反派角色還是很輕松的。
人工智能關(guān)鍵思考
在人工智能和機器人技術(shù)之間,未來既可能是烏托邦,也可能是地獄,還有可能是介于兩者之間的某種世界。如果生活和自由的標(biāo)準(zhǔn)有機會得到提高,但是否值得以犧牲自由和隱私為代價呢?是否存在能夠設(shè)計出這種系統(tǒng)的正途或是歧路?我堅信,答案就在這些設(shè)計師身上。
一組設(shè)計師設(shè)計出強大的機器人,讓人們可以完成此前無法想象的任務(wù),比如用于空間探索的編程機器人;而另一組人則研究用機器取代人類,比如設(shè)計出人工智能軟件,讓機器人可以為醫(yī)生和律師的工作“代班”。有必要讓這兩個陣營找到互相交流的途徑。我們?nèi)绾卧O(shè)計這些日益智能的機器、如何與它們互動,將決定未來社會和經(jīng)濟的本質(zhì)。這將不斷影響現(xiàn)代世界的方方面面,從我們是否生活在一個階層更加分明(或更加模糊)的世界,到身為人類究竟意味著什么。
目前,美國正處于一場關(guān)于人工智能和機器人學(xué)的重要性以及它們對就業(yè)、生活質(zhì)量影響的嶄新討論之中。我們?nèi)缃襁M入了一個很奇怪的時代——辦公自動化已經(jīng)開始動搖白領(lǐng)們的工作,就像20 世紀(jì)50 年代工人被機器所取代時一樣殘忍。“大自動化之爭”(great automation debate)在50 年后回歸,這與《羅生門》(Rashomon)中的某些場景如出一轍:所有人都看到了相同的故事,但每個人都以利己的方式進行了不同的解讀。盡管有關(guān)計算機化造成的可怕影響的討論甚囂塵上,進入辦公室工作的美國人數(shù)量仍然在增加。對來自美國勞工統(tǒng)計局的同一份數(shù)據(jù)進行分析后,分析師們作出了兩個截然相反的預(yù)測:一個是工作的終結(jié),另一個是新興勞動力的復(fù)興。無論勞動力是正在消亡還是轉(zhuǎn)變之中,很明顯,新到來的自動化時代正在對社會產(chǎn)生深遠(yuǎn)的影響。盡管有大量的相關(guān)消息,但是否有人真正掌握了科技社會的前進方向,我們?nèi)圆坏枚?/p>
盡管很少有人見過20 世紀(jì)五六十年代那些笨重的大型機,但仍有一種流行觀點認(rèn)為,這些機器顯露出了某種不祥的、不受人類控制的跡象。隨后,在70 年代個人計算時代到來后,計算機變成了某種更為友善的存在——因為人們可以觸摸到這些計算機,便開始覺得它們處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如今,物聯(lián)網(wǎng)正在興起,計算機開始再次“消失”,這次,它們開始融入人們周遭的一切,看起來就像擁有了魔法一樣——現(xiàn)在,家里的煙霧探測器開始講話,而且可以聽得懂指令。我們的手機、音樂播放器和平板電腦都比幾十年以前的超級計算機擁有更強的計算能力。
隨著“無處不在的計算”時代的到來,我們已經(jīng)進入一個嶄新的智能機器時代。在未來幾年內(nèi),人工智能和機器人給世界帶來的影響將遠(yuǎn)遠(yuǎn)超過個人計算和互聯(lián)網(wǎng)在過去30 年間已經(jīng)對世界造成的改變。汽車可以無人駕駛,機器人可以完成快遞員的工作,當(dāng)然,還有醫(yī)生和律師的。新時代為偉大的物理和計算力量帶來了希望,但它也使半個多世紀(jì)前曾被提出的問題得以重構(gòu):我們還能控制這些系統(tǒng)嗎,或者,它們會控制我們嗎?
喬治 奧威爾(George Orwell)對這個問題進行了充分論證。在《1984》一書中,奧威爾描繪了一個監(jiān)視無處不在的國家,但他也寫到,這種國家控制通過縮減人類的口語和書面語、增加表達的難度,進而約束社會對不同思想的接納。他虛構(gòu)出一種名為“新語”(Newspeak)的語言,這種語言可以有效地限制思想和自我表現(xiàn)。
看看互聯(lián)網(wǎng)為我們提供的數(shù)以百萬計的頻道,乍看之下,今天的我們或許離奧威爾描述的噩夢還有十萬八千里,但越來越多的案例表明,智能機器正在為我們作出決策。如果這些系統(tǒng)只是提供建議,我們很難將其稱為奧威爾提到的“控制”,但是,大數(shù)據(jù)的世界已經(jīng)使互聯(lián)網(wǎng)變得與10 年前大相徑庭。
互聯(lián)網(wǎng)延伸了計算所及之處,并改變了我們的文化。新的“奧威爾社會”呈現(xiàn)出一種更為柔性的控制。互聯(lián)網(wǎng)提供了一些過去無法匹敵的新型自由,與此同時,也矛盾地讓控制和監(jiān)管得以延伸,這已遠(yuǎn)遠(yuǎn)超出了奧威爾最初理解的范疇。每一個足跡、每一句話語都被記錄并被收集,完成這一工作的不是“老大哥”,就是一些正在成長的“小大哥”。互聯(lián)網(wǎng)已經(jīng)成為一項與文化的方方面面有密切接觸的技術(shù)。今天,智能手機、筆記本電腦和臺式機能聽懂我們說話,
完成我們發(fā)出的指令,攝像機或許也能通過它們的屏幕友好地凝視我們。即將來到的物聯(lián)網(wǎng)時代正在將不顯眼的、永遠(yuǎn)在線的、(可能)樂于助人的桌面機器人帶入千家萬戶,就像亞馬遜的語音助理Echo 和辛西婭 布雷齊爾(Cynthia Braezeal)的Jibo。
世界會像20 世紀(jì)60 年代的詩人理查德 布勞提根(Richard Brautigan)所描述的“慈愛機器”(machines of loving grace)一樣成為“一個自由的世界”(a free world)嗎?這里的“free”指的是“言論自由”(freedom of speech)還是“免費啤酒”(free beer)呢?在一個充滿智能機器的世界里,回答這些問題的好方法就是理解那些正在創(chuàng)造這些系統(tǒng)的人們的價值觀。
在硅谷,樂觀的技術(shù)專家很樂意相信“創(chuàng)新”和“摩爾定律”這對雙生力量足以說明所有科技進步的原因。很少有人能解釋為什么某一項技術(shù)打敗了其他技術(shù)、為什么某一項技術(shù)會崛起。這一觀點是社會科學(xué)家提到的“技術(shù)的社會建構(gòu)”(social construction of technology)——他們認(rèn)為是我們創(chuàng)造了這些工具,而非相反。
我們已經(jīng)有了數(shù)百年使用機器取代體力勞動的經(jīng)驗,但是,取代白領(lǐng)工人和腦力勞動者的智能機器還是新現(xiàn)象。比起僅僅取代人類,信息技術(shù)還正在使某些體驗民主化,這不僅是因為使用個人計算機讓我們不再需要雇用秘書。例如,互聯(lián)網(wǎng)和網(wǎng)絡(luò)已經(jīng)極大地削減了新聞業(yè)的成本,不僅顛覆了新聞產(chǎn)業(yè),還在根本上轉(zhuǎn)變了收集、報道新聞的流程。類似的技術(shù)還有音高修正技術(shù),它已經(jīng)可以讓沒有受過訓(xùn)練的人唱出美妙的歌曲,同時,一大批計算機化的音樂系統(tǒng)讓所有人都能成為作曲家和音樂家。在未來,這些系統(tǒng)將被如何設(shè)計,預(yù)示著要到來的是一場偉大的復(fù)興還是更加深邃的黑暗——在人們?nèi)缃裆畹氖澜缋铮祟愃械募寄芏家ㄟ^機器來傳承。麥卡錫和恩格爾巴特的研究定義了一個新時代,在那里,數(shù)字計算機將像工業(yè)革命一樣深刻地改變經(jīng)濟和社會。
最近,一些實驗為我們在理解機器對未來工作產(chǎn)生的影響方面提供了值得深思的事例(這些實驗在世界上最貧困的地區(qū)進行,保障了當(dāng)?shù)鼐用竦幕臼杖?。這些實驗的結(jié)果令人震驚,因為它們與“經(jīng)濟安全削弱了人們的工作意愿”這一主流觀點相左。2013 年,在印度一個貧困村莊進行的一項實驗保障了當(dāng)?shù)鼐用竦幕拘枨螅瑓s得到了相反的效果。這些貧困的人們并沒有安于自己得到的政府補貼,相反,他們變得更加負(fù)責(zé)、更有生產(chǎn)力。日后,我們很有可能有機會在及時世界進行一次類似的實驗。基本收入的理念已經(jīng)成為歐洲國家必談的政治議題。1969 年,尼克松政府首先以“負(fù)所得稅”的形式提出這一概念,目前,它尚未被美國政壇接受,但如果技術(shù)性實驗變得日益普遍,這種局面將會發(fā)生改變。
如果未來的產(chǎn)業(yè)不再需要勞動力,將會發(fā)生什么呢?如果倉庫管理員、廢品收集員、醫(yī)生、律師和記者都被技術(shù)取代,又會發(fā)生什么呢?當(dāng)然,我們無法預(yù)知這樣的未來,但是我猜想,社會也許會在未來發(fā)現(xiàn)人類并非生來就需要工作,或是會發(fā)現(xiàn)能創(chuàng)造價值的類似方式。新型經(jīng)濟將創(chuàng)造我們今天無法理解的工作崗位。科幻小說作家當(dāng)然已經(jīng)預(yù)見了這種未來。讀讀約翰 巴爾內(nèi)斯(John Barnes)的《風(fēng)暴之母》(Mother of Storms)或者查理 斯特羅斯(Charlie Stross)的《漸快》(Accelerando),都是了解未來經(jīng)濟可能模式的不錯選擇。
一個簡單的答案是,人類的創(chuàng)造力是無限的,如果我們的基本需求被機器人和人工智能滿足,那么我們將找出娛樂、教育和照料他人的新方式。這些答案或許很籠統(tǒng),但這些問題正變得日益尖銳,即智能機器是會像盟友一樣與我們互動、照料我們,還是會奴役我們?
在本書中,我將介紹不同的計算機科學(xué)家、黑客、機器人專家和神經(jīng)科學(xué)家。他們都擁有相同的感覺,認(rèn)為我們正在靠近一個感染點,在那里,人類將生活在機器的世界中,這些機器可以模仿人,某些能力甚至?xí)饺恕K麄儗θ祟愒谶@個新世界中的地位有著各種各樣的感受。
21 世紀(jì)前50 年內(nèi),社會將作出艱難的決策,允許這些智能機器擁有成為我們的仆人、伙伴或主人的潛力。在20 世紀(jì)中葉計算機時代的開端,諾伯特 維納曾對自動化的一種可能性提出警示:“我們可以謙遜地在機器的幫助下過上好日子,也可以傲慢地死去。”
現(xiàn)在看來,這不失為一次中肯的警告。
50多年來,人工智能既經(jīng)歷了初期的爆發(fā)式增長,又遭遇過發(fā)展的“寒冬”,而今終于迸發(fā)出了野蠻生長的態(tài)勢。在軟件技術(shù)獲得極大發(fā)展的今天,所有人都將無法避開以下問題:人工智能究竟是天使,還是魔鬼?奇點來臨時,人類將何去何從?《人工智能簡史》一書的作者馬爾科夫?qū)睋暨@些核心問題的本質(zhì),并為我們指明方向。
楊強
中國人工智能學(xué)會副理事長,國際人工智能大會(IJCAI)常務(wù)理事,
騰訊微信事業(yè)群技術(shù)顧問,香港科技大學(xué)教授
在大數(shù)據(jù)時代,移動互聯(lián)網(wǎng)催生了不計其數(shù)的數(shù)據(jù)量;而在機器人時代,萬物互聯(lián)也將使數(shù)據(jù)呈現(xiàn)暴增之勢。隨著數(shù)據(jù)的增長,機器智能的計算能力、深度學(xué)習(xí)能力、人機交互能力實現(xiàn)了大幅度的提升,而它們也正在一步步取代重復(fù)性、低增值信息的人類勞動,這樣看來,各個領(lǐng)域的產(chǎn)業(yè)躍遷將無法避免。那么終,機器人會成為我們的主人,還是伙伴?這一終極選擇的答案就在《人工智能簡史》一書中。
余凱
中國人工智能學(xué)會副秘書長,地平線機器人科技創(chuàng)始人
這是迄今為止完整、可讀性的人工智能史著作。穿越AI(人工智能)和IA(智能增強)半個世紀(jì)恩怨的迷霧,一座座巨星的雕塑參差對立,歷史縱深感和人文主義情懷躍出紙面。
吳甘沙
馭勢科技(北京)有限公司聯(lián)合創(chuàng)始人兼CEO
未來的機器人將會成為我們的伙伴還是弗蘭肯斯坦的怪物?想知道答案,就要閱讀這本書。正如馬爾科夫在他引人入勝的敘述中闡釋的那樣,答案取決于我們自身。
沃爾特 艾薩克森
《史蒂夫 喬布斯傳》作者
我們應(yīng)該如何平衡“機器能為我們做些什么”和“機器能在幫助我們做自己上做些什么”這兩大問題?毫無疑問,馬爾科夫給出了這一技術(shù)時代核心問題的答案。
托尼 法德爾
Nest聯(lián)合創(chuàng)始人,iPod之父
我將這本書視作一部驚悚的間諜片,是因為人類的命運正在其中上演,而且馬爾科夫的描述也是如此迷人。
奧倫 埃奇奧尼
美國艾倫人工智能研究所CE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