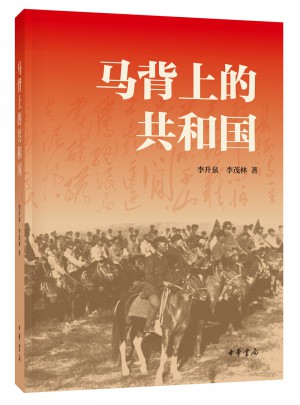
馬背上的共和國
- 所屬分類:圖書 >歷史>中國史>現代史(1919-1949)
- 作者:[李升泉],[李茂林] 著
- 產品參數:
- 叢書名:--
- 國際刊號:9787101121742
- 出版社:中華書局出版社
- 出版時間:2016-10
- 印刷時間:2016-10-01
- 版次:1
- 開本:16開
- 頁數:356
- 紙張:輕型紙
- 包裝:平裝-膠訂
- 套裝: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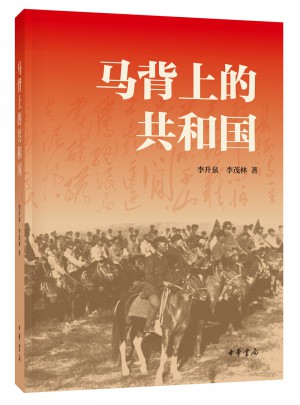
那是一個戰火紛飛的年代,又是由苦難走向輝煌的年代。紅軍將士以奮斗、艱辛,以致生命,創造了那段值得后人永遠銘記的歷史。全書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歷史為背景,以文學筆觸,生動細節,展現了中國工農紅軍扣人心弦且、波瀾壯闊的長征歷程。作者歷時三年、行程萬里,沿著當年紅軍的足跡進行了尋訪,又參閱大量回憶文章、地方史志,以及各類研究著作,寫出這部兼具紀實性與文學性的作品。作品既忠實于歷史,又善于構造情節,同時敢于直面長征中的矛盾和斗爭,不僅尊重歷史細節,更有仰觀俯察的公正評價。
紀實性與文學性兼具,忠實于歷史又善于構造情節。用文學筆觸、生動細節,描述工農紅軍扣人心弦、波瀾壯闊的長征歷程。
直面長征中中共和紅軍內部的矛盾和斗爭。對一、四方面軍分裂、西路軍遠征河西等,書中都有詳細描述。不僅尊重歷史細節,更有仰觀俯察的公正評價。
作者歷時三年、行程萬里,沿著紅軍長征的足跡進行了尋訪。正本清源,激濁揚清,揭示歷史真貌。
李升泉,1956年生于四川開江縣。1976年入伍,1982年畢業于北京大學。少將軍銜。現任國防大學政治部主任。中學時代開始創作,已出版著作《蕭索時代的激情壯懷》《那場悲壯已經過去》《年輕的激情》《思考的快樂》《思想的言說》等,在各類報刊發表詩歌、散文等文學作品百余萬字。
李茂林,1946年生于陜北子長縣,其父為陜北老紅軍戰士。1963年入伍,1970年代開始寫作,后為蘭州軍區政治部創作員。主要從事影視創作,電影作品有《路漫漫》《祁連山的回聲》,電視作品有《三軍大會師》《長征,生命的歌》等。
序............ 劉亞洲 001
引 言................ 001
及時章 莫斯科回來的年輕人,走上中共政治舞臺 005
第二章 風風雨雨中,誕生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 016
第三章 兩個日耳曼人,在中國導演同一場戰爭 032
第四章 第五次反“圍剿”失敗,除了走已別無選擇 042
第五章 長征艱難出發,馬背載走了一個共和國 058
第六章 三道封鎖線順利通過,紅軍領袖陷入困惑 071
第七章 紅軍浴血戰湘江,損兵過半破天塹 080
第八章 危境中力主紅軍改道,歷史也在改道 091
第九章 遵義會議揭開新頁,紅軍命運由此轉折 106
第十章 紅軍四渡赤水,偉人的智慧寫進碧水清波 120
第十一章 共和國本土陷落,血火中有無盡悲歌 142
第十二章 進軍滇東難以立足,渡金沙江再尋出路 152
第十三章 危難中彝海結盟,佳話背后也有隱情 164
第十四章 搶渡大渡河,石開達的命運不屬于紅軍 174
第十五章 一、四方面軍會師,大雪山下不再寧靜 184
第十六章 松潘久攻不克,尋求生存時也有人尋求權力 199
第十七章 北上道路現出曙光,右路紅軍走出草地 208
第十八章 1935年9月9日,度過最黑暗的24小時 225
第十九章 紅軍打下臘子口,萬里征途終于柳暗花明 247
第二十章 中央紅軍到達吳起鎮,結束二萬五千里長征 259
第二十一章 陜北肅反蘇區陷入險境,北上中央挽救危局 270
第二十二章 自立“中央”,南下藍圖轉眼成為泡影 282
第二十三章 紅二、六軍團,艱苦危難中踏上漫漫征程 294
第二十四章 久困康藏,不得已同二方面軍北上 308
第二十五章 踏進甘南又起紛爭,大會師只是一場象征 320
第二十六章 國共兩黨再度合作,結束了馬背上的共和國 333
紅軍長征大事記........ 346
后 記 351
9月9日,似乎是個不祥的日子,秋收起義失敗,同的分裂或者叫作巴西脫險,還有的逝世,都在這24小時。
9日一早,的回電到了:
……
電報上所說各條,都是當時的實際情況,從眼前的形勢和戰術上考慮,南下也是能說服人的。看了電報,沉思了一會,對說:“我看張主席的分析是對的,目前的敵我形勢,還是南下為好。”
在此之前是一直支持中央北上方針的,這時突然態度變了。這既有電報的作用,也有情知左路軍不會來,不愿脫離四方面軍大隊的考慮。長期任四方面軍的總指揮,當然不想讓四方面軍分開,便也表示同意南下。
立即帶上電報,去向中央匯報。
不一會兒,回來了,情緒很不好,說是受到了中央的批評。
坐著生了一會兒悶氣,突然想起今天要去三十軍開會,便同一起去三十軍。
三十軍前幾天請總政治部的宣傳隊去演出,定于這天去,宣傳部長劉志堅正在集合人員。總政治部副主任楊尚昆的妻子李伯釗是紅軍中聞名的文藝工作者,她跳的蘇聯水兵舞很受歡迎。在一、四方面軍會師晚會上,李伯釗被臺下一次又一次的“再來一個!”“再來一個!”的喊聲弄得簡直下不來臺。這時她也要隨宣傳隊去三十軍。楊尚昆知道,說過再等兩天,不來我們就走。也許,李伯釗這一去,他們夫妻就要一南一北地分開了。當時戰事頻繁,形勢變化不定,分開之后,能否再相見是誰也無法預料的。但楊尚昆更不能讓李伯釗不去三十軍,因為這樣會引起別人的懷疑,那將會影響大事。
楊尚昆站在門口,只好看著李伯釗他們在劉志堅的帶領下,高高興興地走了。
中央這邊,在走后,立即又給發報。事已至此,中央的電報態度明確,也比較強硬:“陳談右路軍南下電令,中央認為是不適宜的。中央現懇切指出,目前方針,只有向北才是出路,向南則敵情、地形、居民、給養,都對我極端不利,將要使紅軍陷于空前未有之環境。中央認為:北上方針不應改變,左路軍應速即北上,在東出不利時,可以西渡黃河占領甘、青交通新地區,再行向東發展。”
中央的電報堅持了北上方針,但是在向東還是向西的問題上作了讓步。原來要求向洮河西部北上,中央不同意,現在干脆要南下,只好退而求其次:只要北上,西出也行!
電報發出以后,心里仍非常焦慮,他在思考著會對中央的這份電報作何反映,以及下一步該怎么辦?
這天下午,正在一邊想事,一邊踱步。突然一陣“噔噔噔”的腳步聲上了小樓。這些日子,焦思苦慮,神情疲憊,眼眶布滿紅絲,頭發也顯得越來越長了。
上了小樓,向他點了下頭,算是招呼,仍沒停止踱步。
平江起義后,到了中央蘇區,后來以平江起義部隊為基干,發展為紅三軍團,成為中共蘇區的主力部隊之一。
從五次反“圍剿”直到長征以來,三軍團打得很苦,部隊減員也大。會理會議上受到過的批評。一、四方面軍會師后,曾請吃飯,派他的秘書黃超送給三百塊大洋及糧食、牛肉,還說要撥部隊給他。后來被頂了回去。
在樓門口站住,叫住沒停步的,說:“情況好像有點不對。”
“你聽到什么啦?”的思考中斷了,他對的話重視起來,又指指一條粗糙的木凳,請坐下。
“我上午到前總去,的態度也變了,給我說川康如何好、如何好,看樣子他要南下。”
上午送電報來時,已表示同意南下。態度的改變,已經知道了。
“怎么說?”問。
“心事重重的樣子,沒做聲。”
“看來是要跟走的。”像是自言自語地說。
擔心地問:“中央同前總住在一起,他們要裹脅中央南下怎么辦?”
“還不至于這樣吧。”沉思著說。
“他們人多,為了預防萬一,我們是不是扣他們幾個人?”
臉一沉,立刻說:“不可!斷乎不可!”
“我是想萬一中央被……”
打斷說:“不管南下還是北上,我們還都是紅軍嘛。現在分開,以后還會走到一起,斷斷不可把事情弄到敵對程度。”
不再做聲。正在這時,一陣急促的腳步聲響上樓來,和不約而同地將目光朝向門口。
氣喘吁吁地大步跨進門,叫了一聲:“主席。”
迎上去:“劍英,有事?”
拿出一份電報交給,說:“主席你看這個,是剛剛收到的。”
原來就在剛才,前敵指揮部收到一份的電報。、到三十軍去了沒有回來,是參謀長,機要參謀找不到徐、陳,便把電報給了。一看內容,吃了一驚,趁、不在,便直接送這里來了。
近年來,關于的這封電報說法較多。先是到底有沒有這樣一封電報?在他的《我的回憶》一書里矢口否認;李德在他的《中國紀事》里也說他沒有看到這封電報,并說他后來曾同博古談起這件事,博古對李德說他也沒見過電報;的回憶錄《歷史的回顧》中也沒提到有這樣一封電報。是主要當事人,平心而論他的回憶中情緒化的立論十分明顯,不足為據;李德的書是20世紀70年代初反華特別是反的產物,況且博古早已作古,是否給李德說過沒見到電報的話,實在難以佐證,不足為信史;至于的回憶《歷史的回顧》中確實沒提電報的事。
、聶榮臻、楊尚昆等都提到電報的事。筆者查閱資料發現,“密電”問題最早是1937年2月27日凱豐在《黨中央與國燾路線分歧在哪里》的文章里提到的。但沒有說明內容,原話是:“當中央發覺國燾私自給徐、陳南下密電時,曾經詳述南下的不利,并勸其仍率隊北上。”1937年2月離分裂事件發生不久,況當時已在延安,當為可信。但從這句話的意思看,似乎密電僅僅是要徐、陳南下,沒有提到有企圖危害中央的內容。
更主要的是找不到這份電報原文,所以眾說紛紜。
密電問題至今仍是中共黨史上一個待解的迷。
電報的內容究竟是什么?因沒有原電,無從查證。對這份電報回憶較全的是呂黎平。呂當時是前總作戰科副科長,他回憶說,當時他看過電報內容,電文是:“×日電悉。余經長期考慮,目前北進時機不成熟,在川康邊境建立根據地最為適宜,俟革命高潮時再向東北方向發展,望勸毛、周、張放棄毛兒蓋方案,同右路軍回頭南下。如果他們不聽勸告,應監視其行動,若堅持北進,則應開展黨內斗爭,徹底解決之。”很顯然,這段內容有很大的回憶成分。歷來引用的內容都是“徹底開展黨內斗爭”這一句。可以斷定,不管具體內容是什么,這一句是電報中最足以證明企圖武力危害中央的內容。但這句話既可以理解為武力危害中央,也可以理解為從組織上改組中央。1937年3月31日中央政治局作出的《關于同志錯誤的決定》中也只是說:“他甚至走到以軍隊來威逼中央,依靠軍隊的力量,要求改組中央。”但不管是哪種企圖,中央面臨危險,這是當時的實際情況。
……
紅大的學員正行走在一座小山坡上,幾騎馬奔跑過來。李特遠遠地喊:“停止前進!停止前進!”當時除軍以上的干部外,其他人都不知道中央同的爭論和斗爭。紅大的學員還都認為是去打糧,這時見李特教育長(李當時兼任紅大教育長)追來不讓前進,還不知是怎么回事。
李特等跑近了,騎在馬上對隊伍喊:“四方面軍的同志不要走了!、他們北上逃跑,投降帝國主義!”
紅軍的軍事顧問李德也在隊伍里。遵義會議后,他被剝奪了軍事指揮權,閑來無事,便整天同博古玩撲克打發日子。紅大成立后,他當了一名教官,偶爾給紅大學生講講軍事課。中央同的爭論他是知道的,他不想介入爭論中去,但他同意北上,因為他被剝奪權力后急于北上以便與王明和共產國際取得聯系。遵義會議后的這段時間,中央的情況使他感到已成為中國黨的無可爭議的領袖。
他這時已能聽懂簡單的中國話,見李特大聲地叫喊“”“”什么,從李特的表情和口氣里,他知道李特在罵和。一種日耳曼民族對領袖和的本能的服從與崇拜,使他十分氣憤。他個子高大,走上去一把將李特從馬上拉了下來。
李特一見這個丟了中央蘇區的德國佬把他拉下馬來,十分惱怒,對著李德破口大罵。李德不會說中國話,便用俄國話罵李特。罵了一陣,李特才感到不對,李德聽不懂他的中國話,而他能聽懂俄國話,于是便也用俄語對罵。
吵嚷聲驚動了離此不遠的。拄著一根拐棍向這邊走來,全副武裝的警衛員緊隨其后,等也緊緊跟著。
走近紅大隊伍時,對著混亂的人群大聲說:“四方面軍的同志們,你們愿北上的跟著走,愿回去可以回去嘛。不過,我相信你們將來還會回來的。”
見來了,李德和李特停止了爭吵,李特對說:“總司令沒有命令,你們為什么走啊?”
探頭看了看,見是李特,便說:“是李參謀長啊,這次北上,是政治局決定的。”
李特還要講話,但個子低,在人叢中看不見,十分急躁。李德以為他會對動武,便一把將李特抱住。李德力大如牛,李特動彈不得,急得直喘粗氣,一點辦法也沒有。
又說:“北上的方針是正確的,希望四方面軍的同志認清形勢,跟中央北上。如果一時想不通也沒關系,我們先走一步,你們什么時候想通了再北進,中央也歡迎。”
的話,語氣平和,入情入理。正準備向回走的四方面軍的學員都認真地聽著。李特也安靜下來,李德這才放開了他。
又說:“南下川康即使眼前可行,但沒有出路,我相信你們至多一年,也會北上的!”他又對李特說:“李參謀長,請你帶個話給國燾和昌浩同志,望以革命大局為重,我們先走了,有何意見,可隨時電商。”
說完,轉身朝一方面軍大隊走去。一邊走,一邊回頭向四方面軍的學員揮手,用濃重的湖南腔喊著:“同志們,再見!”
10日晚,中央行至拉界宿營。到了宿營地,疲倦地仰倒在椅子上,長長地出了一口氣,對、博古等說道:“秋收起義以來,我們經過的困難也不算少,可昨天是我一生中最黑暗的24小時。”
終于度過了他一生中最黑暗的24小時,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和政府機關隨同一小部分紅軍,在的率領下通過了不久前紅三十軍和紅四軍同志用鮮血和生命開辟的北上通道。他們,是不是也度過了命運中最黑暗的階段?
同樣寫長征,不同人的筆下會呈現不同品質。而我更看重的,就是這部書的品質:紀實性與文學性兼具,忠實于歷史又善于構造情節,栩栩如生,大開大闔,扣人心弦,展卷開讀令人無法釋手。著作還有一個特點,敢于直面問題,敢于揭露長征中黨和軍隊內部的矛盾和斗爭。……關于一、四方面軍分裂、關于西路軍遠征河西,等等,這部書都有詳細描述,不僅僅是尊重歷史細節,而且更有仰觀俯察的公正評價。
——國防大學政委 劉亞洲上將
用文學的筆觸,描述那段扣人心弦且波瀾壯闊的奮斗歷史;用生動的故事,給后人展現那些跋涉萬水千山的艱辛足跡。
——國防大學教授 金一南少將
欲滅其國,先去其史。對近年來虛無歷史的潮流,斷不能“極高的輕蔑是無言”,唯有堂堂正正,還原歷史真貌,方能撥云見日,以正視聽。這就是我向廣大讀者特別是青少年一代,鄭重推薦此書的理由和原因。
——國防大學教授 喬良少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