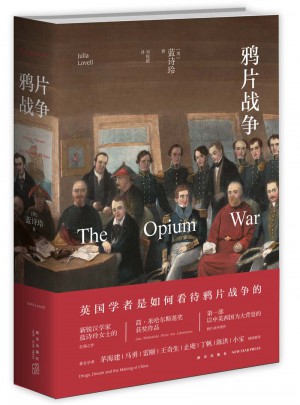
鴉片戰(zhàn)爭
- 所屬分類:圖書 >歷史>中國史>近代史(1840-1919)
- 作者:(英)[藍(lán)詩玲] 著 [劉悅斌] 譯
- 產(chǎn)品參數(shù):
- 叢書名:--
- 國際刊號:9787513318020
-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 出版時(shí)間:2015-07
- 印刷時(shí)間:2015-07-01
- 版次:1
- 開本:16開
- 頁數(shù):--
- 紙張:膠版紙
- 包裝:精裝
- 套裝: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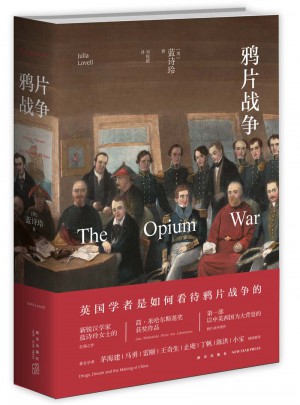
鴉片戰(zhàn)爭是中英兩國所該共同面對的話題,而英國新銳漢學(xué)家藍(lán)詩玲女士的這本新著正是站在一個(gè)更加廣闊的視域來對此加以考察,旨在讓我們跨出地域的限制,認(rèn)真反思這場世界沖突的種種罪惡和矛盾。藍(lán)詩玲充分吸收了現(xiàn)有的相關(guān)研究成果(比如茅海建的《天朝的崩潰:鴉片戰(zhàn)爭再研究》),又能在中英文原始史料中找尋更多動人的歷史細(xì)節(jié)。得力于她深厚的文學(xué)造詣 ,像林則徐、琦善、義律這樣的歷史人物經(jīng)她描寫,仿佛便可浮現(xiàn)于眼前。除了戰(zhàn)爭過程中的細(xì)節(jié)敘述之外,藍(lán)詩玲還往后記述了中英兩國人民對此戰(zhàn)爭的復(fù)雜的歷史記憶,尤其在中國近代國族構(gòu)建中扮演的角色。
英國學(xué)者是如何看待鴉片戰(zhàn)爭的
新銳漢學(xué)家藍(lán)詩玲女士的扛鼎之作
一位當(dāng)代英國學(xué)者眼中的中西誤解與沖突
謹(jǐn)以此書紀(jì)念鴉片戰(zhàn)爭175周年
簡 米哈爾斯基獎(jiǎng)獲獎(jiǎng)作品
奧威爾獎(jiǎng)入圍作品
同時(shí)以中英兩國為大背景的鴉片戰(zhàn)爭著作
著名學(xué)者茅海建、馬勇、雷頤、王奇生、止庵、陳洪、丁帆、小寶傾情推薦
知名媒體《時(shí)代》《紐約時(shí)報(bào)》《衛(wèi)報(bào)》《獨(dú)立評論》《紐約書評》等競相報(bào)道
藍(lán)詩玲(Julia Lovell),現(xiàn)為英國倫敦大學(xué)伯貝克學(xué)院講師,教授中國近代史、中國文學(xué);已出版數(shù)種與中國近代歷史相關(guān)的著作,且以英文翻譯了魯迅、張愛玲、朱文、韓少功、閻連科等中國作家的部分作品;現(xiàn)在正致力于研究思想的全球史,并重譯《西游記》(節(jié)譯本)。
譯者:劉悅斌,中國近代史研究專家、教授;在各類專業(yè)期刊60余篇,出版專著數(shù)種,并翻譯出版《朋友客人同事——晚清的幕府制度》(合譯)、《尋求中國民主》(合譯)等著作。
中文版序
緒論
(一) 鴉片和中國
(二)道光皇帝的決定
(三)廣州之春
(四)鴉片和石灰
(五)最初的沖突
(六)“解釋性宣戰(zhàn)”
(七)甜言蜜語和海參
(八)琦善的倒臺
(九)廣州之圍
(十)去英國化了的英國人
(十一)廈門和舟山
(十二)在蘇州的一個(gè)冬天
(十三)為清朝中國而戰(zhàn)
(十四)南京條約
(十五)和平與戰(zhàn)爭
(十六)黃禍
(十七)民族病
(十八)20世紀(jì)中國歷史中的鴉片戰(zhàn)爭
主要人物
近代中國歷史和鴉片戰(zhàn)爭大事年表
參考書目
致謝
索引
本書中文版自序:
中國讀者可能會好奇為什么一個(gè)英國作者寫了一本關(guān)于鴉片戰(zhàn)爭的新書,因?yàn)橹袊鴮W(xué)者和西方學(xué)者已經(jīng)就這一悲劇性事件撰寫了很多、詳盡的著作。我在撰寫本書時(shí),的確受到了這些學(xué)者們非常大的幫助和啟發(fā),特別是茅海建引人入勝、發(fā)人深省的著作《天朝的崩潰》,該書廣泛利用了中、英文檔案資料。英文學(xué)術(shù)著作方面,我極大地受益于波拉切克的《鴉片戰(zhàn)爭與清廷之內(nèi)部斗爭》和魏斐德的《大門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間華南的社會動亂》。
但是,我之所以決定寫這本書,是基于中國普通民眾和英國普通民眾之間對這場戰(zhàn)爭理解上的巨大分歧,我想要提醒健忘的英國讀者我們國家過去曾經(jīng)從事過鴉片貿(mào)易。
今天,大多數(shù)英國人對自己國家過去的殖民行徑感到非常尷尬,有太多令人震驚的帝國擴(kuò)張活動令我們感到羞恥:奴隸貿(mào)易;用馬克沁機(jī)槍對手無寸鐵的土著居民進(jìn)行的無數(shù)次大屠殺;長達(dá)幾個(gè)世紀(jì)時(shí)間里制度化的種族主義。但是,與其他那些殖民罪行相比,英國帝國主義有一件不可告人的丑事易于被視而不見,這就是鴉片——一種令人十分容易上癮的,它在整個(gè)18世紀(jì)和19世紀(jì)給英帝國提供了滾滾財(cái)源。
19世紀(jì),維多利亞時(shí)代的英國擴(kuò)張得如此之大,形成了一個(gè)大帝國,這使得它很是自豪,認(rèn)為基督教世界比被其征服的民族具有優(yōu)越性。不過,這個(gè)帝國,這個(gè)使英國成為富庶的世界強(qiáng)國的帝國,它的一大半建立在從賺取的金錢上,即英國從在印度的鴉片專賣中賺取的利潤。18世紀(jì)后期英國得到孟加拉后,迅速在那里建立起鴉片制造壟斷制度,強(qiáng)迫當(dāng)?shù)赜《绒r(nóng)民簽訂種植罌粟的合同。到收獲季節(jié),鴉片汁原液在英國開辦的工廠里加工成產(chǎn)品,裝進(jìn)芒果木箱子,然后以極高的利潤賣給中國。
英國不光是從事鴉片貿(mào)易賺取利潤,還為鴉片發(fā)動戰(zhàn)爭。由于中國政府拒絕使鴉片走私貿(mào)易合法化,英國于1839—1842年間和1856—1860年間發(fā)動了針對中國政府的軍事遠(yuǎn)征(在在這過程中,英國攫取了現(xiàn)今香港版圖的大部分),卻聲稱它的主要目的是打開中國自由貿(mào)易的大門。英國在亞洲從事鴉片貿(mào)易及為之發(fā)動戰(zhàn)爭的歷史,是明顯的機(jī)會主義和偽善,因?yàn)樗恼汀⑸倘撕蛙娙硕茧[瞞了他們是在文明和進(jìn)步的幌子下為保護(hù)非法的貿(mào)易而戰(zhàn)的事實(shí)。
從很多方面來說,鴉片對英帝國都很重要。在華南,鴉片換成白銀,白銀為英國公眾購回茶葉,因而,鴉片扭轉(zhuǎn)了英國在亞洲的貿(mào)易逆差,為英國的茶葉嗜好提供了資金;相應(yīng)地,茶葉交易的稅收,又解決了皇家海軍的很多費(fèi)用。1850年代以后,向中國出售鴉片的收入,實(shí)際上負(fù)擔(dān)了英國統(tǒng)治印度時(shí)期的大部分費(fèi)用,并為英國在印度洋沿岸的貿(mào)易提供了白銀。19世紀(jì),嚴(yán)格管理的鴉片生產(chǎn)還為新加坡提供了大部分的政府財(cái)政收入。
不過,在我看來,英國一直竭盡全力忘記它與中國打了兩次鴉片戰(zhàn)爭的事實(shí),在英國中學(xué)和大學(xué)的歷史課上碰不到鴉片戰(zhàn)爭的內(nèi)容是十分可能的。英國對于這兩次戰(zhàn)爭的健忘癥早就開始了。還在1900年前后,一些英國歷史教科書在談到香港和英帝國在東方的管轄范圍時(shí),就不再提及時(shí)次鴉片戰(zhàn)爭,而是委婉地寫道,他們在1842年“得到了”那個(gè)島。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隨著香港成為自由的全球金融中心,它的殖民地的歷史逐漸被抹去了。1841年英國靠炮艦建立香港的歷史,在1991年150周年時(shí)悄無聲息地就過去了。1997年香港移交時(shí)英國高官的告別演說,也對鴉片和為鴉片打的那兩場戰(zhàn)爭避而不談,只字不提。
英國從事貿(mào)易的那些歷史痕跡在倫敦也被有意忽視了。在整個(gè)19世紀(jì)和20世紀(jì)的大部分時(shí)間里,倫敦東部那些巨大的碼頭上卸載了英帝國各地運(yùn)來的奇珍異寶:香料、靛藍(lán)、絲、波斯地毯、煙草、咖啡。東印度公司碼頭(The East India Docks)——倫敦卸載中國茶葉的碼頭——是印度、中國和大不列顛最為重要的牟利貿(mào)易三角(由茶、鴉片、絲構(gòu)成)匯聚點(diǎn)之一。然而,在今天,原東印度公司碼頭在其19世紀(jì)如日中天的時(shí)候,任何一個(gè)時(shí)間點(diǎn)上都有上百艘商船匯集在這些碼頭,很多船上裝滿用印度鴉片換來的中國茶葉,如今已經(jīng)荒廢破敗,靜靜地橫臥在那里,或被成群的野鳥占領(lǐng),或被重新改造為漂亮的玻璃和鋼鐵建筑的公寓式街區(qū)。
但是,這是一段對全球政治依然能產(chǎn)生強(qiáng)烈共鳴的歷史。如果英國——不論是故意地還是只因?yàn)樘珣?mdash;—已經(jīng)忘記其鴉片貿(mào)易的歷史,那么,在大陸中國,對鴉片貿(mào)易和鴉片戰(zhàn)爭的記憶卻大不相同。在中國,小學(xué)生可以從課本、博物館、紀(jì)念儀式和電影中了解到,鴉片戰(zhàn)爭標(biāo)志著近代中國愛國主義的開端,它被看作是西方用和武力毀滅中國的開始,開啟了恃強(qiáng)凌弱的西方凌辱中國的災(zāi)難世紀(jì),也開啟了中國為成為現(xiàn)代強(qiáng)國而奮斗的世紀(jì)。要理解今天中國與西方麻煩不斷的關(guān)系——這是當(dāng)今地緣政治中最為重要的外交關(guān)系之一——西方讀者就必須要明白中國是怎樣記憶鴉片戰(zhàn)爭的,要明白英國在雙方?jīng)_突中的作用。
不過,在利用中、英文原始資料和二手資料研究鴉片戰(zhàn)爭的過程中,我也發(fā)現(xiàn)這段歷史中有讓我吃驚的細(xì)節(jié),這些細(xì)節(jié)與我所熟悉的歷史大不相同。撰寫一部關(guān)于鴉片戰(zhàn)爭的著作,幾乎改變了我對于中國的每一個(gè)偏見。很久以來,鴉片戰(zhàn)爭被明確看作是一場不同文明之間的沖突,即擴(kuò)張主義、自由貿(mào)易的英國與頑固排外、閉關(guān)鎖國的中國之間的沖突。很多西方人依然認(rèn)為,自遠(yuǎn)古以來,中國就是一個(gè)一成不變的地方,其人民一直認(rèn)同于一套單一的、核心的政治和文化理念。1839年中國與英國開始進(jìn)行及時(shí)次鴉片戰(zhàn)爭時(shí),情形卻并非如此。當(dāng)時(shí)的中國是一個(gè)躁動不安的衰敗中的帝國,到處是對帝國中央政府沒有忠誠感的心懷不滿的人。很自然,如果中國老百姓的生命、家庭或財(cái)產(chǎn)受到威脅,他們就會與英國人作戰(zhàn)。但是,也有很多人把這場戰(zhàn)爭看作是從英國人那里掙錢的機(jī)會,他們向英國人出售補(bǔ)給品,為英國人導(dǎo)航領(lǐng)路,甚至為英國人提供情報(bào)。所以,中國在據(jù)稱與英國作戰(zhàn)的同時(shí),也在與自己作戰(zhàn)。在廣州被圍困期間,城里的中國軍隊(duì)卻在忙于搶劫、殺人乃至(在極端情況下)互相獵食,以至于不能同仇敵愾,共同對敵作戰(zhàn)。
我們一般認(rèn)為戰(zhàn)爭會帶來一些異于尋常的結(jié)果,如慘無人道的殺戮、勇敢頑強(qiáng)的精神和愛國主義的情懷。不過人們在單調(diào)乏味的和平時(shí)期常犯的錯(cuò)誤在戰(zhàn)爭中也普遍存在。鴉片戰(zhàn)爭期間,迫在眉睫的人員傷亡和物資耗費(fèi)并沒能阻止悲劇性的粗心大意的官僚行為發(fā)生。在人民被殺戮、城鎮(zhèn)被攻陷的時(shí)候,中國負(fù)責(zé)指揮這場戰(zhàn)爭的有關(guān)人員卻藏匿或丟失了英國關(guān)于戰(zhàn)爭要求的文件副本;他們厚顏無恥地向皇帝撒謊,把事實(shí)上的一敗涂地說成是大獲全勝;一個(gè)將領(lǐng)在本該指揮一場戰(zhàn)斗的時(shí)候卻因鴉片煙癮發(fā)作而頭昏腦脹不能指揮作戰(zhàn)。這場戰(zhàn)爭打了兩年半時(shí)間,花費(fèi)了數(shù)千萬兩銀子,犧牲了幾千人的生命,皇帝卻在給他一個(gè)前線大臣的華麗麗的諭旨中詢問,他想知道,英國到底在什么地方。
因而,我寫這本書有兩個(gè)目的。其一,我希望將英國讀者從他們對我國充滿鴉片的歷史的健忘癥中喚醒。其二,我還想描述這場戰(zhàn)爭紛繁復(fù)雜的某些方面。我使用的很多英文原始資料是由維多利亞時(shí)代參與這場戰(zhàn)爭的英國軍人撰寫的,他們是把它純粹當(dāng)成一場軍事行動來記述的。但是戰(zhàn)爭從來不是這么簡單的:戰(zhàn)爭充滿了傷害、機(jī)會主義、錯(cuò)誤、謊言和喧囂。對鴉片戰(zhàn)爭的研究會給我們多方面的啟迪:關(guān)于中國和英國的歷史,關(guān)于個(gè)人的痛苦經(jīng)歷和文化沖突,關(guān)于政府和社會的功能或機(jī)能失調(diào),關(guān)于人們在絕望狀態(tài)下產(chǎn)生的折中妥協(xié)、措置失宜、欺瞞哄騙及悲劇結(jié)局。
藍(lán)詩玲(Julia Lovell)
及時(shí)章鴉片和中國
讓我們看一幅中華帝國晚期鴉片吸食者的照片。在這張有代表性的照片中,兩個(gè)男子斜靠在一張長榻上,身上裹著有襯里的提花絲織長袍。其中一個(gè)男子把手臂搭在一個(gè)年輕女子的肩上,這個(gè)年輕女子斜靠在他的上半身(看起來有點(diǎn)兒不自然——或許是有吸食者在盯著她看,或許是因?yàn)檎谡障嗟木壒?。兩個(gè)男子頭靠著床頭板,眼神向下越過長榻盯著照相機(jī),眼睛半瞇著,面無表情。(還碰巧其中一個(gè)吸食者手中令人費(fèi)解地抓著一只玩具狗。)即使在今天,合成鴉片制劑使得鴉片看起來毒性不那么大了,在布拉塞(George Brassa,本名Gyula Halász,在巴黎成名的匈牙利攝影大師。——譯者)拍攝巴黎先鋒派把鴉片重新包裝為放蕩不羈的高雅之物幾十年之后,這一景象依然讓人感到有些不適,比一對高加索醉鬼的照片更讓人感到不舒服,盡管這兩個(gè)吸食鴉片的人顯然生活優(yōu)裕,看起來也不是有太大的鴉片煙癮。也許,從現(xiàn)代人的眼光來看,躺著吸食顯得非常頹廢墮落,仰臥的姿勢十分猥瑣齷齪。吸食者用吸了毒的陰沉眼神(我們這樣想象)平視著我們,好像在向我們示威:“我們是故意而且高興地吸食鴉片來毀滅自己,你們想怎么樣?”
不管我們的政治多么自由,我們?nèi)匀粫f片抱持成見,這種成見中既有道德的因素,也有科學(xué)的因素,它是從一百年前就在西方(也包括中國)開始形成的,這種成見把吸食鴉片看作是社會渣滓或?qū)8蓧氖碌娜怂鶚芬飧傻膼盒小2贿^,除了對于吸食鴉片進(jìn)行譴責(zé)外,還要看到,吸食鴉片是個(gè)更為復(fù)雜的社會現(xiàn)象:這就是19世紀(jì)的廣泛爭論,先是西方傳教士和醫(yī)學(xué)界的觀點(diǎn),然后是中國政府決定譴責(zé)中國存在的吸食鴉片的風(fēng)習(xí),把它看作是病態(tài)的、不正常的——是中國所有問題中最根本的人們思想意志上的民族病。
19世紀(jì)40年代初,中英兩個(gè)國家進(jìn)行了一場以鴉片為名的戰(zhàn)爭,鴉片扮演了改變兩個(gè)國家形象的非凡角色。不論是在英國還是在中國,鴉片一開始都只是一種外來的藥品(在英國是土耳其藥品,在中國是印度藥品),先是在19世紀(jì)引種,然后在該世紀(jì)末又作為外來被堅(jiān)決拒之門外。在19世紀(jì)大部分時(shí)間里,不論是在一般大眾眼里,還是在醫(yī)藥專家眼里,鴉片除了能緩解疼痛之外,大家對它并沒有其他共同的看法。它比酒精的害處是大還是小?它會使使用者變得粗野沒人性嗎?它會使人的肺變黑、會像吃了鴉片的蛆蟲那樣爬嗎?沒有人能確切地回答這些問題。“隨著煙毒流入內(nèi)地,煙禍遍及各地沉湎于鴉片者是在浪擲生命”,清末一個(gè)名叫張昌甲的鴉片吸食者在用若干頁篇幅對吸食鴉片進(jìn)行評論前悲嘆道:“鴉片實(shí)為世間不可少之物。” 鴉片吸食者給人的形象通常是萎靡不振,整日昏昏欲睡。對許多人[包括托馬斯德昆西(Thomas De Quincey),他在鴉片酊的支撐下,夜里在倫敦的街頭游走。]來說,鴉片是興奮劑。中國的勞苦大眾靠著在中午休息時(shí)抽幾口鴉片,來恢復(fù)體力和精力去從事繁重的勞動。19世紀(jì)末,一個(gè)牧師注意到,這些人“簡直就是靠鴉片活著,鴉片就是他們的酒肉。” 維多利亞沼澤(Victorian Fens)中的情形與此沒有什么不同:“一個(gè)要做苦工的男人開始工作前先服用(鴉片)丸子。”19世紀(jì)中葉的一個(gè)觀察者寫道:“很多人都往啤酒里放點(diǎn)兒鴉片,要不他們決不喝啤酒。” 關(guān)于鴉片的作用更令人困惑的是,1840—1842年間在中國的英國軍隊(duì)指揮官注意到,清軍士兵經(jīng)常在準(zhǔn)備作戰(zhàn)時(shí)先要飽吸一通鴉片,結(jié)果,鴉片使一些士兵鎮(zhèn)靜下來,使一些士兵為即將到來的戰(zhàn)斗興奮起來,還使另外一些士兵昏昏睡去。
即使到今天,在一個(gè)多世紀(jì)的現(xiàn)代醫(yī)學(xué)發(fā)展之后,鴉片對人類體質(zhì)的影響還有許多未知之處。不論是采用吃的方式、飲的方式還是吸的方式,鴉片的基本作用都是一樣的:它令人產(chǎn)生幻覺的成分是嗎啡,這是一種脂溶性生物堿,它被血液吸收,(根據(jù)準(zhǔn)備的力度、服用的途徑和個(gè)人的感受性不同,在幾秒鐘或幾分鐘內(nèi))撳動細(xì)胞中的開關(guān)——類鴉片活性肽受體。一旦撳動,其中的一個(gè)開關(guān)——μ受體——就會減緩掌管疼痛感的神經(jīng)末梢的化學(xué)傳感器的釋放。嗎啡產(chǎn)生的痛感缺失以及其他的許多相似物,例如海洛因,看起來簡直是不可思議,能在幾分鐘內(nèi)解除巨大的痛苦。鴉片遠(yuǎn)遠(yuǎn)不是僅能夠使痛感消失,因?yàn)樗M(jìn)入血液,到達(dá)腸道,減慢腸道的蠕動,止住腹瀉和痢疾。它通過抑制咳嗽中樞,產(chǎn)生鎮(zhèn)咳作用。或許最為大家熟知的,是它能促進(jìn)多巴胺的釋放,多巴胺是使大腦產(chǎn)生愉悅情緒的荷爾蒙。簡而言之,鴉片能使我們精神愉快。
和所有一樣,鴉片也有其不受歡迎的消極作用。它的一個(gè)缺點(diǎn)是它會引起反胃惡心(這是在40%服用嗎啡的病人中引起的反應(yīng))。 如果服用它是為了緩解痛苦而不是治療腹瀉,它會導(dǎo)致便秘。它較大的直接的缺點(diǎn),是它會減慢甚至是停止大腦中控制呼吸的中樞,因此,使用過量的話,它會令人窒息而死。由于過量服用鴉片的人一般都死得很安靜,很久以來,鴉片是缺乏勇氣的人自殺時(shí)所依靠的良友,是暗殺者的好助手。此外,多巴胺能使人增強(qiáng)滿足感,也能增強(qiáng)其他的、不那么令人愉悅的感覺。它能加強(qiáng)、放大對恐懼和危險(xiǎn)的感知,因而也是導(dǎo)致妄想狂、猜疑癥和精神分裂癥的藥劑——德昆西的幻覺癥就是這樣產(chǎn)生的。(德昆西常年吸食鴉片,出版有《一個(gè)英國鴉片吸食者的懺悔》,書中描述的東方景象就是他的幻覺。——譯者)
鴉片的一個(gè)缺點(diǎn)(像許多由多巴胺產(chǎn)生的反應(yīng),即被由它產(chǎn)生的愉悅感所控制一樣),是它誘使人渴望從頭開始重新體驗(yàn)整個(gè)過程。如果沒有外界物質(zhì)如鴉片的刺激,類鴉片活性肽和多巴胺受體就會以毫不被注意的平衡狀態(tài)安靜地存在于我們的體內(nèi)。然而,一旦一個(gè)受體受到刺激,這個(gè)受體就會變得不再敏感,就會失去平衡,就會要求經(jīng)常性的、或許還是持續(xù)增加的那個(gè)刺激物的供應(yīng)。如果體內(nèi)的神經(jīng)系統(tǒng)平衡和化學(xué)平衡要依靠體外的藥物來維持,供應(yīng)的突然中斷將會帶來不良反應(yīng)癥狀——發(fā)抖、疲憊、發(fā)熱、起雞皮疙瘩[goose-pimples,這是“cold turky”(突然戒毒法)這個(gè)說法的來源]、惡心、腹瀉、失眠——這些癥狀只有靠醒酒液才能緩解。
在過去一個(gè)半世紀(jì)的中國歷史中,鴉片的歷史形象幾乎與它的化學(xué)作用一樣多姿多樣。對歐洲人來說(他們從17世紀(jì)初開始買賣鴉片),它首先是提供了一條通往中國市場的道路(“鴉片交易看起來有鴉片的特性,”一個(gè)金盆洗手的鴉片販子回憶說,“它們傳達(dá)了一種平和的心境,出售鴉片時(shí)付百分之三的傭金,得到百分之一的利潤,沒有壞賬!”);其次,它又賦予了把中國從吸食鴉片的不良嗜好中解救出來的道德正當(dāng)性(“所有的中國人都多多少少道德感不強(qiáng),”1842年后一個(gè)英國傳教士解釋說,“這正像你在任何一個(gè)不信上帝的國家中期望發(fā)現(xiàn)的情形一樣。不過,對于吸食鴉片的人,情況就更糟。”)。 大概在1870年前后,西方反對中國吸食鴉片的風(fēng)習(xí)的因素中,又加入了其他的舊偏見,形成了“黃禍”論(Yellow Peril)。按照“黃禍”論的邏輯,不信基督教的中國人喜歡鴉片,摧毀了他們身上正常的人體反應(yīng)的任何可能:這是“一種癖好”,一個(gè)“潛在的巫師”,使他們成為高深莫測的沒有道德感的、愚昧仇外的吸毒大軍,用來對西方進(jìn)行報(bào)復(fù)。 對于許多中國人來說,鴉片帶給了他們吸食上癮的危險(xiǎn),但也帶給了他們很多好處:包括利潤,解除了不太重的或慢性的病痛,獲得了造成的幻覺、甚至是美感的享受。因而,到19世紀(jì)末,即使是鴉片的形象已經(jīng)徹底變成為只是被詭計(jì)多端的帝國主義者強(qiáng)加給中國的外來之后,對鴉片的這種看法也并沒有維持多久。對西方的憤恨很容易就退而變成對自己的厭惡:民族主義道德恐慌的潛臺詞是,英國人是給我們帶來了鴉片,但這是我們自己吸食上癮的。1839年,在導(dǎo)致了與英國的戰(zhàn)爭的禁煙運(yùn)動前夕,中國主張嚴(yán)禁鴉片的人——包括態(tài)度堅(jiān)決的林則徐——以肯定的語氣譴責(zé)煙毒,說“鴉片之為害,甚于洪水猛獸”、“鴉片戕害生命,將使我中華之人盡淪為蟲豸犬豕”。 但愿事情是如此簡單。
鴉片最初是從邊界含混的“西域”(包括古希臘、古羅馬、土耳其、敘利亞、伊拉克、波斯和阿富汗)引進(jìn)中華帝國的舶來品,中國文獻(xiàn)(一本醫(yī)學(xué)手冊)對鴉片的最早記載在8世紀(jì)上半葉。它可吃可飲,有多種不同的服用方法(磨碎,煮熟,加蜂蜜,泡茶,與生姜、人參、甘草、醋、烏梅、米粉、冬蟲夏草混合使用),可用來緩解各種病痛(腹瀉和痢疾、關(guān)節(jié)炎、糖尿病、瘧疾、慢性咳嗽、體質(zhì)虛弱)。到11世紀(jì),人們認(rèn)識到它不僅能治病,還能給人帶來愉悅。“便口利喉,調(diào)肺養(yǎng)胃。”一個(gè)心滿意足的鴉片吸食者注意到鴉片的作用,“飲之一杯,失笑欣然。” 大約四百年后的一本宮廷編年史著作中詳細(xì)說明道:“鴉片狀若沒藥(又名“末藥”,是橄欖科植物地丁樹或哈地丁樹的干燥樹脂,可作藥用。——譯者)而深黃,柔韌若牛膠焉,味辛,大熱,有毒方士、房中、御女之術(shù)多用之其價(jià)與黃金等。” 鴉片被認(rèn)為能控制射精,據(jù)性學(xué)理論說,控制射精能使男子回精補(bǔ)腦。在中國明代(1368—1644),添加了鴉片的壯陽藥風(fēng)行一時(shí)——這可能是明代皇帝死亡率高(明代總共十六個(gè)皇帝中,十一個(gè)皇帝沒有活過他們的四十歲生日)的原因。1958年,作為徹底根除中國沖刺行動的一個(gè)組成部分,建政不久的共產(chǎn)黨政府發(fā)掘了明朝一個(gè)皇帝、患憂郁癥的萬歷皇帝(盡管他活得很長)的陵墓,發(fā)現(xiàn)他的骨殖中含有嗎啡。大膽的明宮廚子甚至嘗試著用旺火炒嗎啡,把罌粟籽精加工成凝乳,用它來代替豆腐。鴉片是明朝靈丹妙藥“大金丹”(用于治療牙痛、跌打損傷和房事不舉)的主要成分之一,在這味藥中,鴉片與牛黃、珍珠、冰片、麝香、犀牛角、羚羊角、兒茶、朱砂、琥珀、沉香、木香、白檀以及其他藥材合在一起用,這些藥材要先用金箔包上,然后碾碎,和上人乳捏成丸,用梨汁送服。(據(jù)藥學(xué)手冊,一次服用一丸。 )
還有另外一種舶來品——從新大陸引進(jìn)的煙草——也導(dǎo)致了吸食鴉片。煙草是在1573—1627年間的某一時(shí)間點(diǎn)上引進(jìn)中國的(與花生、甘薯和玉米差不多同時(shí)),到17世紀(jì)中葉,吸煙之風(fēng)已經(jīng)蔓延到全帝國。1644年清朝建立后,把吸煙作為“其罪甚于箭術(shù)之荒疏”而予以嚴(yán)禁:吸煙者和賣煙者會被罰款、鞭笞以至砍頭。 但是到了1726年左右,清政府不再把吸煙當(dāng)做是壞事,因?yàn)榫┏峭庖呀?jīng)遍植煙草了。18世紀(jì)早期,一個(gè)新奇的發(fā)現(xiàn)通過來往于中國和爪哇的商船從爪哇傳到中國,這就是:如果先把煙草在鴉片的漿汁(主要是葡萄牙貨)中浸泡過,吸起來感覺會更好。這個(gè)新發(fā)現(xiàn)的及時(shí)站是清政府新征服的臺灣,然后從臺灣傳到大陸沿海,再傳到內(nèi)地。
正是吸煙的方法教會中國消費(fèi)者吸食鴉片的方法。吸煙是社交性的,講究技術(shù),有很高的鑒賞性(要用玉、象牙和龜殼為材料并飾以雕刻、鑲嵌以珠寶的煙具,用銀制燈具加熱調(diào)制鴉片,吸食者要躺靠在漂亮的紅檀木長榻上)。比起吃鴉片和喝鴉片來,吸鴉片對人的生命威脅也小:大約80%—90%的嗎啡通過煙具冒出的或人呼出的煙散發(fā)掉了。18世紀(jì)末19世紀(jì)初,中國形成了自己的鴉片文化:它成了飯后的時(shí)髦享受,(妓女)賣唱生意場上的主要潤滑劑,所有有臉面的人待客時(shí)的必備之物,皇帝及其家人在皇室生活中減輕壓力時(shí)最喜歡用的東西。 鴉片煙館可能會是有益健康的地方,甚至是豪華奢侈的地方,遠(yuǎn)不是狄更斯筆下那種老套的“罪惡之窩”(den-of-vice,指妓院)(像驚詫不已的毛姆在1922年——中國鴉片毒患最嚴(yán)重的時(shí)候——說的那樣,鴉片煙館像是個(gè)“溫馨的啤酒館”),在這里
輕松易讀的敘述之外,(藍(lán)詩玲)還保持了對緊張場景的追述。這是對她寫作技能的考驗(yàn)……藍(lán)詩玲女士是中國近代文化的密切觀察者,同時(shí)追蹤了這次大戰(zhàn)的后來景象,探討了自19世紀(jì)到近當(dāng)代對其產(chǎn)生的不同記憶。
——《華爾街日報(bào)》(The Wall Street Journal)
煞費(fèi)苦心地追述兩大帝國圍繞在貿(mào)易、條約、控告、反控等方面的復(fù)雜網(wǎng)絡(luò)……藍(lán)詩玲頗具匠心地將這些緊張、艱苦的沖突以及170多年后尚能感知到的結(jié)果濃縮到了一本書中。
——《出版人周刊》(Publishers Week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