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為余德慧與其他研究者融合臨終照顧實務與本土心理學理論所寫作的論文集結,主題包括:從臨終照顧的領域對生命時光的考察、臨終照顧的靈性現象考察、臨終過程心理質變的探討、病床陪伴的心理機制及倫理、臨終處境所顯現的具體倫理現象、臨終過程與宗教施為等,為本土生死學研究和臨終陪伴提出跨越性的探索和視野。
余德慧教授多年來一直在花蓮慈濟醫院的心蓮病房擔任志工,陪伴臨終病人,在瀕臨死亡之處,碰觸生命的深刻領悟。 隨書附贈精美書簽 余德慧選集 重慶大學出版社引進了三本余德慧教授的經典代表作形成《余德慧選集》叢書,作為獻給生命的禮物以饗讀者。叢書包括:
生死無盡》
生命史學》
臨終心理與陪伴研究》
余德慧教授(1951.1.10-2012.9.7)臺灣屏東人,臺灣大學臨床心理學博士、開設了華人世界及時門生死學課程,并且聽者云集。曾任臺灣大學心理學系副教授、東華大學族群關系與文化研究所教授、東華大學咨詢與輔導學系(現更名為咨詢與臨床心理學系)創系主任、慈濟大學宗教與人文研究所教授,主要教授:本土心理學、文化心理學、人文咨詢、宗教現象學、宗教療愈等課程。
著作有《生命史學》、《生死無盡》、《臨床陪伴與心理研究》、《生死學十四講》、《詮釋現象心理學》、《中國人的寬心之道》、《中國人的自我蛻變》、《中國人的生命轉化——契機與開悟》、《孤獨其實是壞事》、《男兒心事不輕彈》、《回首生機》、《感應之情》、《生命夢屋》、《情話色語》與《觀山觀云觀生死》等。
2000年成立的心靈工坊文化公司,余德慧是主要的催生者之一,并擔任咨詢顧問召集人,將身心靈整體療愈的觀念帶進出版界。
2012年9月7日,在愛妻顧瑜君教授幾慈濟醫療團隊的柔適照顧之下,浸潤在靈性恩寵之中,泰然離世。
前言 死亡的啟蒙1
及時章 從臨終照顧的領域對生命時光的考察7
第二章 對臨終照顧的靈性現象考察41
第三章 臨終過程心理質變論述的探討94
第四章 病床陪伴的心理機制:一個二元復合模式的提出160
第五章 臨終病床陪伴的倫理/心性之間轉圜機制的探討204
第六章 臨終處境所顯現的具體倫理現象244
第七章 臨終過程與宗教施為277
臨終過程與自我現實的崩解
從我(石世明)進入心蓮病房 [1] 照顧的及時個病人名雄(假名)說起。癌細胞生長在名雄的喉頸部,使得他的臉頰、口腔都改變了形狀,他的舌頭腫大,嘴巴無法閉合;呼吸道的阻塞,使得他必須要在脖子上開一個氣切口,才能讓空氣進入身體。
腫瘤的分泌物、鼻涕、唾液、其他像痰或是膿的黏液,混雜在一起,不斷地從他的嘴巴和氣切口滲透出來,像是關不緊的水龍頭一般。在比較清醒的時候,名雄最頻繁的工作,就是一手拿著鏡子;另一手握著suction 的管子(一種自動吸氣的管子),從鏡子里頭看準分泌出來的液體,將管子靠近,咻!咻!讓管子吸走所分泌出來的黏液。護士說:“他十分在意他身體形象的改變……剛來到我們病房時,他都面對墻壁(也就是和一般人相反的方向)坐在床上。”后來他找到比較適合自己的姿勢,就是跪在病床旁邊的地上,再將整個人的身體向前趴在我們為他準備的枕頭上。有時候即使在床上也是整個人跪著,經過病房的門口,就會發現他奇怪的樣子。大部分的情況,他的身體都必須向前彎下,體內的分泌物才能夠自然地流出。由于他只能夠彎著身軀休息,護士在他下巴下方的大腿上,墊上一塊看護墊,如果他睡著了,或是神智不是很清醒的時候,看護墊就承接流出體外的分泌物,避免沾得衣服、被子到處
都是。
情況當然不只如此,大部分的時間,他的身體都處在疼痛的狀態、藥物的副作用、身體的疲憊和睡眠質量不良,使得神智不是那么清楚。帶著濃厚味道的分泌物,經常沾到衣服、身體、棉被、床鋪,護士不定時就要過來更換。于是,病床邊總是籠罩著一股分泌物的味道,以及吸附分泌物時所發出的沙沙聲。
名雄不能講話,要溝通就要用寫的,但是他很少跟護理人員溝通,義工就更不用說了,病床邊經常沒什么人,他就一個人趴在那里。分泌物的味道的確是讓人很不舒服,臉部看起來也令人不習慣。名雄經常忙于處理身上的分泌物,一張接著一張的衛生紙,不斷地被抽出來,稍微一不小心,衣服、床單就沾得到處都是。
或許他不太理睬靠到床邊的義工,所以很少有人陪著他。這種情況下可以跟他講什么呢?當時我也不知道,好像那種處境下,旁人一句話都沒辦法講,我只能夠問看看有沒有什么事務性的事情需要幫忙。如果沒有的話,我會盡量在旁邊待著,有時候不講話又顯得奇怪,于是需要時就幫他抽衛生紙,小心翼翼地擦去分泌物,但這個小心翼翼卻又有種令人不舒服的奇怪感。總是過不了幾分鐘,我就待不下去了。事實上,護士們看到名雄,都覺得他很痛苦,會很想要幫他,幾位護士會特別花時間來跟他溝通,但是除了生理上的護理措施有限之外,名雄對護士也沒有太大回應。
在一次到了名雄的病床邊時,他獨自坐在床上,低著頭,一副很疲憊的樣子。我試著問他話,讓他知道我來了。他真的很疲憊,因為腫瘤的關系,他的眼睛整個變得很大,在眼球上緩緩滑動的眼皮,似乎蓋不住他的眼睛,這令人看了十分不習慣。聽到我叫他的聲音,他勉強地張開眼睛,眼皮底下包著無神的眼珠子,隨即又半合了起來。后來護士長進來,她說我可以幫名雄按摩頸部,這樣他比較舒服。我就試著幫名雄按摩,我不敢太用力,輕輕地幫他捏著脖子的兩側,再順著脊椎骨的兩旁推下去。
按到一些地方的時候,名雄會皺眉頭,顯示出會痛的樣子。開始時,我并不知道要跟他說什么,因為名雄無法說話,他就用少許的身體動作跟我溝通。后來他的手去扶前面的額頭,另一只手去碰肩膀,我才理解,按脖子的時候應該扶著他的額頭,這樣頭才不會被推往前傾。我心里責怪自己的經驗不夠。
名雄的下巴和嘴里還是持續有分泌物會滲出來,滴到擺在臉下的衛生紙上。以前他會用自動吸氣的管子將分泌物吸入,或許是今天很疲憊,他就不太去管分泌物,而分泌物也會讓病床附近環繞著一股不是很好聞的味道。名雄的臉上持續顯露著痛苦和疲憊的表情,他大部分的痛來自口腔,止痛劑顯然幫助有限。他皺著眉頭,將雙手扶在脖子或是臉頰上,想要叫喊,卻又叫喊不出來,只是嘴里吐出些許氣息聲,表情好像說著:
“痛!痛就要壓碎我的頭了!”前幾次來他都不理睬我,因為他必須不斷忙碌地吸取身上流出來的分泌物,加上疼痛,時時都要耗掉大部分的精力,照顧他的父親和上小學的女兒也無力理會旁人。
…… ……
…… ……
在病情慢慢變化后,自我現實的希望火苗對名雄來說已經逐漸熄滅,在身體疼痛如烈火灼身的情況下,名雄用顫抖的手在板子上寫著:“活下去沒辦法……生不如死……”大家都愣著,眼睜睜地看著名雄,沉默的時間不好過,有人忍不住,只好趕緊再找出話語來填塞,像是“我知道你很苦……”這類的話來作為表面的安慰。事實上,沒有一個人看了名雄寫的話心里面會好過,在有限的時間中,醫療人員除了用表面的話,似乎就不能夠再多說什么。
李雪菱 [1] 指出,自我現實是一種不斷乞求的過程,當重病來臨時,人們不斷地求治療、求健康、求壽命延長,當這些乞求失效的時候,人們開始退而求其次,求無痛往生、求好死,當這個乞求又失效時,人們求消業、求救贖。換言之,死亡的過程就是人們在實際情況之下不斷從自我的現實里撤退出來。依照肯 威爾伯(Ken Wilber,1985,1991)、沃什伯恩(Washburn,1995)的理論,自我現實的建立,依序共有四層,最底層是“我─他”之間的分化,也就是“我”與“非我”之間的分化;第二層則建立在對時空的分化,也就是讓人認識到主客觀、生與死;第三層分化則建立在身心二元的對立,而開始對“我”有了認同意識,并且以為“我”就是意識里的自我;一層的分化則是建立在社會角色,透過社會角色的形塑而出現自我意象(self image)。而臨終過程的自我撤退剛好是倒過來,首先是社會角色與功能的脫離,社會價值的破碎(石世明,2000:48-49),然后才面臨“控制”或屈服的抉擇,亦即在“積極治療”與“放開手,讓本心臣服于自然的生死流轉”之間做個選擇。如果臨終者能夠繼續進行生命階段的開顯,那么對生與死之間的界限就逐漸剝除,而進入所謂生死相通的“瀕臨”狀態(崔國瑜、余德慧,1998)。在這心靈狀態里,生與死的界限模糊,而個人逐漸發展“當下活著”的態度,一直到個人面臨自我的解除,也就是自我與他者之間的藩籬撤除,而人與神圣領域締結,與他人發展前所未有的親密,宛若個人返回母親的懷里。
這每層自我的消解都是一種轉化。在我們實際的觀察里,并不是所有的病人都走過全程,或者應該說,每個人都依照他的情況分布在全程之間的某一種狀態去世,也就是說,個人伴隨著身體崩解的過程,他的自我現實一層層的褪去,至于會剝落到什么程度并沒有一定的定數,但是隨著自我現實的剝落,我們卻可以發現,有些臨終現象會出現,而且會異于一般自我現實,使得我們開始假設是不是有一類叫作“靈性”的領域存在于生命的底層,由于自我現實的遮蔽,使得“靈性”本身無法被我們認識。
恩
非常喜歡,很好
內容還可以 就是裝訂不那么像正版
看了生死無盡之后,把作者的作品都買回來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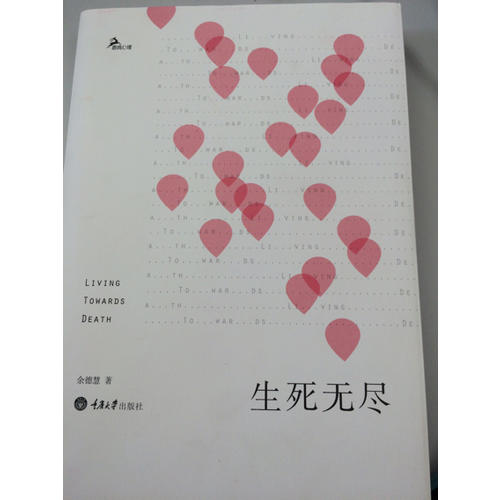 書的裝幀印制都非常精美,還有一個有趣的小書簽。讀來非常棒,文筆很好,說理透徹,令人驚喜,能讓人很沉靜地看待生活中的大小事情。
書的裝幀印制都非常精美,還有一個有趣的小書簽。讀來非常棒,文筆很好,說理透徹,令人驚喜,能讓人很沉靜地看待生活中的大小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