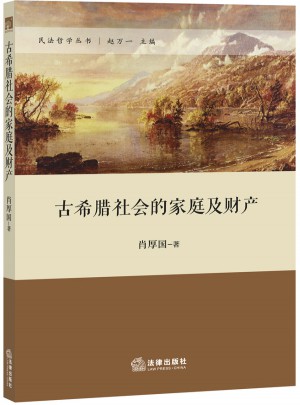
古希臘社會的家庭及財產
- 所屬分類:圖書 >法律>外國法律與港澳臺法律>歐洲
- 作者:[肖厚國] 編
- 產品參數:
- 叢書名:民法哲學叢書
- 國際刊號:9787511862310
- 出版社:法律出版社
- 出版時間:2014-07
- 印刷時間:2014-07-01
- 版次:1
- 開本:16開
- 頁數:--
- 紙張:膠版紙
- 包裝:平裝
- 套裝: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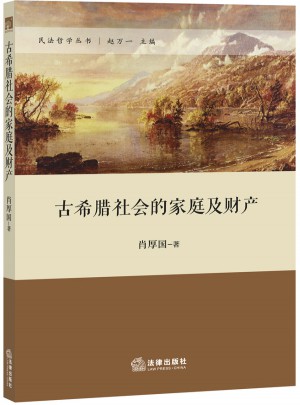
肖厚國編著的這本《古希臘社會的家庭及財產》是一本關于古代希臘家庭及財產的社會史,在古希臘早期社會里,家是一個自足的宗教實體、主要的社會單位以及生活中心。家由家神、家灶、土地及其他財產構成而滲透著宗教的光環,顯得非常神秘,差不多負載著一個人的一切,包括生命。因而,家是一個既給予人們物質上的安全,也給予心理上的價值及滿足感的實體。但在古典時期,家的政治和宗教功能被極大地削弱,其經濟功能被凸顯。家的角色的轉化及其重新定位源于那個時代的人對個體自由及其發展的追求。在民主政治充分發展的時期,城邦占據了公民太多的時間和精力,公民忙于城邦政治而無暇顧及家務,況且民主締造的自由氛圍與活力極大地刺激了文學、藝術和哲學的創造和發展。有抱負的公民的物質需要的滿足必須由家提供;家主事經濟活動,而公民則由此獲得閑暇。古典的家庭圍繞著土地和其他財產的管理和利用而運作,對家庭成員之間權利義務關系的規定和調整也定向于此,其主要目的在于提供物質需要也包括本能的滿足。所以,古典時期的家庭經濟的目的在于消費,而非效益及利潤。家庭的經濟功能在于把少數人從生產性活動中解放出來。所以,在古典時代,任何有關"經濟"的東西依其定義就必然是一種非政治的家事。可見,希臘古典時期的家庭純粹是一項財政建制,這一建制不僅服務于個體家庭的需要,而且也服務于整體的城邦。
肖厚國編著的這本《古希臘社會的家庭及財產》是關于古代希臘家庭及財產的社會史,它以古希臘史的編年順序為線索,嘗試性地描畫出從遠古時期至古典時期的家庭及財產面貌,并以此為基礎探究其政治維度。本書尤其關注古典時期的家庭及財產的政治及法律意義。本書借鑒古典史學家格羅特和摩西·芬利的做法,把古代希臘史劃分為四個時期,即遠古時期(公元前800年以前)、古風時期(公元前800年或750年至公元前500年)、古典時期(公元前5世紀至4世紀)及希臘化時期(自亞歷山大大帝開始至羅馬對東部地中海的征服)。但這份研究只涉及前三個時期。
肖厚國,1965年生,四川大竹人。先后畢業于四川外語學院、西南政法大學以及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獲英語語言文學學士學位、法學碩士學位及法學博士學位。曾訪問孟菲斯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等。現就職于西南政法大學法學研究所。學術興趣及方向為民法哲學、財產的歷史及哲學、法哲學、古典政治哲學、古希臘悲劇及古代希臘史。目前正在從事古希臘法、希臘化時代的歷史及文化研究。主要著述有《所有權的興起與衰落》、《自然與人為:人類自由的古典意義》以及《古希臘的思想與歷史:自由的古典探索》等。
及時章 總論
一、希臘歷史的起源
二、塞諾西辛與城邦的形成
三、城邦的繁盛與衰微
第二章 早期希臘社會的家庭及財產
一、緒論:荷馬史詩與英雄時代
二、早期希臘的社會結構
三、家庭、親屬及共同體
四、家庭的經濟功能及財產結構
五、交換、禮贈與賓客之道
六、財產的倫理價值
第三章 古風時期的家庭
一、氏族社會與家庭
二、財產:新的社會及政治要素
三、克里斯蒂尼的政治變革與家庭的命運
第四章 古典時期的家庭及財產
一、家庭:一項財政建制
二、家長及家屬
三、作為家庭財產的土地
四、余論:古典時期的婦女及其地位
第五章 奴隸:家庭的特殊財產
一、奴隸的起源及意義
二、奴隸的來源及人口數量
三、奴隸的地位及處境
四、歷史的視野:人是否天生為奴
附論:斯巴達的農奴制(helotage)
本書是關于古代希臘家庭及財產的社會史,它以古希臘史的編年順序為線索,嘗試性地描畫出從遠古時期至古典時期的家庭及財產面貌,并以此為基礎探究其政治維度。本書尤其關注古典時期的家庭及財產的政治及法律意義。本書借鑒古典史學家格羅特和摩西·芬利的做法,把古代希臘史劃分為四個時期,即遠古時期(公元前800年以前)、古風時期(公元前800年或750年至公元前500年)、古典時期(公元前5世紀至4世紀)及希臘化時期(自亞歷山大大帝開始至羅馬對東部地中海的征服)。但這份研究只涉及前三個時期,因為正如格羅特先生所說,古典時期的結束乃希臘歷史的終結。關于遠古時期,我們手頭擁有的是一些神話傳說以及像荷馬與赫西俄德那樣的文學文獻。根據神話傳說,公元前15世紀,亦即青銅時代末期,希臘歷史上有一場大洪水;它被說成是宙斯懲罰人類的惡而降下的災難,就如《圣經》中描寫的大洪水一樣。自大洪水后,希臘人的歷史才重新開始。希臘人相信,他們是神的后裔,在他們之先,諸神及其后裔(英雄)實施過統治,自己的歷史乃那一神圣歷史的延續。諸神統治結束后,柏修斯(Perseus)家族、赫拉克勒斯家族和佩羅普斯(Pelops)家族先后入主伯羅奔尼撒半島,相繼對其實施統治。柏修斯締造了希臘史前最偉大的都城邁錫尼(Mycenae)。它因公元前15世紀與克里特文明的接觸獲得了文明的契機,從而發展出邁錫尼文明。邁錫尼文明在特洛伊戰爭前后達至頂峰,自那以后便逐漸衰微。
公元前12世紀特洛伊戰爭后,文明戛然而止,一個新時期即鐵器時代開始,隨后的數百年是一個黑暗時期。說它是黑暗的,乃因歷史一片空白。但在該時期內出現了兩個意義重大的社會現象:鐵的發明以及希臘歷史的曙光。可以說,鐵把史前的希臘人帶到了歷史的門檻處,神話的迷霧、過去的黑暗與歷史的曙光交織在一起。當公元前8世紀文字重現于世的時候,我們突然在希臘大地上發現了城市—國家及執政官制,它們仿佛橫空出世而來。雅典此刻呈現在我們面前的是德拉古統治,而德拉古立法是希臘進入歷史時期后我們所知的及時件事情。正是從這里,我們逐漸見證了雅典,這個希臘世界里最偉大的城市—國家的演進歷程。繼德拉古立法后是梭倫改革,希臘社會于公元前776年最初登上歷史舞臺至克里斯蒂尼的時代為止,希臘人一直在致力解決一個重大問題:對政治實行根本性變革。可以說,梭倫改革奠定了日后雅典民主政制的基礎,于是公元前509年克里斯蒂尼著手對雅典政制實施民主化改造,由此締造出世界歷史上及時個民主政制。自此以后,以雅典為代表的希臘歷史慢慢進入古典時期。在伯里克利時代,雅典民主政治臻于鼎盛;正是在這一時期,不僅作為民主政制的制動器的陪審法庭和作為發動機的公民大會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發展,而且文化及思想尤為活躍。它成就了希臘文明的黃金時代。自伯羅奔尼撒戰爭以來,由于內訌,希臘城邦世界漸趨衰微,終于在公元前4世紀中葉以后被馬其頓控制。亞歷山大大帝死后,希臘古典時期結束。
以上對希臘歷史的簡要勾畫有助于我們分析各個時期的社會結構,并從中清楚地看到家庭與財產的結構及其變遷。正如我在前面已經指出的,關于希臘早期歷史,我們的知識太過貧乏,能夠為我們使用的信息材料乃一些神話傳說及文學文獻。而神話傳說除了提供一些名字外,幾乎沒有什么有價值的東西,因此,我們不得不仰仗荷馬史詩。荷馬認為,他的兩部詩歌《伊利亞特》和《奧德賽》是關于英雄時代的邁錫尼社會的"真實"記錄。然而,考古學則駁斥了這一說法,因為考古學關于英雄時代的諸多發現與荷馬宣稱的"英雄時代"不符。荷馬是詩人和思想家,而非歷史學家,他對歷史少有興趣,對歷史事實未予充分關注。史詩實際上處理的是公元前10~9世紀的社會歷史,盡管如此,仍不妨把它們視為是對英雄時代的描述。誠如芬利先生所言:"倘使歐洲歷史始于希臘的斷言是真的,那么希臘歷史始于奧德修斯的世界也同樣真實,盡管奧德修斯的世界背后也有一段漫長的歷史。"因而,對希臘社會及家庭的研究還得從荷馬開始,從奧德修斯的世界出發。
伊利亞特》和《奧德賽》展示的是一個國王與貴族的社會。他們擁有大量土地及其他財富,過著一種顯赫的尚武生活。國王是祭司、立法者、裁判官及軍事統帥。我們在這個社會發現了一個階梯式的官僚制以及有條件的土地授封。《伊利亞特》關于社會結構的描寫不多,但《奧德賽》則提供了大量的信息。它描寫伊薩卡貴族們的眾生相,同時也展示該共同體中的其他人。由此,我們見到了一個金字塔般的等級結構,位于這個結構頂端的是貴族階層(aristocracy),他們掌握著大部分社會財富及所有權力;伊薩卡社會結構中位于中層者是平民,而處于底層者是大量的奴隸及各種仆人。史詩沒有明確地定義平民的范圍及地位,但顯然他們既不是奴隸,亦非貴族,而是自由人。這一社會階層十分復雜。從史詩的描寫來看,這一階層大抵由手工業者、牧人、農民、預言者、說唱詩人以及醫生構成,當然也包括作為自由人的雇工。注意,在荷馬史詩所勾畫的世界里,無論是無名者,還是奴隸和仆人,都不是處境最悲慘的一群。最不幸的是雇工(thetes),他們是無所屬、沒有財產的勞作者,因臨時受雇他人而勞作。在這樣的社會里,家(oikos)是主要的社會單位,也是生活中心,而共同體則非常弱小,作用極其有限。盡管史詩的世界之發展超出了原始階段,但血緣親屬思想滲透一切,甚至相對新生的、共同體的非血緣建制都盡可能地以家及家庭形象來塑造自己。貴族家庭乃權力中心,在早期希臘社會里,家庭由家神、家灶、土地及其他財產構成,并滲透著宗教的光環,顯得非常神秘,其差不多負載著一個人的一切,包括生命。因而,家是一個既給予物質上的安全,也給予心理上的價值及滿足感的實體。
家庭幾乎是一個萬能的實體。要實施各種活動就必須擁有相應的力量,而家庭力量由家長的管理能力和各類財產構成。必須記住,家庭財產不僅包括土地、房屋以及各種動產,家庭成員和奴隸亦屬于家庭財產的一部分,甚至雇工和扈從的勞動力也概莫能外。土地養育的是階層,并維持社會分層。不過,土地并非最重要的財富,在尚武社會里,金屬乃最貴重的財富,一件金屬物品可能價值連城,其價值甚至超過城池。希臘聯軍統帥阿伽門農為了修復與勇士阿喀琉斯的關系提示出了大量賠禮,其中有銅鼎、大鍋、城池和美女,但居于首位的是銅鼎和大鍋。金屬對尚武社會來說至關重要,因為它意味著工具和武器;沒有它,作為主要的社會及政治活動的戰爭就無法開展,英雄追求的價值—榮譽便不能實現。家庭的財富中心是儲藏室,它珍藏著一個家庭在歲月的流轉變遷中積累起來的所有勞動成果。家庭儲藏室有如現代國家的國庫,家庭經濟就以它為中心,一個家庭靠儲藏室來維持和養育,所以它與家庭的存在同樣古老。儲藏室消失,家庭也就四散而不復存在。家庭財富所滿足者主要是主人的身體需要,并服務于榮譽這一尚武社會的根本價值。
自公元前11世紀以后至公元前776年間希臘歷史出現了一片空白,我們不知道在那一段時期內希臘世界發生了什么。黑暗時期以后,我們突然來到了德拉古時代的雅典。這一時期屬于古風時期,雅典的社會制度是氏族(gente)—胞族(phratry)—部落(tribe)三位一體的結構,部落由胞族構成,胞族由氏族構成,氏族是由大量的家庭匯聚的結果。古風時期的雅典是典型的氏族社會,家是最小的社會單元。家庭的核心是爐灶或家火,家火是家的保護神,亦被稱為戶神或灶神,一切神圣事物都環繞在它周圍。歷史地看,家庭曾是唯我獨尊的中心,個體和共同體都處于它的陰影下。家長乃家的"國王",事實上,共同體的國王也依家長的形象確立起自身。可是,隨著社會的慢慢發展,家的獨立性在法律及經濟上逐漸受到限制;氏族和胞族緩慢而穩步地出現在家庭身旁,但獨立于后者,從而與家庭比肩而立。氏族和胞族的發展導致了共同體的壯大,并隨著城邦在政治上日顯成熟,它慢慢地產生出擺脫家庭的愿望。的確,城市—國家要獲得充分發展,就必須擺脫家庭而擁有自己純粹的政治形式和政治原則。在梭倫的時代,城市—國家已經大踏步地向前發展了,以至于它必須革新氏族社會,因為在日益發展的城市—國家面前,氏族制度的舊原則已無力治理一個此刻已經抵達文明門檻的民族了。革新的基礎乃財產。財產是為政治社會開辟途徑的新要素,這個要素既是政治社會的基礎,也是它的推動力。梭倫借由財產實現了對雅典社會結構的變革,并確立起一種新的政制,亞里士多德把它稱為Timocracy(財權政治)。
梭倫確立的財權政治依財產的多寡分配政治權力,它把那些并非屬于傳統士族的外來貴族接納進政治行列,因而破除了傳統貴族對政治權力的壟斷,由此拓展政治群體和權力群體的范圍。盡管如此,雅典的政治體制并未受觸動,梭倫改革后的雅典仍然奠定在氏族社會上。以家庭為基礎的氏族制度是一個封閉的結構,可是公元前6世紀末,雅典的財富和人口迅速增長,它嚴峻地考驗著古老的氏族制度。結果證明,狹隘的氏族制度嚴重地妨礙著政制的進一步發展。因此,必須破除政制之墻,以一種全新的制度代之以氏族制度。它就是"德謨"。德謨是克里斯蒂尼用以改造阿提卡社會及政治結構的東西,德謨取代從前的家庭而成為政治的基本單元。在克里斯蒂尼那里,德謨既意味著地理區劃,相當于現代社會中的基層單位,也是指政治主體,掌權的公民群體。它是一個中性概念,所有公民被整合進不同的德謨;被整合進德謨的人統稱為德謨特(demote),德謨特是自由公民的別稱。一個人,無論來自何方,有何種起源,只要進入德謨,就被稱為德謨特。可見,德謨特消解了身份和起源差異。
德謨體制對阿提卡進行的重塑拿掉了家庭和氏族的政治之維。自此之后,城邦和家庭分道揚鑣,各自獲得了自己發展的形式而分屬兩個不同的領域。城邦是公共空間,是政治競技場,而家庭是私人領域,應對諸如生殖等必然性的事物。這樣,在古典時期,古希臘的家庭經受了劇烈的變遷。結果是,家庭原有的政治意義喪失而從政治領域退隱,變成一個純粹的經濟單位。家庭,這一"經濟單位",不僅從事物質生產,而且也負責人的生產,即人的繁殖和養育。作為經濟單位的家庭服務于政治目的,因為一個人能否進入城邦這一政治的世界取決于對生活必然性的駕馭而從事物的世界里解放出來,而這最終仰賴家庭經濟及其管理。于是,家庭管理和家庭經濟即家政對一個有政治抱負的人來說就成為尤為重要的事情。
古典家庭的經濟功能被凸顯,這使家庭成為一項純粹的財政建制。這一建制不僅服務于個體家庭的需要,而且也服務于整體的城邦。盡管公元前5世紀古希臘城邦,特別是雅典城邦,獲得了大踏步的發展,但共同體的實力仍然有限,共同體的大型事業諸如城墻和街道的建造,港口、水渠和神廟的修建以及海軍的供給等都由富有的家庭承擔。和平的建設和戰事都仰仗個體家庭的經濟實力。古典家庭圍繞著土地和其他財產的管理和利用而運作,對家庭成員之間權利義務關系的規定和調整也定向于此,其主要目的在于提供物質需要也包括本能的滿足。所以,古典時期的家庭經濟的目的在于消費,而非效益及利潤。然而,必須記住,它并非向所有成員平均地提供物質滿足,而主要針對家長,當然也包括家長以外的男性公民。
家庭的經濟功能在于把少數人從生產性活動中解放出來。這樣,在古典時期,任何有關"經濟"的東西依其定義就必然是一種非政治的家事。色諾芬的《家政學》(Oeconomics)詳盡地闡發了古典的家政思想。正如芬利先生所說,《家政學》教授的是家庭管理藝術,這門藝術有如政治家的政治技藝,因而是民主政治背景下土地所有者或紳士們必備的指南。在該著述中,家庭是一個三分結構:家長、家屬和財產。這是一個典型的紳士家庭。家長經營和控制人力和財產。為了實現公民的理想,有必要動用整個家庭力量。在亞里士多德看來,任何必須為自己的生計而勞作的人都不配享有公民身份。由此可見古典城邦財產的政治意義。無論蘇格拉底、柏拉圖以及斯多葛哲人如何看待財產,古代人關于財富的基本判斷清晰而簡單:財富是必需的,因而是好的(good),它是善的生活的前提條件。在家庭財富中,土地的價值自不待言,可奴隸的經濟作用則值得探討。奴隸在希臘歷史上作為家庭財產的一部分一直存在,但只是在古典時期他才成為一項重要的經濟因素。
古代希臘家庭,尤其是大家庭的經濟需要,促成了奴隸的產生。古典時期的雅典比任何時候都需要奴隸,因為城邦占據了公民太多的時間和精力,公民們忙于城邦政治而無暇顧及家務,況且民主締造的自由氛圍與活力極大地刺激了文學、藝術和哲學的創造和發展,因此像柏拉圖、亞里士多德那樣的哲人需要別人提供家庭服務以獲取時間進行哲思。此外,希臘人需要在家庭之外發展友愛。政治活動、哲思與文化創造以及友愛的發展都需要充分的閑暇,所有這些刺激了對奴隸勞動日益增長的需求。不僅如此,礦藏的開采和大型工程的建設也需要奴隸。古典時期的雅典無疑是典型的奴隸社會,奴隸對古典時期的雅典經濟來說至關重要。無論在被雇用的工作中,還是在社會結構里,他們都很根本。雅典的公民階層,尤其是統治的公民階層,極大地依賴他們及其勞動。這樣一個社會必定有足夠數量的奴隸存在,這是底線,否則社會就無法正常運轉。奴隸制在古希臘世界發展最完善的地方是雅典城邦,它無疑是伴隨公民政治的新形式而出現的一種新需要;這種需要在于解放公民,把公民自身從動物性的勞作中解脫出來而獲得從事公共活動的自由或閑暇。雅典的公民政治代表著古代社會民主制發展的典型形態,而雅典也是利用奴隸制最充分的城邦。雅典的奴隸制最發達,自由也最充分,所以,古典時期的雅典展現為一對不可克服的矛盾及誘惑,它有一雙同時緊握自由和奴隸制而不斷邁步前進的手。
好書好書好書好書好書好書好書好書好書好書
很好用很好用很好用很好用很好用很好用
肖厚國老師堪稱先生,在如今浮華時代,能潛心治學者寥若晨星,肖厚國先生算一枝奇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