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暴力和早期殖民者的壯志中誕生的美國,如今已經(jīng)成為一個(gè)世界強(qiáng)國。不過,這個(gè)國家的歷史仍然作用于當(dāng)下,影響著美國民族身份的塑造。美國對于民族身份的追尋以及對于建國之本的困惑,正是這本書所探討的根本問題。
本書大致按照時(shí)間順序?qū)懢停瑥闹趁駮r(shí)期的美洲開始講起,當(dāng)時(shí),批歐洲人在經(jīng)濟(jì)利益的誘惑以及宗教虔誠的驅(qū)使下,踏上了美洲的土地,隨之而來的疾病則對土著人口造成了毀滅性的打擊……
本書還探討了美國的一些內(nèi)在矛盾:這是一個(gè)打著自由的名號(hào)卻建立在奴隸勞動(dòng)力基礎(chǔ)之上的國家;這是一個(gè)遭遇分裂和內(nèi)戰(zhàn)而被迫維護(hù)團(tuán)結(jié)、重估理念的國家;這也是一個(gè)在20世紀(jì)的金融危機(jī)和全球沖突的背景下努力建立道德霸權(quán)、加強(qiáng)軍事保障并且維持經(jīng)濟(jì)穩(wěn)定的國家。書中對于美國社會(huì)政治圖景變遷的翔實(shí)勾勒中,編織呈現(xiàn)了歷史長河里各色人物的視角:奴隸和奴隸主,革命者和改革家,戰(zhàn)士和政客,移民和難民。正是這些聲音,和當(dāng)今多元化美國社會(huì)中的其他聲音一道,共同定義了今天這個(gè)新世紀(jì)之初的美國。
劍橋大學(xué)扛鼎經(jīng)典 大學(xué)者小經(jīng)典
一本書諳熟美國 //深刻
世界歷史學(xué)家精心打磨的歷史經(jīng)典讀本
格蘭教授的女性視角,作者對美國歷史精彩的洞察力,以及對美國歷史的把握,都非常別具一格。
更作品請進(jìn)入新星出版社旗艦店》點(diǎn)擊進(jìn)入
蘇珊-瑪麗 格蘭特(Susan-Mary Grant)
英國紐卡斯?fàn)柎髮W(xué)的美國史教授。著有《北之于南:南北戰(zhàn)爭前美國的北方民族主義與美國身份認(rèn)同》(2000年)與《為國家統(tǒng)一而戰(zhàn):美國南北戰(zhàn)爭》(2006年),同時(shí)編有《分裂的遺產(chǎn):美國南北戰(zhàn)爭的深遠(yuǎn)意義》(2003年)與《美國南北戰(zhàn)爭主題論文集:州際戰(zhàn)爭》(2010年)等。
引論 一個(gè)新世界的形成 / 1
及時(shí)章 新發(fā)現(xiàn)的土地——想象美洲 / 11
英國內(nèi)外的擴(kuò)張 / 20
第二章 山巔之城——一個(gè)救世主國家的起源 / 45
種族和宗教:切薩皮克 / 53
出埃及記:圣經(jīng)之國的起源 / 57
印第安人、契約與身份:創(chuàng)建一個(gè)白人社會(huì) / 69
第三章 全人類的事業(yè)——從殖民地到《常識(shí)》 / 83
那么,何謂美國人呢? / 95
分離的時(shí)候到來了 / 106
第四章 不言而喻的真理——革命共和國的建立 / 122
生存還是毀滅 / 134
信仰的契約 / 145
第五章 地球上一絲最美好的希望——走向第二次美國革命 / 159
我們的聯(lián)邦,必須保存!/ 176
南北戰(zhàn)爭的爆發(fā) / 184
第六章 帝國的西征——從聯(lián)盟到國家 / 200
進(jìn)發(fā)里士滿、穿越落基山脈 / 213
一個(gè)世紀(jì)的征途 / 225
第七章 應(yīng)許之地——通往美國世紀(jì)的大門 / 238
回顧 / 256
進(jìn)步的國度 / 269
第八章 士兵的信仰——沖突與服從 / 280
新國家主義 / 296
新自由主義 / 308
第九章 在的邊疆之外——美國的新政 / 321
“布魯斯藍(lán)調(diào)” / 334
美麗新世界 / 347
第十章 變革中的疆域——原子能時(shí)代的美國 / 364
美國世紀(jì) / 378
的邊界 / 392
第十一章 夜幕下的大軍——反主流文化和反革命 / 403
“垮掉的一代” / 415
第三個(gè)世紀(jì) / 428
參考文獻(xiàn) / 443
人名、地名、術(shù)語雙語對照表 / 455
譯后記 / 482
第六章 帝國的西征——從聯(lián)盟到國家(節(jié)選)
一個(gè)世紀(jì)的征途
聯(lián)邦在內(nèi)戰(zhàn)中的勝利很容易會(huì)造成一種假象,讓人們誤以為內(nèi)戰(zhàn)前后的美國在道德和物質(zhì)方面存在著清晰的差別。實(shí)際上,一個(gè)人越是接近勝利,對勝利的認(rèn)識(shí)就越難捉摸。北方在內(nèi)戰(zhàn)中“獲勝”,但為此究竟付出了何種代價(jià)卻甚少有人談?wù)摚瑲v史學(xué)家和公眾都只是在思考著南方失敗的代價(jià)。內(nèi)戰(zhàn)之后的數(shù)年中,這個(gè)國家顯然也在西部征途中“獲勝”。不過,在20世紀(jì)那些令人癡迷的電影,尤其是“西部電影”中,這場勝利的真實(shí)面貌及其局限性都被過分簡化了。從黑白電影到彩色電影的轉(zhuǎn)變固然簡單,但這些電影對于西部歷史的演繹卻不能輕易為黑人與白人的沖突涂上絢麗的色彩。西部本身也做不到這一點(diǎn)。人們對于美國種族圖景的定義和辯論,恰恰是基于西部那些戲劇性的、充滿感召力的景象,而不是內(nèi)戰(zhàn)的戰(zhàn)場景象。這場辯論曠日持久,因?yàn)榉N族問題并不是一個(gè)直接簡單的問題。
當(dāng)然,這并不是說內(nèi)戰(zhàn)就必然是一個(gè)直截了當(dāng)?shù)膯栴}。當(dāng)這個(gè)國家從沖突的中心——聯(lián)邦將軍尤利西斯 格蘭特(Ulysses S. Grant)和邦聯(lián)將軍羅伯特 李(Robert E. Lee)之間的戰(zhàn)爭,以及種族問題上的激進(jìn)派和保守派之間的政治斗爭——轉(zhuǎn)移到別處,他所面臨的危機(jī)在1861—1865年,以及隨后的幾年里,面臨著更為復(fù)雜的利害攸關(guān)的問題。新近的美國移民大多從北部登陸,并居住在那里,這場戰(zhàn)爭為他們提供了一個(gè)機(jī)會(huì),讓他們得以證明自己對美國的忠誠,與美國的機(jī)會(huì)平等理念結(jié)盟,雖然他們不一定同意新萌生的種族平等理念。不過,在聯(lián)邦軍隊(duì)中,少數(shù)族裔組成的軍團(tuán)經(jīng)常會(huì)擔(dān)負(fù)各種任務(wù),不論他們是愛爾蘭人、印第安人還是非裔美國人。
即使是非裔美國人這樣在美國內(nèi)戰(zhàn)中占據(jù)如此中心位置的群體,他們的動(dòng)機(jī)也沒有那么簡單。非裔美國人的主要領(lǐng)袖弗雷德里克 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主張武裝起他的黑人同胞,其倡議被認(rèn)為是一種普遍觀點(diǎn)。“一旦讓黑人佩戴上U.S.的黃銅字母、衣服紐扣印上老鷹圖案、肩章繡上步槍圖案、口袋里再裝上子彈,”道格拉斯聲稱,“世界上就沒人再能否認(rèn),他們理應(yīng)享有美國公民的權(quán)利。”不過,也有一些人并不同意這種觀點(diǎn),他們認(rèn)為非裔美國人“一旦被列入戰(zhàn)爭名單,只會(huì)白白送命卻一無所獲”,他們不該認(rèn)為自己有義務(wù)“在那面從不保護(hù)他們的旗幟下戰(zhàn)斗”。
然而,為了自己能夠被美國接納而加入戰(zhàn)斗只是其中一個(gè)原因。一些人參戰(zhàn)只是希望保護(hù)自己的家園不被美國侵犯。威斯康星州格林灣部落的梅諾米尼人、 奧奈達(dá)人和斯托克布里奇—猛西人自愿為聯(lián)邦戰(zhàn)斗時(shí),根本沒有考慮到公民權(quán)的問題。他們僅僅是希望保護(hù)自己的土地免受白人的進(jìn)一步侵犯,希望自己的參戰(zhàn)行為或許可以迫使聯(lián)邦政府意識(shí)到他們的權(quán)利。不過,和美國黑人受到的待遇一樣,格林灣諸部落加入軍隊(duì)的要求最初遭到了聯(lián)邦的拒絕。威斯康星州的民兵指揮官奧古斯塔斯 蓋洛德(Augustus Gaylord)仍舊堅(jiān)持認(rèn)為“只要文明世界里還有足夠的志愿兵,就沒有必要屈尊讓印第安人參與到這場我們同胞之間發(fā)生的沖突中”,因?yàn)檫@些潛在的同盟本是一群未經(jīng)開化的異族。這當(dāng)然是一種種族主義觀點(diǎn),但它并不一定與土著志愿兵的獨(dú)立野心全然相反。
在加利福尼亞州,圍繞著接納還是排斥土著人、同化還是隔離新移民的各種議題尤其突出。在東海岸,議會(huì)艱難地通過并且施行了第十四修正案這一對于美國公民權(quán)至關(guān)重要的契約文件。同時(shí),在這個(gè)國家的另一端,人們正在與國家擴(kuò)張和移民問題苦苦斗爭。造成這種緊張狀態(tài)的原因很簡單:取得美國公民權(quán)和國籍有兩條途徑。一種途徑是生于美國。然而,僅僅出生在名為美國的土地上并不夠,1884年有關(guān)土著美國人公民權(quán)的“艾爾克訴威爾金斯案”一項(xiàng)法律裁決就沒有判給艾爾克公民權(quán)。不過到了1898年,另一例針對華人子女公民權(quán)的“美國訴黃金德案”卻又最終判給了黃金德公民權(quán)。另一種途徑是成為美國人。但是這種獲得身份的途徑有時(shí)會(huì)遭到在種族和宗教問題上的反對者的指責(zé),這些指責(zé)雖然不是,但大多數(shù)時(shí)候都是聚焦在移民問題上。在加利福尼亞,就是中國移民的問題。
由于前一年在那里發(fā)現(xiàn)了金礦,加利福尼亞州在1849年加入聯(lián)邦的決定大受歡迎,并且迅速被接納。加利福尼亞州最開始的憲法與美國其他各州并無區(qū)別,及時(shí)項(xiàng)條款便指出“所有人生而自由獨(dú)立”,擁有生命權(quán)、自由權(quán)和財(cái)產(chǎn)權(quán)這些“不可讓渡的權(quán)利”,上述權(quán)利受到屬于人民的政治力量的保護(hù),并通過一個(gè)“為人民獲得保護(hù)、安全和利益而建立的”政府來表達(dá)。其中沒有規(guī)定任何種族或者人種之間存在差別。不過,30年之后,加利福尼亞州對憲法進(jìn)行了修改,1879年的州憲法提出了一個(gè)非常不同的議案。雖然“白人移民和非洲后裔移民”與“土生土長的美國公民”享有同樣的權(quán)利,但上述權(quán)利并不能擴(kuò)至所有人。州憲法宣稱“中國人,癡呆和精神病人,或被宣判犯有可恥罪行的人”無權(quán)“行使州內(nèi)的選民特權(quán)”。除此之外,加利福尼亞州的任何商業(yè)活動(dòng)都不允許雇傭“中國人和蒙古人”。如果這還不夠的話,州憲法還規(guī)定“所有加利福尼亞州的法律”都“只能使用英文實(shí)行、保存和”。
最令人感到驚訝的也許并不是這些排斥性條款會(huì)被寫入憲法,而是它們竟會(huì)被寫入了加利福尼亞州的州憲法。在加利福尼亞州加入聯(lián)邦時(shí),就已經(jīng)因其潛在的財(cái)富吸引了數(shù)量可觀的移民。同時(shí),在它還是西班牙和墨西哥的舊省上加利福尼亞時(shí),就已經(jīng)居住著大量來自墨西哥的西班牙語土著人口。美墨戰(zhàn)爭結(jié)束后,雙方在1848年簽訂了《瓜達(dá)盧佩—伊達(dá)爾戈條約》,其中規(guī)定墨西哥割讓上加利福尼亞和新墨西哥領(lǐng)地給美國,在這些地區(qū)居住的墨西哥人也就自動(dòng)獲得了美國公民權(quán)。因此,在加利福尼亞州,有關(guān)州憲法的爭論也就比其他很多州都要復(fù)雜,但最終也有可能出現(xiàn)一個(gè)包容性的公民權(quán)概念。
加利福尼亞州在加入聯(lián)邦時(shí)已經(jīng)是一個(gè)廢除奴隸制的自由州,不僅如此,在制憲辯論的過程中,參會(huì)者也非常強(qiáng)調(diào)那些“墨西哥血統(tǒng)的美國人”與美國本土公民應(yīng)該享受平等的待遇。金博爾 迪米克(Kimball H. Dimmick)作為代表之一參與了會(huì)議。他最初來自紐約,1849年當(dāng)選為圣何塞市市長。在會(huì)議中,他強(qiáng)調(diào)“在土生土長的加利福尼亞人和美國人之間”不應(yīng)該設(shè)置任何“分界線”。他的支持者們,也就是那些具有墨西哥血統(tǒng)的人,現(xiàn)在“都聲稱自己是美國人,不會(huì)同意被當(dāng)作少數(shù)族裔看待,”他解釋道,“他們都將自己歸為美國人”。因此,“不論來自哪個(gè)國家”,他們都“理應(yīng)被當(dāng)作社會(huì)主流對待,”金博爾總結(jié)道,“他們相信從此以后自己將會(huì)被視作是美國人。”最終通過的州憲法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這一立場。此外,考慮到加利福尼亞州人口的雙語特點(diǎn),它還使用了英語和西班牙語兩種語言。但是,加利福尼亞州的這種狀態(tài)并不能維持太久。
1849年,加利福尼亞州在種族和語言方面仍持有包容的態(tài)度,但是到了1879年,它卻不可思議地開始公開秉持排華立場。從很多方面來講,這種轉(zhuǎn)變都與美國的發(fā)展趨勢一致。這些趨勢在內(nèi)戰(zhàn)之前就已經(jīng)存在。實(shí)際上在那時(shí),南方和北方之間與日俱增的敵意轉(zhuǎn)移了反對移民,尤其是反對天主教的社會(huì)情緒。不過,這種社會(huì)情緒在殖民時(shí)期就已經(jīng)存在,并且一直都是北方政治、宗教和社會(huì)圖景中一個(gè)固有部分。19世紀(jì)50年代,持有排外立場的美國人黨(或稱無知黨)的短暫出現(xiàn),顯示出這種趨勢的持續(xù)性和局限性。當(dāng)然,很多聯(lián)邦的少數(shù)族裔軍團(tuán),尤其是愛爾蘭人在戰(zhàn)爭中表現(xiàn)英勇,試圖對抗這種反天主教的偏見。但是在加利福尼亞州這種地方卻收效不大,一方面是因?yàn)槲鞑垦睾V菥嚯x東部戰(zhàn)場太過遙遠(yuǎn);另一方面則是因?yàn)榧永D醽喼莸谋就撂熘鹘倘丝诤吞熘鹘桃泼瘛⑿陆桃泼裣嗷ト诤希@讓以新教徒為主的精英們感到驚恐,因此在這里,反天主教情緒的程度更深。
美國歷史經(jīng)常出現(xiàn)這樣的情況,一旦人們認(rèn)同了一種外部威脅,那么即使他們分歧再大,也會(huì)團(tuán)結(jié)在一起。在當(dāng)時(shí)的加利福尼亞州,人們心中的威脅來自于中國人。中國勞工被引入美國,是為了修建能夠統(tǒng)一美國的鐵路,而他們至少在種族問題上統(tǒng)一了美國,讓種族問題的風(fēng)頭蓋過了威脅到加利福尼亞和全國穩(wěn)定的宗教分裂問題。僅僅在1870—1880這十年間,中國移民的數(shù)量就從不到100人激增至超過10萬人。在此之后,由于1882年議會(huì)制定《排華法案》營造了排華的社會(huì)情緒,禁止中國勞工繼續(xù)移民美國,中國移民的數(shù)量才隨之下降。
內(nèi)戰(zhàn)即使沒有全然中止移民行為,但也已經(jīng)減緩了其速度;同時(shí),它雖然沒有壓制美國的排外情緒,也在一定程度上減弱了這種聲音。不過,在戰(zhàn)后的幾年中,兩者卻又卷土重來。在這片托馬斯 潘恩描繪的“人類的庇護(hù)所”的土地上,尤其是在這樣一個(gè)將潘恩的烏托邦藍(lán)圖真正凝結(jié)為自由女神像(1886年)外形的時(shí)代中,對于移民的敵意看起來也許有些自相矛盾。不過,那些倡導(dǎo)“所有美國人享有相同權(quán)利”的人卻發(fā)現(xiàn),內(nèi)戰(zhàn)和接下來的憲法修正案——也就是三項(xiàng)“重建修正案”——都沒能為建構(gòu)一個(gè)包容的新美國國家身份提供實(shí)際的土壤。第十三修正案已經(jīng)廢除了奴隸制;第十四修正案已經(jīng)明確了公民權(quán);第十五修正案也確保了各個(gè)種族的投票權(quán)(當(dāng)然,女性另當(dāng)別論)。理論上講,擁有了這些修正案,美國就可以期許一個(gè)更加積極的未來。但實(shí)際卻證明,想要掙脫過去的牽絆,即使不是不可能,也要經(jīng)歷千難萬險(xiǎn)。
至少按照美國最重要的諷刺作家之一馬克 吐溫(Mark Twain)的話來講,伯克利主教在18世紀(jì)所期許的美國新的黃金時(shí)代,在19世紀(jì)末不過僅僅是“鍍金時(shí)代”(The Gilded Age)。1873年,隨著馬克 吐溫與好友編輯查爾斯 達(dá)德利 沃納(Charles Dudley Warner)合著的《鍍金時(shí)代》一書正式出版,“鍍金時(shí)代”一詞便開始經(jīng)常被用來指稱內(nèi)戰(zhàn)結(jié)束到20世紀(jì)初期之間的時(shí)代。雖然這本書精辟地控訴了當(dāng)時(shí)政治的腐敗和精英群體的權(quán)力濫用,但從理解這段時(shí)期的角度來看,這本書也許有些誤導(dǎo)性。
戰(zhàn)后美國經(jīng)歷了一段快速發(fā)展時(shí)期,其中大規(guī)模的移民居功至偉,同時(shí),這也得益于技術(shù)進(jìn)步,尤其是1865年之后的交通革命所做出的貢獻(xiàn)。不過,學(xué)者們總是輕易將城市化、工業(yè)化和移民這三駕馬車視為引領(lǐng)美國發(fā)展的動(dòng)力,認(rèn)為這些積極和消極的力量將美國推向了20世紀(jì),推向了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美國的世紀(jì)”。在當(dāng)時(shí)看來,這個(gè)過程并沒有事后看來的那么具有決定性。當(dāng)時(shí)的美國人當(dāng)然是將之視為整個(gè)國家的轉(zhuǎn)型時(shí)期,但影響這種轉(zhuǎn)型的因素既有源自過去的財(cái)富,也有來自未來的誘惑。
內(nèi)戰(zhàn)已經(jīng)從經(jīng)濟(jì)上擊垮了戰(zhàn)敗的南方白人,對他們來講,過去也就成為殖民傳奇的黃金時(shí)代。這種傳奇既是短視的,也是虛構(gòu)的,它假定了一個(gè)戰(zhàn)前的過去,那里生活著心滿意足的奴隸、漂亮的美女、風(fēng)度翩翩的紳士,還擁有風(fēng)雅的生活方式。在這個(gè)后來被稱作“舊南方”的所謂“新南方”中,他們既聽不到綁在一起的奴隸向南行進(jìn)時(shí)悲傷沉重的腳步聲,也聽不到拍賣臺(tái)上的痛苦呻吟。在他們對于邦聯(lián)死亡將士的記憶與紀(jì)念中(圖32),南方白人基于自己的戰(zhàn)敗以及與美國其他地區(qū)的區(qū)別,建立了一種獨(dú)特的公民傳統(tǒng)。1866年和1867年的《重建法案》規(guī)定,先前的邦聯(lián)各州仍然實(shí)行軍事管制,聯(lián)邦軍隊(duì)在1877年才最終撤離。為了使南方各州的立法機(jī)構(gòu)批準(zhǔn)第十四修正案,很多之前的邦聯(lián)支持者被要求宣誓效忠這個(gè)國家。這些人因此只能從“敗局命定論”(Lost Cause)的文化建構(gòu)中尋求安慰。這種文化在重建工作開始后逐漸發(fā)展起來,一直持續(xù)到20世紀(jì)。當(dāng)然,諷刺的是,事實(shí)證明邦聯(lián)的主要事業(yè),也就是南方黑人與白人之間的種族分離,遠(yuǎn)沒有遭受失敗;恰恰相反,它才剛剛開始。
奴隸制有不同的內(nèi)涵。它是一種殘忍和恐懼的體系,也是一種身體利用和經(jīng)濟(jì)剝削的體系,但它并不是一種隔離體系。在戰(zhàn)前南方,黑人與白人毗鄰而居。在戰(zhàn)后幾十年中,他們才開始逐漸疏離。后來,很多之前的邦聯(lián)州通過了《黑人法典》,試圖通過合法的形式,將南方非裔美國人重新置于近似奴隸的位置。因?yàn)槿鄙倥`制時(shí)期對于日常接觸和行為進(jìn)行管理的法律,新的種族法律開始出現(xiàn)。在奴隸制中,制定法律的目的是為了維系美國南方的“黑奴制度”,但是美國東部沿海地區(qū),以及整個(gè)西部的土著和移民的經(jīng)歷清楚表明,奴隸制廢除之后的種族法律并不僅僅是南方才有,法律中的條款也沒有特別針對南方。
美國的重建過程一直持續(xù)到1876年才告一段落。在那一年,思考著過去的不只是南方白人。1876年正值美國獨(dú)立百年,一位叫作貝亞德 泰勒(Bayard Taylor)的詩人,也就是1876年7月4日國家頌歌的作者,深思了美國獨(dú)立以來及時(shí)個(gè)百年的發(fā)展歷程(圖33)。對于泰勒來講,獨(dú)立百年的慶典是一次“的測試……評判了我們堅(jiān)定熱情的力量……今后我們再也不會(huì)看到這樣隆重的紀(jì)念日。我們投身于生活之中,英勇奮斗,這給了我們足夠的理由將它銘記于心;生活的記憶也會(huì)將我們與之相連:它又無比遙遠(yuǎn),并因此變得傳統(tǒng)而莊重”。獨(dú)立百年的慶典給美國提供了一個(gè)革命的避難所。這場革命發(fā)生在足夠遙遠(yuǎn)的過去,為國家團(tuán)結(jié)創(chuàng)造了必要的神秘感;它與當(dāng)下的距離卻又不算疏遠(yuǎn),足以讓人們忘卻這個(gè)國家在近些年來所承受的兩敗俱傷的沖突。
不過,1876年,當(dāng)這個(gè)國家在慶祝百年獨(dú)立之時(shí),它尚處于危機(jī)之中。南卡羅來納州、加利福尼亞州,以及其間地區(qū)的街道上仍能看到經(jīng)濟(jì)蕭條、政治腐敗和種族沖突的景象。美國人有理由在國家主權(quán)方面感到自信,但是在文化方面卻絲毫得意不起來。到了1876年,美國是一個(gè)成功的、政治團(tuán)結(jié)的、生機(jī)勃勃的國家,但是它的國家身份仍舊充滿沖突。同樣是在這一年,藝術(shù)、制造業(yè)和土壤、礦業(yè)產(chǎn)品世界展覽會(huì)(簡稱世博會(huì))在費(fèi)城召開,占地兩英畝。世博會(huì)的游客們卻沒有機(jī)會(huì)思考這個(gè)問題。擺在他們眼前的是各種美國豐富的自然資源,以及1776年以來科技進(jìn)步的成果。
升降機(jī)、發(fā)動(dòng)機(jī)、電燈、礦產(chǎn)、隕石、大理石、電話、打字機(jī)、亨氏番茄醬不過只是當(dāng)年費(fèi)城世博會(huì)中展出的一部分產(chǎn)品。會(huì)場中還擺放著代表美國本土物種的填充動(dòng)物玩具,其中有鹿、海象和北極熊。在展會(huì)舉辦之時(shí),這些動(dòng)物已經(jīng)面臨著來自移民的威脅。展會(huì)之后不到十年,曾經(jīng)在大平原上漫步的1300萬頭美洲野牛已經(jīng)因?yàn)獒鳙C而面臨滅絕的危險(xiǎn)。到了1883年,野牛數(shù)量僅剩不到1000頭。這就是美國為進(jìn)步和生產(chǎn)力所付出的代價(jià)。
生產(chǎn)力或產(chǎn)品本身并不是美國的全部,更重要的是生活在這里的人。在這個(gè)意義上,世博會(huì)并不那么值得慶祝,反而值得引起充分的擔(dān)憂。對于土著人口來說,他們當(dāng)中的一些人依靠大平原上迅速衰減的畜群為生,他們的命運(yùn)并沒有世博會(huì)上展現(xiàn)的那么振奮人心,他們的未來也沒有那么充滿希望。他們是一群生活在美利堅(jiān)的有色土著人。但是在1876年的費(fèi)城,他們卻不再是活生生的、正在呼吸的人,而變成了不會(huì)說話的模型。雖然在展會(huì)上,美國土著人被視作是靜止的動(dòng)物填充玩具,但實(shí)際上他們卻是非常活躍的。在蒙大拿領(lǐng)域的小比格霍恩河邊,喬治 卡斯特(George Custer)上校敗在了蘇族首領(lǐng)“坐牛”和“瘋馬”的手下。在百年獨(dú)立慶典期間,戰(zhàn)敗的消息傳到了費(fèi)城。
因此,在美國百年獨(dú)立的那一年,美國人不僅需要思考他們的國家已經(jīng)走了多遠(yuǎn),還需要思考他們?nèi)砸^續(xù)走多遠(yuǎn)。對于這樣一個(gè)移民國家來說,所有這些問題——人民是誰、作為美國公民意味著什么、美國人擁有怎樣的公民權(quán)——仍然是一個(gè)反復(fù)存在的困境。美國建國之時(shí)的那些理念當(dāng)然是具有包容性的,但事實(shí)上其包容性卻相當(dāng)從19世紀(jì)的醫(yī)生和作家奧利弗 溫德爾 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將美國人描繪為“現(xiàn)代世界中的羅馬人——被同構(gòu)的偉大人民”,到1908年伊斯雷爾 贊格威爾(Israel Zangwill)在著名的戲劇《熔爐》中提出的美國社會(huì)“熔爐”隱喻,多年以來,有很多名言表現(xiàn)了與克雷夫科爾所說的“美國人,這種新人”同樣的意思。美國已經(jīng)為實(shí)現(xiàn)這種理想提供了途徑,但卻缺乏足夠的動(dòng)力。麥迪遜害怕這些法律變成一紙空文,但這種擔(dān)憂在美國歷史中的很多時(shí)候都變成了現(xiàn)實(shí)。《權(quán)利法案》并沒有能夠保護(hù)非裔美國人免受白人至上主義極端分子的侵襲,也沒能捍衛(wèi)那些在二戰(zhàn)期間被投入拘禁營的日裔美國人的憲法權(quán)利。
可以說,在20世紀(jì)的反共恐慌中,以及在20世紀(jì)50年代眾議院組成的調(diào)查委員會(huì),即眾議院非美活動(dòng)調(diào)查委員會(huì)的行為中,這種忽視基本原則的傾向達(dá)到了最惡毒的巔峰。從這個(gè)委員會(huì)的名稱中無疑可以看出一種恐懼,而這種恐懼實(shí)質(zhì)上又導(dǎo)致了現(xiàn)代的政治迫害。不過,其實(shí)當(dāng)這個(gè)新國家在思考美國的意義,以及作為美國人的意義時(shí),這種恐懼就已經(jīng)存在了。它在內(nèi)戰(zhàn)之前和內(nèi)戰(zhàn)期間一直存在,并在邊疆地區(qū)真正涌現(xiàn)出來。
出于管理土地的考慮,聯(lián)邦政府自1787年《西北法令》以來,明確了這些地區(qū)只是法律和實(shí)際意義上的過渡州,并將很快變成聯(lián)邦真正管轄下的州。出于管理人口的考慮,政策中也加入了一些過渡性元素,但這些元素被過多的成見和偏見所阻礙。一直以來,這些成見和偏見使他們中的大多數(shù)人無法獲得國家歸屬感。隨著聯(lián)邦在1865年贏得內(nèi)戰(zhàn)的勝利,同時(shí)也隨著第十三、十四修正案相繼通過,非裔美國人至少在法律層面上成為具有選舉資格的“美國人”。奴隸制被徹底廢除,但事實(shí)證明支撐奴隸制的種族意識(shí)卻變得更加富有韌性。在下一個(gè)世紀(jì),種族區(qū)隔和種族差異在大多數(shù)情況下都會(huì)成為國家發(fā)展的基石。而需要面對這一令人困擾的現(xiàn)實(shí)的絕不僅僅是非裔美國人。
第十一章 夜幕下的大軍——反主流文化和反革命(節(jié)選)
第三個(gè)世紀(jì)(節(jié)選)
然而,1981年畢竟不是1776年。到了20世紀(jì)后期,已經(jīng)有大量與個(gè)體相關(guān)的權(quán)利得到提倡和實(shí)施,這也給聯(lián)邦政府增加了大量職責(zé),而這些職責(zé)是聯(lián)邦政府既不能廢除也無法避免的。對反主流文化運(yùn)動(dòng)的抵制將一些思想和利益集團(tuán)松散地聚合在一起,由此形成的新右派涉及思想、社會(huì)、政治、宗教和道德等諸多方面。新右派形成的動(dòng)力在很大程度上來源于宗教復(fù)興運(yùn)動(dòng),而政治與宗教之間日益緊密的聯(lián)系也向一直到20世紀(jì)后期都與宗教毫無干系的政治文化發(fā)出了挑戰(zhàn)。保守的反主流文化在某些方面試圖大規(guī)模重建清教徒村莊,對于那些反對者,則借助一種宗教的狂熱予以打壓。然而,這個(gè)運(yùn)動(dòng)從整體上而言從來沒有成功地拆解過這個(gè)國家與生俱來的權(quán)利。在70年代,為了捍衛(wèi)60年代遺留下來的傳統(tǒng),尼克松推行了一系列環(huán)境政策。在接下來的數(shù)年里,美國政治、法律、生活中的許多其他領(lǐng)域也都推出了類似的政策。越戰(zhàn)時(shí)代將有關(guān)自由的新聲音,尤其是來自學(xué)生的聲音引入到全國的對話中,同時(shí)也放大了那些更傳統(tǒng)的對話者的聲音,尤其是民權(quán)活動(dòng)家和婦女的聲音。在越戰(zhàn)、反主流文化運(yùn)動(dòng)走向衰落,以及水門事件真相曝光的大背景下,60年代的興奮感漸漸消失,或者說消退,一直在推動(dòng)這個(gè)時(shí)展,卻又被淹沒在當(dāng)時(shí)眾多聲音之中的一些力量終于開始被注意到。
美國的婦女運(yùn)動(dòng)就是一個(gè)恰當(dāng)?shù)睦印km然1920年頒布的第十九修正案保障了女性的選舉權(quán),二戰(zhàn)以來女性的就業(yè)率也有所提高,但到60年代時(shí),美國企業(yè)和政府部門里很少有女性位居高位。種種跡象也表明,這種情況并不會(huì)向好的方向發(fā)展。1961年,國會(huì)里還有20名女性成員,到了1969年,只剩下11位。對于大多數(shù)女性而言,她們生活的重心還是家庭。在60年代早期,很少會(huì)有女性自稱是女權(quán)主義者。在反戰(zhàn)運(yùn)動(dòng)中,女性通常也是有意識(shí)地以女性,而不是例如非裔美國人之類的身份來定位自己,這和上一代女性活動(dòng)家的做法極為相似,那些人對于奴隸制或者19世紀(jì)晚期的種族劃分的反對事實(shí)上基于這樣一種綱領(lǐng):女性是家庭的道德核心,因而也是國家的道德核心。
1963年,貝蒂 弗里丹(Betty Friedan)出版了《女性的奧秘》(The Feminine Mystique),關(guān)于女性在社會(huì)地位的論辯隨之達(dá)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同年,美國通過《同酬法案》,并且建立了均等就業(yè)機(jī)會(huì)委員會(huì),徹底改變了女性的就業(yè)狀況以及雇主對待女性雇員的態(tài)度。1966年,全國婦女組織(NOW)成立,在弗里丹的領(lǐng)導(dǎo)下,借鑒民權(quán)活動(dòng)家的手段與修辭,呼吁實(shí)現(xiàn)美國婦女在所有方面的平等。從這種意義上而言,性別與種族在平等問題上常常相輔相成。但在其他問題上,兩者也是會(huì)有分歧的。
60年代中期,針對市中心區(qū)非裔美國人貧困率居高不下的問題,社會(huì)學(xué)家丹尼爾 帕特里克 莫伊尼漢(Daniel Patrick Moynihan)寫了名為《黑人家庭:需要國家為之采取行動(dòng)》的報(bào)告(The Negro Family: The Case for National Action,也稱“莫伊尼漢報(bào)告”)。這份報(bào)告出版后遭到了很多批評,批評者認(rèn)為這份報(bào)告試圖將白人中產(chǎn)階級的規(guī)范強(qiáng)加于黑人家庭,尤其是黑人單親媽媽之上。在如今的美國社會(huì)中,這種辯論仍未平息,許多保守派主張?jiān)俅螐?qiáng)調(diào)由夫妻及其子女組成的核心家庭的重要性,這不一定會(huì)解決所有的社會(huì)弊病,但對于這些核心家庭中的女性卻有著很大的影響。和現(xiàn)在一樣,當(dāng)時(shí)的辯論偶爾也會(huì)跨越膚色和性別的界限,但有時(shí)卻只是在兩者之間的真空地帶徒勞地呼喊。事實(shí)上,在女性權(quán)利的問題上,爭議是常態(tài),這一方面是因?yàn)閱螁瓮ㄟ^一份憲法修正案并不能維護(hù)的平等權(quán)利,另一方面是因?yàn)檫@些得到維護(hù)的權(quán)利本身也正在被割裂開來。
1967年,全國婦女組織在婦女權(quán)利領(lǐng)域推動(dòng)了兩方面的重大進(jìn)展:平等權(quán)利修正案(ERA)和墮胎權(quán)。前者在20年代就曾被提出過。兩個(gè)議程的實(shí)現(xiàn)似乎都勢在必得。國會(huì)將平等權(quán)利修正案下發(fā)給各州,滿心期待批準(zhǔn)州達(dá)到3/4的低數(shù)量,這項(xiàng)修正案就可以被通過。到1973年時(shí),這項(xiàng)修正案已經(jīng)得到了36個(gè)州的批準(zhǔn)。國會(huì)信心十足地認(rèn)為這項(xiàng)修正案一定會(huì)通過。沒想到的是,修正案最終卻沒能通過,而其原因竟是來自婦女的反對。菲利斯 施拉夫利(Phyllis Schlafly)領(lǐng)導(dǎo)的草根運(yùn)動(dòng)建立了停止平等權(quán)利修正案全國委員會(huì),指出支持平等權(quán)利修正案的人都是反家庭的,這一立場也獲得了其他一些像“母親們在前進(jìn)”這些聽起來有些可怕的團(tuán)體的支持。然而,國會(huì)仍然熱衷于推動(dòng)平等權(quán)利修正案的通過,甚至于將批準(zhǔn)法案的截止時(shí)間推遲到了1982年。盡管如此,1977年之后,已經(jīng)沒有哪個(gè)州會(huì)去碰這個(gè)修正案,更不用說批準(zhǔn)了。
與之相反,在一樁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較高法院裁決案“羅伊訴韋德”案(1973年)中,墮胎權(quán)得到了承認(rèn)。但這項(xiàng)權(quán)利也曾并且繼續(xù)遭到直接的質(zhì)疑(見圖67)。就在墮胎權(quán)得到通過的同一年,生命權(quán)利全國委員會(huì)也宣告成立。1989年,在“韋伯斯特訴生育健康中心”案中,較高法院判決認(rèn)可了密蘇里的一項(xiàng)
蘇珊-瑪麗 格蘭特的美國歷史新述為我們這個(gè)動(dòng)蕩時(shí)代提供了一個(gè)典范文本。該書提綱挈領(lǐng)地闡釋了美國民族認(rèn)同中的尚武根源,字里行間充滿了洞見,信息量極為豐富,且不乏尖銳的批判。對于美國如何走上當(dāng)今世界霸主之位感興趣的人都應(yīng)當(dāng)閱讀此書。
——羅伯特 庫克,薩塞克斯大學(xué)
蘇珊-瑪麗 格蘭特的這本書文筆優(yōu)美凝練,內(nèi)容通俗易懂,視角新穎獨(dú)特,對于美國國家觀念的形成與維系有著敏銳的洞察。本書呈現(xiàn)了美國的民族認(rèn)同如何在殖民時(shí)期以來的戰(zhàn)爭與沖突之中得到塑造與重新定義,以及民族韌性又是如何在公民理想與現(xiàn)實(shí)的差距之中保持著非凡的堅(jiān)韌。對于普通讀者來說,《劍橋美國史》無疑是一本了解美國歷史的典范讀本;對于專家學(xué)者而言,作者筆下舉重若輕、揮灑自如的真知灼見,也同樣值得研讀。
——理查德 卡沃丁教授,牛津大學(xué)基督圣體學(xué)院
做活動(dòng)買下的喜歡的,
別具一格。
書不錯(cuò),最近一個(gè)月買了3批書,但包裝就呵呵了,每一次都破破爛爛,用個(gè)好點(diǎn)的箱子不行啊!看到自己想要的書折了角損壞了包裝封皮郁悶啊。不過也有好處,每次快遞都不送到家,因?yàn)榘b與眾不同,自提的時(shí)候真的好找。
最近突然對歐美國家的歷史感興趣了,于是買下一本來讀,劍橋編寫的書,品質(zhì)應(yīng)該不錯(cuò)
這套劍橋小史有外語社出版的英文版,只是市面上比較少。可以互相對照著看,不過英文的讀起來更好一些,翻譯的也還是可以的。
 準(zhǔn)備收齊一套~
準(zhǔn)備收齊一套~
非常不錯(cuò)的包裝
品質(zhì)高超!忘記密碼是什么樣子都
很好很好很好
品質(zhì)很好 可讀的很強(qiáng) 內(nèi)容豐富
在當(dāng)當(dāng)買書,省錢又快捷!
好書好書好書
 買給娃兒看
買給娃兒看
經(jīng)典歷史書籍,版式開本都很不錯(cuò),當(dāng)當(dāng)活動(dòng)實(shí)惠,感謝好書好當(dāng)當(dāng)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很不錯(cuò),還沒開始看
真的很不錯(cuò)
紙張和印刷質(zhì)量都不錯(cu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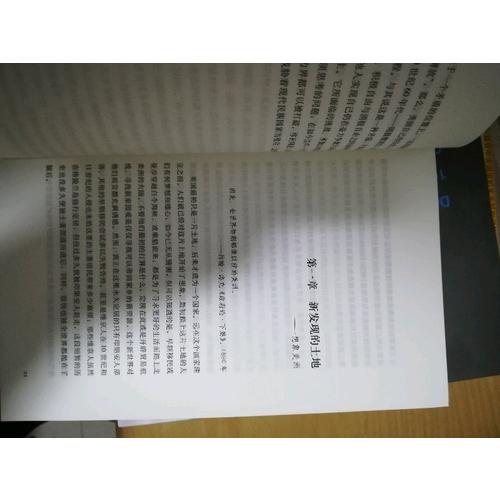 對這套書早就仰慕已久,這次雙十一以非常便宜的價(jià)格拿下,一定要好好拜讀!
對這套書早就仰慕已久,這次雙十一以非常便宜的價(jià)格拿下,一定要好好拜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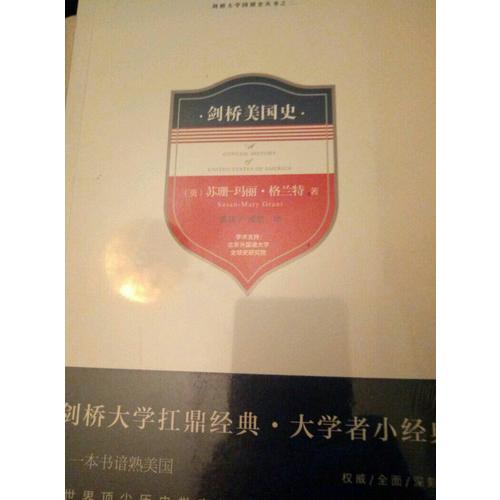 經(jīng)典歷史書籍,版式開本都很不錯(cuò),當(dāng)當(dāng)活動(dòng)實(shí)惠,感謝好書好當(dāng)當(dāng)
經(jīng)典歷史書籍,版式開本都很不錯(cuò),當(dāng)當(dāng)活動(dòng)實(shí)惠,感謝好書好當(dāng)當(dā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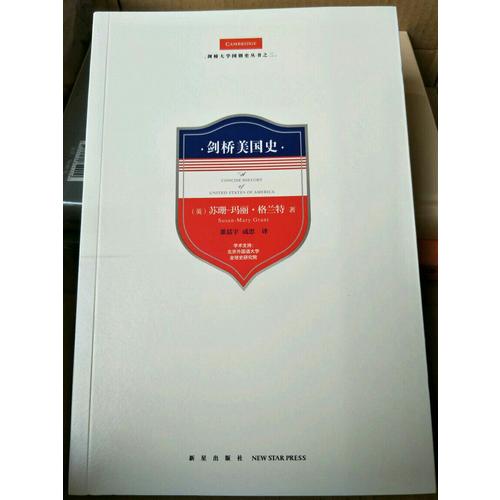 美國史汗牛充棟,能已劍橋命名的應(yīng)該有所期待。快遞給力,昨天下單,今天就到了。
美國史汗牛充棟,能已劍橋命名的應(yīng)該有所期待。快遞給力,昨天下單,今天就到了。
關(guān)于美國,此書可值一讀。讓人多了解這個(gè)超級大國的歷史!